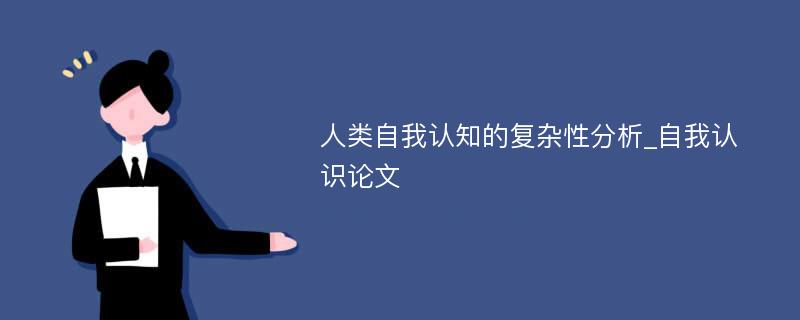
人类自我认识复杂性之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人类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人类对自身存在认识的历程,会发现极为复杂的诸种不一致:古人与今人不一致,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致,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不一致,同一时期同一共同体中不同个体的认识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等等。譬如,在人的本性问题上,就存在着诸多二律背反,即是说,只要有一种人性论,就一定会发现有另一种与之相悖的人性论。一种人说人性是善的,另一种人则说人性是恶的;一种人说人性是理性的,另一种人则认为人性是非理性的;此外,还有人的本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能动性和被动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等等的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的认识现象呢?是否象康德所说的纯粹由人对人自身存在的主观立法所致,或如现代建构论者所说的由人们的主观建构作用所致,以及如现象学所讲的由人的主观意向性结构造成,如宗教家所说的由上帝对人的启示引起,如黑格尔所讲的由绝对理念的本性(即必然要从自在发展到自为,最终能够自我认识自我)所致?都不是。
当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来观照人的自我认识的复杂现象时,就豁然开朗了。原来,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的意识都是人们自身存在的现实的反映。人之所以对人的理解相去甚远,首先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相差很大;人之所以对人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也首先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不停地变化。一句话,人的自我意识的不同根源于人的存在之别和之变中。别的本质也是变,所以,一切应于此“变”字。对于人之变的现象,人们早已意识到了。斯芬克斯之谜寓言中所蕴含的就是人之变的朦胧意识;大舜之“道心惟微”的“真传”中所意指的那个“微”字,实质上也是“变”字。因为人心总是变动不居的,所以才会使人感到微妙神奇,难以把握,难以使人合道。后来的思想家们则更自觉地来研究人之变的根源了,但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并无揭示出人之变的谜底。真正揭开此谜底的人是马克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所谓“历史之谜”,而且揭开了人的存在发展演变的“斯芬克斯之谜”。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会不停地变化,并非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推动,乃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不断变化,由此推动了人之存在的不断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社会实践在人之变动中的作用,我们就找到了理解人之变的钥匙,并且扬弃了以往抽象的人之变思想,把人之存在真正地理解为一个辩证过程。不仅把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过程,把人身上的社会因素的增多理解为一个过程,还把人的外在存在方式即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复杂化理解为一个过程,从而就可以把人之存在形象地理解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株永远生长着的没有定型、没有完结的生命之树,一座永在建造中的永不封顶的大厦。正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是变化日新的,因此,人们对之认识才会复杂多样、变化日新。可是,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思想家不懂得此道理,虽然也看到了人之变化现象,但总体上又执着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看不到人之存在的历史的辩证的性质,所以也就不理解人的自我认识之复杂性的根源。
其次,人之自我认识复杂性不仅与人的现实存在本身之变动有关,而且与人们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有关。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远古人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所以他们常常考虑的就是人的自然存在及其与万物的关系问题;到了苏格拉底和孔子之时,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化起来,所以人们便把眼光转向了人的伦理存在方面,整个中世纪可以说都是以人的伦理存在问题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打倒神权和君权制度,把等级专制下的伦理的人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自由的人。所以,与此相应,每一时代人们对人的规定或解答都不同,远古人们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产物;中世纪把人理解为善的存在物;近代则把人看作自由的存在物。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那样:“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究其原因,乃是由每一时代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马克思还形象地把人们的历史比作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剧,其中,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作为“剧中人”,他要在前人创造的历史舞台上活动;作为“剧作者”,他又要继续创造历史、创造自我的角色。因此,人就只能在自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提出并回答问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极深刻的,不仅使我们理解了人类自我意识的特殊性,还使我们理解了个体自我意识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个人都确实是社会舞台上的一种或几种角色,因而,人的自我认识也就只能是从自身的角色方面去发问、去回答。这便是人的自我认识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所在。
其三,人之自我认识的复杂性还跟人们具体实践活动的复杂性有关。人的任何实践活动本身都是一种程序,其间有着严密的客观的内在逻辑,即实践逻辑。实践逻辑的特点是非常严密和精确,若无此严密性和精确性,人的实践活动就不能连续进行。实践活动若能正常进行,人们也就不会提出什么问题;一旦实践活动不能照常进行时,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任何问题的提出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首先是由客观实践活动所“碰到”和“发现”的。可见,实践活动进展到何种程度,问题就提到何种程度,相应地问题的解决就到何种程度。人的自我认识也是如此。人们决不会在随便什么时候提出人的存在问题来,而只是在遇到人生实践困难时或遇到人之存在发展的新关头时才会提出。从人类自我认识的历程上看,人的存在问题的大讨论多发生在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如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苏格拉底和孔子时期(即古典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公元15世纪左右的文艺复兴时期(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向发达资本主义转变时期)。从我国近现代情况看,人的存在问题的大讨论发生在“五·四”时期和近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就个人来看,情形也是如此,一个顽童不会提出人的存在问题,一个老于世故者也无须讨论此问题。只有刚涉世而又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才最易提出并探讨此问题;一个尚未意识到人类命运的人不会提出普遍的人之存在问题,只有那以人类命运为自己命运者才会提出并深入探讨此问题。而且,还须注意,虽然人们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能相似,但其内蕴可能是很不同的,比如同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在18世纪的哲学家那里和在今天的哲学家这里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同样,在青年人和老年人那里所意指的东西大不相同,就是因为人们的具体活动不同,人生实践所深入的程度不在同一层次。
其四,人之自我认识的差异与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密切联系。人也是一种存在物。所以,对其认识的深广度是与人们对一般存在物认识的深广度相一致的。在人们对一般事物认识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人的存在的认识水平也必然较低;反之亦然。儿童和童年人类对人的认识只能是外表的、直接的,只有成人和现代人类对人的认识,才能深入到其内在本质及其外化方式中,从而全面把握其存在整体。
正是由于人的现实存在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具体实践问题在不断更新,人们的认识能力在不断深化,人们的自我认识才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状态来,呈现为一种特殊的认识长河,只要人类存在,人的自我认识现象就永远不会完结。
人的自我认识变化的因素或许还有许多,但以上四因素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由此我们便可大致窥见到人类自我认识长河中的一些规律性东西。
第一,人的自我认识历程中存在着诸种圆圈。最大的圆圈就是人之自我认识的三种形态。它们分别是人的自我认识的直观领悟阶段、理性抽象阶段和理性具体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具有感性具体的性质。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与人的认识能力低下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认识的意向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方面却在于人的现实存在本身只具有简单的、多是自然方面因素的性质。强调这后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这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自我认识的真面目。人不同于物,就在于人是不断由简单到复杂变化着的;物虽也变化,但与人之变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人的认识不能等同于对物的认识。当我们认识能力提高的时候,我们无疑可以在物中看到物之为物的更多的东西;但无论我们的认识能力有多高,也不可能在一个原始人或婴儿身上看到其人之为人的更多的东西,原因在于其现实存在中包括的人的即社会文化的因素太少。以往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常常只从人的主体方面去理解古代人的自我认识的浮浅性,而不知从人的客体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虽然直观到了人的客体,但并不了解它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客体。所以,到头来也不得不用主观的理性能力去理解古代人自我认识的表面性。
在第二阶段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具有反思抽象的性质。从主体方面看,此种认识已属对人的理性认识,是力图对人的存在作抽象规定的思维过程。从客体方面看,此种认识已深入到人的现象背后,是力图把握人之为人的那些性质的意识活动。之所以会这样,固然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意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时人的现实存在本身所具有的人之为人的东西,多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即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复杂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以至于不认识和解决的人就不能安身立命,就不可维持社会稳定,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存。于是,对人的类本质作反思才成为迫切需要,同时也成为现实的可能。
人的自我意识的第三阶段,是对人的理性具体性认识。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对人的存在的辩证思考,因而能够在人的意识中再现客体的人的现实的全貌。此种思考方式是由马克思开创的。这当然与19世纪以后科学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的认识能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要求解放、个体要求独立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出现了,即人的本质力量充分体现出来,人的对象性活动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普遍的人类性即全球性,人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真正的世界性人类社会的关系。然而,人的此种现实的存在方式却是在私有制的束缚下展开的。所以,不正确认识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不认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具体特质,就不能使劳动者从私有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甚至也不能使剥削者从其偏见中解放出来,也就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进一步发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此种历史事实的存在,使得对人的具体存在方式的认识成为必要和可能。
当我们进一步反思时,会发现人的自我认识的三种形态中还分别有着许多小的圆圈。不论大圆圈还是小圆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的自我认识都常常是从人本身开始,然后到人之外化活动中去找人,最后又回到对人本身的认识,亦即对人的直接性认识,到间接性认识,再到综合性认识。每一次循环又都使人的自我认识深化了一步。
第二,人的自我认识历程是人的现实存在本身矛盾发展过程的意识表现。
人的现实存在本身中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矛盾就是人自身内部的身心矛盾。所以,人们较早认识到的人之矛盾就是身心矛盾。在苏格拉底之前人们广泛讨论的人的问题就是身心问题,或灵与肉的矛盾问题;中国在那时则表现为人心与道心的矛盾问题。自然论者常常把人归结为肉体存在,以为人的本性在于肉体的生命活动中,以为快乐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心灵论者则以为人之为人在于有良心、善性。中世纪关于人的魔鬼性与天使性的争论,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关于人之自然性与理性的争论以及本世纪的关于非理性与理性的讨论,均可看作是远古关于人之身心关系思考的深化。人自身的身心矛盾也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起初主要是自然的欲望与满足和控制此种欲望的精神之间的矛盾,但随着人的社会化,人的欲望变成了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对其满足和控制的精神力量也就具有了多种意义。人自身的发展就是在这两种势力的矛盾作用中进行的。有时内在的非理性欲望占主导地位,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时理性占统治地位,对人的稳定生存起着重要的维持和协调作用。所以,反映在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中,有时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有时理性主义又占统治地位。人的自我认识的发展就总是在这两种思想的对立统一中不断深化,宏观上便显出认识运动的圆圈性来。
因此,从本质上讲,人的身心矛盾又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因为不仅人的身心矛盾的形成是在社会中进行的,无社会便无人的真正的精神,至多只能有高等动物的心理;而且人的身心矛盾的内容也是社会的内容,因为人的内在的身心矛盾在现实中,就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我和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之间的矛盾。所谓“良心”、“人心”等等,实际上都是人作为人的那种理性,即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应具有的社会理性。倘若一个人不在社会中生活,那也就无所谓良心、人心可言了,本质上也就无人之为人的身心矛盾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有时人的个体性占主导,有时社会性占上风。反映在人学思想中,有时个人自由被强调,有时社会理性被强调。人的自我认识也总是在此种矛盾中不断发展的。这也是人的自我认识具有发展的圆圈性的原因。
总之,人的自我认识是极其复杂的,要彻底澄清其根源和规律性需要专门研究,我们只能在此对之作以上简单剖析,理清其发展的基本原因和某些规律性东西,为理解和发展前人的思想找到基本的“可靠”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