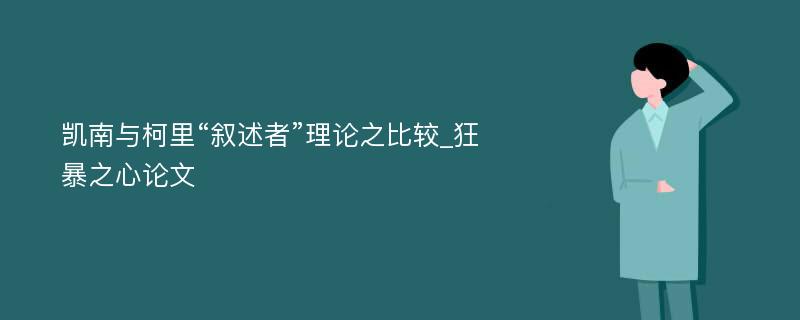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和论文,叙述者论文,理论论文,柯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6)06—0715—03
对叙事者的研究,从传统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学有了根本的转变。国外众多论著中有关叙事者的阐释为数不少,且各有千秋。本文拟比较两部较典型的著作对叙事者的论述,即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与英国学者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叙事者的论述,以观照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凯南: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具有不同层次
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的叙述者理论具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特点。她在《叙事虚构作品》第七章“叙述:层次与声音”中专门讨论了“叙述交际场合的参与者”。凯南从布斯的叙述观点出发,围绕叙述和故事的关系,探讨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认为隐含的作者是基于作品本文的构想物;隐含的作者和隐含的读者应排除在交际场合的描述之外;同时应该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为必要的构成要素纳入叙述交流过程。进而,凯南在叙述和故事关系的基础上,对叙述者进行了分类。凯南在书中这样指出:当查特曼1978年试图用符号学交际模式说明布斯(1961年)的叙述观点时,他提出了如下图表,即真实作者—隐含的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隐含的读者—真实读者。这个图表里列出的六个参与者当中,有两个被置于叙述交际范围之外,亦即真实作者和与其相对应的真实读者。在作品文本里,他们是由布斯和其他许多人称为“隐含的作者”和“隐含的读者”的替代者来“代表”的。布斯所说的“隐含的作者”并不只是文本的一个姿态,而似乎是人格化的实体,常被叫做“作者的第二自我”。按照这个看法,隐含的作者是在作品整体里起支配作用的意识,也是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标准的根源。他和真实作者的关系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心理复杂性,但是除了布斯曾提出过隐含的作者在智力上和道德标准上常远远高于真实作者实际本人之外,这种复杂的心理关系还没被分析过。不论怎样,已有人提出真实作者和隐含的作者不必要、事实上也往往不是同一个人。凯南进而指出,隐含的作者既区别于真实作者,也不同于叙述者。在论证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区别时,凯南以查特曼的解释为例,说查特曼似乎作了明确的符号学的解释:“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不同,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进行交流的工具。它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依靠它为了让我们理解而选用的一切手段,无声地指导着我们。”由此出发,凯南认为叙述者只能靠循环论证的方式被界说为文本的叙述“声音”或“讲话人”,而隐含的作者,相对于叙述者,按照定义应该是没有声音的、不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隐含的作者应该被看作是作者从文本的全部成分中综合推断出来的构想。这样,把隐含的作者看作是基于作品文本的构想物比把它看作是人格化的“意识”或“第二自我”似乎要可靠得多。
此外,凯南认为隐含的读者和隐含的作者一样,也是一个构想物,它也和真实读者和被叙述者不同。她说,在查特曼看来,每篇作品文本都有一个隐含的作者和隐含的读者,但是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却是可以取舍的。当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都存在时,交流就从隐含的作者开始,然后传到叙述者,再传到被叙述者,最后传到隐含的读者。假如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都不存在,交流就局限于隐含的作者和隐含的读者之间了。不过,凯南认为,她在查特曼的模式里发现了问题,即如果隐含的作者只是一个构想物,如果他的特性是“没有声音,没有直接进行交流的工具”,那么让他在交际场合担任信息发出者的角色似乎就矛盾了。然而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隐含的作者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也不是否认这个概念在分析或者仅仅理解叙事虚构作品时的作用。相反,凯南认为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凯南的主张是,如果要始终坚持把隐含的作者和真实作者、叙述者区别开,就必须把隐含的作者的概念非人格化,最好是把隐含的作者作为一整套隐含于作品中的规范,而不是讲话人或声音(即主体)。照此推论,隐含的作者不可能是叙述交际场合的真正参与者。
凯南在提出应该把隐含的作者和读者排除在交际场合的描述之外后,进而提出应该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为必要的构成要素纳入叙述交流过程。凯南说,她对查特曼的模式的另一个不同看法是对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处理方式,故她建议应该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为必要的构成要素,而不作为可以取舍的成分纳入叙述交流过程。因此,她不能接受查特曼关于“正如叙述者是可有可无的,被叙者也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看法。和查特曼不同,凯南给叙述者下的最简单的定义是至少在进行叙述,或为满足叙述的某些需要而进行活动的那个媒介。对于被叙述者,凯南认为情况也一样。被叙述者至少是本文中隐含的叙述者的叙述对象。因此,凯南认为,在查特曼的六个参与者里,和他的叙述观点有关的只有四个:真实作者、真实读者,叙述者、被叙述者。并且,凯南还指出:“和叙事虚构作品的诗学理论关系更为密切的并不是作者和读者的实际交流过程,而是文本与之相对立的叙述者和被叙述者的交流。”由此出发,凯南探讨了叙述与故事的关系,并对叙述者进行了分类。她认为叙述者所属的叙述层次,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叙述者的作用被感知的程度,以及叙述者的可靠性,都是决定读者如何理解故事,对故事采取何种态度的关键因素。因此,叙述者的类别也是按这些标准来划分的。这些标准并不相互排斥,还允许不同类别交叉结合。
在论述叙述层次时,凯南引用热奈特的观点,认为一个可以看作是处在他所叙述的故事“上面”或高于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和他所属的那个叙述层次一样,是“超故事的”。此外,如果叙述者同时又是超故事叙述者所讲的第一叙述故事里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叙述者就是第二等级的,即故事内叙述者。凯南进而说明了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她认为超故事和故事内的叙述都可能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出现或不出现。不参与故事的叙述者叫作“异故事的”,参与故事的叙述者,至少就他的“自我”的某些表现,是“同故事的”。由于参与故事的程度不同,对叙述者的可感知度也不同。
二、柯里:叙事者是控制者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的叙事者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色,他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在该书的第一章“身份的制造”中,柯里从“个人身份”入手讨论了这一问题。从个人身份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的论点出发,柯里提出了叙述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从小说叙事中造成读者的幻觉来展开。柯里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既定的道德人格。作为个体,在读完小说之后,我们的道德价值会与人物的道德价值遭遇,从而引起反应并进行判断。这部分地因为小说叙事中的所指幻觉,使我们对小说人物做出了对真实人物一样的推理。柯里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叙事学在理解对这种反应及推理的技术控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亦即揭示出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由叙事修辞所制造的”。为此,柯里对叙事学的“视点”展开了分析。“视点”(point of view)一词有一种潜在的误导作用,暗示着有关某一话题所持的观点或立场。将该词的叙事学上的意义理解成某种视觉隐喻会更准确,也就是说,在叙事中有一个点,叙述者似乎真的从视觉上由这个点去观察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就像拍电影时的摄影机一样,叙事声音可四处移动,从一个视角转向其他视角,常于不知不觉中由外观而转为内视。源于叙事视角分析的术语,很多是视觉隐喻,如叙事距离、聚焦等概念。但在阅读中唯一的真实视觉就是印刷出来的词语引起的视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才是隐喻。话语叙事中的视觉比电影中的视觉更明显地是一种幻觉,“在话语叙事中我们看到的虚构世界要比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更加虚幻”。
柯里认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伟大胜利之一是对视角的分析。视角分析的力量部分地来自具有分析力的术语的力量。这些术语描写了叙述声音的微妙变化、出入他人大脑的运动或表现人物话语和思想的各种方式。但对视角的分析不只具有描写力,它是在小说修辞中的一种新探索,小说可以为了某种道德目的给我们定位,驾驭我们的同情,拨动我们的心弦。“最为重要的是,对视角的分析使批评家们意识到,对人物的同情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在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它是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叙事学的开端,似乎要向人们宣称,故事能以人们从前不懂的方式控制我们,以制造我们的道德人格”。柯里由此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对小说中的视角的分析是对作者控制的揭示。”他赞同韦恩·布斯的看法:小说技巧是与读者交流的艺术,说布斯的著作是对小说中说服艺术的分析。
叙事视角的技巧是怎样控制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呢?柯里就此进一步展开了论述。他认为这个问题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情一些人而不同情另一些人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对于有关同情的两种观点,柯里这样分析:它们既适合于叙事又适合于实际生活。(1)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2)当我们发现一些人由于不能像我们一样进入某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或者错误的判断时,我们就会对这些被误解的人物产生同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亲密交往或奥普拉·温弗里式的向被访者直接提问而获得这种信息。“而在小说中,这种信息通过叙述者而获得。信息既可以源于叙述者的可靠叙述,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获得”。在有关同情的问题上的一些特殊情况,柯里也有深入的剖析,并注意到对以上两种观点存在着反对意见:如果我们所进入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病态的心灵,或是一种扭曲的动机,或是一种邪性之类的东西,它与我们已有的道德价值相违背,其结果就不会是同情。然而,很多当代小说正是通过对道德上令人生厌的人物表示同情而引起对作品的道德之争的。
除了从阅读心理上分析同情反应外,柯里还从信息流量、信息来源以及信息表达方式的精心控制分析叙述者是怎样“掌握着读者的判断”的。为了说明视角在判断控制中的作用,他总结了布斯对简·奥斯汀《爱玛》为一个并不可爱的女主人公引发同情的方法的分析。爱玛并不能自动地引起读者的同情。她不大方,没有自知之明,领悟力也不强。柯里认为,布斯是把这个事实作为艺术家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开始他的分析的,小说《爱玛》在控制与人物的距离远近方面有着绝妙的变化,简·奥斯汀通过将爱玛作为一种叙述者的方法拉近了我们同爱玛的距离。并且,内视点可以创造一种不受中介的阻碍而直接接近爱玛的幻觉,因而对她性格的评价显得直接而不受任何控制。就算读者在她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内视点也创造了对爱玛的同情。但是,柯里虽然提出叙述者是控制者的观点,但他坚决反对控制者成为说教者。他说:“作者从来就不应说教。即使是在有明显道德或哲理目的的故事中,也永远不应露骨地说教。”
柯里还分析了“各种不同的距离”。他说,在《爱玛》中叙述声音因借奈特利先生之口说出判断式的评价而使自己与对爱玛的判断之间拉开了距离。叙述声音采用了反讽的口气,并常常滑向一个依稀可辨的人物的声音,因此创造了一种布斯称之为“同情的笑”的现象。叙述者转述一个孤立的想法,而不是通过爱玛的眼睛持续地进行聚焦。叙述者将一次对话或一种想法进行总结,而不将这些作为直接引语或内视角让我们直接进入。总之,我们作为读者,发现自己被叙述者所控;我们在视觉上和道德上的距离都被层层的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视角的微妙变化、被所给的或故意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了。
三、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之同异
从以上的比较来看,凯南和柯里都很重视布斯的理论,并且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同时,他们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展开论述了叙述和叙述者。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具有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自己的理论。这表明,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他们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方面。
但是,凯南和柯里理论有着显著的差异,隶属不同的叙事学流派。从时间上说,凯南的著作出版于1983年,柯里的著作出版于1999年。从内容上看,凯南的著作属于经典的或结构主义叙事理论,柯里的著作则属于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具体而言,凯南作为20世纪80年代虚构叙事理论学者,其著作是传统的、典型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正如她在书中说明的那样,“本书将要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叙事作品,即‘虚构叙事作品’,不论其形式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叙事诗”。凯南的论述是从布斯的叙述观点出发,围绕叙述和故事的关系,在探讨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基础上,认定隐含的作者是基于作品本文的构想物,隐含的作者应排除在交际场合的描述之外。另一方面,凯南认为应该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为必要的构成要素纳入叙述交流过程。在叙述和故事的关系的基础上,凯南对叙述者进行分类,认为叙述者所属的叙述层次,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叙述者的作用被感知的程度,以及叙述者的可靠性,都是决定读者如何理解故事,对故事采取何种态度的关键因素。与这种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不同,柯里的叙事学属于20世纪90年代末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这种叙事学不仅不再是以故事为中心,而且是对传统叙事学的挑战。柯里从当代叙事学转折的三大特征即多样化、解构主义和政治化出发,突出了叙述者的“身份的制造”,强调叙事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叙事视角的技巧是怎样控制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在对“叙述主体”的论述中,柯里这样写道:“当代叙事理论普遍地认定这样一个思想,即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我到现在一直在描述着的是一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叙事中的自我意识。”
由此可知,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看待;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这是他们有关叙事者观点的根本不同。
[收稿日期]2006—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