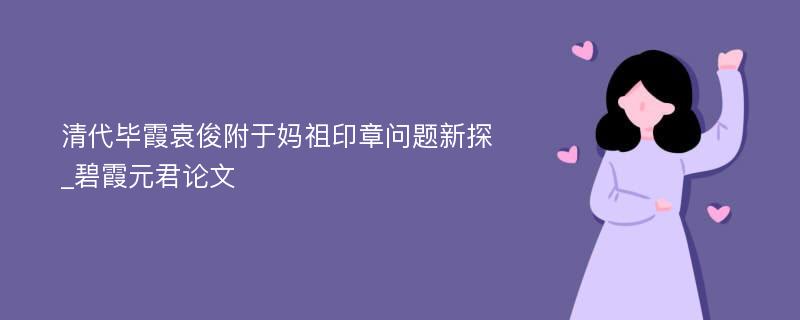
清代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妈祖论文,封号论文,清代论文,碧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清一代,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现象日渐普遍,从而形成了泰山女神与湄洲妈祖共享碧霞元君之名的格局。其源头在于康熙朝翰林院检讨汪楫在杭州见到的《天妃经》所谓崇祯帝曾封妈祖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和“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的传言。虽然清廷对妈祖的敕封不断累加,最终封号多达64字①,而且其中并无“碧霞元君”4字,但这没能改变汪楫传言引发的附会之风。 民国时期有人指出,“加天妃以青碧字,义意不协”②,并由此推论汪楫《使琉球杂录》关于崇祯帝敕封妈祖的说法有误。不过,其没有深究此说的来龙去脉。还有人认为,《使琉球杂录》与清《黟县志》所言妈祖曾被封为碧霞元君的主张均系“误会天妃为天仙”;所谓作为观音化身的海神天后与泰山女神均有“碧霞元君”之封号的说法“则歧之又歧”。③此论断亦未附相关的解析。 目前学界对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历史背景、原因与主要当事人等进行了多方探讨,澄清了其中某些疑问,但仍留下一些谜团悬而未决,比如明代是否对妈祖敕封过“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名号,将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做法是否系清初道士所为,该附会现象在清代流播的路径等等。④已有研究成果在史料分析上存在着误读、臆断的局限,从而使原本迷雾重重的二者混淆的历史更为复杂。 本文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明清官方、道教与地方儒生文士将碧霞元君和妈祖封号联系起来的路径及其相互关联,对照考察清代方志与碑刻资料的真伪及其矛盾,试图进一步澄清妈祖封号与碧霞元君纠缠的历程及其真相。 一、妈祖封号与汪楫的传言 以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明确将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文字记录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的汪楫《使琉球杂录》一书。在此书中,汪楫自言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经过杭州孩儿巷的天妃宫时得到了一函《天妃经》,该经书称崇祯帝曾于崇祯十三年封妈祖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后又加封“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⑤可惜汪楫所言的《天妃经》今不见传本,也难辨其真伪。今有学者据汪楫之言推论,《天妃经》所谓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说法,是清初杭州的道士为抬高妈祖在道教神灵谱系中的地位而进行的“炒作”之术。⑥其立论的前提是崇祯帝从未将妈祖敕封为碧霞元君。不过,道士“炒作”说目前尚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其前提的相关历史问题需要继续考探。 由于相关文献的匮乏,目前仍不能确定崇祯帝是否敕封过妈祖。据官方史料可知,明代朝廷对妈祖的敕封共有两次,一为明太祖于洪武五年(1372)封其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二是明成祖于永乐七年(1409)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此外,明末管绍宁《赐诚堂文集》称,弘光政权于崇祯十七年(1644)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安定慈惠天妃”⑦。以管绍宁晚年曾任礼部右侍郎的经历而言,该记载虽系孤证,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由此推测崇祯帝很可能没有敕封过妈祖。还有文献表明所谓妈祖的封号“天仙圣母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乃是崇祯帝对泰山女神的敕封。康熙《颜神镇志》云:“崇祯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敕谕另道经掌坛官梁之洪虔贡香、帛,前往东省泰山设醮,恭告行礼,加封群神:天仙圣母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⑧此说虽不能确认崇祯帝对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加封究竟增加了哪些字,但也从侧面表明“天仙圣母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与妈祖无关,因为朝廷不可能将同一个名号敕封给两位女神。要注意的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修(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记》碑云:“明兴,敬神恤民……历圣天子封神为‘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护国庇民碧霞元君’,敕赐庙额。”⑨该碑文表明,明代皇帝曾封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为“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护国庇民碧霞元君”。这一封号多达20字,在时间上早于康熙《颜神镇志》所载的相关封号。当然,《重修(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记》所言的碧霞元君封号,不见于明代官方记载,很可能借自明代道教《元始天尊说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与《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的相关说法。⑩从《赐诚堂文集》、康熙《颜神镇志》与《重修(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记》的记载看,崇祯帝敕封泰山女神之说还需要旁证的支持,也不能由此确证崇祯帝是否将“碧霞元君”名号敕封给妈祖。不过,迄今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撑《天妃经》关于崇祯帝敕封妈祖的记载。至少在崇祯朝之前,明廷不曾将女神封过“元君”,而且“元君”一词也不曾出现在明朝祀典的封号中。可以说,崇祯帝封妈祖为碧霞元君之说既缺乏证据,也不符合明代朝廷敕封女神的体制与惯例。再考虑到《赐诚堂文集》与康熙《颜神镇志》对崇祯帝敕封妈祖说的否定,《天妃经》的真实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康熙朝曾任礼部侍郎的纳兰揆叙虽然相信“明崇祯朝封天妃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之说,但因为明白“元君与天妃非一神”,因而质疑崇祯帝对妈祖的敕封“果何据乎”。(11)因此,《天妃经》关于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记载很可能是该经书编写者的杜撰。 汪楫所见《天妃经》的编写者未必是清初的道士。以当时写经、刻经的情况而言,印行《天妃经》这样一部经书非一人之力。若是杭州孩儿巷天妃宫道士的“炒作”结果,至少是该处道士们的集体行为。这是第一种可能的情况。不过,细推之,若他们确实有意“炒作”,自然会广为传播所谓《天妃经》,但据汪楫的观察,当时相距不过数公里的吴山天妃宫道士竟对此一无所知,颇令人费解。第二种可能是,《天妃经》系当时杭州民间信众私刻的经文,他们将此经文放到孩儿巷天妃宫,赠送给来此祈祷的香客。仅凭汪楫之言,难以断定是前述两种可能情况中的哪一种,抑或二者皆非。 当然,清代道士对于建构妈祖封号与碧霞元君的关联并未全然无关。他们已经看到,明代碧霞元君的地位远高于天妃妈祖,尤其是万历、崇祯两朝的皇室将碧霞元君当作生命的皈依之神,而视妈祖为其治下的俗世水神,不可皈依。况且明代道家确有借碧霞元君名号抬高其他神灵地位的做法。明艾南英《论宋天地合祭》一文就批评当时的道家妄祀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圣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后已”。(12)因此,为进一步神化妈祖,清初道士确有可能将妈祖与碧霞元君联系在一起。康熙三十九年(1700)问世的《历代神仙通鉴》一书称:“(妈祖)累封天妃,证位碧霞元君”(13)其将“碧霞元君”看成是道教修炼的一种等级或境界,而非泰山女神的专用名号,并认为妈祖只是修炼到这种等级或境界的一位女神而已。该书作者虽非道士,但这一说法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包括道士在内的清初时人以妈祖攀附碧霞元君的心理倾向。道光朝道士李西月编撰成书的《吕祖全书》认为,天妃妈祖由麻姑化身而成,“功德崇高,证位碧霞元君,历代敕封不可具述。”(14)这可以说是清代道士对妈祖享有“碧霞元君”封号的另一种解读,而“证位碧霞元君”一语当是延续了《历代神仙通鉴》对妈祖的说明。另外,清代福建的方志将该地女神临水夫人陈靖姑附会于“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15)。其背后有道教闾山派道士活动的身影。由此推测,清代道士确有可能参与将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信仰活动。 尽管《天妃经》所言崇祯帝敕封妈祖之事尚无确证,而且该经书也未必是清初道士所作,但汪楫却相信了《天妃经》之言,在对天妃进行介绍时称: 天妃,莆田林氏女也……明太祖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成祖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庄烈帝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皇清仍如永乐时封号。(16) 此说经过《使琉球杂录》一书的传播,深刻影响了后来出使琉球的官员。他们路经泰山时拜谒碧霞元君,以示对海神妈祖与泰山女神的双重尊重。康熙朝奉使琉球的徐葆光有“何代山巅祀碧霞,万里应同护客槎”的诗句,并自注称“海神天妃,亦有元君封号”。(17)乾隆朝李鼎元《使琉球记》云:“十一日癸亥,微雨,决意登岱,恭谒碧霞元君祠,以天后于明末时曾封‘碧霞元君’故。”(18)他们的这些观念与行为使妈祖与碧霞元君在神职和角色上更多地重叠在一起。 汪楫关于崇祯帝敕封妈祖的传言流传日广,一些官员与儒士信以为真,将其编人类书与方志。《古今图书集成》的《神异典》称:“愍帝崇祯□年封天妃为‘碧霞元君’。”(19)乾隆《江南通志》关于安庆府宿松县小孤山天妃庙的记载称:“明加封‘天妃圣母碧霞元君’,有司春秋致祭。”(20)乾嘉间孙星衍在《重修台州府松门山天后宫龙王堂碑记》称,明代天妃加封“碧霞元君”。(21)光绪《城北天后宫志》明确称,据汪楫《使琉球杂录》,“庄烈帝崇祯□年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又封‘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22)光绪《湄洲屿志略》称:“庄烈帝崇祯□年封‘天仙圣母清灵普化碧霞元君’。崇祯□年加封‘清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23)该志书将封号中的“青”字一律改为“清”字,还附注称“‘清灵’一作‘青贤’,疑误”(24)。经过这些类书、方志与碑刻信息的传播,后世更多的人相信汪楫的传言。 针对汪楫的传言,康熙朝的一些官员明确指出天妃妈祖的封号与碧霞元君无关。《古今图书集成》之《职方典》的编纂者认为碧霞元君是泰山女神的专称,与天妃无关。其对于天妃的解释称:“己丑加封‘弘仁普济护国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岁以为常。若淮上之祀起于宋,至明而崇奉显盛,第止宜称‘天妃’,而不察者谬加以‘碧霞元君’字号,此则泰山之神非漕运之灵济者矣。”(25)在他们看来,将碧霞元君加于天妃妈祖是“不察者”的谬举。乾隆朝有官员明确指出汪楫关于妈祖与碧霞元君之关系的误会。进士出身、曾任榆社知县的程穆衡注意到“俗以(碧霞)元君佐岳帝注生,故有圣母之号”(26),“其祠自泰山而北至燕蓟,南遍江淮”(27),这位女神与天妃妈祖迥然不同,因而明确指出“汪楫《使琉球杂录》则谬以元君为天妃矣”(28)。尽管当时不乏官员注意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但汪楫造成的二者混淆的迷雾却越来越浓。 二、妈祖“元君”化:民间、官方与儒士的多层次附会 汪楫关于妈祖被敕封碧霞元君的传言在后世广为流传,但其并非清代混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唯一路径。从康熙朝至宣统朝,朝野上下以不同的路径混淆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区别,其要者有三:一是普通民众沿袭了明代民间将妈祖与碧霞元君同视为天妃的信仰习俗;二是清帝和朝廷官员不经意间将二者合为一体;三是参与编修方志的地方官员与儒生文士直接或间接地延续了汪楫的传言,甚至进行无中生有的编造。这些路径的混淆现象与汪楫的传言并存互联,形成了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合唱曲。下面分别解析此三者。 其一,清代普通民众延续了明代混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信仰习俗,进而衍生出二者互相侵夺名号的新现象。(29) 乾隆朝以降,华北民间信众多有将妈祖与碧霞元君混同者。乾隆朝韩锡胙《元君记》称,到北方民间的“佞佛者”将海神天后与泰山玉女都看成是观世音的化身,而且二者都享有“碧霞元君”的封号。(30)此系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新解释。 在华北民间社会中,虽然将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传言影响深广,但还出现了以碧霞元君附会妈祖封号的特殊现象。晚清时期,天津天后宫的一些民间进香团体因曾被朝廷赏赐而号称“皇会”,其将“天后”名号看成是朝廷对碧霞元君的敕封,而且不把妈祖当作该地天后宫的主神。其中的门幡老会称天后宫主神为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其封号为“敕封护国庇民显神赞顺垂佑瀛埂天后圣母明著元君”(31),该封号是借用元、明、清三朝对妈祖的封号与赠匾以及碧霞元君的名号拼接而成,不见于他处。对于此封号,《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的绘制者代表他们宣称: 天津卫天后宫老娘娘真正灵应,天后二字别处没有,都写天仙圣母,有天妃圣母。别处不能写出天后圣母。别处娘娘庙神位没有赶上敕封,比方山东泰安山娘娘庙香火大,神位无赶上敕封,称为天妃圣母。到东顶娘娘庙神位,称为天仙圣母,无赶上敕封。西顶娘娘庙神位,称为天仙圣母,无赶上敕封……其实说起“天仙圣母娘娘”、“天妃圣母娘娘”、“天后圣母娘娘”神位,通常都是这一位娘娘。(32) 该绘制者列举的泰山娘娘庙、北京东顶娘娘庙、西顶娘娘庙等都是主祀碧霞元君的庙宇。他认为“天津卫天后宫老娘娘”是碧霞元君,而非妈祖,因为当时各地妈祖庙都供奉“天后”的神位。显然,这是夺取妈祖的“天后”名号,又将其安在碧霞元君的身上。尽管天津还有诸多信众和“皇会”传扬妈祖的神迹,但在该地的门幡老会等皇会看来,天后宫的主神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他们献媚邀福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位女神。若从晚清天津民众普遍信仰的王三奶奶与“四大门”角度看,碧霞元君对民众的影响更是远高于妈祖。可以说,天津天后宫是晚清时期华北碧霞元君信仰覆盖妈祖信仰的一个典型例证。即使在今天,河北某些地方的天妃庙仍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并不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 乾隆朝以降,华南民间社会中逐渐出现以妈祖为“天后元君”或“天后圣母元君”的信仰习俗,以广东一带最为显著。乾隆五十年(1785)立石的《新建川沙天后宫记》碑云,该宫供奉“天后圣母元君”。(33)此说未言“天后圣母元君”是朝廷封号,仅系广东地方信众对妈祖的一种尊称,其根源在于清初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现象。光绪元年《乙亥春月重建天后古庙碑记》云:“惟我油麻地一湾居民铺户,乐建天后元君古庙,供奉有年。”(34)光绪二年(1876)《天后古庙重修碑记》云:“原夫天后元君也,昭代功臣,护国著英声之誉。”(35)民国《重建天后圣母古庙碑记》云:“天后庙正座崇奉天后圣母元君,左奉关圣帝君、洪圣大王、康公真君,右奉财帛星君、鲁班先师、华佗先师。”(36)由上可见,广东一带自乾隆朝始,已广泛认可妈祖是“天后元君”或“天后圣母元君”,只是省去了“碧霞”二字。 清代民间信众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信仰习俗,源自明代妈祖与碧霞元君共享“天妃”名号的民间信仰传统。明人王权在《修天妃庙记》一文称,山东德州境内“泰山元君祠,恭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识之,而漫无所识别。”自嘉靖朝始,南方逐渐出现妈祖庙宇与碧霞元君祠庙互相替换,二者并称天妃祠或天妃庙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漕运工人大多信仰无为教,尤其崇拜被纳入民间宗教的碧霞元君,“天妃宫”亦因此多改成“碧霞行宫”与“泰山庙”。(37)在此情势下,碧霞元君在民间话语中也拥有了天妃的名号。马一龙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途径江苏淮安天妃庙,写了两首题为《入天妃庙侯升舟上洪呈同行诸君》的诗,诗云:“泰山曾入天妃庙,今日洪头又一过。喜得南风送北客,惊闻楚地能吴歌。”(38)可见,马一龙将泰山碧霞灵应宫视为天妃庙,相应将碧霞元君视为天妃,而其所言“今日洪头又一过”的天妃庙是指淮安清口的惠济祠。由此推之,当时“天妃”虽是明廷对于妈祖的封号,但民间也将其用于碧霞元君。民间视碧霞元君为天妃的习俗自运河流域不断向外延伸,江浙一带亦受其影响。嘉靖进士钱薇为其家乡浙江海盐天妃祠所写的《天妃歌》云:“峨峨庙貌天妃祠,问祠所自人罕知。尝闻青帝司东土,降主东岳安东陲。东岳行祠乃其故,不识何代称天妃。”(39)显然,这一原本作为东岳碧霞元君行宫的祠庙被当地民众视为奉祀妈祖的“天妃祠”。由于妈祖与碧霞元君共享“天妃”名号,明代民间信众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神,而且这一信仰习俗富有较强的生命力,至清代而不衰。 其二,康熙帝和一些朝廷官员未能明确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客观上为汪楫的传言提供了更多的存续空间。 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帝在《御制重修西顶碧霞元君庙碑》碑文称:“元君初号天妃,宋宣和间始著灵异。”(40)其将妈祖的事迹和封号加到了碧霞元君的身上。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对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关系也不清楚,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为北京丫髻山碧霞元君行宫所撰《丫髻山天仙庙碑记》一文中云:“元君者,西王母之第三女也,诞于四月十八日,此华山石池玉女洗盆之说也。或曰不然,乃湄州林都检之女,渡海云游,于宋宣和间以护佑路行人功,始有庙祀。历元明,累功封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徽号。”(41)张玉书列举了碧霞元君来历的两种说法,难以分辨孰是孰非。其中妈祖“累功封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一说,显然有汪楫关于妈祖被敕封为碧霞元君之说的影子。不过,除《丫髻山天仙庙碑记》外,尚未见妈祖被封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其他证据。 清人在妈祖附会碧霞元君的问题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国史馆纂修毛奇龄明确宣称,天妃本是碧霞元君的名号,但有人将妈祖附会为天妃。他在《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一文称:“神名天妃,旧传秦时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顷,出玉女于岱山之巅,至今祀之,所称神州老姆是也。时以地主阴,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为职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称莆田女子契玄典而为水神,此则后人所附会者。”(42)将“天妃”说成是碧霞元君的本有名号,当然不合乎事实。而将泰山玉女说成是管理河海的水神,并且认为有人将妈祖附会于这位水神的说法,不知有何根据。毛氏曾参纂《明史》,但在此碑记中没有提及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之事。虽后人曾注意到毛奇龄的这一说法,但其影响并不明显。 康熙帝与一些朝廷官员不能明确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差异,甚至将妈祖的事迹安于碧霞元君之身,或是指称有人将妈祖附会成原本为碧霞元君角色的水神。这些载于碑刻的说法无助于分清两位女神的身份与角色,反而促使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说法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其三,参与方志编纂的地方官员与儒生文士对汪楫的传言信以为真,还编造出乾隆帝与嘉庆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诸种谬说。 尽管康熙朝僧照乘刊印的《天妃显圣录》、乾隆朝林清标刊印的《敕封天后志》均不采信《天妃经》有关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说法,但后世诸多地方官员与儒生信以为真,将其编入方志。嘉庆《重刻江宁府志》称,位于南京水西门内的天后宫为“敕封天后圣母碧霞灵应元君庙”。(43)事实上,此宫是由乾隆朝在南京的福建籍仕商捐资而建,奉祀天后妈祖,与“碧霞灵应元君”毫无关系。该志的编纂者似没有亲见此处嘉庆十七年(1812)立石的“敕封天后圣母宫地府水西门内系福建仕商捐建”碑,只是依照传言编造了该天后宫的名字。 还有方志编纂者编造出乾隆帝与嘉庆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多种谬说。道光《重修蓬莱县志》称:“乾隆三年封‘护国佑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天后’。五十三年加封‘显神赞顺慈惠碧霞元君’。嘉庆五年加封‘垂慈笃佑天后圣母元君’。”(44)该县志所称乾隆帝、嘉庆帝加封妈祖为“碧霞元君”、“圣母元君”的说法不知所凭何据。光绪《湄洲屿志略》称:“乾隆五十三年加封‘显神赞顺灵惠碧霞元君’。”(45)这一封号与道光朝《重修蓬莱县志》的相关封号差一个字,前者有“灵”无“慈”,后者有“慈”无“灵”。光绪《浦江县志》则完全借用道光朝《重修蓬莱县志》的说法,也称:“(乾隆)五十三年加封‘显神赞顺慈惠碧霞元君’。嘉庆五年封‘垂慈笃佑天后圣母元君’。”(46)光绪《城北天后宫志》称:“乾隆二十二年加‘诚感咸孚显神赞顺’,敕封‘护国庇民明著妙灵昭应宏仁普济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天后圣母慈惠碧霞元君’。”(47)显然,这一记载在完整表述乾隆五十三年妈祖封号的基础上,又任意添加了“圣母慈惠碧霞元君”8字。有清一代,朝廷从未将“圣母”二字封过任何女神。 相对于清代而言,民国时期的一些方志在伪造妈祖的“碧霞元君”封号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海康县续志》在承袭道光《重修蓬莱县志》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又编造出“(嘉庆)七年敕封‘天后圣母无极元君’”(48)的新封号。 由上可见,清代民间的普通信众,康熙帝与一些朝廷官员,参与方志编纂的地方官员与儒生文士,分别在各自的文化层面混淆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身份与角色,从而使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现象出现了远比汪楫的相关传言更为复杂的局面。 三、惠济祠:妈祖“元君”化的特殊案例 清代汪楫关于妈祖封号的传言和朝野多层次的混淆、附会之说,使妈祖“元君”化成为一种层累的历史积淀现象。其中,淮安惠济祠并祀妈祖与碧霞元君两位女神的礼俗现象作为一个特殊案例,使前者封号附会后者的历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相。 清代江苏淮安清口的惠济祠自康熙朝开始并祀妈祖与碧霞元君。该祠原本是明正德朝道士袁洞明卜募款建筑的奉祀泰山碧霞元君的庙宇,俗称“奶奶庙”、“铁鼓祠”。嘉靖初年,章圣太后登临该祠,赐“黄香白金”,并将其名改为“惠济祠”。清初,康熙帝曾数次来到惠济祠观水势。为求河运平安,他谕令在该祠中增祀天妃妈祖,由此形成了一祠并祀南北两位女神的礼俗景象。当然,这一礼俗景象并非惠济祠所独有,早在明万历年间,天津天后宫就出现了此种现象。(49) 惠济祠并祀妈祖与碧霞元君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该地官民将这两位女神混为一体的多种误会。 其一,妈祖封号的误会。乾隆《大清一统志》在解说惠济祠的条文中称:“惠济寺,在清河县旧治东,旧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祀天妃。嘉靖初赐额惠济。本朝雍正二年重修,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50)这是首次出现的关于雍正帝敕封妈祖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的官方志书记载。 其实,雍正帝从未敕封妈祖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根据清代官方档案记载,雍正帝确实曾敕封妈祖为“天后”。这一敕封可以说是其在误信康熙帝敕封妈祖为天后之传言的追认。已有学者考证清楚,“不管真假如何,妈祖至晚在雍正三、四年已取得官方认定的敕封天后身份。”(51)这一身份与碧霞元君无关。乾隆十七年(1752)潘荣陛记载乾隆驾临惠济祠拈香情况的碑文云:“惠济祠即旧天妃庙,中有铁鼓,又名铁鼓寺,实为泰山圣母之行祠也,建自明正德三年。我世宗朝因时显庇河漕敕封天后”。(52)他明确指出,雍正帝只是追认性的敕封妈祖为天后,而不是“天后圣姥碧霞元君”。所谓雍正帝曾敕封妈祖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的说法,系《大清一统志》编纂者的伪造。记载江南河道总督衙署内天后宫祭祀典礼的《南河祀典》也称妈祖有碧霞元君封号。 后世淮安地方志书承袭了《大清一统志》关于雍正帝敕封妈祖的错误记载。乾隆《清河县志》记载:“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康熙中累封天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姥碧霞元君’。”(53)该县志将雍正帝敕封妈祖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的时间更改为雍正五年,不同于《大清一统志》的相关时间。在“惠济祠”条目的按语另外,该县志又称:“神姓林,福建莆田人,殁后显神于河海,护潜有灵,雍正五年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54)这是再次说明雍正帝敕封天后为碧霞元君的时间。此外,咸丰《清河县志》也称“(惠济祠)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姥碧霞元君’”。(55)这一县志还批评《南河祀典》的相关记载,称:“纂《祀典》者……不知(惠济祠)有始祀太山今祀天后之异,通合为一,致抵牾云尔。”(56)显然,将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观念在淮安地方流传甚广。直到光绪二年(1876),文彬、吴昆田等人注意到乾隆《清河县志》所载“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姥碧霞元君”一句存在歧义,认为前朝修志者“不知有始祀太山,今祀天后之异,通合为一,故致抵牾”。(57) 另外,有漕运官员编造出乾隆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说法。嘉庆朝漕运总督许兆椿称:“高宗纯皇帝特封为天后圣母碧霞元君,于清江浦勅建惠济祠,饰以黄瓦,亲洒辰翰,勒诸丰碑。”(58)许氏关于妈祖封号的说法与乾隆《大清一统志》一样,均为缺乏依据的杜撰之言,但前者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如后者。 其二,惠济祠别称“天妃庙”、“碧霞元君祠”造成的误会。 淮安惠济祠在嘉靖初年因章圣皇后赐额“惠济”而得其名,天启《淮安府志》称其为“天妃庙”。前已提及,马一龙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途径淮安惠济祠时写了两首题为《入天妃庙侯升舟上洪呈同行诸君》的诗,明确将该祠称为“天妃庙”。作为惠济祠的天妃庙主祀碧霞元君,但并不奉祀妈祖。其名“天妃”与妈祖无关,只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将碧霞元君视为天妃的观念。(59)顺治十年(1653),史学家谈迁沿运河北上途经清口,其《北游录·纪程》称惠济祠为“碧霞元君庙”(60)。这表明清初惠济祠仍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行宫。 康熙朝因增祀妈祖,而改惠济祠之名为“天妃庙”。此“天妃庙”中的“天妃”二字指妈祖。咸丰《清河县志》追记称:“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乾隆中复改称‘惠济祠’。”(61)以天启《淮安府志》而言,此说不确。由于明代文士俗称惠济祠的“天妃庙”之名与清康熙时官方改惠济祠而称的“天妃庙”之名完全相同,加之诸多文士将妈祖与碧霞元君皆视为天妃,康熙朝以降淮安地方儒生混淆二者的情况实非意外。康熙朝淮安地方文士汪之藻在为惠济祠写的《天妃庙赋》一文中自题注云:“庙在黄淮交汇处,俗人供天妃以镇压河流。中有铁鼓,又名铁鼓祠。”(62)其所言“俗人”在惠济祠供奉的“天妃”究竟是妈祖还是碧霞元君,已不可知。而淮安民间信众因为妈祖与碧霞元君在神职上的重叠与相似,更容易将二者当成一神。不过,惠济祠的名称在清代官方档案中并未全由天妃庙代替。康熙朝官方仍并用“天妃庙”与“惠济祠”称呼该庙。(63)康熙《清河县志》所附《清河县图》仍称该庙为惠济祠。另外,乾隆《淮安府志》所附《清河县图》上将此庙标注为“奶奶庙”。这一民间俗称反映出淮安信众在精神传统上更多地沿袭了对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信仰,而康熙朝在惠济祠中增祀的妈祖并不能超越碧霞元君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乾隆朝惠济祠又由天妃庙改回原名,但实际上仍是“碧霞元君祠”。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依照京师坛庙规格大规模重修过了惠济祠,并将康熙、雍正时所用的名称“天妃庙”改为原名“惠济祠”。扩建后的惠济祠建筑格局较为独特。该祠坐东北朝西南,分为左右中三路,共有六进院落。中路最为宽阔,最南端为牌坊,沿中轴线向西北依次是山门、仪门(二门)、正殿、篆香楼、三清阁与后罩殿。正殿奉祀天后妈祖,篆香楼供奉碧霞元君的坐像与卧像。在正殿的东西配殿与三清阁等处增祀多位神灵。在这次扩建中,乾隆帝无意以妈祖取代碧霞元君,而是充分尊重了该祠奉祀碧霞元君的传统,因而扩建后的惠济祠山门上仍书写“碧霞元君祠”五字。惠济祠扩建之后,该地官员也称该祠为“碧霞宫”。乾隆五十一年(1786),两江总督李世杰在向朝廷汇报淮安清江浦遭遇洪水情况的奏折中称当地的“碧霞宫本有两处”,其中一处就是“清口惠济祠”(64)。 乾隆帝扩建的惠济祠为何仍被人们普遍视为碧霞宫呢?这不仅与当时惠济祠并祀妈祖与碧霞元君有关,更在于惠济祠的山门上有金书“碧霞元君祠”五字。这一字样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时人张煦侯记录了惠济祠的景象称:“大殿之前有门,金书‘碧霞元君祠’五字。……正殿奉天后圣母像,相传为泰山之女,所谓碧霞元君也”(65)。正殿奉祀的天后圣母应是妈祖。张煦侯提到的天后圣母即“所谓碧霞元君”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人们将妈祖当成碧霞元君的习俗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形成,确实又与惠济祠山门所书“碧霞元君祠”密不可分。尽管乾隆五十三年(1788),惠济祠的妈祖祭祀被列入地方祀典,由翰林院撰拟祭文,地方官春秋二季致祭,但此举无助于消解妈祖与碧霞元君混淆的现象。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民国时期,来惠济祠的人们像张煦侯一样,看到的还是“碧霞元君祠”的名号,不自觉地会将惠济祠当成是明代以来流传已久的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行宫,仍称之为“奶奶庙”。 在民间多神信仰的文化传统中,淮安当地普通民众通常只是进庙上香,并不关心惠济祠中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区别,而此地先有的碧霞元君信仰绝非后来的妈祖信仰所能轻易超越。乾隆朝清河县有一座已经改祀妈祖的城隍庙也被视为“碧霞宫”。《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在注解清河县玉带河北的“碧霞宫”时,称该宫旧为城隍庙,乾隆中改祀天后之神,并加按语云:“碧霞元君太山之神,而俗以天后当之,亦为小误。”(66)显然,该县志的编纂者已意识到当时较为普遍的将妈祖当成碧霞元君的误会。此亦可见,在淮安地方信众的观念中,碧霞元君的信仰传统根深蒂固,几乎完全覆盖了后来的妈祖信仰。 嘉庆二十二年(1817),清廷在北京绮春园建造了一座惠济祠。不过,这座惠济祠与淮安惠济祠大不相同,仅仿造了后者奉祀妈祖的大殿,而没有所谓山门、后殿、篆香楼等建筑。很可能为弥补绮春园惠济祠的局限,嘉庆帝将京西妙峰山顶奉祀碧霞元君的灵感官改名为惠济祠。直至今日,该惠济祠的山门上仍嵌有嘉庆帝御笔“敕建惠济祠”的汉白玉石额。 四、结语 清代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历史进程十分复杂。其源头可视为汪楫《使琉球杂录》所言的《天妃经》,但该经书来历不清,也不能由此推论其与清初道士的关系。迄今未发现可以支撑《天妃经》提及的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之说的证据。已发现的否定此说的史料尚不足构成完整的具有排他性的证据链,因此,仍不能完全确证此说的真伪。自康熙朝以降,汪楫关于妈祖封号的传言影响深远,使妈祖元君化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传播。 在汪楫的传言之外,朝野上下还有不同层面的将妈祖与碧霞元君两位女神混淆、比附的文化现象。普通信众沿袭了明代混淆二者的民间信仰习俗,还衍生出两位女神互相侵夺名号的新问题。康熙帝与一些朝廷官员不能明确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这种模糊的认识为汪楫的传言提供了更大的传播空间。一些参与方志编写的地方官员与儒生文士或是延续汪楫的传言,或是编造乾隆帝与嘉庆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谬说,使清代妈祖元君化的历史进程更为复杂。 在清代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历史河流中,淮安惠济祠并祀妈祖与碧霞元君的礼俗现象确是一个特例,其引发的女神封号误会为妈祖元君化的历史增加了新的面相。 周郢先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注释: ①按:清廷对妈祖的最终封号只有64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见昆冈、李鸿章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414,礼部,群祀,惠济祠,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②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9年印行,第102页。 ③容庚:《碧霞元君庙考》,顾颉刚编著《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④按:相关研究如下:其一,郑丽航先生认为,以妈祖附会碧霞元君的始作俑者为清初的道士(郑丽航:《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莆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鉴于汪楫《使琉球杂录》提及的《天妃经》来历不明,恐始作俑者另有他人。其二,王见川先生认为,新发现的《道缘汇录》可能为明嘉靖时陆西星所作,该书称天妃“证位碧霞元君”应是指妈祖修炼的境地,因此妈祖的碧霞元君封号是“道封”(也即民间私封),而非帝王敕封(王见川:《妈祖封号“碧霞元君”的由来:读〈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札记之一》,《2012华人宗教变迁与创新:妈祖与民间信仰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手册》,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2012年)。周郢先生不同意王说,认为《道缘汇录》是汪楫所见《天妃经》之后的产物。其三,周郢先生依据康熙《颜神镇志》等史料,认为崇祯帝曾将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加封为“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妈祖与泰山玉女拥有相同封号的直接原因是“明清时期二者同有‘天妃’之称”,其根本原因是此时期的“南北两大女神渐呈融合之势”(周郢:《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兼论泰山娘娘与妈祖信仰之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不过,崇祯帝将泰山玉女碧霞元君加封为“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之说,尚需要更多证据才能坐实。其四,孙晓天、李晓非对崇祯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之事持存疑态度(孙晓天、李晓非:《妈祖与泰山女神共享“天妃”、“碧霞元君”称号考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其五,张富春先生依据明末管绍宁《赐诚堂文集》的相关记载,认为崇祯帝根本没有封妈祖为碧霞元君(张富春:《新发现的南明天妃封号》,《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⑤故宫博物院编《使琉球杂录》(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⑥郑丽航:《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莆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⑦(明)管绍宁:《赐诚堂文集》卷五《加封水神疏》,《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第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⑧(清)叶先登等纂《颜神镇志》卷三,飨祀,康熙九年刊本,第十七页B面。 ⑨《重修(浚县)碧霞元君行宫记》,浚县文物旅游局编,《天书地字》(大伾山文化系列丛书之二),中国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⑩按:《元始天尊说碧霞元君护国庇民普济保生妙经》称:泰山玉女碧霞元君“位证天仙之号,册显碧霞之封”,被尊为“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溥济保生真人护国庇民弘德碧霞元君”。《太上老君说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为泰山灵应宫内明万历铜钟铭文,属藏外遗经。该经称泰山玉女“受敕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真人”、也被称为“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溥济保生真人护国庇民弘德碧霞元君”。见范恩君:《〈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考辨》,《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1)(清)揆叙:《隙光亭杂识》(《续修四库全书》第11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2)(明)艾南英:《论宋天地合祭》,(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14《祭祀志》(四库全书本),第12页B面。按:或以为艾南英所言的“天妃圣母碧霞元君”是指作为天妃圣母的妈祖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若此说为真,则可以推定排在前面的妈祖要比排在后面的碧霞元君显要、尊贵,但事实并非如此。或以为明代妈祖与碧霞元君在神职上出现了重叠的现象,因此在神灵的名称上也出现了将两神并作一神的情形。这种情况在普通民众视野中不为罕见,但对于天启年间举人出身的艾南英而言,不至于如此混淆二者。 (13)(明)徐道编撰,程毓奇续撰《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九,第六节,王秋桂、李丰楙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册,(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3191页。 (14)吕洞宾原著,陈全林点校,董沛文主编《新编吕洞宾真人丹道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916页。 (15)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五,寺观,(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339页。按:容肇祖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恐是巫师附会冒名窃取,文人不察,遂以为是的”。见容肇祖:《与魏应麒先生讨论临水奶》,《民俗》1929年第61、62期(合刊),第24页。 (16)故宫博物院编《使琉球杂录》(故宫珍本丛刊),第34页。 (17)(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附《游泰山诗》,康熙六十年徐氏二友斋刻本。 (18)(清)李鼎元著,韦建培校点《使琉球记》卷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9)(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49册,卷二十八(博物汇编·神异典·海神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095页。 (20)(清)黄之雋等:《江南通志》卷四十一,舆地志,坛庙五,乾隆元年刻本,第1页A面下栏。 (21)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22)(清)丁午纂《城北天后宫志》,光绪七年刊,第16页A面。 (23)(清)杨浚:《湄洲屿志略》,卷一,封号,光绪十四年冠悔堂刊,第9页B面。又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5辑,第16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4)(清)杨浚:《湄洲屿志略》,卷一,封号,光绪十四年冠悔堂刊,第9页B面。又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5辑,第16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5)(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12册,卷七十五(方舆汇编·职方典·淮安府部·纪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96页。 (26)(清)桐西漫士、程穆衡、许锷:《听雨闲谈 燕程日记 石湖櫂歌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27)同上,第204页。 (28)同上,第205页。 (29)(明)王权:《修天妃庙记》,《重修德州志》卷五,祀典,天妃庙,康熙十二年刻本,第9页A面。 (30)韩锡胙:《元君记》,汤贵仁,刘慧主编《泰山文献集成》(第三卷),泰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31)望云居士、津沽闲人撰,张格点校《天津皇会考纪》,来新夏主编《天津皇会考 天津皇会考纪 津门纪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 (3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天后圣母事迹图志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合辑》,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72页。 (33)华伟东主编《浦东碑刻资料选辑》,浦东新区档案馆1998年印行,第218页。 (34)(清)潘叶舟:《乙亥春月重建天后古庙碑记》,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编《香港碑铭汇编》第一册,香港市政局1986年印行,第157页。 (35)(清)潘藜阁:《天后古庙重修碑记》,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编《香港碑铭汇编》第一册,第167页。 (36)《重建天后圣母古庙碑记》,郑炜明编《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版,第123页。 (37)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38)蒋维锬、刘福铸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1页。 (39)蒋维锬、刘福铸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40)(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0页。 (41)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委员会编《畿东泰岱:丫髻山》,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按:有学者误读张玉书《丫髻山天仙庙碑记》,认为张氏主张碧霞元君就是“湄州林都检之女”(孙晓天:《辽宁地区妈祖文化调查研究——以东港市孤山镇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42)毛甡:《募修德胜坝天妃宫碑记》(康熙二十三年),《艮山杂志》卷二,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771页。 (43)(清)姚鼐纂《重刻江宁府志》卷十三,祠庙,嘉庆十六年修,光绪六年刻本,第1页B面。 (44)(清)王文焘纂《重修蓬莱县志》卷三,文治,海神庙,道光十九年刻本,第14页A面上栏。 (45)(清)杨浚:《湄洲屿志略》卷一,封号,光绪十四年冠悔堂刊,第10页B面。又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5辑,第16册,第39页。 (46)(清)善广修,张景青纂《浦江县志》卷十三,祠庙,民国五年黄志瑶再增补铅印本,第28页。 (47)(清)丁午纂《城北天后宫志》,光绪七年刊,第二十二页B面。 (48)梁成久纂修,陈景棻续修《海康县续志》卷六,坛庙,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52页B面。 (49)李世瑜:《天后宫何来泰山娘娘》,《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9页。 (50)(清)和坤等修《大清一统志》卷六十五,淮安府二,祠庙,惠济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A面。 (51)王见川:《台湾妈祖研究新论:清代妈祖封“天后”的由来》,《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2期。 (52)淮阴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淮阴金石录》,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4页。 (53)(54)(清)朱元丰、孔传楹修,吴诒恕纂《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坛庙,惠济祠,乾隆十五年刻本,第19页A面。 (55)(清)吴棠修,鲁一同纂《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咸丰四年刻本,第16页A面。 (56)同上,第16页B面。 (57)(清)文彬修、吴昆田纂《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坛庙,惠济祠,光绪二年刊本,第17页B面。 (58)(清)许兆椿:《天后宫碑记》,《秋水阁杂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页B面。 (59)《天启淮安府志》云:“灵慈宫:郡天妃宫有四,一在府学西,一在郡城西南隅万柳池,一在新城大北门内,一在清江浦。祀天妃神,神姓林,莆田湄洲人,海、漕二运,大著神功。”见(明)宋祖舜修,方尚祖纂,荀德麟、刘功昭、刘怀玉点校《天启淮安府志》,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页。有学者认为,“至晚在明末天启年间,清口惠济祠已经被同时视作天妃庙,两位女神的祀宇在此混为一体”(贾珺:《灵祠巍焕,飞阁凌空——淮安府清河县惠济祠历史、格局、祀神及御园仿建始末考略》,《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3年第1期)。应当说,明末清口惠济祠确实有“天妃庙”的称谓,但若因此认为妈祖与碧霞元君在此被混为一体,尚缺乏有力证据。 (60)(清)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页。 (61)(清)吴棠修,鲁一同纂《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咸丰四年刻本,第16页B面。 (62)(清)汪之藻:《天妃庙赋》,(清)朱元丰修,吴诒恕纂《清河县志》卷十三,乾隆十五年刻本。 (63)《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3页;《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清)胤禛编《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411册,第544页。 (64)《李世杰等复奏清江被淹庙宇及民居已未涸出情形折》,周焰等编《清代中央档案中的淮安》,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 (65)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66)(清)文彬修、吴昆田纂《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坛庙,碧霞宫,光绪二年刻本,第17页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