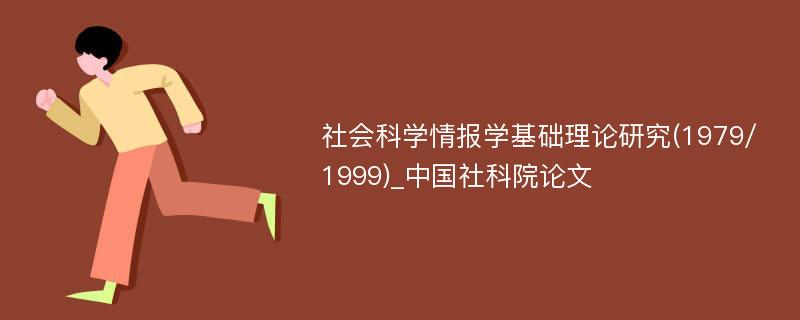
社科情报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979-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理论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对整个社科 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起着指导作用,而且其间所涉及的内容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科 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水平。总结国内外20年来社科情报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历程,对于我 们深化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1 社会科学概念
对社会科学概念的不同界定直接影响着对社科情报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因此,社会科学概 念一直是国内外社科情报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由于理论渊源的差异,在国际领域,各国对“社会科学”一词的理解尚无一致意见。最显 著的分歧是,有些国家常常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行为科学区分开来,有些国家则不然。 1930年美国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将社会科学分为纯社会科学、准社会科学和社会关 联科学[1,2],它实际上已将人文科学包括在社会科学之中了。60年代,心理学家皮 亚杰 (Jean Piaget)在其《学科分类与跨学科联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类与社会科学”(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概念其实质也同样如此[3]。在INFROSS研究中,莱恩(Line)给出了一 个涵盖广泛的定义。他认为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互动或群体行为的知识”,故将社会科学 界定为: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将他认为共属于人文科学 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共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还有他认为尚存疑问的法学以 及应用类的管理、商贸、市场营销、广告、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管理都列入了“社会科学” 范畴[4,5]。30年后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6]。
从70年代后期的研究来看,英国情报学家斯莱特(Margaret Slater)虽然也承认人们较为认 可的核心学科是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较有争议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等,可 他对莱恩的观点不完全认同,认为尽管莱恩对社会科学的描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却并不 一定十分权威[7]。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源:文献指南》(第三版)将社会科学概括 成 八大领域:历史、地理、经济与商业管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及政治学,但 同时认为语言学、统计学、人口学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8]。荷兰情报学家德哈尔特(Hoge w eg deHaart)认为,社会科学一词应包括:人类学、信息科学、犯罪学、人口统计学、经济 学、教育、环境规划、未来学、地理学、历史学、劳动科学、法学、图书馆和情报学、管理 科学、哲学、政治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社会政策、社会学、统计学、宗教科学、科 学学[9]。虽然他认为“把社会科学的情报局限在有限的社会科学范围之内的方法是可取 的”,但实际上却将哲学、宗教、历史等人文科学分支学科均包括在内了。其他观点,如普 雷斯切尔与伍德(Barbara M.Preschel,Lawrence J.Wood)认为,社会科学除了包括人类学、 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也常常包括商业与财经、教育、历史、法律; 此外,一些交叉性学科,如民族学、人口统计学、妇女研究、校勘(校雠)、图书馆与情报科 学、衰老学、社会工作、犯罪学、口述历史、传播学等也可包含于此[10]。斯文·基维克 认为,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11]。
在中国,“社会科学”概念通常是指广义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 学[12]。它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而言的、将人文科学包括在内的学科门类。国内 社会科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将哲学包括在内,后者则不然。
根据对该领域研究的分析,我们发现:第一,尽管由于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产生了 大量新兴学科,但国外学者对社会科学概念的基本界定在20年来却未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为 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比较基础。第二,虽然西方国家对社会科 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的含义界限混淆不清,但其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界在实际研究中对社 会科学范围的界定却是基本一致的——以狭义社会科学为主、也包括行为科学及部分人文科 学的分支学科在内,这又可以为中外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提供横向比较的基础。
2 社会科学的特殊性
30多年前,不少学者专家已经对社会科学特殊性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库恩的(Kuhn)的“前 科 学”(prenormal science)学说[13],斯多尔(Storer)关于“硬科学”、“软科学”的描 述 [14],以及普尔(Pool)等人概括的社会科学“四特点”[15],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 总结了社会科学的特点及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区别;而莱恩列举的“13大特点”,则 从情报需求出发阐述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16]。 70年代后期以来,除了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之外,例如,邦齐(Susan Bonzi)采 用符号关系模型(syntactic patterns)比较揭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17], 国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社会科学某一具体特点的研究上,尤其是社会科 学的本土性与国际性问题。比如斯文·基维克在1982年通过调查比较挪威4所大学社会科学 著作的发表模式的差异,对社会科学的国际性问题进行了研究[18];布里顿对第三世界国 家社会科学本土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应当更加注意本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工 作[19];内德洛夫(A.J.Nederlof)和诺扬斯(E.C.M.Noyons)对人文科学的两大分支学科语 言学与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重点讨论了本土性与遍生性之间的关系[20],这些均标志着 该领域研究正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
3 社会科学交流机制
科学交流是指“影响科学家之间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科学情报的出版、机构、机遇、学会活 动和传统的总和。”[21]研究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科学家在其 利用科学信息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从而去改善社会科学交流系统的状况。
西方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从来就将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研究放在重要地位。无论是加维(W.D.Ga vey)等主持的心理学科学情报交流计划(The Project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xchang e in Psychology)[22]还是INFROSS[23,24]、DISSIS[25]研究,其根本出发点都是 为了改善社会科学交流状况。
70年代后期,这一研究仍未歇止。代表性成果有:前苏联学者对自然、社会、技术三大学 科门类交流模式的比较研究[26],荷兰学者对社会科学文献利用状况的研究[27,28], 法国学者对特定用户类型交流模式的调查[29],日本学者对人文科学交流情况的研究[30 ,31],马来西亚学者对人文科学交流特点的计量分析[32],等。
基于对INFROSS调查的分析,布里顿在《社会科学的国际性——情报传递的含义》、《社会 科学中的情报服务与知识结构》、《论世界社会科学产品》等几篇著名论文中对社会科学交 流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将之概括如下:(1)从交流范围上看,大多数社会科学产品的 非国际性影响了不同国家间社会科学知识的流通并导致了第三世界的本土化运动;(2)在知 识积累方面,社会科学并不存在普赖斯所谓自然科学中的“积木”现象和自我净化机制;(3 )在信息利用上,存在着对二次文献的抵制和对信息的随意性寻求现象;(4)在研究方法上, 藐视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交流方式往往类似辩论,而不是进行科学的论述。(5)在成果评 论与检验方面,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理论和模式往往很快被推翻,但又常常改头换面地出现, 难以证实和证伪,缺乏寻求一致的机制[33]。布里顿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社科情报服务部门 改善情报服务,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研究也甚为重视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具有代 表性的论著如范并思《论我国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的根本改变》[34]和他对社会科学交流机 制的定量研究[35]。梁邻德的《社会科学情报学》对社科情报交流中的特殊障碍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概括[36];陈誉《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则从社会科学交流过程、交流形 式、交流工具、交流功能和交流障碍五个方面全面总结了社会科学交流的特点[37]。
毋庸讳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研究仍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8 0年代初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后来的文献计量研究和一些实证性调查研究由于规模小 、范围窄、回收率低等原因也难以在信度和效度上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部分研 究之间甚至还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周期过短、研究经费较少、研究范围过窄、研究 方法不够严谨等等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
4 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是决定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方向与重点的重要因素。
对于世界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将其归纳为综合性研究、 定量化研究、应用化研究三个变化[38];《社会科学史》归纳为整体化、主体化、应用化 、国家化国际化四个变化[39];彭斐章先生等指出社会科学发展出现了五个新动向:综合 化、应用化、“大科学”化、定量化和预测化[40];范并思认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变 化趋势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科学应用化趋势[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在理论价值取向、理论形态、研究方法、学科结构、科学组 织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理论进步。以夏禹龙的《社会科学 学》为代表的研究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国内社会科学的变革成就与发展规律[42]。
定量地研究社会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是该时期研究的又一成就。伍德(Judith B.Wood) 在 1988年对1880-1984年共105年间美国与加拿大的学位论文作了计量统计,目的在于分析人类 科学整体发展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门类的发展轨迹。他发现,社会科学 比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科学整体的发展轨迹,而人文科学陡增陡减的现象较为明显[43]。从 国内情况来看,范并思利用《报刊资料索引》(光盘版)统计分析了18年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的数据,证明中国社会科学所发生的变革,尤其是其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方面发生 的变 革与二战后世界社会科学变革的大趋势是一致的[44]。这一研究对于准确地了解中国社 会科学在现代国际社会科学发展和中国社会变革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把握社科情报事业 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5 社会科学情报问题
社会科学情报问题是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基本课题,它有助于构建社会科学情报学 科的基础,促进理论与方法研究向体系化方向发展。对该课题的研究主要包括社科情报的定 义、特性、成分、类型、价值、功能等方面。
70年代社科情报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中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就是社科情报的特殊性。 例如德哈尔特《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一书通篇论述的都是社科情报各方面的特点,集中反 映了这一时期的理论趋势[45]。进入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像ERIC等一些社科情 报系统的成熟和商业性联机情报系统对社科情报的渗透,政府也逐渐减少了对社科情报问题 的调查研究基金资助,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80年代中后期以后欧美国家社科情报问题研究 成果的明显减少。比如,英国1980年创刊的《社会科学情报研究》(Social Science Inform ation Studies)在短短几年内便转向改名,其中和该研究领域的投稿量减少不无关系。
由于滞后的原因,国内对社科情报特点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才形成热点。在最初的研究中 , 人们将社科情报与社科文献的特点加以笼统的认识[46],90年代初期以后,视角得以 拓宽,研究得以深入,如有的研究从知识内容、表述、运动和价值四个方面来分析社科情报 的特点[47];有的从内容、表述、运动三个方面来进行归纳[48];还有的则从文献内容 、文献类型、文献情报产品和文献时限几个角度来研究[49]。透过这一研究侧面,我们也 可以看出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
该问题领域的另一重点是关于社会科学情报成分的探讨。这一问题与国内社科情报界大、 小情报观之间的争论直接相关[50-52]。“小情报观”强调社科情报的核心成分——科学 情报,而“大情报观”则认为社科情报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产生的两部分情报构成 的。大、小情报观的争论不仅关系到社会科学情报学科建设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着社科情 报机构如何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情报观” 得到公认,关于社科情报(信息)成分的讨论也便有了较为圆满的结局。
其他文献还涉及到社科情报的价值[53]以及诸如社科情报商品化[54-56]等相关问题的 研究。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和完善了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