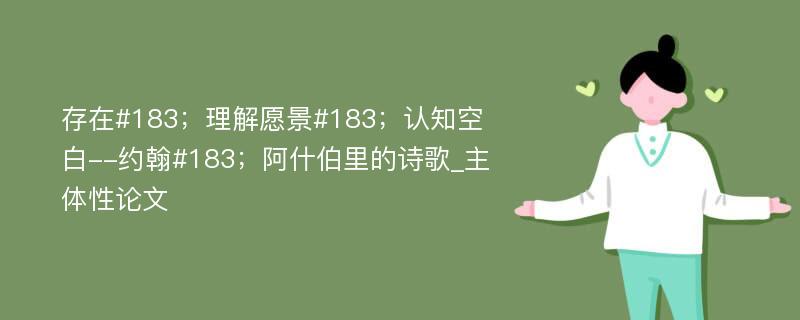
存在性#183;理解视野#183;认知空白--试论约翰#183;阿什伯里的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认知论文,试论论文,诗歌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在其所著的《后现代,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一书中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1927~)是“最杰出的后现代艺术家之一”。[①]但耐人寻味的是,阿什伯里本人却抱怨说:“现在是样样都被标榜为后‘这’,后‘那’,如后现代派,后逻辑,真是太糟糕。那么给将来留下什么呢?”[②]很明显,阿什伯里反对把自己贴上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在他看来,自己的创作是记录“心灵运动的轨迹,即心灵怎样从某一点滑向另外一点的路径”。[③]其实,阿什伯里并不拘泥于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也未滑入后现代主义追求“精神分裂美学”[④]中的纯粹语言形式试验的窠臼,正如乔德·诺顿所说:“约翰·阿什伯里是最后一个探索主体的诗人,也是第一个通过自由谓项[⑤]寻找主体性存在的诗人。他介于《荒原》(呈现出多声部,可以被读作后现代诗歌……)和语言派诗人(……偏离单个主体、注重诗歌形式及把诗歌的焦点转移到作为文化的开放本文中的语言形式试验)之间。”[⑥]
阿什伯里的创作体裁多样,有诗歌、戏剧、小说、杂文、文评等,但阿什伯里主要是一位诗人,也以诗歌见长。从1952年发表第一部《图伦多特诗集》起至1991年,共出版诗集23部。关于阿什伯里诗歌艺术的界定,许多评论家(甚至包括阿什伯里本人)都惯用贴标签的方式,或说是“新新-古典主义”,或说是“达达艺术派”,或说是“超现实主义”(分别见本文第二部分),有人则说是“后现代主义”。笔者认为,阿什伯里创作的时间跨度较长,前后期风格手法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出现上述各式各样标签式的评论也不足为奇。但纵观诗人的创作,我们发现有一条隐含的线索贯穿于诗人几乎全部的作品,那就是:存在--语言--理解,这是任何一种或几种简单的标签所指代和概括不了的。阿什伯里关注的重心是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和图式,这一过程和图式不仅只能发生于语言之中,也被看作是一种语言。所以对于诗人来说,诗歌思维就只能是沉思和反省性的:即作为思维的主体(诗人)通过语言沉思和反省自我的主体性。这样,主体性不再是一种透明的、自足的、稳定的及连贯的,而是一种主体的自我互证(即主体自身反省主体本身)。正因为诗人这种在诗歌主题、形式、审美上以语言为中心来探索主体的存在,所以理解和解读诗人的作品就应该把它放在现当代语言哲学的理论背景中去把握(特别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因为阿什伯里和这些语言哲学家一样都对主体性和语言本身提出了质疑。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从贯穿于阿什伯里诗歌的主题焦点、风格技巧、审美特征这三方面作一些分析和论证。
Ⅰ、主体的存在性:诗的主题焦点
存在性(Existential)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意指主体理解(认识)主体自身的一种基本限定,也就是说,作为“为自己的存在本身而存在”[⑦]的主体受语言的限制和支配对自身理解的界限。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石是把作为谓项的及物性当作本体性看待(即把to be当作being)。而这个“是”(to be)并不能指向任何确定的意义或本质,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悬设而已,主体在意义的追求中不断进入具体的关系之中,但永远也得不到终极的、永恒的意义和真实的主体性存在。在阿什伯里的诗歌中,纯粹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主体的自我认识经常由一系列反省性的联想话语组成,犹如快速翻滚的影视图像,瞬间浮现又瞬间消失,所以主体就只有某种瞬间的存在性,而不具有本体性质的“实体性”。这样阿什伯里和海德格尔一样提出了当代语言哲学的两大中心命题:存在、时间,即探索存在的时间维度(存在性)和时间对主体的存在可能性(主体的存在瞬间)。这一主题贯穿于阿什伯里的诗歌创作。
美国诗评家杰夫·冈迪在其《傲慢的谦卑与精英的感觉迟钝: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中指出:从70年代以来,美国诗歌的大多数“脱离政治与社会生活”,脱离“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多注重个人生活的琐事,这一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阿什伯里”。[⑧]诗人对美国大众讲求物质利益的反应就是使自己的诗歌避免道德的说教和判断,因为对于阿什伯里来说,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人们都按照某种结构性的模式进行思考和感知,总逃脱不出这种支配性结构模式的束缚,用诗人安蒙斯(A.R.Ammons,1926~)的话说:“主体受主体之外的法则和自然过程的支配。”[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阿什伯里不愿注重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原因。诗人避开大众生活和社会道德问题,集中探索这种支配性的结构模型及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和图式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阿什伯里诗歌所反省的主体性,许多批评家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意指“主体性的无限视野”,[⑩]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主体只能通过语言所看到的“世界的阀限”;(11]有人认为“主要是一种功能,而不是实体”;(12]有人则认为是一种“类比的游戏”,(13]即主体只能通过语言的隐喻和换喻指向主体存在而永远达不到存在本身。上述看法的共同点就是主体性在主体的再现中永远是一种“缺席”。因此,阿什伯里将语言的诗化本质同存在的“缺席”本质联系起来,在语言的诗化中寻求一种无法之法。这样,由存在--语言--理解之途实现了诗歌向作为“无限视野”的主体性的拓展,实现了更内在的意识与无意识、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形态转换。在阿什伯里诗歌所呈现的多声部里,总是缺乏一个支配性或方向性的主体意图,诗中瞬间掠过的主体存在总具有一种结构性过程或句法,作为这种结构过程的思维主体就变成主体存在瞬间的时间维度。于是,自我与诗歌话语的界限消失,主体性也就变成一种语言。所以,主体不可能透明地认识主体的存在,只能通过语言理解主体性的瞬时存在--主体的存在性:主体性就成为一种语言话语的永恒替换。例如阿什伯里的《幻影火车》(1981)一诗中的几节:
在镜子里,我看到了那映像,
但它并不算什么,或不足于表明什么,
它不过是那大学之城古老而平庸的光
编织的自我
而后,乘车旅行
已经耗尽了我本来就很少的钱财。
在沾满水气的玻璃后面,他在争辩,
与一位看不见的主体。若你不拥有,你又为何物呢?
是这,还是那?似乎所有的时刻
都是这样:依稀,令人失望。
每一次回归,都有失去,
直到有一天,你把画布从画架上撕掉
带回家中,……诗歌第一节:“在镜子里我看到了那个映像”,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映像”。也就是说,“看”(用心灵去“感受”)并不能认识真正的主体,至少“不足以”认识主体。即使看到主体“映像”,那也只是一种被语言和文化编织的“幻影”,而真正的主体总是存在于“幻影的背后”。这里,诗人使用“幻影火车”一词作为类比,暗示主体存在的方式。“那大学之城古老而平庸的光”指语言和文化传统,主体就是依此为媒介“编织”所谓的主体性和自我;第二节:“乘车旅行已经耗尽我本来就很少的钱财”指探索自我(“乘车旅行”)只能使主体性又消失在传统的框架之中,正如拉康所说,主体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即前语言阶段),主体还是“理想的主体”,但进入语言阶段之后,主体便永远地消失,主体性便自我分裂,即处于“我思我不在、我不思我在”(14]的状态。
在本诗与阿什伯里的其它所有诗歌中,“I”、“You”、“We”、“He”、“They”这五个人称代词是互用的,没有严格的界限,就连做为物主代词的“it”也常常既指人又指物,界限不明。这种现象许多批评家给予不同的解释,如博格曼认为:阿什伯里的“弱化自我”(即人称代词混用)“可能与阿什伯里的同性恋心态有关。”(15]的确,在阿什伯里的诗歌中,“同性恋情节”时隐时现,但阿什伯里本人却否认说:“我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诗人”。(16]笔者认为,阿什伯里诗歌中的人称代词的互用,人称代词模糊化或人称物主代词的不确定性至少有三种意义:首先反映了诗人对自我主体性的理解。在阿什伯里的诗歌中,主体被认为依存于社会及文化语境的符号结构,语言既作为主体认识的基础,又是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纯粹的个体意图和意识是不存在的,自我主体性只是一个具有集体性质的功能,意识以语言作为反映和存在的媒介既具有个性(我性)又具有集体性质(它性)。所以人称代词互用实质上反映了一种诗人主体与他者界限的消失。其次,诗人故意消弱自我意识表明自我的非透明性,从人称代词的转换使用中使诗人能够很容易地滑向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多元声部,这是诗人诗艺的最典型的代表。再次,人称代词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探索自我的努力,是一种“试图真实地再现当代精神困惑和反对主体心理图式呆板化”(17]的创作方法。所以,诗人才写道:“在沾满水气的玻璃后面”,“他(也是“I”、“You”、“We”、“They”)被看见在争辩”。但透过这“半透明的玻璃”依稀窥见的争论主体究竟是谁却不得而知。而这半透明的玻璃暗示了诗人一种薄雾般、模模糊糊的记忆、幻想、梦境。第二节的最后这两行非常明显地暗示了阿什伯里赞同尼采对笛卡尔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故我在”意味着有思维就一定有“思维的主体”。阿什伯里沿续尼采的批判,认为笛卡尔实际上把思维的主体概念放在一个“先在真实”的地位,是“我们传统语法的思维形式”(即以语言具有绝对的透明度为前提)。(18]在阿什伯里看来,人类的无意识和意识的系统一旦被语言格式化,主体就永远成为一种“缺席”、主体就永远有个“看不见的主人”。
第三节,诗人困惑道:“是这,还是那,似乎所有的时刻都是这样:依稀、不令人满意……”主体虽依稀可见,但总处于我们“无限视野”的远方,可望而不及。在这样积极追求但又屡遭失败之后,又使作者联想起画家因找不到灵感而“把画布从画架上撕掉”,“带回家中”。至此,诗人以画论诗,暗示了诗人“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夸张提喻的风格。最后一节,特别是诗的最后两行表现了诗人后存在主义的悲叹和惆怅:人生只是存在,但存在却完全不得而知,如诗人在70年代的一首《分三部分的诗歌》(见诗集《三首诗》,1972年)所说:
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记住
但却没有必要,知道它是什么,
一切都明明白白,但没有什么我们会知道。
由此可见,阿什伯里诗中的主体性只是主体瞬时的存在性,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主体存在的时间维度”。但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诗人虽强调语言结构在主体思维中的作用,却没有把语言放在一个本体性的先在地位,其诗歌也仅仅运用语言中介呈现一个“现象世界”作为一种功能性思维,永远指向主体而不是主体本身。所以,语言产生主体性、主体性来源于语言是阿什伯里诗歌创作的基本模式和主题。
Ⅱ、理解视野:诗的技巧与风格
阿什伯里的诗艺与风格有许多不同的阐释:詹姆逊把阿什伯里的诗歌归结为后现代主义艺术“最典型的语言拼贴”,即视诗歌创作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布鲁姆则认为是“误读个性化”的产物,(19]是一种对传统意义随意性的“颠覆、扭曲、疏离、省略、晦涩化和肢解化”;(20]美国诗人、文评家罗伯特·布莱在他所著的《美国诗歌:野性与驯服》(1990)一书中称“阿什伯里的创作具有达达主义的片断破碎性同时是一种随机拼贴性的意象代数”,(21]也就是说,阿什伯里诗歌试图再现某种超现实性,诗中的随机性,破碎的意象只是一种数学中的代数系列,并不具体指代任何确定的“内容”;诗人、文评家韦恩·多德在与布莱一次谈话中称阿什伯里的诗歌为“新新-古典主义”的创作风格,多德的评论理由是:“阿什伯里的诗歌强调形式和理智、几乎完全缺乏诗歌情感”。当布莱提及阿什伯里本人承认自己的创作手法”基本是超现实主义”时,多德解释道:“阿什伯里有时带有超现实主义创作色彩,这是事实,但我所发现的是,他的诗歌缺乏情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所谓超现实主义并未达到某种现实之外的、更令人感动的主观建构,相反,诗人不断地背向这种超现实的主观建构。”(22]的确,阿什伯里并不追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提倡的“主观化的现实建构”,也不寻求某种“超越现实的世界存在”,(23]而是试图寻找主体本身的建构方式,探索主体的瞬间的存在性,正如阿什伯里在评论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沉思的诗节》一诗所说:
“《沉思的诗节》给人一种时光流逝感,一种事件发生的‘情节’感,虽然很难准确地说清楚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有时,诗的话语具有一种梦的逻辑……,有时在某一瞬间开始都变得明明白白,犹如风向的一阵突变使我们听到远处正在发生的一场对话……。但斯泰因感兴趣并不是所发生的事件,而是‘事件发生的方式’。《沉思的诗节》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个普遍的,多目的性的叙述模式,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输入自己喜好的故事细节。此诗就是一首关于多种可能性的赞美诗”。(24]
笔者认为,阿什伯里的诗歌正是围绕主体存在性的主题展示了诗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呈现出了这种多声部拼贴的独特效果,并使读者能够进入“诗人与读者的共同话语”,(即诗歌),即使诗歌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也使读者从诗歌自由的类比隐喻中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用当代接受美学的话来说,诗人呈现的某种“理解视野”转化为诗歌固有的一种“期待视野”或“召唤结构”,以其开放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使不同读者对其进行具体化时隐含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所以,阿什伯里的诗歌并不能用上述任何一种批评标签标定其诗歌的艺术特征,我们只能用一个大体的词语“理解的视野”来形容诗人这种诗歌的再现艺术特征。
阿什伯里再现“理解视野”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常用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意象拼贴和明/暗喻(或称元明喻meta-simile)的使用。例如在诗集《划游艇的日子里》(1977)的《曳船路上》和《烙烫画》二首。在《曳船路上》一诗中:中世纪传奇、伊丽莎白时代的露天戏剧、连环漫画、亚瑟·拉克姆童话、迪斯尼T恤衫、花案墙纸、奶油蛋糕、婚礼场景、舞台道具、牧羊女浮雕、恐怖主义分子合唱的赞美诗等一系列感官刺激、联想离奇的杂合意象群似乎在某一瞬间投射到梦幻般的舞台上,由一个中心声音粘合在一起,但刚要显露一种隐含的意义,瞬间又消失在这杂乱拼贴意象群中。如果说象征主义诗歌(如艾略特的《荒原》)所呈现一堆杂乱无章的意象群就已经让读者难以捉摸,但杂乱无章的意象群最终仍有一个中心声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全局整体,还可以使读者最终解读。阿什伯里却再进一步,总是在那即将显露核心意象时把它破碎。在《烙烫画》一诗中,诗人采用烙铁在木板或皮革上作烫烙画这一绘画技法乃是隐指记忆、印象和意识的形成过程。炽热的烙铁快速从木板或皮革上掠过,恰如记忆和印象瞬间从意识中掠过一样,模模糊糊,踪迹不清。诗的场景是美国的芝加哥城,但又好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这里,“马车在充满橡树香味的天空下行走”,穿越“旋转的扇形郊区”,“黑洞般的城市”。诗歌意象连续滚动和翻转,令人目不暇接,但诗人最后落脚何处,诗中只是说“湖泊城市”,而且又困惑地说道:
我们怎能居住在
这只有三面墙的房间里,
就像一个舞台或玩具小屋
所以只能住在失去外形的空间中,面对着星空。
整首诗给读者的感觉是“走来走去没有根据地”,展示了诗人“理解视野”的无限距离。
与象征主义运用“通感”(如波德莱尔)、“客观对应物”(如艾略特)、或意象派运用“情感与理智的瞬间结合”(庞德)制造意象不同,阿什伯里经常使用德里达所称的“粗糙的隐喻”(25]再现诗人“理解的视野”,也就是说,一种“似乎”或“可能”的诗歌表达方式。诗人最独特的创造便是一种称作“元明喻”(即be/as结构),即介于隐喻和明喻中间的一种语言修辞模式。在这种杂交的修辞模式中,隐喻的“是”(如:人生是一首诗)与明喻的“像”(或“似”,“如”等,如:人生像一首诗)相结合产生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诗歌言说,但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诗人的诗歌思维方式和诗歌技巧(人生是/像一首诗)。这种谓项的不确定性表明了存在的不确定。如诗人一首《冗长的祈祷》(见诗集《正如我们所知》,1979)。这首50多页的诗歌每页有两个纵列(祈祷与回应并置的安排形式),如下四行:
All life
Is as a tale told to one in a dream
In tones never totally audible
Or Understandable.
诗言道:“人生是/像一个故事”,“一个在梦中给他人讲述的故事”,但又“以完全听不见的语调”讲出,又使人“无法理解”。这种be/as元明喻结构肯定了存在,但同时又限定了存在的界限。阿什伯里运用这种“模糊逻辑”拓展了诗歌意义的多种可能性,运用破碎化和瞬间性的意象展现了存在的“现象世界”,最终建构了一个媒体化(语言)的主观形成过程,娱乐化的艺术审美,诗人也就充当了一个“享乐主义的沉思者和观察者”,(26]从主体自我反思的语言游戏中得到了诗歌艺术的愉悦。
Ⅲ、认知空白:诗的审美效果
如果用老子的“幌兮惚兮,道之所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来描述阿什伯里的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毫不为过的。的确,阿什伯里所关注的是玄学问题,即主体的存在问题,所采用的手法是再现主体理解视野的“现象建构法”,那么留给读者的就只有这“梦幻般的现象世界”,最终留给读者的是一片“认知的空白”,更确切的说,整诗首充满福克纳式的“喧哗与骚动”,而最终“没有所指任何意义”。正如戴维·帕金斯所说:
“当你经历了这些而达到了乌有之境,你此刻在哪里?当你所感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没有把握,你作何想?当你没有理由或动机作任何事时,什么是值得作的呢?阿什伯里的处境只能是在悖论之中”。(27]
所以阿什伯里的美学就是这样一种“悖论美学”,带有后现代主义作家所追求的“精神分裂美学”色彩,但又没有完全滑入后现代主义彻底的精神分裂美学的窠臼。在阿什伯里的代表作、长达552行的《凸面镜中的自画像》(1976)一诗中,在前20行,读者就确切地知道诗人是在进行关于自我的沉思,但自我又远离真正“实体性的自我”及个体生活的体验;接下来诗人对主体的“灵魂”进行更深入地反思,通过诗人所呈现的多重而活鲜的意象,读者似乎进入了一个“灵魂的世界”,“心的天国”。但诗人又说:“这灵魂并不是真正的灵魂”,而只是一种灵魂的表征。对于主体的本质,诗人说:“没有词语可以说出它是什么?”。
《凸面镜中的自画像》是一首灵魂的哀歌,但诗人并不知道这灵魂是什么、在何处,读者也无法得知诗中灵魂的所指和位置,只有一种“缺失的”惆怅。实际上阿什伯里的全部诗作都充满这种被压抑的哀叹,给人一种后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悲怆意识。这使我们联想起尼采所说的疯人白天提着灯笼找上帝的隐喻,阿什伯里也是在青天白日中寻找“自我的灵魂”,虽最终没有找到。在拉康对弗洛依德的自我形成理论重新修正之后,在福科对主体的存在颠覆之后,在德里达对认识本性解构之后,主体性在当代哲学心理学中便成为一种无穷无尽的替换和缺失。同样,在阿什伯里的诗歌中主体性也是一种永远的“缺席”。对于诗人来说,没有信仰,也没有希望,而只能沉醉于无穷无尽的自我分析之中去发现人生与自我的意义和价值,但自我分析结果又是什么呢?诗人没有答案,读者也从诗中找不到答案。所有这一切沉思、自省、拼贴、求索最终都是一片空白,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
最后,所有的主体符号
开始消失,使画布变成
一片白纸。(28]
但阿什伯里并没有完全解构主体性,正如《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中的意大利画家弗朗西斯科·帕米奇阿尼诺意象告诉我们的,它并不是诗人“同性恋情节的反映”,同性恋也不占重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隐喻,意指诗歌的“向我思维结构”,用戴维·萨皮罗的话说:“本诗呈现了一种无限的向我思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29]所谓“向我思维”即是说思维永远指向自我(虽然不可能认识自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阿什伯里的诗歌才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之作。也就是说,在主体性完全被解构之后,所有后现代主义文学才算真正开始。
注释:
①④Frederic Jameson,Postmodern,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o,1991,p.26;p.28.
②阿什伯里在华沙接受诗人、文评家派·素摩(Piotr Sommer)采访时所说,见张子清(美国当代诗歌现状探析》--载于叶逢植主编《欧美文学现状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③阿什伯里于1987年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接受美国诗人,文评家保罗·莫恩(Paul Munn)采访时所说。见"Interview with John Ashbery",New Orleans Reviews,vol.17,ii:pp.59-63.
⑤谓项(predicate),即联接主体与客体的路径,通常表示为X is Y(X表示主体,Y表示客体,be表示谓项)。阿什伯里赞成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在诗歌中只能接近主体而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主体的观点,认为诗不是“在”本身,而是在“缺席”,同时也存在“召唤”,所以诗人只能运用“谓项”形态(to be)实现诗的语言向本体自身的拓展。
⑥Jody Norton,Whispers out of Time:The Syntax of Being in the Poetry of John Ashbery,Twentith Century Literature.Spring 1995,p.281.
⑦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12页。
⑧Jeff Gundy,Arrogant Humility and aristocratic Torpor:Where HaveWe Been,Where Are We Going?,Leonard M.Trawick,world,Self,Poem,Kent State UP.1990.pp.20-27.
⑨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1990,Ed.,David J.Nordloh,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374.
⑩John Koethe,The Metaphysical Subject of John Ashbery’s Poetry,in David Lehman,ed.,Beyond Amazement:New Essays on John Ashbery,Ithaca,New York:Cornell UP,1980,p.96.
(11)路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本文引自蒋永福编《西方哲学》(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2)Charles Alteri,Self and Sen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New York:Cambridge UP,1984,1.162.
(13)Charles Alteri,John Ashbery an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Visual Arts.Critical Inquiry,vol.14(1988),p.82.
(14)Jac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Norton,1977,p.166.
(15)David Bergman,Gaiety Transfigured:Gay Self-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46.
(16)(20)John shoptaw.On the Outside Looking Out:John ashbery’sPoetry Cambridge:Harvard UP,1994,p.4.
(17)David Kalstone,Five Temperaments,New York:Oxford UP,1971,P.183.
(18)Friedrich Nietzche,The Will to Power,ed.,Walter Kaufman.Trans.Walter Kaufman and R.J.Hollingdale.New York:Random House,1968,p.286.
(19)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4页。
(21)(22)Robert Bly,American Poetry:Wildness and Domesticity,Harper & Row,Publishers,Inc.(New York),1990,p.41;p.314.
(23)Malcolm Brandbury et al,ed.,Modernism:1890-1930,Penguin Books,1976,p.292.
(24)James Vinson ed.,Contemporary Poets,St.Martins Press(3rd edtion),1980,p.47.
(25)Ja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rans,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Baltimore:Hohn Hopkins UP,1976,p.276.
(26)Paul Brishin,The Psycho-political Muse:American Poetry Since the Fif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216.
(27)见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28)见阿什伯里《一些树》(Some Trees,1965)诗集,此为《画家》一诗。
(29)David Shapiro,John Ashbery:An Introduction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