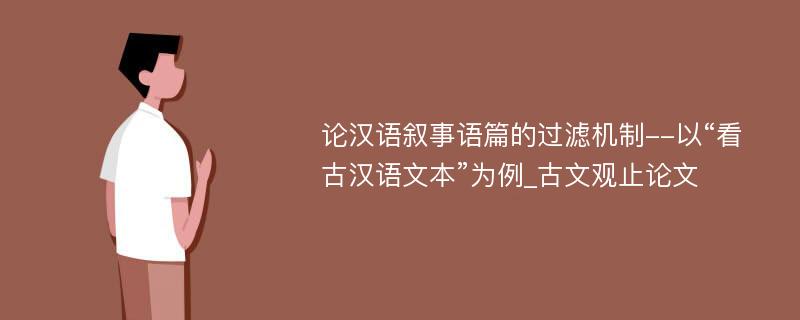
论汉语叙事文本的过滤机制——以《古文观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古文论文,为例论文,文本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汉语叙事文本的研究,虽然不乏细致的解读,但在总体上却停留在文章鉴赏的水平,缺少完整、严密的理论框架,因而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结论。①本文将以《古文观止》为例,对汉语叙事文本中的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作一些分析,着重考察“事件”在文本中的分量,以及其他表现手段(尤其是议论)在叙事中的运用。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粗浅的问题,但事件在文本或叙事中所占的比例,显然会影响整个文本的结构,也会影响到文本的意义。而且,通过细致的文本形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比例并非自然或偶然形成的,汉语叙事文本中缺少记事的成分,实际上是因为汉语对于事实有一套十分有效的过滤机制,而在过滤掉大量的事实之后,文本的意义就更需要借助于想象、暗示、议论等手段来实现。
一、叙事文本的“非典型性”
如果按照叙事、抒情、议论三分法来对《古文观止》中的文本进行分类,我们将很难找到剥离了抒情和议论的典型的叙事文本。但如果把一些并不“典型”的叙事文本算进去,则叙事文本所占比例大约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先秦。其中,《左传》(34篇)、《国语》(11篇)、《公羊传》(3篇)、《榖梁传》(2篇)、《国策》(14篇)是公认的历史著作,《礼记·檀弓》(6篇)也被看做是史实的记载。所选《史记》14篇中仅有4篇是完整的叙事文本,即《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滑稽列传》。除了这些历史性质的文本之外,仅有少量游记、传记和杂记之类的文本具有较多的叙事成分,如《桃花源记》(陶渊明),《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柳宗元),《袁州州学记》(李觏)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历史著作和纪实性质的散文是叙事文本的主体,所以,《古文观止》所选文本基本上是能够代表各类叙事文本(包括小说)的。而且,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还可以将《古文观止》所选汉语叙事文本中的语段看做汉语叙事的基本构件,它既可以组合成短篇叙事文,也有可能组合成长篇叙事文。事实上,在汉语中,许多不同的文体都是由结构相似的语段组成的,文体的分类并不总是意味着语段结构或语言形式上的差异,而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学惯例等外在的力量。因此,我们只要弄清这些语段的基本结构和组合原则,大体上就可以理解汉语叙事文的一般建构原则了。
在各类叙事文本中,历史和小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两种类型。一般说来,历史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小说则是一连串的虚构。历史与小说之间的紧张,一直是困扰西方思想的一大难题,但在汉语思想中似乎并不存在,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在汉语中的区别也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彼此混同(比如各种野史和历史演义)。《史记》被誉为“实录”却大量采纳民间传说,大量采用文学手法,尤其是关于人物和事件之细节的描写,那些不可能为人所知的内幕却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左传》《国语》《礼记》《战国策》中的叙述也加入了大量的想象,比如关于骊姬害申生的故事,《左传》《国语》都有较为细致的描述,但却彼此不一致,显然存在着想象和杜撰的成分。
显然,尽管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汉语思想并未在二者如何划界这一问题上进行持久的努力。无论是真(true)假(false)之分,还是真实(real)与虚构(imaginary)之间的区分,在汉语思想中都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汉语历史文本,也并没有将记录事件当做首要目的。传说中的孔子删《春秋》,自比于《春秋》的《太史公自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都将历史叙事看做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材料,而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则往往并不在意。那些常见的人物传记,则经常使用小说笔法,文中的事件让人难以分清到底是虚构的情节还是真实的事迹。比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似乎是一篇传记,但作者对于传主的基本资料竟然毫无兴趣,关于传主的身份,文中仅有简略而模糊的交代,而“传主”郭橐驼的全部表现,就是在讲了一番种树的道理之后,又欣然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且不说一个种树的农民能否讲出这一番大道理,单是这文绉绉的措辞,就与传主的身份完全不符。同样,柳宗元的另一篇散文《梓人传》也未提供多少有关“传主”的信息,梓人的出场如同小说中的传奇人物,背景模糊而又举止怪异。而且,这个人物的活动仅仅延续了一个段落之后(实际上重复了第一段的信息),就从文本中消失了。接下来两倍于此的篇幅,都成了作者的借题发挥,与传主几乎毫无关系。而且,文本的后半部分也不再有叙事的成分,叙事已经完全被议论所取代。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也是如此,关于传主事迹的介绍仅占六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文章的主体部分是传主的两大段议论,结尾是作者的一番总结和引申。从这些形制短小的“名篇”可以看出,韩愈、柳宗元的叙事散文,与其说是在“叙事”,不如说是在“作文”,它并不关心“事”之本来面目,而只关心能否从中引申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以及如何令这种表达显得巧妙、得体。一方面,这里的叙事只是为主题服务的,所以只需点到即止。一方面,这些底层人物的语言,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文言,不仅十分文雅,讲究修辞(比如对偶的运用),而且雄辩有力,气势恢弘。苏轼的《方山子传》对于传主的描写与此类似,基本上是漫画式的、写意式的描绘,并无多少叙事成分,对于传主之生平事迹着墨不多,而对于其神态气质的渲染亦多从侧面入手,意在勾勒出高人隐士的形象和对于隐居生活的赞叹,实际上是一篇精心制作的“美文”,而不是真正的传记。
由此回溯《左传》《战国策》等早期叙事文本,那些可以独立成篇的片断(如《郑伯克段于鄢》)又何尝不是如此。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学者都从文章学的角度立论,往往倾向于发掘、解释、称赞这些叙事文本的表达技巧,因而忽略了这些技巧对于叙事的抑制和损害,也忽略了这些文本对于事实的过滤和遮蔽。
在《古文观止》中,“典型”的叙事文本的缺乏,当然与该选本的性质有关:它是一部“古文”选本,主要目的是供初学者入门揣摩文章作法,因此不得不尽量“简而该”,字数一般在千字左右,很难照顾到篇幅相对较长的叙事文本。然而,在那些被人们归入叙事作品的汉语文本中,最以叙事见长的历史文本也往往缺乏典型性。人们通常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看做两种不同的叙事类型,但这种区分其实源自西方,中国学术界虽然接受了这一区分,但在实际的文学史和历史研究中则常常并不认同,而是坚持“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算是一个旁证。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我们所认定的那些较为典型的叙事文本,其中的叙事成分也往往远低于我们的预期。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汉语叙事(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叙事)并不比西方叙事更缺少“真实性”,也并未更多地借助于想象来完成。但是,与西方叙事文本相比,这些文本显然更重视“行文”方面的技巧,而不是叙事的技巧,更不是所叙之事的完整、全面与真实性。尤其是在史传和篇幅较为短小的叙事文中,叙事中所包含的事实或史实一般都很少,叙事文本对“事”和“叙”都缺少足够的兴趣,而且文本中的事件往往并未构成一条紧密的叙事之链,而虚构性的想象、人物刻画、议论则大大超出了叙事的成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虽然十分繁复,但古代汉语文本的分类原则却不关心叙事、抒情、说理之分,而仅关心惯例和文本形式上的细微差异,这也说明汉语文本尚缺乏自觉的叙事意识,未将叙事文本看做是可与抒情文本和论说文本并驾齐驱的文体类型。
二、简洁、省略与过滤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汉语叙事文本缺少叙事成分的呢?是汉语句法的简单、汉字的表意特性,还是其他什么因素,似乎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因此,本文仅限于如实地描述,而对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暂且不予深究。
《左传》被刘知几誉为“叙事之最”,它对后世的影响既有叙事方面的(对于历史著作和小说),也有文章作法方面的(对于后世散文),但主要还是文章作法方面的: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②
言简事详不仅是《左传》的特点,也是后世史家的追求。如果考虑到《春秋》叙事之简略和笔法之隐晦远甚于《左传》等历史文本,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简洁和曲折是汉语叙事的两个显而易见的特征。让我们就从这一点入手,对汉语叙事的机制进行初步的分析。虽然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散文史都对《左传》和《史记》等著作的叙事技巧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但学者们也都承认,叙事在汉语文本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往往只是表达主题的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早期叙事文(包括《左传》和《史记》等)显得异常简略与拘谨,其叙事“在整体上常常是高度的概括与笼统,缺乏条分缕析的描述,未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生活”③,只能对事件进行简略、晦涩、大而化之的勾勒。叙事的简略(简洁),显然不能等同于真实。相反,越是简略的叙事,如果不能全力聚焦于事实,就越是容易有意无意地遗漏事实,从而使得所叙之事的意义随之扭曲。在汉语叙事文本中,这样的风险不仅随时存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虽然早期汉语叙事总体来说并不生动,但历史与文学的混同还是使得汉语叙事染上了浓重的文学色彩,因此,人们往往将这种文学色彩误认为叙事功能的强大,实际上是将文学效果混同于叙事能力。张卫中认为,“早期汉语在叙事功能上的薄弱不外乎两个原因,即词汇的相对贫少与句式的单调”④,词汇的贫乏是因为汉语缺乏外倾性,追求精练而不追求精确,而句式的单调使得“表达单调、拘谨,无力全面、精密、舒展自如地陈述事实,从而大大限制语言的表现能力”⑤。缺乏长句,叙事只能点到即止,使得事理无法伸直。在诸多正史当中,未有系统地叙述一代之大事者。由于形制短小局促,即使篇幅稍长,也只能重复相同的结构,而难以衍生出新的叙事方式。叙事乏力的结果,是深陷于“琐事”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了叙事方式的因袭。
任何叙事都是对于事件和事实的一种建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解释,但并非所有的叙事都会采用同样的建构方式。对事实的取舍、组合,往往取决于作者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动力和结果的认识;在阅读中,叙事方面的安排也会影响读者对于事件之因果关系的看法。《左传》叙事,对于事件发生的过程往往叙述得比较简略,而对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细节却十分重视。即使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五大战役,对于战役本身的叙述也十分简略。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不仅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作了交代,而且在叙述中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则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左传》还常常对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作道德化与神秘化的解释,记载了很多源自占卜、梦境、天象的预兆。这正如王靖宇所说:
对《左传》的作者来说,历史分明不仅仅只是一些事件的记录,为了使历史产生意义,事件必须像在故事里那样加以安排组织。像所有的善讲故事者一样,《左传》作者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他可以使用的全部修辞手法,以此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记叙春秋时代的写作意图。⑥
由于汉语难以建构长句,而短句在描述细节的时候不仅显得笨拙,而且难免啰嗦或跳跃,从而影响到叙事的完整性和语句的流畅性。实际上,汉语叙事文本在叙述一个事件或描述一个事实的时候,大都省略掉了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各种细节,而仅保留了少量的基本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汉语叙事其实是一种“梗概叙事”。如果其中出现细节的话,这些细节也不是以事件的基本组成部分的面目出现的,而是具有突出地位和特殊意义的部分。即使作者在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并无深意,它们也会在阅读当中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在相关事件的整体建构中获得重要的地位。《左传》中有不少琐碎的细节描写,比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皆为无关紧要的琐事;“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竟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都只是“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⑦,而无助于揭示历史真实。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尚且如此,以记言为主的《国语》和《战国策》就更难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了。因为“《战国策》专记当时策士纵横捭阖的奇谋诡计和谲诳倾夺的辩难说辞。这些记载往往并非实有其事,而只是假设主客问答,以表示作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加强其观点的倾向性和言词的说服力而已”,《国语》则常有“剪裁疏漏之处,存在记载琐屑、议论枝蔓的毛病”。⑧
《左传》等早期文本缺乏叙事能力,与汉语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申小龙认为,“在上古汉语中,连贯铺排的双段施事句占绝对优势,占双段施事句总数的95%。并列铺排的双段施事句只占5%。这表明上古社会的思维中将两个命题并置起来思考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⑨。而重在表达两个事件之间依存关系的耦合句在后来采用近代汉语写成的文本(如《水浒传》)中的大量出现,也主要是有助于文气的连贯,“它把对事象的描述两两相待而为一体(句),形成结构关系互为映衬的句法语义‘场’,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句型的组织空间,使汉语句法单位简洁而富于弹性……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拓开语文表达与理解的巨大空间,生出无数言外之景、言外之意、言外之情”⑩。叙事能力的欠缺虽然不利于描述事实,却有利于营造一种言外之意,因为正是叙事的简略,给读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空间。
实际上,早期叙事文所叙之事都十分简略,关于事件本身的信息并不丰富。一些有限的事件之所以能够组合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文本,往往是因为在叙事的缝隙之中填充了大量虚拟的人物对话,而那些缺少对话的文本则显得十分单薄,甚至支离破碎。《古文观止》所选叙事文大都如此。《郑伯克段于鄢》是该选本的第一篇,向来以叙事技艺高超而闻名,它讲述的事件大体包括:郑庄公与母亲之间的矛盾,庄公封弟时的预谋,共叔段的行动与庄公的反应,庄公克段并与姜氏决裂,母子和好。但就在这个文本中,人物语言及作者议论占去了大半篇幅。文中交代了故事的基本线索和梗概,但细节大都语焉不详。比如,武姜为何仅仅因为难产就讨厌大儿子,她是如何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两个儿子的,大叔与庄公之间的矛盾有何表现、如何激化,都只有简略的交代。在文字表达方面,这段文本也远未达到圆熟的地步。即使以第一段叙事的语句而论,由于多处省略掉了行为的施事人(“武姜”),这段文字的文气并不十分通畅,但如果按照僵硬的句法来补上所省略的部分,却同样会显得生硬。诸如此类的现象表明,简略是文言叙事不得不采用的策略。所以,即使在《虬髯客传》等知名的文言小说当中,叙事也有意无意地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而部分宋元话本和大量的明清小说,则因白话的介入而使叙事能力大为增强,对于事件、场景、人物行为的描绘在整个文本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篇幅。当我们继续考察早期叙事文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与《郑伯克段于鄢》相比,《周郑交质》叙述郑庄公与周平王交换人质的事件,更为简略。这段叙述仅用73字,而后面一段议论则用了98字。这种情形在其他篇目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如:《石碏谏宠州吁》记事91字,记言136字;《臧僖伯谏观鱼》几乎全篇记言,且所记臧僖伯的一大段言语皆为说理。《古文观止》所选《左传》其余各篇也大抵如此,而且这种情形在《左传》中具有普遍性。以记事闻名的《左传》尚且如此,擅长记言的《国语》和《国策》就更不用说了。
王靖宇主张从情节、人物、观点和意义等四个方面对《左传》等中国叙事文进行分析,但他发现前人“绝大多数是把《左传》当做‘文章’而不是叙事文来看待的”(11),他们特别注重分析文本中的用字、修辞和文章结构而忽视叙事过程。这种状况固然暴露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语叙事缺少“具有连贯性(followability)和先后顺序的事件记录”(12),而更多的是事件的排比罗列——当然,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就绝非“简单”的罗列。尽管人们可以凭借想象来“补足”省略的事实及其联系,但那毕竟是叙事文本本身所未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这种想象性的补充也更容易偏离事实,使真相发生扭曲。事实上,至今仍有学者认为,“《左传》作为史书,不属标准的叙事文学,与王氏所说的‘叙事文’不符”,必须在对各个要素的解析中考虑到“《左传》的意义即作者通过惩恶劝善的奖惩机制而恢复礼制”,才能提示出中国叙事文的特性。(13)
在汉语叙事文本当中,简洁来源于省略,而省略掉事件的诸多细节以及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非偶然,也并非完全无意,而是一种过滤机制。它所要过滤的,是事件的诸多可能的面目,以及对于事件进行解释的其他可能性。林语堂所说的“文言极不适合于讨论或叙述事实”(14),原因大抵在此。可以说,在汉语叙事文本当中,对事实的排斥和过滤是结构性的,而这些文本的作者是否有意回避、掩盖或过滤事实,已经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仅仅从虚构事实(尤其是细节)这一点上来看,汉语叙事文本并不比西方叙事文本更具有虚构性。在对事实缺失状况进行估价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些叙事话语所处的基本语境:几乎每一个字都需要借助于注解,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歧义。以过滤的方式来对事实进行重新组合,并最大限度地为想象和解释留下余地,这才是汉语叙事的特别之处。
三、记言、议论与叙事文本的意义建构
早期叙事文的简洁,与书写工具的笨重、简陋有关,但将叙事的简洁完全归结为书写工具的简陋,显然缺少说服力。正如前面所述,《古文观止》所选叙事文本在叙事的过程中或结尾处出现了大量的引用和大段的议论,甚至远远超出叙事本身所占的比例;而人物语言(对白)也常常占据文本的中心地位。这与叙事的简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耐人寻味。刘师培认为,“文章之巧拙,与言语之辩讷无殊。要须娴于词令,其术始工。词令之玲珑宛转以《左传》为最”(15),他所说的“词令玲珑宛转”虽不限于人物语言和作者议论,但一语道破了汉语叙事文之重视语言表达而轻视叙事的实情。
叙事文本的任务应该是记事,但汉语叙事文中的记言却常常“喧宾夺主”,这大约是从《左传》开始的。《史通·载言》篇说:“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由《左传》开创的“言事相兼”的写法后来成为了汉语叙事文本的基本特征。
《公子重耳对秦客》(《礼记·檀弓下》)一文就主要由四段对白组成:秦穆公劝说重耳抓住机会回国袭位;舅犯告诫重耳假装仁义;重耳按照舅犯的意思回答秦国使者;秦穆公赞扬重耳。而描述事件或动作的仅有“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和“(重耳)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两句。另一篇被编选者评价为“奇幻”的叙事文《杜蒉扬觯》有大量的动作描写,这些描写虽然很简略,但简略的描述中留下的诸多空白很容易引发读者的想象,因此显得生动、有力。不过,从全篇布局来看,这些动作描写都只能算是铺垫,其作用在于引出后面的对话。文中的杜蒉实际上是在以曲折的方式进谏,而作者也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从表面上看,作者仅仅按照时间顺序直叙其事,但人物对白所占比例如此之大,则让人无法相信作者仅仅是在叙事。因为,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对白完全可以一笔带过。对于描述事件而言,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冗余信息。
《左传》中的议论往往假托为“君子曰”“君子谓”“仲尼曰”,《史记》中的议论则为“太史公曰”,同时在大量的人物语言中也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对于有关事态的议论。在文末出现的议论,除了《郑伯克段于鄢》《周郑交质》之外,《左传》中还有不少篇章以类似的语句结尾,而《檀弓》《国策》也有一些议论性的结语和一些解释性的文字,如《曹刿论战》末尾曹刿对于战术的解释,其功能与前述之议论类似,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至于《国语》中的议论,可谓比比皆是。《史记》的本纪和列传部分则将这种以议论作结的方式固化为一种模式——先叙后赞,个别篇目甚至“以议论代叙事”(《伯夷列传》)。后来的各种正史乃至小说都受此影响,习惯于对事件或人物作出评价,尤其是道德评价。议论和引用在文本中的比例明显失衡,表明汉语叙事所关心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于事实的解释和重新建构。在《史记》之纪、传当中,结尾的“赞”“太史公曰”之类的评论有时会与叙事文的正文部分相矛盾,比如关于韩信的叙述与评论(16)。就叙事而言,我们可以将这些评论看做“窜入”的文字,但就文本的整体而言,这些评论却是无法分离的部分,而且往往更受重视。
可以说,在这些叙事文本当中,过多的议论和对白已经改变了文本的结构,使得文本由叙事文本变为一种介于叙事、议论与抒情之间的混合文本。这虽然与文本的性质有关(《左传》是对于经文的解释,同时又和《史记》一样属于历史著作),但只要我们把这些文本当做叙事文本来看待,就不能不认真对待议论和对白过多的问题。我们看到,虽然事件在汉语文本中并非无足轻重,但若和事件的意义相比,则事件本身的确要“轻”得多。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从《春秋》“断烂朝服”(王安石语)式的过于简略,到《左传》《国语》等著作的记言胜过记事,其间有一个不变的线索,那就是事实仅仅是构成意义的次要部件。对于事件的叙述不仅过于简略,而且总是伴随着叙述者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总是倾向于干扰叙事的客观性。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过滤的机制,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非个人化的道德情感和议论,而尽可能多地省掉了事实。
用极少的事实大做文章,并且能够做出绝妙好文,《古文观止》所选《史记》各篇叙事文都是典型的例子,对于因文献不足所导致的事实的模糊以及信息的贫乏,这些文本所采用的补救措施就是议论和抒情。
在《伯夷列传》中,仅有的一小段关于伯夷的叙述包含了兄弟相让、叩马谏武王和隐居饿死三件事迹,不仅叙述简略,而且其间多模拟人物语言,还收录了一段明显是虚拟的歌辞。即使是这样的一段叙事,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到三分之一,文章一开始就绕了一大圈,先叙述尧舜禹禅让故事来带出传主,后又花大量篇幅谈论颜渊及时世、引用孔子之言,且文辞华丽,情绪激昂。正如选编者所说,该文是“以议论代叙事”,“通篇以孔子作主,由、光、颜渊作陪客,杂引经传,层间叠发,纵横变化,不可端倪,真文章绝唱”。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该文确实成功地传达了作者的观念,修辞效果显著,但这种成功和效果却是以牺牲叙事的准确性、完整性为代价换来的。
《管晏列传》对于“管仲一生事业,只数语略写”(选编者注),而对于鲍叔牙事迹的渲染,所引管仲语录,以及语言上的讲究(排比、对偶)则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篇史传对于“晏子一生事业,亦只数语,约略虚写,与管仲一样”(选编者注),却花费了较多篇幅讲述越石父和御者的故事,尽管司马迁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但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这样的处理还是会让人感到惊讶。管仲和晏婴除了同为齐相之外,相隔百余年,几乎互不相干,管晏合传的理由主要在于该篇主题——朋友相知的可贵。正是为了突出这一主题,文章在结构上作了精细的安排,尤其是管仲自述、作者对叔牙的赞语、晏子轶事、作者对晏子的赞语和“忻慕”,使得文中关于管仲和晏婴政治事迹的记述反倒成为了陪衬,“通篇无一实笔,纯以清空一气运旋”(选编者评)。
《屈原列传》关于屈原事迹的叙述,仅包括简略的生平、被谗和两次劝谏失败,却插入了一大段查无实据的与渔父的对话和《怀沙》全赋。作者的议论则在该传的前半部分已经展开(“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一节),而且模仿骚体,铺排夸饰,文采斐然。全篇不仅不回避褒贬好恶,而且“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歔欷欲绝”,叙事已经为作者的感叹所压倒,全文成为了一篇带有叙事成分的借题发挥的抒情散文。
《滑稽列传》对于人物事迹的描述则更近乎小说,不仅细节的描绘显然是出自作者的想象,而且修辞手段起了关键作用——“一飞冲天”“道旁禳田”是比喻,淳于髡关于酒量的解释则铺张排比,句式整齐。这种描述的目的在于生动、形象地塑造人物的性格,而不在于如实地记录历史。
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出,即使是语言的表现力大为提高之后,汉语叙事也未注重详尽的事实记述和曲折的情节安排,而是极力发展了议论、抒情和修辞技巧。历史著作尚且如此,后世文人所苦心经营的各类散文(“文”)在叙事、议论、抒情的杂糅方面就更自由了。《古文观止》选录了28篇题中含有“记”字的散文,这些散文都含有叙事成分,但是否应该划入叙事文的范围,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者的议论,都是一种解释事实、重构真相的手段。当事实未能充分描述出来的时候,这种解释和重构的作用便更加突出。比如,将神话改造成历史,以及将现实中的人物加以神化,是中国叙事文的一个传统。前者如《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孔子对于“黄帝四面”的解释;后者如历代帝王传和《太平广记》中的人物故事。(17)无论是哪一种改造,都试图在神话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由转换的机制,从而在事实上掩盖了神话与历史的根本差异。事实的缺乏,更准确地说,是事件多而事实少,这在历代的正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开国皇帝的本纪,所述战争、兼并、统一天下的过程大都十分繁复,但少有细致描绘者,犹如流水账。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如果缺少史观的支持,难免支离破碎,满足于琐细史料的“实录”,而缺乏对事实的如实挖掘和深度阐释,最终流于泛泛而论。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汉语叙事文本与西方叙事文本的一个细微的差异,那就是汉语叙事对所叙之事总是信心十足,很少表露出迟疑。如果要在事实真相和圆满的解释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古人几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圆满的解释。当然,这种圆满仅仅是文字、形式上的完美,而非逻辑上的完满。比如下面对六十四卦之排列顺序的解释: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18)
这种环环相扣的解释,在令人惊叹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或者感染力。但这种力量与其说是来源于论证和解释的严密性,还不如说是源于汉语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程度。这种对于形式完美的追求,并不限于那些讲究节奏、韵律的骈俪文。在任何一种文体当中,只要有机会,这种形式上的追求总是会占据上风,比如对偶等修辞方式的运用就是一例。据统计,在《左传》等早期叙事文中,对偶的运用已经十分广泛,尤其是2-5字的小型对偶,它们使“行文得以整散有致”“议论得以严谨清晰”“语音得以抑扬顿挫”“感情得以鲜明浓郁”“文字得以含蓄蕴藉”“语势得以连贯流畅”。(19)不过,《左传》的句式和叙事虽然广受赞誉,但与后来的叙事散文相比,由于句式参差不齐,而又未及充分考虑节奏和韵律的问题,难免显得有些笨拙。在唐宋以后的叙事文中,对偶的运用更加密集也更加熟练,叙事也就更加受制于语言形式方面的需要了。
另外,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汉语叙事文本的特长也不在于叙事,而在于叙事之外的因素。在观点(视角)方面,汉语叙事不仅惯于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而且叙述者显然比西方历史著作中的叙述者更为自信。比司马迁稍晚的古罗马史学家提图·李维尽管“在写作时没有采取谨严的态度和批判史料的方法”,但在提到一则传说时却说:“对这种远古的问题,即使把或然之事当做真实,我也感到足够了。像这种宜于点缀戏剧的神奇性而难以令人置信的叙述,是既不值得肯定,也不值得反驳的”(20)。这种对于叙事的自觉意识,是不难从西方史学家那里找到的,虽然那些史学家也大量采用文学手法,但对于事实和叙事的重视远远胜过对“劝惩”之类的道德说教的重视。
在人物方面,汉语叙事注重塑造人物形象,但人物性格往往缺少变化,文本中缺少人物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的直接描绘,人物塑造多通过对话、行动和他人的评价来完成。在情节方面,主要采用线性的情节模式。在意义方面,更重视道德准则而非真实的细节。(21)诸如此类的特征,都让我们看到汉语叙事对于现实建构的巨大热情,以及对于事实本身的或多或少的冷淡。即使是到了白话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20世纪,我们还能看到古代汉语叙事的儒雅而冷漠的身影。文言词语及句式的使用,代表了一个文雅、含蓄的传统,它雍容华贵、温柔敦厚,却很难让人认清现实世界和表达真实的情感。在现代汉语的衬托之下,古代汉语叙事的过滤机制暴露无遗,而古代汉语叙事文本所提供的“冗余”信息也更加引人注目。在文言词汇逐渐被现代汉语词汇所取代的过程中,中国的官方文告及某些意识形态话语仍然保留并发展了那一套历史悠久的过滤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将古代汉语叙事的基本模式移植到了现代汉语之中。(22)事实上,从简略曲折的“春秋笔法”到《左传》等早期文本及历代正史中的事简言繁,乃至唐宋以后小说文本的铺张想象,汉语叙事始终都在借助议论和抒情来完成现实的意义重构,而将事实、事件和故事当成了意义重构的一种辅助手段。
注释:
①一般都是从散文史和文章学的角度立论,寻找这些文本的长处,比如认为《左传》记事的特点是叙述完整,文笔严密简洁,结构严密,记言委婉有力,等等。
②刘熙载:《艺概·文概》,《刘熙载文集》,薛正兴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③④⑤张卫中:《母语的魔障》,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00、109页。
⑥王靖宇:《论〈左传〉的修辞手法》,《<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⑧程千帆、程章灿:《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⑨⑩申小龙:《汉语语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371页。
(11)(12)(16)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1、19页。
(13)罗军凤:《文化和传统在“中国早期叙事文”中的迷失——对王靖宇<左传〉研究的批评》,《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
(14)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15)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17)参见朱迪光:《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及其对中国叙事文的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8)引自《四库全书》所收《子夏易传·序卦传》。
(19)参见何凌风:《〈左传〉对偶艺术之实证研究》,《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0)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2、167页。
(21)参见王靖宇:《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2)参见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
标签:古文观止论文; 史记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语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战国策论文; 伯夷列传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