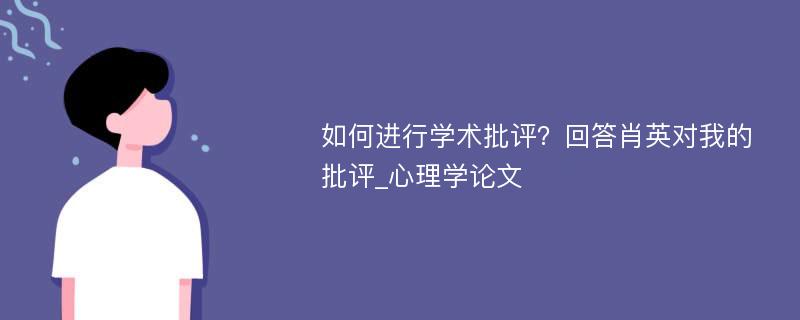
怎样作学术批评?——答肖鹰对我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学术论文,答肖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刊登了肖鹰所作《怎样批评朱光潜?》,专门批评我的著作《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据称原文长达12000字,将刊于《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作者愿意用如此大的篇幅对拙著作出批评,我很欢迎——如果学风、文风端正而非构陷的话。长文尚未见到,现在这篇短文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指出我的著作“学风、文风不端正”,这显然是批评者“独具只眼”的发现,因为此前所有的评审意见和公开发表的书评,几乎无一例外地称此书学风严谨、扎实,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书评者也是如此——当然,肖鹰先生出来以后,就有例外了——学风究竟如何,我只希望读者能够对照一下我的著作和他的批评文章,就自然能够明辨,不须我多绕舌。该文在否定了邓晓芒先生对《选择,接受与疏离》的评价后,先是说该书“有一些错误”,接着又说“包含了很多的错误”,继而写道:“我通过下面的讨论要揭示的是:《选择》作者不仅没有把握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没有把握克罗齐、尼采的美学思想”,但我反复寻找,实在没有找到他发现了什么错误,他是怎么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而我又是怎样理解错误了的,因此也令人无法比较他的理解与我的理解有何差别,他这种批评法恐怕是其独创的“空手道”和“无影脚”结合的批评新招式——那么他文章所谓的“下面”,看样子是要“下”到《文艺研究》的版“面”上去了——我视野狭小,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活用“下面”的,这就是他的“端正”的文风?该文认为我错误理解王国维、朱光潜的原因,是为了把他们作为例证展示我的西学东渐的“新”的阐释模式。他引述了著作结语的一段话,而那只是我研究得出的结论,并非既定的什么模式——他的引文也截取掉了更为重要的实质性结论——所以我建议读者读肖鹰先生的引文一定要对照原文读一读。
这个建议对于读下面这一段近乎构陷的文字更为重要,他所举的我学风、文风不端正的关键例证是“在《选择》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列入了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未置一词。但是《选择》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是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选择》第166-167页),与麦氏文章中相关论述的文字和观点都很近似(而且同样空洞)。(《新文学史料》1981/3,第244页)这使读者不能不意识到《选择》这部分内容与麦氏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王攸欣在《选择》正文中只字不提麦氏,如果不是学风问题,也是文风问题”。如此言之凿凿,甚至指示了具体的页码,如果不是对照我的著作和麦氏的文章去读,哪位读者会怀疑其真实性呢?肖鹰大概以为没有多少读者(包括编辑)会真正对照我的著作和麦氏的文章去读,才敢如此不负责任地大胆放言,不过我只须把这两节文字一字不易,一字不刊地过录如下,其论点必然不攻自破。以下是拙著第166-167页的关于《悲剧心理学》的全部文字: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的博士论文,对西方传统的悲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并综合成自己的结论,尤其致力于悲剧快感研究,这部著作作为第一部中国学者探索西方悲剧理论的专著,具有首创之功,而且本身也不乏灼见,原著用英文写成,直到80年代才译为中文,所以在中国学界影响并不大,但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本文并不专门研究该书的成就,为了本章主旨反而只讨论其失误处,请读者勿以为我们试图否定这部著作。《悲剧心理学》因其具体目标的关系,所以不像朱氏其他著作那么平易朴实,为了显示掌握资料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有时沾染了一点浮夸之气。如他在第一章说:“颇为奇怪的是,也许除了博克之外,他们都没有想到悲剧与崇高的美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叔本华和黑格尔都详细讨论过悲剧,也讨论过崇高,但都没有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18(原注:《朱光潜全集》第2卷,页215)这说明他并没有通读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该书第二卷第37节明确讨论了悲剧快感源于崇高:“我们从悲剧中获取的快感并不属于官能,而是由崇高引起的。”19(原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佩因英译本第二卷纽约1969版P.433)类此的失误还有一些,我们不论,关键在看他是怎样运用悲剧概念的。他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悲剧,甚至欧洲近代以来也已经无法产生悲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族和现代人的作品都不符合他的悲剧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他的,而是他接受的古典主义悲剧概念。他并不从现代的那些已被公认为悲剧的作品中去寻找悲剧性和悲剧精神,却抱定悲剧必然和不可知的命运相联系的想法,以此去裁判所有的作品,凡属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宿命感和悲壮感的戏剧、小说在他看来都是缺乏悲剧精神的,即使在我们看来比古典悲剧更为深刻,更具有悲剧感的现代名著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也不能称为悲剧——后者同时违背了他的悲剧与宗教不相容的观念。很显然,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唯理论的,他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和已经出现的现代作品中去重新确定其悲剧观念,却拿几个世纪以前形成的范畴去裁定发展了的经验事实,从整个悲剧的发展史看,就忽视了部分研究对象,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部分。这无疑损害了整个论著的价值。同时他又把悲剧概念与价值评价混淆起来,认为悲剧与伟大同在,所以不免感叹“悲居的缪斯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原注:《朱光潜全集》第2卷,页450)而暗示文学也日趋衰微,近乎末日了。可喜的是他并非总是执着于这种思维方式,写《西方美学史》的时代就已经改变了这样的观点,把一些中国作品和现代作品也算作悲剧了。
肖文“仅有的”一词,暗示我对《悲剧心理学》写得不够,这说明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论题,也没有注意我在这段文字中的说明,论题既然是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研究,克罗齐很少论及悲剧,我为什么一定要花很大篇幅在《悲剧心理学》上?这一段是为了论述朱光潜具有唯理倾向的思维方式,才谈及其《悲剧心理学》的,因为朱光潜的悲剧观念,恰可作为唯理倾向的例证。肖鹰所指麦克杜哥的原文如下(按:前一句引自243页):
朱光潜的论点是,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悲剧的样本。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同印度人和希伯来人一样。和欧洲流行的东方宿命论相反,不能真正欣赏命运的作用。“(引文略)”朱光潜然后向他的西方听众同样片面地叙述了中国文学:“(引文略)”朱光潜未能显示出中国严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相互作用,他又不乐意在这种情况下区别悲剧的形式和精神,因而导致他发出了一些夸大的空泛议论:“(引文略)”
我们很想这样答辩:俄底甫斯的婚姻本来就有意义要使观众震惊,不过中国戏剧确实没有和希腊戏剧完全相似的范例。站不住脚的是这种言外之意,即中国文学全然缺乏悲剧精神,朱光潜不承认像杜甫这样的悲剧诗人和《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小说是非常奇怪的,特别是鉴于他后来把道德上的崇高归功于希腊民族的议论:“(引文略)”
朱光潜关于近代悲剧的讨论也是有错误的,他同样立足于信奉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和他早期的关于方法的声明相反,他求助于理论而不是求助于悲剧的典范。朱光潜认为尽管基督教和孔子学说一样,“是不折不扣地和悲剧精神相敌对的”,可是“基督教的衰落并不与悲剧的复兴一致。”在近代,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引文略)”
面对着这样任意地歪曲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看到在朱光潜的理论中除了可能不妥当之外,毫无疑问还有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他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得知朱光潜了解易卜生、奥尼尔和梅特林克的作品,似乎把他们看得很高。在这同一范围内,他还为传统的中国戏剧辩护。很可能在这里朱光潜想要表现他对中国传统的客观态度,(有迹象表明他对西方关于东方人物的概念感到恼怒,虽然他不幸又画出了另一幅漫画。)他对中国和当代文学的傲慢态度可能也是由于学院中的趋炎附势引起的。他所受的大学教育大半忽视了当代的著作,并且大半忽视了艺术中的非西方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回到中国后这些态度很快丢弃了。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朱光潜总结了他的发现,首先是艺术的性质,其次是悲剧的特性。“(引文略)。”
如果不是怀有偏见,会认为上引两段文字有血缘关系?两段在文字上确有惟一的一处相似,那就是划线那两句,都有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这三个词,即使是这一句,句式、语法、三词外的其他词都完全不同,而且两段文字都是转述朱光潜本人的话,如果肖鹰读过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第12章的话,他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该章第2小段说:“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420页)如果转述研究对象的话,有几个词相同,就认为是“存在血缘关系”,那任何两部研究同一对象的著作之间都会存在肖鹰所谓的血缘关系了。朱光潜否定其他民族和近代悲剧、小说具有悲剧精神,是他的《悲剧心理学》的突出观点,我和麦克杜哥都注意到了,但她只是就其悲剧观来谈,则是就朱光潜的思维方式来谈的,就对朱光潜悲剧观的概括而言,我们完全是以不同的文字来概括其同一观点,指出其问题,如果真正差别很大的话,要么是她概括不准确,要么是我概括不准确了。而事实上,我今天才对照这两段文字,发现除了我们对《悲剧心理学》的总体评价不相同外,对朱光潜观点的具体评价也差别甚大,她对朱光潜关于近代小说、电影排挤悲剧女神的论述,认为是“任意歪曲当代文学”,而我认为“他把悲剧限定在戏剧范围之内,虽然也是固执古典悲剧的概念,却是可以理解和赞同的”;她认为朱光潜这种悲剧观念在他回到中国后很快丢弃了,而我认为他到写《西方美学史》的时代,才抛弃了这种思维方式。更令人惊奇的是,上述引文的其他绝大部分文字讨论的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肖鹰不知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没有理解把握的能力。我并没有特别看重麦克杜哥的研究,为什么不能不置一词呢,书末的参考书目中还有相当多的著作我也“未置一词”,按他的方法,只要有几个词相同就存在血缘关系,肖鹰为什么不去寻找更多的“血缘关系”?
肖鹰反复强调我对朱光潜的错误理解是因为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两位外国学者撑腰”,这其实是把他自己的不良心态投射到别人身上,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对朱光潜的研究,都有他们的长处,沙巴蒂尼作为意大利哲学教授,对克罗齐理解相当深入准确,麦克杜哥对朱光潜学术经历的研究也确下了很深的功夫,但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观点,在总共两处提及沙巴蒂尼时,一处持批评态度,另一处持保留态度。沙巴蒂尼认为朱光潜是“移西方之花接道家之木”,而我批评他说:“沙巴蒂尼认为朱光潜是借克罗齐概念来发挥道家的人生观,并非毫无根据,但我们认为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尤其王夫之)的观念都最多和叔本华的纯粹直观一样是导致朱氏误解克罗齐直觉的因素之一。写《文艺心理学》时,朱光潜的主观意图确是介绍西方美学,而不是沙巴蒂尼所说是为了移西方之花接道家之木。”(拙著第130-131页)肖鹰为了论证他的“臆断”,竟然连我看待沙巴蒂尼的观点和态度都没有领会,这样的水平和心态能够作学问和学术批评吗?朱光潜并不太难懂,但是肖鹰先生以如此理解力去研究朱光潜的话,我劝他应该再慎重考虑。
肖鹰指责我没有读过《美学》英译本,却摆出很有研究的样子。确实,我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译本,我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过,可惜没借到,但我也实在并没有“摆出很有研究的样子”(见拙著第八章,第196页)。克罗齐《美学》是意大利文写的,英译本只是译本之一,朱光潜认为错误颇多,1940年代,朱光潜参照英译本和意大利原文本第5版,仔细译了原理部分,此后又作了修订,对研究朱光潜来说远比英译本重要,朱光潜对译名有反复的说明,事实上我也还懂点英语,知道译名尤其是某些已经学界讨论的关键性概念可能出现的问题,难道研究朱光潜中译本及其研究成果就只是“用朱光潜批朱光潜”,不可能得出超出于朱光潜的结论吗?那任何研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研究恰恰在比较朱光潜的不同译文和他自己的说明中,得出了新的结论——很多学者觉得令人信服,并表示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