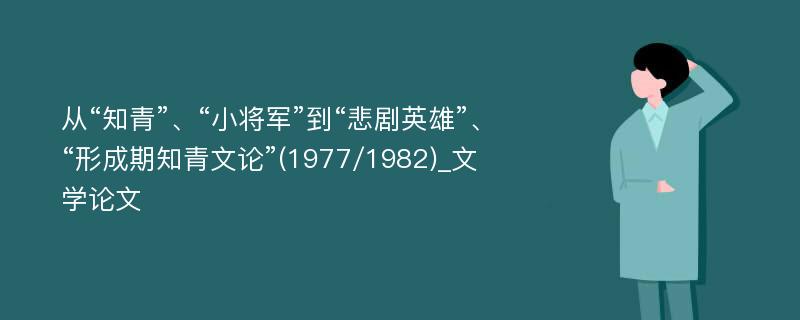
从知青——小将到悲剧英雄——成形期知青文学论(1977~198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小将论文,悲剧论文,英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知青文学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现象之一。它一般被看成是由知青作家所写的,反映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识的特殊的文学现象。这种看法实质上认为存在着一个先在的实体性的知青代际主体。这一代际主体不仅为广大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所认同,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所指认,而且也成了本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知青文学研究的一般前提。尽管上山下乡运动早已停止,变化了的社会也早已把过去的知青吸纳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作为某种类流派性的知青文学现象也已在80年代后期结束,然而“永远的知青神话”并没有消解,而且还借着“老三届文化热”,在90年代初中期再次泛滥。(注:参见戴锦华《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钟山》1995年第2期。 《“老三届”文化热透视》,《东方》1995年第2期。 姚新勇等《“老三届”文化现象批判》,《青年探索》1996年第6期。)难道说, 真的存在一个超时代而存在的知青代际主体吗?(注:此种超时代性最为典型且也颇为滑稽的是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此书后所附知青运动大事年表,竟然列有90年代的《中国知青部落》的首发式等其他活动。)其实,这是很可疑的。阿尔都塞、拉康、福柯等人都早已从不同角度质疑了主体的实体性存在。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理论来看,由知青文学呈现出的、并被社会普遍指认的知青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特征,就是那种提供给每个知青个体(也包括其他个体)去体认、去认同的“主体类型”。它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包含多样性成分的意识形态表象体系的制造物,它的出现既是多种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又是统治阶级借文学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规划主体的结果。它既以其社会存在性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招募具体的主体,同时通过对具体个体对它的指认而得以维持。对此我们可以用70年代以来的整个知青题材的文学写作加以证明, 不过这是一篇短文所不可能承载的, 所以在此我只想对1977~1982年左右的知青题材小说进行一些分析,由此揭示新时期知青主体和知青文学的意识形态成形史。
由于从伤痕的控诉到回归的梦怀已成为对初期知青文学发展的最一般的描述,下面我将围绕着对它的解构来展开讨论。
二
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应该从何时开始讨论新时期知青文学。无疑发表于1978年8月的《伤痕》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起点, 但是我以为应该将《分界线》(注:张抗抗:《分界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这类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写作作为历史考察的起点。因为它们以其特有的文革政治话语制造了一个知青—小将主体类型,这构成了知青主体类型意识形态转型的客观历史前在,或曰逻辑的起点;而《伤痕》不过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中继点而已。(注:现有的知青文学论从三个方面涉及了《伤痕》之前的知青题材写作:一是主要从题材的相关性着眼(如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二是注意到新时期初期的知青题材作品与前期同类写作模式的相关性(如赵园《地之子》);三是以知青代际身份想当然地将前后两段衔接起来(如郭小东的一系列知青专论)。不过他们实质上都是把《伤痕》看成是知青文学的崭新开端,并由此而正式讨论知青文学。)下面的分析将会逐渐证明我的观点。我们还是稍微来看一下这种知青—小将型作品的大致特点。
与同期的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一样,文革型知青文学具有一套僵硬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化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层面的意义指向:主导层面指向文革话语的中心意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附属层面展现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的故事,即红卫兵小将—知青这种合二为一的青年怎样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故事。在这种叙事模式中,知青—小将这一形象虽然也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主体类型,但由于其所属的文革高强化性政治叙述话语,严重击伤了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不仅文学的形象性被抽干,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赖以发挥功能的主体的自主、自我、自由的幻觉性被基本否定了,知青—小将这一主体基本就成了一种干瘪的类政治符号的存在。这种政治符号性身份,早已在文革中后期就不被大多数知识青年所接受,可它仍然在1977~1978年上半年占据着知青文学的一统天下(甚至它的一些简单变形的作品到了1981年还存在)。例如在我所查阅到的发表于1977~1978年上半年的9篇知青小说中, 至少有5篇都属于这种典型的“文革型”知青作品, 而其他几篇也未能摆脱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成长的意义指向和叙述套式。(注:这9 篇作品是:《丹梅》、《高高的红石崖》、《北大荒人物速写》(分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3、7、11期),《额吉卓尔的女儿》、《铁鹰》(分载《内蒙古文艺》1977年第2、6期),《柿树林中》(《汾水》1977年第3期),《一日官》(《广东文艺》1977年第3期),《向春辉》、 《阿衣古丽会计》(分载《新疆文艺》1978年第1、2期)。)当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知青与之斗争的对象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们,原先那些被批判的人物(如老干部、搞生产干实事的人)被赋予了正面的意义,另外阶级斗争的调子有所缓和。
三
从1978年下半年起,知青题材的写作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当然与“伤痕文学”有直接的关系。80年代有关伤痕型知青文学的评论,几乎都是强调它的抑制不住的愤懑之情,强烈的控诉情结,普罗米修斯式的彻底的反叛行为。(注:唯一例外的是许子东的《当代文学中的青年文化心态》(《上海文学》1989年第6期)。 但它只是单部作品的个案分析,而且未突破“代”的前提。)这些几无差异的描述,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具有高度性格一致性的群体意象(也即一种集体主体),它似乎自然地衔接起了从愚昧到愤然觉醒的主体的跳跃性转变,抹去了这个转变过程中意识形态选择的纷杂性,将一个大写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神圣的英雄主体矗立在人们面前。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与知青题材相关的伤痕写作既不专属知青出身的作家,而且从知青主人翁在“伤痕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功能来看,更不存在这种整齐划一的愤懑的青年一代。
根据我的查阅,可以把“伤痕型”知青作品分成三类:第一类,知青主要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的角色为他人或社会苦难的诉说而存在;第二类是知青自身的苦难经历的展示;第三类是前两类的混合。第一类作品主要是由非知青出身的作者所写,仍然还可算是前述知青文学的沿袭,也即知青人物虽然在表面上是作品的主角,但写作的意图和作品的实际主题,并非指向知青,而是针对其他人和事。不过,由于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的大幅度变化,知青在此类作品中所承担的功能大为复杂化了,不再仅仅是叱咤风云式的知青小将了。他们或者在被展示为可怜羸弱的苦命人之时,被间接曲折地充当着“右派”苦难命运的承载体,如《蓝蓝的木兰溪》(《人民文学》1979第6期)中的肖志君; 或者借着他们恋爱的选择与冲突,间接展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政治风云,如路遥的《夏》(《延河》1979年第10期);或者以知青的苦难为引子,正面描写1976年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暴露“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凶残,讴歌周恩来总理,如岑桑的《躲藏的春天》(《花城》1979 年第2期);或者将知青生活的刻画、命运的选择同对陈景润式的知识分子的歌颂,对当时社会特权化现象的批判相结合,如张斌的《青春插曲》(《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与新的知青主体类型成形关系更为直接的是第二类作品。细读自《伤痕》开始的伤痕型知青题材的作品,不难看到在知青的自我苦难的诉说中,隐约存在着一种历史变异的线索,即由更近于哀怜式的、祈求宽恕式的忏悔与苦难伤疤的展示相交织的诉说,到激烈愤懑的控诉。前一种诉说大多出自1978年底和1979年,而后一种控诉多属1980年之后的事情。我们不妨大致排列两个作品系列:
一、《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上帝会原谅》(《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苦难》(《红岩》1979年第1期),《爱的权利》(《收获》1979年第2 期), 《殊途同归》(《收获》1979年第4期),《在小河那边》(《作品》1979年第3期,以下简称《小河》)。
二、《黑玫瑰》(《花溪》1980年第1期), 《无果的花》(《红岩》1980年第1期),《聚会》(《北京文艺》1980年第2期),《燃烧的爱情》(《上海文学》1980年第2期), 《阿勒克足球》(《十月》1980年第5期),《红棉几时开》(《北京文艺》1980年第12期, 以下简称《红》),《火的精灵》(《当代》1981年第3期, 以下简称《火》)。
《伤痕》开启了第一系列作品的基本叙述指向:制约故事情节发展的矛盾纽结就是那些曾在文革中犯了罪的青年,能不能够被允许重归曾被他们唾弃了的家。作者知道他们犯了罪,但他要以他们犯罪时的幼稚和无知,更要以他们在农村所遭受的身心折磨,来洗刷他们的前罪,得到他人的宽恕,从而来争得(求得?)重归城市,重归生活的权利。以现在习惯的思维来看,上述作品可说是都表现了红卫兵一代出身的知青作者的共同忏悔和急于摆脱文革“原罪”的心理,反映了一代人共有的思想意识和情感症结。然而上述作品并无刻意的代的提示,更没有以一代人的名义来称谓知青,甚至连主人公的知青身份都有些模糊不清。而且作者相当注意与这些不幸的主人公“划清界限”。《小河》题记中的“我们”、“他们”的区分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到了198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种祈求宽恕者的形象,逐渐被淡化,而被愤懑的控诉者所替代。比较一下张抗抗和孔捷生的两组作品:《爱的权利》和《火》,《小河》和《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点。《火》里作者不再让代自己而言的主人公以某种半伪装的身份和不很明晰的角色出场,而直接还原其红卫兵—知青的身份。虽然全篇也充满了祈求他人、社会原谅自己的情感,但主人公岳米达不再像舒贝那样被动地等待着别人施舍爱的权利,而是以烈火来烤炙自尊的心灵,将祈求性的忏悔尽量地转化为自恕性的忏悔。而且人物活动的场景也从明媚欢快的城市海滨,推移到了原野山林中,从而使主人公免去了落伍的可怜相,增添了几分粗犷的豪迈。更有意味的是颜冰这个对照性人物的设置。她集红卫兵、无辜受害者、宽恕施舍者三种身份于一体,通过最后与岳米达的会合,将原先交予外界的宽恕权和再生权,想象性地收归为自己一代来掌握。而且作品结尾之前,主人公岳米达基本都是以代词“我”来引导意识的展开,而到结尾时,则通过与颜冰的对话,将代词“我”转换成了“我们”。同样,《小河》的主人公还是有着沉重的负罪心理,还是希望被人理解和原谅的。而到了《红》这种心理几近全无,代之以一种孤愤的、饱经风霜的、骄傲的自我倾诉。与此相一致,《红》不再以生活中的悲剧故事来打动读者,而将情感作为基本的叙述旋律结构全篇,故事情节则被切割成一些片断性的材料。所以作品就不仅采用了第一人称书信体,而且由于情感主旋律构架配之以浓郁的诗化语言,因而更为接近诗体小说。然而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种孤愤的、自我情感的诉说,严格地说来,并不是主人公对一个个体的他者化的自我分裂体进行倾诉或对话,而是在向自己的一个同体、一个战友、(甚至)一个情人在诉说。这样,这里的自我既是与一定主体性相连接的自我,也更为直接的是一种群体性认同的自我。这同《火》是相同的。正是通过这种同辈人之间(或说向同辈人)的诉说,作为单个个体的红卫兵—知青,才与自己的群体达成了认同,或者说促成了一个群体性镜像的诞生,使他们在这个群体性的自我镜像中,去发现自我,确证自我,建立起既直接属于一个群体的又直接属于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
上面的论述显然隐含了一种从被叙述的知青向知青的叙述的视角转换。然而我们不能把这种转换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代人主体意识的逐渐的自我苏醒。很简单的一个反证就是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该作已经将自传体第一人称全知叙述引入了知青题材的写作,冲破了全知第三人称叙述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它还通过对母亲的歌颂,不无自豪地讲述了一个知青变为草原之子的故事,而且这种歌颂和讲述又与大自然的审美异质性发现比较和谐地糅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它既与传统扎根话语拉开了距离,又避开了乞诉哀怜式的忏悔,还与以后知青小说的大自然审美趋向和叙述语态遥遥相关。
四
如果说伤痕型知青作品不仅仅是一代人觉醒后的控诉,同样知青文学回归潮的出现,也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互动的产物。
第一是它与传统“扎根”话语的关系。关于这点需要以城市—乡村何处为家这个角度切入。从50年代文艺作品反映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之时起,城市与农村何处为家的选择就是这类题材作品的母题(或曰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矛盾纽结),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沿袭性,其基本主题意旨就局限于表现知识青年如何扎下根来的,可名之为“扎根”话语。不过根据其具体表现形态又大致可划分为前文革期和文革期两大类型。前文革期的主要表达模式为:一方面用知识青年在农村生产、科研上的活动与成绩来表现他们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另一方面又以他们个人或家庭生活方面的干扰性阻力来表现他们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不易。约在1979年之时,用这种母题来构造知青故事的作品还继续存在,尽管它们主要刊载于边缘性的地方性杂志上(只有一篇刊登在《人民文学》这样有全国影响的期刊上),应该承认,当时由于“伤痕文学”席卷全国,这些作品被人们忽视了,但是其中有些作品已对传统的知识青年扎根山乡边疆大有作为的意旨和表达模式有所突破,还蕴含了后来知青文学回归主题特定呈现方式的转化性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更需要》(《新疆文艺》1979年第6期)。 它比较明显地涉及了知青大返城事件,这显然是属于新的内容表现要素。但是作者则是以两个传统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处理的。一是个人要求的小道理服从支援边疆的大道理(这更靠近前期“扎根”话语),二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然而此时中央和地方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已在显性社会舆论层面上难以彻底掩盖;作者已不可能再理直气壮地完全按照传统知青作品的模式来处理去留问题了。这样作品就出现了多方面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大道理上,作品借正面主人翁之口一再强调知识青年支援边疆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以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否定这个方向。但既然承认了工作中有许多问题,而且也承认了有成批的上海知青坚决要求返回上海,那么这正确的大方向就显得空洞无力了。而且更有趣的是,扎根派的正面典型周晓薇反对丈夫回上海,劝说他留下来的第一席话竟是这样说的:“我倒是想回,就怕上海装不下”,“我们上海家里的条件到底有多好……真的回去了我们住哪儿?往后还怎么给家里贴补?况且我们两家都有兄弟姐妹,撇开国家利益不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到底是留在这儿,还是回去对家庭更有帮助?”不难看出,该作品实际已更为直接地切近了当时现实中存在的知识青年的思想与生活问题,而且至少也比较明显地涉及了两年之后《本次到站终点》(以下简称《终点》)正面展开的情节内容;另外也更为及时地将知青大返城运动纳入了创作视野。这些都是在当时那些重点期刊中难以直接发现的。
可是进入1980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与“扎根”话语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作品,全面出击,在地方性杂志和中心刊物上同时出现,而且一批日后的主流知青作家,都同“扎根”话语发生了关系。我们不妨列些作品以资为证:
季冠武《回城》*、李国文《车到分水岭》*、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以下简称《西望》)、王安忆《从疾驰的车窗前掠过的》(分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5、6、10等期),张承志《青草》(《北京文艺》1980年第1期),陈村《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张宝发《月亮小镇》*、越峻防《我们寻求幸福》*、陆星儿、 陈可雄《留在记忆中的长辫》(分载《上海文学》1980年第3、4、8、12期), 何鸣雁《洁白的山茶花》* (《当代》1980 年第2 期), 孔捷生《那过去了的》(《花城》1980年第6期)。
上面标*号的作品表示与传统“扎根”话语关系较为直接,它们把“扎根”话语的叙述模式同新的内容要素和表达手法进行直接嫁接的意图更为明显,由此造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张。这样就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话语转型期特有的不成熟性。严格地说,一直到1982年止,试图这样嫁接的作品都失败了, 包括陆天明的《啊, 这一夜》(《新疆文学》1980年第7期), 尽管它比《终点》还要早地直接涉及支边青年回城后的生活困窘与情感矛盾。不过他的《野麻花》(《十月》1982年第5 期)和范小青的《飞扬的尘土》(《文汇报》1982年6月17 日)或可算是仅有的例外。它们较为成功是因为其基本叙事结构和内容更为疏离“扎根”话语,将扎根问题做了更为个人化的处理。回城还是留乡,返回内地还是呆在边疆,不再主要是服从党和祖国的安排和号召的问题,而基本成了主人公的自我选择。相较而言,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陈村这些更“标准”的知青作家,则与扎根话语模式的告别来得更早更利索,上面提到的他们所写的作品也显得更为早熟一些。例如《从疾驰的车窗前掠过的》,完全放弃了传统的表达模式和主题展开的角度,将临别情怀掩藏于平淡而琐碎的乡村小事和平凡人物中,零散、点滴、跳跃、复沓地细密道来,流溢出悠深而略近苦涩的伤感。你很难再把这类作品看成是扎根作品,但亦不能否认两者间暧昧的关系。
第二,让我们从更为切近知青返城后生活的作品来分析。这类作品大都涉及到了返城后生活对知青主人公的挤压,这常被看成知青回归意识产生的关键因素。但作者对这种生存压力处理的意义指向却不仅仅是回归,而是多方面的。例如甘铁生的《现代派茶馆》(《花城》1981年第5期)和叶辛的《追回青春》(《十月》1982年第4期),就很明显是想以这种挤压为契机,一方面表现他们这一代人的乐观、自信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又为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新出现的个体经济编织合法性依据。而这后一点显然溢出了单纯“知青”的观照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大都用旧的情感观念来处理社会的经济生活变革所带来的矛盾。如甘、叶两人就是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和思维模式来为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根据,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变成了简单的传统善恶对立的冲突。在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中,易杰的那种更近于西方19世纪反城市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的对现实的愤懑不平,使其似乎带有了更大的叛逆性与自主性,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说孔捷生达到了一种美学水平的超拔,达到了知青话语和知青主体的成熟期水平,但却仍在诸多层次上大大落后于社会历史水平所要求的意识高度。再如王安忆的《终点》和孔捷生的《普通女工》都是以并不具有思想洞察性或情感穿透性的个人视角去观照一个家庭、一个小组,而且在具体的表述上,又都从人际关系情感上着眼。这样现实经济利益的利害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琐细的情感磨擦和不畅,最后,问题都通过主人公对一种温情与关怀的发现(或说是拟想)而得以化解。从社会学的认识功能来看,它们遮掩了真实的社会矛盾性;而从美学审美功能来看,虽然比不成熟期的知青话语来得更为含蓄、和谐,可列为最早的一批知青经典文本,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张爱玲从平凡、从琐细升华到人的存在的凄艳的悲剧性孤独体验之境界。
出乎意料的是蒋子龙和王润滋这两个非知青作家却贡献了两篇非同寻常的作品:《宝塔底下的人》(《延河》1982年第4 期)和《赎》(《北京文学》1981年第12期)。它们相当直接而集中地表现了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落在社会个体头上的经济压力与生存压力,而且就把情节、结构的枢纽定位于此,相当严峻地表现了个人在新的经济变化面前束手无策的困窘。不过虽然这两篇作品显示了当时知青作家的作品所缺少的内涵,但它们显然都是针对知青,而且就是针对易杰、慕珍这类知青而发的,这与前面所谈及的其他身份的人写知青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从侧面证明,到了此时,新的知青主体类型已基本成型,并为普遍社会意识所认同。
行文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知青文学回归潮根本不是继“伤痕文学”而来的1981年才出现的历史现象。以往的观察视角,实际上以一个天然自主的群体性历史意向的审美选择的自由性,掩盖了它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既情投又叛逆,既谋合又超脱的复杂关系,掩盖了所谓的回归潮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多方策动性。
五
我想进一步分析一下《西望》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 以下简称《土地》)对知青悲剧英雄主体最后成形的意义。尽管《西望》写的是文革前发生的故事,但其实际上是第一篇更为成功地将祈怜式知青叙说,转化为愤懑式申辩叙说的作品。这表现了它与前期作品的联系;但是它又通过知青自我苦难的他者化而疏远了它们。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更为显性的“反思”视角的引入,不仅直接接通了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新动向的联系,(注:此期当代文学正显出较强的反思意向,如王安忆的《苦果》和王蒙的《蝴蝶》等作品。)而且以这种新的具有某种俯瞰性的位置,开启了成熟期知青作品的历史超越性意向。所以,应该把它看成集转型与成熟于一体的中介性作品。
《西望》中苦难的他者化是很明显的,它就包含于叙述主人公自我苦难的诉说和对张种田的悲剧性奋斗生涯的观照这两者之间的互渗性关系上。被推出在文本空间前场的张种田这个落伍了的老革命的悲剧奋斗史,正提供了知青生活性悲剧史向美学性悲剧史转换的契机。作品通过理想主义的桥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把前者的光荣辐射到后者身上,从而遮盖这一代人过去的丑陋。张种田在新时代的落伍,本来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但因其光荣历史、因其理想主义的操守而染上英雄暮年的悲剧色彩。当这样一个过时了的英雄被历史抛弃时,“我”,这个知青的代言人,却以浓彩为他涂抹了一幅落日晚霞的泣血之景,(注:参见“风停了……金红色的世界,像一道闪电,就要滑过去了,就要消失了”这段描写。)悄然地把严峻的历史反思,更多地转向某种对命运不公的感慨。这时读者很可能就已将对张种田的同情与对知青一代的同情联系在一起了,从而为“我”对张种田的反思而敬佩,为“我”对他的理解与宽厚而感动。这时,原先伤痕型知青作品中那个软弱的祈求宽恕的苦难者,就被一个占领了新历史制高点的反思者取而代之;原先那个生活悲剧的苦难承受者,就大大接近于审美悲剧的主人公。
然而,尽管如此,《西望》还是终究因与历史的直接联系而胶着于历史,还未从既存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形象化、定性化了的历史中“彻底”超拔出来,成为真正的悲剧英雄。只是到了梁晓声的《土地》,知青文学才达到了历史的重返—超拔的共时性畸变。所谓重返是指由于现实的矛盾和压力而重新去审视历史,通过对历史的新的解释而超越现实的困窘,达到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这一点是新时期以来知青文学的基本历史指向。但是在《土地》之前,知青文学所重返的历史,基本是一种具有现实真实性外观的历史,基本是与人们意识中所习惯认为的那种具体的生活表象的历史相一致的,是人们惯常认为的真正发生了的历史。而《土地》则不同,它不再去再现这种具体“真实”的历史,不再去通过重返历史去审视知青一代人的命运。相反,它把知青们从文革的社会历史中迁移出来,置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超历史的大自然空间中,或说是一个拥有了不同具象性的特殊的历史天地里,从而从粘着的历史事物中摆脱出来,赋予知青一代超历史的象征性存在。正是在这时,知青和历史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种审美的畸变:历史的知青变为了知青的历史,前一个历史属于社会学、政治学范畴,而后一个历史则成了艺术审美的对象。在这个审美对象化了的历史中,他们不用再去扮演可怜的祈恕者,也不必再煞费苦心地去编写他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块垒,他们甚至也都不必去摘取历史反思者的桂冠,而只需在自己创造的历史舞台上,上演属于他们自己的正剧,扮演悲剧英雄的主角。这时候知青就从命运和历史的被主宰者,变成了自动的献身者,进而将意志指向为自己命运和历史的主宰者的意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看上去似乎是无所傍依的,超越了时空的一代人才真正站立了起来,以知青——一个共同的名字——向世人宣告一个大写的人的诞生。(注:由于篇幅限制,有些比较重要的作品没有涉及。另外,对知青文学回归潮与“新时期”文学大自然审美发现间的知识—权力的共生转换关系也未加详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