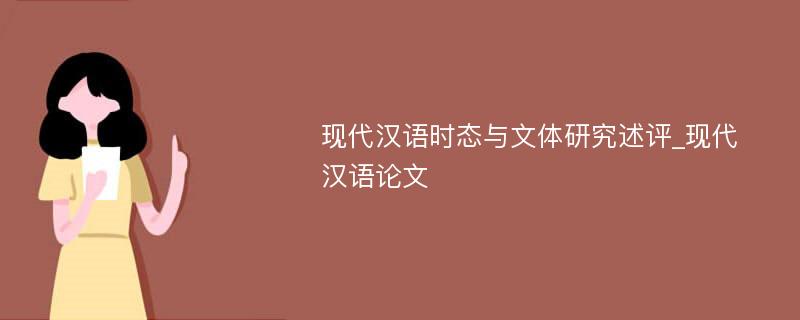
现代汉语时体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现代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也称时制,tense)和体(aspect)是同语言的时间(time)性密切相关的两个语法范畴。通常认为,时侧重动作或事件发生的时间,体侧重动作或事件的进程。现代汉语的时和体能否构成独立的语法范畴我们姑且不论,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现代汉语的时体问题确实有着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其一,汉语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屈折形态,因而更多地依靠广义形态和分析形式来表现时体意义;其二,时体意义对时体形式的选择具有灵活性,两者不是一一对应的;其三,时意义、体意义往往共用一个语法形式,相互纠缠,难以区分。正是以上特点给现代汉语的时体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正因如此,它才引起了语法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对现代汉语时体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借以理清头绪,交换意见,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现代汉语时体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20年代到70年代末为初探阶段。这一阶段时间跨度较大,开始以借鉴西方的语言理论为主要特点,其间经历了较长的缓慢发展过程。从80年代初至今为发展和深化阶段。这一阶段充分重视了汉语自身的特点,不仅在语言事实的发掘上有所突破,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独到的建树。
一、初探阶段
早在20年代,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已对时体问题有所涉及。基于与英语语法的比照,黎氏认为“后附的助动词”(如“了”、“着”、“起来”等)可以看成“表动作完成或进行之动词词尾”,而“动词‘时制’(tense)的变化,依靠‘时间副词’和‘助动词’的参伍活用”。这实际上是把时间副词和助动词看成与英语的词形变化相应的时体表现手段,即时体标记。
此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从汉语的个性特点出发,对汉语的时体问题作了更为细致的论述。王力(1943)认为汉语“着重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究其在何时发生”,因此汉语有“体”(王力称为“情貌”)而无“时”。王氏归纳的情貌类型和各类的语法表现形式与当时的其他归纳相比更具合理性和概括力,为后来的很多学者所接受。吕叔湘(1942)从表达论的角度对汉语“时间”和“动相”的表达方式作了详尽描写。吕氏认为汉语的时间观念依靠时间词来表示,而“动相”(即“一个动作的过程中的各种阶段”)主要依靠一些意义虚化的限制词(如“将”、“方”、“已”等)和专门起语法作用、近于词尾的词(如“着”、“了”等)来表示。他还逐一分析了汉语的“三时”、“十二相”、其中改造“三时”观(把“现在”、“过去”、“将来”改为“基点时”、“基点前时”、“基点后时”)和明确区分“绝对基点”与“相对基点”,为后来时意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高名凯(1948)的时体研究颇具建树 ,他不仅强调了时与体的区别,而且充分阐述了汉语有“体”无“时”的观点,明确指出“汉语没有表时间的语法形式”。
五十年代后期,汉语“有体无时”的观点受到了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雅洪托夫和国内学者张秀等人的挑战。龙果夫(1952)认为汉语的语尾兼具表体和表时功能,可以看成体·时标志。他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汉语时范畴的两大系统——过去时系统和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系统。雅洪托夫(1957)也肯定了汉语时范畴的存在,指出“汉语的时间范围……是由于附加的体意义以及部分地由于能愿的细微意思而复杂了的时间范畴。汉语动词的时,和许多其他语言动词的时一样,是混合的体—时范畴”。张秀(1957)认为汉语没有绝对时制,而有关系时制(即相对时制),因为汉语的关系时制有其相应的语法表现形式。尽管三位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即汉语不但有体范畴,也有时范畴。这一观点在当时未能引起语法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对后来(特别是新时期)的研究者颇有启发。
以上述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汉语时体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1.理论探讨占优势。初探期的研究侧重对西文时体理论的引进、消化、改造和汉语时体框架的建构,包括对时、体内涵的界定,关于汉语有无时、体范畴的争论以及对汉语时体基本格局的初步构拟,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色彩。其中关于汉语有无“时范畴”的理论探讨对后来的影响尤为深远。王力、高名凯等的“汉语有体无时”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一观点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2.时体框架的建构缺乏客观标准。学者们对汉语时和体的初步认识不尽相同,而真正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未开始,这使得早期汉语时体框架的建构带有较大的主观任意性,各家创立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归纳出的时体类别、时体数目和时体形式千差万别。比如,王力归纳的体类型有七个,分别为普通貌、进行貌(“着”)、完成貌(“了”)、近过去貌(“来着”)、开始貌(“起来”)、继续貌(“下去”)和短时貌(重叠);赵元任的归纳与王力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个“不定过去态”(“过”);吕叔湘把体归为十二类,略显庞杂,有的类可以合并;高名凯归纳的体类型中还有结果体(“着zháo、住、得、到、中”)和加强体(同义词连用)。
3.具体描写相对薄弱。早期的研究立足于汉语时体基本框架的构拟,因而具体描写显得比较薄弱。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时体类别、时体形式的简单归纳和概括说明上,缺少专门针对某一时体类别、时体形式的深入描写。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单篇文章也讨论了个别的时体形式(注:如俞敏(1952、1954);黄盛璋(1952);林裕文(1959);王还(1963);李人鉴(1964);范方莲(1964)等。),但大多只是对它们的语法意义和用法的浅层分析,距离深入细致的描写还差得很远。
初探阶段的汉语时体研究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基础,建构汉语自身的时体范畴体系,虽然还谈不上深入和系统,但汉语时体基本框架的建立为后来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某些体形式(如“了”、“着”、“过”、动词重叠)也逐渐得到了公认。
二、发展与深化阶段
现代汉语时体研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后,到8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深化。这一阶段的成果较多,也较为集中和突出。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评述。
(一)对个别时体形式的深入描写
对个别时体形式的深入描写是这一阶段时体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学者们在前人构建的时体范畴体系雏形的基础上,对几个主要的也是人们公认的时体形式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描写。
对时体形式的描写,除了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82)以及几部虚词词典性专书外,更多地体现在单篇文章中。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说明。
(1)对单个时体标记的研究。有的文章侧重对体标记的语法意义的重新审视:刘勋宁的《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1988)对当时的流行看法即词尾“了”表“完成”提出异议,认为“了”的基本语法意义是“实现”;而王还在《再谈现代汉语尾“了”的语法意义》(1990)中对刘文提出了商榷,指出不能把“完成”与“完”等同起来,“完成”不一定意味着结束;黎天睦的《论“着”的核心意义》(1989)运用标记性理论和核心意义分析法分析了“着”的核心意义——“惯性”,并指出其准确意义和功能是由与之连用的动词的类别决定的。有的文章侧重对体标记的句法分布情况的考察:刘宁生的《论“着”及其相关的两个动态范畴》(1985)考察了“着”的分布与动词性质的关系;李兴亚的《试说动态助词“了”的自由隐现》(1989)则从全句着眼,探讨了谓语动词、副词、时间词、数量短语、结果补语等一系列句法因素对“了”的分布情况的制约。此外,刘公望(1988)、费春元(1992)、卢英顺(1995)等也从不同角度细致考察了单个时体标记。
(2)时体标记之间的比较研究。孔令达的《关于动态助词“过[,1]”和“过[,2]”》(1986)首先分析了“过”的两种语义——表完毕(“过[,1]”)和表曾经(“过[,2]”),然后比较了它们与“了[,1]”、“了[,2]”的结合能力以及它们对句式的选择;刘月华《动态助词“过[,2]”“过[,1]”“了[,1]”用法比较》(1988)从语法意义、使用场合和句法结构特点等三个方面系统地比较了“过[,2]”“过[,1]”“了[,1]”的异同;类似的文章还有房玉清的《动态助词“了”、“着”、“过”的语义特征及其用法比较》(1992)等。而陈刚(1980)和赵世开、沈家煊(1984)通过与英语相应的体形式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汉语体标记的特点。
总体看来,对时体形式的研究越来越注重语法、语义、语用的结合,而这种多方位的考察促进了研究向纵深和精密化的发展,但仅有这样的描写还不够:“点”毕竟代替不了“面”,考察个别的时体形式永远也把握不了整个时体系统的全貌;同时,有些文章偏重于具体事实的描写,而在理论阐释方面似嫌不足。
(二)理论探索与事实描写相结合的系统性的研究
1.系统性 王松茂早在80年代初就对汉语的“时范畴”和“体范畴”作过比较系统的讨论。他归纳了十种体类型和五种时类型,并详细分析了各类的语法表现形式。尽管他的时体观难免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认为体形式是动词之后的辅助词和重叠式,时形式是在动词之前的时间副词),但就研究的系统性而言,确为当时学者所不及。
随着系统观念、体系观念的深入人心,汉语时体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陈平的《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1988)从系统观点出发,分析了现代汉语时间(注:这里的“时间”指一种广义的时间性因素,不同于所谓的“时意义”。)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时相(注:“时相”是动词的词义所包含的时间性特征,不属语法范畴。)结构、时制结构和时态结构,目的是“为全面阐释现代汉语中与时间性相关的语法现象建立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文章虽未对时制和时态作重点分析,但提出的某些理论见解颇具启发性:一是强调了时与体分开处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是认为汉语时制的语法特证在表现方法上具有隐蔽性;三是在方法论上主张从大的系统出发,通过系统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联对比来把握考察对象的性质,具体到时体研究,就是把时和体置于整个时间系统框架中进行考察。尽管陈文的某些观点还值得商榷(注:如陈文认为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是一个语法范畴”,龚千炎(1995)、左思民(1997)等对此持不同意见:竞成(1996)、李铁根(1996)等则认为三元结构并非处于同一平面,“时相”是上位概念,不宜与“时”、“体”并列提出。),但他的系统观念和从整个句子的时间性特证着眼的研究角度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和创新,因此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龚千炎为陈平的时间系统框架填充了丰实的内容。他的《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1995)是第一部全面论述现代汉语时间结构系统的专著,也是一部对时、体系统进行综合考察的专著。书中逐一分析了时间系统的三维结构,其中对汉语最为发达的严密的时态结构论述尤细。此外,该书注重考察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时制对时相的选择、对时态的限制以及时态同时相、时制的对应关系等)和子系统内部成分之间的配合情况,试图揭示汉语时间结构网络的全貌,这与陈平的主张是一致的,而龚千炎在这方面作了更多的具体工作。
陈平、龚千炎都是以整个时间结构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而有的学者则单就某一个子系统(时系统或体系统)进行了考察。戴耀晶的专著《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1997)深入考察了汉语的体系统。书中采用语义分析法,详细讨论了完成体和非完成体两大类中的六种体,对每一种体形式所反映的体意义都提取了数项语义特征,从而以简明的语义概括驾驭了各类体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特别强调了时、体范畴与时、体意义的区分,指出前者总是与一定的形态形式相关,而后者则可通过词语形式、形态形式、语调形式、格式形式、言语环境及说话者心理等各种手段来表现,因而在任何语言中都有所反映。明确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澄清长期以来人们对时体概念的模糊认识。相对而言,时的系统研究比较薄弱,原因在于“汉语有无时范畴”始终是研究中的敏感问题。在为数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李铁根的《“了”、“着”、“过”与汉语时制的表达》(1997)很值得注意。李文肯定了汉语“时”的语法表现形式的存在,并对三个主要时标记的表时功能及它们在各种句法位置上的使用情况作了全面考察,指出“了”、“着”、“过”作为绝对时标记时,都表已然,与未然相对;作为相对时标记时,“着”表同时,“了”、“过”表异时;它们都是既能表时又能表体的语法标记。此外,李临定(1990)、石毓智(1992)等学者也分别考察过汉语的时、体系统。
2.理论性 80年代后期,学者们的理论意识大大增强,除了上面提到的论著外,一些侧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也开始陆续出现,如马庆株的《略谈汉语动词时体研究的思路——兼论语法分类研究中的对立原则》(1996)、张济卿的《汉语并非没有时制语法范畴——谈时、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96)、左思民的《现代汉语的“体”概念》(1997)、《现代汉语体的再认识》(1997)等。也有的文章虽不是专门讨论时体问题的,但其中也提出了对时体或时体研究的个人见解(注:如邓守信(1985);竞成(1996);郭锐(1997)等。)。这些理论探讨不仅涉及到“汉语有无时范畴”之类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涉及到时体研究的思路、方法等,对于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时体,拓宽研究思路,改进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思路 这里的“意义”,属于逻辑概念范畴。90年代的研究注重从汉语中时间性因素(时意义、体意义)的表达入手,探求时间观念的各种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开放型的研究思路,可以引导我们对某个语义范畴的各种表达手段及其相互关联进行多维的探讨,从而最终建立起这一语义范畴的表达方式体系。就“时意义”的表达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少数文章外,更多的文章是探讨“时意义”的词汇表现手段(时间词、时间结构、特定句式等)的(注:如李向农(1994);金昌吉(1996);刘叔新(1997)等。),而语法手段、词汇手段和其他手段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时制观念的表达方式体系。这种研究思路是对传统的单纯从时体形式分析时体意义的研究思路的开拓,也是与系统观念相辅相成的。
(三)研究中的争议焦点
随着时体研究的深入发展,“汉语有无时范畴”这个长期以来的敏感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涵盖了对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的看法分歧。
1.对“时”、“体”本质属性的不同理解。多数学者认同传统说法,即“时”、“体”是属于动词的语法范畴,研究“时”、“体”,要从谓语动词的语法形式着眼;有的学者则把“体”理解为语义范畴概念,认为句法上的“体”具有民族性,而语义上的“体”具有普遍性,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注:参见张黎(1996)。);还有的学者主张从三个平面的角度来理解“体”,即“体”是一个语义—语法—语用概念(注:参见左思民(1997)。)。同样,如果从语义角度来理解“时”的话,自然得出汉语有“时”的结论。由此看来,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时”、“体”概念,同时注意表述上的严密性,避免将“时”(或“体”)与“时意义”(或“体意义”)混为一谈。
2.对时、体范畴的不同理解。多数学者认为时体属于形态范畴,应由动词的形态成分即围绕或附着于动词的虚化语法标记来体现;而有的学者理解的时体范畴较宽泛,它既可用形态成分表现,也可以用特定的语法格式表现。无论哪种理解,都要满足语法范畴形成的基本条件,即系统性和各个语法意义在语法形式上的对立性。从目前的研究看,形态成分在表时体方面显然更具系统性。
3.对“了”、“着”、“过”等体标记的表时功能的不同看法。作为公认的体标记,“了”、“着”、“过”是否兼有表时功能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们表时兼表体,只是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而对此持否定意见者居多:有的认为它们是专用体标记,根本不表时;有的认为既然它们充任了体形式,就无法同时充任时形式;有的认为体标记所含的时意义是非常次要的附带意义;还有的认为体标记的表时功能缺乏一贯性、系统性,很多场合是可用可不用的,因此不能视为时标记。
4.对“曾经”、“已经”、“正在”、“将要”等所谓的“时间副词”的性质和功能的不同看法。在“时间副词”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们应看成词汇形式还是语法形式?一种意见认为,这些词都是实词,具有词汇属性;另一种意见是,所谓的“时间副词”已部分地虚化为语法形式了,只是虚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其二,它们究竟表“时”还是表“体”?将以上两方面的分歧综合考虑,只有肯定了它们作为语法手段的表时功能,才有可能得出汉语有“时”的结论。
“汉语有无时范畴”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需要对很多问题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在这些问题尚未弄清之前,我们不可能作出定论。
除了上面的争议焦点外,在对个别词语(如“起来”、“下去”、“了[,2]”、“来着”、“的”等)的归类定性和时体类型的划分等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而时体术语上的分歧更为严重:有的叫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把“体”叫做“时态/态/时体”;也有的叫“动态助词/形态词/词尾/动词后缀/动词语后缀”等,多少反映出个人对体标记性质的不同理解。但术语分歧毕竟不利于学术的交流,统一有关的时体术语是非常必要的。
三、结语
现代汉语时体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的系统性和解释力也在逐步增强。但是应该看到,时体问题毕竟是研究中的难点,很多相关的语法现象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和合理的解释,甚至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加强对各种相关语言事实的深入探讨。对于目前尚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语言事实出发。比如对“时”的问题,很多具体的考察工作才刚刚开始,各种与“时”相关的语法现象还有待充分的描写和解释,这是解决“汉语有无时范畴”这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基础环节。
2.放开眼界,拓宽思路,多向多维地研究。可以结合方言来研究时体,既能从中受到启发,又能验证或补充我们的某些想法;可以从语用的角度、动态的角度研究时体,对时体标记的使用情况和意义改变等作出合理的语用解释;还可以从句子自足的时间因素的表达入手来讨论时体标记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有的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3.坚持系统的普遍联系的研究观点。不仅要考察时、体系统在整个时间系统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要看到它们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联以及系统内部成员间的密切联系,比如联系句子的情状、动词的内在时间性等来研究“体”;对体系统(或时系统)内部各类体形式(或时形式)之间的共现、替换、连用、嵌套等情况作全面考察。
4.注意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的结合。归纳的时体类型应该是意义与形式结合的语法类,也就是说,每个时体小类都必须有相应的语法表现形式,这样才能体现出类与类之间的对立。没有语法形式的证明,仅根据意义分类就会多少带有主观色彩,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建立完备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时体系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5.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海外一些学者(注:如屈承熹、李讷、戴浩一、谢信一等。)在汉语时体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很值得学习和借鉴,如从语用、认知功能角度来研究时体。今后还应加强与海外的学术联系,关注时体研究的新动向,充分吸收和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加快汉语时体研究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