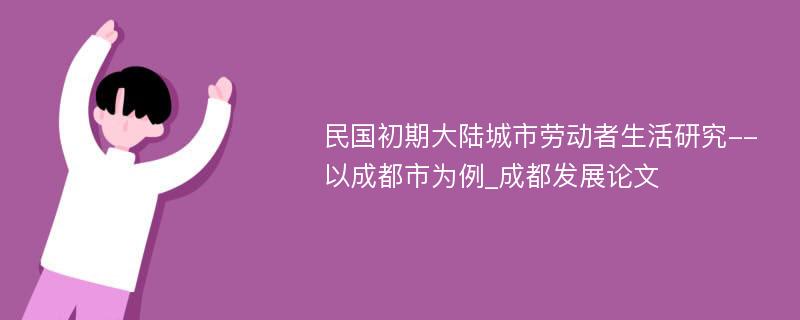
民国前期内地城市工人生活研究——以成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论文,为例论文,民国论文,工人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应地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工人群体开始崛起并逐步发展壮大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对工人这一近代城市中的重要社会阶层的相关研究已有很多,然多集中于近代工业较为发达之地区,对近代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和缓慢的内陆地区则涉及较少。成都作为重要的内陆中心城市,民国以降,其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变迁亦自有其特色。本文即欲对抗战前成都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作一个初步考察,以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广大内地城市中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及其对城市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一、抗战前成都工业发展与工人构成
成都的现代工业虽然从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起步,但成都因远离技术源、资金源和人才源,又非工业原料生产地,兴办工业难度较沿海城市为大;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成都的工业发展非常缓慢。而从民国初年到30年代中期,四川战乱频繁,更是严重影响到成都工业的发展,故在此20余年间,成都的现代工厂寥若晨星,到30年代中期亦不过70余家,而真正有一定规模者仅17家。据统计,成都市17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共有职工1864人,仅占全市人口的0.41%,占第二产业人数的3.1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是手工业者[1]。由此可见,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都工业仍集中于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传统手工业,现代机器工业十分稀少。手工业占绝对优势乃是其时成都城市产业结构的一大特色。基于上述因素,本文中所述之“工人”并非仅限于现代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个包括产业工人、传统手工业者、佣工乃至苦力等在内的广泛的工人群体。这可能也更为符合时人对“工人”的界定。在1936年进行的一项成都各业工人统计中,统计者即将其按职业工会分为了七大类,即:机械工人、手工业工人、交通工人、运输工人、制造工人、佣工工人和杂业工人[2]。而他们皆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根据193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其时成都市共有工人205954人[3]。而当年成都市人口总数为440859人[4]。这样,其时成都市工人就占了全市总人口的46.72%,如果除去失业人口和非劳动人口,工人在成都市的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为可观。因此,对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或许可以一窥其时成都城市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生存状况。
二、工人的工作状况与收入
其时成都各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村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前者多从事苦力,如人力车夫、运输工、佣工等,后者则多分布于手工各业。抗战前的四川,由于拉丁派款,天灾人祸所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而城市则因其拥有的较多的从业机会而吸引了大量破产农民的涌入。据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所作的调查可知,在全川64县中,有154837户农民离乡迁移,占总农户的6%。其中,迁往城市(包括逃难、做工和住家)的农民占全部迁移户的61.1%[5]。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自是首当其冲。从1939年所进行的成都市牙刷业工人调查中可以看到,在141名职工和学徒中,其籍贯为成都的仅有38人,占总人数的26.95%,其余人员则来自省内其它地区[6]。此外,在1935年所进行的一次成都市人力车夫生活调查中的309人中更只有23人的籍贯为成都,其余均为省内其他市县[7]。以上两例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都对于省内各地劳动者所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时成都城市工商业发展较为缓慢而使得它对劳动人口的消化和容纳能力有限,出现了大量过剩的劳动人口。这样,无论是由农村来的破产农民,还是原来的城市居民,广大的工人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低廉的工资待遇而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以求温饱,并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1931年成都市各业工人工作时间与工资一览表
业别 每日工作时间 平均月得工资 业别
每日工作时间 平均月得工资
(小时)(元)(小时) (元)
兵工厂1020
造币厂 1110
机械厂1114
棉织业 11 7
绸缎长机 11 7
生绉业 10 6
绫纱业10 7
纺织业 12 4
成衣业10 7
理发业 10 7
金银饰1012 服装 1010
茗工 10 5 泥工 10 6
木工 10 6 雕工 10 7
油漆 10 7 懈工 10 6
石工 10 6 厨工 10 7
屠案 10 7 锡工 1010
牛骨业10 5
饭店业 11 7
面食业12 6 笔业 11 7
印刷 1114
色染业 1010
治铜业11 6
丝烟业 10 8
制帽业10 8
制革业 10 8
靴鞋业1010
制花业 10 6
铁货业10 5
纸柴业 10 6
钱纸业10 6
刀剪业 10 6
机关杂役 11 7 平均 10小时30分弱 8元弱
(资料来源:《苦矣成都市的工人》,《社会导报》第1卷第6期,第25-28页,1931年6月15日。)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工人们的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甚而长至12小时,其平均工作时间为10小时30分,其劳动时间之长,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而工人们如此辛勤地工作所换来的工资待遇却是十分低下的。上表中也有统计,工人们的平均工资尚不及8元。而1931年成都市食米的平均价格维持在每石30元左右,由此可见工人工资水平之低微[8]。虽然工人们多由资方供给膳食,或许亦为工资的一部分。而从当时的印刷业调查中可知,“伙食普通多每日两顿,三顿者,仅有一二家”,由此可见,此部分回报实为有限[9]。而根据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21个行业中285700名工人工资的调查,其中男工平均月工资为17.52元[10]。又如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全国29个城市工资调查,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5.43元[11]。可见成都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上海等发达地区,甚而还低于全国各城市的平均水平。虽然成都地处素有天府之国之誉的四川,物价水平较低,然1932年间,一名成都平民“每日生活费,亦在三角以上”[12],以一家四口计,以成都工人的工资水平,单凭其一人之力显然是难以养家糊口的,因此,普通工人家庭不得不依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业人口的收入来勉强维持,同时,由于收入的低下,一般普通工人家庭往往不得不让未成年的子女去当童工、报童、小贩,甚而从事苦力劳动。在1939年所进行的成都市牙刷业工人调查中,年龄在14岁以下者占了总人数的52.48%[13]。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工人家庭在内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家庭出于生计的需要而不得不把年幼的子女送去当学徒。而1932年的成都《平报》更曾报道称市内各人力车公司多招用幼童出外拉车,最小者只有10岁,故市政府特训令工务局,严禁15岁以下之幼童拉车,违者则会追究各公司,以维人道云[14]。工人阶层生活之艰辛跃然纸上。
此外,工人们还要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如据成都《新新新闻》1935年的记载,当年入春以来,成都商业极其疲滞,手工业多紧缩范围减少雇工,工人失业者甚多。棉织与丝织两业失业工人已达五千人以上,缝纫业失业亦不下四五百人,其他如染房街之骨货工人,东御街之铜货工人,亦多无工作可作,铁路公司三倒拐鞋铺,全街铺户一百余家除学徒外,雇用工人不及十人,由此可见一斑,其他行业工人失业者更不知若干[15]。由于其时成都工商业发展的不景气,商号、工厂之裁员与倒闭时有所闻,工人们亦自是朝不保夕,时时面临失业的危机了。
三、工人家庭生活
工人们的家庭生活也相当困苦。如前所述,工人收入的低下决定了他们的家庭规模不会过大,且生活是极其贫困的,其家庭的消费水平也是极低的,“他们的工作不外乎求温饱而已”[16]。
家庭规模通常指家庭人口的容量。据1928年内政部的调查,21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户规模为5.14人[17]。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状况是决定家庭结构和人口多少的一个主要因素”,收入相对低下的工人等城市社会阶层的家庭规模也就相应较小[18]。据近代社会学者的调查,中国几个主要都市中贫民家庭的平均人口都在4-5人之间(注:根据《成都市牙刷工业与工人生活概况调查》中对其时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都市中贫民家庭的相关统计可知。)。成都工人家庭规模也大致如此。
1934年成都市劳动负贩界之人口数目与家庭大小表
业别 小贸 车夫 棉织 长机 成衣 理发 木工 泥工 金工 饭食 茶工 平均
平均每家人口 4.5 3.1
7.6
7.2
4.7
5.1
3.6
3.3
8.1
6.6
3.2
5.18
平均每家成年 3.5 2.45 6.46 5.83 3.66 4.26 2.82 2.63 6.20 5.37 2.52 4.15
男子单位数目
(资料来源: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第8页,第1表,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研究丛刊第五号[19]。)
上表或可对我们了解其时成都各工人家庭规模大小提供一定帮助。不过,由于上表中家庭人口统计,除亲族外,尚包括雇工在内,而棉纺、长机等手工业作坊中多雇佣工人,故其数据所反映并非完全为平常意义上之家庭,而诸如小贸、车夫者因无需雇佣工人,故被统计的家庭人口应多为一般意义上之家庭成员。综合多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推测其时成都工人家庭规模以4人左右者居多。而其时成都商贾店主界和军政教育界的家庭规模则分别为6.52人和6.47人,皆高于工人家庭。同时,上表中还反映出其时成都工人家庭中成年男子比例极高,这应“因为收入低微的家庭中不能生产者或不必要居留城市者,均居留乡间,以省开支”之故。这电是近代城市中出现的一种家庭小型化的新趋势。
此外,由于经济条件欠佳,生存环境恶劣而造成的人均寿命过短,婴儿死亡率过高也应是工人家庭规模不大的原因之一。20世纪20-30年代,成都工人大都居住于御河、后子门一带垃圾堆边的棚户区,卫生条件及其恶劣,瘟疫时有发生。如1932年8月10日上午6时至9时,仅3小时,因死于霍乱的出丧户即达34起,多为穷苦之人[20]。工作劳累,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精神压力大,也使得广大的工人群体极易受到疾病的侵扰。从对141名成都市牙刷业工人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其中仅有60.99%的工人身体堪称健康,其余则或有病痛或有残疾[21]。而工人所患之疾病多有如下几种。
1939年成都市牙刷业职工及学徒疾病种类
类别 肺病 生疮 发热 腹痛 肝病内病总计
人数 22985
2
1
47
百分比
46.7919.1317.0210.614.342.11
100.00
(资料来源:《成都市牙刷工业与工人生活概况调查》,《成都市政府周报》第22、23期“专载”,1939年。)
从上表中可知,在其时成都牙刷业工人所患疾病中所占比例最大者为肺病,而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此一病症几为不治之症。而在其时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之下,一些极为平常的病痛都极有可能使人丧失生命,因而当时工人阶层的平均寿命是较低的。对于抵抗力极弱的儿童而言,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以1935年对成都市校工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为例,在142个校工中有87个是有子女的。在87个当中,有53个是死亡过子女的,生产数与死亡数相较,大概可以说是生两个死一个[22]。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工人阶层儿童的高死亡率,而它对工人阶层家庭规模的扩大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工人收入的低微也使得工人家庭节衣缩食,生活水平极为低下。根据测定生活水平的恩戈尔定律,如食品消费所占比例越高,则生活水平越是低下。而其时成都工人阶层的生活费分配有如下表所示。
1937年成都市劳动负贩界每成年男子所消费各类物品之价值百分比
物品
食物类 衣着类 房租类 燃料类 杂项类
总计
百分比 63.342.65
12.968.00
13.05100
(资料来源: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第26页,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研究丛刊第五号。)
从其中食物类消费高达63.34%可以看出,其时成都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广大工人往往“只求一啖饭地,以暂维生,于愿已足”[23]。因收入有限,工人们的大部分开支均用于基本衣食所需,甚至连衣服费用都很少,绝大部分都用于食品与燃料。
据调查,1929年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开支中食物、房租、衣着、燃料和杂项等所占比例分别为53.2%、8.3%、7.5%、6.4%和24.6%[24]。根据恩格尔定律:生活水平直接与食物、房租、衣着、燃料、娱乐教育等杂项这五类支出比例有关。食物费所占的比例随收入的增高而递降;房租衣着与燃料的比例,不随收入的增减而变化;娱乐教育等杂项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的增高而递升。从成都和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的比较中不难发现,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中食物费所占比例远低于成都工人家庭,而杂项费用比例则接近为成都工人家庭的两倍。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显然远高于地处内陆的成都工人家庭,他们更能享受到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从各类杂项消费中则可以一窥其时成都工人家庭的生活观念和消费方式。
1937年成都市劳动负贩界每成年男子单位杂项消费价值之百分比
类别日用嗜好
教育 娱乐 交际
医药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12.11
16.17
6.05 0.84 7.51 16.93 40.39 100
(资料来源: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第46页,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研究丛刊第五号。)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日常杂项的消费中日用、医药等满足生活必需的项目占了较大比例。而杂项中的另一项较大的花费为“嗜好”,即指烟、酒、赌博等不良习惯,这主要是由于工人们生活苦闷,加之他们多迫于生计而失去上学的机会,文化水准普遍不高,缺乏正当的娱乐以消解疲乏所致,当然也与其时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密不可分。根据《国民公报》1931年所援引的成都市工会的统计,全市工会会员中“工人识字者仅占五分之一稍强,而吸烟者竟达五分之二以下”[25]。而在杂项中教育所占比例仅为6.05%也反映出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是显然不足的,这在他们的子女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在1935年对成都市校工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可见,在被调查的校工子女中,学龄儿童108人,而其中未入学者达49人,占了总人数的45.37%[26]。总之,贫困及对教育的忽视使得工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往往偏低,这不仅会对其时成都的人口素质形成影响,也使得广大的工人子弟在将来的择业及社会流动中也往往会重复父辈的道路。
四、结语
通过对抗战前成都市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的数量、工人的工作状况与收入、工人的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其时成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而收入则极为低微,受其所限,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是十分低下。其时成都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应该代表了最广大劳动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一方面成为了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生存的压力以及对社会不公平的激愤的累积也使得他们容易产生变革的呼声。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自发式的斗争到建立自己的组织,成都市的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广大的工人阶层也成为了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总之,民国前期成都市工人阶层开始崛起并逐步走上社会的政治舞台,为成都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也是民国前期广大内陆城市工人阶层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