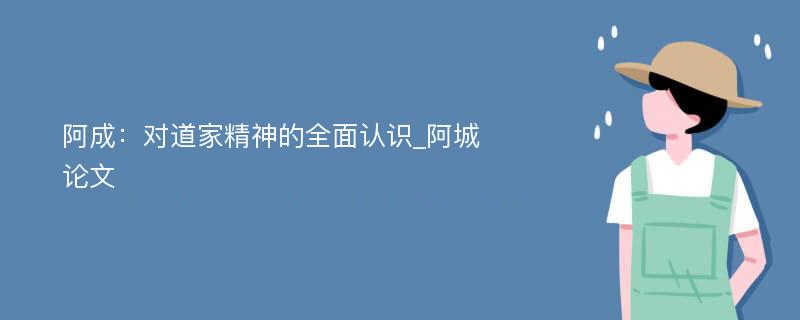
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城论文,道学论文,体认论文,完整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20(2002)01-0038-07
一
阿城一登上文坛,便以《棋王》的道家风范而饮誉于世,众多批评家从一开始就认定 阿城所揭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时至今日,关于阿城小说的道学精神问题似乎仍 是批评家们所热衷的话题。这里,不妨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批评家们在道学精神问题上 对阿城的是非论评。
最先从道学精神的角度对阿城进行评论的似乎是苏丁和仲呈祥,他们认为:“讲究造 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 棋道如此,王一生形象的岸然道风就不缺少根据了。王一生被号为‘棋呆子’,成天心 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无论是浩动中派仗冲突的烽火、 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绪、蹉跎岁月里的内伤外侮,都似乎未曾搅乱 他内心的平静。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 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 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他心如止水,万物自鉴,空心寥廓,复返宁谧。在那个‘一句 顶一万句’的迷狂时代里,这种不迎不捋、无动于衷的呆痴,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的消极,这种在‘大而无当’中遨游的超脱,不正是对动乱现实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明智 选择吗?不正是不愿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吗?道家哲学讲究从反面着手达 到正面价值的肯定,所谓‘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就是这个意思 。看来,阿城的本意是要写王一生的大智,写他在同辈青年中过人的聪慧,却故意突出 他的痴呆和顽愚,这不能不说是深得道家哲学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和超越的妙谛”[1]。 自此之后,围绕道家学说的精神内涵,不少批评家展开了自己的分析,如蔡翔认为:“ 阿城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相当重要的乃在于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极富审美情致的超然 态度。阿城欣赏的是人的‘状态’,进入‘状态’,就能达到某种‘不为物喜,不以己 悲’的审美境界,自得其乐,从而保持了人在困境中的自我完整性。这种思想蕴涵了相 当丰富的人生哲理”[2]。袁文杰则认为王一生从“平常道心”中获得了精神自由:“ 在《棋王》里,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 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但是王一生却绝对要在吃饱饭 的前提下才能下棋,生存是第一要义,没有人能够脱离正常的物质需求,关键是王一生 在一种平凡的生活状态中凝聚着某些形而上的、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他于吃无争, 不苛求麦乳精、油多,只要‘顿顿饱就是福’,以一种禅机式的‘平常道心’赢得精神 上的极大自由,进而成为棋王,在平凡中又见出一种辉煌,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完美再 现”[3]。张法的观点与蔡翔相近,他认为正是王一生的“无知无欲”助成了他成为棋 王:“王一生记忆好(奇);有深情(呆);无多少知识,对古代正统文化(包括最有名的 曹操的《短歌行》)不知道,对西方文化(包括最有名的杰克·伦敦、巴尔扎克)不知道( 无知);无现实利害计较,处于饥饿却并不以饥饿为意,爱下棋被坏人利用而不知(无欲 ),完全靠个性、情致、智慧爱上了象棋。在性情个性上对当下现实‘绝圣弃智’式的 超越,这是他成棋王、得棋魂的基础”。[4]
当然,也有对阿城的道学精神内涵乃至对道学精神本身持否定态度的。如陈炎发问: “为什么道家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以刚克刚、以强胜强、以十万变应万变呢?……这些疑 问加在一起,使我对老庄哲学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我怀疑那迷人的超脱和潇洒只不过是 庸人的自欺和弱者的自慰,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精神胜利法’。翻开我们民族的 词典,到处都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齿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急 流勇退、逆来顺受等格言警句,这种压抑主体欲求、蔑视竞争意识的民族弱性,不正是 来自那貌似超脱、潇洒的老庄哲学吗?”对阿城的作品,陈炎认为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 一个“忍”字:“我自信找到了阿城小说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别的,就是一 个‘忍’字。正像历代文人曾把梅花‘不争春’的弱性美化为一种高洁的品格一样;阿 城则把国民那‘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弱性美化为一种宝贵的德行。有了这个‘ 忍’字,王一生才可能进入那‘不为物喜,不为己悲’的审美境界,‘孩子王’方可能 保持那种‘进亦不喜,退亦不忧’的人格完整,李二才可能像一截‘树桩’那样默默地 度过自己的残生”;而且,“阿城的作品只是‘哀其不幸’,而决不‘怒其不争’;相 反,他还要把这种‘不争’的奴性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赞赏,把王一生们对现实生 活的认可和逃避描绘成令人神往的‘孔颜乐处’,美化成人生价值的积极证明”[5]。 李文田则认为阿城小说不仅反映了道家学说,也有儒家学说,而且是两家的糟粕部分: “以《棋王》为例。这篇小说就是鼓吹逃避现实,回避斗争。什么‘何以解忧,唯有下 棋’,什么‘呆在棋里舒服’。逃避现实就是避免与恶势力对抗和斗争,因之必然反对 争强斗胜”,“阿城笔下人物即使有反抗,也不是对恶势力的抗争。像《树王》中的肖 疙瘩,他反对大规模乱伐原始林木,曾挺身而出,护卫过‘树王’……但作者只是把肖 疙瘩当作维护‘无为而治’的理想王国的象征罢了”;另外,“知足常乐,安常处顺是 阿城小说人物的另一特征。王一生说:‘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种思想并 非老庄所独有,它正好纳入儒家中庸之道的藩篱之中”,“中庸之道终于成为中国国民 奉行的道德准则,这就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恬淡自守等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为害甚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生命被窒息,多少天才的创造被扼杀”。因此,李文田 的结论是:“阿城小说所反映出的‘文化’,大多属于儒、道学说中的糟粕部分”[6] 。李东晨、祁述裕表示了与李文田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王一生不为外在贫穷富贵 、成败荣辱而苦思殚虑,怀有道家的旷达与超脱、儒家的执着和坚定”,“不可否认, 这种人生态度,对于陷入困境的清醒者,自然具有对个人生命、自我完善的积极作用。 它相对于那种心为形役、为改变个人处境而不惜出卖灵魂的人生观,不用说也迸射着人 格尊严的光芒。这与中国古代文人遁避山林、淡泊明志,不求有誉于前,但求无毁于后 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本质上它是以放弃人的社会责任为前提,以 与丑恶现实共存为结果的”,“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传统式的旷达与超脱已很难为我 们现代人所真正具有。从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一生式的放达和超脱,已失去了阮 籍、陶渊明的理性特色和潇洒神韵;而且,作者为了追求传统的单纯,把王一生所应有 的复杂性也抹去了,带有一种浓厚的非现实性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为《棋 王》所肯定的人生观,无法照亮我们的灵魂向新时代迈进的道路,更不可能强化我们积 极进取的信念”[7]。
还有人认为阿城所反映的其实并非道学精神,如黄凤祝认为:“道家要求对任何事物 、作为都应抱着恬淡的态度。恬淡即是反对沉迷,但却不是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而是对事 物有所作为,只不强求得失,不过分地计较,一切都应顺应自然地对待”;但王一生却 过于“沉迷”:“王一生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钱,而对其他事物 不感兴趣……唯有棋与吃他才牵肠挂肚。这亦非老子‘无为’的精神”。因此,黄的结 论是:阿城的王一生“还够不上一个真正道家的资格,阿城对道家文化的真谛也还未曾 悟彻懂透”[8]。
也许就因为王一生有更“沉迷”的一面,所以有人认为“道”只是其外表,其实质则 为“儒”,如雷达认为“王一生所体现的,是‘人的自觉’、‘人的发现’和人的胜利 的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不是那种屈服于生活重压的人,却 又表现得那样淡泊、自适、无为。他是‘道’的外表,‘儒’的真髓”[9]。
那么,阿城自己又是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的呢?他在《棋王·自序》中说:“大概是《棋 王》里有些角色的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我的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 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要 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10]”这里,阿 城所说的“用儒家写道家”显然已不是作品的精神内涵问题,而是表现方法或手段的问 题了。如此说来,阿城虚晃了一枪之后,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小说是属于道家,因为 儒家只是方法手段,其目的所在则还是“写道家”。既然是写道家,那么又如何解释“ 棋王”的沉迷呢?我以为,只看见“恬淡”,只注重“超脱”,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对道 学精神的片面理解;实质上,道学精神既有恬淡超脱的一面,也有沉迷执着的一面,二 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道学精神,而阿城恰好就在二者的结合上反映了完整的道学精神。
道学精神的突出特征是追求精神自由,而要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就必须超脱物欲的羁 累。人生俗世间,既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寿夭的命运捉弄,也要面对无法回避的尊卑 贵贱的现实处境,与此相联系,人们往往会产生苦乐悲欢之情和是非荣辱之心,这些所 谓的“人之常情”破坏“天之真情”,迷失人的自然本性,并诱使人们一步步走向世俗 的深渊,产生浮躁的功利欲望之心;这种功利欲望之心是无法完全满足的,于是就给人 带来无尽的痛苦,并进而给人生带来极大的伤害。为解救人生的苦痛,避免人生的伤害 ,老子和庄子都相应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为解脱功利欲望对人的干扰以求得精神的自由,老子开出的药方是“守柔处卑”。老 子认为,人应该像婴儿一样不造作不隐情,不生过分之欲,不亏自然之需,也就是说, 人应该去掉过分的追求,去掉机巧诈伪之心,顺从自然本性而行。自然本性是什么?老 子认为就是无为,无为则顺应一切,无为则不与人争,无为则不处人先,这也就是老子 的名言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顺守本性的人,明知什么是雄健,却甘居 雌弱的地位;明知什么是洁白,却甘居污黑的地位;明知什么是荣耀,却甘居卑辱的地 位——这就是“守柔处卑”的行事原则。就人之常情常理而言,一般都是争强好胜争名 夺利的,而这也正是人生苦痛的根源;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甘居人后甘处卑辱之位,自然 也就解脱了功利欲望的羁绊,可以与天地自然相往来了。
当然,如果人们有着强烈的尊卑荣辱观念却又要心甘情愿心平气和地奉守卑辱之位, 这确实是太勉为其难了,所以庄子所找到的药方似乎更有效一些,他的药方是“齐物逍 遥”。“齐物”也就是将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一样”的:“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即是 说,不仅物的大小、人的美丑可以“通一”,物的成毁也可以“通一”,甚或是人与物 也可以“通一”,譬如庄周与蝴蝶就可以“物化”。所以在庄子看来,既然天地间的一 切都是同一的,那么人世间所谓的生死寿夭、苦乐悲欢、是非荣辱、高低贵贱等等的区 别,就只是愚人的自扰,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犹如庄周梦蝶,人生本是一 场梦,整个人世的存在也是一场梦。梦中无所谓真假,梦中的一切都是无法确认的;既 然无法确认,便不必费心去确认了,任凭事物的自然存在也就是了。到了随其自然而无 所用心的时候,事物的区别在人的心中也就淡化了;待到泯灭了事物的一切区别,人与 物、与人的相处也就自在了。有了这种自在,也就可以进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逍遥无待”之境界了。
仔细分析一下,无论是“守柔处卑”或是“齐物逍遥”,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 极力要超脱世俗的功利欲望,以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又在极力提倡一种“ 意念”,即试图让人们乐意接受甚至是主动争取卑辱的地位,或是彻底泯灭尊卑贵贱生 死荣辱的界线,将人的自我“齐同物论”,在精神上达到逍遥无待的极境。就人之常情 常理来说,追求功利欲望易而超脱功利欲望难,因为“追求”者总被某个现实的目标所 吸引,不需要“意念”的控制;“超脱”者面对富有诱惑力的现实目标要能够拂袖而去 ,则必须有坚定的“意念”才能够不为所动。因此,在对功利目标恬淡超脱的背后,必 定是对某一“意念”的执着追求,或者说,恬淡超脱是以沉迷执着为基础的。由此而言 ,完整的道学精神也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它所超脱的是世俗的功利欲望, 所执着的则是个性化的精神“意念”。
那么,什么是“意念”?这里所谓的“意念”是与“观念”相对应的一个词。观念是一 种公认的思想意识,是大家所必须遵循的,特别是历久形成的传统观念,对人更有一种 顽强的约束力,所以观念具有确定性凝固性的特点。意念则是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一种 想法,意念的强烈可以接近于信念,也可以吸引人为之奋斗;但意念再强烈也不能等同 于信念,信念必定是群体的,必定有一批人共同坚守,意念则纯为个人的,意念不仅人 各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念,所以意念具有个性化流动化的 特点。在道学精神中,是多意念而少观念,因为老庄所提倡的,都不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所以并不要求人们必须遵循;其涵义也是不确定的,并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色,老庄 哲学尽管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但在看问题的角度上老子与庄子却是各不相同的,即 便是道家学说的核心概念“道”,也仍然具有流动化的特点。“道可道,非常道”,“ 道”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不能用概念性的解释术语来进行界定,那么人们带着自己的 体验来理解“道”的内涵时,也就可以给出各自不同的答案,这些不同的答案,无疑都 打上了个性化的印记。而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也就体现在其笔下的人物超脱于 世俗的功利欲望而执着于自己的意念,并在这种超脱与执着的结合中体现出一种刚性和 韧性。
二
阿城的作品无疑是以“三王”为代表的,从发表的顺序来看,是《棋王》、《树王》 、《孩子王》,“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一个顺 序”(《棋王·自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阿城自己认为,这三部作品代 表了他创作上的三个时期。那么,我们就按照阿城所说的写作顺序,先来分析一下这三 部作品的主人公,看看他们究竟是超脱什么执着什么。
阿城在《棋王·自序》中说,《树王》是他“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原因是写得 太幼稚,“好像小孩子,属撒娇式的抒情”。但在我看来,正因为幼稚才显得真实,不 幼稚才是“虚矫”,因为从阿城自己所说的创作时间来看,“《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 ”,当此之时,正是全民幼稚的时候,能保有自己“成熟”看法的,似乎只有顾准式的 思想家才能做到;而且,任何人的创作都是从幼稚开始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当他面对 初始阶段的幼稚时,完全可以会心一笑而了之,阿城将它当作一块心病,也恰好说明他 确实“对道家文化的真谛也还未曾悟彻懂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以一个作家的直觉 来反映完整的道学精神。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树王》中的肖疙瘩,这个人物一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显得与众不 同:力气大得惊人。然而,却又有点儿呆笨,他干起活来挺在行,说起话来却又笨嘴笨 舌,而且,什么重活脏活他都自顾自地干,当林场所有的劳力都在进行着热火朝天地砍 山竞赛,大干所谓的垦殖大业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默默地种着菜。他完全超脱于生活的 主流之外,似乎在过着一种世外桃源式的恬淡宁静的生活,因而这一人物从最初的印象 来看,确实有着道家的风范。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肖疙瘩内心世界的逐步袒露,读 者可以发现恬淡宁静只是他的外表,其内心则翻腾着激烈的波澜,他内心情感的丰富, 甚或超过任何人。例如,当一棵大树将倒未倒之时,他孤身一人深入险境,清除险情, 帮助几个知青摆脱了危险;事后还不顾自己被管制的身份,向支书提意见,认为不该让 没经验的知青单独砍那样的大树,以致招来支书的一顿批不说,还汇报上去,被当作了 “新动向”。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太呆气太不知趣,然而他的认真而执着的个性又使 得他不能不这样做。最不知趣也最为执着的体现是他对“树王”的护卫,知青李立说是 要破除迷信,砍到树王,而肖疙瘩竟以性命相搏,以血肉之躯护卫着“树王”;虽然在 支书的威压下他不得不离开大树,但在砍树的四天里,他不吃不喝日夜守护在大树旁, 短短的四天,他竟白了发,失了神。我们可以想见,当大树被一刀一刀地砍倒时,他的 心也在被一刀一刀地剐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树被砍倒,他的血也流完,生命也 就枯竭,作为植物之躯的“树王”与作为人体之躯的“树王”终于同归于尽。有评论家 认为,纠缠肖疙瘩的死因是没有意义的,而我却认为,肖疙瘩形象的意义恰好就在他的 死因中。他是为什么而死?仅仅是为一棵树吗?显然不是,因为当“我连连劝他不要为一 棵树而想不开”时,“他慢慢地点头”表示了同意(《棋王》,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第122页。下引仅注明页码),但他还是没有想开,终于平静地死去了。死时除了牵挂那 位被他踢残的战友外,似乎对一切都不再关心,对一切都已感绝望,那“一双失了焦点 的眼睛”明白地昭示出,临死前的肖疙瘩已经心如死灰。那么他的死就不应该只是为了 一棵树,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死于绝望;但他的绝望却不是因为“希望”的破灭,而是 因为一种“意念”的破灭。这种“意念”是什么?他认为树“是个娃儿,养它的人不能 砍它”(第113页),凭着山民的直觉,他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只要有一棵参 天大树的存在,就可以昭示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亦可成为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明证, 这就是他凭直觉所感知到的而且自认为是千真万确的“意念”。然而,当一切大小树木 全都被砍倒烧掉之后,随着“明证”的彻底消失,也就意味着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彻底 破灭。这对于一个完全倚赖于山林而生活的人来说,其打击自然是致命的,他到哪里再 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呢?一个完全失去精神寄托的人,唯一的归宿便只有死。因此, 我们不能责怪肖疙瘩是那样地执迷不悟,为了一棵树竟以性命相搏,因为他护卫的实在 是自己生存的根据,他的生命的游丝就寄寓在这最后的一棵大树中,以性命相搏或许还 可救下这棵树,也可救下他自己,否则,便只有同归于尽。
需要说明的是,阿城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以意念作支撑而背离观念的,如肖疙瘩所执着 的就是意念而非观念,他的想法完全是个性化的,是与当时人们所共同遵循的观念相对 立的;与此相联系,他的执着也就并非儒家式的,因为儒家所执着的往往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公认观念,为了遵循这一观念的约束,儒家在“修身”阶段就极力压抑 自己的个性,破除带个性色彩的意念,而使自己的思想尽量地适应“治国平天下”的需 要。所以,儒家往往以自觉服从为天职,决不会执着于自己心中的某一意念。《树王》 中很爱读书的李立,满嘴政治术语,似乎颇有主见,其实所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他的所 作所为也都是以上级或权威为准,他的执着沉迷才是儒家式的。肖疙瘩的执着沉迷与李 立相反,当然不属于儒家而应属于道家。
《树王》也确实有幼稚的地方,它的幼稚之处倒不在作者自己所说的“满嘴的宇宙、 世界,口气还是虚矫”,这个作品关于“宇宙、世界”之类的空议论还是少有,口气也 并不“虚矫”;这个作品的幼稚所在,是作者硬要给肖疙瘩加个侦察英雄的名头。本来 ,作为一个山民,生于山林长于山林,整个生命维系于山林,他爱树护树乃是发乎天然 的顺理成章之事,这与一个侦察英雄的行为毫无关联之处;而且,仅仅为了一个橘子, 就踢断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的一条腿,更何况这个橘子还是作为班长的肖疙瘩所同 意摘的,这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再者,从结构上说,侦察英雄的故事游离于主体情节 之外,在本来很自然的叙述中,突然插上这一笔,使情节的顺畅发展受阻,显得生硬; 从人物性格上说,侦察兵时期的肖疙瘩是那样野蛮,图名图利,因自己的一等功和班上 的集体功被取消,竟“气得七窍生烟”,这与林场场员时期的肖疙瘩显然有天壤之别。 作为林场场员的肖疙瘩是那样地谦卑忍让,不计名利,可以默默无闻地做着一切,也可 以默默无闻地忍受着一切。他只依着自己认为该做的做去,不在乎利害得失,也不在乎 别人的是非论评,有这种心态和境界,怎么可能为一只小小的橘子而勃然大怒?同时, 只因一等功被取消而觉得“无颜见山林父老”,于是不愿回家乡而转业来到了林场,说 明他是十分注重面子的;但到了林场之后,似乎又根本不把面子当回事,即便是受“管 制”,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资格,他也不往心里去。这前后的反差和矛盾,简直不可理喻 。加进一个侦察英雄的故事,引出了如此多的前后矛盾,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呢?是为 了说明一时的冲动所造成的恶果给了肖疙瘩以教训,故而才修炼到后来的境界?但该作 品的题旨显然不在此。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侦察英雄的故事都是多余的。但作者 之所以要加进这个故事,恐怕是为了给最后的护树壮举提供点“英雄本色”的基础,而 就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普遍认识来说,似乎只有军队才是个大熔炉,才是培养英雄的地方 ,所以肖疙瘩当上了侦察兵,并成了侦察英雄。这个故事在作品中虽属多余,但它恰好 留下了七十年代初的印痕,从了解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看,还是有其史料价值的。
有意味的是,《树王》是超历史的,即便是放到现在来读,不仅不会有丝毫的过时感 ,反而会觉得更切时弊,因为它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环保故事来读,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 加强,该作品的价值可能会越来越被人所重视。有此“超前”的价值在,阿城应该感到 欣慰,其心病也应该祛除。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树王》所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肖疙瘩认为 凡树都有用,而且他更看重的是天然林,他所说的“有用”与李立所说的“有用”决非 同一层次的概念,李立所说的是经济概念,肖疙瘩所说的则是哲学概念。因为肖疙瘩是 个一字不识的粗汉,作者没办法让他大谈哲学问题,但李立作为肖疙瘩的对立面,他是 谈了哲学问题的。我们结合肖疙瘩的“意念”和李立的“观念”,可以发现他们的所思 所想其实都共同切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只是在“合一”于谁的问题 上发生了分歧。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儒家的观念是天“合一”于人,所以强调的是“ 人定胜天”的主观努力。李立驳斥肖疙瘩说,人开出了田,“养活自己”,人炼出了铁 ,“造成工具,改造自然”(第114页),显然是在强调人通过主观努力,使自然适合于 人的需要。道家的意念则是人“合一”于天,所以强调的是“返朴归真”的清净无为。 肖疙瘩一定要留下一棵天然林以“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并与这棵天然林共存亡,他 其实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人与自然的同体,人应该回归自然。
如果说《树王》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棋王》所反映的则是一个 人生价值论问题。在《树王》中,肖疙瘩的哲学“意念”无法通过他的口说出,作者似 乎意有未尽,所以到了《棋王》里作者便尽力弥补这一缺憾。王一生虽然读书不多,谈 不上什么理论水平,但对自己的人生体验总还可以总结一下,于是,“何以解忧?惟有 象棋”的人生“意念”便通过他的嘴反反复复地说出,还通过“我”的嘴不失时机地 大发议论。所以从大段的议论来看,《棋王》倒确实有点“口气虚矫”。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棋呆子王一生究竟是沉迷于棋还是沉迷于自己的意念?对这一问题 的区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虽然王一生的意念是“以棋解忧”,这其中决离不开棋,但 棋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一问题不解决,也就难以区分王一生的沉迷究竟是精神追求 还是物质追求的问题。黄凤祝认为“王一生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 钱”(见注释8),如果棋是王一生沉迷的目的,当然就与酒色、金钱无异。但王一生的 目的显然不在棋而在“解忧”,正因为目的在解忧,所以下棋就仅为下棋,即不“为生 ”,亦不在乎参赛的名次,甚或也不在乎输赢,当冠军老者提出言和,他便毫不犹豫地 就说“和了”。正因为他在下棋的问题上淡泊名利,从来没有想到要比赛拿名次,最后 却又大战群雄,杀败了十位高手而成为棋王,所以众多的评论家们便都说他是道家之棋 ,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也只能解释王一生的超脱,却不能解释 王一生的沉迷。其实,仅仅是超脱名利是不能带来棋艺的精进的,必须有超乎常人的沉 迷才会有超乎常人的水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那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就具体的技艺 而言,则必须靠耐心细致的“水磨工夫”,即便是庖丁解牛,也是破损了多少把刀之后 才“游刃有余”的。所以,棋王的成功,决不是由超脱无为所促成,而是由沉迷执着带 来的结果,只因他所沉迷的非名非利,所以被误会为超脱。应该说,他一门心思所想的 就是如何解忧,为了解忧,他才沉迷于棋艺的精进;解了忧,他才能正常地生存。他的 一生实在有太多的不幸,儿童时代就因家庭的困顿而失去了常人应有的欢乐,年纪稍长 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直被生计所累,如果不能在棋里超脱一下生活的重压,其身 心就将因不堪重负而垮掉,那么也就不会有“棋王”的辉煌。所以,王一生于不幸之中 又是万幸的,多亏他在叠书页之时偶尔遇上了一本“讲象棋的书”,从而使他迷上了棋 ,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忧”之道;更为幸运的是,棋还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辉煌, 他没有像肖疙瘩那样与“树王”同生死,相反,他是与“棋王”共荣耀的。这或许也就 是阿城在人生价值的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充分自信,生活的重压可以迫使人们去寻找“ 解忧”之道,而在“解忧”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会铸造人生的辉煌。这是否就是 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呢?但我以为阿城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执着 于“解忧”之道是其“为”,超脱于世事纷争名利得失则是其“不为”。《棋王》相对 于《树王》,如果说在“文化小说”的意义层次上有提高,那恐怕也就体现在阿城对“ 有所不为”的认识上,并为王一生找到了有所不为的“解脱”之道。
王一生除专注于棋之外,还专注于吃。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吃是他的物质追求,而棋 是他的精神追求。吃是生存的必需,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 (第9页),“吃”对“棋”的决定作用,王一生肯定比谁都体会得深,所以当“我”说 “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时,他便坚决反对:“我可不是这样”(第9页 )。对于吃,他是绝对不敢轻视的。但他重视吃,决不能视为一种物质追求,因为物质 追求的本身,就暗含了物质享受,王一生是坚决反对物质享受的。他要严格区分“吃” 与“馋”的内涵,认为在吃上“想好上再好”那就是馋(第11页),所以他说巴尔扎克写 邦斯舅舅的好吃“是一个馋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第14页);而杰克·伦敦的《热爱 生命》他反而认为是一个“吃的故事”,那么,他的重视吃,也仅在维持生命存在的需 要。正因于此,他对生命所需热量的算计才那样精细,而且其精细程度决不亚于他对棋 艺招数的算计。例如,当“我”说曾有一天没吃饭时,他非得要问清楚是否确实到“当 天夜里十二点”一点东西没吃,还要问第二天吃了什么。问过之后,他十分认真地说: “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 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 ”(第10页)这种算计确实是够精细的,但也确实是“呆”,正是这种精细与呆的结合, 才可见出王一生在吃的问题上的一个“意念”:能维持生命所需的热量即可,想再好便 是馋。所以他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第24页)。“顿顿饱就是福”,这无疑 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能保证热量的维持,解除生命存在之“忧”。因此 ,从“意念”上说,棋为解忧,吃亦为解忧,二者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所以王一生才 同样地执着而沉迷。
阿城之所以要将棋与吃摆在同样的位置,这也反映了他对现实人生的看法。在一般人 看来,棋为高雅之物,需得高雅之人带着清纯的心态才能为之,王一生的母亲认为下棋 是有钱人的事,拣烂纸的老头其家训是“为棋不为生”,均代表着这种看法。但阿城却 偏偏要写王一生在饥肠辘辘中迷上了棋,让棋进入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棋以解忧与吃以
解忧进入同一档次,这反映了阿城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似乎是怕读者不能真正理解作者 的心思,阿城还让“我”直接出面发议论,如当“我”看到观棋的群众竟那样踊跃,“ 一个个土眉土眼,头发长长短短吹得飘,再没人动一下,似乎都要把命放在棋里搏”时 ,便由此引发了一通议论:“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 。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目瞪口呆,倒 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 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第58—59页)。 在阿城看来,只有像黑脸士兵、樵夫、呆子的母亲这种普通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 所以在作品的结尾,阿城借“我”之口将这一意思更明确地告诉读者:“不做俗人,哪 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 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不太像人。 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第65页)。那么,按照阿城的意思,普通人的 真实人生本就是幸福的,只因人们未能“识到”,所以才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幸福 只在“意念”中,解忧也就是对“意念”的追求。“我”是已经“识到”了,不再“囿 在其中”,于是顿感幸福,竟睡得那样沉那样惬意。
阿城所要肯定的本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无论“树王”或“棋王”,却又总带着几 分传奇色彩,这便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所以到了《孩子王》里,阿城便尽量祛除主人 公的传奇色彩而使其平淡化朴实化,还其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孩子王》是作者“自认 成熟期的一个短篇”(《棋王·自序》),其成熟之处恐怕主要就体现在作者完整地实现 了自己的创作初衷,而且也没有《树王》中所有的结构上的败笔和《棋王》中所有的“ 虚矫”口气。
同前两部作品一样,《孩子王》的主人公“我”一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也仍然是一副 恬淡超脱的神态:“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 ,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做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 。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第128页)。有这种“坦然”的心境,所 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做到不喜不悲无怨无悔。本来已安安心心地在生产队干活,没 曾想突然被安排去教书,这意外之喜本可以让他高兴得“蹦”起来,但他没蹦,当同室 的老黑问他捆行李的原因时,他只是“轻描淡写了一番”,老黑反倒高兴得“一下蹦到 地上”(第129页)。队上的知青们听说后都高兴地来祝贺,说他“时来运转,苦出头了 ”(第130页),他自己却并无这种感觉,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我去教书”(133页)。在 他看来,似乎原因比结果更重要。正因为“进”本无喜,所以“退”亦无悲,当老陈传 达总场和分场的意思,让他自己找一个生产队“再锻炼一下”时,他竟心平如镜,毫无 波澜:“我一下明白事情很简单,但仍假装想一想,说:‘哪个队都一样,活计都是那 些活计,不用考虑。课文没有教,不用交代什么。我现在就走”(第189页)。这样地轻 松痛快,弄得原以来很要做一番说服劝解工作的吴干事和老陈反而不知所措了。而且, 他不仅立即离校去队上,在路上走着走着,竟“不觉轻松起来”(第189页)。一场时来 运转的“孩子王”美梦,就这样骤然而来又骤然而去,这种大起大落的命运捉弄,本可 以在人的心海中激起狂澜巨涛,甚或引发出人生中多少风雨雷电的,但“我”却轻描淡 写地将一切如轻丝一般随手抹去,这般恬淡超脱,真可谓已臻极境,即便是棋王王一生 ,也未能达到如此境界。阿城自认为《棋王》只是“半文化小说”,那么作为“成熟期 ”的《孩子王》就应该是“全文化小说”了,它的“全”,恐怕首先就体现在人物心态 的这种高境界上。
“孩子王”的恬淡超脱甚或有过于“棋王”,其执着沉迷却也不亚于“棋王”,而且 仍带着那一分呆气。教书还没有开始,“我”的执拗之劲便上来了,听说自己是因为上 过高中才被选来教书的,便向教导主任老陈反复申辩,说“高中我才上过一年就来了, 算不得上过”,就怕自己“教不了”(第134页);勉强接受任务,一看是教初三,更是 “说了无数理由”,要“坚决推辞”(第138页)。老陈和其他教师都说教书不难,只要 把学生带到18岁能参加工作就行了,他却仍然“心里打着鼓”,深怕“误人子弟”。好 不容易被劝进了教室,一看学生没有书,他的认真劲又上来了:“做官没有印,读书不 发书。读书的事情是闹着玩儿的?”(第141页)他气鼓鼓地去找老陈,老陈却轻松地一笑 ,说这种小地方常常是没有书的。真正教起书来他就更认真了,为了尽快教好书,他不 顾班上学生王福说他“混饭吃”的讥笑,而虚心向王福请教。特别是看到学生对课文中 的字竟有三分之二不认识、作文又老是抄社论时,他更是心急如焚,立意要将这种状况 扭转过来。于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丢开课文不教,每天只教识字和“写流水帐”。 “半月之后,学生们慢慢有些叫苦,焦躁起来”(第170页),总场教育科也说要来“整 顿”他,但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动摇。他这样地执着乃至执拗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还 是为着他心中的一个“意念”:“教就教有用的”(第173页)。课文之所以不教,是因 为他“分不清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区别。学生们学了语文,将来回到队上,是要当支书吗 ?”(第173页)正因为他认为语文课本学了无用,所以弃之不教,当教育科吴干事问他为 什么不教课文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用”(第188页)。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所 说的“有用”,似乎所强调的也是一种实用价值,与《树王》中李立所说的“有用”似 乎是同一层次的含义。这是否意味着,阿城的创作思维转了向,转到了原来的对立面去 了?当然,仅就“有用”所表达的含义来说确实并无多少差别,但得出这一结论的思维 来源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立的结论来源上级来源权威,并非他自己的思考;“我”的 结论则是与上级与权威相对立的,是自我思考的结果。这也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 就是“三王”所执着的并非“树”、“棋”、“书”等具体的物件,而是他们自己心中 所独有的“意念”,这种“意念”是别人不可强加也不可强夺的,它所折射出来的其实 就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因此,从本质上讲,“我”的执拗的性格与李立相悖而与肖疙瘩 倒是一脉相传的,只是“我”比肖疙瘩有文化,因而在独立思考的问题上更有自觉性。 “我”要求学生的作文一定要写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所以“我”给初三班所写的“班歌”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五四三二一,初三班争气。 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第185页)带着自己的脑袋去思考,执着于自己所确认的 “意念”,这是“三王”主人公所共有的特点,“孩子王”似乎更自觉更明确也更执着 一些,他可以对别人所羡慕的教师职业不屑一顾,而对别人所淡然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 容却极度认真,宁可失去教师的职位也不愿更改自己的“意念”,这就是恬淡超脱与与 沉迷执着的结合;而从二者的结合中所体现出来的则是超乎常人的刚性与韧性。有人说 阿城的小说是提倡“不争”的奴性,这其实是误解了阿城。阿城的人物有着鲜明的独立 思考的个性,本质上正是反奴性的。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阿城笔下的人物其共有的突出特点就是恬淡超脱与沉 迷执着的结合,他们所超脱的是世俗的个人名利,所执着的则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意 念,二者相比较,恬淡超脱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表层,更深层的则是沉迷执着,阿城在 文学寻根方面的更为突出的贡献也就是写出了道家风范的沉迷执着,这也可以说是阿城 对道学精神的独特体认。
在道学精神的流传过程中,历来所重视的只是其恬淡超脱的一面,人们仅仅注意到了 道学所提倡的自然无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就说,道学所强调的是顺应万 物之自然本性而任其自由自在地发展,而反对有人为或强迫的成分,这也就是道学精神 所正面提倡的核心内涵。但其反面的根据是,正因为万物不能顺着其自然本性自由自在 地发展,所以才有“辅”的必要。因为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自然本性已经发生了“异化 ”,要顺其“自然”,首先就得经历回归“自然”的曲折。因此,为了帮助“异化”了 的自然迷途知返“归根复命”,就需要“辅”之以外力,即“始于有作”而“终于无为 ”,或曰“雕琢复朴”。之所以要“始于有作”,是因为自然本性上已积累污垢,它不 会自行消失,必须靠人不断地清扫。这种“清扫”,从人性的返朴归真来说,可以理解 为引导人们进行刻苦的修炼,修炼本身就是“有为”的;但“有为”只是手段,目的还 是经过“有为”的苦修而进入“无为”的境界,所以是“终于无为”。因此,“终于无 为”也就是指经过脱胎换骨的修炼之后所达到的“道我通一”、“齐物逍遥”的境界, 它是一种身在尘世却又能超凡脱俗的状态。由于这种状态是经过逆异化之心、顺自然之 本而达到的,所以是“不敢”强为、却又能“辅其自然”的“无为”,目的即在于辅助 万物排除干扰、克服“异化”、顺其自然本性而自由自在地发展。
早期道家的“始于有作”、“终于无为”的思想,更为后来的道教开启了修道成仙之 门。道教认为人的存在可以有三种形式,即人、鬼、仙。人死为鬼,但经过修炼却又可 以成仙。从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意义上说,所谓“成仙”的结果,其实也就是指人 的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无为”状态。成仙的结果是“无为”,但成仙的过程则必须“ 有为”。道教强调:“学道首在受戒”。“受戒”即是借助“他律”的力量,戒除一切 陈规陋习,使心灵消除“异化”的痕迹,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便是虔诚。所谓“虔 诚”也就是看人们是否有脱胎换骨的强烈“意念”和抗击时俗的叛逆精神。因为对“自 然”的回归也就意味着对现有的规范、习俗的超越,而世俗的偏见又是那样根深蒂固, 如果要想从世俗生活的深渊中超脱出来,不下大功夫,不经一番沉迷执着的追求,是绝 不可能得道成仙的。所以,尽管“成仙”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自在的发展,但手段却 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严格的修炼来克制后天的功利欲望,以发扬人的自然本性 。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道家或道教,其实都是以沉迷执着为基础的,它首先 树立起一种“意念”,帮助人们从外在的行为方式的“他律”中,进入到内心世界的提 炼与升华,在实现对世俗生活的超越之后,再度实现人的心灵的净化,最终达到与道的 契合,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理想,这也就是所谓的“归根复命”回归自然,即“自 我”最终回复到“本色”、“本位”。到了这一境界,人还是那个人,却能在尘而超尘 ,脱俗又不离俗,既过好世俗的生活,又始终不忘人生的终极追求,从而带动自我的全 面实现。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吗?人类的存在本就具有双重性: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又超越自然;人是物质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但长期以来,人类 太得意于自己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又主要集中在物质的追求上,于是,因物欲横流 而引发的环境灾难,已成当今社会难以救治的痼疾。只要我们还能想到人是自然的一部 分,就应该懂得回归自然的可贵性,而不应该认为道学精神只是“消极无为”;只要我 们还能想到人也是精神的存在,就应该懂得“齐物逍遥”、“得道成仙”的合理性,而 不能只当它是奇谈怪论。所以,由“沉迷执着”所引发出来的对道学精神的完整理解问 题,则还有着更为广泛而又切中时弊的内容。阿城将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寄予在 文化寻根之中,不仅让读者联系道学精神思考现实问题,还引发了人们对道学精神的完 整认识,这可以说是阿城创作的独特贡献。
收稿日期:2001-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