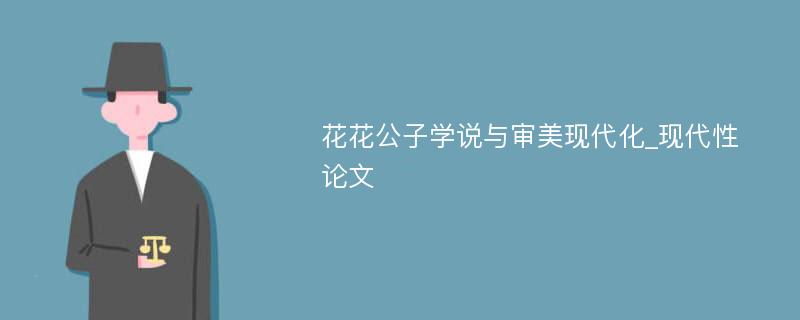
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纨绔论文,现代性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124-05
纨绔主义(dandyism)(注:dandyism在法文中的拼法为dandysme,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郭宏安翻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将其译为“浪荡作风”;本文鉴于这个概念在后来的历史衍变中所获得的丰富的文化意味,将其译为“纨绔主义”。)作为一种凡俗的生存风格,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的英国,而它在审美语境中获得意义,是从19世纪初期的乔治·布鲁梅尔(1778-1840)开始的。布鲁梅尔是英国摄政时期一位中产阶级纨绔子弟,他蔑视本阶级平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沉溺于自身形象的完美和智力的优越。他的服饰的考究、讽刺的优雅、逸出常规的行为及绅士运动俱乐部等,激发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模仿,并启发了文学中的纨绔主义。[1](P6)随着1816年布鲁梅尔逃债到了法国,纨绔主义在法国也吸引了广泛的追随者,衍生出新的、更为理念化的形式。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经历了各种形态的不断发展,融会了英、法两国的文化因素,积淀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感受、情绪、意识,终于涵育成一种极富现代性特征的审美精神,渗透到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的审美诉求中。
然而国内学界对纨绔主义还注意得不够,在近年来有关审美现代性(注:审美现代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讨论得相当多、但至今尚未能确切界定的一个概念。本文借鉴周宪教授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在广、狭两层含义上使用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广义上的审美现代性即是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同步、并与之相对立的文化现代性;狭义上的审美现代性则指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另外请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以及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的论述。)的探讨中也罕有涉及。为此,本文拟对英法19世纪的纨绔主义运动从渊源到流变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进一步剖析纨绔主义的内在、外在矛盾,以反思审美精神在现代进程中的两难和曲折,并期待着把审美现代性的研究从“大话语”(large words)引向具体个案的剖析。
一、纨绔主义的演变
在英文中,dandyism来自dandy。dandy一词大约出现于18世纪后半叶,最常用的意思是:浪荡子、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但确切的语源不详。据艾伦·莫尔斯考证,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流行的一首英国人嘲笑美国兵士的歌曲“Yankee Doodle Dandy”,直接关系到纨绔主义的起源问题:
Yankee Doodle came to town
Riding on a pony,
Stuck a feather in his hat
And called it Macaroni
(歌词大意:吊儿郎当的美国佬,骑了匹矮种马进城来,帽子上插了根羽毛,叫它“麦克罗尼”。)
Doodle是美国口语,指那些吊儿郎当的人,Doodle、dandy两个词音、形相近,它们又都与歌中另一个词Macaroni意思相关。Macaroni来源于意大利语maccarone,原意是“意大利通心粉”,歌词中显然用的是Macaroni的引申义:时髦男子、花花公子。稍后的1764年,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社团在伦敦成立,其成员都游览过意大利,并且致力于将南欧时髦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服饰装扮引荐到英国来,名字也叫“麦克罗尼俱乐部”(Macaroni club),该俱乐部后来成为伦敦近代纨绔主义的重要发源地。由Macaroni到Doodle再到dandy,这一条衍生的线索应该说是可信的。
至1813-1816年间,“dandyism”开始被用于指称那些优雅时髦的浪子的趣味、作风、理念、格调等等,此间纨绔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应该首推乔治·布鲁梅尔。巴尔扎克在《风雅生活论》(1830)这一具有戏谑风格的长文里,专门讨论了布鲁梅尔式的生活风格,论及风雅生活对于一切与个人有关的事物的完美性的追求,发现“风雅生活的核心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条理清晰,和谐统一,其宗旨是赋予事物以诗意”。[3](P25)漂亮的布鲁梅尔则被他比作风雅生活中的拿破仑。[3](P31)这里所谓的“风雅生活”,根据巴尔扎克的描述和把握,其实就是最初作为一种生活时尚和生存风格出现的纨绔主义。
在纨绔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法国人于勒·巴比·德·奥里维尔(Jules Barbey d'Aurevill)做出的概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巴比称纨绔主义是“一套完整的生活理论”,[4](P59)在一个衰颓的社会中,它产生于“适当与厌倦之间无休无止的挣扎”。[4](P59)它的特色——或者说它的职责——就是对整齐划一、平庸、鄙俗的痛恨,相应的后果则是对新异的偏爱胜过快乐:“一直不停地制造意外——那些习惯于陈规旧俗的人所无法依据逻辑预料的意外。”[4](P59)由于认定“活跃意味着兴奋;兴奋意味着在乎某件事情;在乎某件事情就等于显示了自己低劣”,[4](P59)浪子们虽不无才智,却宁愿游手好闲,在他们看来,松弛懒散无疑是优雅的。柏拉图《会饮篇》中美貌放浪的少年亚尔西巴德,被巴比指认为浪子最早的原型。
巴尔扎克的描述与巴比的概括,在推动19世纪纨绔主义进展上的意义固然不容小觑,但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无论是作为一个浪子还是一位纨绔主义理论家,都显得更为重要。波德莱尔赞赏精美的服饰和化妆品,推崇能够使自然得到美化的人为技巧,他自称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在梳妆室里。在《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中,波德莱尔提出生活和艺术不可分离的观点,认为艺术中的现代性除了姿态和姿势,还体现为对现代着装的描绘。在对浪子的精神层面的把握上,波德莱尔特别强调其高傲气质和对抗姿态:“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相信派、漂亮哥儿、花花公子或浪荡子,他们同出一源,都具有同一种反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楚平庸的需要。”[5](438)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是波德莱尔心目中理想的浪子。
到了19世纪90年代,纨绔主义与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熔合到了一起,因为生活中的风格与艺术中的技巧已经无法截然分开了。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和旗手,在《谎言的衰朽》中明确提出了“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6](P357)的观点,与纨绔主义的生活理论和处世风格一拍即合,成为其新出现的当然代表。王尔德不仅在生活中以“带着一个使命的浪子”[7](P307)自命,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兴致十足、惟妙惟肖地扮演着一个风流倜傥的浪子角色,(注:安德烈·纪德回忆王尔德的一段话十分生动传神:“在巴黎,只要他一来,他的名字便口口相传;人们传诵着几个荒诞的轶事:王尔德还是那个吸全过滤嘴香烟的人,他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朵葵花。因为他对欺骗上流社会的人士很在行,他懂得如何在他真正的人格外面罩上一层有趣的幻影,他扮演得有声有色。”参见《王尔德全集》第5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页注释。)而且将纨绔主义精神气质赋予他的大多数作品,讽刺喜剧《不可儿戏》在伦敦演出的轰动,标志着纨绔主义艺术辉煌的成功。至此,纨绔主义运动经过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酝酿,终于达到了辉煌的顶端。
二、纨绔主义与审美现代性
尽管纨绔主义在英国的产生,有着鲜明的意大利文化背景,其后在法国的影响也有赖于乔治·布鲁梅尔的媒介作用,但这一跨国界的现象决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催生的必然结果,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文化的审美性质态。
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贵族阶级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却逐渐增强。随着财富在市场体制中被重新分配,社会各阶层出现了分化和重组,封建等级秩序和特权日趋衰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原则欲求着、创造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浴室大老板的私生子和有才能的人,他们与伯爵的公子享有同等权利。人与人的差别只能以人的内在价值来划分。……倘若还存在什么特权,那么它也是来自精神的优越性。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良好的教养、纯正的语言、文雅的举止、大方的仪表(包括服饰在内)、房间的陈设,一句话,一切与个人有关的事物的完美都具有极高的价值。”[3](P23)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这种削平趋势,激发了从封建等级秩序中解脱出来的个人,寻求现代认同、张扬独立个性的内在冲动,使其努力以高雅的趣味证明自身的优越,并最终诉诸审美判断。这是纨绔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对此,波德莱尔也有过精到的论述:“浪荡作风(即纨绔主义——引者注)特别出现在过渡的时代,其时民主尚未成为万能,贵族只是部分地衰弱和堕落。在这种时代的混乱之中,有些人失去了社会地位,感到厌倦,无所事事,但他们都富有天生的力量,他们能够设想出创立一种新型贵族的计划,这种贵族难以消灭,因为他们这一种类将建立在最珍贵、最难以摧毁的能力之上,建立在劳动和金钱所不能给予的天赋之上。”[5](P438-439)在这里,波德莱尔所强调的“天赋”,是绝对地个人化的,它不仅指智力的优越,也意味着独特敏锐的感受力,而后者恰恰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本出发点。
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发生,启蒙意识形态引领的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变革,颠覆了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思想。宗教在西方世界的衰微,意味着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建构、凡俗的文化和社会逐渐成型。随着“所有意趣、思想和诉求之此岸性的超常高涨”,[8](P300)即凡俗化的推进,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也就势在必行。人们终于开始亲切地打量自己的身体,怀着喜悦和欣慰的心情体验着感官带来的愉快。而美,作为感官所能审察到、也是感官所能承受的唯一灵性形象,越来越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寄寓现代人的灵魂的新的神圣殿堂。美学在1750年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获得命名后,也得到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康德提出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性的观念以来,艺术审美拥有了独立自足的评判标准,而不必再担负认知、教化的功用,人们相信无功利的审美活动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使理性的观念与感性的兴趣相调和。特别是到了19世纪,市民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又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压迫、人的异化和道德堕落,起源于理性主义的进步观念和乐观哲学,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促和虚妄。这时,美代替宗教成为在精神荒原上流浪的现代人获得救赎的最高希望。
正是基于上述语境,西美尔认为现代文化质态是审美性的,他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喻为一件艺术品,因为这样的主体心理世界,有如由艺术的形式构筑起来的世界,成为一个自在的整体,无需与外界或他物发生关系,从而使“人的心性乃至生活样式在感性自在中找到足够的生存理由和自我满足”。[8](P302)纨绔主义就是现代审美性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甚至极端的代表,对美的崇拜和追求,成为它的主旨;为此,波德莱尔又将其称作一种“现代宗教”。对于纨绔主义者来说,精神与物质生活的艺术化是统一的,精神的优越首先要借助于生活中各个细节的完美来体现,所以寻常的服饰也有了非凡的意义:“服饰集科学、艺术、习俗、感情于一体。”[3](P63)“正如艾伦·莫尔斯所说:“浪子被等同于艺术家,社会也就理所当然应对他们殷勤供奉。布鲁梅尔的确是所有艺术家的原型,因为他的艺术与他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高雅的装束和风格就是活生生的杰作。”[2](P263)成为艺术品,意味着生活中瞬时的新奇、精彩、惊颤等感性体验升华到审美愉悦,同时也赋予浪子一种戏谑的、表演性的、玩世不恭的人生心态。
出色的纨绔主义者往往是集浪子与艺术家、诗人于一身,生活的艺术在他们那里甚至高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据安德烈·纪德所说,王尔德讲过:“你想知道我一生的伟大戏剧吗?事情是我把自己的才能都交给了我的生活,我没有把它交给我的劳作。”[7](P1)耳闻目睹过王尔德的言行风度的人,应当不会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就在这里,潜伏着纨绔主义的深刻危机。丹尼尔·贝尔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点。他认为,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仅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这就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反过来又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9](P98)贝尔的这一观点,不仅表明纨绔主义冲动在现代主义艺术家中普遍存在,并且道出了它脱离,甚至取消艺术创造活动的倾向。但实际上,纨绔主义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三、纨绔主义的矛盾
纨绔主义既是一种凡俗的生存风格,又是一种现代性的艺术审美诉求,它于外在社会现实和内在精神需求这两方面均遭遇了矛盾冲突,纨绔主义的危机,深刻反映了审美现代性的困境。
纨绔主义的外在矛盾主要体现为:它是作为资产阶级平庸生活方式和清教主义价值理念的反抗者和对立面出现的,但对社会的否定和反抗又相当暖昧含混。按照韦伯的观点,从基督教禁欲主义到近代资本主义启蒙理性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到后者的演化意味着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与机器生产技术和种种经济条件一起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形成一种庞大的机制,如一只铁的牢笼控制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10](P142)众所周知,英国是清教主义统治最稳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超前的欧洲国家之一,铁笼式的压迫和异化无疑更为严重。纨绔主义懒散无为、玩世不恭的生活风格是作为对这种压迫的逆反出现的,它与资产阶级平庸、琐碎、讲究实利的生活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尽管这种对立后来在不同的纨绔主义者那里的表现不尽相同:在波德莱尔那里,体现为“一个贵族理想,即一个精神和感受性的理想的反抗”;[11](P679)在王尔德那里,则是“唯美主义代替伦理道德、美感主导生活法则”。[7](P452)雷吉尼亚·加尼尔在分析浪子与中产阶级绅士之间的区别时曾指出:“绅士是中产阶级的产物,而纨绔子是被压抑下去的大众社会的无意识。一个庞大的系统发展出一种自我批判。纨绔子表现出绅士们所牺牲掉的一切:乖僻、优美、情谊、天生的贵族气质。‘艺术’一词充满魅力,但又是一个恋物式的词语;而纨绔子用它来代替那些在机械化大生产时代中失去的东西。”[12](P55)可以说,无论是作为一种生存风格,还是作为一种审美精神,纨绔主义都鲜明地体现着审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之间的矛盾对立。
然而,纨绔主义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纨绔主义不可能根本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脱离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瓦尔特·本雅明就曾敏锐地指出浪子面部惯常带有的那种痉挛和扭曲的表情——这种表情曾被认为是一个优雅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就展转来源于伦敦股票交易所传出的那些频繁多变、难以预料的金融信息。[13](P117)另一方面,纨绔主义是一种极富于表演性、展示性的处世风格,浪子“只能以反对的姿态出现,只能在别人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的存在,从而保证其存在。其他人便是一面镜子”。[14](181)“在镜子面前生活和死亡”(波德莱尔语)是它的箴言。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正好充当了这样一面忠实的镜子。作为密友,罗伯特·罗斯对这面镜子在王尔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就非常清楚:“有两样东西对他来说是绝对必须的,用佩特的话来说,就是接触优美事物和社会地位。”[15](P780)其中的“社会地位”即意味着社交生活的镜子与纨绔表演的舞台。
纨绔主义内部也矛盾重重,主要体现为审美的态度与媚俗、颓废的形式的悖反。纨绔主义处世风格意在将人生打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以至于那喀索斯式的自恋情结在19世纪的浪子艺术家身上得到空前膨胀。(注:在王尔德笔下,映出那喀索斯之美的池塘,因为少年的死而变得悲苦;但是它爱那喀索斯,并非因为少年之美,而是“只因为他躺在我的岸边低下头看我时,在他眼睛的镜子里我看见我自己的美映了出来。”参见《王尔德全集》第3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他们对于自身服饰、居室、日用器皿等的美化装扮、对艺术品和工艺古玩的鉴赏收藏,都不得不依托于丰厚的经济实力,并受到资本主义供求关系的制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开销往往迫使并无多少祖产的浪子、纨绔主义艺术家参与商业文化炒作:“他们象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13](P57)另一方面,随着中产阶级美的理想逐渐占据了审美消费上的主导因素,各种形式的美,就像服从供应和需求这一基本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同时,任何其他商品也可以披上形形色色美的外衣,去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这样,生活艺术化的追求,也就不可避免地纳入商业化、媚俗化的浊流。在这一点上,乔治·杜·摩里埃可谓慧眼独具,他发表在当时的画刊《喷趣》上的那些讽刺漫画,已经将王尔德的审美态度看作商品拜物教了。
纨绔主义的另一个危险陷阱是颓废。颓废也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它因为深深植根于时间的破坏性、人的没落的宿命以及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之中,而成为审美现代性中的一个关键词。纨绔主义与颓废的关联也正是在审美的层面上得以顺理成章地建立。众所周知,隐藏在一切艺术享受和感性创造背后的基本力量是快感官能。差不多同在世纪末,尼采曾将这种快感所引发的身心状态归结为“醉”:“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16](P319)尼采列举了许多种醉:性冲动的醉、强烈情绪的醉、激烈运动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的醉、因麻醉剂作用而造成的醉、以及意志的醉等等。正是对于谨慎、理性、平庸的生活的厌倦冷漠,正是对于“醉”这种灵感状态的渴望追寻,激励浪子超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美的历险中一往无前,加速度地消耗自己的生命,甚或跨越伦理道德的藩篱,涉足危险邪恶的禁地,从而使纨绔主义成为“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5](P439)波德莱尔与王尔德等人的放浪生活是众所周知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一冲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刻划。前者的诗歌,在邪恶、丑陋、堕落的“恶之花”中耽迷;后者的小说,任凭其主人公“把作恶看成实现他的美感理想的一种方式”。[17](156)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死亡本能,在道连·格雷的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也许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弗拉基米尔·扬克列维奇说“颓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18](P166)然而,颓废乃至死亡,恰恰意味着审美的退场和终结。这里绽露的正是审美的超越性和生命的有限性的本质对立。
实际上,纨绔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审美性因素从内在诉求向外在实践不断扩张和增强的过程。艺术审美作为此岸救赎的途径,在反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理性对感性的压抑性暴政中,的确能够调节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紧张,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务、尤其是摆脱逐渐增加的理性和实践理性主义压力。[19](P102)然而,由于审美的调节意味着加强感性,反抗理性,这一调节机能又不能无限度地使用。一旦审美性被推入极端,它不仅不会实现人生的救赎,反而会像荣格指出的那样,导致“对迄今为止最高的价值标准的贬斥”,导致一场“文化的大劫难”和“野蛮状态”的复归。[20](P141)纨绔主义之所以陷入唯美与媚俗、先锋与颓废的窘境,主要就是因为它在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的格局上,不断强化和夸大审美的感性因素,逐渐走上了另一极端,并终于在王尔德那里爆发了纨绔主义审美姿态与资产阶级道德法律的激烈冲突。随着王尔德1895年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起诉和判刑,纨绔主义与唯美主义运动也一起走向沉落。纨绔主义的兴衰,作为一个历史个例,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