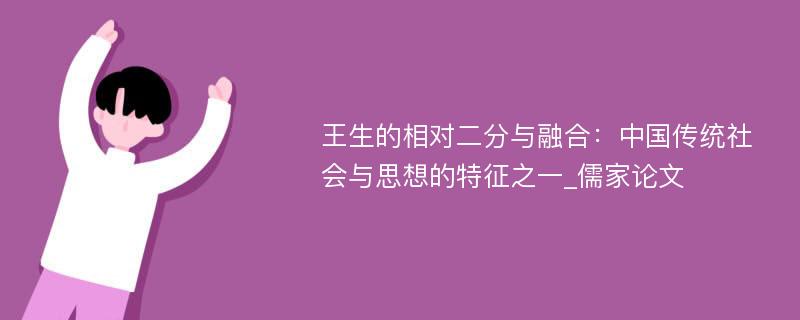
王、圣相对二分与合而为一——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而为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圣关系问题,就大体而言,它是文化之纲,关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全局;就实质而论,它是文化之核,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如果说王与道的关系问题,其根底在于寻求权威合法性,那么王与圣的关系问题,其目标则在于确立权威理想性。圣是道的人格化,王圣关系问题是王道关系问题在人的社会角色上的展开。
一、文化转型:从神化到圣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其后,以崇圣为主。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大创造,也是一大特点。
殷代思想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情感,沉湎于“率民以事神”的氛围之中。从现存的资料看,殷人对神还缺乏终极追求意识,也缺乏道德意义。他们崇拜上帝诸神,一方面是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另一方面,他们所求于神的,大抵只限于实用价值,即对吉、凶、祸、福进行判断和选择。因此,还处于宗教的初级阶段。
周取代殷,对殷人的上帝崇拜有因有革,这表现在“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有机统一。从现有资料看,不能说周人仅仅把上帝、上天当做工具使用,他们在思想情感上依然十分崇拜上帝、上天,而且十分投入。但与殷人相比,也有重要变化,这就是神人相需、互补、互动,其中枢是“德”。天唯德是佑,人则以德配天。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明显增加了,而这又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周初诰命中反复强调的“敬”、“慎”、“无逸”,以及有关“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注:《尚书·君奭》。)的警告,都可视为理智的标志,也可称之为实践理性。这里强调一点,即周人的智慧和贡献与其说是上述观念的本身,毋宁说是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在敬神中会把神抽空,或者说,实践的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把神性排挤到后边。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为这种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条件,给人们的历史创造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复杂的社会角斗中,人们进一步悟出了如下的道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注:《左传·桓公六年》。)重民,主要是从政治力量上讲的,如何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就需要智慧了。于是在用人问题上,突出了用贤和使能,于是有“使能,国之利也”(注:《左传·文公六年》。)之类观念的兴起,有以贤能为“国宝”之喻。在用贤、使能的浪潮中,“圣”被凸现出来。从认识运动看,春秋时期突出圣人,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即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从历史的运动看,突出圣人,反映了神的功能的下降,人的能动性的上升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的增长。
在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这一历史运动中,老子和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在老子那里有两种圣:一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圣;一是凭借直观感觉之智规范事理之圣。老子认为后一种圣人是世俗之圣,只懂形而下之事,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只会带来灾难,对这种凡俗之圣应摈弃。反之,那种以形而上的方式“得道”的圣人才是真正的圣人。老子的观念无疑有极大的偏颇,但他推崇形而上的抽象,无疑大大推动了理性认识的发展。而这正是圣人的本性之一。
孔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高扬了圣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乎理想国的头等大事。在孔子看来,尧、舜还有点不够格。“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的高尚和当政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功能。圣人的历史作用无以复加矣!
老子、孔子是春秋战国新兴文化的两位巨擘,他们虽都不否定神鬼,但由于崇尚理性和相信人的能动性而把神鬼放在侧位,而理性及其实现是由圣人来承担的。沿着老子、孔子的思路,后来更加高扬圣人。终战国之世,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文化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
二、圣人“知道”与圣、神相通
1.圣人是理性的化身。
圣人作为理性的化身,主要表现在通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并能把道理和规律与实践结合起来,达到预期的目的。“体道”这个词便包含这两层意义。
《尚书·洪范》说:“思曰睿”,“睿作圣”(今文“睿”作“容”,这里不论)。“睿”,“通也”。孔安国注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白虎通义·圣人》说:“圣人者何?圣也,通也,道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神鬼合吉凶。……万杰曰圣。”周敦颐说:“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注:《通书》第九册,《周子全书》。)无所不通可以说是认识的极致、完成和终结。又如钱大昕所说:“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注:《经籍纂诂·序》。)这种观念不限于儒家,圣人穷尽真理是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共识。
圣人无所不通的核心是通道。老子、孔子开始以道定位圣人。在《老子》一书中;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孔子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注:《论语·里仁》。),把道视为最高的追求。从此以后,整个思想文化界把通道、闻道、问道、知道、得道、思道、事道、体道视为认识和实践的根本问题。发明、发现、揭示、实行道是最深奥、最神圣的事业,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便是圣人、君子。圣人和道是一种一体关系。这又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况:其一,有时把圣人视为道之原,《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中庸》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圣人吃掉了宇宙,吐出了天道、地道和人道,圣人无以复加矣!如果细加分析,对立天道、地道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以此立论,但对圣人立人道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分歧,人道源于圣人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共识。其二,道高于圣人,独立于圣人之外,圣人的功能是对道的体认和发明。诸如“则道”、“中道”、“体道”、“达道”、“通道”、“得道”等概念所表达的大抵都是这种意思。《大戴礼·哀公问五义》说:“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通道中也包括神道,《易·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其三,道、圣分工协作成就万物和人类社会。其要义就是“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八个字,“生”与“成”是相继过程,又是完善过程;无“生”固无“成”,无“成”则“生”纯属自然而散漫。“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注:《国语·越语下》。)《易·彖传》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又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以上分析只是为说明道与圣的组合形式,其实在诸子的理论中这三种关系并没有逻辑上的区分,常常是混同或混用的。
道与圣人是相依相成的关系,圣人是道的体现者,道要靠圣人发明而显现。道虽然无处不在,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只能由圣人引渡、传播才能有所悟。《鹖冠子·能天》说:“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圣人把知识穷尽了。
与通道、知道、体道等大体相近的还有如下一些:
知“必然”,又称“必”和“然”。如“圣人知必然之理”(注:《商君书·画策》。);明主“见必然之政”(注:《管子·七臣七主》。);“万物尽然,明主知其然”(注:《管子·禁藏》。);“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注:《韩非子·显学》。)等等。
知“理”。“理”的含义很多,理与道意义相近,只是没有道那种本体和主宰的意义。韩非对道、理之分曾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注:《韩非子·解老》。)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注:《庄子·秋水》。)。理作为规律的意义,既包含自然,也包括社会。有“天下之理”、“物理”、“天理”、“天地之理”、“万物之理”、“事理”、“人理”等等概念,为各家各派所共用。在一些人的论著中理与道几乎没有差别。“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注:《经法·论》。)圣人“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伐当罪,必中天理。”(注:《经法·四度》。)天理这个概念以后有极大发展和扩充,特别是在理学家那里尤为突出。圣人成为天理的化身。
知“数”。如果说“理”是对规律性的定性概括,那么“数”是对规律性的定量表示。“圣人审数以治民”(注:《商君书·算地》。);圣人“修道理之数”(注:《淮南子·主术训》。)。
表示规律的概念,还有“度”、“序”、“经”、“纪”、“一”、“常”、“势”等等。圣人与这些也是同体的。
“知道”是圣人在认识上的特性,也是理性的最高表现。在实践上,圣人的最大特点是“知为”。知为就是知道实践的条件和机遇。行道、遵道、践道等概念的提出,把认识原则与实践原则一体化,应该说这是极其高明的。行道是总原则,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准则,即“贵因”、“执中”、“用当”、“知要”、“原宗应变”。
所谓贵因,就是善于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条件和依据,不可主观行事,任意而为。道家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充分,同时也是诸子的共同认识。《管子·心术上》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执中与用当大体相同,执中为儒家所倡导,用当为道家所倡导。中和当就是恰到好处。知要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关键,解决主要问题。要的本质就是道。《管子·君臣上》说:“道也者,万物之要也。”商鞅说:“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注:《商君书·农战》。)以后思想界一再讨论以一驭多,以一驭万,都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原宗应变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孔子所说的“权”就是这个意思。“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注:《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能达到权变自如的,非圣人莫属,荀子说:“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注:《荀子·非十二子》。)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共同命题,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性的最高范畴和最高境界,而其核心所表达的是本体性、必然性、规律性、规范性、决定性、不可超越性等等方面内容。这些东西或者由圣人制定,或者由圣人发现,不管什么途路,都形成了道与圣人一体化的关系。于是,崇道必崇圣,崇圣必崇道,这成为中国传统中的一条铁则。
2.圣人使人成为人。
人作为“一类”的观念起源于何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殷代的文献中,“人”已经是一个“类”概念。
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的提出或许很早,不过从有文字记载看,是西周时期的事。《诗经·相鼠》有言:“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个问题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礼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失去了礼,就失去了生存的资格。《礼记·礼运》篇在论述以礼作为人的本质时即引此诗作为经典依据。问题的提出是理论认识的先导,从现有的资料看,具有理论性的认识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诸子百家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共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礼义道德、有制度、能“力”(劳动)、有“群”(社会性或群体性)、有“天理”等等。
儒家把礼义道德作为人与动物区分的基本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注:《论语·为政》。)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注:《孟子·离娄下》。)所谓“几希”,即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忍人之心”,亦即仁、义、礼、智。《礼记》中多处把问题说得更明确,“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注:《冠仪》。)荀子除讲礼义外,又进一步提出了“群”这个标志,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注:《荀子·王制》。)“群”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团体性。人何以能群?还是因为有礼义。理学家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天理”亦是礼义。
儒家所说的礼已经包含着社会制度的内容。这里再强调一下“制度”,因为法家、墨家对礼不那么强调,但他们认为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墨子还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分在“力”。禽兽不耕不织,靠自然生存,“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注:《墨子·非乐上》。)。这个思想极其光辉,遗憾的是他没有深论。
礼义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那么礼是怎样产生的呢?一种看法是,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制定的。其实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天生礼也要通过圣人之手。所以作为创制礼的主体,大抵都归结为圣人。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论述多多,无须征引。
法家、墨家所讲刑法、行政制度,同样是圣人创立的。《商君书·君臣》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管子·任法》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由于圣王创立了行政制度,才归于有序,才与禽兽有别。
汉以后法、墨不彰,他们所说的制度也可以包括在“礼”之中,以礼义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遂成为公论。
先秦诸子对“器物”在人的文明化中的地位也十分注重。他们在追溯人类的历史时,大都认为有过洪荒的初始阶段。在那遥远的过去,人们茹毛饮血,无器物之用,裸体而行,栖息山野,一派原始状态。后来圣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器物”,使人类步入了文明。
孟子在《滕文公上》中历数了舜、益、禹、后稷等教民耕稼、人伦,而后人才与动物揖别。《易·系辞》历数了器物发明史,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斤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黄帝、尧、舜“夸木为舟,炎木为揖”,“服牛乘马”,“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炎木为矢”;“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墨子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未知为衣服”,“未知为饮食”,“未知为舟车”,生活异常困难。于是有圣王出,发明了宫室、衣服、饮食、舟车,便民之用,在圣人的指导下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注:参见《墨子·节用中》。)。
商鞅、韩非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上古”时期,人与禽兽杂处,人、兽难分,后来有圣人出,“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使人与禽兽区分开来。
《世本》一书中有“作篇”,专门记述了器物发明史。齐思和先生曾写过一篇《黄帝制器考》,收集资料甚详。我们的先人把器物发明权都系于圣人的名下。
圣人的第一历史作用是引导人与禽兽相别,使人变成了人。其后,则是使人进一步成为完善的人。如何使人完善,其术多多,要之:一、圣人是“体道”者,把“道”撒向人间,使人提升为知道的人;二、“圣人,尽伦者也”,所以使人变成道德化的人;三、圣人治天下,使人成为安居的顺民。
人类赖圣人而成立,《易·文言》说:“圣人作而万物睹。”又如《中庸》所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韩愈说得更简明,“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注:韩愈:《原道》。)
3.圣、神相通。
圣本是理性的标志和理性的人格化,然而由于圣人垄断了理性,而且在历史上又是使人成为人的“塑造者”,于是圣人逐渐从“人”中分化出来,在圣人身上逐渐增加了超越性。其结果是圣人与神相通,圣、神合一。
老子与孔子在以圣人推进理性,以理性塑造圣人方面具有空前的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把圣人置于神的同列。在老子的描述中,圣人不仅仅是“知道”者和“体道”者,同时又是超越人的感官认识和实践能力的神秘人物。孔子眼中的圣人是超越尧舜的,而尧舜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神性的。如果说孔子对抽象的圣人的神化还是含蓄的,那么他们师徒在自我圣化和神化方面却走得相当远。弟子们把他视为圣人而加以崇拜,如日中天,仰之弥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日一直具有神性,只要同日结缘,也无不具有神性。孔子虽然自谦不是生而知之者,可是他又自称“天生德于予”,传统文化都凝结在他身上,如果他出了意外,中国的文化就会断绝,这无疑是在自我神化。应该说,孔子已有圣、神结合的意味,于是有“天纵之将圣”之说(注:《论语·子罕》。)。老子和孔子通过高扬圣人发扬了理性,同时他们也为圣、神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战国以降,圣、神合一,圣、神相通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天降圣人,圣人法天,圣人通天,圣人如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注:《易·彖传》。)“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注:《礼记·礼运》。)“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注:《淮南子·泰族训》。)“夫圣人为天日,贤人为圣译。”(注:《潜夫论·考绩》。)“圣人如天,圣神一体。”(注:《传习录》上,见《阳明全集》卷一。)“圣人之智犹天也”(注:胡翰:《五行志序论》,《胡仲子文集》卷一。)。
第二,圣、神相通。“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注:《孟子·尽心下》。)“圣人为天地主,为川山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注:《春秋繁露·郊语》。)汉代谶纬化的经学中,所有的圣人都是神、人的统一体。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注:《论语集注·述而》。)
第三,圣人是“气”之精。在传统思想中,“气”为万物之本说有广泛的影响。在“气”说中,圣人同样处于特殊的地位,他不同于一般人和一般物,圣人是由“精气”、“和气”、“清气”等等超常之气凝结而成的。实际上,这种气与神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圣人过“性”。在传统的思想中,人性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人们通过人性来说明人的本质和变异。在人性论中,虽有圣人与一般人同“性”之论,但更有超“性”之论。孟子说,圣人是出乎其类,拨乎其萃者。荀子认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和奇异之处就在于能“化性起伪”。董仲舒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注:《春秋繁露·实性》。)圣人过性,同一般人不能同日而语,属于超人。
第五,圣人是先觉者,穷尽了一切真理,是认识的终结。《中庸》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没有圣人所有的人只能处于昏昏然的状态。朱熹如下一句话把问题说得也很清楚:“道理,圣人都说尽了。”(注:《朱子语录》卷六。)既然圣人把道理都说尽了,那么人还有什么意义呢?结论只能是:代圣人立言,践圣人之教。人不再具有创造性,是一群侏儒而已。
三、圣、王合一
在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由神性向理性转型过程中,“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理想的主要命题。诸子百家对圣人有各式各样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把圣人与“治”连在一起,或者说圣人问题的归结点都是“治”。“圣人之治”无疑具有明显的理想性和设计性,它同当时十分流行的另一些命题,如“先王之道”、“王道”、“先王之治”等等,几乎是同义语,或者说是同指、同价。这样圣人与王便结下不解之缘。在许多人言论中,圣人与王是没有区分的,圣人的本质和功能就是王的本质和功能。且看两位思想巨擘老子和孔子的言论。
在老子那里,圣人有这样和那样的功能,而其主要的职责就是治天下,“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注:《老子》第49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注:《老子》第3章。 )
孔子的圣人同样也是以政治为主要功能的,圣人的社会、历史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又超越尧舜,非王而何?
在先秦诸子以及其后的整个思想界,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的,几乎没有不同政治联在一起的,没有不同治理天下联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联在一起的。在思想史界,一些学者认为,圣人主要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是社会理想的化身,特别是理学家们,已经把圣人从王权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标准,等等。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实际上有极大的片面性。如果我们认真面对事实,面对资料,那么无论如何不应忽视,所谓的圣人之治始终是圣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功能,也就是说,圣人首先是政治人。正如墨子所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注:《墨子·兼爱上》。)《管子·乘马》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圣王”一词的创立把圣和王统一起来了。
从现存的文献看,“圣王”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诸子著作中,《墨子》一书中“圣王”一词屡见,圣人与圣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一个内容,有时用圣人,有时便用圣王。所谓圣王,从历史上看,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先王。
圣王在诸子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凡属理想政治都与圣王相联,圣王是理想的实现者,是最伟大的仁慈者和创造者,圣王几乎都是崇拜的对象,都是希望所在,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假定来说明,即如果把圣王一词去掉,可以断言,所有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的论述就失去了主体,就会散架。圣王论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圣王的提出,适应了思想文化由崇拜神性向崇尚理性和人文转化的需要,使王由原来的神化人格转为理性、人文和道德人格。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圣王具有不同学派的性质和形象,但在这点上又有一致性。在先秦诸子中,圣人与圣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圣人有时更侧重于理性、人文和道德本身,圣王则是这些品格和权力的结合与统一。正如荀子所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注:《荀子·解蔽》。)从荀子的论述看,圣王应该说比圣人更全面、更崇高、更伟大。
谁来作王呢?圣人当王成为当时的一股强大思潮和诸子的共识。有些论述十分明快,如:“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注:《管子·兵法》。)“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注:《管子·乘马》。)荀子提出“尊圣者为王”(注:《荀子·君子》。),又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注:《荀子·正论》。)在诸子论述历史时,那些著名的先王都是圣王,“帝德广运,乃圣乃神。”(注:《尚书·大禹谟》。)“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注:《大戴礼记·诰志》。)圣人当王虽然不是唯一的理论,还有其他的,如王权神授,兵胜者为王等等。但是圣者当王,其理性色彩无疑更为突出,更具有说服性和合理性。
圣王思潮还包含着极大的创新精神。在历史上圣王都具有伟大的历史贡献和创造,人们对他们充满了英雄崇拜的情绪,甚至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儒家呼唤法先王,其中虽不乏守成精神,甚至还有极其浓厚的复古气息,然而由于先王是极其伟大的,且不说达到先王的标准,仅仅是认真学习就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在法家那里,他们不主张法先王,甚至认为那是复古,是倒退,但他们并不否认先王们的伟大贡献,只是时代变了,现在需要新时代的英雄和圣王,即他们所呼唤的“新圣”。新圣就必须有新的贡献和新的创造,要敢于打破一切成规和过时的东西。新圣理论与法先王不同,但仍然属于圣王理论中的一支。
因圣而王,打通了知识、道德与权力之间的通道,这在当时以及以后,对权力独占是一个挑战。人们既然把圣作为王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作为合理性的重要依据,那么,在逻辑上就出现了这样一条路,谁是圣人,谁最有知识和道德,谁就有做王的理由。孔子本人就有点以“王”自居之味,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很明显,他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他的弟子们把他置于尧舜之上,宰我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注:《孟子·公孙丑上》。)。尧舜是公认的圣王,孔子比尧舜还伟大,把他列入圣王之列,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的徒子徒孙就有把孔子尊为王的舆论。《墨子·公孟》篇记述儒家信徒公孟认为孔子应为天子。孟子也是雄心勃勃的,他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周文王、周武王算起,到他生活的时代已超过五百年,于是他豪迈地称:“夫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注:《孟子·公孙丑下》。)虽然我们不能说孟老夫子要称王称帝,但他同孔子一样,把自己同文王视为一系。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政治雄心。正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这其中不能不说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抱负。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把君子、圣人、圣王视为一系,君子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成为圣王的。荀子在《儒效》中就论述了大儒为帝王的可能性,文中曰:大儒“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又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大儒与帝王之路是相通的。《礼记·学记》中有一段论述也同样耐人寻味:“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圣与王相通是诸子的共识,连庄子也说,“静而圣,动而王。”(注:《庄子·天道》。)孔子没有当上王,无论如何是儒家的一大遗憾,后来的儒生们,为了填补心灵的不平衡,把孔圣人列入王之列。荀子率先发此议:“孔子仁且知不蔽,故学乱(作“治”解)术足以为先王者也。”(注:《荀子·解蔽》。)其后的儒生尊孔子为“素王”,像吸鸦片一样,在精神上过过瘾,圆了圣人当王的梦。后来有些儒生一直在这个梦中盘桓,清代的曾静说:“皇帝合该是我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注:《知新录》。)在他看来。孔子、孟子、程颐兄弟、朱熹、吕留良等都应该做皇帝。其实,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为依据而称王的,也是有其例的,这就是王莽。其他帝王也几乎无不以圣作为自己合理的依据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在圣王观念中还蕴含着批判精神。在理论上,圣王与一般的王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所谓统一性,即圣王与王都是王,同属一系,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矛盾,即两者的等次不同,有好坏之别,甚至天壤之别。所以一般的王应该向圣王学习,应该力争做圣王。圣王是衡量王的标准,是品评王的依据。在春秋战国,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当时的王都采取批评态度和立场,有些批评是极其尖锐的,有时竟使一些王在朝堂上十分尴尬,当众出丑,下不了台。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强大的呼唤圣王出世的思潮中,当时的王没有一个敢以圣王自居。由于当时的王都没有达到圣王的标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批评,或为了使自己成为圣王而主动接受批评。
圣王观念与革命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革命观念是在殷周之变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殷周之际的革命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命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殷周之际的革命主要还是一种宗教观念,革命的主体是上帝。由于殷纣王暴虐失德,周文王、周武王有德,于是上帝更改自己的命令,选择新的代理人,命周取代商。春秋战国兴起的革命思潮,无疑承继了殷周之际的革命思想资料,但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的主体由上帝变成了圣人,可以说是“圣人革命论”。圣人革命的基本依据是“有道”。以有道伐无道,乃是最大理由,最高的依据。有道者就是圣王。
在圣王这一观念中,既包含了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与权力结合为一体。中国历史上的王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治的体现,不管历史有过多少沧桑之变,王权专制体制没有质的变化,从总的趋势看,而是越来越强化。圣王在体系上同现实的王是一个系列。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在政治理想上有极光辉的创造和极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构思了极美好的图景,但他们同时却把画笔交给了帝王。所以在圣王观念中,理想政治与王权专制是一体化的,不可分割的。应该说,政治理想与专制的合一,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归结点。
四、秦始皇称“圣”与王、圣同体两千年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不停地制造古久圣王的神和理想境界,同时又呼唤新的圣王出世,秦始皇的伟大功业把人们想象的圣王从遥远的古代移到现实中来。人们不禁大呼:啊,圣王就在阿房宫!
秦始皇在同他的臣僚们总结自己胜利的原因时,说了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而其中富有理论意义的是如下十二个字:“原道至明”、“体道行德”、“诛戮无道”。诸子喋喋不休地说“得道而得天下”,秦始皇的大业应该说已基本满足了这一理论要求。他把自己的胜利说成“道”的胜利,是顺理成章的。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作为“体道”者的秦始皇称圣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被称为“大圣”、“秦圣”;他是圣的化身——“躬圣”、“圣智仁义”;他立的法是“圣法”;他的旨意是“圣意”;他做的事是“圣治”;他撒向人间的是“圣恩”。总之,圣与现实的帝王合为一体。
秦朝短祚,秦始皇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不停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谴责,可是秦始皇制定的一套皇帝制度却被继承下来,秦始皇整合和规范的一套皇帝观念同样被继承下来,其中便包括帝王与圣同体观念。其后两千年,帝王的一切无不与圣结缘。
帝王的尊称为“圣上”、“圣皇”、“圣王”、“圣明”、“圣仪”、“圣驾”、“圣主”、“圣帝”等等。
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令”、“圣喻”、“圣策”、“圣诏”、“圣训”、“圣敕”、“圣诲”等等。
帝王的决断称为“圣裁”、“圣断”、“圣决”等等。
帝王的政事、功业称之为“圣政”、“圣文”、“圣武”、“圣德”、“圣勋”、“圣业”、“圣功”、“圣治”、“圣绪”、“圣统”等等。
帝王的尊号中,圣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第一个有尊号的帝王是汉哀帝,这位死后谥号为“哀”的帝王,生前竟然得了“陈圣刘太平皇帝”的美称。唐朝是尊号大兴之世,“圣”成了主体词。
帝王的谥号(唐以后尊号与谥号有混通)、庙号也多有以圣为标榜,甚至连那些昏庸的皇帝也不例外。
帝王的感官与智力都以圣来形容,如“圣览”、“圣听”、“圣问”、“圣聪”、“圣谋”、“圣虑”、“圣意”、“圣猷”、“圣略”、“圣思”、“圣心”、“圣鉴”等等。
以圣称颂王的词汇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圣虽不乏神性与不可知性,但主要还是理性、人文和道德精神,总括了人类最美好的文化成果,是文明的最高标志。只要与圣发生联系,便具有不可怀疑和超越的性质。人们在圣面前,只能作学生,作服从者,作矮子。
古代思想家虽然有一些人,一直在努力把圣人与王分开,力图让圣人代表理性和道德,让王代表权力。然而由于王权太强大,不仅王要独占圣,把圣变成王的附属物和王的一种品格,使圣为王服务,为王张目,成为王的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家们,由于大多数依赖于王权,认同王权,又把圣的理想寄希望于王,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把圣与王分开,更多的是把圣交给了王,特别是当朝的王,不管如何,大多称之为圣。
这里仅以理学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理学家号称是张扬圣学的,在理论上似乎全面主张道高于君,就历史的评价来说,在他们眼里,三代以下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王。然而别有意味的是,理学家们的多数却把一顶又一顶的圣冠戴到当朝帝王的头上。以倡导道学著称的韩愈作《元和圣德颂》,以颂扬唐宪宗的所谓功德。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把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吹捧为圣王,作《三朝圣政录》,又作《庆历圣政颂》,而且远过唐尧、虞舜,亘古所无,肉麻之极。这同他们鼓吹的道学精神相距甚远。二程在奏疏中对皇帝多有批评,但称圣道神的语言也不少。如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称颂仁宗“德侔天地,明并日月,宽慈仁圣,自古无比,曷尝害一忠臣,戮一正士。”这类的阿谀奉承之辞同上疏的内容是极不协调的。陆九渊、王阳明是有个性的人物,然而,他们的奏疏中也不乏上述之类的语言,如陆九渊在《荆门到任谢表》中把昏庸的宋光宗称颂为“道同舜禹,德配汤文,勺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于亲授,广大蔚乎天成。”王阳明在《乞养病疏》中把昏庸的正德皇帝称为“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的仁慈之主。
或许有人说,称颂帝王为神圣是当时的套话,这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在套话中恰恰包含了更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也常常是人们不假思索的前提,是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当然的、无可怀疑的理论基础。对此尤其值得认真分析。
帝王对圣的占有,是对理性占有的一种表现,是权力支配理性的证明。在中国古代,理性虽然比神性有更突出的地位和发展,然而,理性终于没有摆脱权力婢女的可怜地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五、结语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可作三段论:1.神化阶段。三代时期,其特征为神道设教,率民以事神。2.圣化阶段。自春秋至辛亥革命,从事神转向尊圣,从神道设教转向内圣外王,圣王即是神。3.民主化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从圣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从王权转向民权。这三个阶段,圣化阶段承上古,开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的基本价值,皆于此阶段形成。其历时之久,影响之深,传播之广,举世公认,所谓传统,主要在此。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毛泽东诗云:“六亿神州尽舜尧。”时隔两千余年,文化价值一脉相承,传统之伟力,于此可见一斑。今天,我们处在民主化时代,可我们的价值观却留着圣化的烙印。圣化能与民主化兼容吗?从圣化的传统中,能“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来吗?内圣外王能开出民主化的新天地吗?回答这些问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走出圣化,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圣王不死,大乱不止,中国两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荀子论文; 圣王论文; 国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论语·子罕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