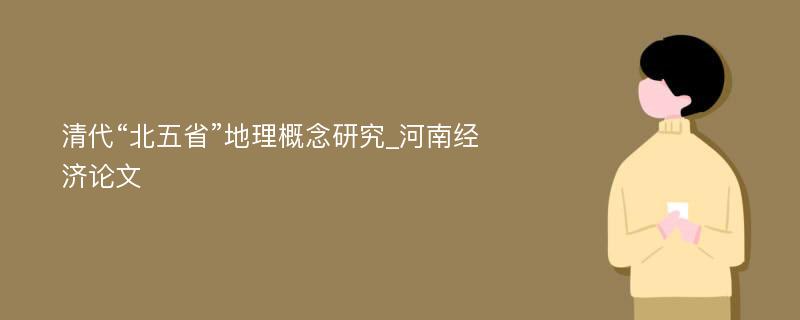
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地理论文,概念论文,北五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五省”一词,曾经较多出现在清代官文书中。本文研究发现,该词作为地理概念有其自身形成的演变过程,而区域范围应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甘肃六省,之所以出现“名不副实”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藉此不仅有助于理解此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还能为相关问题的思索提供参考,诸如清初的分省过程,行政文书中旧省名长期存在的现象,南北方区域社会发展差异的文化影响,以及我国北方区域地理概念的形成历史等等。
一 官文书中“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形成
以笔者管及所见,“北五省”一词尚未在雍正年间以前的文献中作为地理概念使用。清人王庆云在其私家笔记《石渠馀记》中曰:“(康熙)六十年,以各省积贮虽报称数千百万,州县侵蚀,存仓无几,令平粜北五省常平,直隶一百六十万、山东四百七十余万、河南百三十余万、山西四十余万,并陕西散赈。”①这似乎表明早在康熙时“北五省”就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使用。但作为道、咸时人,王氏之说值得勘验。检《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②,未见相关谕旨,又核《清圣祖实录》得:
户部等衙门遵旨议奏,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被旱……应令四省抚臣遣官分赈并平价粜卖。③
其中未见“北五省”。因此,不排除王氏是将后来出现的地理概念追用于前,故仅据此恐难立论。笔者在梳理有关史料时发现,“北五省”概念在雍正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偶见到逐步被认同使用的过程,现就此讨论如下: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下文简称《朱批谕旨》)④中记有多处“北五省”,兹引数条于下,如卷二三上山东巡抚黄炳于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奏:
如果臣言可采,并请通饬北五省一体遵行……雍正帝朱批: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尔等一省内之刑名、钱谷、案件,循规蹈矩一一秉公料理尚恐有所未协,何得于事外越例搜求?况赋税出自田亩,连年北五省率皆薄收,正供维艰,何堪再有更张之举?⑤
朱批:近畿数省自去冬今春以来微缺雨雪,昨于三月三日普雨沾足,中外庆幸,不知是日云南曾有雨否?查奏以闻。兹四月初十日正在盼雨之际,又得甘霖透足北五省,麦秋大有可望矣。⑥
朱批:阅奏大慰朕怀。北五省今岁苗稼亦好,目下时雨溥遍,秋收可望。⑦
朱批:今冬北五省皆得盈尺瑞雪矣,似此分寸沾濡恐无济于事,当竭诚修省,黾勉吏治,务有以感召天和,获蒙春雨接续,方可冀来岁丰登之庆也。⑧
诸上奏折朱批始于雍正元年,迄于雍正六年末,都径直使用“北五省”一词而无需解释,故可认为该词作为专有地理概念此时已大体得到官方认可,从而在行政文书中加以运用。不过,此论不免草率,因为一个词汇的出现或许有随意的成分,但若要成为一个地理概念则必须得到使用者的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往往要经历一段适应的过程。而前引“北五省”作为地理概念的大量使用,似乎过于“直接”,令人颇感疑惑。故其之源起,尚需谨慎考察。
事实上,《朱批谕旨》自雍正十年开始编选,当年即成,次年刊布,乾隆三年又续出新刻本。冯尔康指出,“它所汇集的奏折和朱批虽是根据原始文献刊刻的,但在编选时,雍正和他的助手对原文作了一些改动”⑨,至于这些“改动”,“业经修饰增删,与朱批奏折之原件颇多歧异”⑩。换言之,前引出现“北五省”概念的史料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其书并非原件,而是曾经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的重新编订。因此,据之定论恐怕仍嫌说服力不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下文简称《奏折汇编》)一书,是汇集该馆所藏原件并台北故宫博物院辑《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合编而成,具备较高的原始性和可信性。故参照前引《朱批谕旨》,将《奏折汇编》的相应部分检出如下,以便对读:
黄炳奏:如果臣言可采,并请通饬北五省一体遵行……朱批:此等事外之事不□□寻,况北四省连年歉收,哪里当得起此等大更张之举?(11)
朱批:都近数省冬春少乏雨雪,三月三日普雨沾足,中外庆幸,不知此日云南可雨否?查明奏来。四月初十正又望雨,又下一天透雨,北省麦秋大有望矣。(12)
朱批:大慰朕怀。北数省今岁亦其好,目下时雨普降,秋收有望。(13)
朱批:北五省皆得赢尺瑞雪矣,此寸余之雪想未济于事,来春雨泽,当竭诚□□□勉吏治。(14)
将《奏折汇编》和《朱批谕旨》相应内容比较后,不难发现明显的“修饰增删”痕迹,前者中雍正帝朱批多为白话,而后者则基本是文言。不过,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不同还在于“北五省”一词的使用。两者除黄炳所奏皆用“北五省”概念外,在后者一律为“北五省”之处,前者朱批则分作“北四省”、“北省”和“北数省”等称谓。由于《奏折汇编》为原件影印者,故知诸上称谓其实是后来编修《朱批谕旨》时方才改动的。那么,为什么《朱批谕旨》要将原件中的诸多不同称谓一律为“北五省”?这样做又说明了什么呢?
上文引雍正帝君臣之间的奏折朱批,都是有关地方日常事务的呈报和批复,故基本可将《朱批谕旨》进行改动的目的,是出于政治斗争考虑的可能性排除。《朱批谕旨》对原件的改动主要集中在朱批部分,而内容多是文字形式上的重加修饰,例如将许多白话改为文言等。倘若如此,则将“北四省”、“北省”和“北数省”等语一律为“北五省”便可视为较大的改动,特别是如改“四”为“五”,就地理概念而言,实属前后“歧异”者。不过有趣的是,此番修改的为首者正是当年“朱批”的本人雍正皇帝,其中如此多处的地理概念皆被改为“北五省”,想必没有经过他本人的认可也是说不过去的。此外,《朱批谕旨》以“北五省”替换原件中的地理概念时并非“一对一”的改动,而是成为一类地理词汇的替换概念。换言之,此番改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统一的标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朱批谕旨》的改动虽有强制使用“北五省”这一地理概念的趋势,但却并非最早使用者。在《奏折汇编》中,“北五省”不仅早在雍正元年黄炳就已使用,后来在雍正六年末的朱批中也出现了这一地理概念。
综合诸上分析,笔者以为尽管在雍正君臣的奏折朱批中早已偶有“北五省”一词的使用,但开始其并未成为一个公认的地理概念;雍正十年至乾隆三年编订《朱批谕旨》时,以雍正帝为代表的官方将原本许多不同表达的称谓统一改为“北五省”,这极有可能是该词开始成为官方认可的地理概念的标志之一,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此番改动的原因。而从一个地理概念形成的角度分析,这样理解也有利于打消《朱批谕旨》带来的疑惑。当然,这仅仅是对《奏折汇编》和《朱批谕旨》进行比较的结果,还不能作为最后的结论。笔者在检索《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北五省”这一地理概念的使用,而《奏折汇编》所载的雍正君臣早年对该词的使用也确实流露出随意的特点。就目前学界掌握的清代汉文奏折来看,基本是出现于康熙中期以后,(15)换言之,“北五省”即便在雍正年间以前的奏折朱批中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公认使用的地理概念的可能性也非常小。除了奏折外,在检索《清历朝实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北五省”一词是在乾隆年间方才出现,并随之使用日益增多的。(16)显然,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结论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肯定的是,“北五省”的广泛使用至晚应开始于乾隆初年。故综而论之,笔者认为该地理概念是出现并形成于雍正年间,以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为其中的关键阶段。
二 “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区域范围
使用一个地理概念的价值在于运用它所具有的区域指代作用。表面上,“北五省”的范围包括哪些地区似不难确定,只要找出对应的五个省区,其区域之和即是答案。下文研究中遇到的资料表明,这个问题远比人们想象得复杂,本应有五个省区对应的“北五省”,却因甘肃的加入而成为“六省”,尝试解释这一“名不副实”的现象就成为确定“北五省”范围的关键。还是先从史料说起:
沈廷芳……又称北五省连岁有荒歉之处……强者鹿铤,弱者填壑。伊岂不知上年直隶、山陕俱属丰收而捏造此无稽之语乎?(17)
朕思……边省暨北五省庶吉士类然。翰苑中江浙人员较多,而远省或致竟无一人者,非所以均教育而广储才也。嗣后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令习清书。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亦视其人数,若在三四员以上,酌派年力少壮者一二人。(18)
奉上谕禁止烧锅一事:“……朕屡次所降谕旨及孙嘉淦所奏与王大臣、九卿等所议,悉行抄录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督抚各抒己见。”……烧锅一事……又命北五省督抚各抒己见。(19)
北五省最重麦田……豫省河以南南阳、汝宁、陈州、光州等府州属南阳、汝阳等州县亦于初五日得雪二三四五寸不等,盖以地近江南,故得雪之日亦同。而河北卫辉等三府……山东、山西、陕西、直隶等省近日俱未奏报得雪。(20)
诸上史料虽未明说“北五省”到底包括哪些省区,据语境推知即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省份皆在北方且数目对应,似与“北五省”所指若合符契,故区域范围即可划定。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也有类似如下的记载:
河南巡抚硕色奏称……朕思北五省情形大率相近,即州县中无额设公费。而伊等原奏皆有酌量兴修之处,何以不能依限完竣?著将硕色此折,再行钞寄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督抚阅看。(21)
议立北五省烧锅躧麴禁令。各省督抚覆奏,大抵以开行兴贩着宜禁,而本地零星酿造宜宽……惟陕西省奏称:秦俗本俭,民间祭祀庆吊,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烧酒,用黄酒专需细粮,转于民生不便。且边地兵民藉以御寒,势难概禁。甘省则以本非产酒之区,勿庸设禁,乃令因地制宜,并定违禁律。(22)
北五省: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均奏报于五月得雨优渥,只甘肃未据报到。而江南今据萨载、吴坛、闵鹗元先后驰报通省甘霖大霈,处处沾足,秋成可期,一律丰稔云云。(23)
史料多次提及甘肃,而一般认为陕甘早在康熙六年即已分省。难道明明“六省”,却偏称“五省”?矛盾背后,到底是何原因?
作为地理概念,指代范围具有弹性不难理解,学界对“江南”的厘定便是一例。(24)然而,“北五省”却不能套用惯例,这与其特殊性有关。该词是依行政区划构造出来的,政区又是人为划定的施政区域,此与划分“江南”原则的多面性特点迥然有别。换言之,其一旦作为专有地理概念得到公认,对应省区即应确定,区域也就随之划定。因此,这里不能以指代范围具有弹性来寻求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甘肃是否应纳入“北五省”的范围,只有对清代甘肃及相关省份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方有可能为解答提供思路。陕、甘二省原统于明代的陕西布政司,后经康熙六年陕西分省,甘肃始自成一区。学界多将陕西与同时期的江南、湖广相提并论,认为三者的分省是“由旧省制向新省制的改革过程”(25)。但相比之下,对江南、湖广分省过程的关注要远多于陕西分省,(26)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始终是讨论的热点,诸如史籍记载分省年份的差异和旧省名长期沿用的原因等。有趣的是,两点中对于陕西分省除前者稍有争议外,后者却从未引起类似的疑问。而所谓旧省名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指分省后,实际意义上的“江南省”、“湖广省”已不存在,但其称谓却在官方文书中沿用至清末。笔者以为,学界从未就陕西分省的旧省名沿用问题产生质疑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类似的现象。其实,稍做分析便可发现陕西与另外两省的细微不同。江南、湖广省一分为二,分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两个原省称谓本应“实亡名亦亡”,陕西省一分为二得陕西、甘肃,陕西之名并未消失而是沿用下来。清人魏源对此间微妙差异曾有洞悉,其云:“本朝又分十三省为十七省,若湖广为湖南、湖北,江南为江苏、安徽,陕西之西为甘肃,直隶关外为奉天。”(27)前曰陕西分得陕西、甘肃,说法别扭且有失严谨,魏氏已然察觉,故才有如是说法。换言之,甘肃从陕西分出后,“新陕西”虽与“旧陕西”在地域范围上迥然有别,但其称谓却完全一样。如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倘若在陕西分省后的官方文献中仍然出现陕西实指原来的情况,我们却无法辨别而只能将其理解为分省后的新陕西。这或许就是学界从未对陕西分省是否存在旧省名沿用现象投以关注的原因。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还需引用史料继续讨论:
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有老瓜贼……近又闻得此种老瓜贼北五省皆有,而陕省固原州等处尤多。(28)
北方五省,惟甘肃尤为瘠贫。(乾隆)二十一年以后叠免连年额赋。(29)
以上二条史料不难理解,但所用地理概念却稍有些前后矛盾。前者固原州在陕甘分省后一直属甘肃,此处却云“陕省”,后者则意指甘肃为北方五省之一。其实,留意一下其他官文书和文人笔记的记载,类似情形并非孤例。难道时人在如《实录》这样的官文书中也会“疏误”至此吗?笔者以为,原因绝非此一言可蔽之。此处的“陕省”只有在实指分省前的陕西时,云“陕省固原州”于理方通。反言之,这正表明“陕西(省)”一词在分省后的官文书中是存在旧省名沿用现象的。同样,甘肃被纳入北方五省,只能用其在地域上归属分省前“陕西省”的范围来解释。总之,承认陕西分省后存在旧省名沿用的现象是我们对这一系列“矛盾”的唯一合理解释。据此便可对前文甘肃是否应纳入“北五省”的问题进行回答了。
史料在出现甘肃的情况下,北五省中的“陕西”当是指分省后其所对应的区域范围,即与今日之陕西省境相近。而未提及甘肃的史料,则无法判断其是指分省前后的哪一个辖境范围。如果是指分省前的陕西,那么显然就应当属于和江南、湖广省类似的旧省名沿用。如果是指分省后的陕西,则会面临一个问题,即甘肃这一区域就会遭到排除。因此,很有可能正是要顾及到甘肃,故才出现前面提及该省的情形发生,但如此一来却不免造成“北五省”领有六省的“名不副实”现象。如果不承认“陕西省”存在旧省名长期沿用的问题,那么上述这些在研究“北五省”范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便无法得到圆满解释。而在陕西分省后,官文书中并没有就前后两个“陕西”在区域上存在的差异做出说明,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明,因此并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清初以后文献中的“陕西”一词便一定是指分省后陕西的区域范围。
在史料中,笔者无法辨别随距离分省时间的久远,官文书中因意识到此时“陕西”已非过去“陕西”而刻意提及甘肃有所增多的趋势,也就无法从时间划分的角度对文献中不同区域范围的两个“陕西省”做以区别。行文至此,面对官方文书中一面“口口声声”的在使用“北五省”,另一面所指却有六省的矛盾便可豁然解决了,“北五省”所谓的“五省”包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其中“陕西”在地域上实指分省前的陕西省,也就是分省后的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范围。“陕西(省)”一词在清代文献中和“江南(省)”、“湖广(省)”一样都存在旧省名长期沿用的现象,提及甘肃正是为了避免因为新陕西的出现而遗漏指代区域的问题。
上文研究认为,“北五省”是雍正末年逐渐被官文书认同并正式作为统一的地理概念开始使用的,但陕西分省却早在康熙初年。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北五省”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康熙初年以前北方地区省级行政区划的情况,或者说,尽管在今天看来康熙初年陕西分省是“无可辩驳”的史实,但在清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陕西和甘肃仍可合而为一视之。其实这也说明,从明代以来北方地区即已形成的五个高层政区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三 “北五省”概念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
北五省没有任何对应的行政机构产生,为何要使用范围如此之大、又无对应行政机构管理的地理概念呢?下文拟就其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进行简要分析。
(一)明清高层政区的不断调整变迁
省自元代始成为高层政区,其划分历有争议,周振鹤指出:“其作用主要不在行政管理,而在军事殖民。”遵循犬牙相入,而非山川形便,特别是“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30)。此外,多数省的幅员异常广袤。如中书省、河南江北行省都坐拥后世数省之域,幅员之恢宏为历朝所不逮。明代改其为布政使司(习称省)并加以调整,总的趋势是缩小幅员,如分中书省为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从河南江北行省中分出。尽管其时北方地区由五个高层政区构成的格局已经出现,但“北五省”的称谓却并无出现的可能,一方面因布政使司是高层政区的正式称谓,另一方面也和明代的两京制不无瓜葛,其中南、北直隶是有别于一般布政司的高层政区,纵使其与其他布政司并列,也不习称为省。(31)换言之,北直隶并无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并称“北五省”的可能。
清代高层政区幅员继续缩小,如分陕西西北部为甘肃。在此基础上,改两京十三布政司为十八个高层政区,之所以无正式称谓,盖因当时将总督、巡抚辖区调整与原先布政司重合,并使之成为最高长官,原来省所对应的行政长官——布政使——反成为其下属,此时若再称高层政区为省就不免牵强。起初确实如此,但后来情况又有改变,人们逐渐接受督抚辖区成为高层政区的事实,并将过去对高层政区的俗称——省——沿用过来,官方文书中的使用遂又增多。北直隶入清后改为直隶,成为十八个高层政区之一,官方文书中直隶称省亦习以为常,此方为北五省的出现提供了客观可能。
尽管从地理词汇的角度,“北五省”本身可能要晚至康熙年间以后方能出现,但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我国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所谓北方地区,基本由五个高层政区组成的行政空间格局却由来已久,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北五省”,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理概念。
(二)南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
对以自然地理为基础导致的我国南北方区域差异的认知,自古有之。唐宋以降,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使区域社会的发展总体大大超越北方,而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扩大了原本就已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性。这一差距在明清时期并未缓解,反而日益拉大。对此,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必然都会在行政管理的层面有所认识和应对,前引提及北五省庶吉士习清书事和并举北五省、江南雨水情况的描述,都是类似区域差异性的侧面反映。类似的史料还有许多,例如:
朕六十年来,留心农事,较量雨旸,往往不爽。且南方得雪有益于田土,北方虽有大雪,被风飘散,于田土无益。今岁山东得雨,河南、山西、陕西未甚得雨,备荒最为紧要,不可不预为筹画。若直隶、山东、河南已难料理,至山西、陕西其补救尤难。(32)
今定以入学一名,州县取六十名,府取三十名。如大县入学二十五名,则州县应取一千五百名,府取半之。在北五省尚恐不及此额,仍无可为为去取。南省如福建、江西、江南、浙江则一州县儒童,常至盈万,少亦数千。(33)
至北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其应如何劝戒百姓,或延访南人之习农者以教导之。(34)
诸上史料在使用“北五省”这一地理概念时,皆以之与南方地区进行比较,这实际反映出,时人对南北方区域差异性及其社会发展不平衡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明清时期长江以南的地区而言,“江南”是地理概念中最具独立性和特色的一个。除清代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省外,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江南指苏南浙西地区,对此时人已有以五府或七府的政区划分方法来进行界定。(35)后者在地理范围上日益受到重视和区分现象的本身就反映出其在全国范围内地位的突出。北方似乎一直缺乏类似“江南”一类的用来描述自身范围的地理概念,“北五省”的运用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种缺失的表现。
此外,还有一些可能促发“北五省”地理概念产生的因素。比如美国学者施坚雅就曾指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显著。”(36)尽管施氏得出该观点是为了引出对“另一种空间层次认识”需要的讨论,但这足以提醒我们应当对明清以来行政区划体系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保持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在政府管理的层面更应注重各级政区从中发挥的作用。显然,在时人日渐以行政区划来进行空间认知的背景下,“北五省”一词的出现无疑会更容易被社会、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所接受和认同。
四 “北五省”地理概念的消亡
前文对“北五省”这一地理概念考察的依据,主要基于官文书或地方官员的奏议、笔记等。民间文献中的类似记载,笔者虽收集到一些,但总体而言数量不多且与本文欲解决的问题并无直接联系。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北五省”作为一个宏观的地理概念主要为官文书所用并不难理解,其实也只有从国家这样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观察地方,才会在描述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构造出“北五省”一词。随着清末民初政治形势的改变,该词没有被沿用下来,而是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五省”是一个具有浓重行政意味的地理概念,由清代北方设立的五个省共同组合而成,它具有十分广大的区域范围,可以说是为了满足当时国家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而构造出来的。当支撑这一地理概念使用的政治基础消失后,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也就成为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进入民国时期,政府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使用“北五省”一词,其他文献中也已不多见。(37)除与政治基础的变动有关外,“北五省”概念的消失可能还与民国初年北方地区省级区划的调整有关。在清末奉天、新疆、台湾建省以前,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在当时全国设立的十八个省(38)中确实位于北部,并且涵盖了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合而称之为“北五省”并无不妥。但实际上,清代的国土疆域范围却远比所谓的十八省之境大得多,到民国初年不仅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已建省,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原本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区也成为与省平级的特别区域,它们纷纷组织省制促进会,发表宣言,积极推动改省,并终于到南京政府时期实现了设省之议。(39)此时如果再翻开地图来观察“北五省”在全国省级政区中所处的地理位置,那么显然其称谓与实情之间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总之,政治基础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省级政区调整都应是造成“北五省”概念消亡的根本原因。
“北五省”一词虽然日渐淡出,但整个社会对于寻求一个指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地理概念的努力却并没有消失。“华北”地理概念的出现,显然使之得到满足。据张利民研究,16世纪末以后,来华传教士使用“North China”或“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来描述中国北方。后者常出现在传教士撰写的报告或文章的题目中,一般被译作“北方诸省”。到1891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中文期刊《华北月报》,其英文刊名中包括“North China”。20世纪初,由“North China”汉译而来的“华北”一词“成为人所共知的有一定空间范围的地域名词”(40)。换言之,“北方诸省”和“华北”两词的英译皆可作为传教士描述中国北方的地理概念。笔者以为,“北方诸省”与本文讨论的“北五省”颇具神似,至少在使用几个省级区划来共同描述中国北方这一层面,两个分别被外来传教士和清政府官文书使用的地理概念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然,这不意味“北五省”和“华北”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前后替换关系,“华北”地理概念自有其出现、形成、传播和认同的演变过程。本文只想强调,“华北”一词“成长”为地理概念的过程如此顺利,以至于“北五省”在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此,新地理概念的出现虽然不是导致“北五省”一词消失的根本原因,但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可以将其看作是外部因素。
五 余论
以上所论“北五省”在雍正和乾隆初年间的转变,基本可将此地理概念出现的时间过程勾勒出来。至于区域范围,本文倾向于说明这样的逻辑关系,即只有承认官文书中的“陕西(省)”,也和“江南(省)”、“湖广(省)”一样存在旧省名长期沿用的现象,才能对史料中出现“北五省”对应六个省的“抵牾”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样,相信史料中出现的“抵牾”绝不是“偶然疏误”的结果,其背后必然蕴涵着可以解释的深层次原因,又是支持“陕西(省)”存在旧省名沿用现象的基础。二者可谓互证关系,缺一不可。该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在使用清代文献中的“陕西(省)”一词时,应对其指代的区域范围做具体的分析,以往持有的片面认识应有所修正,同时也应将其纳入到对清初分省过程的系统研究中,改变过去认为陕西分省“过程简单”的成见。学界对“江南省”、“湖广省”称谓长期存在的原因已有深入讨论,其中之一就是明确提出:“‘省’不但是省级行政区划的俗称,也是总督、巡抚、布政使司等省级官员和衙门的通称。”(41)换言之,是江南、湖广总督的长期存在,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前述两省名称得以沿用。陕西分省的结果稍与之不同,乾隆初年陕甘总督之设成为定制以后,(42)我们并未找到“陕甘省”的称谓,文献中沿用旧称的“陕西省”恐怕还是指作为区域概念的省级行政区为主。“省”这一概念在清代作为习称,可能更具弹性,江苏、安徽可以各称为省,合在一起仍可称为江南省,同样,陕西、甘肃各称为省,合在一起也可称陕西省,尽管在制度层面上,这并不符合概念条理化的逻辑,但在当时却是约定俗成的使用。甘肃出现在“北五省”的范围内,或许只是对此的小小修正。
“北五省”作为地理概念,包括的范围十分广阔,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长城以南的北方全部地区,它具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多在官方文书中出现,也说明该词主要是出于方便行政管理的需要。其特殊性还表现在,是由数个高层政区组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似乎也是省制以来并不多见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北五省”的出现,可以视为是当时社会对北方区域整体趋同性认知的反映,这种认知既有来自区域内部自身的整合力量,也有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日益加大的客观推动。在明清以来我国内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从一个区域对应地理概念的形成史角度出发,“北五省”概念还是我国传统意义上北方区域概念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论成熟与否,其毕竟在清代中后期成为那个时代官方指代北方区域最为常用的地理词汇。由于支撑其使用的政治基础的崩溃,以及民国时期省级政区的不断调整,它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但大的历史环境并没有改变,“华北”一词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北五省”概念的消亡,而且最终成为全社会接受认同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广为使用的地理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清]王庆云著,王湜华点校:《石渠馀记》卷四《纪常平仓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五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44页。
④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6—425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下同。
⑤《四库全书》第417册,第388页。
⑥《朱批谕旨》卷一七六之一“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云贵总督臣高其倬谨奏”,《四库全书》第423册,第637页。
⑦《朱批谕旨》卷四“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臣杨宗仁谨奏”,《四库全书》第416册,第186页。
⑧《朱批谕旨》卷二二三上“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署理江苏巡抚臣尹继善谨奏”,《四库全书》第425册,第818页。
⑨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年,88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编辑说明》,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第2—3页。
(11)《奏折汇编》第1册,“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按地摊丁以除穷民苦累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第498页;“□”为笔者无法辨识之字,下同。
(12)《奏折汇编》第2册,“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雨水米价折·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第646页。
(13)《奏折汇编》第2册,“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报雨水收成粮价折·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第973页。
(14)《奏折汇编》14册,“署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报地方得雪日期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编辑说明》,第2—3页。
(16)案,《清高宗实录》中有关“北五省”的使用,下文讨论还会引用,兹举笔者见到的最早一例,即《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乾隆二年五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725页。
(17)《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七,乾隆八年七月下乙巳,第531—532页。
(18)《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乾隆十六年闰五月上甲戌,第125页。
(19)[清]尹会一:《健馀奏议》卷二《河南上疏》,乾隆年间刻本。
(20)《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七六《两江总督书麟报雪诗以志事》(乾隆壬子冬)诗中注,《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134—135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乾隆十三年正月下戊申,第19—20页。
(22)[清]王庆云:《石渠馀记》卷五《纪酒禁》,第267页。
(23)《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七五《山中》(乾隆庚子六月)诗下注,《四库全书》第1308册,第518页。
(24)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25)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26)参见谭天星:《湖广分省时间小议》,《江汉论坛》1986年第5期;季士家:《江苏建省考实》,《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季士家:《安徽建省考》,《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季士家:《江南分省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朱楞:《江苏建省时间辨析》,《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单树模:《“康熙六年江苏建省”说确切无误》,《江苏地方志》1990年第6期;王社教:《安徽称省时间与建省标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王亮功:《安徽建省考析》,《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季士家:《安徽建省时间再议》,《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刘范弟:《湖南建省考疑》,《湖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王社教:《再论安徽称省时间与建省标志》,《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张建民:《湖广分省问题述论》,《江汉论坛》2003年第12期,及傅林祥前揭文。案,此间竟无一篇专文论及陕西分省者。
(27)[清]魏源著,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下)附录卷一二《武事余记·掌故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0页。
(28)《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九,乾隆七年正月下壬午,第10页。
(29)[清]王庆云:《石渠馀记》卷一《纪蠲免》,第16页。
(30)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241页。
(31)按,明人的一些说法可资佐证。如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以卷分区,云:“两都”、“江北四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以王氏之见解足窥时人对全国大区划分的基本认识。而晚明徐光启在《辽左阽危已甚疏·守辽事宜》,云:“推举重臣二员,总理江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边选练事务,委任责成。”虽以“五”冠之,但仍称“省直”者,亦可为证。《明经世文编》卷四八八《徐文定公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382页中。
(32)《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康熙六十年四月己酉,第840页。
(33)《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九年十二月上丁巳,第972页。
(34)光绪《清会典事例》第2册,卷一六八“乾隆二年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132页。
(35)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第4页。
(36)[美]施坚雅(Winiam Skinner)主编,叶光庭等合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37)参见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地理志·交通》。另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曾于民国十年发表论著《北五省旱灾之主因暨其根本救治之法》,针对当时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灾情提出治灾之策(参见中国水利学会、黄河研究会编《李仪祉纪念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第43、214页)。
(38)清代所谓的“十八省”之地,大抵可看作是承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而来,如《清史稿·地理志》云:“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
(39)参见傅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65—66页。
(40)张利民:《“华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41)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42)按,康雍至乾隆初期,围绕川、陕、甘三省间的总督设立异常繁复,总的来看,四川、陕甘总督的分合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和平时期两者并立的趋势比较明显。康雍时期陕甘总督实际一直称为“陕西总督”,至乾隆以后才改为“陕甘总督”。至于改动的原因或许可以从本文的结论中获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