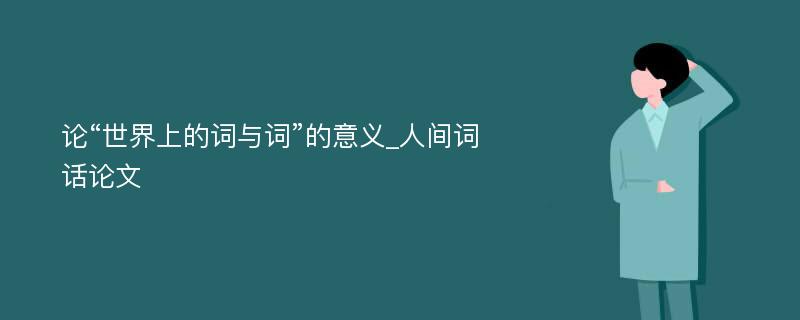
《人间词话》意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意境论文,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说的本义,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两方面论述了意境的始源及其发展,阐明意境说的局限,得出了“不能以意境之有无判断诗歌优劣”的结论。
关键词 意境 词 本义 始源 局限
自从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以来,“意境”便逐渐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当代,诗学界、词学界、美学界、艺术界、文学史界、语言学界、文艺理论界,乃至哲学界、心理学界、园林建筑界,等等,都大有人爱谈意境;发表有关意境问题的论文之多、专著之夥,均呈现出空前盛况。
至于对意境本义的探讨,则有所谓“真情景”说、“情景交融”说、“主客观统一”说、“形象或典型”说、“感兴联想”说、“心理场”说、“读者审美”说、“作者读者共创”说,等等。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在美学领域,更有人将意境置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中心位置”,迷恋于凭意境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美学科学体系”。据说,意境产生的历史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甚至可以远推到半坡文化彩陶出现之时;而其适用范围,则只要能名之“艺术”者,均可囊括无遗。同时,还断言意境具有“无穷尽的生命力与包孕力”,将千秋万代永远主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从而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区别开来。
人们对意境内涵的理解竟然如此分歧,而其时空外延又竟至如此广阔;那么,此中奥秘究竟何在呢?为此,本文将从探索《人间词话》意境之本义入题,并进而追溯其始源,最后论述意境并非万应灵丹,中国古代诗词之本质更在于展示作者之情感个性,以求较准确地把握意境之真实内涵,还原其本来面目,在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美学史上给意境一个合乎其身分的恰当位置。
一、意境的本义
《人间词话》论词以意境为核心,且多以“境界”替代意境,开卷第一至九条便专论词的境界。第一条云: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王国维这段话表述得非常清楚:他的意境(境界)说是用来论词的。即使对词来说,意境也不是评论的唯一标准,而只是“最上”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唯有五代、北宋之词“独绝”;至于南宋词,就不免差劲了。在《人间词话》及其《删稿》、《附录》的全部论述中,王国维是基本上坚持了以上观点的。试看: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
这里说的所谓工不工,就是以意境作为衡量标准的:工者,有意境也;不工者,无意境也。诚然,王国维赞赏的词家,确实有其代表性,较准确地反映出了五代、北宋之词的艺术成就,其深具意境美则更不待言。但是,这又不免暴露了意境说的极大局限性,它基本上不能用来衡量南宋词,更难用来衡量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这些对宋词发展有杰出贡献的大家、名家。然而,王国维终究具有非常敏锐的艺术鉴赏眼光。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并不以意境去范围一切词人词作。在其批评实践中,除意境外,他还常用“气象”、“气韵”、“胸襟”、“品格”、“神理”、“风骨”、“自然”、“性情”、“寄兴”等传统诗词批评用语,进行具体鉴赏分析。例如,他深知苏轼、辛弃疾在宋代词坛的崇高的历史地位,更明白不能以意境说去局限苏、辛词。这时,他的批评就另具慧眼了——
苏、辛,词中之狂。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
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可拟耶?
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
这些评论,对苏词则根本不涉及意境;对辛词,虽云“有意境”,却又曰“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但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这些评语都言简意赅,精确切当,堪为苏、辛词评之圭臬。由此可见,《人间词话》虽以意境说为其理论核心,却实在没有将意境作为词学批评的唯一标准。
从形式逻辑角度来看,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那么,意境的内涵究竟如何呢?《人间词话》有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话: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不论对意境作何种解释,人们大都认为这段话最能体现王国维对其意境内涵的界定。事实上,这种看法完全误解了《人间词话》意境说的真意。其原因就在于王国维是以意境来评论词体,特别是唐五代、北宋词体的审美特征。“词与诗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被偶人以袞服,饰淫靡为周、柳、假豪放为苏、辛,号曰诗余,生趣尽矣。亦何异诗家之活剥工部,生吞义山也哉。”(田同之《西圃词说》)由此看来,所谓“真景物、真感情”虽然是构成意境的基本因素,但却是诗、词、曲,乃至某些抒情性山水散文所共有的,并不能体现词意境的独具有审美特征。而最能体现王国维词意境所独具的本质审美特征的,当为《为间词话》中另一段名言: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这段话通过诗、词比较,阐明了词体两方面互相联系的审美特征:一是“要眇宜修”,二是“言长”。所谓“要眇宜修”,语本屈原《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王逸注云:“要眇,好貌”,“修,饰也”。洪兴祖补注云:“此言娥皇容德之美。”这是形容湘夫人意态窈窕娴静,修饰打扮得恰到好处。王国维借用此语,则是形容词体精微柔婉,转盼多姿,含蕴深隐,富于感兴。这正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引御卜(黄鸥)所言:“词体如美人,含娇掩媚,秋波微转,正视之一态,旁之又一态,近窥之一态,远窥之又一态。”所谓“言长”,则是对词体“要眇宜修”美的补充,意为情韵深长。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强调词体“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可以说是“词之言长”的最好注释。
王国维强调的这种与诗不同的词体特质,也就构成了词的意境。这种词意境是兼具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言的,主要在于阐明词体有如美人的精微柔婉的外在形式,传达深隐曲折而富于感兴力量的心绪心曲,特具悠远深长的余意余味。通观《人间词话》以意境(境界)为标准所评及的全部词人词作,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所谓“有境界”,便是具有此种特质;而所谓“无境界”,便是不具有或缺乏此种特质。事实上,王国维所赞赏的五代北宋词家冯延已,李煜、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诸人,均属传统婉约词人,其词作也都是深具此种特质的。再看其对姜夔的批评: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其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不论这种批评是否准确,是否能使不同鉴赏眼光的读者满意,王国维意境说之主旨却是率直地透露出来了——这就是所谓“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王氏认为姜夔词是缺乏意境美的。其实,如果从传统表现手法来看,这种意境美也就是词体的“深于比兴”。陈匪石《声执》卷上“比兴说”条云:“夫论词者,不曰‘烟水迷离之致’,即曰‘低徊要眇之情’。心之入也务深,语之出也务浅。骤视之如在耳目之前,静思之遇于物象之外。每读一遍,或代设一想,辄觉其妙义环生,变化莫测,探索无尽。庄棫曰:‘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实有未易以言语形容者……故造此境难,读者知之亦难。”这段话,即以词体“深于比兴”为出发点,具体地、细致地论说了《人间词话》所强调的“要眇宜修”及“言长”特质,也就是词体的所谓“最上”境界了。
总之,词意境虽大率由情意,景物所构成,并特别要求“真”,反对“伪”;但即使有了真感情、真景物,并能情景交融、主客观统一地表现出来,却仍然不一定能构成“最上”的词意境。因为构成“最上”的词意境的更为本质的条件,还在于描绘烟水迷离的境界,蕴含低徊要眇的情感,具有探索无尽的余意余味。这种“最上”的词意境,也就是词之所以区别于诗的最本质的审美特征。
二、意境的始源
王国维以意境说词,其核心在于对词体的“要眇宜修”与“言长”的本质审美特征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其实并非王国维的个人发明,而是宋代以来绝大多数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北宋后期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一文,就曾明确提出了所谓“韵”的审美观点,要求词作具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深厚韵味。南宋末张炎《词源》卷下评秦观词亦云:“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沈义父《乐府指迷》引述吴文英“论词四标准”,其中两条便特别强调:“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至清代,词学中兴,这种见解更成为词人与词论家们的共识。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说:词“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张惠言《词选序》以“意内言外”释词,虽歪曲了“词”之本意,却较深刻地把握了词体“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比兴特征。自此以后,词学界对词体本质审美特征的认识日益深入,而词境之说也随之兴起:
司空表圣云:“梅正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严沧浪云:“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此皆论诗也,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刘熙载《艺概·词概》)
蔡小石《拜石词序》云:“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紵地,余霞绮天。此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飚飞摇;骏马下坂,泳鳞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翛然而远也。”诒案: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七)
词“必须沉郁顿挫出之,方是佳境”,“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这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卷一)
实际上,清代出入常州词派的词论家们,如果不论其艺术见解的差异,其主寄托,主意境却是一致的,而寄托说与意境说又相辅相成,并驾而行。尤其是陈延焯与况周颐,对词意境更有深入的阐说,况周颐比王国维年长十八岁,仅早逝世一年,其《惠风词话》虽主“重、拙、大”说,但意境说实已成为其论词主导思想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只因为其“重、拙、大”说所掩盖,而未能使人认识其本来面目。《惠风词话》有两段论述词境、词心的名言: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怅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
这两段名言,纯以形象描绘取胜;但对于词体意境内涵的认识,却比《人间词话》“要眇宜修”与“言长”说更丰富,也更深刻。首先,它从“要眇宜修”的词境直入词心,深切地把握了词体描写人类深层心曲的心绪文学性质。其次,它摒弃了传统的那种仅止于表象的对词体的香艳美人的认识,发掘出词中深蕴的“万不得已”的“无端哀怨”,即由“忧患意识”积淀成的悲剧型美感。
至于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意境说的贡献,就在于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意境说为其词论核心,对意境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并以此评论词人词作,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使意境说风靡开来。
就大范围来说,词仍属于古代诗歌领域,它只是一种配合唐宋兴盛的燕乐而歌唱的新体抒情诗而已。因此,词意境的源头实出自诗意境。诗意境虽然深深植根于儒、道、释之哲学理论(如《易传·系辞上》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庄子·外物》之“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说,禅家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顿悟说,等等)。但儒、道、释的种种理论,只能视为哲学。它们能启示人们的文学意识和审美观念,却不能替代人们的文学意识和审美观念。即如佛家的“境界”说,也仅止于一种“无差别”的“涅槃”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境界虽与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境界颇有相似相通之处,但也只是相似相通而已;无论其对意境说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却决不等于意境说,也不能视为意境说的始源。
意境说的真正始源,实为诗家的比兴说。汉儒们解释比兴,无论是郑玄还是郑众,都还只认识到情、物之间的比较简单、比较原始的表面联系。直到梁代钟嵘《诗品序》以新义解释比兴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这种强调诗歌审美效果的认识,就比较接近于意境了。随之,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提出“比显而兴隐”的意见。其《隐秀》篇则更明确认识到:“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彩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这些话虽还未能提出“意境”或“境界”来;但对“意境”的基本内涵,无疑已有了比较深刻的理性认识。
唐代,古代诗歌发展到极致顶峰;丰富而成功的创作实践,自然孕育了意境说的诞生。中唐诗僧皎然主张“诗情缘境发”(《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在《诗式》中,他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最高标准: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诗式·辨体一十九字》又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强调诗歌写作的关键在于“取境”,也即是意境的创造。至此,意境说方才正式降生于艺术审美的广阔天地间。
唐末,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韵味”说,强调“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而美味却在“咸酸之外”(《李生论诗书》),主张诗歌要讲究“象外之象,景外这景”(《与极浦书》),“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就不但论及了诗歌意境的创造,而且认识到了欣赏者在审美过程中进行的意境再创造。其《与王驾评诗书》更说:“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所谓“思与境偕”,即是要求意境基本构成因素——物、情关系的和谐融贯:物是诗人情感加工改造过的物,情是既生发于物更支配于物的起主导作用的情。在《二十四诗品·含蓄》中,他又提出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主张,这与皎然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见解,可说是一脉相承了。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依盛唐诗歌之准则,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强调指出: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胧,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议论,除以禅喻诗之体例及现实针对性外,其他则不过是皎然、司空图意境论的系统化与凝炼化。至此,古代诗歌的意境说基本上已经完成,以后各代各家之说,皆不出乎其左右,但是,也正由于严羽的系统化、凝炼化作用,极大地扩大了意境说的影响。从此,由诗而词,而书画艺术,意境的使用范围也日益扩大了。《人间词话》第九条在全文引述了上引严羽那段高论以后说:“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词意境说,实际上也是传统诗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三、意境说的局限
与任何美学范畴一样,“意境”也是有其义界限制的。它仅能反映诗词艺术或其他相关艺术的一种含蓄、隐曲的风格或境界,而绝不可能囊括一切美学范畴,绝不可能具有“无穷尽的生命力与包孕力”。数千年文学创作的历史证明:中国古代诗歌主在抒情,主在表现诗人们的情感个性,而其抒情方式则大率表现有两种:一为含蓄隐曲,一为率直痛快。率直痛快的抒情诗歌无意境可言,但由于抒发的感情浓郁而真挚,却能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叩击读者心灵深处,并不妨碍其为绝妙好诗。
李白《将进酒》、《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名篇,杜甫《醉时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佳作,那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愤懑倾泻,那种“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的胸臆直抒,如大江奔流,似火山爆发,虽无含蓄隐曲之意境,却激动人心,震撼千古。谁能说这些名篇佳作不美呢?即以律绝类小诗来看,唐诗中亦确实存在一部分绝无含蓄可言的优秀作品。例如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淡笑静胡沙。”杜甫《三绝句》其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背留妻子?”或咏怀言志,或叙述议论,均独具特色,流传千古,谁能否认其崇高的美学价值?同时,唐诗中还有一类叙事性很强的咏怀写实诗歌,如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等,这些名作在文学史上都享有盛誉。如以意境说去加以局限,去寻求什么“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含蓄隐曲美,那也就无异于缘木求鱼,瞎子点灯自费蜡了。
与诗相比较,词更讲究含蓄隐曲;这即是说,词最具意境美。但是,多数苏、辛豪放词又别具另一种激动人心的超旷壮大美;这一特点,王国维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并不以意境去评论苏、辛词。至于柳永的许多俗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词情发露,形容务尽,当时即已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对宋词实具开创之功。虽为陈廷焯批评为“意境不高”,王国维指斥为“儇薄”、“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但这也只能说明“意境”说之局限,并不能否认宋代民众的审美慧眼。
文学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精神产品。万紫千红才是春,不可能只准许一花独放。词的流派风格,技巧手法及审美观点,也自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貌。即使是传统的婉约词作,除深婉隐曲、含蓄蕴藉,深具意境美者外,还有一类在情感表达上显直真率的精品。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孙巨源语曰:“小词有绝无含蓄,自尔入妙者。孙葆光之《浣溪沙》也。”贺裳《皱水轩词筌》曰:“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弃,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王士祯《花草蒙拾》曰:“顾太尉‘换我收,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袭此。然已为柳七一派滥觞。”以上三位清代词伦家例举的这些词作,都是婉约恋情词,但所抒之情显直真率、热烈深厚,“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绝无含蓄隐曲之态,但却堪为小词中之妙品、神品。如此婉约情词,也是不可能用“意境”去赏析其美的。
杨万里《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其《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又云:“个个诗家各筑坛,一家横割一江山”。诗家作诗如此,词家填词如此,各类艺术创作又何尝不如此。“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唐宋词的主体风格虽然深隐婉曲,以含蓄蕴藉见长,富于意境美;但婉约派各大家、名家亦各自具其面目,各自以词展示出各不相同的情感个性。更值得重视的是:柳永、苏轼、辛弃疾诸家,冲破传统,自树帅旗。词如其人,他们各自利用小词,分别表现出才子词人、高旷志士、爱国英雄的独特抒情个性,不但极富创造性,而且成为宋代词坛开宗立派的宗师。这就充分说明:唐宋词丰富的创作实践,比较偏于一面的意境理论更具有“无穷尽的生命力与包孕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