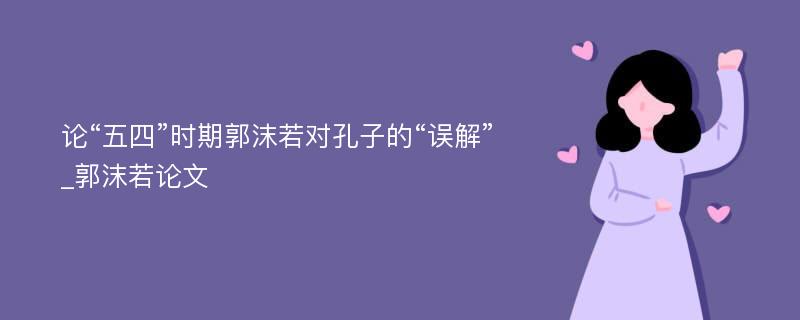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孔子论文,时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着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1919年底至1920年初,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这期间,他写出了《女神》中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堪称当时新文坛最杰出的诗章。学术界公认,这一部分诗作最能代表“五四”的时代精神,最强烈地呈现了郭沫若蔑视传统、蔑视偶像的叛逆性格。可谁曾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激昂口号的呼啸声中,作为“五四”时代精神杰出代表的郭沫若,高喊破坏传统、破坏偶像的留洋学生郭沫若,却在给他的好朋友的信中大谈孔子如何伟大,其赞美的程度近乎无以复加。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数篇褒扬孔子的文章。70多年来,对于这一奇特现象,众说纷纭,有“发展说”、“矛盾说”……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
一、作为青年诗人的“曲解”
对于这一问题的困惑也许首先来自于思维方式的简单化,即认为杰出人物正式发表的文字便是他全面思考的结论,便可以作为确定他当时思想的可以推而广之的依据。若发现以后的言论与之不同,便说成是“发展”;若发现同一时期的言论相互抵牾,只好解释成“矛盾”而空留困惑。其实,一个人的言论总是出自于特定的语言环境,总有言论者自己特定身分、特定前提、特定言论对象、特定言论出发点和特定的言论表达方式等一系列具体的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此作具体分析。
郭沫若这时期谈论孔子,其前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①郭沫若的出发点似乎是想把人们对孔子的误解纠正过来。可结果却是:他在纠正的同时自己又把孔子大大地曲解了。这种现象固然令人遗憾。但是,纠正一种偏颇的同时又走向另一种偏颇,这本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在青年人那里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又需要我们从郭沫若当时的特定身分来看他所理解的“孔子”。
孔子被郭沫若理想化了。他眼里的“孔子”具有以下特征:“球形的发展”的人;完全进入“自由”境地的人;将个性发展到极至的人;能自强不息、不断更新自己之人。不难发现,这时的郭沫若是在孔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而这种人格理想显然是出自于郭沫若此时作为“年轻诗人”这一特定身分的。当时的青年郭沫若,正处在从以自我为中心到摆脱自我为中心的转化中,处在从“权威危机”到确定人格楷模的过程中。此时,郭沫若显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以一个青年诗人的眼光看孔子。以这样的眼光看人,被观测者必然被涂上情绪化的色彩。这种情绪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他象年轻人那样渴求人格的全面发展。当时郭沫若把孔子视为十分“圆满的人格”。他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有他Rantheism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②。你看,为显示人格的“全”,郭沫若拔高了孔子在某些领域的成就(如作为科学家的成就),为强调“全”,郭沫若大量使用诸如“圆满”、“通人”、“精通”、“精透”等字眼。这都体现了年轻人思考问题不擅深思熟虑、用语常常缺乏分寸的情绪化特征。
这种情绪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他象年轻人那样渴求人格的独立和自强。孔子在郭沫若笔下是“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他以人之个性为神之必然的表现”。他赞美孔子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能“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③。“对于吸收一切知识为自己生命之粮食,他的精神每不知疲。他努力要作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真的‘自强不息’之道。人生在他是不断努力的道程,是如哥德所思‘业与业之连锁’。休息的观念在他是死,是坟墓。……他投身于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净化着去”,“把自己充实着去”④。这时的郭沫若是在把孔子奉为人格神。这是年轻人习见的对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伟大人格的向往。青年人本质上的展望性,使之特别向往“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的人格精神。然而青年人本质上的意志脆弱性,又使之难以达到实现自我完善的境地。青年郭沫若在孔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人格理想。于是,他不惜夸大孔子的自强不息精神。
其情绪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他以自己的诗人之心认同孔子。孔子本是一个讲究“克己”、讲究秩序的理性极强的思想家。可郭沫若却淡化了孔子的这些本质特征,而强化了他的“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忘我ecstasy(引者注:‘迷狂’)的状态”,强化他生活中的诗意:言孔子“坐于杏林之中,使门人各自修业,他自己悠然鼓琴的那种宁静的美景;他自己的实生活更是一篇优美的诗”。他渲染孔子“对于音乐的俊敏的感受性与理解力”⑤。他将孔子的“克己复礼”解释为:“所谓‘礼’,决不是形式的既成道德,他所指的,是在吾人本性内存的道德律,如借康德的话来说明,便是指‘良心之最高命令’”。⑥总之,他淡化孔子学说(本质上)的理性、克制、集体主义等特征,强化了孔子身上(非本质)的感性、自由、个性主义等特征。这分明是把孔子形象做了诗人化的改造。
原来,“五四”时期郭沫若所谈论的“孔子”是以他青年诗人的眼光所“看”到的形象,是他理想中的孔子形象。只是我们自己把他笔下的“孔子”与“孔家店”里的孔子合二为一了。焉能不产生疑惑呢?
也许有人要问:郭沫若此时看问题常带诗人的眼光是人所共知的,可他撰写那些褒扬孔子的文章时,他的年龄是在27岁至30岁。在那个年代这还算青年人吗?国际青年学研究界对“青年”的界定,主要依据三个方面:青年生理年龄,青年心理年龄,尚未获得职业和建立家庭。这时的郭沫若生理年龄处在“青年”后期,可他的心理年龄似乎还停留在“青年”中期乃至前期,虽然他已与安娜共同生活,可还没有结束学业。学生生活的延长和获得职业的推迟,使他依然保持着青年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结束留日回国以后,郭沫若才承受了来自求职和家庭的沉重压力,才开始出现了中年人的心理体验和行为特征。到40年AI写作作《孔墨的批判》时,表现出了中年人的成熟,论述孔子则显得客观、冷静而不象“五四”时期那么情绪化了。
二、“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
当承认了一个伟人曲解了另一个伟人的时候,我们的惯常思维表现是:或为之惋惜,或生怕因自己的浅薄而低估了伟人的高深,于是便想方设法为之寻找合理性和正确性依据,用以说明其实并没有曲解。这种反应和努力也许大可不必,只要确认曲解是历史的事实。
马克思早就揭示过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真理--“曲解的形式是普遍的形式”。他在1861年7月22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做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⑦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即后人对前人及其成就和经验进行为现实需要的“曲解”是“普遍的应用形式”。不“曲解”,就无法发展,更无法创新。而且,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内核的不同,因而在对不同文化的接受中难免不出现“曲解”。从中外文化发展史上看,几乎无不如此。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借鉴是这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也是这样。
事实上,所谓的“正解”本身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的理解(无论“曲解”还是“正解”),都只能是基于目前自身状况对事物的推想,也就是说对事物的理解,无论它是如何高深,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人们总是把最适应现实需要的理解视为“正解”。在生活中对事物的许多“曲解”,由于它满足了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反而被时人看作“正解”。甚至,一时的“曲解”竟能产生高于后人公认的“正解”的价值。只要“曲解”者能为自己的理解找到充分的论据,即使对事物的理解偏离乃至背离了原意,依旧能获得人们的共鸣。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孔子的崇拜,明显是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较大的曲解。这本身并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一直在被后人曲解着。如孟子、汉儒、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曲解孔子则如鲁迅所言“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反孔大旗,所反的是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代表偶像的“孔子”,而非孔子本人。李大钊在当时就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如此说来,郭沫若的崇拜孔子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既然当时的尊孔者绝大多数是站在封建旧营垒的一边,而郭沫若的立场是在新文化阵营一侧,可他为什么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与同一阵营的人们截然相反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新青年》杂志成员(一批较为成熟的中年人)为核心并领导着国内一代青年学生进行的。这批青年中即使与《新青年》杂志成员没有师生关系的人也几乎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们全新的知识、他们的思想观念、以至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几乎都来自《新青年》诸君。因而他们对其领导人是充分信赖的。再加上青年人在众多群体中的“从众”心理作用,使得他们难以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新青年》上所载的论述得凿凿有据的反孔文字。尽管他们与郭沫若年龄接近,也都是青年人。但郭沫若与《新青年》诸君没有师承和感情联系,不会自觉地受其观点的左右。他在国外受到西方文化长时间的亲知亲炙,能够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产生不同于国内学人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在郭沫若看来,他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是“一种新价值观的创造”。
三、曲解也是“一种新价值观的创造”
郭沫若在人生道路上总是擅于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事物作出自己的解释。如前所说,郭沫若这时期崇拜孔子,当然不是与封建复古派一同唱和。他不是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那样依据“弃古取今”的历史使命把孔子看作“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而是依据自我发展的心理需求在孔子身上看到了作为泛神论者、人本主义者、个性主义者的形象。先不说他这样理解对象本体是否准确,我们首先应当确定的是他在孔子身上是否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积极的东西。
“五四”中国需要冲决坚固封建精神壁垒的文化运动,郭沫若发现老子和孔子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Renaissance(引者注:‘文艺复兴’)”⑨。郭沫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经沉潜了几千年,要就我们几千年来贪婪好闲的沉痼,以及目前利欲熏蒸的混沌,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⑩显然,郭沫若不是全面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吸取被蒙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首要敌人是代表封建专制制度的“君”和“神”,郭沫若发现并利用了作为泛神论者的孔子。他把孔子和老子都认定为泛神论者。他说他在孔子和老子那里听到的是这样的心音:“我们的这种传统精神--在万有皆神的想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以至于无限……”(11)这是在以泛神取代具体的“君”和“神”。是想利用新的崇拜观念取代旧的崇拜观念。在否定“君”和“神”的同时肯定了作为万种“神”之灵长的“自我”。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专制制度的天然合理性,肯定了自我发展的天然合理性。
要推到代表封建专制制度的“君”和“神”,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郭沫若又发现了作为个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者的“孔子”。他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正是以个人为本位”(12)。“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待言是动的,是进取的”(13)。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正是推倒“君”和“神”所需的“动与力”。由此来看,郭沫若对孔子崇拜的意义不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观测传统的“眼光”。这是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化人、又不同于封建复古派的一种“眼光”。当中国古典文化运行了几千年面临着重新进行选择的时候,《新青年》诸君选择了借外力再造中国新文化,郭沫若则是想“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14)。但是,能否以此证明郭沫若比《新青年》诸君更高明更富于远见呢?
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历史老人只能是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事情”。当时中国的新文化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无疑是要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需得“刨祖坟”(批孔)。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应是决裂后的另一件事情。无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少精华,但它在本质上是封建精神的载体。当时的新文化人没有办法甚至都没有可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封建文化中剥离出来。当普通人还弄不懂“民主”、“自由”、“科学”对于他们有多大意义的时候,当封建复古派正高叫着“国粹”、“尊孔读经”的时候,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又迎接着封建复古派殊死顽抗的国内新文化斗士,若要他们既能继承孔子学说的精华、又能完成反封建的重任,这是他们的理智和感情都不会允许的,也是他们不可能意识到的事。倘使郭沫若身处国内反封建战斗的第一线,他还会这样固执己见吗?这可以用他以后的表现来证明这种假设不会成立:当他从日本归国以后不久,很快就放弃了留日时期的绝大多数文化艺术主张。并非是他的那些主张本身不合理,而是它们在实践中缺乏有效性。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⑨(11)(1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259、261-262、259、260-261、257、262、257页。
②⑩(12)(13)《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0、157、156、149-15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8页。
⑧《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