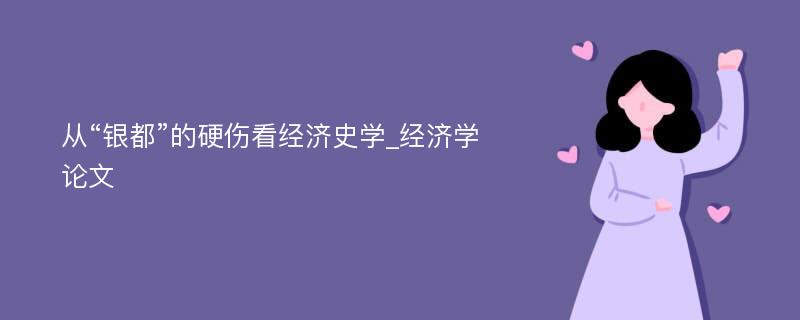
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硬伤论文,资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的《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中国中心论”:即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①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尽管该著作出版已经七年了,但学术评论此起彼伏,中国国内的经济史专业、经济思想史专业和历史专业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由此可见该书在中国影响之大。本人在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时,在导师的推荐下第一次读《白银资本》,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时,再读《白银资本》,近来给我的研究生讲授世界经济史,第三次读《白银资本》。三次阅读跨时八年,每次都以不同的心态阅读,第一次抱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态,感谢弗兰克为中国说话,第二次以审视的心态阅读,审视弗兰克以白银流动来判定谁是世界的中心这条思路是否可行,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两个月抱着反思的心态阅读,读毕,掩卷沉思,感叹良多。既感叹弗兰克的学术大胆,又感叹经济史学科的尴尬,想的更多的是经济史学科如何走出尴尬。基于这种感叹,怀着野人献曝的想法,从《白银资本》的硬伤联想到经济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②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如果把《白银资本》的前四章看作是描述性经济史的话,那么后三章则是典型的分析性经济史。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即繁荣阶段),17世纪初期中国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即衰落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入康氏周期的A阶段,1762-1790年中国进入危机和衰退时期,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阶段,而欧洲却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这就是1800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晚近的主流看法是,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无异于张冠李戴,这是《白银资本》的另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不过,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白银资本》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旗手,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白银资本》的硬伤给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学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严肃问题:在其他学科领域,带有硬伤的著作传世尚难,在经济史学界,却为何能引起经济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引起轰动效应?为什么具有轰动效应的经济史学著作往往出自并不通晓经济史的非专业经济史学家之手,而专业经济史家却难以写出这样的著作?
熟悉经济史文献的人都知道,近半个世纪来,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大都不是出自专业经济史学家。如《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所给出的分析框架和从经济史上得出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被经济史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广泛引用,但该书的作者诺思也不是专业经济史学家,他主要是一个以研究制度经济学著称于世的理论经济学家;再如《经济史理论》中,作者希克斯把人类历史上经济形态的演进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每种经济形态的运作机制与特点,这个概括几乎被当作一个公式或公理,各国经济史学家用来分析本国经济的演变,但希克斯从不作专业经济史研究,他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旗手,他著称于世的理论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IS-LM理论模型。在中国国内,经济史学家所撰写的论著,读者群往往局限于经济史学界,引起国际影响的则凤毛麟角,真正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史论著同样是出自非专业经济史学家之手,如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农业大危机的研究成果,被刊发于国际上公认的一流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来,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史命题,国内经济史学家也做了不少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却引起不了世人的关注。
以上所言,直指经济史学的尴尬,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经济史学的尴尬?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从自己视阈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于是又被它所折服,折服之后,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套用。由此看来,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再看一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素养。经济史因其学科特色而分为两支: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和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这两支从经济史产生之日起,就各自独立发展至今天。这种状况在英、美等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出身于历史学界的经济史学家,有深厚的史学功底但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研究成果是描述性经济史,这类经济史论著的功效在于复原历史真相,但不能从经济史中抽象出具有解释力的经济理论。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经济史学著作除了小圈子阅读市场外,很难进入非本专业学者的视阈,遑论轰动效应了。出身于经济学界的经济史学家,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但缺乏历史学素养,其研究成果是分析性经济史,这类经济史论著的功效在于抽象经济史规律,但由于其分析往往不是以史料为依据,不是依时序展开,所作推论经常有悖于历史逻辑,所得结论经常有违历史真相。此类经济史论著好看但不可靠,难以传世。
经济史家若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写出经受得起理论和史料双重检验的经济史著作,那经济史学科就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某一天经济史可能会沦落为其他学科的依附学科。这是因为从学术发展史看,很少有学科的经典著作不是由本专业的学者撰写的,若不然,这个学科就会丧失其独立性,缺乏独立性的学科又怎能不被人们所忽视呢!中国的经济史学状况就更加令人堪忧,不仅鲜有经济史学家写出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史著作,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加写不出优秀的经济史著作,至于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史著作,中国目前恐怕还没有产生。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水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有一个评价:在经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他给中国同行打A,价格理论是A[-],宏观经济学的打分不超过B,经济史和经济学派是C或C[+]。③蒙代尔对中国经济学水准特别是经济史研究水准的评价应该是中肯的。中国经济学界,一流经济学家当政府顾问和企业独董,二流经济学家当教授写论文(中国区分一流与二流的标准不完全靠学术水平的高低)。一流学者忙于顾问,自然无暇研究经济史甚至还看不起经济史,因为它不实用;二流学者出于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不愿意研究经济史,因为经济史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写出来的论文缺少载体来承载,专业刊物只有《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而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刊物多达100多家,费力不讨好的事是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不愿意干的。目前,只有历史学界的研究者们出于无奈固守在经济史研究的阵地上,出身于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者能改行的大部分改行了,或者是把经济史研究当作副业,愿意献身于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家屈指可数。这样一个状况,中国怎能产生高水准的经济史著作呢?
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以经济学和历史学为主阵地,涉及地理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方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生态学等学科,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科学学科。④譬如研究区域经济史,经济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研究基础,翻阅地方典籍,必须具备方志学、语言文字学乃至考古学的知识储备,如果研究的区域是民族地区,就要运用民族学理论,如果研究内容涉及到区域经济与人口的关系或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就得运用人口学和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要对区域经济变迁作田野调查,就必须掌握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研究领域的宽广性要求经济史学研究者具有综合学术素养,一流的经济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大师,必须上知源头、下明流变、中通相关学科。惟有通才,才能写出融历史感、现实感、理论感于一体的经济史论著。惟有这样的论著,才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史学也才能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
最后,向国内经济学家提出重视经济史研究的建议,也算是一个呼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史与经济学说变迁史之后发现,自1776年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经济学大师都产生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业革命至一战,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一战以后至今,一流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舒尔茨的解释是:某国一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那么解释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的理论就具有世界影响,谁最够资格解释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当然是生活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学家。按林毅夫的观点,不出现重大政治变故,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因之将产生一批经济学大师。林毅夫乐观地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⑤中国经济学家要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从现在起就要做好知识储备,优化学识结构,其中,经济史学识需要大补。国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其中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理论成就直接来源于经济史研究,除前列的诺思和希克斯,还有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及其弟子们、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等都写出过不朽的经济史著作并从中抽象出了经典经济学理论,如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就是从美国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近百年的货币史分析中推导出来的。经济学最善于节约学习成本,国外经济学家走过的路,国内经济学家不能视而不见。
注释:
①[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②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③[日]冈崎哲二著、何平译:《经济史上的教训》,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④赵德馨:《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养成》,《中国经济史学会2008年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部版)》,第3页。
⑤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