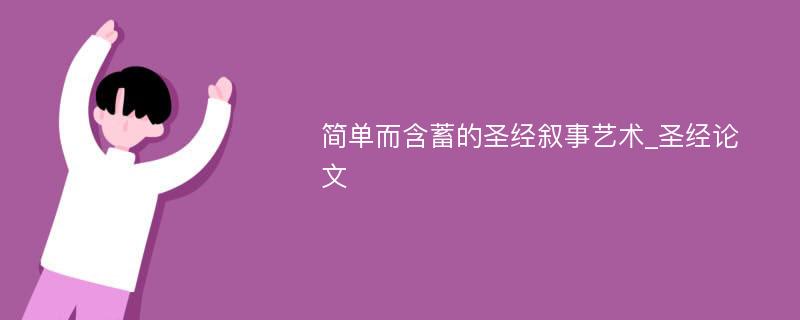
简约、含蓄的《圣经》叙事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简约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O;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1)01-0066-06
《圣经》研究同《圣经》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没有人认为《圣经》本身有什么文学价值。虽然《圣经》在信仰者心目中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但不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是世俗读者都把《圣经》文本看作形式上比较杂乱的一个集子,它包含了律法、家族谱系、历史故事、神话寓言、传说、诗歌等多种文类。就语言而论它也比较复杂,前后用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记述,又经过拉丁文和英文的漫长翻译和编辑历史,所以似乎无法谈及它有何艺术上的完整性和特点。
然而,这种看法到20世纪40年代被一个西方文化饱学之士的独创见地给改变了。他就是犹太学者艾里克·俄尔巴哈(Erich Auerbach)。二战期间俄尔巴哈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逃亡到土耳其。就在欧洲文明遭到法西斯摧残,面临绝灭的严峻时刻,俄尔巴哈从他藏身的小小角落,以他独有的方式,为保存和发扬西方文明作出了贡献。当时条件很差,他在不具备搞研究的起码环境、也没有图书馆可以查阅资料的情况下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评论专著《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Literature)。这部文论的目的是讨论历代对文学反映现实,或称模仿现实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表达手法和效果。他从柏拉图把文学模仿生活现实定位在真和善之后的第三位谈起,逐渐聚焦到19世纪法国文学的巨大成就,称之为完全摆脱古代文学和思想理论约束的现代现实主义的发端。他声称当斯汤达和巴尔扎克把任意一个普通个人放在历史大环境里来查看他那坎坷、悲惨的人生之时,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就摆脱了古典教条的控制,普通人和贱民不再只是轻喜剧或取乐闹剧的角色,他们也可以成为严肃和悲壮主题的主人公了。他指出法国的现代小说给西方现实主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从那时起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就蓬勃发展起来。
俄尔巴哈在这部书里探讨了上起荷马史诗和《圣经》下至弗吉妮亚和普鲁斯特的主要西方文学作品,纵横评议了像塔西佗、圣奥古斯丁、圣弗朗西斯、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蒙田、歌德、席勒、福楼拜和左拉等文学巨匠的写作特点和贡献。正如有些西方评论所指出的,《模仿》是20世纪后半叶美学和文学史领域里最重要和最出色的著作,因为它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宽度和深度,对如此众多的写作形式和方法做了精辟的剖析,充满了独特的见解,显示出了博大的智慧,并在理论、批评和历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部书里,《圣经》的文学性和文体上的独特之处得到了首次阐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俄尔巴哈的《模仿》、具体说是书中十分出名的第一章“奥得修斯的伤疤”,开启了从20世纪下半叶迄今仍方兴未艾的《圣经》的文学性和它的文学解读的研究。
在俄尔巴哈之后,《圣经》的文学性研究大部分属于文体和叙事分析以及结构与形式等方面的批评,但是也不乏从神话原形、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心理学和女权主义等多个角度的审视。百花争艳,众说不一,但这些评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文本应该得到同所有其它文学巨著一样的关注。比如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撰写了《圣经的叙事艺术》(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一书, 该书成功地在《圣经》貌似杂乱的叙述中寻求潜在的联系和规律,并且用新批评的细读文本手段阐释了许多精彩篇章。艾尔特之后最有建树并超越和批评了以艾尔特为代表的纯文学解读《圣经》的学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诗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斯腾伯格的力作《圣经的叙事诗学:意识形态文学和解读的戏剧性》(ThePoetics of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Reading)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 因此任何忽略了这一点的纯文学评论都有简单化歪曲《圣经》的可能。他试图纠正文学阐释的偏差,并且致力建立一个《圣经》文学批评的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除去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外,值得提到的还有加拿大文学教授和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和他论《圣经》的专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The Bible and Lierature)。弗莱是研究神话和文学原型理论的,在这本著作里,他对语言、意象和隐喻在《圣经》和西方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对创世记神话都做了精彩的论述。叙事学学者米柯·巴尔(Mieke Bal )著有《死亡和相反的对称:士师卷里的对应政治》(Death and Dissymmetry:The Politicsof Coherence in the Book of Judges),从女权主义角度对《旧约》士师卷描述的牵涉女人的谋杀和死亡进行解读,很有特色。马里兰大学教授苏珊·韩德尔曼(Susan Handelman )在她的《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的犹太教士解读影响》(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Theory)一书中,更进一步地探讨了犹太教士对《旧约》解读的方法和认识论如何影响了弗洛伊德的解梦学说,并成为拉康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基础。目前在国际上,这个由俄尔巴哈发端的对《圣经》、特别是对《旧约》的文学性讨论还在如火如荼地延伸着,它不仅是我国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学研究新领域,并且也涉及我们对西方文化、宗教和政治思想意识的深入认识。然而限于篇幅,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只着重介绍其源头:俄尔巴哈和他对《旧约》文体的分析。
俄尔巴哈在《模仿》一书的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里对比了荷马史诗同《旧约》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异,分析了造成各自叙述风格的原由,并得出结论说:《圣经》是同荷马史诗比肩的伟大史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奥德赛》的读者们都不会忘记该史诗第19卷是如何描绘奥德修斯结束了10年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又漂泊了10年,最终回到了伊萨卡自己的家中。在他滞留异乡期间,许多无耻的求婚者住到他家里来向他妻子佩涅洛佩求婚,并大肆挥霍他的家产。为了安全,奥德修斯回家时只能化装成一个乞丐请求主人容许留宿。老管家尤利克里娅曾是奥德修斯的奶娘,按照待客规矩侍候奥德修斯洗脚,发现了主人腿上的伤疤,认出了奥德修斯。俄尔巴哈选择了《奥德塞》里的这段故事,用它同《旧约》中亚伯拉罕将以撒做祭品献给上帝的故事做了详尽的比较,深入而令人信服地阐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文体,证明《圣经》的简约、含蓄文体实际上同洋洋洒洒、气魄宏大的荷马史诗一样伟大。
先让我们回忆一下“奥德修斯的伤疤”的故事和荷马的叙述。荷马是这样描写的:尤利克里娅一边忙着倒水一边伤心地对客人讲她漂流在外的主人,她说奥德修斯就是客人这个年龄,而且客人的身量和举止都很像她家主人。此时奥德修斯记起自己腿上的伤疤,为了避免被识破,他立刻向灯光昏暗处挪了挪,但是当老妇人的手触到那块疤时,她立即知道来人是谁了。在大吃一惊的刹那,尤利克里娅失手让奥德修斯的脚落入水盆,把水溅得四处都是。就在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喊出来时,奥德修斯用手捂住她的嘴,轻声吓唬她,不许暴露他的身份,同时细心地用她熟悉的亲热称呼呼唤她,令她安心。而在他们相认的这个过程中,荷马告诉我们佩涅洛佩的注意力被跟来保护奥德修斯的女神雅典娜转移到别的事上,所以她虽在场,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荷马不但非常详尽地讲述了洗脚认主这个戏剧性场面的所有细节,比如奥德修斯是用右手去捂老仆人的嘴,同时用左手把她搂到自己身边,而且在尤利克里娅摸到伤疤和失手让奥德修斯的脚落下的这一瞬间,诗人插入了70多行诗来解释伤疤是怎么得来的。这段回忆以插叙形式把读者带回奥德修斯的童年:一次他来看望姥爷,在随成年人猎野猪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敢。他在追猎中与野猪搏斗,被那畜生的长牙刺伤了腿,这就是伤疤的来由。在用了70多行插叙诗仔细交代完毕这块疤的来龙去脉之后,荷马才让奥德修斯的脚落入洗脚盆中,几乎把盆打翻。
在带领我们回忆了奥德修斯化装回家,洗脚时因腿上的伤疤而几乎暴露身份的故事后,俄尔巴哈开始分析这段荷马史诗所显示的英雄史诗的各种叙事特点。他指出,荷马史诗总是尽铺陈之极来描述每一个事件和人物,场面气魄宏大,常常采用插叙、倒叙来交代因果和往事,可以说没有任何细节被遗忘,也决不留存任何疑点。在荷马史诗里不仅一切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用华丽铺陈的语言娓娓道来。比如那70多行的插叙不但交代了伤疤的来由,而且描述了奥德修斯姥爷的性格,他的宅子是什么样子,老头子得外孙后的欣喜,这次少年奥德修斯来探访老人时如何问候姥爷,老人为外孙设下的欢迎宴会,受伤后奥德修斯如何养息和恢复,回到伊萨卡后父母关切的询问等等……,所有这些细节都一一展现给读者。 俄尔巴哈称这种毫无保留的描述为“外化的叙述”(Externalization of All Elements)。(注:见Erich Auerbach 著Mimesi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P,1953),第3-23页。“Externalization of All Elements”出现在第4页上。)
现代人也许会认为荷马采用这
70 多行的插叙是为了制造悬念(suspense),增加紧张气氛来吸引读者;起码是卖关子,像中国的章回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手法,在关键时刻打住,且听下回分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尔巴哈提出了他自己对荷马史诗文体的一个重要见解,那就是荷马史诗里不存在悬念,或很少有悬念。根据他的解释,这一长段细致又生动的狩猎描写已自成体系,它并不依赖某个悬在读者心头的谜来存在。比如我们在福尔摩斯故事里常常看到的需要破译的血迹或符号,或者是行踪神秘的人物出现,或者忽然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都直指应该侦破的中心秘密,它们令读者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深地卷入故事而不能自拔。可是这段关于奥德修斯童年遭遇的描写却不同,它是个自成独立体系的小故事,它完全靠自身的魅力来取悦和吸引读者。而且荷马在叙述上还采取了把过去事件前置的手法,虽然它的叙述是回顾洗脚发生之前很久的过去,但它的详尽和铺陈、它的生动和历历在目,使它完全占据了读者现在的时空。因此,讲到精彩处读者会几乎忘却前面洗脚一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与其说这段插叙会令读者更紧张地等待奥德修斯暴露身份后可能发生的危险,还不如说它是在伤疤被发现所造成的紧张气氛里的舒缓剂。这种插入是史诗叙述文体中常见的做法,它一方面可以给史诗带来更博大和宏伟的氛围,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读者或听众的紧张心情得到片刻的松弛,从而能够更悠游地欣赏诗文之美。
俄尔巴哈认为荷马的史诗之所以没有含蓄和悬念,不去做心理演化过程的深层描绘,而是完全“外化和前置”所叙述的每一个事件,力尽铺陈豪华之极,其原因首先是美学考虑,要让诗文美,给读者或听众最大的美感满足。然而,这种文体还有其更深的根源。俄尔巴哈十分敏锐地指出这种文体是由史诗创作目的所决定的。荷马和他前后的诗人创作史诗为的是愉悦听众,他是在讲故事,也就是在虚构,在说谎,因此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诗人就等同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怎么编能使故事更好听,怎么讲能使诗文更精彩,他就会那么去做。这个创作目的决定了荷马史诗那夸张、明了和铺陈的外化文体。
作为对比,俄尔巴哈接下来就分析了《旧约》“创世纪”里第22章亚伯拉罕把以撒做祭品献给上帝的故事。同“奥德修斯的伤疤”那洋洋洒洒上百行诗(注:第19卷整个讲的是奥德修斯那晚化装回家到上床之前的遭遇,全卷共604行。佩涅洛佩吩咐老仆人为客人端水洗脚从第350行开始, 奥德修斯捂住她的嘴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段描写止于第490行,其中猎野猪的倒叙从第394行至466行,共计72行,但整个关于认出伤疤和伤疤的来由占据了约 140 行诗歌。 见诺顿评论版《奥德赛》(1974),第256—273页。)相比较,这段故事真是很短很短了。(注:本文用的英文《圣经》是London and New York:Collins'Clear-TypePress印发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见该版“创世纪”第22 章“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首先,俄尔巴哈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故事一开头就显示出与荷马史诗截然不同的叙事特点。一天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唤,他赶忙答应“我在这里。”(Goddidtempt Abraham, andsaid unto him,Abraham:and he said,Behold,here I am.Gen.22:1)众所周知,上帝和普通人并不属于一个范畴或层面,也决不会常常通话或会面。叙述开头显得十分陡然,上帝从什么地方呼唤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当时又在什么地方?故事文本全都没有清楚的交代。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到上帝在哪里,也无法知道上帝什么样子。他不同于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及众神,我们知道他们如何议事,如何争风吃醋,而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无法描述的。亚伯拉罕的“我在这里”并不能回答他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设想亚伯拉罕当时正在帐篷外面,也可以认为他在田野里。我们可以设想他听见上帝呼唤时取站立姿势,两手高举仰面朝天;我们也可以设想他立刻匍匐在地,把脸贴在地上,毕恭毕敬。很明显,在这段《旧约》故事里,作者对亚伯拉罕听见上帝呼唤的描述没有采用荷马写奥德修斯如何用右手去捂住老奶妈的嘴又用左手搂住她以示亲昵的那种细致明晰的手法。那么,“我在这里”到底要说明什么呢?俄尔巴哈指出,这句话不是要交代地点,而是反映了亚伯拉罕对上帝那种一呼即应的绝对服从的态度。这种描述不是为愉悦听众,而是要承载道德和宗教的内涵。恰恰是为了突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绝对忠贞,《圣经》的作者省略了那许多可能喧宾夺主的细节,如对时间和地点的交代以及对背景和环境的描述。因此,“我在这里”的例子十分有力地说明了《圣经》文体把思想意识置于一切之上的特点。
同样受到简略对待的是亚伯拉罕去献祭的那漫长的3天路程。 读者可以说对那3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所知, 我们只读到他们丝毫不敢延误,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亚伯拉罕用驴子驮上祭祀用的木柴,带上了以撒、两个仆人和一把刀。途经3天,第三天早上, 他们到达了上帝指点的目的地,但是这个地方在哪里,故事也没有交代,只是在上帝提供了一只羊来代替以撒做供品之后,叙述者告诉读者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了个名字。整个的3天旅途就这样被省略了,像是一段真空。 他们路经何处,在哪里投宿,以及以撒和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叙述者都无可奉告。这种叙述上的简约在前置和外化的荷马史诗中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实际上,马上要亲手弑子的亚伯拉罕同儿子走过的这漫长的3天路程,如果让现代的自然主义或意识流小说家来描述, 恐怕可以写出一部《尤利西斯》那种长度的小说来。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不利用戏剧性的手法,把3天来路上的遭遇和心情好好渲染一番呢? 俄尔巴哈在这里又讨论了悬念问题。按照他的理解,如果把3 天的经历像奥德修斯被野猪咬伤那样去大做文章的话,那么故事开始时上帝要亚伯拉罕把独生子杀死献祭所造成的沉重气氛以及给读者带来的紧张和悬念就会被冲淡。相反,这个故事里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以沉默来代替了,这种无言恰恰令读者深感压抑,他们的心弦绷得紧紧地等待那最后的悲剧。因此,一切从简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注意力不必要的分散,要把故事的紧张气氛发挥到极至,让读者时时不忘亚伯拉罕所受的考验,并集中精力体验他的忠贞品德。用这一观点来查看这段故事,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同“我在这里”意不在说明地点一样,强调第二天一早亚伯拉罕就带着儿子上路的这一描述,也不是重在交代时间,它要说明的仍旧是亚伯拉罕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按照上帝的吩咐行动了。
除去地点和时间上的含糊,俄尔巴哈进一步就《旧约》叙述的另一个特点做了与荷马对比的剖析。他指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看上去很干巴,简短,甚至没有对人物和景物的描绘,连个形容成分也很难得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长得什么样儿?他们的性格和脾气如何?两个仆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否忠心?这些都只字未提。对人物唯一的修饰词语只有两处,两处都是用在以撒身上的:一处是在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以撒做祭品时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他献为燔祭。”(And he said,Take now thy son,thine only son Isaac,whom thou lovest, and get thee into the land of Moriah; and offer him there for aburnt offering....Gen.22:2)(注:亚伯拉罕不止一个儿子,但是只有以撒是他婚配妻子撒拉所生,而且是两人老来才得的儿子。);另一处是在上帝阻止亚伯拉罕杀死以撒后肯定他的忠心时,再次提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for now I know that thou fearest God,seeing thou hast not withheld thy son,thine only son fromme.因为我知道了你敬畏上帝,没有把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 留下不献给我。Gen.22:12 )为什么在总体上非常精简的叙述中以撒一个人就得到两处限定性的形容词语?对以撒重复使用的这个修饰成分,与其他人物的无修饰、无描述是否很不协调?怎么看待《圣经》叙述中繁复和简约的选取?这种现象是出自《圣经》作者们的杂乱无章,还是他们高超的叙事技巧?俄尔巴哈在此做了很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个例子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旧约》作者是很有意识地对简繁叙述作出了抉择,决不是随便把故事捏一捏,凑一凑。上帝在要求亚伯拉罕献出以撒时,特别说了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他所爱的儿子,这说明上帝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最爱以撒,但却偏要他亲手杀子来表示对自己的忠诚,可见这是故意要考验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叙述者有意识地告诉读者这个考验是多么沉重,让读者去想象它在亚伯拉罕心中会引起什么样的痛苦。因此,即将要发生的弑子的可怕考验就形成了叙述中的一个巨大的黑影,一个悬念,令读者揪心地等待着以撒的厄运付诸实现。俄尔巴哈在此处引用了席勒对悲剧的说法。按席勒的意见,悲剧诗人要剥夺观众/读者的情感自由,要把他们的全部智识和精神力量控制到一个方向上。(注:Mimesis,p.5.)俄尔巴哈认为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完全达到了席勒所界定的悲剧诗要求,而且取得了壮美的(sublime)效果, 因此以它为代表的《圣经》叙事完全够得上史诗的标准,它只不过是与荷马史诗不同文体风格的另一类史诗。
接着,俄尔巴哈又进一步强调两者之所以风格不同,是写作目的不同造成的。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荷马写《奥德赛》是为了愉悦听众,他是虚构,是说谎,要的就是制造生动的感官享受效果,并不需要为他故事的真实性负责。而《圣经》则不然。《圣经》是基督教宗教经文,它首先是要读者相信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俄尔巴哈把这叫做《圣经》叙事的“真理认同”性质(the truth claim)。 《圣经》的叙事者宣称他所讲的都是代表上帝的真理,他要求读者绝对相信《圣经》里记载的一切。这一对真理的考虑压倒了包括美学考虑的一切其它写作因素。因此,《圣经》的故事不求读者喜欢,不投其所好,而是力图控制读者,令他们信服。为此,《圣经》的叙事者不能任意铺陈,不能取代上帝像荷马史诗的叙事者那样成为全能全知。这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考虑结果就造成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所见到的:上帝从头到尾是神秘而不可及的,甚至故事中的许多事实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也都从略,不去做清楚的交代。结果,这种叙述给每个读者留下了极大的隐含内容去理解,去认识体会,去做自己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圣经》的文本比《奥德塞》这样的史诗要深刻得多。如果说荷马史诗只需读或听就能懂得其内容的话,《圣经》的叙述就不是一读就懂那么简单了,它需要我们去阐释,去解读,去挖掘其中无尽的内涵。事实上,古代英雄史诗虽然在美学上层次很高,但内容却偏简单容易,缺乏深度,因此较难得到现当代追求思考和辨析的读者的青睐;而《圣经》叙述的简约、含蓄却提供了多种理解可能,读者能从貌似简单的故事里挖掘出无尽内涵,从而在解读的戏剧性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通过比较“奥德修斯的伤疤”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俄尔巴哈就这样得出了《圣经》是同荷马史诗和其它世界经典文学比肩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20世纪下半叶研究《圣经》文本的文学性的势头。(注:俄尔巴哈在“奥德修斯的伤疤”这一章中对《圣经》整个文体分析虽然精彩,但结论却也引起了后人的争论。持不同意见者主要对“亚拉伯罕献祭以撒”这个故事的简约、含蓄的叙述是否可以代表整个《圣经》文体风格提出了疑问。)
标签:圣经论文; 奥德修斯论文; 亚伯拉罕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荷马史诗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奥德赛论文; 以撒论文; 旧约论文; 基督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