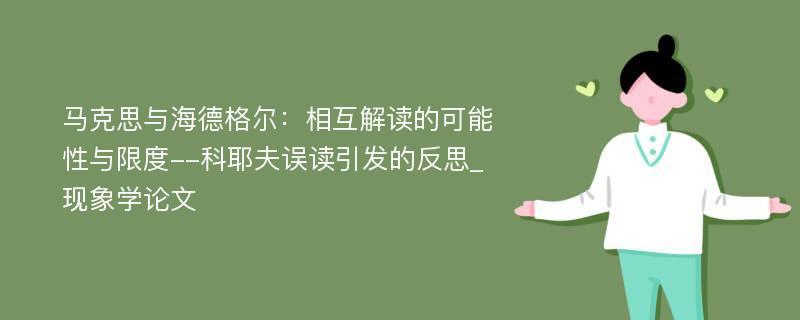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互阐释的可能性及其限度——由科耶夫的“误读”所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误读论文,限度论文,耶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3-0011-06
近年来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类比,用以重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倾向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路径无疑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马克思早期文本获得新的解读路径,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研究中对马克思的评判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两位思想大师的碰撞所引发的共鸣同时还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深度。然而他们思想的融合并非肇始于今,早在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哲学研讨班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融合已经悄然发生了。科耶夫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一文中曾指认了其思想的三个重要来源:黑格尔、海德格尔与马克思。[1]在某种意义上说,科耶夫所推崇的“哲学人类学”正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思想融合的结果。但直面这一对当代法国哲学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却不得不提请我们留意以“海”解“马”所可能存在的误区:科耶夫在让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遇之后却构建了一种近乎倒退的哲学思潮——向人本主义的回归,由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已经完成了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被抹杀了。而科耶夫的这种解读却在当代法国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解读是一种哲学的创新,但却是建筑于误读基础上的“创新”。这种“误读”警醒我们在试图让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遇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本文将以探寻科耶夫误读的原因为入手点展开两条不同的以“海”解“马”的道路。在这种比较性分析的过程中,提请学界在以海德格尔为视角来解释马克思,或者以马克思为视角来研究海德格尔的时候,应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科耶夫推崇现象学,因此他的“哲学人类学”又被他称之为“现象学人类学”[2]。在他的理论中,时间、死亡在黑格尔哲学中都成为了关键词。黑格尔关于生命与欲望的主题在其中被极力夸大,以作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阐发路径,至此,“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如同一对双胞胎”[3]:一方面,“精神现象学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其对象是作为‘存在现象’的人,人在自己的存在中和通过存在向自己显现。精神现象学本身是其最后的‘显现’”[4]。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不独立于存在,人也不存在于历史之外。因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存在的’,如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它必然被当做一种本体论的基础”[5],最终,“精神现象学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他的主体是作为人的人,在历史中的实在存在。在现代的意义上,它的方法是现象学的。因此,这种人类学既不是一种心理学,也不是一种本体论。它试图描述人的整个‘本质’,即人的所有‘可能性’(认知的,情感的和活动的可能性)。一个时代,一种给定的文化(实际上)只能实现一种唯一的可能性”[6]。
科耶夫在此完成了一个无条件的理论跳跃:将黑格尔的现象学等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同时将其等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种等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误读。在其中,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对象即现象学所要显现的“现象”成为人以及人的存在,据此,精神现象学成为了一种“哲学人类学”,其中的人是“作为人的人”,存在是“在历史中的实在存在”。这样的表述带有着浓重的早期海德格尔的味道,但对“存在”的强调并不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论”。海德格尔正是因为洞悉到了法国存在主义中的“人类学”本性才决议要与其划清界限。但对于当时的法国学界来说,打破当时统治法国的唯灵主义的独霸,将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带入哲学,是一个迫切需要完成的哲学任务。波伏娃就曾抱怨,1900年左右盛行于法国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唯灵主义的视角都忽视了“人的历险”,萨特和梅洛-庞蒂也认为两者的认识论路径并不能触及真实的世界。[7]正因如此,科耶夫研讨班对于人类学的关注影响了一代法国学者。虽然这一人类学的起点源于对笛卡尔“我思”的研究,但科耶夫却似乎并不执着于对意识哲学之根基的探求,相反,对“我思”的追问,所引入的是对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及其欲望结构的分析,这一点迎合了当代法国思想界所渴望的对“社会现实”本身的关注。其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特质填补了当时哲学所留下的精神空白,而随后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特质的加强与放大。①
但这种人本主义却披着海德格尔的外衣,这一点从科耶夫那里就是如此,到了萨特那里愈演愈烈,由此形成的法国存在主义影响之深远甚至逼迫海德格尔本人也必须要对其有所回应。海德格尔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书信》(这里的人道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就是对此回应的产物。
在这封信中,海德格尔指出:“人道主义的这些种类有多么不同,它们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homo humanus(人道的人)的humanitas(人性、人道)都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自然、历史、世界、世界根据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也就是说,是从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的角度被规定的。”[8]换言之,所有的人本主义在回到“人是什么”的追问之时——这正是科耶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都将人界定为某类存在的一份子,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等等,于是人成为了某种种类中的一种,对这一种类所具有的种种描述同样适用于人。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人本主义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它的规定方式,即它所谓的本质存在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这种规定方式并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出人不同于动物与植物等各种自然存在的特殊之处(因为他仍然在范畴中找寻人的规定,而并没有能够深入到前概念的生存论根基),因此从根本上没有逃离形而上学的基本特质——虽然海德格尔将批判直指萨特,但科耶夫作为其思想源头,这一批判自然同样也切中其要害——当萨特将存在主义界定为“存在”先于“本质”的时候,所完成的不过是对柏拉图以来“本质先于存在”的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作为这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它就与形而上学一起固执于存在之真理的被遗忘状态中”[9],因此,意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不可能将自身的理论局限在人类学的话语体系当中。
基于这一批判,我们或可断言科耶夫将对人及其存在的现象学描述等同于一种人类学,根本有悖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基调。但问题在于科耶夫在展开自身哲学的时候却一直标榜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来阐发黑格尔。这一点难免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科耶夫所讨论的“现象学”会走向“人类学”?难道是因为科耶夫对海德格尔思想理解不够深入?问题显然并不如此简单。
科耶夫于1948年10月给唐·迪克陶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黑格尔究竟在他的著作中试图说些什么,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我只是借助于黑格尔的文本来展开我的现象学人类学。”[10]这种“有意误读”近乎成为了科耶夫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度。因为在这种“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中,科耶夫所彰显的总是自己的思想,对待黑格尔是如此,对待他所钟爱的海德格尔也是如此。
科耶夫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人类学的过程中,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开始,科耶夫的回答是“人是自我意识”[11]。由此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所有论述都不过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讲述。基于这种“等同”科耶夫完成了从“现象学”向“人类学”的转变。然而对这种等同何以可能科耶夫却不予讨论,它构成了科耶夫隐性的理论背景。这一隐性的背景,在笔者看来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也曾经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了一次“文本解读”,在其中马克思同样提到了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的等同。只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一等同在批判的语境中被提出来。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做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现实的即真实的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做现象学。”[12]
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其意在指出黑格尔哲学作为一般形而上学所具有的“意识”特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人的本质的现实的异化才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的表现,相反,黑格尔认为人的现实的异化要以自我意识的异化为本质。这是一种意识与“现实”之间的颠倒关系。虽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完成这样一种颠倒绝不是最终目的,但在其早期的批判当中,特别集中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过程中,意识哲学以“意识”为出发点来讨论问题的弊端总是被强调出来,这一强调强化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在科耶夫那里,自我意识的展现过程与人的本质的展开过程是同一过程的话,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其实也是如此,只是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在自我意识与人的本质之间区分出究竟谁才是根本。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根本,而马克思却认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才是自我意识的根本。尽管在这种评述中充满批判,但对“自我意识=人”马克思是持肯定态度的。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耶夫哲学立足的根基所在。
然而,自我意识的演变能否完全等同于人的本质的展现过程?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会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继承和超越了黑格尔,而这正是我们反观科耶夫对马克思的误读所必须要走出的第一步:在“非误读”的意义上,马克思究竟如何看待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其意并不在单纯探讨“人是什么”这样一个主题。马克思在此所读出的正是黑格尔试图传达的一种精神,即“现实”与哲学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赞同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后者用纯粹理性批判所实现的是经验的现实的世界与哲学世界的分裂。因为在知识论的意义上,理性对于是否能够认识那个现实的世界只能不置可否,由此形成了黑格尔所看到的当下文化的现实:“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13]而黑格尔试图完成的是将现实的世界与合乎理性的世界结合起来,以完成长久以来西方文化中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世界的统一。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论证这一分裂的统一究竟是何以可能的,而他的自我意识的观念是走向统一的最为重要环节。因为自我意识是意识的自我反思的结果,带有着“精神”演进中最为重要的“对象性”特质:即意识的对象不过是意识异化、外化、对象化的产物,由是异化的对象向意识的复归就没有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意识的一部分,这是对象性观念的核心思想,这种对象性特质保证了分裂的统一。从自我意识的提出开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科学(集中于对知性的探讨)转向了哲学(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探讨。正是在这一探讨当中,黑格尔对现实的理解也逐渐浮出了水面:现实是哲学的对象化产物,因此它与哲学本来就是一体的。对于这一点洛维特说得很清楚:“既然把意识的内容置入思想的形式从而对现实进行‘反思’对于作为哲学的哲学来说如此具有本质性,那么另一方面,弄清楚哲学的内容无非就是世界或者可经验的现实的内容,就也是具有本质性的。哲学与现实的一致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他(黑格尔——引者注)真理性的一块外在的试金石。”[14]
对现实的这种提升是黑格尔哲学的贡献。关于这一点,1844年的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在批判黑格尔及其精神现象学,但显然这种批判建立在对其理论展开过程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之上,认为黑格尔所描述的意识发展过程之所以还“不是作为当做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5],原因只是因为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6]。换言之,黑格尔所描述的意识过程也是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只是前者是这一过程在意识(哲学)层面上的显现,而现实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却需要脱离这一意识哲学的视域,从而从根本上去除这种意识哲学的先验性与既定性。因为意识哲学的先验性最终会让哲学趋于保守:既然“现实”本身不过是意识的对象化,那么现实就先验地具有了合乎理性的规定,并有了发展的既有轨道。黑格尔哲学中将现实与哲学的辩证统一,注定要让自己的哲学走向对既存现实的合理化论证的保守主义一方。
在此基础上,我们回过头再来思考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的深意,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上。在这种“等同”当中黑格尔的意识哲学被马克思逐步瓦解。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内来理解自我意识=人,那么只能意指着现实与意识的统一性。并且现实的存在只是为了确证意识的指向,现实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但对于马克思来说,将自我意识=人,那么意味着人也具有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只是在现实中的人的对象化活动——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就是劳动——所触及到现实却并不能成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相反,由社会经济事实所构筑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否定”着人的力量。由此现实与意识无法统一了,两者的关系成为了对抗性的。
思辨哲学最终与现实相脱节。马克思抓住了这一点给予批判,并希望以此找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立足点来完成对这一思辨哲学的超越。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批判打开了通向现实的分析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异化”问题仍然带有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这里的人及其劳动却“正在”摆脱传统哲学固有的抽象规定:马克思所讨论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工人与资本家;劳动也不仅仅是对外物的“陶冶”或者“加工”,劳动的产品、劳动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存在而并没有给工人带来肯定性的“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现实。而能洞察这一现实的根本在于抛弃一切先验的概念规定。人不需要任何抽象规定的限定,人的“存在”在其社会关系当中,这就是马克思的“生存论”哲学。
至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遇了。早在海德格尔写作《存在与时间》之前,海德格尔对于哲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有了不同于旧有形而上学的看法。当胡塞尔试图将哲学进一步严格为一种科学的同时,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只有作为前理论科学(pre-Theoretical Science)似乎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当代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将哲学进一步科学化,而是所有理论过于“科学化”,从而遗忘了“存在”本身。[17]对于“存在”究竟为何,如果真正遵循着海德格尔式的追问方式也决不能被概括式的回答,为此海德格尔用组合、拆分的方式,将诸多的情景结合起来,以期表达这种不能被界定的“存在”。尽管在种种的阐释当中,学界习惯于将早期海德格尔思想称之为一种哲学人类学,但实际上活跃于其中的Dasein总是在其发生情景(如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说明,并且海德格尔从来不曾将其直接指认为“人”。换言之,海德格尔从来不会用一个可被“界定”的概念来阐发思想,更不会给“人”下一个定义,因此从海德格尔整体思想出发,这个哲学人类学的界说是不能接受的。但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概括,科耶夫却没有问题。那么究竟科耶夫如何误读了海德格尔?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科耶夫将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误读”加入到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读当中,即科耶夫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人”直接作为其哲学前提,并且只是看到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肯定性方面,而没有看到其否定性的方面,据此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现象学演变视为关于人的现象学演变,并在将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无条件等同的情况下,逼迫被“误读”的海德格尔与被“误读”的马克思相遇。由此科耶夫所发现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相似性就与我们的理解有了巨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其相互阐发的基础。这个基础在于他们对形而上学的共同批判以及两者建构哲学时极为相似的理论出发点。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将黑格尔哲学与一般哲学对等起来[18],并在其早期著作中总是试图将自己与“哲学家”②的名称剥离开了,这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哲学相决裂的立场。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拒斥也始终贯穿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当中,这种决裂在马克思哲学那里进一步表现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与传统哲学的出发点的根本差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费尔巴哈》当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所谓“历史的起点”究竟为何的问题,尽管对此在不同版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不同的侧重,但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的基调不会变。这一点恰恰与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有很大的不同。
黑格尔曾经盛赞笛卡尔,认为哲学在笛卡尔那里终于停止了漂泊,看到了陆地。[19]因为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是“我思”,或者说是“意识”,这正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秘密所在:即意识内在性的基本特质。从这一起点所开启的哲学也永远只能在意识内部找寻所有的答案,而这种“唯心主义”决不能仅凭“唯物主义”的“颠倒”被颠覆。恰恰相反,正如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无论是对意识还是对物性的强调,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但对于黑格尔来说,由于固有的绝对精神的视野,这种彻底的超越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只有当马克思在将对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问题放在了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当中,他才能为哲学找到新的起点。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哲学的起点并非是对抽象的人的界定。这种下定义的方式不是马克思探讨哲学的方式。马克思哲学有着一种“社会性”的视野,这一视野在其哲学展开的过程中表现为对“关系”的强调。任何问题或者现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都有着隐性的“社会关系”的背景,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20]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从其产生的生活世界来探寻,这其实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世界被遮蔽了的存在论基础。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在马克思相对成熟的研究著作中,人总是作为“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或者“资本家”等等出现。这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存在状态恰恰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存在”。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海”解“马”的思路当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
但科耶夫的误读却让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遇的方式。在对黑格尔理论的解释中,科耶夫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念所引出的竟然是海德格尔反复批判的人本主义,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就学理而言,其中的问题恰恰在于科耶夫在其思想的展开过程中对马克思要素的吸收,即通过对于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人”的批判性公式单向度的接受,科耶夫将“现实的人”的起点看做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起点。然而事实上,首先,海德格尔不会以任何一个既定的存在者为其哲学的起点——特别不会以“人”为起点,这是科耶夫对海德格尔的误读。其次,科耶夫也彻底误读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哲学把握方式。在此,科耶夫过于关注早期马克思对人的讨论的诸多“表面文章”。因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关于人的讨论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痕迹确实很浓重。但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分析中就已经在挣脱这种对人的抽象本质的规定,这一点并没有被科耶夫所理解,这表现在科耶夫在谈到关于人的存在所具有的三个要素之一——劳动的时候与马克思所具有的不同的路径。对于科耶夫来说,劳动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规定,因为“一方面,劳动改变和改造世界,使之人性化,使之适合于人;另一方面,劳动改造、培养和教育人,使之人性化,使之符合人对自己形成的观念,——最初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一种理想”[21]。正是劳动在对世界与人的双重改造中,创造了物质文明,推动了人的历史演进,并且在科耶夫的强调中,这种创造的“物质性”内涵被放大了。例如科耶夫在研讨班中反复强调的正是劳动产生了黑格尔撰写《精神现象学》时所使用的书桌,于是当黑格尔思考历史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这张书桌。书桌是劳动的产物,是历史的积累,它凝聚了的劳动彰显了人们否定自然的成果。这就是科耶夫眼中的“劳动”。这个“劳动”的意义看似很现实,实际上非常抽象,因为它的本质仅仅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并且在这种否定的当中肯定自身的力量。这种解读是黑格尔自我意识对象化活动的一种延伸。科耶夫在这种劳动中看不到现实对人的否定性,看不到异化劳动,自然也无法将对人的分析引向对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即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分析。因此,尽管他努力通过强调“桌子”的优先性来加重了马克思的色彩,但本质上却早已回归到被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共同批判的旧有思辨哲学的藩篱之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耶夫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双重误读,却同样让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遇了。由此使我们发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遇有两种不同路径,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找到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共同点,只是这两个共同点却截然不同,由此导致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一个凸显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哲学的革命性,一个则成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又一表现形态。后一种解读虽然是一种误读,但却也警示了我们在让两者相遇的时候可能有的误区,这个误区并非显而易见。例如科耶夫在其思想的展开过程中似乎也在努力逃避这种人的本质的规定,这体现在科耶夫将死亡、斗争与劳动视为人的规定,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却都带有着某种不可被规定的色彩。它们在本质上都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状态,就其范畴的内涵来说都是一种活动,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些概念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性。当科耶夫明确指认了人是死亡、斗争与劳动构成的动物的时候,他所传达的仍然是对人的一种理论的规定,而就这种规定得以成立的存在论基础的探讨,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从未深入到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所深入到的这一维度上。
以上的讨论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哲学的相遇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解路径,这一路径需要我们不能拘泥在马克思本人的诸多表述上——因为这种表述往往是在用旧有哲学语言表达新的哲学观念,因此可能存在着字面意义与深层内涵之间的偏差。如果仅仅驻足于对表面文字的引用,往往会误入歧途。科耶夫的误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我们从这一实例中看到的并非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遇的不可能,而恰恰是他们的合理性。在否定一条道路的时候,彰显了另一条道路的方向。
注释:
①有资料显示,在萨特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他通过梅洛-庞蒂间接地获悉科耶夫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在其理论构建中有着不可被忽视的影响。对此可参阅Mark Poster,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②例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所指:“哲学家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标签:现象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精神现象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人类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