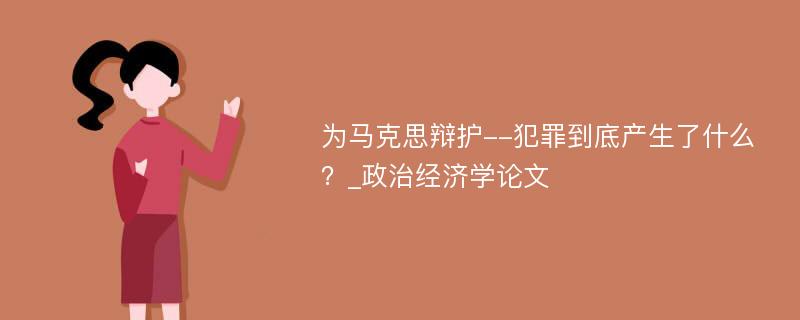
再为马克思辩护——犯罪到底生产了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再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附录(11),标题为“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中有这样一些文字:“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关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搬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再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也提供一种服务……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一)册,(第415—416页)。梁根林先生在《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犯罪功能别议》(《法学家》,2001年第2期)一文中作了如此引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法学界有种错误的理解,认为以上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是马克思对“犯罪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推动进步的“积极功能”,所作的“辩证和理性的分析”(注:梁根林:《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犯罪功能别议》,载《法学家》2001第2期,第12页;陈兴良、梁根林等:《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载《金陵法律评论》(秋季卷),第8页。)。而实质上,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这篇附录恰恰是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所进行的批判。部分法学工作者断章取义,完全错误理解了马克思,并且,这种观点影响很大,(注:北京大学副教授梁根林先生的《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犯罪功能别议》一文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法学家》上,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2001年第7期全文转载;在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刑事法论坛”上,梁根林先生再一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并且,该次论坛的内容后又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金陵法律评论》(秋季卷)。)因此,对于所谓的“马克思犯罪功能说”的是非问题非常有必要再来个“正本清源”。
二、正本清源
只所以是“再”来个“正本清源”,是因为早在1986年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李光灿教授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一书中就有过“马克思犯罪功能说”的观点,(注:参见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一文的[附后],《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当时上海师范大学政法系的毛信庄同志就对这种观点提出过质疑与批判,(注: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8—19页。)李光灿教授不仅从善如流,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注:参见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一文的[附后],《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而且将毛信庄同志的文章推荐到《法学杂志》,(注:参见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一文的[编者按],《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8页。)并发表于《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上。李光灿教授承认“误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话,当成马克思的话并予以肯定,都是错误的”,其原因就是“直接引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法的编著而没有细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第一册附录中的引文”所致。(注:参见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一文的[附后],《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至于,现在的“马克思犯罪功能说”的论者是否也是这个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毛信庄指出,通观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生产说”(“犯罪功能说”)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观点,而是持“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观点者和其辩护论者的见解。具体地说,主要是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施托尔希、加尼耳、西尼耳、罗西、特拉西伯爵等人的观点。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施托尔希、加尼耳、西尼耳、罗西、特拉西伯爵等人的这一观点是针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以下称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而发的。
斯密把劳动区别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成为他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把生产劳动看成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马克思在评价斯密的这个理论时说:“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9页。)经济学家中的二流人物如施托尔希等人反对斯密的理论,把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令人难以容忍的庸俗化,从而挑起了一场论战。施托尔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把人的文明要素如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看成“内在财富”,认为在没有这些内在财富之前决不会生产财富。因此他说:“内在财富的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力手段。”意思是说,精神生产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所以他说,医生生产健康,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同样也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不安全生产君主,等等。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加尼耳则把一切得到报酬的劳动都纳入生产劳动的范畴。他认为,只要劳动能引起用以支付它的那些产品的生产,即能得到相应的报酬,那么“任何劳动都必然是生产的。”(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09页。)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西尼耳更是露骨地宣称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他说:“有些国家,没有士兵的守卫便根本不可能耕种土地”。(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300页。)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罗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说得很明白:“在街上巡逻的宪兵、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关押犯人的狱吏、守卫国境防卫敌人侵犯的军队,所有这些人都促进生产。”他把“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结果”都算作是“生产的”。马克思在批判罗西的这个论调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照你那么说的话,那么“假誓约对那个靠假誓约获得现金的人来说是生产的。伪造文件对那个靠伪造文件赚钱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杀人对那个因杀人而得到报酬的人来说是生产的。诬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献媚者,只要他们的这种‘服务’不是无酬的。他们的这些勾当对他们来说就都是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306页。)马克思说:“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胡说八道,好象每种服务都生产某种东西:妓女生产淫欲,杀人犯生产杀人行为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311页。)
显然,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合理性及其理论意义。批判了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庸俗化。在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这种区分决不可忽视,而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都对物质生产发生影响,物质生产也对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发生影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76—477页。)马克思认为,所有的辩护论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家向资本者大献殷勤。根据前者,那么小偷也是生产者了,因为他间接地生产出刑事法典;而后者正是辩护论者的实质所在。
毛信庄总结说,从理论上弄清了关于生产劳动这场论战中反对斯密的那一派为自己辩护的观点,说明了“罪犯生产说”(“犯罪功能说”)恰恰是庸俗经济学家的胡说。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了。
有了上面的论述,足以说明马克思在犯罪作用上的观点并非象一些人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但是毛信庄同志没有点明这场论战的根本背景及其根本意义,仍使人难以深刻理解。为此,笔者再简要介绍一下这场论战的最初起因及其根本意义,再次证明“犯罪功能说”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就是《资本论》的第四卷,而整个《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其中虽然也体现了马克思在其他方面的思想,但,其他方面在《资本论》中都是围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存在的,是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服务的,经济问题也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所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于犯罪的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时都不能脱离马克思经济学说。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中,统治者总为自己的统治去寻求合理的依据,为自己的剥削寻找科学的借口。当然,经济问题就成了统治者为自己寻求依据、为自己寻找借口的最终焦点与根据地。于是,“正统”的经济学家门也纷纷为自己主人的统治与剥削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
在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思想家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都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述。色诺芬最先使用经济一词。他的《经济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经济著作,这部大约公元前401年写成的著作,主要讨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以及怎样经营奴隶主的家政问题。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主要发表在《政治论》和《伦理学》这两部著作里。他视主奴关系为首要关系,他研究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和奴隶制社会生产力,从维护奴隶制自然经济出发,论述了财富的性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所关心的一个主要经济问题就是如何组织和管理奴隶,以便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维护奴隶制经济关系。
欧洲封建制度是在古罗马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从5世纪到17世纪中叶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圣经》和教会成为意识领域的垄断者,经济思想自然也是受教会思想支配的。西欧中世纪最著名的教会思想家是托马斯·阿奎纳。他的《神学大全》推崇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不平等的论断,竭力为农奴制和封建等级制辩解,阿奎纳认为社会等级的区分是上帝的旨意,私有制是人类理性为了人类的生活而采用的办法,反映了封建教会统治者利益的见解。
16世纪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重商主义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学说,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他们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把贵金属的积累视为增加财富的唯一方法。认为利润是商业中“贱买贵卖”的结果,因此,是资本创造了财富而不是生产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由发生到成长阶段形成的一种经济理论。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上半期。这期间,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处于成长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这就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可能无顾虑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同时,哲学领域出现了与封建经院哲学直接对抗的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新的方法论,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作出了初步的科学分析。其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利润、利息和地租作了阐述;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初步分析;对分工、货币、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经济危机等理论也作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府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局限性和历史时代局限性,因而他们的理论中,包含着一些庸俗的因素,这些庸俗因素后来为庸俗经济学家所吸收和发挥,成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斯密的思想深受培根、休谟的影响,广泛吸收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斯密区分了商品价值与交换价值,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的非生产性劳动,初步应用劳动价值论探讨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而且只有生产性劳动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
斯密的这一理论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如果按照斯密的理论,生产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那么,一切对生产劳动者的统治与剥削都是不合理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施托尔希、加尼耳、西尼耳、罗西、特拉西伯爵等人针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企图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寻求理论基础,为资产阶级的宪兵、法庭、狱吏、士兵、“有闲者”、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寻找借口。他们认为:1.“吃粮食的人和生产粮食的人一样,也是生产的。因为,为什么生产粮食呢?就是为了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179页。)2.“任何劳动,不管其性质如何,只要它具有交换价值,就是生产劳动,就是生产财富的劳动”,而且“交换既不考虑产品的量,也不考虑产品的物质性,也不考虑产品的耐久性”;(注:加尼耳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08页。)3.“任何有用劳动(在他们看来,罪犯和妓女的劳动都属于有用的劳动)都是真正的生产劳动,社会上任何劳动阶级都同样应当称为生产阶级”;(注:特拉西伯爵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77页。)4.“(财富的源泉)不应追溯到这些生产工人,而应追溯到使用这些工人的资本家”,“把产业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产业资本家实际上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88—289页。),等等。“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颂扬,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312页。)
针对这些“有教养的资本家”、“有闲者”的代表及其辩护论者的荒谬说法,马克思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本目的“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98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以及庸俗经济学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针对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论战实质上就是谁创造了世界上的财富、谁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之争。当然,答案只能是劳动和劳动者(此处的劳动是马克思语义下的劳动),这个答案也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统治理论的基石。
至此,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附录(11)中的真正目的与思想。
对这场论战的过程有了了解,也就很容易使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原意。既便不了解这场论战的过程,也并不妨碍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原意。
为了能使这个问题一目了然,不妨将马克思的这篇短文全部抄录如下:
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中间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415—416页。)
在这个附录中,马克思集中了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论者的谬论。这里的关键是要从标题开始把这篇附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读。这篇文章一气呵成,全篇的语言风格前后一致,表述的都是辩护论者的意见,表述的方法没有采用辩护论者晦涩的语词而改用了孟德维尔那种“勇敢得多、诚实得多”的语言。(注: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充满了对辩护论者的反诘与讽刺,特别是每段的最后一句,更是耐人寻味。不难发现,马克思把辩护论者的全部议论作了系统归纳,准备了充分的素材。如果我们只简单地选取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容易把马克思的观点错误化。
马克思在这篇附录的最后引用了孟德维尔的一句话来比喻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会衰落。”显而易见,“附录”是马克思作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批判的素材的。虽然他对反面材料作了简要的清理和归纳,但还没有进行正面的、深入的批判。我们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在此没有作正面批判,就把“罪犯生产说”误解为马克思的观点。(注: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
为什么马克思把“附录”作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批判的素材的而没有进行正面的、深入的批判呢?
这就必须要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从19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计划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经过长期、系统研究,于1857—1858年写了一部经济学手稿,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这部分手稿的大部分,也是准备最充分的部分构成了《剩余价值论》。手稿的其余部分即理论部分后经马克思重新修改和补充,形成了《资本论》的前三卷内容。
由于1864年9月成立有名的第一国际,马克思全身心投入到其中工作,成为第一国际的灵魂。“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加紧张的理论研究中,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即《剩余价值论》部分)。”(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马克思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他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没来得及整理及出版《资本论》的第四卷(即《剩余价值论》部分)。(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451页注释1。)就这样,《剩余价值论》经过两位伟人之后仍只能以手稿的面貌流传于世。
在这个手稿的内容中也明显记录了马克思在收集资料,整理论点,准备专门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手稿的第ⅩⅤ本中研究收入及其源泉的问题时,对庸俗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本第935页注明参看“论庸俗经济学家一节”,即他的著作中尚未完成一章,这一提示表明马克思打算专门写一章来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手稿第ⅩⅧ本中,马克思在结束对霍吉斯金观点的分析并提到后者对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理论反驳时,注明:“要在庸俗经济学家一章中谈这一点”。这句话也证明马克思打算以后专门写一章来论述庸俗政治经济学。在1863年1月拟定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计划中,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庸俗政治经济学”。(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451页注释11。)正如上述原因,马克思没能完成他的计划。所以,“附录”仅是马克思的手稿,是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基本素材。由于工作和身体的原因,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正面的批判,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
因而,“马克思犯罪功能说”与马克思风马牛不相及,它的实质和一般倾向都是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注:毛信庄:《“罪犯生产”说是马克思的观点吗》,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第19页。)
三、犯罪“功能”的哲学分析
“犯罪功能说”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是肯定的,是不容置疑的。但,并不是说关于犯罪是否具有“功能”的问题不能讨论。
拜读《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犯罪功能别议》(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根林博士,以下简称《梁文》)之后,对梁先生的“反常思维”(注:《梁文》引用了[法]迪尔凯姆的一句话“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作为其论证的开始,因此,《梁文》的思维方法是“不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反常思维”。)的研究方法敬佩不已,也受益匪浅。但是,从犯罪、犯罪功能的本身,尤其是从该文的“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社会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实现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注:参见《梁文》。)之目的出发,《梁文》认为犯罪存在促进功能(积极作用)有明显的不当之处。现也就该问题作一探讨。
1.功能阶位与价值评价。功能阶位就是指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事物功能的层次规格或事物作用的角色。如果对事物功能的阶位不清楚,认识角度选取不正确或不到位,那么,对事物有没有功能或者有什么功能就难以获得科学的评价和准确的判断。(注:参见陶富源著:《哲学的当代沉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振第、邹林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刘向在《说苑·杂言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名士)甘茂使于齐,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尔,君不能自渡,何为王者说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骏马一日千里,宫室捕鼠不如猫;干将铸利剑,木工之用不如斧。今持楫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王,子亦不如茂矣!’”
刘向通过这个故事,通俗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事物功能的正确认识必须认准该事物的性质、特点和作用角色。否则,就会功能定位不准。
同样,对犯罪功能的正确判断也首先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犯罪是法律(刑法)规定的结果,也就是说犯罪本身是法律文字“假设”的结果,(注: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徐久生编著:《德国犯罪学研究探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福田平、大冢仁主编,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刑法是一国之政权制定的用来维护其利益和国家稳定的最锐利武器,一国之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稳定其必然将那些它认为对其一切有严重危害(罪恶)的行为犯罪化。(注: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9页;[意]加罗法洛著:《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9页。)因此,犯罪的角色只能从法的角度、国家利益和国家稳定的视角去认定,犯罪也只能相对于一定的法、处于政权的对立面而存在。那么,对一定的社会来说,无犯罪规定则无犯罪后果,犯罪永远是相对的,而犯罪的当罚性(罪恶性)一定是绝对的。
对犯罪功能的认定实质上也就是对犯罪价值(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的评价。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以自身的某种属性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的效应关系,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39页。)如果一个事物能够对主体发生积极的作用,能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它对主体就有价值,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越大,它对主体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如果一个事物对主体的作用是消极的,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甚至妨碍主体的某种需要,它对主体就是无价值的或者有负价值。可见,价值是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产生的,价值既有客体性,又有主体性,是客体的特性与主体需要的有机统一。所以,评价事物的价值就必然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需要和内在的尺度,二是客体的性质和特征,二者缺一不可。所谓价值客体就是在价值关系中的价值承担者;价值主体是指一定价值关系中的需要者,即发现、评价和享受价值的人。(注:参见陶富源著:《哲学的当代沉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李振第、邹林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根据价值判断的基本原理,要对犯罪的价值作出合理、恰当的认识,除了正确判断犯罪的性质外,还必须认清主体的实际需要和价值标准。上文对犯罪的性质已经论述,它是法律规定的结果。那么,这里我们就必须再认清国家对犯罪的需要和判断其价值的标准。对于国家来说其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治者的统治。而犯罪之所以能成为犯罪就是因为犯罪行为破坏了国家的稳定,甚至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基于这一标准,犯罪对犯罪时的政权来说,只能是负价值,不可能有所谓的功能或者积极作用。
对事物功能的认识(价值评价),还必须明白事物功能所处的层次。从功能本身而言,应当是事物的直接效果、本能的作用,而不是经过加工,选择后的作用。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其影响也就非常广泛而深远,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但事物的功能应当是自身直接的、必然结果。所以,功能与影响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将事物的可能影响夸大为事物的功能,造成对事物功能的判断错误。比如,食物,可以充饥,使人精力旺盛,增强人的体力,杀人犯因此更加顺利地完成了犯罪,难道我们说食物有杀人的功能?就象我们判决杀人犯有罪而不能判决制造菜刀的人有罪一样,我们也不能把犯罪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极其有限的影响夸大为功能。马克思对这种事物普遍联系的影响也并不否认,但是,影响绝不等于就有直接功能,我们必须要注意某些必要的区分。“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达种区分决不可忽视,而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都对物质生产发生影响,物质生产也对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发生影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76—477页。)
2.本质与现象。对犯罪功能(价值)的认定实质上还涉及对犯罪本质的定性问题。对一个事物需要采取何种态度,作出何种评价,关键要看该事物的本质。我们不能因为某个蚊子传播了花粉而就理性地说蚊子促进了生物界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因为毒蛇的粪便有肥田的作用就理性地将冻僵的蛇揣入怀中。
何谓本质?本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最根本性质,是由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矛盾决定的,是事物扎实、稳固的一面。(注:参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第107页。)犯罪这种社会表现的本质如何?我们必须看到,犯罪中固有的特殊矛盾是犯罪对公民、集体合法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侵害与维护权利、维护统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犯罪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对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的破坏以及对当时法律制度的公然挑衅。由此也决定了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注:梁博士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参见《梁文》。)
当然,犯罪的本质也要通过一定的现象来表现。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事物外部的联系是普遍的,纷繁复杂的,也决定了事物的现象会多种多样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真象,也有假象。能直接、真实地表现事物本质的是真象;歪曲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是假象。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真象与假象都有客观性,假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其所依照的参照物不同,它所反应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需要注意的是假象与错觉完全不同。错觉是主观的,而假象是客观的。(注:参见陶富源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李振第、邹林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比如,从地球上观察到的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绕着地球转,这就是一种假象,它歪曲地表现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运动。而穿上竖条纹的衣服人就显的瘦一些,这就是错觉。实质上肯定派所谈到的犯罪积极功能都是基于不同的参照物对犯罪所产生的假象性认识。我们还必须注意,本质是同类事物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我们可以根据事物的本质而全称肯定的判断该类事物都有这一特征。比如,鸟类是有羽毛的,麻雀是鸟类,因此,麻雀也有羽毛;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也可推论出所有犯罪都严重危害社会。而现象则是个别的、具体的。我们不能由个别的、具体的现象来推论整体的本质或整体的某一属性,如果需要推论的话,我们也只能采用选择肯定判断,不能用全称肯定的判断(无论结论量的大与小)。比如,蝙蝠会飞,而蝙蝠属哺乳动物,我们就不能由此推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飞,我们最多只能说有的哺乳动物会飞。我们当然也不能仅仅看到一个、一类或几类犯罪,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即便这种现象是客观的)就简单的用全称肯定来判断犯罪是有促进作用的(注:参见《梁文》。)(虽然肯定派强调了这种促进作用的有限性,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判断逻辑上的错误(注:另见陈兴良、梁根林等:《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载《金陵法律评论》(秋季卷)第11页。))。
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现实性(必然后果),而事物的现象仅体现的是事物的将来一种可能性(或然后果)。犯罪的本质决定了犯罪必然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各种形式(危害国家安全、行贿、杀人、强奸等)、犯罪的各种手段(电脑黑客、回扣、宣传邪教、劫持飞机等)这些犯罪的表现现象有一些将来可能会有积极功能(《梁文》所证明的都是这种将来的可能性),但决不是犯罪的必然性后果,只是一种可能性后果而已。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既便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要转化为现实性(对社会有积极作用)还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注:参见陶富源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李振第、邹林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否则,这种可能性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毛泽东曾指出:“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努力。这时主观的作用就是决定的了”。(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比如,一个故意杀人犯罪案件,这个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现实的;同时,这个案件将来可能会成为我教学内容中的一个案例,成为我“讲授提纲”(注:参见《梁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册,第415—416页。)的一部分,或者就产生了一个“讲授刑法的教授”。(注:参见《梁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册,第415—416页。)但这些都需要我个人的加工、努力和选择,而不是犯罪给我的必然后果,即犯罪仅有的可能性功能也不过是人类主动应用的结果,而不是犯罪本身的必然结果。既然不是本身必然结果,那么就不是事物本能上的功能,充其量不过是事物的影响而已。
3.动力成本与动力效益。《梁文》又以矛盾论的观点,用反正法来推论犯罪存在是有意义的,不能消灭犯罪。(注:参见《梁文》。)他认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犯罪被消灭,那么与犯罪相关的矛盾就不存在了,社会的这一发展动力也就没有了。于是,《梁文》提出,消灭犯罪是不现实的,刑罚以消灭犯罪为目标也是不合理的。《梁文》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然。
矛盾是事物(注:注意:此处是“事物”而非“社会”,我们只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事物来考察时,才能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此时犯罪与反犯罪之间的矛盾与“社会矛盾”就相差甚远。)发展的动力,但只有事物的基本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基本矛盾。因此,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犯罪与反犯罪之间是一对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梁文》错误的把善与恶、有序与无序的矛盾作为社会基本动力的同时,(注:参见《梁文》。)更没有注意到动力效益与动力耗费,也没有注意到矛盾的消灭与矛盾的转化。
矛盾的不断斗争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首先要指出的是动力既可以推动事物向前进,也可以拖着事物后退。推动事物向前的动力,我们称之为前进力,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到;拖着事物后退的动力,我们称之为阻力,比如,病人与病魔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会使病人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会使病人恹恹一息,甚至终结生命;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会使国力日渐衰退。判断矛盾的动力是前进力,还是阻力,关键就要看矛盾所围绕的核心要素是否与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社会进步的基本表现和标志就是社会文明,(注:参见陶富源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而犯罪恰恰是(至少自然犯罪都是)社会文明的破坏者,所以,如果说犯罪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它仅仅是阻力而非积极性的前进力。其次,斗争是需要成本,需要耗费资源的。矛盾所带来的前进动力的大小就是动力效益;斗争所需要耗费的资源就是动力成本。我们是维持,还是消灭这个矛盾关键要看动力成本与动力效益之间的关系,如果动力成本小于动力效益就可以维持这个矛盾,相反,如果动力成本大于或等于动力效益就可以消灭这个矛盾,因为,赔本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干。试想,有谁愿意花100元的燃料费,最后得到的动力所带来的效益只有10元,甚至还少。拿犯罪来说,一场恐怖活动给人类所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而我们的收益也仅仅是一个教训而已;一次惨烈的交通肇事,留给我们的也仅仅是警示后人的几张图片而已;一个让人撕心裂肺的杀人案,也仅仅是我们的“讲授提纲”中的一个内容而已。
而且,矛盾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然而,当旧的方面灭亡以后,“旧的事物性质就变为新事物的性质”,(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于是就会出现新的矛盾。正因如此,矛盾的转化是矛盾消亡的主要方式,旧的矛盾消亡,新的矛盾又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不去化解、消灭矛盾。就拿犯罪来说,当犯罪被消灭之后(至于是否能消灭,我想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违法与合法,道德与不道德就可能凸现出来,成为我们善与恶中的主要矛盾。据此,我们的刑事政策和刑罚,以消灭犯罪目标也未尝不可。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资本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