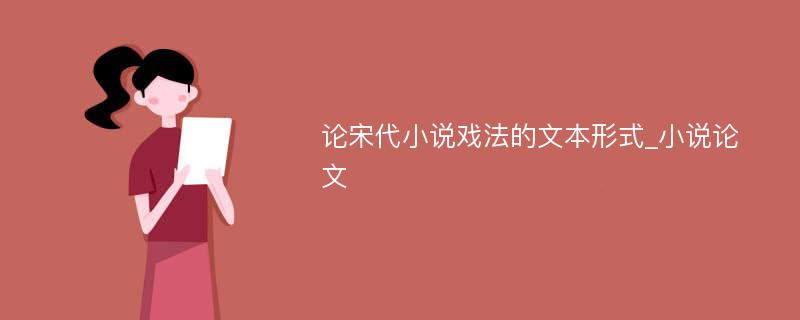
论宋代小说伎艺的文本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形态论文,文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醉翁谈录》是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
自从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1]在日本被发现后(注:颇有人怀疑《醉翁谈录》为元代刻本,理由是书中《吴氏寄夫歌》和《王氏诗回吴上舍》中的两位女性皆为元人。李剑国在《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中予以辨证,认为“以二女为元人实是明人的误断”,“记事中提到太学、斋、上舍,全是宋代国学制度,与元无涉”(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见甚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受到了现当代研究宋代小说学者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所载传奇文”“其中也有很可宝贵的”;而“罗列的小说名目一百余种更是研究话本小说的珍贵资料”[1](P2)(注:一般学者认为罗烨《醉翁谈录》是《永乐大典》卷2405引《苏小卿》所从出,但由于今本缺失此文,故进而认为现存罗烨《醉翁谈录》并非全帙。)。对于《醉翁谈录》一书的性质则定为“传奇集和杂俎集[1](P1)。认为它是“一部很重要的说话参考书”[2](P152)。
笔者认为:将该书定性为说话伎艺人的专业用书可能更确切些。
《醉翁谈录》的开篇甲集卷一是《舌耕叙引》,下设《小说引子》和《小说开辟》。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小说伎艺的致语而不是一般书籍的序或跋。什么是致语呢?致语类似于致辞,是宋代说唱伎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表演程式,是伎艺表演前的开场白,广告词。就它的形态而言,它同书籍的序或跋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序或跋可以不止一个,致语也可以不止一个;序或跋一般不单独存在,与正文相结合,致语也总是与后面的伎艺演出紧密相连,等等。但是,伎艺的致语与书籍的序、跋不同的地方更多:(1)伎艺的致语是为了表演用的,是本门伎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艺术形态与后面的伎艺形态一致;书本的序或跋是文字评论,是说明,不仅可以与书本的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在文体上也可以不一致。(2)致语的表演者一般也是伎艺的表演者,起码属于同一个演出团体;序或跋的作者却可以是书籍作者本人,也可以是他人。(3)序或跋所牵涉的是作者的经历、文章的内容、文笔的技巧等,重在学术和文本;致语讲的却是伎艺的来龙去脉,演员的迷人,演技的高超,——落脚点始终在伎艺表演上。(4)序或跋可以褒贬;致语却纯褒无贬,具有强烈的商业广告色彩。(5)书本的序跋,具体,个别,只适用于此而不适用于彼,这本书的序或跋决不可以用到另一本书中;伎艺的致语却抽象,一般,具有程式性,可以张冠李戴,稍加修饰即可适用于本伎艺的所有其他节目当中。
《舌耕叙引》正是宋代小说伎艺的致语。首先,“舌耕”已经点明了它的伎艺指向。其次,它论述的内容不是小说文本而是小说伎艺。固然它有“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的话,但紧跟着便说:“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为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所谓“小说者流”云云不过是追根溯源,标榜门户,而落脚点强调的则是小说的表演。它所要彰显宣传的不是著作的小说而是小说的伎艺。它一则说“言非无根,听之有益”,再则说“靠敷衍令看官清耳”,最后说“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讲说的都是诉之于听觉印象的小说伎艺特征。一般传奇杂俎的序或跋也会谈论表现的技巧,但所指是文字的技巧;《舌耕叙引》所展示的则是“试开嘎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讲的是表演技巧;而且强调“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呈现的完全是一个演出的氛围。《舌耕叙引》并不是为某一个具体的小说题目而写,也不是为某一个演员而写,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谓小说伎艺行当的广告词。从它有“演史讲经并可通用”的话来看,它甚至适用于整个说话伎艺。
如果我们认可《舌耕叙引》是致语的话,那么,《醉翁谈录》在甲集卷一之后,从甲集卷二到癸集卷二,其所收录的就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传奇和杂俎,而是当时小说伎艺的文本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后面附录的作品不是顺理成章的话本而是传奇和杂俎。那么,讲说的话本和供阅读用的传奇杂俎之间怎样区别呢?可粗略划分为四点:(1)由于小说伎艺是服务于市民阶层的,它在审美理想和趣味上就必须迎合市民的口味。《醉翁谈录》所收录的作品都是“闺情云雨共偷期”的事关风月之作。其中的诗词也充满蒜酪味,像“和尚性好耍,贪恋一枝花,见说醉归明月夜,滋味难禁价。金帛宁论价,毒手遭他下。料想从今难更也,空惹旁人话。”不是文人词,而是市井词。(2)小说伎艺话本固然需有文学性,但是更重视展现说话人的伎艺,也即显示“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从而给说话人的表演艺术留有较大空间。《醉翁谈录》中的作品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但其中的诗、词、花判相当突出,正是体现了“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的特色。(3)小说伎艺的篇章不能太冗长,且具有收费的阶段性特征。小说伎艺原是在瓦舍路歧中进行滚动性商业演出的,不仅演员需要间歇调整,更重要的是需要收取费用,这只要看看《水浒全传》中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便很容易明白。因此《醉翁谈录》中属于宋人的作品要么是简短的游戏文章,要么在较长篇章中的诗词,间隔正好可以作为收费的提示。(4)小说伎艺不仅题材丰富多样,而且伎艺趣味和风格也要丰富多样。小说伎艺的演出当日是在瓦舍路歧中进行的,它必须在节目的编排上具有丰富性,多样性,有穿插,有主次,才能适应市民的多重兴趣的需要和演出节奏调整的需要。《醉翁谈录》中的那些被称作是杂俎类的作品,比如“嘲戏绮语”、“花衢记录”、“闺房贤淑”,“花判公案”等,有的是笑话,有的是掌故,有的是趣闻,有的是念诵伎艺。虽然混杂,但正体现了瓦舍路歧中小说伎艺的特点。
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话本的名称”一节中将话本分为“说话人的底本”、“供阅读”的“话本小说”和“模拟话本而创作的”“拟话本”三种类型[2](P155)。从《醉翁谈录》在文本中疏淡故事情节而重视易忘的诗词骈文来看,它具有说话伎艺备忘录——说话人的底本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醉翁谈录》不是传奇和杂俎集,而是当时说书艺人讲说小说伎艺的专用书,由此,我们推断作者罗烨很可能就是说书艺人。
二、传奇体文言曾经是小说伎艺的话本
许多人认同《醉翁谈录》收录的文言小说是话本资料,但不承认它们即是当时演出的文本形式,理由是它们不是白话的口语,也与后来的元明话本体式不合。这当然有一定的理据。这个理据却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我们是从明清人的著录中确定宋人话本名目,然后又从元明人的话本中推断宋人话本的体制和程式的。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证明书目上的所谓宋人话本很多不可靠,一般采取了宋元话本一起含糊论述的方式;但许多学者在讨论中一直存有惯性,那就是往往从拟话本小说的形态来推论宋代小说的形态,从话本语体到话本程式都颇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任何一种文艺的语言形态不仅受当时当地的口头语言的影响,而且都受到其邻近同类文艺样式的语言形态和所承继的文艺传统的影响,说话伎艺也不例外。
采用浅近文言作为散说的体式,不仅为小说伎艺所专有,也为宋代其他说唱表演伎艺所采用。《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注:《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宝颜堂秘笈本。),曾被王懋的《野客丛书》(注:王懋《野客丛书》,见《稗海》振鹭堂本。)所引用,确为宋代作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说参请话本(注:参见张正锒《问答录与说参请》,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小说家的话本,而且还吸收了合生和商迷的成分”[3](P257)。它的语言形态就是浅近的文言。比如:
佛印持二百五十钱示东坡云:“与你商此一个迷。”东坡思之少顷,谓佛印曰:“一钱有四字,二百五十个钱,乃一千字,莫非千字文迷乎?”佛印笑而不答。
在语言形态上,它们与《醉翁谈录》中的“嘲戏绮语”、“妇人题咏”、“花判公案”中的文字并无二致。
鼓子词是宋代的说唱伎艺,它的散文部分所采用的文言更为雅驯。赵令畤在《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中说《莺莺传》的故事当时“无不举此以为美话”,“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4](P492);《醉翁谈录》也有“论《莺莺传》……此乃为之传奇”的话,可见当时小说伎艺有《莺莺传》的故事。但鼓子词中的散文部分却是分段节录唐代元稹《莺莺传》的文字。
宋代的小说伎艺在题材上从远处说承继的是文言小说的传统,从近处说承继的是唐宋传奇的传统。《醉翁谈录》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秀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注:皇都风月主人编《绿窗新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论才词有苏黄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正是指明了这种联系。《绿窗新话》是学术界公认的宋代说话的重要参考书,它所收录的154篇故事除去少量来源于正史、杂传、诗话词话和别集总集外,大部分取材于志怪传奇和笔记小说。题材既然来源于文言小说,宋代小说伎艺的语言形态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时讲说的语言甚至是全面承袭照搬过来的。
《醉翁谈录》收录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前代的文言小说,如《封陟不从仙姝命》、《刘阮遇仙女于天台山》、《裴航遇云英于蓝桥》等,它们或节录或改写,请看《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一节:
柳毅应举不第,将归还湘滨。因过泾阳,见一妇人牧羊。毅怪而视之,乃殊色也。然而眉(蛾)脸不舒,凝听翔立,若有所待(伺)。毅问(请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是)?”妇始笑(楚)而谢,终泣而对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嫁与(父母配嫁)泾川次子,为婢妾(仆)所惑,日以厌薄,乃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又复得罪,乃毁黜至此!”言迄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信耗莫通,闻君还乡(将还吴),甚近(密通)洞庭。欲(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可乎?”……(注:括弧中乃唐传奇《柳毅传》(见《太平广记》卷第419,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的文字,录以相较。)
可以看出,《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一方面是承袭旧文,一方面又依照讲说伎艺的要求,根据当时的语言习惯,对文字作了适当的调整,但保持了原作的文言形态和基本风格。承袭旧事的题材,依托旧文加以讲说,是很难摆脱旧文的语体形态的。宋人如此,明人也是如此。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收有《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都经过了冯梦龙的加工,但也都保持着文言的形态便是明显的例证。
另一类是当代的故事,比如《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苏小卿》、《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等,它们有着较浓郁的宋代口语特色,更通俗,也与后来话本的语言形态更接近。试看《王魁负心桂英死报》的开端:
王魁者,魁非其名也,以其父兄皆显宦,故不书其名。魁学行有声,因秋试触讳,为有司搒;失意浩叹,遂远游山东莱州。莱之士人,素闻魁名,日与之游。一日,为三四友招,过北市深巷,有小宅,遂叩扉。有一妇人出,年可二十余,姿色绝艳。言曰:“昨日得好梦,今日果有贵客至。”因相邀而入。妇人开樽,酌献于魁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使足下待桂英而饮天禄,乃来春登第之兆。”桂英谓人曰:“此大壮之士。”又谓魁曰:“闻君誉甚久,敢请一诗。”魁作一诗曰:“谢氏宴中闻雅唱,何人嘎玉在簾帏?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
《王魁负心桂英死报》较之《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显而易见要通俗得多,也更接近于后来的话本语言形态,但是,绾结而言,它并未离开宋代文言传奇的语言形态。它通俗平实,固然更口语化,却也未尝不具有宋代传奇的语言特色。
任何语言形态的发展都是渐进的,说唱伎艺的语言形态也是渐进并有规律可寻的。从传奇体的文言到说话体的白话,说话伎艺的语言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它不可能背离产生它的母体去另外建立一套语言系统。从《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看,在宋代的小说伎艺中,文言小说和传奇故事的数量相当多,因此小说伎艺的早期语言形态受传奇文本的影响自然较大。大概宋元之后,随着新话的增多,随着市井口语的影响加大,小说伎艺的语言形态才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用伎艺语汇上形成了定式。宋元时代新产生故事的创作及其演出活动催生并促成了小说伎艺的程式化和语言形态的定型化过程。但这一过程既是说话伎艺人学习并适应市井语言的过程,也是消化磨砺文言传奇语言形态的过程。宋代小说伎艺的语言不可能如同元人,特别是如同明人“三言”“二拍”的语言一样,正像宋金杂剧的体制和语言不可能像明清传奇一样是很自然的事。
三、关于宋人小说的演出体制
宋人小说伎艺的演出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的体式,二是演出的程式。
(一)叙事的体式
孤立地考察叙事体式并不容易,但假如采取比较和对照的方法,那么叙事体式的特点就容易凸现出来。宋人小说伎艺的叙事体式与唐传奇相比较,除了在语言词汇上有所改动,以适应讲说的需要外,其一是在结构上它删繁就简,砍削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蔓,使得矛盾冲突更加突出,线索更加明晰流畅,趣味更加适应市民需要。比如《醉翁谈录》中《柳毅传书遇洞庭水仙女》删去了迎龙女回宫后的欢宴,听火德真君论道,柳毅成仙后与故人相遇等情节;《裴航遇云英于蓝桥》删去了裴航与樊夫人的过多瓜葛和洞天仙府烦琐的礼仪,这不单是因为两者趣味侧重点不同,唐传奇的卖座热点是神仙之事,而宋人的关注焦点是浪漫之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删削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有关。唐传奇是为阅读而创作的,在结构上可以枝蔓丰富,盘根错节,而宋人小说是为讲说而创作的,它在时间与空间上就需要相对单纯紧凑,才能引导听众探幽揽胜。是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促成了小说伎艺的叙事模式向单纯的线形结构发展。其二是宋人小说伎艺在叙事中有意识地掺入大量的诗词韵语,有的话本故事甚至通篇由韵语连缀而成。韵语表述以“诗曰”、“词曰”的引用程式出现。有无“诗曰”、“词曰”既是前代传统题材故事入选的重要条件,更是当代新编故事话本的结构模式。比如《醉翁谈录》中《静女私通陈彦臣》静女与陈彦臣先是以诗互通情愫,然后以词歌咏两人欢会。爱情发生曲折时,两人又以诗词互诉衷肠。公堂之上两人受命各吟一诗,最后以宪台王刚中花判作结。《崔木因妓得家室》写崔木因诗词先是认识妓女赛赛,后又通过赛赛以诗词之力娶了黄舜英。宋人小说伎艺是一种综合表演艺术,必须“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诗词曲语不仅可以增加文字的表现力,更可以活跃气氛,调整叙说节奏。如果说唐传奇中“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的话,那么,宋人小说伎艺中大量掺和诗词韵语,则不仅是为了文章,更是为了表演伎艺的需要才出现的。“蕴藏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后来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穿针引线的普遍模式。其三是宋人小说伎艺中模拟表演的细节得到了加强,试看《醉翁谈录》中《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一段:
一日,生谓李氏曰:“我之父母,近闻知秀州,我欲一见,次第言之,迎尔归去,作成家之道。”李氏曰:“子奔出已久,得罪父母,恐不见容。”生曰:“父子之情,必不致绝我。”李氏曰:“我恐子归而绝我。”生曰:“你与我异体同心,况情义绵密,忍可相负?稍乖诚信,天地不容!但约半月,必得再回。”李氏曰:“子之身,衣不盖形,何面见尊亲?”生曰:“事到此,无奈何!”李氏发长委地,保之苦气(疑应作‘苦命’),密地剪一缕,货于市,得衣数件与生。乃泣曰:“使子见父母,虽痛无恨。”生亦泣下曰:“我痛入骨髓,将何以报?”李氏曰:“夫妻但愿偕老,何必言报。”次日将行,李氏曰:“不果饯行。事济与不济,早垂见报。稍失期信,求我于枯鱼之肆!”言迄哽噎,泪成行下。彩云曰:“君之此去后,使我娘子将何以度朝夕?但愿早回,以济不足。”生亦悲恨而别。
这样细腻繁复的对话在唐宋传奇中显然是没有的。它的出现,与其说是文字描写的进步,不如说是带有浓厚戏剧表演色彩的酣畅笔墨,是话本式的叙事体式的进步,是“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的产物。
(二)演出的程式
现在治文学史的人提起宋代小说伎艺往往认为是表演故事的,话本也就是故事的文本。这当然不错,但过于简单化了。实际宋人小说讲说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不仅包括传奇故事,也包括掌故、方物、逸闻、笑话、诗词名句、花判联对。所以,现在看《绿窗新话》、《醉翁谈录》中的“花衢记录”、“烟花品藻”,我们认为是杂俎,是资料,而当日它们却是小说伎艺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话本。它们之所以成为小说伎艺的一部分,一方面来源于“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的传统观念,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演出的需要。宋代小说伎艺的演出地点虽然有瓦舍,但路歧茶楼更多,场次并不十分固定,演出的时间也无定准,观众流动性很大,演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伎艺,才能在演出场次的调度上,趣味变换的调节上适应需要。因此,演员自己标榜“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而演出则需要“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社会上要求他们“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称他们是“书生”、“贡士”、“万卷”。
宋人小说伎艺有广告题目,而且,不论篇幅长短,不论叙事与否,均同等对待。《绿窗新话》就是把长的、短的、叙事的、不叙事的一律给以一个叙事型的七言题目的。比如《柳毅娶洞庭龙女》、《裴航遇蓝桥云英》、《吴绛仙蛾绿画眉》、《寿阳主梅花妆额》等。不过,初始宋人的小说题目大概都是文言小说型的,简明,以人物为中心,如郑樵在《通志·乐略》所说“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之类,与唐宋传奇题目没有什么区别。大约在北宋后期,随着小说伎艺盛行,题目开始讲究起来,刘斧的《青琐高议》出现了文言小说题目之外的七言副标题,鲁迅说:“因疑汴京说话标题,题材或疑如是,习俗浸染,乃及文章”[5]。后来的《醉翁谈录》中的标题虽然是杂言,但七言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简单的文言小说型的标题演化为七言或多言的伎艺型的标题,从一般性的标题演化为叙事性的标题,主要不是出于修辞方面的目的,而是适应市场的需要,宣传的需要,希望以故事情节耸动吸引人的需要。不过,有宋一代的话本小说,文言小说型的题目形式仍然不绝如缕,体现了传奇文体的巨大影响。
宋代小说在演出前像其他瓦舍伎艺一样有致语。按照《醉翁谈录》的记载,先讲“引子”、“开辟”,“引子”、“开辟”讲完后,“便随意据事演说”。“引子”、“开辟”适用宽泛,不仅适用于小说伎艺,也适用于演史讲经。那么宋代的小说伎艺有没有“入话”或“散场”等程式呢?大概没有。“入话”一词不见于宋人文献,首见于明人所刊《清平山堂话本》中。“散场”一词也不见于宋人文献,首见于元刊小说《红白蜘蛛》中(注:见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入话”的本意,依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它的出现缘起于宋人小说伎艺的演出方式:“话本为什么要有入话呢?这是因为说话人都是卖艺谋求衣食的,聚集听众当然越多越好。他们不论在街头或瓦肆中讲说,都得拖延一些时间,以便招徕更多的听众,还要稳定住已到场的听众。到了适当的时刻才‘言归正传’。”[2](P137)但是,需要“入话”的功能和当时是否就有“入话”的形式并不是一回事。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当时的致语完全可以履行“入话”的功能,假如有了致语,那么再诉求于“入话”就显得叠床架屋了。再者,这一功能,也可以由简短而独立的掌故、笑话、琐闻、诗词名句等来充任,如同戏剧中的“冒头”、“折子戏”之与押轴戏的关系。尤其是,现今发现的“入话”有很大数量是由诗词来充任的,但是,在非常重视诗词,几乎是有闻必录的《绿窗新话》、《醉翁谈录》话本中,从未见有诗词起、诗词结故事的先例,换句话说,假如有,我们不可能不在《绿窗新话》、《醉翁谈录》中发现痕迹。可见,起码在宋代的话本小说中是否存在“入话”非常可疑。入话的出现,大概是在瓦舍消亡之后,“瓦舍众伎”失去了因聚集竞争,因汇演而竞喧的环境,各种伎艺开始独立演出,致语失去了伎艺广告词地位,而其“开辟”、“引子”的功能,其首尾有诗词的形式,逐渐被小说伎艺的单独故事“入话”所采用。
宋人小说伎艺也没有“头回”。“头回”虽然是宋人瓦舍伎艺语汇,但指的是独立的首次演出而言,如“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6](P29)。元至治年间刊刻的《秦并六国平话》中虽然有“这头回且说个大略,详细根源,后回便见”[7]那样的话,但显然是讲史分回演出的用语,与宋时小说演出“顷刻间提破”不合。小说话本出现“头回”的字样,当也是小说伎艺脱离瓦舍,演出场所和观众较为固定后,由于小说伎艺篇幅加长,于是借鉴讲史的“头回”而形成的。
至于“散场”的问题则比较复杂。宋人喜好议论,小说伎艺也不例外,“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从《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来看,议论很少在故事中夹叙夹议,而总是在故事的结尾以“某某曰”的形式出现,估计是在小说伎艺演讲完之后进行一番评论。但从两书有议论的篇章并不多来看,在宋人的说话伎艺中虽有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评论作伎艺结束的形式,但不普遍,不能当作一种结尾的普遍程式来确认,更很难就认为当时已经形成如元人那样的散场程式。“入话”、“散场”为后来的程式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宋人《醉翁谈录》和明人《清平山堂话本》中都收有《蓝桥记》,除去题目《醉翁谈录》称《裴航遇云英于蓝桥》略有不同外,内中文字几乎完全相同,所异者就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多了“入话”诗和散场白。
总之,宋人小说伎艺虽然“举断模按,师表规模”,确实形成了某些程式,但是否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入话”、“头回”、“散场”则值得商榷和探讨。
四、宋代话本小说研究的尴尬
宋代说话伎艺的出现,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其自身有不容忽视的审美意义,后来的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说唱文学乃至戏剧文学的发展更是与之血脉相连。但是假如我们翻开文学史著作,却会发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它们的描述,一般是在作品篇目上宋元相连,含糊不清;在体制形态上甚至宋元明三朝不分,混为一谈。
比如目前学术界对于宋代话本小说篇目的认定方面,下面的说法带有相当的代表性:“下列作品是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说话本:《张生彩鸾灯传》(见《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风月瑞仙亭》、《杨温拦路虎传》、《西湖三塔记》、《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以上见《清平山堂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以上见《古今小说》);《错斩崔宁》(又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上见《醒世恒言》);《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又题《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定山三怪》(又题《崔衙内白鹞招妖》)、《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上见《警世通言》)等。”[8](P244)不能说这些论断没有一定根据,因为他们是“依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等文献对宋元小说话本的记载,再与明人刻印的有关作品相互参证”[8](P244)得出来的结论;也不能说这样表述没有道理,因为上列小说进一步断代确有很大的困难,亦为苦衷所在。但假如我们排比这些作品,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其中的作品有的古朴、简明,描写相对粗糙,故事结构相对简单,而有的作品有着细致流畅的文字描写,有着细密曲折的故事结构,其中的差异,并不是文字风格的而是基本形态的。
再比如,就话本的体制而言,一般是这样叙述的,仍以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发生的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权作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艺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作散场’之类套话作结。”[8](P246)
表面上看,这种三段的说明入情入理,但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归纳总结了现存宋元明三代的话本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东拼西凑的归纳,并不符合资料引用的同一原则。比如在上文所讲的“比较可靠的宋元小说话本”中就找不到“正话”字样,也根本无法弄清“入话”和“头回”之间的关系,支持上述说法的例证其实大多数是明代的拟话本。假如联想到从宋金杂剧到元杂剧,从南戏到明清传奇在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及其因袭变化,我们还能容忍说话这种说唱形式从宋代到明代几百年不变的混沌叙述吗?
不可否认,传统的目录文献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宋代小说的研究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传统的目录和考据学对于宋元话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它们没有把宋代的说话当成综合演出的伎艺来看待,而是更多地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加以审视。它们承认故事的本事或情节具有累积性和变异性,但无视或忽视伎艺形态和演出程式也具有累积性和变异性。它们排斥短小的“嘲戏绮语”、“花衢记录”、“闺房贤淑”、“花判公案”等是小说话本,只认定长篇,长篇中又只认定有著录或有明确话本程式的是宋元话本,还排斥传统题材改编的话本是宋元话本,流风所及,即使1941年《醉翁谈录》在日本发现,也只承认它是“话本参考资料”。既然将相当部分的话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当然研究的结论也就带有缺损。随着宋代话本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渐渐发现明人提供的研究平台并不可靠,于是开始运用文献考据学的办法,一篇一篇加以排除。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梳理现存宋代话本小说的研究中基本采用的是减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在“现存的宋人话本”中举了“《碾玉观音》等四十种”,而上引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可靠的宋元小说话本”加在一起叙述,才不过十几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干脆说:“以前认为是宋代话本的,今天看来基本靠不住。”[9](P135)尽管学者的辨伪工作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是一篇一篇的甄别,并未对话本小说总体形态进行断代,结果仍然出现了上述混杂的尴尬现象,也由于缺乏总体的定性和整合,缺乏明确的伎艺形态和文体形态的界定,便产生了虽然宋代的话本一篇一篇被怀疑被否定,但对于宋人小说体制的原有结论仍然袭用着的情况。
传统的目录学和考据学在小说话本的研究中是不应该被冷落的,而且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难道不应该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路径以改变在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中的混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