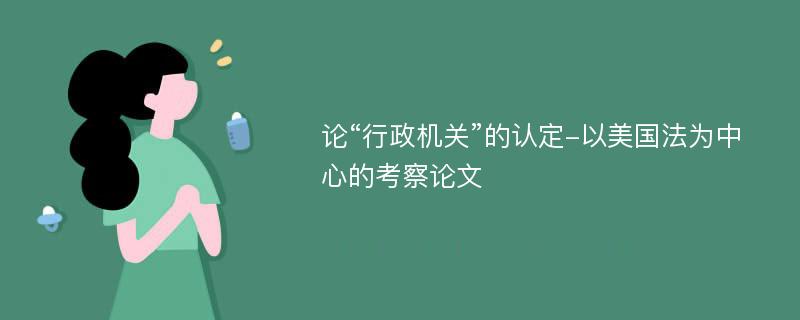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
——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王 军*
摘 要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关键词 行政机关 认定标准 判例法 行政主体
目 次
一、行政机关的识别难题
二、规范变迁中的行政机关概念
二是调整水利资金计提政策和标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按照原地表水、地下水征收标准的三倍进行征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调整为按全年土地出让总收入的2.5%计提,计提资金比2012年增长300%。一年来全省各项水利规费征收突破62亿元,比2012年增长120%。
三、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机关认定
四、认定标准的功能及变迁
注重与社交网络平台的融合,注重分享,让一个人有趣的体验成为众人的饕餮盛宴,更加快速地实现旅游信息的传播,让AR成为更优秀的载体。
五、对中国的启示
实质独立的权力是“行政职能”标准的核心。Soucie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案中涉及的科学和技术局是否是《行政程序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一审中,哥伦比亚地区法院的主审法官普拉特拒绝了原告的请求,认为科学和技术局不属于行政机关,而仅是总统办公室的一部分。二审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的主审法官贝兹伦执笔了最终的判决,判定科学和技术局是行政机关〔43〕 448 F.2d 1067 (1971). 。其认为,《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机关明显指的是那些在行使特定职能时具备实质独立权力的行政组织,涉案的科学和技术局不仅具有独立实体的地位,还承担了评估联邦行政机关开展的科学研究项目、在完成科学和技术领域相关的联邦政策时为总统提供建议和协助等功能,因而具备了“实质独立的权力”,从而属于行政机关。由此,具有标杆意义的Soucie案确立了行政机关认定时的“行政职能”标准,其从待判断的组织的独立实体地位展开审查,最终核验其是否具备“实质独立的权力”,并结合《行政程序法》的主要目的,将权力定位在规章制定和行政裁决这两类典型的行政权之上。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私主体可以承担广泛的公共职能,那么其是否也可如行政机关一般负担法律责任,毕竟《行政程序法》只为行政机关提供行为的标准和统一程序。〔2〕 See 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S. 33, 41 (1950). 也即,为了“确保民营化、外包以及其他旨在放权给私方当事人的措施,不会挫伤行政法试图规定的责任性、程序正规性以及实体理性的公法规范,非常紧迫的挑战在于确定何时以及如何将法律的要求扩展到履行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3〕 参见 [新西]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认真对待私人权力”的论断,认为应当改变原来的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行政权观念,并将公私协商关系作为替代方案。〔4〕 See Jody Freeman, “The Private Role in Public Governance” 75 N. Y. U. L. Rev 543 (2000).鉴于此,应当探索私主体承担公共职能是否同时承担相应公法义务的根源,这就牵扯到行政机关认定的问题。
一、行政机关的识别难题
对于行政机关司法认定的讨论,有必要以公共职能承担主体为主线梳理美国自建国起行政机关的演变史,并分析机关的倍增、权力的扩展如何在三权分立的体系中得以维系,透视《行政程序法》实施以前行政机关在数量和权力上所体现出的特点,特别是在此前提下形成的行政机关的识别难题。
因而,总体而言,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主要受教师价值观、与学校相关他人的关系、所教学科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一)行政机关在数量上的激增
在美国,行政机关的数量经历了一个划时代的激增过程,行政活动也从较少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重要因素。与此相伴随,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也从最早的财经、对外政策、国防等事项扩展到更为宽泛的事务上,不管是农业、商业、旅游业等范围的扩展,还是规章制定、行政裁决等权力的增加,都不断造就着“规制国”的出现与维系。
美国建国初期,国会仅设立了战争部、军事部等行政机关,行政活动也局限于财经政策、对外政策、国防等少数几个领域。就权力来看,所涉范围非常有限。〔5〕 国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三部授权的法律,其中两部法律是当前由财政部、海关署实施的法律的先驱,另一部有关补助金的法律现由退伍军人管理局实施。分别参见Act of July 31,1789.1 Stat 29 (1st Cong,1st Sess., Act of September 1,1789,1 Stat 55 (1st Cong, 1st Sess.) , Act of September 1,1789, 1 Stat 95(1st Cong, 1st Sess.). 就行政机关的组成人员来看,也呈现出较少的势态,即便是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也只有4800余人。〔6〕 参见谭融:《西方国家官僚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60页。 究其原因,这与当时的政府架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建国之初,社会关系和经济交往相对简单,人们通常更加重视作为民主意志代表者的议会的作用,因为其承担着制定法律的重要职能,而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机关只被看作是法律的执行者,其享有的仅仅是法律的“执行权”,并不具备现在我们看到的典型行政机关所具备的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等权力。〔7〕 See Cuthbert W. Pound, “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Freund e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 Thomas Law Book Co. , 1928, p. 111.具体而言,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有限政府”的伏笔,行政机关不但要接受内部来自总统的领导和监督,还要时刻面临国会的监督以及法院的审查,〔8〕 See Stephen G. Breyer and Richard B. Steward,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 Aspen Publishers, 1992, pp. 3-4.这也是美国行政法上“传统模式”的重要体现。〔9〕 See Richard B.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88 Harvard Law Review 1667 (1975).建国后期,随着经济事务的丰富和私人活动的活跃,源于对这些事项予以规制的需求随之产生,对于铁路业竞争的规制即是典型。〔10〕 See Marshall J. Berger and Gary J. Edles, “Established by Practice: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Independent Federal Agencies” 52 Admin. L. Rev. 1123(2000).
《行政程序法》开篇,界定了在其立法目的之下的概念内涵,其中第一项内容便是对行政机关的界定:“行政机关”,是指联邦政府机构,不论其是否设在另一行政机关内部或者接受另一行政机关的监督,但它不包括——(A)国会;(B)美国联邦法院;(C)美国领地或属地的政府;(D)哥伦比亚特区政府;或者,除适用本编§552的规定以外,不包括——(E)由纠纷各方当事人的代表或由纠纷各方当事人所在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以解决纠纷的机关; (F)军事法院和军事委员会;(G)在战时战区或占领地的军事当局;(H)根据《美国法典》第12编§1738、§1739、§1743和§1744;第41编第2章,第50编附录 §1622、§1884、§§1891-1902,以及 §1641(b)(2)规定行使职权的机关。
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促使美国成为了世界工业大国,引导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伴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化以及各类社会运动的蓬勃开展,行政规制的进程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政府管理的事务项目逐渐走向多元化。1887年,国会通过制定《州际商业法》建立了州级商业委员会,负责铁路业的监管事务,这代表着具有现代意义的规制机构的产生。〔11〕 See Ronald A. Cass, Colin S. Diver and Jack M. Beerman,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Wolters Kluwer, 2006, p.124.由此开始,这类行政机关的数量出现激增的现象,1902年成立的公共健康署、1913年成立的联邦储能委员会等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法院的判决中,对《行政程序法》中定义进行解释的标志性案件是Soucie v. David案(以下简称Soucie案)。〔42〕 See Ann H Wion, “The De fi nition of ‘Agency Record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31 Stan. L. Rev . 1093,1115(1978-1979).Also see Grumman Aircraft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v. The Renegotiation Board, 482 F.2d 710 (1973), 157 U. S. App. D.C. 121(1973).该案确立了行政机关认定的“行政职能”标准,其不仅在解决个案上具有定纷止争的效果,而且形成了审理同类案件的判例法。
如上所述,在《行政程序法》实施之前的美国,行政机关的数量经历了成倍的增长,特别是整个十九世纪更是建立了大量的行政机关,〔13〕 See Jerry Mashaw, “Federal Administ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Gilded Age” 119 Yale L.J . 1362 (2010).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不管是在经济起步期对于垄断的控制,还是经济繁荣时对于新兴领域的规制,抑或是经济受挫、百废待兴时期刺激经济发展的需求,都不同程度上需要行政机关承担公共任务,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可期待性预期,并防止市场自由发展中天然存在的各类弊端。
(二)基于规制需求的权力扩张
从行政机关数量增长的现实中,可以发现行政机关逐渐在事务范围上拓展了自身的权力,而与之相匹配的是,行政机关在行使的权力范围上也产生了明显的扩张。
建国初,分权原则的引入使得政府权力总体划分为立法、司法和执法三大部分,以防止权力滥用。〔14〕 See William B. Gwyn, The Meaning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 New Orleans, 1965, pp. 127-128.在这样的政府结构下,行政机关仅仅具有执行法律的权力,而不具备司法、立法两项职能。〔15〕 See R. Pierce, S. Shapiro and P.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 Foundation Press, 1999, p. 25.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诞生,实质上将权力扩展到以铁路运输为代表的运输业之上。随着国会不断赋予州际商业委员会更多的实质性权力,〔16〕 See Thomas K. Craw, Propres of Regul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7.以及法院对于州际商业委员会权力范围的态度从完全对抗逐渐转为基本认可,〔17〕 参见张兴祥等:《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一个具备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行政机关就此产生。〔18〕 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自此,以独立规制机构为代表的行政机关,在权力范围上从最初的纯粹执行权转为执行、立法、司法三权合一,并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
红琴离开茶庄后,风影忽然感到头部隐隐作痛。他从肺腑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接着漫不经心地来到了她挂红丝带的地方,他站定,睃了一眼,又目不转睛地盯住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她曾经也在山湾里挂过红腰带,他们每幽会一次,她就打一个结。可眼下的红丝带,还有上面的千千结,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她每次下山从村子里回来,都要来到这个山坡上,在这红丝线上打一个结。他知道这打的是心结,可是她打这些心结还怎么能够打得开呢?她为什么要打这些结呢?
行政机关在规模上的扩张和权力上的扩大,客观上为公民识别何为行政机关造成了困难,因为相比在行政机关数量有限、权利受限的时代,承担行政任务的部门开始变得纷繁复杂,此为其一。〔19〕 See Duncan Kennedy, “The Stag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130 U. Pa. L. Rev . 1349 (1982).另外,人口的增长、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都实质上要求规制的提供,这大大扩展了行政机关的工作任务,并对行政机关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新要求。〔20〕 See Daniel E. Hall, Administrative law: Bureaucracy in a Democracy (3rd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6, p. 11.然而,行政机关的扩张没有带来相应资源配备的增长,因此还是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21〕 See Pierce,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Actions in a Period of Diminishing Agency Resources” 49 Admin. L. Rev . 61 (1998).所以,除了进行理论修正和赋予更大的裁量权,政府要有效应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问题,还要在特定任务中引入外部力量承担一定的公共职能,以解决能力不及和精力不足所产生的管理缺位问题,〔22〕 本文使用私有化一词的含义是政府将公共职能交由私主体运用市场竞争方式完成的方法。See Jody Freeman, “Extending Public Law Norms Through Privatization” 116 Harv. L. Rev . 1285 (2003).基于此,合作治理的模式得以确立。但是,问题在于,当公民正迷惘于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承担公共职能时,私主体的出现却加剧了这一困境,此为其二。
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既与经济、社会推动下行政机关的扩张有关,也受到私主体承担公共职能的影响。归结起来,其共同指向的问题则是行政机关的判断问题。即,除了明确隶属于三权分立中“作为享有权力的机构组合概念”的行政分支〔23〕 See Richard E.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and the Modern Presidents: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Free Press, 1990, p. 28.的那些机关以外,如何来辨识当前正在承担公共职能的组织是否属于行政机关。
二、规范变迁中的行政机关概念
(一)行政机关的最初定义:《联邦行政程序法》的界定
由于原发性乳腺肉瘤比较罕见,生物学差异大,临床上很难有统一的治疗模式。手术是该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乳腺肉瘤局部切除术和广泛切除术是目前常用的手术方式。同其它肉瘤一样,乳腺肉瘤对放化疗不是很敏感,放化疗一般用于含高危因素较多的原发性肉瘤的术后辅助性治疗。为进一步探讨乳腺肉瘤的临床特点及合理的治疗方案。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立医院和安徽省肿瘤医院2001年7月至2014年7月共收治的17例乳腺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
从文义上来看,行政程序法的定义以联邦政府机构作为行政机关的同一表述,实质上并未明确指出具体范畴,而“不论其是否设在另一行政机关内部或者接受另一行政机关的监督”也只是将一些内部管理机关或者受监督机关纳入进来,并未实质性地产生限定作用。因此可以说,该定义实质上是将那些凡是有权力的机关都纳入进来了。〔24〕 Se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S.7, 79th Congress, 2d Session, Report 1980, 253(1946). 从认定方法上看,行政程序法并没有以机关名称来进行界定,而是以行政机关在具体情况中的功能和活动来划分的。〔25〕 Se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 Handbook of Law and before Federal Agencies (2d ed), 1946, p. 113. 反之,如果行政机关的定义是以部门、委员会等称谓展开的,那么就属于形式主义的遴选,会造成实务操作时的严重误解。
综上,行政程序法在其定义条款中对行政机关的界定,基本上是采取了“权力标准”,而且是以功能和活动来作为认定方法的,这代表了立法者在立法时所要实现的目的,〔26〕 See Staff of Senate Comm. On The Judiciary, 79tr Cong., 1st Sess.,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13 (Comm.Print 1945). 也是后续该法条进行适用、解释的重要起点。
(二)行政机关定义的衍变:《联邦信息自由法》的推进
其一,在旧的等级制度和威权体制经过启蒙思想的洗礼之后,宪政理念开始萌芽并成为指导国家成立的重要思想。尽管由于历史传统、伦理意识等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具体宪政制度各有不同,但它所建构的秩序结构与之前的封建等级秩序相比,显而易见的新东西是:旧的层层节制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并立的二元结构。〔61〕 金自宁:《公法/私法二元区分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此时,国家权力来源的理解,被理解为经由市民自愿让渡的权利集合,因此首先意味着公民对于国家的监督权和主人地位,其次才是国家对于公民基于公共利益的管理和公民的相应服从。在美国,行政体制向政府架构内部的国会、总统和司法机构进行渗透的同时,〔62〕 See Peter Woll, American Bureaucracy (Second Edition ), W. W. Norton &Company, Inc., 1977, Preface, p. 1.还通过职能下放、职能外包、合作治理等方式将私人和私人机构牵连进来,成为公共任务的完成主体,此时“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就不断发生着重要变化。〔63〕 See Sean Farhang, “Public Regulation and Private Lawsuits in the American Separation of Powers System” 52 Am. J. Pol. Sci .821 (2008).也正是这样的变化,影响着行政机关认定标准中出现了从组织到事务的审查对象上的变化。
为了保障公民个人获知信息的权利,扭转信息经常不予公开的现状,国会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这是对《行政程序法》最为重要和显著的修改,〔30〕 William H. Allen, “The Dur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72 Va. L. Rev . 235, 252 (1986).其不仅明确取消了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限制,〔31〕 See Theodore Sky,“Agen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 Admin. L. Rev. 445 (1967-1968).还在后续修改中对“行政机关”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扩大了“行政机关”的范围,〔32〕 See Wion Ann H, “The De fi nition of ‘Agency Record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31 Stan. L. Rev . 1093(1978-1979).这从国会在立法时的目的可见一斑。〔33〕 See Richard J. Pierce,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Fourth Edition ), Aspen Law &Business, 2002, p. 3.更为重要的是,该定义还被《隐私权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所采用,〔34〕 See Jay M. Zitter, “What is Agency Subject to Privacy Act Provisions” (5 U.S.C.A. § 552a), 150 A.L.R. Fed . 521(1998). Also See Kevin W. Brown, “What is ‘Agency’ within Meaning of Federal Sunshine Act” (5 U.S.C.A. § 552b), 68 A.L.R. Fed . 842(1984).成为目前探讨行政机关认定最为重要的依据。
山洪灾害防治是福建省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总结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前期经验的同时,也应思考和分析山洪灾害防治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例如,项目运行管理难度大,乡村防洪基础依然较薄弱,山丘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仍有待增强等。当前,福建省正在加快完成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任务,加强运行管理,不断提高山洪灾害防治水平。
1974年《信息自由法》的修正案中明确了行政机关的定义:〔35〕 5 U.S.C. § 552(e) (1976). 根据本节的立法目的,本节所称“行政机关”和本编§551(1)的界定一样,包括任何行政部门、军事部门、政府公司(government corporation)、政府控制的公司(government controlled corporation)和属于政府行政分支(包括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其他机构,以及任何独立规制机关。可以看出,该定义一方面明确了其与《行政程序法》定义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从国会立法时的资料来看,扩宽了《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机关定义。〔36〕 Se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Source Book: Legislative Materials, Cases, Articles, S. Doc. 93-82, 93d Cong., 2d Sess.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自由法》的定义中,除了明显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部门、军事部门、政府分支机构和独立规制机关之外,还包含了政府公司和政府控制的公司两类特殊机构。因此,与《行政程序法》相比,《信息自由法》中行政机关的范围有所扩展,将那些不属于《行政程序法》中行政机关的组织纳入新定义之中。〔37〕 Se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 Amendments of 1974 Source Book: Legislative History, Texts, and Other Documents, at 128 (Jt. Comm. Print 1975). 同时,国会在《信息自由法》立法之时,对于定义条款所赋予的期待依然是“权力”标准,具体表现为运用政府职能的方法来加以界定。〔38〕 Se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 Amendments of 1974 Source Book: Legislative History, Texts, and Other Documents, at 128 (Jt. Comm. Print 1975).
三、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机关认定
鉴于行政机关在识别中存在的难题,尽管立法通过专门条款进行了澄清,〔39〕 See 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Seventies” 4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60, 269(1976).但是法律条文的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相当模糊和可供解释的空间。〔40〕 See James O. Freedm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the Contro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19 U. Pa. L. Rev. 1 (1970-1971).具言之,即便国会通过立法文本宣示了其立法目的,但在条文的具体适用时,定义的判定还有赖于法院的具体审查,并通过判决的方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对于《行政程序法》中何为“机构”的这一看似简单问题的判断,更是存在认定困境。〔41〕 See Edward C. Walterscheid,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Data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5 Rutgers Computer & Tech. L.J . 1 (1989).Also see Kenneth Culp.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Seventies” 4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60 (1976).早期的法院采取了司法谦抑的态度,并没有过多地对该类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特别是涉及私主体行使权力的案件,则更是鲜有判决。不过,随着立法的推进和行政事务的繁杂,私主体越发成为承担公共任务、实现公共目标的重要外部力量,其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可回避地面临公众对于其权力来源的民主性、权力行使的合法性等质疑。因而,在司法审判中明确“行政机关”的标准,并对可能的权力外溢和失控加以钳控,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行政职能”标准
1929年,美国迎来了一场以股市“黑色星期四”为开端的严重经济危机,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的萧条使得新任总统罗斯福不得不采取“新政”措施。在自由放任思想观念在“进步时代”得到初步修正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市场本身存在的重大缺漏,并产生了由对民选官员负责的行政机关来进行统筹管理的意愿。同时,在很多领域内,行政机关往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专业智慧,这也使得行政机关具备足够的行动能力来改变萧条的现状。纵观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的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扩展,行政机关的数量也在大量社会事务的恢复中呈现倍增的现象。〔12〕 See Kenneth C. Davis, 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ment , West Publishing Co., 1960, p. 27.
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深深植根于公私分立、公私有别的基础之上,政府作为代表公众行使行政职能的主体,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而私主体则以盈利为目标,不断追求更多的私人利益。在该视野中,法律关系是比较单纯的、容易识别的。此时,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往往体现为法律优先、正当程序以及禁止授权等内容,并通过“正当化政府权力的运用推动着行政法这门学科的发展”。〔1〕 参见 [新西]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然而,随着现代行政任务的繁杂化、公私融合以及民营化、权力下放等趋势的出现,上述图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政府开始频繁地与私主体共同完成公共任务,从专业领域外包、行政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草案起草到行政许可的协商颁发、行政职能的全面外包,都呈现出私主体承担公共职能的现实样貌。
“行政职能”标准成为判例法上的标准,在后续同类案件中得到反复适用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自身的丰富与完善。首先,法院对“行政职能”标准进行了反复的忠实适用。Expeditions Unlimited Aquatic Enterprises, Inc. v. Smithsonian Inst.案、〔44〕 566 F.2d 289(1977). Judicial Watch, Inc. v. U.S. Secret Service 案〔45〕 726 F.3d 208(2013). 等大量案件即是明证。其次,后续法院在适用中还对“行政职能”标准中的权力要素进行了细化和丰富。考虑到“实质独立的权力”仍包含着不确定的认定因素,后续判决中逐渐出现了对权力要素进行细化和丰富的内容,这既体现在对于权力范围的发展上,〔46〕 Meyer v. Bush, 981 F.2d 1288 (1993). 也体现在对权力形式的丰富〔47〕 Washington Research Project, Inc. v.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504 F.2d 238(1974). 和权力效果的强调上〔48〕 See Edward C. Walterscheid,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Data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5 Rutgers Computer & Tech. L. J. 1 (1989).。最后,后续的案件中还出现了“行政职能”标准之下新的审查内容。某一主体的设立方式和内部架构等组织因素成为法院适用“行政职能”标准时不断审查的内容,〔49〕 See James O. Freedma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the Contro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19 U. Pa. L. Rev . 1(1970-1971).这可以统合归纳在“行政职能”标准之下,形成更为完整的审查要素。
防治小麦锈病主要方法就是加强栽培管理工作,选择抗锈病的小麦品种。适当调节小麦播种时间以及播种量;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适期播种。在小麦生长过程中做到合理灌溉、科学施肥;病害发生后;亩用100克的代森锌可湿性粉剂,对水30kg喷雾。
(二)“监管关系”标准
在信息公开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原有的《行政程序法》中的定义及认定标准越来越无法解决信息公开的新问题,〔50〕 See Edward C. Walterscheid,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Data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5 Rutgers Computer & Tech .L. J. 1 (1989).这不仅会引起“行政职能”标准的式微,〔51〕 See Nicole B. Casarez, “Furthering the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in Privatized Federal Corrections: The Need for Access to Private Prison Records” 28 U. Mich. J. L. Reform 268 (1994-1995).还会引起法院在个案中或创设或寻觅新的司法审查标准,〔52〕 See James T. O’Reilly, Feder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Volumes 1 ) , Westlaw, 2013, p. 66.形成新的判例法。在具有标杆意义的Forsham v. Harris案(以下简称Forsham案)〔53〕 445 U.S. 169, 100 S. Ct. 977, 63 L. Ed. 2d 293, 5 Media L. Rep. (BNA) 2473 (1980). 中,法院确立了“监管关系”的标准。〔54〕 See Craig D. Feiser, “Privatiz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 Analysis of Public Access to Private Entities Under Federal Law” 52 Fed. Comm. L. J . 21 (1999-2000).
“监管关系”标准的形成经历了从民法规则到行政法规则的演进。从1976年的United States v.Orleans案〔55〕 425 U.S. 807 (1976). 开始,法院在《联邦侵权赔偿法》上提出了“监管关系”标准的基本内容,并对社区行动机构的法律性质做出了判断。这可以看作是“监管关系”标准在侵权法上所做的准备。接着,1976年的Rocap v. Indiek案〔56〕 539 F.2d 174, 176 U. S. App. D.C. 172(1976). 也运用了“监管关系”标准的基本要素对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作出认定。可以看出,“监管关系”标准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和一蹴而就的,其本身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且是在判例法的形成过程之中不断得以积累的。
“监管关系”标准在后续同类案件中得到了普遍适用。以Irwin Memorial Blood Bank of San Francisco Medical Soc. v. American Nat. Red Cross案〔59〕 640 F.2d 1051(1981). 为例,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国家红十字会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法院判决,不论将国家红十字会认定为机关、公司还是其他组织,要使其成为联邦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前提性的要求是具备联邦控制或者监督,而案中的国家红十字会既未受到联邦的任何资金支持,也没有来自政府官员对于其日常事务的监督,政府控制的程度非常低,因而不构成《信息自由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后续还有大量的案件适用了“监管关系”标准,并形成了一系列同类判决。
“监管关系”标准的核心是行政机关对于待判断主体的实质监管。Forsham案〔57〕 445 U.S. 169 (1980). 中,争议焦点之一是大学群体糖尿病项目小组是否构成《信息自由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伦奎斯特执笔了案件的判决书,其从三个角度展开审查:从立法原意来看,“国会议员指出他们确实‘不想将虽然接受一定资助,但既没有联邦特许也未受到联邦控制的公司纳入进来’”,而本案中的大学群体糖尿病项目小组即属此类;从监管要素来看,“联邦的资助通常不产生与受助人之间的合伙或者合资关系。如果缺少了广泛的、具体的和日常的监管,其也不会将受资助者的私人行为转化成政府行为”,因而大学群体糖尿病项目小组不是行政机关;从尊重自治权的角度考察,一旦将其认定为行政机关,将严重背离尊重受资助者及其自治权的国会初衷。由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将实质监管作为认定行政机关的标准,这可以归纳为“监管关系”标准,其对后续同类案件的判决发挥了判例法的作用,时至今日仍是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时最为常用的认定标准。〔58〕 See Nicole B. Casarez, “Furthering the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in Privatized Federal Corrections: The Need for Access to Private Prison Records” 28 U. Mich. J. L. Reform 268 (1994-1995).
制备氧化铋的物料取自铅冶炼系统中贵金属工序的铋渣,铋渣成分为铋46.56%、铅13.16%、铜18.12%、银1.202 7%,经过磨细后,按照5∶1的液固比,加入浓硫酸和氯化钠[9-13],实现铋的浸出。在铋浸出的同时,铜也随着铋浸出,而铅和银则以硫酸铅和硫酸银的形式沉入渣中,实现铋、铜与铅、银的分离。铋的浸出液含铜较高,根据铋和铜沉淀的pH不同,调节溶液的pH,使铋优先沉淀,而铜继续在溶液中,实现铜与铋的分离。得到的沉淀铋进行水洗、碱洗等富集后,得到较纯的氧化铋,其Bi含量为81.52%,可直接用来除氯。
四、认定标准的功能及变迁
(一)认定标准的客观功能
在控权论的视角下观察,“行政职能”标准指向对于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特别是对难以识别的政府职能及其行使主体有了一个明确的、要件化的标准,因而对权力的控制能够起到直接的限制和规范作用。反过来讲,相较于将待判断的组织“一揽子”式地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做法,“行政职能”标准的出现实质上为私主体接受司法审查设置了较为明确的界限。这既有效控制了权力下放后造成的外溢现象,又划定了司法审查的法定范围。另外,通过司法审查的有序介入和不断发动,司法作为三权分立中对于行政分支的监督部门,也更好地、更多地发挥了自身的功能,提升了自身作为空间的同时还确立了司法审查的空间,为“规制国”下权力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监督路径,并免遭“司法审查走得过远”的诟病。
相较于“行政职能”标准,“监管关系”标准对应的法律定义更为宽泛,并体现出明显的积极功能:一则从关系的角度统一了法律适用。“监管关系”标准对于行政机关的认定并未从作为结果呈现出来的行政权力着手,而是力图考察联邦政府与待判断的组织之间的监管关系。因此,“行政职能”标准着眼于待判断的组织本身的做法,在“监管关系”标准中转变为从关系的角度考察行政机关的存否。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受资助人是否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难题,统一了法律适用,另一方面则构建了行政机关认定的新标准,在对待判断的组织进行审查时确立了类似“外部”视角的方法,更具解释力和适用性。二则既保障又规范了行政活动的开展。Forsham案〔60〕 445 U.S. 169, 100 S. Ct. 977, 63 L. Ed. 2d 293, 5 Media L. Rep. (BNA) 2473 (1980). 中,法院通过“监管关系”标准的适用得出结论认为大学糖尿病研究项目小组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这客观上为行政机关通过资助、外包等方式将公共任务交由私主体承担提供了保障。三则为“政府信息”概念的澄清提供了助力。当行政机关可以较为清晰地予以认定后,才能开展对于政府信息是否存在的进一步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关系”标准为行政法上政府信息概念的明确提供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认定标准的结构性变迁
认定结构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对组织属性的审查衍变为对事务属性的审查。“行政职能”标准中,国会和法院都将待判断的组织视为审查的核心对象,并对其是否具备行政职权作为审查的重点,这可以概括为围绕组织属性展开的审查。后续,随着私主体越来越多地承担相当领域内的公共事务,单单审查组织本身显得不再自足。“监管关系”标准,将对组织的审查置于关系的视野中,并将其与典型行政机关的实质关系作为审查对象,这相较于单纯以组织为审查对象的做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组织不管作出何种行为,只要其在行为过程中受到行政机关的实质影响,也即该事务属于行政机关实质参与、实质监督的事务,该组织即构成行政机关。相应地该事务也即是公共事务。因此,在认定结构的角度上,行政机关认定的标准出现了从审查组织属性到审查事务属性的变化,并可以从“国家—社会”关系、“公法—私法”关系边界变动的事实中得到启示。
第二,建筑类专业英语课程的设置需要以就业为前提,不仅要为学生传授理论知识,还要不断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需要多与建筑企业沟通,了解企业需要的哪方面的人才,及时调整教学计划与教学内容。
《行政程序法》第3条中虽然规定了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但同时对申请人资格作出严格规定,申请人还经常会遭遇行政机关以“正当理由”等为由不予公开的情形,〔27〕 5 U.S.C. §552(d), 1946. 这一方面赋予了行政机关对于是否公开过大的裁量权,〔28〕 See William F. Fox, Understanding Administrative Law , Lexis Publishing, 2000, p. 365.另一方面也使得第3条实质上成为行政机关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重要依据。〔29〕 See Theodore Sky, “Agen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 Admin. L. Rev . 445 (1967-1968).
其二,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问题。在文义上,公法一般涉及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以及公务员与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而私法则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总称。〔64〕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The State of Madison’s Vision of the State: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107 Harv. L. Rev . 1328(1994).在公法和私法的意义上,观察社会事务成为国家事务的过程可以发现,原本由私法调整的内容很可能会转变为公法的覆盖范围。在美国,这一界限是模糊的,因为一方面,公法所使用的行政机关,连联邦政府也无法确定其数量和具体的名称,〔65〕 See Mary Whisner, “Some Guidance about Federal Agencies and Guidance” 19 Law Library Journal 385(2013).另一方面,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使得这一工作的难度非常之大。〔66〕 See C.Sampford, “Law, Institutions and the Public/Private Devide” 20 Federal Law Review 185(1991).公私界限模糊的事实会让审查组织属性的方案变得困难和无法推进,而对事务属性的审查则可以化繁为简,另辟蹊径地解决这一难题。
认定结构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单方的命令—控制关系衍变为参与式的合作治理关系。“行政职能”标准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行政权的外溢,保障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这是从管理者与被管理人的角度展开的认定。与此不同,“监管关系”标准存在的前提是私主体业已承担了相当程度的公共事务,其要保障参与其中的私主体可以在合法性基础上实现公共物品供应质量和效率上的双赢。更进一步讲,该变化牵扯到行政法的作用范围问题,与第一个变化中所提及的“国家—社会”的融合、“公法—私法”的混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67〕 参见 [新西]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一般而言,行政法的范围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及其合法性判断规则的构建,当然也包括对于行政过程及其结果良好性的追求以及所提供的规制行为,但对何为公权力以及公权力的行使,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行使主体性质十分模糊的情况下,能否运用宪法要求、程序要求来对该主体进行规制,尚缺少较为明确的一般标准。因此,参与式的合作治理关系下的认定方案将私主体作为外部的合作者,既能实现行政权受到规制,又能最大程度上追求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行政资源的节约,这是合作治理产生的基础和优势所在。
“管理芒果,我们人人都是讲究的‘技术挂’!”农场生产部负责人如是说。据他介绍,芒果从结果到果实成熟虽然仅几个月,却要耗费果农们的诸多智慧和精力。
五、对中国的启示
整理、归纳美国联邦层面上行政机关的认定及其结构变迁,最终的目的是为中国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智识。根据我国两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认定问题的典型体现是行政诉讼中适格被告的确认。因此,与美国法上采取实体认定方法对行政机关展开认定不同,我国采取的大致是程序认定的方法。就行政机关的认定而言,新《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与旧《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的规定相差甚少。因此,二者在实施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是相仿的,都可能在被告的确定、被告的范围方面存在难题,并与已有的其他规范内容和诉讼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首先,现行法规范下,被告的确定可能会因为规定自身的复杂、社会组织的多元治理等现象而出现难题。有学者认为,现行法定的被告确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第一,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被告问题。第二,多阶段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被告问题……〔68〕 参见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为此,有意见认为行政诉讼法对于被告资格的规定过于复杂,建议简化被告确定规则,不妨实行一级政府原则,由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属的政府为被告。〔69〕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翻看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除了第一款本身存在着行政机关如何认定的问题之外,其余五款分别针对经复议的案件、共同行政行为、行政委托行为、行政机关变更等特殊情况做出了细致规定,总体上形成了“1+5”的规范体系。然而,过于缜密的另一面是烦琐,这样的规定无疑会加重当事人、法院的认知难度和操作负担。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历经11个省,红军每到一处,我们党不仅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民族政策,更重要的是还培育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这些民族干部在长征期间,为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部门,都认识到了当前被告范围受制于行政主体的概念而存在过于狭窄的问题。〔70〕 参见周伟:《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之反思》,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具体来看,第一类意见从行政权的角度入手,有的认为类似高等学校、村民委员会行业协会等一些公务法人和组织被赋予了部分行政职能,应允许其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71〕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这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已经得到确认。〔7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24条。 有的认为应当将所有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统统纳入行政主体的范畴。〔73〕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第二类意见从管理关系的角度入手,有的认为应当将那些具有纵向管理关系的组织明确规定为可以成为被告的组织,比如村委会、业主委员会等。〔74〕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5、84页。 更为详细的意见认为,一些社会团体、自治组织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其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产生了实质影响,因而应当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75〕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51页。
最后,已有的其他法规范已经为行政主体以外的组织成为被告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对行政诉讼法上的规定提出了挑战。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法院也开始为非政府组织成为适格被告打开通道,这从实践的角度为法规范的规定提供了有力反馈。在信息公开诉讼中,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承担主体,虽然在具体操作时与前三十六条的行政机关、授权组织有差异,〔76〕 参见朱芒:《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如何信息公开》,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制定过程中也因双方意见争执不下而放弃做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案件参照本规定”的规定,〔77〕 参见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但是在后续的行政争议中公共企事业单位被证明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与王聚才不履行信息公开答复职责纠纷上诉案”〔78〕 参见(2011)南行终字第78号行政判决书。 和“张某不服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案”〔7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主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9页。 可以为此提供判例支撑,而学者关于从行政任务角度对行政机关进行认定的论述〔80〕 参见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则提供了充足的学理支持。除此以外,高等学校在行政诉讼中出现了向适格被告转化的现象。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成为司法审查无法介入的场合,但是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 以来,后续出现了很多的同类或者类似案件,以至于当前对于高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被告的观点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2)不同类型的短路故障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三相电压暂降。三相对称短路故障会造成各相电压暂降同时开始,并且每相暂降幅值相等;其他类型的短路故障造成的电压暂降有时还伴随有电压暂升现象,并且三相幅值不相等。
所以,就现行的法律规定而言,还存在着被告认定困难、被告范围过窄以及规范与实践相冲突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出规范本身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应该进一步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进一步展开分析,力求真实、准确地展现出行政机关认定的中国面貌。
就中美两国而言,相似的是经济上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组织承担行政任务的问题,有的学者称之为“行政权的社会化”问题。〔82〕 参见胡晓玲:《行政权社会化的边界界定理论探析》,载《行政与法》2015年第1期。 举例而言,新近出现的福利提供、专业咨询、拍违有奖等活动即属于明显的事例,就连传统上只能由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如消防活动、警察治安、道路工程等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可以发现社会组织的身影。可以这么讲,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历史上的问题具有同质性。因此,对于解决中国同类问题而言,应通过对行政机关认定的比较法研究,在充分关照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架构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基础上,探索在政策层面和规范层面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在解决行政诉讼被告争议的同时,以美国经验为起点充分考量我国行政法整体制度的改进。在政策视角中,行政机关认定问题的解决涉及公权、私权的划分及相应义务的承担或者排除,体现出国家对于公民财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保障力度,也体现出政策的朝向和初衷。在规范的完善上,司法对于行政的监督及其边界可以在行政机关认定的过程中得到呈现,这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被告范畴,对于我国同类问题的解决具有立法借鉴的作用,也有法解释上的帮助。最后,行政机关认定的原理在我国的既有实践中不同程度地也得到了验证,反映出国家层面对于权力边界、效率—公平等价值的重视,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法上同样关切的问题。
另外,应当注意的是,除了国体、政体等国家架构和社会构成有很大的区别之外,美国法上的内容与中国本土的实践也有一些相异之处:美国法上的认定标准源于法院确定公法义务承担主体的需要,属于从实体法上将待判断的组织纳入或者排除出行政机关的范畴开展的工作。然而,我国的做法是以法院确定行政诉讼中被告为基础,力求在立案阶段就将行政机关的成立与否进行一次判断,因而更多地属于从程序角度展开的认定。因此,中美两国在行政机关认定问题上的经验互通,还需要从更为周全的角度、更为充分的考虑出发,方能制订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尽可能避免出现“水土不服”和强硬嫁接等负面效果。
* 王军,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政府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限制研究”、2016年度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研究”(项目号CLS(2016)D30)及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瀚英”科研基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