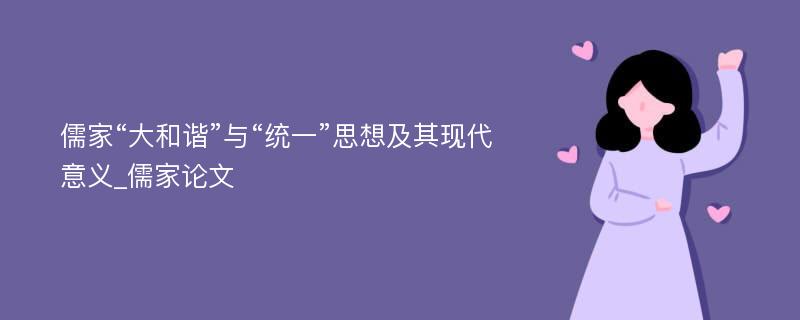
儒家“大同”与“一统”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05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4310(2000)06-0060-04
“大同”思想和“一统”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属社会观,侧重于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后者属政治观,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主张以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设计,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支撑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思想资源。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时候,反观儒学的大同思想和一统观念,寻绎其与现代社会生活和未来发展之间的结合点,是颇有意义的。
一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在先秦古藉中,“大同”一词虽时有所见,如《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庄子·在宥》:“大同乎涬溟”,“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列子·黄帝》:“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等等,似所指乃“同一”“同化”之义。据考,产生元前611年以前的《诗经·硕鼠》中所咏之“适彼乐土”、“适彼乐国”,则可能是迄今留存的关于“大同”理想的最早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在这样一个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多种多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其中,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最具代表性。
农家“并耕而食”理想的产生,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的民族有关。我国农业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初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中国数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小农经济,绝大多数思想家在构想理想社会时关于劳动的形式,都确定为农耕,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提出君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1]“这里并耕不是只做一个仪式,而是要君主亲自扶犁下田劳动,参与生产的全过程,其他人都得参加农业劳动。“饔飧而治”则更具体:“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自当炊以为食,而兼治民事也。”[2]即指从种庄稼到烧成熟食的一切劳动。
既言“并耕”,君民则处于平等地位,自然没有剥削,也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而在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中,按等价原则,自然也不存在商业欺诈。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则认为统治者的压榨与剥削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公,人类文明又带来了种种罪恶,因此必须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工艺技巧,还要无为、无事、无欲,连货币交换也不要。老子的理想众所周知: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
老子所言小国实际上几近邻村,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互相隔绝,从事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不用工具,废弃文字,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损有余而补不足”[4],均贫富求平等。人人以此为满足而不求上进。这种“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此外,道家庄子的理想世界也是一个大公的世界。这个社会“不拘一世之利为己私分”,“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人们“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富贵。”[5]不过庄子的齐物论把寿天,穷通都等同起来,他当然不会把财富放在眼里。
比起农家和道家,儒家的“大同”理想要详尽、完整,也更美好和更具诱人的力量。《礼记·礼运篇》对其作了典型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种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丽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间。
《礼记·礼运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虽曰托名但不是毫无根据的。孔子面对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世界,天下无道使他痛心疾首。他“发愤忘食”,“席不暇暖”,不惜离家别国,周游列国13年,处处碰壁仍不改初衷,有人说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他一心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境界。因为,对理想的追求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他主张“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歌颂尧能效法天的善施无私,歌颂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这都反映了孔子“公天下”的思想。所以,匡亚明认为,“可以确定《礼运篇》所载‘大同’、‘小康’思想,是可以反映孔子的真实思想的”。[6]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概括出“大同”社会的特点:第一,天下为公,这是大同思想的核心。首先是财富共有,“货”不“藏于己”,即不私人占有,无所谓贫富,而且人人爱惜公共财物,“恶其弃于地”,反对浪费;其次,由公众选举愿意忠诚服务的贤能之人来负责管理这个社会。第二,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力,恶其不出乎身”,但出力完全是为公,劳动不是个人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社会风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社会分工,做到“男有女,女有归”,人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各得其所。第三,互助博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一家。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和培养,由社会共用承担,即便是鳏寡、孤独、废疾者,也“皆有所养”,人与人乃至国与国坦诚相待,讲信修睦,“谋闭不兴”,全社会和谐而安定,“盗窃乱贼不作”,“外户不闭”。
总之,孔子寄希望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的政治纲领;选贤任能的组织路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分配原则;讲信修睦,老安少怀的道德规范。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既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向往,反映了孔子远见卓识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
然而“大同”思想毕竟是超越现实的高远理想,它既是对已逝的美好时光的回忆,也是对未来世界的梦想,人们惯常把它与西方的“乌托邦”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其实,儒家的大同学说与西方各种仅仅驰骋于空想境界的乌托邦式的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礼运篇》在这段话的前面载有孔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的话,就是说,除了这大道之行的大同世界他本人没有亲历,即便是被他一再称赞的“三代之英”(夏、商、周)他也没有经历过,只不过他将大同视为最高理想,有志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努力。所以紧接着这一段,他又提出了相对于大同世界的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以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有人说这是两个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的社会,一个是理想社会,一个是现实社会。而理想社会可能在远古社会的低层次上曾经有过,同时,它又是未来社会的高层次上应当有的。就社会性质社会关系而言。现实的“小康”是远不如“大同”的一个倒退的非理想的社会。[7]此言极是,但能否也认为这是孔子面对现实,提出的近期目标。而《礼记》通篇论述礼的起源以及礼对治国治世的意义,实际上谈的都是小康之治。儒家的小康目标更具引人入胜的力量。用今天的眼光看,小康乃是通向大同的必由之路,或者说小康乃是孔子退而求其次的更切实际的努力。这便是儒家大同与西方乌托邦的分野。
《礼运篇》是先秦诸子社会思想的汇合和总结,是古代社会理想的集大成者。其实,孔子对“大同”思想曾多所论列,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等。即是孟子论“王道”那段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何尝不也是小农社会里的一种美好境界!
如果说“大同”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古代儒家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那么,小康便是私有制产生后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阶级社会的“盛世”,这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力促其实现的现实目标。
儒家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影响深远。宋以后“小康”社会往往是一些思想家和变法者向往的蓝图或奋斗的目标。而“大同”世界则吸引和鼓舞着一些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和叛逆者,如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孔中山等人都受其影响。
二
中国古代的一统观念出现颇早。据古籍载,自五帝以来声教法化就已经远及于天下四海之广。《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书·益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这是以一统的眼光来描述舜禹时代,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尽为臣仆,因而使声教德化远播四极。周武王灭商后东征,结束了商朝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把统治疆土从黄河中游扩大到黄河下游,建立了广大的统一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医”(《诗·北山》)这是对一统思想的最初表述。由于周朝实行的是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的分封制度,诸侯政治经济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社会发展弊端渐露,使周朝一统的疆土最终瓦解为一百多个诸侯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打破了原有的统一,各国为了争霸中原,纷纷改革政治建制,变贵族世袭制为官僚制,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权力真正集中在国君手中,形成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集权国家的形成,为统一中国作了准备。
与纷争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思想理论界十分活跃,诸子百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如何统一作了理论探讨。儒家方面,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仁者“爱人”[8]的原则,主张通过周礼和仁消除纷争各方的矛盾,实现一统。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但他所处的时代周礼已彻底催毁,君主制已基本确立,因此他不主张复礼,面是主张君主施仁政,以礼治国。《孟子·梁惠王》谓天下“定于一”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所以孟子所谓“一天下”仍然是那种以仁义德教致使四海一家的模式。而荀子则多处论及“一天下”及“天下为一”。《王制》曰:“尧舜者一天下也;”《正论》:“古者天子千官……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讲的都是分封制下的王天下。他承继了老子万物统一于一和宋尹学派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确立了他的“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的社会观,王道与霸道并用。韩非则接受荀子的法治思想而排斥礼治,主张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方法,来维护中央专制集权。产生于战国的公羊学说集孟、荀两家学说而有所发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在注释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子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以注经的方式,第一次明确提出“大一统”概念。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从思想体系上看,一统思想也是《公羊传》政治理论的一个主题。在《公羊传》看来,天下有王,乃是一统局面的理想形式;天下无王,也要依靠现实权威维系起一统的秩序,使一统局面在变通的形式中得到实现。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被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公羊传》往往以“实与而文不与”的委婉形式,对诸侯的一些僭越行为表示宽容,其背后的原因,便是对一统局面的深切追求,王道既不可得则退而求其霸道,表现出违经求权的不得已。《公羊传》主张的是周王控制下的大一统局面,“王者欲一乎天下”“欲天下一乎周也。”但在天下无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依靠现实的诸侯霸主来维系起一统的等级秩序,清楚地表明了对大一统追求的深切之情。
《公羊传》所极力推崇的大一统观念,很快在秦汉时代思想家的言论和著述中有所反映。如李斯初见秦王时就曾说“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9]秦统一中国后以暴政治天下,仅十九年就被推翻了,人民希望统一,但绝不希望建立在暴政上的统一。《公羊传》的一统说,通过汉初儒学而得到继承和发扬,秦汉之际各种思潮、学说、流派,在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中产生和发展,并在长期相互抵制、颉颃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儒家日益融合道、法、阴阳三家占据主干地位。《吕氏春秋》自觉地企图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之也。一则治,两则乱。”这是明白地要求结束先秦百家群议,取得思想的统一。而董仲舒不仅在其著述中多处使用一统的概念,而且还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论证了中国实现大一统的问题。首先,他认为,要加强皇权,继续推行“强干弱枝、削除诸侯”的政策,要“一统乎天子”[10];而天子作为根本,也要善于理解天意,树立正的风气,为天下作表率。这里在强调皇权的同时,也强调了天子榜样在大一统中的作用,这比秦王朝是一个进步。其次,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更化”,革除秦时的弊政,以达到礼乐文明的世界。再次,他认为,人间的德刑,是上天阴阳的体现。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而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在他看来,德就是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这样的德。最后,他强调不能“师异道,人异论”,[11]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统一思想来实现统一政治。董仲舒的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反对诸侯分裂,要求领土完整、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当然,这些思想以唯心的天人感应理论为立论基础,是不足取的,但是它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对促进中国统一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儒家大一统思想正是经过董仲舒的论证而大大丰富,并以较为完善的理论形态出现,这标志着儒家大一统思想经过千年理论和实践的反复酝酿而最终形成。
一统思想涉及到各个方面,不仅疆土或政治的一统、思想的一统,更有文化的一统。中国文化其所以能顽强地生存发展并绵延至今。究其原因,最显著者便在于它的统一性。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华夏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统一,这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固然,这是由多种因素和条件构成的,诸如政治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共同的文字等等,但其中十分重要的则是对儒家一统思想的提倡。从中国古代的帝王、贤哲到下层百姓,都有了强烈的统一愿望。当然,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不同,要求统一的动机也就不同。一般讲来,中下层人士要求统一,是基于对战乱、分裂、割据所造成的生活流离、痛苦的恐惧,因此只要保持社会的统一,保持生活的安定,宁可社会停滞不前也在所不惜。中国人为社会的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也从社会的统一中得到不少利益。
当历史上的某一个王朝崩溃以后,出现暂时的分裂局面。地方割据势力各据一方,但没有一个霸主真正愿意划一方之地以保偏安,都毫无例外地极欲兼并其它对手,以成天下之王。其动机姑且不论,从效果上说,无不对中国的统一造成一种动力。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统一的时间远比分裂的时间长。
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有理想主义的大一统思想,儒家的“大同”更是儒者汲汲追求的远大目标。荀子说:“大儒者,善调天下者也。”这是儒家典型的主张。荀子不仅主张政治和社会的统一,而且主张“一制度”“风俗以一”“隆礼而一”“乐者审一”等等,即主张制度、礼仪、道法、风俗以及艺术、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统一的局面。
这种统一性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在各种文明的比照中往往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文化象征。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名称,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内在的精神。[12]
上文粗略地论及儒家的“大同”与“一统”思想,那么,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其现代意义何在呢?
大同,是一种和谐有序,温情脉脉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一统思想则是一种政治观,以往的实践又与专制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大一统是着眼于承认某种权威,并对这种权威绝对支配体系的向往和美化,所以“大一统”是统治者的社会理想,“大一统”愈“大”,愈“一”,对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呼唤和依赖则愈强烈;而大同呢,那是与“一统”无关的人文理想,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大同走向大一统,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大一统的优越表现了对时空的超越,给中国文化的升华提供充分“自酿”的机会,毕竟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13]
其实,“大同”与“一统”且不说字义上相近。从关系上讲儒家“一统”是“大同”的前提,而“一统”又是以“大同”为旨归的。所以康有为作《大同书》则干脆将“大同”代“大一统”,他把政治上的一统阐释为社会性质的变革。从《礼运篇》到《大同书》,大同理想可以说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宣告了这一古典思想的终结。
社会的进步,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一旦“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实现了大一统,则世界就有可能进入大同。汉文景之治,唐贞观、开元之治,清乾隆之治,可算盛世、治世,自然无法等同于大同,在何休等人眼里只不过是“升平世”够不上“太平世”。但相较于历史上那些衰世、乱世,则无疑它们与大同社会要接近了许多。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何谈作成大同梦?
换言之,大同社会出现首先要靠大一统的实现。退一步,如果说大同是一个永难企及的憧憬,那么局部的大同景象也得凭依统一来保障。当年孔子就有统一天下的雄心: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5]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心目中,不仅没有鲁君的地位,连周天子也被置诸脑后,他要当仁不让,亲自在东方建立周朝那样的事业。对此,《史记》也有印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昔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尝庶几乎!”[16]简直要效法文武,重创天下了。
孔子一生空有壮志,含辛茹苦,周游列国,终于未被重用,无从实现其理想,这当然主要由于缺乏社会条件,当时任何国家都无力完成统一大业。而孔子的伟大理想在当时的任何诸侯国都是难以容纳得下的。
把大同与一统放在一起考察,还基于以下考虑:儒家的大同思想讲人与人之间和睦,不为私不为己,同时又各得其所,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种思想是道德化的,是认同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因而充满人文主义精神。而儒家的“一统”也并不等同于韩非思想以及秦始皇的专制操作,而是把儒家的仁义思想包容进来以及含有某种多样性的高度和谐的统一。有了这个人文根基和共同理念,坚持和追求一个合乎人性化的、合乎儒家礼仪的社会理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转换性的创造,来迎合时代变迁的需要,使之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动力。
在人类文化走向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果要避免全球化的文化冲突,避免战争,就必须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旋律,追求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儒家的“大同”的思想启发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不仅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还要克服狭隘的民族观念,为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共同创造理想的明天,描绘人类新的“大同”蓝图。
跨入21世纪,祖国统一被提到了迫在眉睫的议事日程上。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曲折发展,但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却从未受到多大影响。大同和一统的思想在炎黄子孙中是根深蒂固的。重温和进一步阐发其内涵,使其成为海峡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是有很现实的意义的。海峡两岸同宗同源,任何违背祖国统一的思想和两岸人民意愿的言行都是非常可悲的。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大一统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
收稿日期:2000-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