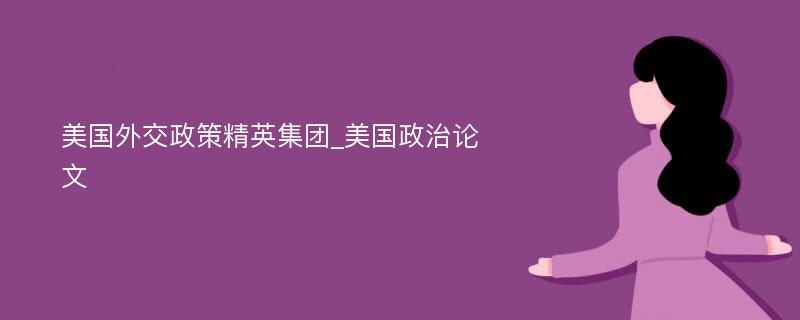
美国对外政策精英集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精英论文,政策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对外政策精英集团由政府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部分组成,在政府、公司和思想库三类组织中行使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这三类精英群体共同制定和确立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对外政策最终决策者的政府精英,由于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安全和外交经历,日益形成了排他性的圈子。美国大公司或者跨国公司在国内具有深厚的组织基础和权力资源,在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的公司间具有私人权威,成为对外政策的推手,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美国的对外政策。知识精英不仅在思想库作为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影响着日后的决策进程,而且随着思想库与政党、政界背景联系的日趋强化,政策的执行权也实质性地落入了知识精英的手中。思想库作为对外政策精英权力链的重要一环,通过形成对外政策观念,储备和输送对外政策精英,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一、政府精英
对外政策作为国家的对外行为,首先是由政府精英制定的。就美国政府而言,白宫和行政机构的外交政策精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代表着美国,制定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精英定义为行政当局的外交政策精英,并不是否认国会参众议员的角色和地位。美国宪法规定了政府间权力的分享与制衡,就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来讲,行政执行机构——总统和国家安全团队与对外政策团队是对外政策的领导者和制定者;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和代议机构,是国内党派政治、地方政治、各种政治团体、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舞台的角力场,作为美国国内社会与对外政策精英之间的“传送带”,将国内各种政治利益和观念的诉求贯彻到对外政策中。
美国对外精英集团的兴起,源于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案的立法。该法为当代美国对外政策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相继建立,与国务院一起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主要机构。当然,由于美国联邦行政机构庞大,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等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对外政策进程。随着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界限的逐渐模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低级政策与高级政策难以截然分开,将会有更多行政部门卷入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更多行政部门在与传统对外政策机构分权的同时,也加强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总统越来越依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其工作班子管理以白宫为中心的对外政策程序。外交政策精英的权力不仅来源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法定组织的制度授权,也因为精英之间紧凑的“社会学”关系而传承——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安全、外交工作仕途,使精英之间门徒相传,衣钵相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我永存”的外交政策精英圈。
(一)相似的教育背景。从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教育背景看,他们大多出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宾夕法尼亚、乔治城等大学,以及海军学院、西点军校等军事、外交专业的“常青藤”院校。同校、同级、同门、共同的大学社团等各种共同关系使得精英们在投身政策规划之前就相互熟识,也为未来相互政治支援埋下了伏笔。乔治·邦迪、哈里曼和洛维特同是耶鲁骷髅会的成员;艾奇逊和哈里曼同是耶鲁划船队队员;拉姆斯菲尔德和卡路西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室友与摔跤队友,卡路西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引路人,两人都走向了国防部长高位。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哈佛前后届(第52、53届博士)同窗,师出同门,同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姆·伊里亚特的门生。伊里亚特曾是罗斯福智囊团成员、战时生产部副主任,冷战期间历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肯尼迪、约翰逊等六位总统的外交和安全顾问。随后,布热津斯基也将哈佛大学的同事亨廷顿招募,出任卡特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计划处主任要职。
(二)共同的外交安全经历。放眼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政府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这些精英很早就供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等部门,有的还在不同的部门得到历练,具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如盖茨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中情局长和国防部长的职务。这一现象在内阁次职级精英中也同样存在,如执笔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的尼采,先后在国务院(杜鲁门时期,政策规划处主任)、海军部(肯尼迪时期,部长)和国防部(约翰逊时期,副部长)任过职;沃尔福威茨先后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卡特时期)、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里根时期)、国防次长(老布什时期)和国防部副部长(小布什时期)等等。
(三)四个关键人物。二战期间担当陆军部长的史汀生和担任海军部长的弗雷斯特是战后美国外交精英集团的奠基人。史汀生在担任罗斯福政府陆军部长期间,将同是耶鲁骷髅会成员的洛维特、哈维·邦迪(乔治·邦迪的父亲)以及哈佛的罗伯特·帕特森、麦克罗伊招致麾下,充当其顾问和助理。弗雷斯特则招募了以前在迪龙里德公司的同事尼采和德雷普,他也是凯南的政治“施主”。凯南署名X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即是应弗雷斯特的要求而作,也正是在弗雷斯特的推动下,马歇尔启用了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处的主任要职。①史汀生和弗雷斯特所招募的对外政策精英,与罗斯福战时内阁的同事艾奇逊、杜勒斯等成为美国冷战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设计者。这些精英的助手和门徒,诸如腊斯克、罗斯托、乔治·邦迪则延续了上一代所设计的冷战框架。②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新一代专业精英人士的导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招募的国家安全工作班子打造了一个对共和党、民主党政府都具有持续影响的豪华阵容。其在尼克松和福特任内的助手包括黑格、伊戈尔伯格、斯考克罗夫特、麦克法兰、内格罗蓬特、罗德曼、里克(后转投民主党)、霍尔布鲁克、洛德等,后来都在国家安全、外交等部门高就。在基辛格出任福特时期国务卿时,斯考克罗夫特“继承了”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位,期间招募了奥尔布赖特父亲的学生赖斯和哈德利。到赖斯担任小布什竞选顾问时,斯考克罗夫特对她的职业生涯已经指导了10余年。③布热津斯基是奥尔布赖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顾问,其在卡特任内将奥尔布赖特招募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奥尔布赖特则是赖斯长期的导师和朋友。赖斯先是在国安会供职,奥尔布赖特任国务卿时力主克林顿将这位被认为“主张社会同化的黑人精英分子”任命为助理国务卿,④奥巴马上任后则任命其为奥尔布赖特曾经担任过的职务——驻联合国大使。
(四)总统是外交政策的领导和核心。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其国内政治背景,总统作为外交政策的领导者,是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结果,也是美国内治理哲学的集中体现,其个人性格、观念、领导方式无疑影响着外交政策精英。在任何一个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总统作为首要人物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判断在整个决策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⑤但作为美国总统身边的外交政策顾问和圈内人,政策制定者也强烈影响着总统,这种影响早在为总统充当竞选顾问时就业已存在,总统与其对外政策班子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双向说服的关系。
冷战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基本上呈交替执政局面,选举政治使得外交政策精英随着总统和内阁的更替而暂时离开,但他们始终没有淡出对外政策圈。“一朝天子一朝臣”,下一次的政党更迭使得前任总统的“门生故吏”再次浮出台面。小布什任用了其父亲的老班底,宣称变革的奥巴马启用了至少同样多的克林顿的旧臣。赖斯、鲍威尔、盖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佐利克不仅服务于老布什,也在里根,甚至尼克松、福特内阁从事外交和安全工作。琼斯、希拉里、苏珊·赖斯、詹姆斯·史坦伯格、汤姆·多尼伦也都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从事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奥巴马的新东亚政策团队核心——贝德、坎贝尔、米德伟——几乎是克林顿时期的翻版。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交替执政期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对外政策权势小集体,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
二、公司精英
“对通用公司有好处就是对国家有好处”,二战期间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主任、被认为是战后促成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关键人物、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朋友、通用公司总裁、后来出任国防部长的威尔逊的这番话让当时的美国人全都“震惊了”,而今天,这种表述就会被认为很恰当。⑥《新闻周刊》的调查表明,70%—75%的美国人认为公司在美国拥有太多的权力。⑦从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对外政策过程两方面考察,公司精英在塑造美国对外关系过程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一)对外关系史主题下的美国公司的地位。
1、殖民地时代和建国初期。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各州政府,脱胎于建立殖民地的商业公司的体制。弗吉尼亚最初没有独立的政府,一切决断来自伦敦公司总部,马萨诸塞初期的政府则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体制完全一样。⑧美国独立之初,聚集在费城制宪会议的13个州的代表就认为:“对外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关系。”⑨立国之初,联邦政府的制度和各种政策大多倾向于保护商业精英集团的利益。汉密尔顿作为联邦主义经济计划的缔造者,将商业精英集团作为新兴美国社会的核心,同时建立了私有公管的国家银行,将国家金融机构、金融集团和联邦政府连接在一起。⑩
2、公司资本主义的崛起与门户开放。美国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殖民地和建国初期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两个阶段后,于19世纪末进入了公司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基于充斥美国社会的公司和类似的高度组织化团体的公司制度。随着公司资本主义的崛起,大公司和公司精英主导了美国的历史。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将保护贸易、控制国外市场的动机、来自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和国外列强威胁策略的压力提炼、合成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是“门罗主义的工业化”,“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与工业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成为美国1900年到1958年的对外关系史”。(11)
3、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美国跨国公司的历史远在20世纪初就获得显著发展,到二战以后上升为国际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主要因素,(12)在建立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垄断石油供给、注资军事外交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元的国际地位和核武器的优势一并成为战后美国霸权的互为紧密联系的三根支柱。(13)
4、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冷战结束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由美国以其遥遥领先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主导。克林顿作为冷战后美国首任总统,为弥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经济上的弱点,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这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既是美国冷战后对经济全球化的关切,也是跨国公司权力伸张的一个脚注。全球化使财富向大公司进一步聚集,反过来也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精英的权力。
(二)公司推动对外政策制定的三个平台和两种权力。跨国公司不仅在美国国内政治平台上拥有深厚的权力资源,而且在全球影响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在全球公司之间的“司际”(inter—firm)平台上也拥有私有权威。跨国公司正是在这三个平台上,通过这两种权力影响对外政策,甚至将自身的经济利益定义、上升为“国家利益”,推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进而将其利益全球化。
一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平台,公司精英不仅通过旋转门机制在政府出阁入相,也通过“互联董事会”在公司之间形成“股份公司群体”,(14)而且与大学、思想库等社会精英组织间保持紧密的联系。正是通过其国内广泛的组织网络,大公司渗透到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深厚的国内权力资源。对1933-1965年234名外交决策精英人员的背景研究显示,大商业公司、投资公司和律师(通常是有公司经验的律师)出身占据了59.6%,而布鲁金斯学会在对同时期五角大楼和三军负责人的调查表明,这一比例占到86%。(15)卡尔·多伊奇曾指出:“读一下1947年以来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许多副部长和助理部长的名单,仿佛就在点这类重要集团(银行、投资机构和私人工商业公司)的名。”(16)公司精英通过游说、竞选资金支持、政治任命、军事工业复合体、咨询委员会等各种渠道和形式影响国内政治精英。更为重要的是,公司不仅眼睛向上,也不仅仅只是专注于盈利这一企业的单一目标,而是通过兼职董事与其他大公司、大学、思想库、基金会等社会精英组织之间保持正式、非正式的紧密联系,从而拥有广泛的组织力量,在整个社会具有深厚的权力资源。这可以高盛公司为例来观察美国公司权力的国内基础。
冷战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盛公司充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旋转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在国际关系学界颇具影响。2008年底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财政救助计划将前高盛总裁、财政部长保尔森和他以前在高盛公司的属下、原高盛旧金山公司副总裁、负责金融稳定和国际经济与发展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卡什卡里推上政策前台。事实上,高盛相继推出了三任财政部长弗洛尔、鲁宾和保尔森以及佐利克、罗杰斯、博尔顿、弗里德曼、考等高官,也产生了不少参议员、州长、众议员。从高盛公司高管的背景和各种头衔来看,这些几乎清一色的哈佛大学同学,又是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芝加哥、康奈尔、布朗等“常青藤”大学的理事或顾问,商业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三边委员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在该学会现有的董事中,就有4名高盛前任和现任高管)、肯尼迪艺术中心等社会精英组织的理事或会员,同时又与通用、波音、杜邦、德州仪表、3M、花旗、塔吉特等大公司通过互联董事会保持紧密的联系。比如,高盛公司现任总裁贝兰克梵就是哈佛大学资深校务委员会委员、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监事、纽约市合作组织主席、印度商学院管理董事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原总裁鲁宾目前则是花旗银行董事长、对外关系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和哈佛大学的理事;原总裁、现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桑顿也是英特尔、福特、传媒巨头NEWS CORP公司的董事,高盛基金会、全美美中关系委员会、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理事,中国网通、中国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集众多经济、社会精英组织头衔于一身。众多高盛人结成了精英组织的庞大“互联网”,高盛公司的触角遍及美国肌体的方方面面,并且还延伸到中国、印度、欧洲等全球化社会精英组织中。现公司董事、办公室主任,曾任福特时期白宫办公厅研究人员、里根时期财政部长助理、老布什时期助理国务卿的约翰·罗杰斯曾坦言:“高盛公司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实际上提供了让每个人都广泛参与各种活动的平台,不管是商界的、学术的还是公共服务的。因此,毫不奇怪,高盛公司比其他任何我想到的组织都推出了更多的参与公共服务的人员。”(17)
二是在全球政治、社会平台承载着美国与东道国的关系。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触角深入到全球各地。例如,总部设在加州的惠普公司,拥有14.2万名员工,分布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消费者技术公司,也是欧洲、俄罗斯、中东、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18)众多富可敌国、惠普一样的美国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这一纽带,将美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种经济的联系必然蔓延、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东道国的内政,最终不可避免地传导、作用到两国间的关系。一方面,美国政府将促进海外的经济利益,保护跨国公司的投资利益作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商务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服务跨国公司的机构,影响东道国的经贸政策。另一方面,东道国也利用跨国公司在其境内的投资利益,通过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影响美国对其政策。
虽然跨国公司的利益首先主要是经济利益,但是源自跨国公司发生的美国与世界各地东道国之间的国家间关系绝不囿于经贸联系,而是经常外溢到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1954年,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就曾参与了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的行动。在全球化的当今,跨国公司更广泛地卷入了东道国与美国之间的环保、人权、民族、劳工等各种政治社会事务,承载着美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威亚尔达所指出:“大企业不需要影响美国政府,因为它本身就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19)
三是在国际公司间平台上具有私有权威。国家之间基于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存在着国际或者国家间关系,公司之间基于生存和发展也存在着“司际”关系。正像大国通过权力、联盟和国际机制调整国际政治关系一样,大公司也采用非正式的产业规则和惯例、卡特尔、生产联盟与分包、商业伙伴、机制等多种方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进行私有治理。虽然私有治理的历史和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长远,但是全球化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变革、市场的逐步扩大提高了私有公司相对于国家的权力。公司之间合作惯例化和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公司权威,使得跨国公司在塑造国际经济关系过程中不仅仅跨越国家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超越国家管辖的“跨国施动者”。
此外,通过对互联网规则和标准的制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标准机制、债券等级评定、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矿物质市场的管理等案例的研究表明,在国际经济领域广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权力的默许或退出,跨国公司行使着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的私有治理现象。(20)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杜邦、通用电气、通用汽车、IBM、惠普、强生、默克、辉瑞等12家美国跨国公司于1984年组成的知识产权委员会,动员其在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公司伙伴形成跨国联盟,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关税和贸易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到的最终目的。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本来在美国国内的执法都相对宽松,却于1994年通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知识产权法案,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保护。(21)
三、知识精英
美国的思想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栖息地,作为“君子儒”的储备,可谓学术与政治的桥梁,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关键组织平台,是华盛顿精英政治权力链的重要环节。作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体,美国思想库经过百年的发展,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美国思想库的缘起、发展和变化。研究思想库的学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发端看法不一,有的追溯到内战以后,或者更早。多数学者将20世纪初期至一战以后,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政府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等一批智库的相继建立,及其在塑造国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持久历史痕迹作为美国现代思想库之滥觞。(22)美国思想库强劲崛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选举行为的变化、大政府的出现促进了美国的政治转型,以政党、国会、总统铁三角为代表的老传统发生了巨大变化,观念(信息、数据、意识形态、专长、意象或者其他)日趋重要。因此候选人、蜂拥而至的新阶层专业雇员、媒体记者、利益集团、选民等各个群体都对思想库有新的巨大需求,催生了思想库的崛起,并使之成为今天美国政治的一个“固件”。(23)经过一个世纪演进,进入21世纪,美国思想库已约占世界思想库总数(接近5000家)的一半,形成了强大的政策产业。研究对外政策领域中诸如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对外政策关系委员会等重量级智库,其有四个显著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人员结构逐步专业化。随着20世纪70年代思想库的强势发展,思想库在人员专业构成上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像麦克罗伊、杜勒斯、麦克纳马拉、洛伊特等以银行家、律师、商人为骨干的东海岸权势集团大多被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为代表的政策专业人士所逐步取代。(24)
二是政治色彩、党派印记日趋浓郁。虽然一些思想库宣称是独立的、两党的,但是大多数思想库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党派倾向。越南战争损害了冷战后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思想库的崛起同时也是共和党对民主党在思想库领域对决的政治反应。共和党一直梦想拥有与布鲁金斯学会对垒的自己的智囊。在自由主义时代过后,保守主义竭力要给华盛顿提供它认为所缺少的观念——做大美国企业研究所、建立传统基金会,并将其作为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思想阵地。今天,从民主党的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共和党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策观念和人员政府背景来看,其在思想和组织上都具有明显的党派阵营色彩。
三是资金来源更多依靠大企业。研究需要资金,即便思想库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意识形态,也无法独立于金钱。美国思想库也是公司资本主义的法人组织,资金来源因思想库的性质而异,政府、家族基金会、公司基金会是主要的注资渠道。比较自由倾向的福特、洛克菲勒、梅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金投向了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保守倾向的皮尤、斯凯夫、布拉德利等基金会的资金则更多流向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近年来,美国思想库资金最大的来源,从政府和家族基金转移到大型私有企业和企业基金会,约占60%甚至70%。(25)
四是“全球化”方兴未艾。虽然主要的对外政策思想库位于美国本土,或聚集在华盛顿K街、马萨诸塞大道这一狭小地带,但在其机构设置、议题的研究、专业研究人员的构成、资金来源等诸多方面都有全球化的势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莫斯科、北京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也有世界各国的学者和访问学者加盟,某些议题的研究也吸纳世界各地知名专家学者的参与,各国的政界学界将美国思想库作为表达国家对外政策、发表研究成果、影响美国知识精英的重要场所,思想库成为美国与世界接触的另一个窗口。
(二)思想库在美对外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和影响。借重外脑和思想库的作用,是当代决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美国对外政策思想库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正如对外关系委员会总裁、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主任哈斯所指出,思想库是“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最重要也最不易察觉的一个组织,作为美国的一个独特现象,一百年来,塑造了美国全球接触战略”。(26)通过对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官员的调查发现,相比公众舆论和特殊利益集团,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库对官员的长远影响更大,相比媒体报道和与国会的议员互动,很多情况下,思想库更具长远影响力。(27)美国对外政策智库知识精英的角色和影响,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观念和职位两个方面。
一是观念角色。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栖息地,思想库从事可信研究并将其专业的知识公众化,充当意见领袖和观念掮客,进行精英舆论的引导和公众舆论的动员。美国上诉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理查德·波斯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为一般公众而不是仅仅为学术和专业听众,在公共事务或者在宽泛的意义上就政治事情,也包括意识形态、伦理、文化视角下的文化事情而写作。公共知识分子比学者更注重实用、更当代,更具结果取向,但又比技术人员更宽泛。
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国际关系的关注群体相对要小,专家的意见对于公众舆论的动员显得尤为重要。(28)白宫、国会山和官僚机构倚重思想库的专业知识,通过听证会、咨询、合同研究、行政过渡小组各种渠道吸纳知识精英的行家意见;思想库生产思想,并将其产品——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剔除国际关系中的术语行话,通过出版、报纸、杂志、电视、公开会议、网络等大众媒介,予以市场化和大众化。在整个社会对外政策观念的形成和传递的观念链中,思想库作为政策观念的始作俑者,同时处于上通下达的中间环节。正如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创始人杰勒吉安指出,一个思想库推出的某一个观念很少变成公共政策,通常情况是,这些观念促成了全国辩论,间接地影响了政治气候,有时,这种影响是重大的。(29)
二是职位角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作为“君子儒”的储备,思想库成为卸任官员和候任官员学术与仕途的旋转门。
由于两党制原因,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层次的总统任命的官员随着政府更替而离开政府部门,思想库和大学、公司一样,成为政治精英转为知识精英的一个主要去向。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主要思想库的学者甚至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或多或少都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情局、国防部、国会等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从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中国研究项目研究人员(或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政府履历可见一斑: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贝德、道斯、李成;美国进步中心的哈奇格恩;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费立民、葛来仪、墨菲;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李洁明、卜大年、施密特;传统基金会的布鲁克斯、谭慎格、费浩伟等都有深厚的政府任职背景。
思想库与政府的人员关系并不是单车道,而是通过接受政府内阁、内阁次级或官僚职位,充当总统竞选顾问、服务政府过渡小组、特别工作组、设立议员联络办公室、接纳政府人员做短期研究、邀请政府人员参加闭门会议和研讨会等各种渠道,保持与政府精英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紧密联系,渗透到整个外交政策网络。充当总统竞选外交政策顾问,是知识精英转向政治精英的关键步骤。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都曾作为总统竞选顾问而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传统基金会在里根政府,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小布什政府,布鲁金斯学会在卡特政府、克林顿政府都留下了深刻印记。总统大选也是思想库的政治机会,外交政策作为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问题领域,为不同思想库的知识精英,依附党派和候选人进行政治——学术总动员提供了经常性机遇。20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等候选人的对外政策顾问涵盖了主要思想库,也是美国全国主要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华盛顿邮报》戏称之为“书呆子的战争”。(30)奥巴马的对外政策顾问团队就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热津斯基、理查德·丹泽格(曾被认为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布鲁金斯学会的苏珊·赖斯(后出任奥巴马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贝德(后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处主任)、达尔德(后出任驻北约大使)、里德尔、高登、美国进步中心的麦克多诺(后出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等等。思想库成员与政治联姻如此紧密,以至于有的分析家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一两个思想库工作过,不管是助理、工作人员,还是研究小组的参加者,否则,升到政府外交及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职位的可能性极小”。(31)
注释:
①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著,王观生等译:《美国智囊六人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②Richard J Barnet,Roots of War,Atheneum,1972,p.53.
③詹姆斯·曼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布什战争内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④http://en.wikipedia.org/wiki/Susan_Rice.
⑤Morton H.Halperin,Priscilla A.Clapp,Arnold A.Canter,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p.16.
⑥参见阿兰·沃尔夫为《权力精英》2000年版的后记,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崑、许荣译:《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页。
⑦G.William Damhoff,Who Rues America? 15th Edition,Mc Graw Hill,2006,p.xi.
⑧李剑鸣:《美国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⑨(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⑩高程:“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第38—55页。
(11)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A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Reader,Ivan R.Dee,1992,p.128.
(12)Burton I.Kaufman,"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US Foreign Policy Encyclopedia,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gx5215/is_2002/ai_n19132432/.
(13)同注⑥,第161页。
(14)互联(互兼)董事会(Interlocking Directorate)指一个大公司的董事同时也兼任其他大公司的董事。赖特·米尔斯认为,这种互联董事会巩固了企业圈,形成了公司利益共同体的社会基石,以及观点和政策的一致性,构成了达姆霍夫所称的“股份公司的群体”。社会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公司网络的存在。参见: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38页。
(15)Richard J.Barnet,Roots of War,Atheneum,1972,p.179.
(16)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郑启荣等译:《国际关系分析》,1992年版,第77页。
(17)高盛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2.goldmansachs.com/ourfirm/about-us/our-story.html.
(18)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译:《世界是平坦的——21世纪简史》,2006年,第293页。
(19)熊志勇主编:《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20)A.Claire Culture,Private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1)同上,第169—192页。
(22)Donald E.Abelson,A Capital Idea,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McGill-Queen's University.
(23)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Yale Univercity Press,1993,pp.103—181.
(24)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Yale Univercity Press,1993,p.143.
(25)Howard J.Wiarda,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115.
(26)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nd Advocates,Routledge,2007,p.91.
(27)David M.Ricci,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Yale Univercity Press,1993,p.7.
(28)Ole R.Holsti,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utledge 2006,pp.237—267.
(29)James 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S:Academics,Advisors and Advocates,Routledge,2007,p.4.
(30)"The War Over the Wonks,A Lis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Advisers to the Leading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from both Parties",Washington Post,Wednesday,October 2,2008.
(31)转引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