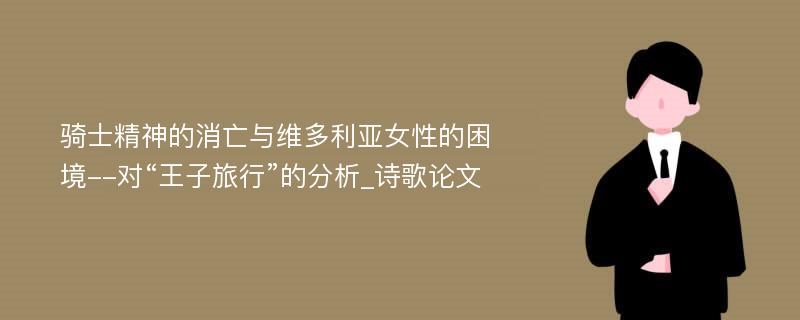
骑士精神的消亡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困境——《王子出行记》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困境论文,骑士论文,王子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1-0091-07
出版于1866年的《王子出行记》,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具有童话风格的诗歌: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苦苦等候前来迎娶她的王子。而王子在旅途中经历了种种诱惑和考验,耽搁了行程,等他赶到目的地的时候,公主刚刚过世,正在举行葬礼。和罗塞蒂的其它诗歌相比,《王子出行记》的象征意义过于晦涩,[1]西方学者的关注较少,国内未见专论。罗塞蒂谈过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讲述《睡美人》的故事。[2]184她不单单是改写一则简单的童话故事,而是借用《天路历程》和《雅歌》的叙事结构,以戏仿的手法颠覆骑士传奇即西方浪漫文学的传统,巧妙而含蓄地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
《睡美人》的改写——最初的悼亡诗
《王子出行记》的最后六个诗节共60行(481-540行),是罗塞蒂最早完成的部分,这本是一首可以独立成篇的悼亡诗。诗歌创作于1861年10月11日,手稿现存于大不列颠图书馆,其标题是《珊珊来迟的王子》。1863年5月该诗发表于《麦克米兰杂志》(第8期,36页),标题改作《珊珊来迟的白马王子》(以下简称《白马王子》)。[3]266笔者将其精彩部分翻译如下:
太迟了,爱已不在,欢乐不复,/太迟了,太迟了!/你在路上游荡得太久,/你在城门口将光阴虚度,/失魂落魄的鸽子在枝头上/死去,没有伴侣;/失魂落魄的公主在城堡里/在窗栅后沉睡,死去;/她的心一直在渴望/是你让她如此等待。//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如果那会儿你及时赶到,/尽管已经太晚;/还能看到她活着的样子/现在已不可能:/冰冻的泉水本可以奔涌,/花蕾本可以绽放,/和煦的南风本可以苏醒/消融冬天的积雪。//……我们觉得,华冠下/她苍白的额头总是痛楚,/直到她褐色的秀发/露出缕缕银丝。//……你本应昨天为她落泪,/在她的床边肝肠寸断;/但为何你今天才来哭泣/而她已经死去?……①
这首诗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中常见的戏剧独白体,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使用该体的是丁尼生,而将这一形式发展到极致的是勃朗宁。[4]艾布拉姆斯指出,戏剧独白属于抒情诗,诗中的语者(明显不是诗人自己)在某个特殊场景的关键时刻所说的话构成诗歌的主体,戏剧独白的目的是为了刻画语者的性格特征;戏剧独白的另一个构成要素是听者,尽管他默不作声(因而不构成对话),但从语者的话中可以得知听者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因此,诗歌中的戏剧独白不同于戏剧中的人物为展示内心活动的自言自语。[5]
根据艾布拉姆斯的定义,诗歌中的戏剧独白体有三个要素:戏剧化的场景、语者与沉默的听者。罗塞蒂的《白马王子》完全具备这三个要素:其一,罗塞蒂在诗歌里营造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景:王子来得太迟,公主已香销玉殒,无缘相见;其二,诗中也有一个语者。虽然语者的身份无法确定,但极有可能是公主身边的侍女。日后罗塞蒂扩写的部分,以及其兄但丁·加·罗塞蒂为此诗绘制的插图,似乎也可以印证这种推测。侍女的话,如泣如诉,道出了公主凄凉孤独的一生,言辞之中流露出对王子的不满和谴责,类似《红楼梦》中紫鹃在林黛玉死后对贾宝玉的述说;其三,罗塞蒂笔下沉默的听者是侍女口中的“你”,即公主苦苦等待的恋人,正是由于他的拖沓延宕,导致了公主抑郁而终。从标题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迟到恋人的身份是一位王子。
但罗塞蒂的这首《白马王子》,与艾布拉姆斯的归纳有一点很大的差异,即戏剧独白的目的不同。一般而言,戏剧独白的目的是为了刻画语者的性格特征,例如罗伯特·勃朗宁往往借戏剧独白的方式,表现语者或偏执或病态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如《我已故的公爵夫人》、《教兄利波·黎比》和《波菲利亚的情人》。但罗塞蒂这篇戏剧独白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突出语者(侍女)的性格特征,而是刻画听者(王子)的性格特征。罗塞蒂巧用戏剧独白的表现手法,借侍女的话追述公主的不幸遭遇,矛头直指拖沓延宕的王子;王子作为沉默的听者,面对指责,只能是无言以对的困窘和羞愧。
《白马王子》一诗以悲剧收场,彻底颠覆了以《睡美人》为代表的童话故事中“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快乐”的大团圆结局。1863年10月,罗塞蒂在写给另一位女诗人格林威尔的信中提到:“得知您喜欢我逆向改写的《睡美人》,我感到非常高兴:恐怕除了童话世界之外,类似的逆转总是经常出现的”。[2]184这说明,罗塞蒂清楚地认识到童话世界虽然美丽而实则虚幻,于是在《白马王子》中自觉地解构了这则维多利亚时代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
其一,时间的流逝取代了时间的静止。在《睡美人》中,玫瑰公主的手指一碰到纺锤就被扎了一下,昏睡过去,整座城堡也随之进入梦乡。城堡内的时间就这样被凝固了百年,直到王子的出现,被吻醒的公主还像15岁时一样年轻漂亮。而在罗塞蒂笔下,时间无情地流逝,“一年”、“五年”、“十年”(491-92行),直到公主的秀发间出现了缕缕银丝(504、519-20行),失去了青春和美貌。
其二,《睡美人》中的王子充满勇气和信心,就算得知不少王子在穿越城堡周围的荆棘时命丧黄泉,也没有丝毫动摇。他的行动敏捷果断,绝不拖泥带水。而罗塞蒂笔下的王子犹豫拖沓,“在路上游荡得太久”,“光阴虚度”(483-4行),使得公主早生华发,最终撒手人寰。
其三,婚礼变成葬礼。《睡美人》的结局是举国欢庆,王子和玫瑰公主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他们幸福欢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而在《白马王子》中,王子赶到的时候正碰上公主的葬礼,二人已是阴阳相隔。
罗塞蒂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解构了《睡美人》的故事,她笔下的童话世界是一个魔法失灵的世界:在这里时间不会停下脚步、公主不再永葆青春美丽、王子无法顺利营救苦难中的公主。在这个故事中,更没有仙女的庇护使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欢乐,有的只是泪水、孤独、无尽的惆怅以及无法弥补的遗憾。
骑士传奇的戏仿
在哥哥但丁·加·罗塞蒂的建议下,罗塞蒂将这首仅有60行的悼亡诗,发展成一首540行的带有基督教寓言风格的骑士传奇,扩充的部分写于1864至1865年的冬天,[3]266题为《王子出行记》。诗歌的押韵格式也有所变化,原先完成的部分(481-540行)每诗节10行,偶数行押韵,而扩写的部分(1-480行)则是每诗节6行,韵脚为aaabab。于是,原本以抒情为主的悼亡诗,发展成一篇有完整情节的骑士传奇,而最早完成的戏剧独白变成了《王子出行记》的结尾,成为全诗的高潮。
骑士传奇是在中世纪流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主题大都是游侠为了荣誉、爱情和基督教信仰,在历险中展现崇高的骑士精神。[6]19世纪初,狄格拜曾写过一部研究骑士传奇的经典著作,名为《荣誉的巨石》。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他将骑士精神定义为对美和崇高的追求。[7]就爱情而言,骑士往往侧重精神恋爱的层面,在他们眼中,心爱的女性就是理想的化身,对她的追求同样体现了对美和崇高的向往,这就是所谓的典雅爱情,它有这样几个标准:热烈的爱慕和崇拜;至诚至真,忠贞不二;勇于牺牲,为了心上人的幸福和荣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8]弗莱指出,骑士传奇中男主人公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骑士历险的过程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9]
在《王子出行记》中,罗塞蒂主要是借助基督教寓言《天路历程》的故事框架,来检验王子是否具有真正的骑士精神。班扬的《天路历程》是罗塞蒂熟知并喜爱的一本书,连《王子出行记》(“Prince's Progress”)的标题也是仿效了《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二者甚至押相同的头韵。从深层看,它们的叙事结构更是如出一辙:《天路历程》中天路客离开毁灭城,一路克服种种磨难,奔向天堂城;而罗塞蒂刻意安排王子和公主一个住在“尘世尽头”(13行),一个住在巍峨的崇山峻岭之间(403-32行),象征王子历尽千辛万苦,前去迎娶天国的新娘。表明罗塞蒂依照基督教寓言的传统,将王子行走的旅程和精神上的旅程并置,核心是灵魂的考验。
诗中灵魂的考验,是通过诱惑和磨难来展现的——王子只有在历险的过程中证明自己具备真正的骑士精神,才能迎娶梦中的新娘。来自外界的诱惑主要有三个方面:挤奶姑娘的性诱惑、长生不老药的诱惑、温柔乡的诱惑。罗塞蒂巧用全知(上帝)的叙事角度,使读者看到、听到、感受到事件的种种征兆,而旅程中的王子却只有凭他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做出判断。
第一次诱惑发生在王子离开舒适的宫殿后不久。口干舌燥的王子向挤牛奶的姑娘讨鲜奶喝,姑娘索要回报,慷慨的王子便让姑娘自己开价。于是姑娘给王子两个选择,要么摘一轮“满月”送她,要么坐在苹果树下陪伴她一天一夜(80-4行)。挤奶姑娘的提议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玄机。按照诗人的创作意图,“满月”即为王子的象征:罗塞蒂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她在刻画王子的时候,特意用了“满月”的意象来衬托王子的性格。[2]228那么,挤奶姑娘的两个选择其实就是一个,王子须以自身为酬劳。[10]
此处,罗塞蒂借用了《圣经》的典故和象征,为笔下的王子设置了第一重考验:以“蛇女”和苹果树暗示“性”的诱惑。女郎的美貌和蛇的意象紧密相连,加上二人共憩的地方在苹果树下,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伊甸园中诱惑夏娃的蛇。一般认为,智慧树上的禁果即为苹果,所以在基督教的文化中苹果象征诱惑,②而亚当、夏娃在偷食智慧树的果实后对赤身露体感到羞耻,则是非常明显的性的暗示。
王子犹豫再三,“出于礼貌,他不得不/恪守自己高贵的誓言”(87-9行),于是“在苹果树荫下舒展身躯,/与姑娘一道,谈笑风生”(91-2行)。表面看来,王子慷慨大方,信守承诺,对女士也彬彬有礼,似乎很符合骑士精神。但通过全知的叙事角度,罗塞蒂使读者看到女郎的“眼睛越来越亮”(69行)、“眼眸闪着粼粼绿光”(71行),“头发编成一个精致的发辫/像盘踞的蛇,鳞片闪闪,/牢牢地留下他一天一夜/在她狡黠的圈套里。”(93-6行)可是王子对周遭的人和物感觉迟钝、麻木,更缺乏足够的意志力抵抗美色的诱惑:他只看到女郎“红润白皙”的脸庞、“波浪般”的长发、灵动的眼神,却察觉不到她的恶意与妖气,居然愚蠢地向她展示风度、甚至做交易,轻易地陷入罗网,难以自拔。
罗塞蒂笔下充满致命诱惑力的女性形象,明显受到济慈的影响。济慈在其名篇《拉米亚》中,将“蛇”与“美女”的形象重叠糅合,出神入化地塑造了美丽而危险的女性形象,这为罗塞蒂笔下的“妖女”提供了文学原型。但济慈在刻画危险的美女形象时,往往强调她们凭借歌声夺人魂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妖(Siren)一样,而罗塞蒂笔下的此类女性形象则以长发为诱惑的主要手段,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罗塞蒂笔下富有诱惑力的长发意象,来源于其兄但丁·加·罗塞蒂的绘画和诗歌。但丁·加·罗塞蒂于1864年绘制了一幅名为《莉莉丝》的油画,画作中的莉莉丝慵懒地斜靠着,对着梳妆镜漫不经心地梳理头发。罗网一样的长发几乎占据整个画作的1/4,而且是中心位置,极富视觉冲击力。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首14行诗《莉莉丝》(日后更名为《肉体之美》),也写到女子长发的诱惑力,“用一缕令人窒息的金发,”缠绕着男子的心。[11]罗塞蒂的《王子出行记》,与其兄以莉莉丝为主题的绘画和诗歌差不多创作于同一时间,克里斯蒂娜在构思第一重诱惑时,极有可能从哥哥的作品中得到灵感:以“秀发”暗喻罗网,使青年人在不知不觉中迷了心智、丢了性命。同样用长发表现诱惑,兄妹二人描写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哥哥笔下的长发是披散开的,“纠结缠绕”,“闪亮的”金发像“明亮的网”,强调莉莉丝性感的一面;而妹妹笔下的长发则编成精致的发辫,盘在头上,像蛇一样“鳞片闪闪”,强调挤奶姑娘狡猾的一面。挤奶姑娘精心编织的陷阱,正如她的发辫一般层层叠叠,鲁莽轻率的王子注定无处可逃。
罗塞蒂巧用创世纪的典故,暗示王子刚走了一里路(59行),就丧失了骑士精神中至关重要的“纯洁”和“正直”,这与中世纪骑士传奇的名篇《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形成鲜明对比:高文爵士连续三天抵制住漂亮女主人的诱惑,不为所动,而王子则很快在女色的诱惑面前败下阵来。
在穿越一片荒原之后,王子迎来了旅程中第二个艰巨的考验——“永生”的诱惑。王子遇到一位风烛残年的炼金术士,正在洞穴中炼制长生不老药。老人同意王子借宿的请求,但作为交换条件,王子须为老人工作:拉一扇巨大的风箱。老人还允诺王子,药炼成之后可送他一份。于是二人合作,一个配药熬制,一个添柴加火,期待锅内的汤汁有朝一日冒出粉红色的蒸汽,那是长生不老药炼成的标志。可死神却抢先一步夺去老人的性命,就在老人垂下的手指浸到汤里的那一瞬间,药终于炼成了。于是王子便自己盛了一小瓶,继续赶路。
罗塞蒂通过全知的叙事角度,使读者察觉到老人无论是样貌神态还是所作所为,都令人产生怀疑,虽然他承诺永生,却自始至终都和死亡的意象紧密相连:老人居住在洞穴中,“见不到阳光或空气”(199行);“伛偻着身子”(178行);他形容枯槁,“满是污垢的爪子紧紧攥着,弯曲变形,/皮包骨头,鹰钩鼻瘦骨嶙峋,/身体颤抖,眼光狡黠而猜疑;/双目闪烁,几乎容忍不了/一丝阳光。”(182-86行)。洞穴的火光看上去像是“坟墓”中燃烧的眼睛(169-70行),“骷髅”似的老人(181行)用颤抖的声音尖叫着:“干活抵账,交易公道”(194-5行)。反讽的是,老人花了99年多的时间,不眠不休来炼制的长生不老药,必须以他自己的死亡为代价,最后一味配料恰恰是他自己的性命。老人向王子许诺“永生”,而事实表明一切皆是枉费心机。故事的结尾暗示,王子辛辛苦苦换来的“长生不老药”,根本无法恢复公主的青春、美丽和生命。
而王子却对身旁种种明显的提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对这位与黑暗为伍、无处不透着古怪甚至癫狂的炼金术士深信不移,“想都不想”就把他当成是好客的主人(188-92行),与他达成交易,“拉着风箱,满怀希望;/心中盘算,‘我的爱人和我将会永生。/就算我耽搁,但又如何,长生如此美好,/她定会原谅我。’”(219-22行)迟钝和轻信的王子看不穿整件事的虚幻与荒谬,把希望寄托在虚假的承诺之上,一再延误迎娶公主的宝贵时间。
老人住在荒原上的洞穴中,这一场景的构思取自《天路历程》。不管是人物的塑造,还是营造的意境,以及暗示的象征意义,均与《天路历程》中的“死荫谷”极为相似。两处均为旅者必经之地且荒无人烟:“背后的土地贫瘠,/但前面更加荒凉。”(125-26行)都是“不生也不死的土地”(151行)。而且,二者都有风烛残年的老人住在洞穴中。罗塞蒂巧用文本的互文性深化了“炼药”这一场景的反讽意味,“死荫谷”正是“永生”的对立面,在“死荫谷”中制造“永生药”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一场闹剧。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而言,永生的唯一途径是耶稣基督将其带入天国,而王子却将之抛在脑后,把永生的希望放在了炼金术士身上。罗塞蒂笔下的炼金术士,正是虚假信仰的象征。关于炼金术士的文学原型,彼得森认为是《天路历程》中的教皇;[12]阿森诺则认为是《仙后》中的魔术师阿奇玛戈(Archimago);[13]汉普福瑞兹则认为是哥特小说《流浪者迈尔墨斯》(Melmoth the Wanderer)中名叫亚多尼亚(Adonijah)的犹太老人。[14]不管是代表天主教的教皇或阿奇玛戈也好,还是代表犹太教的亚多尼亚也好,炼金术士都是虚假信仰的象征,因为罗塞蒂本人是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在她看来,英国国教才是真正的信仰。
骑士精神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坚定的信仰,而意志薄弱的王子轻易被虚假的承诺所迷惑,误入歧途,与所应追寻的真理和幸福(在诗中以公主为化身和象征)背道而驰,蹉跎了岁月,致使公主在最年轻最美丽的时候与泪水和孤独为伴。
王子离开山洞之后,开始了一段涉水的旅程。这段描写,蕴含着基督教的深意,即洗礼的仪式。洗礼是洗去罪孽,以接近天国。王子的涉水之举,与《天路历程》“黑水河”中关于基督徒涉水的描写颇有相似之处。在《天路历程》中,如果信仰真诚,水则浅;信仰不够真诚,水则深。由此来看,王子涉水时遭受的灭顶之灾,恰好说明了他没有真诚的信仰。
在万分危险之时,王子被一群美丽温柔的女孩子救上岸来,也同时迎来了旅程中最后一次诱惑——温柔乡的考验。女孩子们将快要溺毙的王子从河里救起,殷勤体贴地竞相照顾他:“一个人绞干他乱发里的污泥;/另两个人擦热他的手,无一处遗漏;/还有一个人撑起他垂到一边的头/……轻轻抚慰,举止温柔”(337-48行)。罗塞蒂似乎想再给王子一次机会,可惜的是经过洗礼的王子并没有脱胎换骨、消除他性格中的弱点,再次流连温柔乡,向她们倾诉旅途的艰辛(357-58行),在第三次诱惑中错失了寻找公主的最后时机。
穿插在三次诱惑之间的,是三段枯燥而孤独的旅程:荒原、渡河、登山,这些是自然界的磨难。罗塞蒂认为,人生旅途中必须忍受的枯燥和寂寞,是更为严峻的考验。[2]226这一点从时间的长短上也可以看出来。三次诱惑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年左右。那么在其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子都不得不忍耐长途跋涉中的孤独与沉闷。意志薄弱、耐不住寂寞的王子甚至期盼诱惑再次降临,“渴望有人陪伴。//山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山谷中也没有;/树叶,还是树叶,没有什么变化。/再碰到一个女孩就好了”(294-98行),这就完全背离了骑士精神。
在诱惑与磨难面前,罗塞蒂笔下的王子表面看来身强体健、相貌堂堂、彬彬有礼、信守承诺,但实则意志薄弱,缺乏向往尊严与崇高的灵魂,不具备分辨真与假、善与恶的智慧。他虽然有追求的目标,但“并不太把公主放在心上”(267行),因此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他太容易被中途的诱惑缠住前进的脚步——“他磨磨蹭蹭地前行,很容易转向”(301行)。而且,王子无法从挫折中吸取教训,改正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屡屡在灵魂的考验中败下阵来。
罗塞蒂将骑士传奇和基督教寓言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斯宾塞在《仙后》中也曾经用过,但两人的目的却大相径庭。斯宾塞是为了培养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贵族,使他们具有骑士精神,效忠伊丽莎白女王。[15]363罗塞蒂虽然仿照骑士传奇,但又颠覆了骑士的核心价值,这可以说是罗塞蒂对骑士传奇的一种戏仿。《王子出行记》中的王子丧失了典雅爱情,也就丧失了对崇高的追求,显得平庸而世俗,罗塞蒂以此暗讽在追寻世俗享乐的维多利亚时代,真正的骑士精神早已名存实亡,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们所奉行的骑士精神(或绅士风度)只是徒有其表。
“影子”公主与《雅歌》的变奏
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对女性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她)是实体呢,还是影子?”(401行)罗塞蒂在《王子出行记》中以暗喻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诗中的女主人公便是一个影子,即使她贵为公主。
王子是全诗的核心,整首诗都是围绕着王子及其旅程展开的,而公主几乎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出现。她就像一个影子,远远地投射在那里,作为王子出行寻找的目标。在540行的长诗中,她只说过一句话:“暑去寒来,我要再等待多长?”(7行)她终日愁眉不展,泪水涟涟,只有沉睡可以使她暂时忘记等待的痛苦,完全丧失了行动力,徒劳地等待王子前来救赎。《王子出行记》的叙事结构、意象、象征意义,都与《圣经·雅歌》颇为相似,只是对调了故事中的角色性别,“影子”由男子变成女子。《雅歌》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子,她积极主动地、漫山遍野地寻找自己的爱人,经过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结成良缘,以盛大的婚礼场面结束。在《雅歌》中那女子处于前台,她在说话,她在行动;而在《王子出行记》中则是王子处于前台,他在说话,他在行动,公主反而成了一个影子。罗塞蒂的这种写法是对《雅歌》的变奏。
《王子出行记》描写这样一位公主,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可悲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的无奈与无助。在维多利亚时代,出身高贵的年轻女子拥有的财富与社会地位,给予她们更多的社交机会,可以保证她们能够顺利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而诗中的公主却没有与其身份相当的选择权和影响力,被困在城堡中,像被囚禁在金子做的鸟笼里,无助地等待着被施舍的婚姻和幸福。“从没有福佑降临给她,/让她可以跑去迎接。”(529-30行)公主彻底放弃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似乎只剩下一具躯壳,一个影子,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灵魂和意志:“她对自己的穿戴不甚留意,/裙子,花冠,或长袍”(515-6行),“我们从未见她露出笑容/或是皱起眉头”(511-12行),诗中的公主最终没能盼来成为新娘的荣耀。
这位丧失了话语权和行动力、命运可悲的公主,倒更像是中产阶级女性的代表。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因为社交圈子太窄,而社会习俗又不允许她们主动去追求心仪的男性,所以难以得到幸福的婚姻。正如克瑞尼蒂斯所说,对于一位中产阶级的淑女而言,“惟一可收获的荣耀便是成为新娘,婚姻是她惟一可经营的事业”。[15]38而那些过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嫁出去的中产阶级女性,很容易成为“过剩女子”,终生得不到爱情和婚姻。根据社会学家格瑞戈在1862年的统计,英国当时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多达75万。[16]
其实,对于女性而言,无论她出身高贵也好,低微也好,总希望自己在最年轻美丽的时候遇到“白马王子”,缔结良缘。然而女孩子的青春总是特别短暂,经不起岁月蹉跎。罗塞蒂笔下的公主,如同凋零的玫瑰一般,错过了生命的花期,最终成为死神的新娘(471-74行)。
罗塞蒂五岁时写过一首诗,诗的内容是写一位名叫塞西利亚的小女孩,她从不去上学,除非她的角斗士陪她一起去(“Cecilia never went to school/without her gladiator.”)。从这首处女作中可以看到罗塞蒂在幼时的幻想和渴望,她似乎等待着人生中出现这样一位勇士,为她而战,带给她安全和保护。而30年之后的罗塞蒂,早已看透童话故事和浪漫传奇中所谓“白马王子”的欺骗性,《王子出行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将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和罗塞蒂的《王子出行记》对比,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两位女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中产阶级女性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困境,但勃朗特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缔造了一个童话(《简爱》结尾处明显有童话故事《莴苣姑娘》的原型:简爱付出的爱情使罗契斯特失明的双眼恢复了部分视力,在《莴苣姑娘》中莴苣姑娘的眼泪使瞎眼的王子复明),而罗塞蒂则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解构了童话故事,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现实。
《新约》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比作新郎与新娘,不少罗塞蒂的研究者将王子比附为基督,③或者将公主比附为基督,④认为《王子出行记》是罗塞蒂唯一脱离正统基督教思想的作品,因为二者没有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罗塞蒂并没有在这首诗中塑造基督的形象,无论王子或者公主都缺少基督的基本特点。[17]公主也许有一些基督的品质,例如坚韧、忠贞,但她缺少基督必备的睿智。罗塞蒂在《王子出行记》中只不过是借用基督教寓言的框架,曲折地表现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地位、爱情、婚姻问题的关注而已。
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们对骑士传奇的兴趣逐渐减退,直到19世纪初这种体裁才又复兴起来。骑士文学的复苏,以丁尼生、拉斐尔前派为代表,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和追求。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主人公形象过于女性化,力图塑造更有阳刚气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认为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失去了女性的温柔和娴静,并为此感到遗憾,因而虚构一些勇敢的、奋不顾身的英雄营救受害女性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为了塑造骑士的英武,往往把女性写成被动的、等待救赎者,并把这种女性作为理想女性来写,她们引发骑士的热情和勇敢,并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情操。骑士们身穿金光闪闪的铠甲,手握长剑;而女性则往往披着美丽的金发,衣衫不整,被捆绑着,等待英雄的到来。罗塞蒂的《王子出行记》解构了这类英雄救美的故事,反过来写一个软弱的王子未能救赎公主。由此可以看到罗塞蒂对骑士文学复兴的反思,她比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世界之外的树林》整整早了30年。[18]《王子出行记》对那位影子公主的描写,既沿着上述的模式,又让人感到这类女性并不能激励出英雄的骑士,这正是罗塞蒂的睿智之处:符合男性作家和画家的标准,塑造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完美女性的形象,美丽、顺从、忠贞,但这个只会哭泣和沉睡的公主显然无法提升王子(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化身)的精神境界,无法使他更崇高、更有责任心。罗塞蒂以几乎不露痕迹的方式讥讽那种父权制荒谬可笑的逻辑。
注释:
①本文作者的翻译没有按照原诗的韵律和节奏,只是译出其意思而已。
②"apple,n.3"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nd ed.1989 OED Online,Oxford UP,10 Jun.2009
③将王子比附为基督的评论家有Angela Leighton,Victorian Women Poets:Writing Against the Heart(Harvester Wheatsheaf,1992)160.Linda H.Peterson,“Restoring the Book:The Typological Hermeneutics of Christina Rossetti and the PRB,” Victorian Poetry 32(1994):220.Sara Fiona Winters,“Questioning Milton,Questioning God:Christina Rossetti's Challenges to Authority in ‘Goblin Market’ and ‘The Prince's Progress’,” The Journal of Pre Raphaelite Studies 10(2001):21-25.
④将公主比附为基督的评论家更多些,例如Joan Rees,“Christina Rossetti:Poet,” Critical Quarterly 26(1984):67-68.Jeffrey T.Schnapp,“Introduction to Purgatorio,”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ed.Rachel Jacoff(Cambridge:Cambridge UP,1993)203.Joan Rees,“Christian Rossetti:Poet,” Critical Quarterly 26(1984):67-68.Simon Humphries,“Who is the Alchemist in Christina Rossetti's The Prince's Progress?”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58(2007):684-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