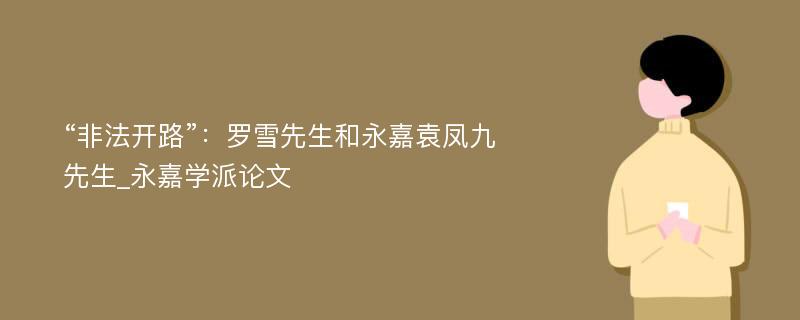
“违志开道”: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嘉论文,元丰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6-0108-07
永嘉学派是以地域性名词分类的学术派别,因该学派传承的主体是永嘉籍人士,于是,永嘉这一地理名词就成为该学派的指称。这种命名法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学派的地域色彩,不如说是出于归类上的方便。因为就永嘉学派而言,无论学术思想的内涵还是思想家的活动范围都超越了永嘉的地理和行政范畴。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永嘉思想在历史中有其自身深化和延续的理论逻辑,但其对于普遍性的哲学思考与理论智慧均是在宋代学术的框架内产生和展开的。永嘉学者对于二程洛学的传承,就思想衍生与分析的外缘情境而言,已完全超出了学派所依赖的永嘉这一地域社会结构;而在传承的路径上,学者从偏于一隅的永嘉走向当时的学术中心洛阳,人物实际的活动同时标示出永嘉学术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
很明显,永嘉虽在东晋太宁元年(323)已置郡,但在北宋的境域图上,永嘉离当时的主要人口中心还是太遥远,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它的资源和安全问题跟边缘地区的位置差不了多少。而在文化意涵上,宋代以前永嘉的学术传统、地域声望毫不起眼,学术上的荒芜与地理位置的偏僻近乎正比。永嘉学术的成长得益于宋代以来科举制度的革新,士人群体日益增加意味着文化阶层的扩大,同时为边缘地区的士人向学术中心的靠拢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家庭财力、赶考生涯中的各种资源与机会跨越地理障碍,去接触、聆听、感悟、辨析后来成为永嘉思想来源的洛学,这些人成为学术中心对学术边缘发生作用的中介。北宋时期,以周行己等元丰九先生为代表的永嘉士人正是这一作用的媒介者。在永嘉学术体系化之前,元丰九先生以其求知的热情与渴望,接受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话语,并力图将之组织成一个体系,在历史的场景中实是一种超拨于俗流的行动。正是这种行动及其成果,既为后来永嘉学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永嘉学术的一个阶段。
一、元丰九先生的“违志开道”
“元丰九先生”是后人对元丰年间(1078-1085)到太学求学的周行己(1067-1125?)、许景衡(1072-1128)、刘安节(1068-1116)、刘安上(1069-1128)、戴述(1074-1110)、赵霄(1062-1109)、张辉(1063-1117)、沈躬行(生卒年不详)、蒋元中(生卒年不详)等士人简便而过誉的概称①。事实上,永嘉士子进入太学的时间并不一定都在元丰年间,譬如元丰最后一年,戴述年仅11岁,进入太学似乎就过早了;此外,九先生中个人的名位、成就亦不可等而视之。作为九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周行己对除自己以外的八人有过专门的介绍与总结:
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子弟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服从而师友焉。蒋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禄。刘元承今为监察御史,元礼为中书舍人,许少伊今为敕令删定官,方进未艾。戴明仲为临江军教授,赵彦昭为辟雍正以卒。张子充最早有闻,每举不利,今以八行荐于朝。凡此吾乡之士皆能自立于学校,见用于当世,其间或先或后、或贵或贱、或寿或夭,则有命也,然不可谓不闻矣。②
依靠此段线索,我们简单地对九先生做些介绍。1-2.蒋元中、沈彬老(即沈躬行),两人生平事迹不详。《温州府志》称蒋元中著有《经不可使易知论》,后太学刻于石。绍兴初(1131),郡守张九成(1092-1159)下车诣学,曾口诵此论③。3-4.刘元承、刘元礼,即刘安节、安上兄弟两人。元祐(1086-1093)年间,两人联荐于乡,同入太学。安节于元符三年(1100)擢进士第,初任越州诸暨主簿,河东提举学司管勾文字。后除监察御史、起居郎,迁太常少卿,不久谪知饶州(今江西波阳),移宣州(今安徽宣城)。政和六年(1116),卒于任上。有《刘左史集》4卷存世。安上是绍圣四年(1097)进士,初授钱塘尉,升处州缙云县令。大观元年(1107)提举两浙学事,后除监察御史。次年迁侍御史,后升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给事中等官。政和二年(1112)外调,以徽猷阁待制历任寿州、婺州、邢州等地知州。有《刘给谏集》30卷,今存5卷。5.许少伊,即许景衡,人称“横塘先生”。元祐年间(1086-1094)在太学④,元祐九年(1094)进士。大观中(1107-1110),为勅令所删定官,后迁承议郎、少府监丞,任福州通判。宣和六年(1124),召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除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后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建炎二年(1128),卒于京口,谥“忠简”。著有《横塘集》30卷,今存20卷。6.戴明仲,即戴述,少游京师太学,元符三年(1100)进士,调婺州东阳县主簿,后为临江军军学教授⑤,卒年37岁。与弟戴迅著有《二戴集》,今已佚。7.赵彦昭,即赵霄,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任颖昌府长葛主簿、济州州学教授,迁辟雍正,兼摄司业⑥。8.张子充,即张辉,人称“草堂先生”。以八行荐于朝,任南昌州学教授,后为辟雍、小学司纠⑦。9.周行己,字恭叔。因曾在温州浮沚书院讲学,又被称为浮沚先生。元丰六年(1083)补太学⑧,元祐六年(1091)进士,曾任温州、齐州州学教授,乐清、原武县令,秘书省正字等职。著有《浮沚集》16卷、后集3卷,今存文7卷,诗2卷、补遗1卷。
九人之中,仅许景衡在《宋史》中有本传。周行己称包括自己在内的九人,“或先或后、或贵或贱、或寿或夭,则有命也,然不可谓不闻矣”。所谓的“不可谓不闻”,恐怕并非只是居太学期间“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事。这段欲言又止的文字在叶适(1150-1223)的笔下表达得就直接多了:“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⑨
需要细看周行己与叶适以上两段文字。周文指出后来被称为元丰九先生的共同特征是九人在元丰以后进入太学,且“学行修明”;叶文则指明这几人更有学术旨趣上的相同处,即所谓“违志开道”。显然,“违志”、“开道”之语带着时人强烈的学术倾向与判断。按留元刚的说法,“违志”指的是永嘉九先生在太学读书期间,“时右新学,违而之他,甘心摈黜”⑩。换言之,九先生从王安石新学转而求二程之洛学,即所谓“违志”而之他。这一说法在叶适另一篇有名的《温州新修学记》中也有所提到:“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11)很明显,“违志”是指九先生在二程洛学与荆公新学之间的取舍态度与反应方式,而舍弃新学在当时的语境中也就意味着违背最初进入太学以求仕进的志向。
“开道”即开温州之闻伊洛之道,这无疑是更值得关注的行为。九人在求学期间或由开封至洛阳亲炙于二程问道,或私淑。其中,周行己约在元祐年间赴洛阳向程颐问学,《二程集》中有关于周行己行迹的零星记载。二刘约在绍圣年间(1094-1098)从程氏学(12)。戴述亦“尝从洛阳程氏问学”,从而“知圣人之道,近在吾身”(13)。沈躬行在父亲的资助下,从洛阳程颐学(14),叶适称其“北游程氏师生间,得性命微旨、经世大意”(15)。许景衡也“得程颐之学”(16)。但戴、沈、许三人赴洛阳师从二程的时间不详。其余三人,按清代学者全祖望(1705-1755)的说法,“张氏、赵氏、蒋氏疑未见伊川者,盖私淑也”(17)。
叶适以“违志开道”来形容“九先生”作为群体的共同特征,如果“违志”仅仅是个人志业的转向,那么“开道”则是建构起学术的趋势,这对于“僻远下州,见闻最晚”的永嘉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顺着“违志开道”这一意义去追溯“永嘉太学九先生”、“永嘉九先生”或“元丰九先生”等称呼背后的含义,这种简约的称呼大致是对永嘉向二程学习“洛学”者最初性质的标示。如果从这一含义上看,那么,“永嘉之为洛学者,尚不止此”(18),鲍若雨、谢佃、潘旻、陈经邦、陈经正等人均应列入其中。鲍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因有屋于雁池名为“敬亭”,因此学者称之为敬亭先生(19),“久从伊川”(20),著作有《伊川问答录》、《敬亭集》,今已佚。谢佃,字用休。潘旻,字子文,与鲍若雨等人入洛阳从伊川学,隐居不仕。陈经邦、经正为兄弟二人。经邦,字贵新,大观年间进士。经正,字贵一。两人均从伊川游,《二程集》中有二人问道的记载。虽然这几人的资料记载不详,但作为永嘉最初的洛学者,他们在道学的传承与区域学术的生成中同样产生了不可抹煞的意义。
二、洛学与永嘉知识群体的标识
当元丰九先生“违志开道”,去接触、聆听、接受洛学时,这批人作为洛学的一种集合体而被历史有意地书写并凸现了出来,这可能并非这些最初走向洛阳的士人有意的选择,而是历史过程本身的综合作用。随着洛学在此后政治中的起沉,“永嘉”及“永嘉士人”这一名词亦随着洛学的扩展逐渐为士人所知,并在全国建构起充满了地域特性的“永嘉”知识群体。毫无疑问,这一建构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是散漫无序的,它存在于士人参与求学的行为本身,亦源于后人对洛学的梳理清厘。
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永嘉士子对二程语录的记载。“以身任道”(21)之初,二程就对“文”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22),他们避免采用将自己体悟的“道”作为文章流传,而是采用了口头指点门生的方式(23)。这种以口传道的方式不仅为儒学“提供了另一个表达其教诲的一般性渠道”(24),而且当那些初到洛阳的学子怀着求道之心面见二程时,他们不独获得了直接问学的机会,同时,他们用自己的笔所记录下的话语与教诲,也成为某种佐证,为后世所重视。高闶说:“伊川先生议论不事文采,岂有意于传远哉?然独班班可考者,以有刘元承之徒口为传授故也。”(25)这里,刘元承作为一个典型人物被证明是继承了来自程颐直接陈述的知识。谢良佐说:“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二刘各录得数册。”(26)
今存《河南程氏遗书》卷18题为“刘元承手编”,卷23为“鲍若雨录”,卷17则称存疑,“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刘安节元承”(27)。可以肯定,参与笔录者应该是拥有一定资格的洛学学者,虽然他们通常只是作为提问者出场,但这样的提问是拥有一定的共识以及常识的洛学成员之间的演练。在这些语录笔记中,笔录的学生、包括学生的提问与评论伴随着老师的声音一同被记录下来了。随着二程洛学渐次成为思想的主流,二程弟子们的笔记得以翻刻流传,这些学生的名字也被人熟知。虽然后来朱熹在整理二程著作时,曾对二程门人翻刻的《程氏遗书》颇有微词,认为有“传者颇以己意私窃鼠易”(28)的迹象,但当他选择底本时,“着当时记录”、“未更后人之手”(29)的最初记载显然是优先选择的对象,这样,刘元承等亲炙于二程的记录者再次被标识出来。朱熹说:“伊川语,各随学者意所录……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30)“永嘉”原本只是一个地名,并无深层的含义。当朱熹在习惯的观念中使用地理名词指示自己所要谈论的那群人,并以空间范围构建自己的认识图景时,尤其是当“语絮”被作为永嘉诸公的书写特征为人所认识时,作为一种知识群体,“永嘉”也就有了自身的含义。
与此同时,随着二程著作的刊行,文本中所提到的人物、事迹亦以一种更为具体的知识得以流传。程颐在《答鲍若雨书并答问》(31)中对儒家思想的讨论、阐释,潘旻、陈经邦、经正等人的问学记录,永嘉学子的名字作为一种标题而频频使用。程颐对刘元承的议论,还展现了另一种生动的智识活动:
或问:“刘子进乎?”曰:“未见他有进处。”问:“所以不进者何?”曰:“只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为有根,故一年长盛如一年。”问:“何以见他未有进处?”曰:“不道全不进,只他守得定,不变却,亦早是好手。”(32)
在通常的思维习惯下,程颐的比喻与评说很容易使人陷于对刘元承的价值判断中,却忘却了刘元承作为一种符号被标识出来的社会作用与影响。同样,刘元承关于二程的论说也因为双方之间的亲密接触被人记载并传播,如谢良佐记载刘元承论明道先生:“诚意积于中者既厚,则感动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临政,上下自然响应。”(33)
隔着时间的距离,人们需要借助文字、口述、回忆等手段去发现二程的人格特征,以便赋予其新的含义。包括刘元承在内的亲见者,其谈论内容因为信息来源可靠、说服效果强,被作为重要的资源传承下来。同样被记录下来的还有这些学者的名字。来自永嘉的学子凭借着这种工作而使得“永嘉”这一背景性的地域名称逐渐为人所知,尽管这并非永嘉诸公所预期的。
概而言之,随着二程著作不断翻刻,笔录者与文本中所提到的人物或故事,得到了人们富于想像力和同情心的阅读。正是在此过程中,“永嘉”学子作为洛学的倾听者,逐渐成为一个集体名词并有了自己的特性。朱熹说:“周恭叔、谢用休、赵彦昭、鲍若雨,那时温州多有人,然多无立作。”(34)无论永嘉诸公成就如何,作为洛学中的初期人物,其名字却是无法绕过的。因此,当朱熹着手编撰《伊洛渊源录》时,吕祖谦写信给他说:“永嘉诸公遗事,当属薛士龙访求。”(35)朱熹答吕祖谦说:“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即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36)不久薛季宣病故,复又嘱陈傅良。吕祖谦随后的信又说:“《渊源录》事,书稿本复还纳,此间所搜访可附入者并录呈。但永嘉文字娄往督趣,独未送到。旦夕陈君举来,当面督之也。”(37)显然,收集工作十分周折艰苦。成书后的《伊洛渊源录》中载刘安节、鲍若雨、谢用休、潘子文、陈贵一、贵叙、周行己等永嘉诸儒凡七人,虽未甚详,但“永嘉”这一知识群体在朱熹对洛学的思想清理与建构过程中已获得了历史地位。
三、洛学与永嘉区域思想的追叙
当元丰九先生以“违志开道”的形象出现在洛学的语境中时,永嘉士人社群逐渐被洛学的追随者所认识。这些来自于同一地理区域的上人,无论在思想状态上还是在行动上均具有同质性,而当“永嘉”作为他们的指称名词为人所熟悉时,这一地理名词不仅赋予他们归属感,而且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其背后所阐扬的哲学观念影响着区域的思想偏好。
当我们将元丰九先生的含义放置在洛学的背景中去检视时,共同的游学经历与学术旨趣是其中的核心;但当我们转换视角,将元丰九先生放置在永嘉这一区域情境中时,九先生之间的角色、身份、社会关系亦是需要重视的内容。作为九先生中的代表人物,周行己曾经为沈躬行之父子正、戴述、赵霄,以及许景衡的哥哥景亮作过墓志铭,为张辉写过祭文(38)。许景衡曾为刘元承及其父刘弢作过墓志铭,还有祭赵霄之弟赵沾(字彦泽)之文(39)。戴述是刘安上的妹夫(40),刘安节、安上为同祖兄弟。虽然难以解说这种交叉的关系对于永嘉学派的形成、学术思想的归趣是否起过作用,但至少它提供了情感上的紧密联系,这对于地域内部的社会交往是十分重要的。运用乡谊关系、道谊关系、师友关系等等词汇,可以解释并涵盖包括政治、经济以及学说倾向等等在内的大部分行为。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等温州士子对乡里隐士林石、丁昌期的高调褒奖,大致也可以据此来进行解释。
丁昌期(生卒年不详),字逢辰,学者称为经行先生。哲宗三年(1088)举明经行修科而不获用,归隐于家乡。三子宽夫(字包蒙)、廉夫、志夫(1066-1120,字刚巽)皆科举有成。第三子志夫曾两任徽宗朝国子监丞,名声尤佳,据说他在京师三十年,“乡人及四方游旧疾病死丧急难,皆赖公以济;其父母妻子之在远者,亦曰:‘丁公在,庶几无失所也’”。丁家与周行己、刘安节、许景衡等人既有姻亲关系,私交又甚笃。周行己曾经为丁昌期祖父丁世元作墓志铭,铭文有云:
吾家曾大父赠屯田君,与丁君世元顾籍文无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号称长者。而二人亦独相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归世元之子……昌期,盖周出也。(41)
此外,许景衡有祭丁昌期文,并为其妻蒋氏、子志夫作墓志铭(42);刘安节也有祭丁昌期文(43),而且昌期之子宽夫为刘安上妹婿,安上有《祭丁包蒙(宽夫)文》(44)。排列这些关系,有助于我们解释有关丁昌期声望的原因。丁昌期曾筑“醉经堂”讲学,并无著作传世,其他社会活动亦十分少见。昌期之于永嘉学术究竟有何贡献,实是不清楚的。全祖望评价丁昌期说:“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继之者为塘岙先生林氏……而先生参之。”(45)全氏以“参之”二字评之,显然是对前人的一种尊重。丁昌期之所以被建构成永嘉学术史中的一员,并不源于他本人的作为,而是通过各种亲谊关系在后人的追叙中逐渐获得的。
与丁昌期一样,林石的名望亦是经由周行己等人得以彰显的,但却表现出建构者不同的内在诉求。林石(?-1101),字介夫,因其居于瑞安塘岙,学者称其塘岙先生。曾追随古灵先生陈襄的学生管师常学习《春秋》,但“是时《三经新义》行,天下学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废弗讲”(46),而且王安石有意“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47),因此,林石“不复仕”,隐居乡中,以《春秋》教授乡诸生(48)。周行己说:“洛阳程颐正叔,京兆吕大临与叔,括苍龚原深之,与吾乡先生介夫,皆传古道,名世宗师。”(49)周行己将林石教授《春秋》一事誉为“名世宗师”之举,并将他与程颐、吕大临并列,这样的赞誉毫无疑问会引起争议,后来陈傅良为此作过一段注脚:
恭叔之铭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关中吕与叔与介夫同为世宗师。”少伊亦云尔,且曰:“非诗书勿谈,非孔孟勿为者。”以二公所同尊诵如此,然而海内之士知有程、吕,而先生独教行于其乡,人以其所居里称之,不敢以姓字,他无所概见焉,岂非其居势使然欤?要之,永嘉之师友渊源,不曰先生之力哉!(50)
陈傅良以“师友渊源”一词来解释周、许两人对林石的称扬,并无失当,但是,周、许两人着力建构“林石”这一象征符号,其含义并不只是宣扬“师友渊源”,而是基于学术取向上的认同。陈傅良曾指出由于林石以《春秋》教授乡里,于是,“永嘉之学不专趋王氏,其后《春秋》既为世禁,先生(林石)竟不复仕,而周公恭叔、刘公元承、元礼兄弟、许公少伊相继起,益务古学,名声益盛,而先生居然为丈人行”(51)。陈傅良在历史场景中以“务古学”来梳理林石与周行己、二刘、许景衡等的学术宗旨,但周、许等人对林石的推崇则有其当下的目的与深意。林石这一名字之所以被人们所记住,并非严格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立场,即“不为新学”,这一点正与周行己等人的取向相一致。北宋时期的永嘉距离京师遥远,相对僻远的地理环境也造成了学说流动性的阻塞。当周行己等人以“洛学”的传承者出现时,他们希望通过林石在地方上追认一种传统,将自己的学说与地方传统相衔接,并作为一种集体趋势逐渐在地方中取得发言权,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合法化,树立起地域中的学说宗旨。从此后永嘉洛学的历史看,元丰九先生的努力显然是卓有成效的。
张九成是宋室南渡以后的程门后学之一,这位状元曾因反对秦桧而著称于当时,而且曾出知温州,对永嘉学术有着切身感受。他说:“永惟仙里,圣学盛行。元承、元礼、少伊诸公,表见于朝廷,而彦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于太学。渡江以来,此学尤著,精深简妙,深入洙泗堂壶中。其至矣哉!”(52)张九成将洛学在永嘉盛行的源头归于周行己等人,并将永嘉这批最初的洛学者的作用与意义划分为“表见于朝廷”与“力行于太学”两类,然后认定这些人的影响造就了永嘉本地“此学尤著”。楼钥也注意到了洛学在温州的流行:“河南二先生起千载之绝学以倡学者,此邦之士渐被为多,议论词篇,类有旨趣。”(53)
这些记载以叙述性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洛学在温州的发展图谱:从元丰九先生“违志开道”到区域内部圣学“渐被为多”、“精深简妙”直至“深入洙泗堂壶中”。别有意味的是,这一历程似乎被当作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发展过程。由此,洛学或者确切地说还有关学,逐渐作为区域文化、政治等等的解释背景而存在于各种记录中。王十朋说:
吾乡谊理之学甲于东南。先生长者,闻道于前,以其师友之渊源见于言语文字间,无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自得,以诏后学。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场屋,笔横渠而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贵其身,光大其门者,往往多自此涂出,可谓盛矣。(54)
“笔横渠而口伊洛者”是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现象,我们将另文讨论,此不赘述。王十朋的描述大约可见乡谊、学术认同与科举之间的联系,但其主题仍然采用一种叙述性的方式,指出洛学、关学的存在,某些历史关联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洛学、关学思想的影响和长久性。毫无疑问,洛学或关学是他的预设背景,至少在他的文字中看不到那些非关学、非洛学者的反应。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十朋又说:
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儒先数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词醇味长,乡令及门孔氏,未必后游、夏徒也。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江南。(55)
南宋时,温州人才辈出,甲于江南。贾志扬(Chaffee)曾对宋代的科举及第者进行全国规模的统计,并按照府州进行了划分。根据他的研究,整个宋代,温州进士及第者人数仅次于福州、建州,居于全国第三位(56)。这只是南宋的情形,北宋的情形并非如此,其进士率并不高(57)。众所周知,温州进士率高与南宋定都临安有着莫大的关系,但王十朋却有意将转折点追忆至元祐时期永嘉的儒学传统,虽然不确定作者指向元祐这一特定时期的深意,但这一时间大约是周行己等人赴洛阳从二程学习的时期。
同样的例子还有陈傅良对林石的记叙:“吾乡去京师远,自为吴越而士未有闻者。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之间,宋兴且百年,介夫以明经笃行著称当世……名动京师。”(58)陈傅良将林石作为温州士子中“名动京师”的第一人,而在上文所引材料中,他承认林石只是一隐士,“独教行于其乡”,“人以其所居里称之,不敢以姓字,他无所概见焉”(59)。之所以造成如此自我矛盾的认识是因为作者的思考背景发生变动,当他强调熙宁、元丰之间林石名动京师时,是有意把永嘉放置于全国主流的学术脉络尤其是洛学的背景中去叙述的。
综上所述,借助于洛学,永嘉学子在全国获得了集体性的意涵;同样借助于洛学,永嘉士人社群有了其集聚或凝聚的力量,既确立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同时拥有了对本土和群体本身共同的情感。这一基础为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及对学脉延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平台,也为洛学在各地传承的社会图景提供了缩影。
注释:
①“元丰九先生”的称号起于何时实难考证,按叶适说:“绍兴末,州始祠周公(行己)及二刘公(安节、安上)于学,号三先生。”参见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29《题二刘文集后》,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第598页。薛应旂《嘉靖浙江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称:“至元中,称元丰太学九先生。”
②周行己:《浮沚集》卷7《赵彦昭墓志铭》,敬乡楼丛书本。
③参见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1页。
④许景衡在祭刘安节文中说:“公游太学,我亦诸生。”参见刘安节:《刘左史集》卷4附许景衡《墓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此估计其入太学约在元祐年间(1086-1094)。
⑤《浮沚集》卷7《戴明仲墓志铭》。
⑥《浮沚集》卷7《赵彦昭墓志铭》。
⑦《浮沚集》卷7《祭张子充文》。
⑧周行己回忆自己求学经过时,曾说自己“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浮沚集》卷5《上祭酒书》)。据此推算其入太学当在元丰六年。
⑨《叶适集·水心文集》卷29《题二刘文集后》,第598页。
⑩《刘左史集》,留元刚《序》。
(11)《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第178页。
(12)祝穆:《方舆胜览》卷9,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年,第153页。据周梦江考订:周行已、刘安节等六人从程颐学,时间在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管涪州(今四川涪陵)之前。参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13)《浮沚集》卷7《戴明仲墓志铭》。
(14)《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志铭》。
(15)《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7《沈仲一墓志铭》,第335页。
(16)脱脱等:《宋史》卷363《许景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46页。
(17)(18)《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4册,第405,421页。
(19)《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0《敬亭后记》,第163页。
(20)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引祁宽记《尹和靖语》,收入《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5页。
(2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6《上太皇太后书》,收入《二程集》,第546页。
(22)例如,二程认为:“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河南程氏文集》卷8《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收入《二程集》,第580页。他们相信后世儒者对作为形式的文章、经术的在意,妨碍了对道本身的索求。
(23)二程说:“以书传道、与口传道,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收入《二程集》,第26页。“道”虽然可以借助于文字的写作予以言说,但那些弦外之音、表达中所隐含的不言而喻的意思,则无法通过文字传达详尽,即二程所谓“书虽言多,其实不尽”,而这些未尽的部分,在传道者与被传者相见之时,却能“因事发明”,通过师徒之间的接触传情,感知那些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表达而只能通过内心体悟的“道”。
(24)贾德讷:《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体的几点思考》,收入田浩:《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
(25)《刘左史集》附高闶《伊洛辨》。
(26)谢良佐:《上蔡先生语录》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27)《河南程氏遗书》,目录第4页。
(28)(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程氏遗书〉后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30)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7《程子之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480页。
(31)《河南程氏文集》卷9《答鲍若雨书并答问》,见《二程集》,第617-618页。
(32)《上蔡先生语录》卷1;《伊洛渊源录》卷11《遗事》。
(33)《上蔡先生语录》卷2。
(34)《朱子语类》卷101《程子门人·总论》,第2557页。
(35)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3《与朱侍讲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3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5《答吕伯恭》。
(37)《吕东莱文集》卷4《与朱侍讲书》。
(38)《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志铭》、《戴明仲墓志铭》、《赵彦昭墓志铭》、《许少明墓志铭》、《祭张子充文》等文。
(39)参见许景衡:《横塘集》卷19《宣义刘公墓志铭》、卷18《祭赵彦泽文》,永嘉丛书本;《刘左史集》卷4附许景衡《墓志》等文。
(40)《浮沚集》卷7《戴明仲墓志铭》载:“(戴述)娶右谏议大夫安上之妹。”
(41)《浮沚集》卷7《丁世元墓志铭》。
(42)参见《横塘集》卷18《祭丁二丈文》、卷19《丁大夫墓志铭》、卷20《丁昌期妻蒋氏墓志铭》等文。
(43)《刘左史集》卷2《祭丁逢辰文》。
(44)刘安上:《给事集》卷4《祭丁包蒙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319页。
(46)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48《新归墓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47)《宋史》卷327《王安石传》,第10550页。
(48)《止斋先生文集》卷48《新归墓表》。
(49)《浮沚集》卷7《沈子正墓志铭》。
(50)(51)《止斋先生文集》卷48《新归墓表》。
(52)张九成:《横浦集》卷18《与永嘉何舍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楼钥:《攻媿集》卷53《温州进士题名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54)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27《送叶秀才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55)《王十朋全集·文集》卷25《何提刑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08页。
(56)贾志扬:《宋代科举》附录3《宋代各州进士总数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289-298页。
(57)两宋时期温州共有进士1228名,其中,北宋81名,南宋1147名。参见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8,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史部·传记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71页。
(58)(59)《止斋先生文集》卷48《新归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