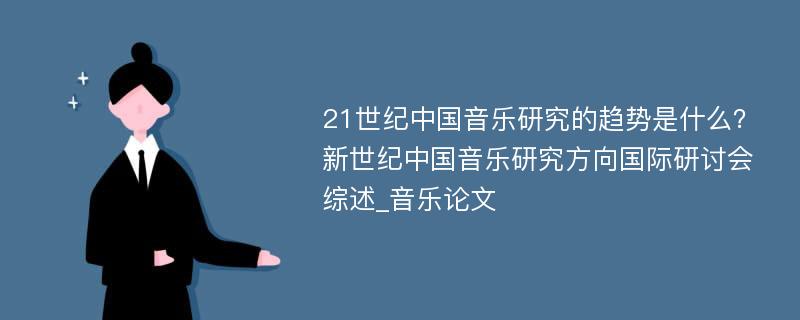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研究走向何方?——“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音乐论文,新世纪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李沛良教授的“前言”论述中拉开了帷幕:
现在踏入21世纪,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探究出真正适合中国音乐多元属性及内涵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经过上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音乐的研究又有那些关键性急需解答的问题?为了探讨及解决的这些问题,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连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发起并组织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并从事中国音乐的教授及研究的学府,我们就以此研讨会作为庆贺崇基学院金禧校庆活动的第一个项目。
谨在此祝愿中国音乐不断有新的发展,与世纪各国的音乐共同照耀人间,为全人类带来温暖、和平与希望。
2001年1月5日至1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行了“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学者近百人,参加学术研讨会发言的学者70余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论题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音乐研究的理论、概念、方法与学科建设
这一专题的讨论旨在对20世纪自王光祈以来的中国几代音乐家以及海外民族音乐学学者在中国音乐史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等领域的不同阶段所遵循、采用的研究方法、观念、学术取向等进行多方位的探讨与总结;并展望中国音乐研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将会遇到的挑战。
罗艺峰(西安音乐学院)为研讨会的第一个发言者,他在其论文“民族音乐学‘全观法’与‘文化全元论’:试论21世纪中国音乐学的方法论问题”中提出,音乐是与民族整体的文化有着复杂的、多层面联系的文化事象,离开了“文化”和“比较”的一般观念以及民族音乐学中关于“传播与适应”的问题,离开了对于思维逻辑的掌握,离开了建立在价值无涉的经验认识和价值关联的人文关怀上的方法哲学,离开了全人类普世文化的“全元论”和民族音乐学“全观法”立场,我们就无法进行自己的工作。然而,置身于全球化历史进程当中,并面对网络化方式可能带来的“一体化”范型,仅仅“护守传统”或者“全盘引进”的中国音乐学研究,都必须搬出一个姿态,以重新调整自身反战的策略,提出构想。韩钟恩(中国音乐研究所)以在寻求“可感知物”的实践活动的同时,再寻求“可陈述物”的理论基础,并且使作为历史的“元叙事”所说和作为逻辑的“元意义”所在得以真正互动的观点,阐述了他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与新世纪工作界面——21世纪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构想”。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提出挑战,对许多传统观念和现存理论持怀疑态度并加以诘难。杨沐(澳大利亚)的论文“后现代时期的音乐研究方法论思考点滴”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关注,他在文中讨论了音乐研究方法论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音乐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形态研究之间的关系和在理论建树方面“破”与“立”的关系,以及对待新、旧理论的态度几个互相关联、难以截然分开的问题。乔建中(中国音乐研究所)受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启示,提出了“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刍议”对建立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系统提出几方面的工作准备:1)建立一套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目索引,2)参照“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模式及规范原则,进行一些典型抽样调查;3)探讨学理,初步建立有关中国音乐的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框架。乔文强调,“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意义在于可以强化我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而且可以改变以往中国音乐学研究中历时(史学)与共时(民族音乐学)分离甚至隔膜的状态,促使其相互渗透和转换,从而使它向深度发展。
民族音乐学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要实现作为一门能够包含所有音乐的学科。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应该是一门对全人类都具有价值的以及实用意义的学科,但是,对一些亚洲或者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来说,他们既反对民族音乐学中保留的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因素,又重视西方学者研究“异文化”音乐的方向。因此,美国及欧洲所称的Ethnomusicology这门学科是不是合适于非西方的学者?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民族音乐学的国际性的理想与一个地区的独特的音乐特征及学术传统结合起来?韦慈朋(香港)认为这是一种“民族音乐学亚洲化的挑战”。
阐明理论、规范概念和明确方法是建立和完善一个学科及有关分支学科的基础,对于这些问题的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有利于学科的定位和发展。音乐考古学作为音乐学中的一门子学科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然而它的定位是什么?它与一般考古学是什么关系?怎样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规范考古学?方建军(西安音乐学院)就这些问题从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实物考察、音响测试、模拟实验、综合分析等方面,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王子初(中国音乐研究所)强调“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中最基本概念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音乐考古学则是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是音乐史的一个部门;同时,音乐史属于艺术史,也是历史科学的一个专门分支。
乐律学是与中国音乐史学有着紧密关系的另一个子学科,乐律研究的总结对于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从古代的乐律研究、20世纪的乐律研究和新世纪的乐律研究三个层次,进行了“乐律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新世纪乐律研究的新进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1)乐律学的概念和范围将有所扩展,2)古代乐律文献整理、辑佚、点注、校释、解题、今译等工作会有全面展开,3)四大集成的出版将为乐律研究提供大量传统音乐作品的实例,对新世纪的乐律研究倾注新鲜血液,从而把乐律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乐律研究相关的是乐调的研究,崔宪(中国音乐研究所)从习惯用法中的调、调与七声和五声、与五声和七声相关的调几个方面进行了“释‘调’”。
中国音乐研究学科建设中无疑将涉及对音乐自身认识的一系列有关的音乐美学问题。其中,音乐的本体论问题,也就是音乐存在方式的问题,是音乐哲学美学的第一性问题。修海林提出“‘乐本体’与‘音本体’:中西音乐学的分水岭”是一种关于音乐本体认识上的理论分型,通过对这一音乐学研究的基础理论的探讨,对无论是处于共时状态还是历时状态中的人类音乐活动,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深度地、立体地揭示某些音乐现象的本质或规律,从而形成对历史活现实音乐生活的更深入的认识。费邓洪(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从“重心需要转移的音乐内容之研究”提出,我们紧迫的任务是在不低估“显内容”研究的重大成绩和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其理论到实践日益暴露的局限和弱点,有意识地将重心转移到对深藏的“隐内容”的研究上来,将“隐内容”所显现的生动的音乐审美现象放到本应归属的审美心理学的基座上予以审视和把握。薛艺兵(香港中文大学)在“乐在其中——对音乐行为过程的人类学阐释”中认为,对于音乐行为过程的研究是生命和艺术本质的要求,因为人在音乐行为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艺术应该是人性尊严和良知的体现。
陈铭道(中国音乐学院)以“欧洲音乐学作为知识:他的理论和协作”为论题,呼吁当新的学术时代来临的时候,通过检讨欧洲音乐学的历史,警惕现代化陷阱的同时,要警惕欧洲音乐学的陷阱。他认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应该明白欧洲音乐学学科理论在思维范式上的遗漏和在研究上的不足,欧洲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大陆,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如果忽然这一点,就会陷入盲目的世界主义幻想中,把欧洲当成世界,把欧洲音乐当成全人类音乐的典范。
中国传统音乐既是根植于古代社会的一种历史文化,又是经历了现代文化变迁的一种当代文化。怎样认识这种文化的历史特性?它在现代文化变迁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薛艺兵(香港中文大学)对于这些宏观问题,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处境”的理论阐释。他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关键影响;当代文化处境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表现为上层传统的“文化排斥”与“文化萎缩”,同时也涉及到“边缘文化”对新“主流”的文化排斥、民间音乐的“原生性”和民间音乐作品的“经典化”等问题。仪式音乐一直是民间传统音乐中的重要内容,它所涉及到的有关信仰、象征、理念以及有关联的生活习俗都是仪式音乐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仪式音乐的研究对于了解、认识和保存中国传统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仪式音乐研究也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长远工作。为了使研究更为深入和完善,曹本冶(香港中文大学)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定位及方法”。他认为,信仰(包括概念和认知)、仪式行为、仪式的音声三部分是研究艺术音乐的主导理论结构模式,结合这一理论模式,在实际运用上配合“远近”、“内外”和“定活”三各基本性的两极变量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理论方法基础。
在音乐理论研究中,一些具有共同学术思想基础、研究领域及特色,从而形成了一定核心人物为代表的学者集体,这样的集体可以称之为学派。高兴(山西大学)就“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学研究中的杨荫浏学派”为内容,对这一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以及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对新世纪中国音乐学发展的启迪进行了论述。
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资料的梳理。如何用现代的观念和手法来整理和管理音乐资料,将对中国音乐在新世纪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萧梅(中国音乐研究所)提出了“无墙的博物馆——网络时代的中国音乐资料建设”,从音乐数据库建设的构想出发,以《中国佛教音乐数据库分类格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陈列室文档管理系统》和《中国乐器数据克(样库)》为例,对网络时代的中国音乐资料建设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中国音乐的传承与变迁
该论题涉及中国音乐研究诸多领域,范围包括:传统音乐形成、发展与特定自然、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对传统音乐传承、生态格局在潜在影响;20世纪专业音乐教育对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与变迁的影响;研究者对音乐变迁的看法与局内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之间的差别;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一种蕴藏丰厚的文化资源对新一代中国作曲家所具有的特殊的标志意义等。
20世纪所发生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各种碰撞与交流,在深度、广度和速度等方面都是空前的。学堂乐歌运动将西方音乐引入了普通教育课堂,只用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西方音乐占据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以及专业创作和表演等领域的前沿阵地。刘勇(中国音乐学院)从传统音乐的本质和非本质方面、本质方面的稳定性和非本质方面的易变性的原因、变化与稳定的关系等“论中国传统音乐的易变性和稳定性”,阐述了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音乐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它的本质方面依然是稳定的观点。“易变”和“稳定”是传统传承和变迁中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将以具体的音乐形态和功能表现出来。田耀农(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论中国音乐在功能转化中的形态变迁”把中国音乐的功能概括为实用性和听赏性两大类,实用性音乐向听赏性音乐转化是按照由民间入宫廷、低俗化向高雅的方式实现音乐转型的变迁,而听赏性向实用性转化则相反。民间音乐和社会主流音乐互动共进所构成的螺旋式双向循环是中国音乐形态变迁的基本模式。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老传统和新传统的矛盾碰撞之中,杨红(中国音乐学院)认为,中国音乐要保持的是一种生命力的机体,更新的则是延续生命运动的表现,二者要统一。她“从民族器乐的发展谈起”,对民族器乐的创作意识的觉醒、创作样式的选择、器乐形式的拓展、表现形式的蜕变、传播行为的直面性传播方式的多媒性等进行了具体分析,论证了“中国音乐的老传统与新传统之变异”。
“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是音乐文化传承和变迁中常见,但又是复杂的现象。周吉(新疆艺术研究所)通过列举大量的乐器命名称谓,对“新疆各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现象”进行了论证,他指出,在我们对于某国家、地区、民族的音乐进行剖析、介绍和比较研究的时候,一定要以音乐文化的本体的实际为依据,而决不能仅凭乐器、乐象、乐曲的名称“望文生义”。乐器、乐象和乐曲的消失、产生和变迁是音乐文化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和规律,新疆是这样,蒙古也是这样。乌兰杰(中央民族大学)以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乐器口簧、草原游牧文化时期的乐器火不思、马头琴为例,提出“蒙古音乐时代风格变迁与乐器进化刍议”,“刍议”以蒙古人音乐审美意识的变化为纲,从新的视角审视了蒙古一些乐器兴衰绝迹的历史轨迹。毛继增(中央民族大学)根据自己多年对西藏“囊玛融汇其他民族艺术成分的艺术经验”,分析了囊玛的“融汇”表现在乐队构成、音乐风格和韵味的多姿多彩之中的汉族文化因素,总结了“化合而非混合、渐变而非突变”的音乐文化传承和变迁的现象在囊玛艺术中的体现,“化合而非混合”使外来艺术经过改造而融为自己的血肉机体,“渐变而非突变”在人们心理承受力的范围内不断演进,这就是囊玛音乐艺术吸引外来艺术成分的宝贵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走出了贫瘠,正朝着相对富裕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旅游业逐渐成为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同时也对这些地区的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桑德诺瓦(中央音乐学院)对“旅游开发对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了具体分析和归纳。旅游、商业、城市化的现代生活内容使得传统音乐的含义和功能发生了变化,李莘(中国音乐学院)考察了丽江城市纳西人的音乐生活状况,以及参照北京成立的纳西人的音乐生活情形,论述了“城市中的纳西人:音乐文化的适应与变异”,探讨了城市纳西人在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存、阐释和生产文化,以及文化与经济及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民间乐社与经济供养”是一个典型的音乐与经济关联的课题,张振涛(香港中文大学)以南高洛乐社为“田野”基地,对该社所保留的碑文中的有关集资、募捐、赞助等与演出有关的经济账目进行了调查、分析,从大量的账目数据充分反映了民间乐社与经济的关系。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花儿”的传承和变迁问题上,马玉宝(青海省音乐家协会)在“‘花儿’研究的基本问题”中指出,由于大众媒介的介入,“花儿”的原生状态的特征受到了损害,造成了“花儿”失去了地域特征、民族特征,以及丢失了原有的伦理传统,使之成为了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快餐”文化中的一种。
传统音乐的变迁和传承中体现出来的音乐文化经济化、商业化、城市化、大众媒介化,以及现代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因为音乐和社会从来都是紧密不可分离的。以音乐与社会为研究立足点20世纪音乐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当我们迎来了21世纪的时候,新世纪的音乐社会学的责任在哪里?曾遂今(中国音乐研究所)对“世纪之交:音乐社会学对象观念回顾与学术展望”进行了论述,他指出,20世纪音乐社会学表现为社会成因观、社会作用观和阿多诺的双重对象观,而在21世纪的历史时代里,音乐社会运动观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来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音乐社会学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社会音乐生产、社会音乐传播、社会音乐商品、社会音乐职业,而且也涉及社会音乐人文环境方面的问题。社会人文环境对音乐的传承和变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四位代表先后就古琴音乐如何在新的人文环境中的传承和变迁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社会人文环境对文人音乐音律观念的影响:从古琴徽位谈起”(李玫,中国音乐研究所)、“20世纪50年代以来琴乐文化的变迁:从古琴进入音乐学院说起”(杨春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人文环境的变迁对古琴音乐的影响:从20世纪后半叶的古琴音乐创作看古琴音乐文化的流向”(闫林红,中央音乐学院),以及“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对古琴传统传承方式的影响”(王建欣,天津音乐学院)分别从各个角度对环境与古琴音乐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也以古琴为立足点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符号的重建:理论、目的与方法”。人文环境对音乐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孙凡(武汉音乐学院)以道教音乐为例讨论了“现代人文环境中的‘十方韵’”是如何受到经济社会的影响,使得“十方韵”具有了某些商业化的倾向。佛教音乐的传承也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杨秋悦(中央音乐学院)对“梵呗《戒定真香》研究:从‘早晚课颂’看佛教音乐的中土化”,说明了在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特定的人文环境将直接影响到音乐的变迁和传承,而且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已经形成的汉化佛教音乐,可以探寻出佛教音乐创立者的初衷、历史中形成的仪轨、固定仪轨与音乐的关系,以及修持者对它的态度和审美体验。研究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变迁还体现在怎样理解国外的中国佛教音乐功能和含义,蔡璨煌(英国牛津大学)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提出“在英国的‘中国’佛教音乐是谁的?论研究音乐和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的论述不仅让人们从另一则面看到新的社会人文环境对传统音乐的传承、生态格局有着潜在的影响,而且更可能使我们对现有的研究方法及立场产生新的质疑,而这些质疑可能成为理论突破的关键。
历史传统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文环境的差异,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对传统音乐传承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有积极的因素,也会有消极的成分,这些因素和成分使得传统音乐的传承出现了多种形式。齐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徽州祠堂礼俗音乐研究”,她指出,在当前徽州的社会人文环境中,礼俗音乐仍然具有传承的可能性,只是其形态出现了多种变体,传承体系中也已打破了旧的格局。而且,王英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碰八板’研究”却表明,目前一方面由于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碰八板”这种民间乐种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
音乐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内容,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不同的。由于角度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音乐将呈现给我们许多不同的形象。中国在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世界各地的音乐也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变成跨国文化。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文化已经不是可以仅用“描述”就可以说明,而中国音乐历史也不能以单一的“语调”可以来讲解。因此林萃青(美国密执安大学)呼吁建立“21世纪跨国多语调的中国音乐史学”,以多价值、多方位、多层面的方式来研究中国音乐文化迫在眉睫。在民族音乐学中“局内人”和“局外人”就是音乐文化的多层面、多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余咏宇(香港城市大学)从“解构‘局内’和‘局外’——以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研究为例”对哭嫁及其相关音乐活动进行了社会和文化性质的考察。“局内/局外”与“主位/客位”是一组民族音乐学中一直被讨论的论题,洛秦(上海音乐学院)认为,这一组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同等对应关系来认识,而事实上两者是不同的。“主位/客位”所涉及的是研究者对实物和现象在认识观念上的不同角度,而“局内/局外”则是观察者的文化身份或具体文化立场上的不同角度。前者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不是辩证的,也不是相对的,而后者的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他作为“一位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看美国街头音乐活动”,提呈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尝试实例”。这个实例为中国学者从“客位”的角度和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研究美国音乐、社会和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历史之间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中,音乐传承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袁静芳(中央音乐学院)从对洞箫历史的回顾与社会运用功能以及组合形式的考察,“再探泉州南音历史源流”,从而对南音文化的特征提出了新的认识,即南音文化具有悠久的音乐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特征,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殊的音乐形态构架,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人类友谊的桥梁。音乐文化是人的文化,人创造了音乐和文化,人应该是音乐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项阳(中国音乐研究所)在研究音乐文化传承的问题上从“乐籍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着手,对历史上宫廷、军乐地方官府所属专业贱民乐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以乐籍制度下的乐人为主线,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乐户问题所引发的思考,将会对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各个承面的重新审视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音乐的研究是与会者所关注的论题之一,三位学者分别从“清代音乐研究回顾与展望”(罗明辉,香港中文大学)、“清代宫廷满洲乐舞及其礼乐观念”(刘桂腾,辽宁丹阳文化局)以及“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仁丹增班觉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嘉雍群培,中央民族大学)进行了讨论。
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将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对音乐本身的认识和理解问题。王小盾(上海师范大学)提出“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反映了礼乐制度、焦化功能对音乐的影响和制约,是中国音乐学史上最重要的观念。喻意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中国音乐是同文学共同生长起来的,文学史音乐的重要载体,以“释《通志》‘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论中国古代音乐中声与辞的一体关系”。
三、中国音乐与周边音乐文化的交流
该论题既触及到历史,也包含着当代;既论述中国音乐与亚洲各国音乐的交流与接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可以探究中国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渗透、演变。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汉朝就已经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唐朝,中日文化的交流到达了极盛。由于这种交流,唐朝对日本的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纳?中国音乐传到日本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日本是怎样吸收和同化当时强盛的中国音乐文化的?这些问题是代表们围绕该专题讨论的中心内容之一。王耀华(福建师范大学)“从琉球御座乐对中国音乐的受容看音乐文化传播中的‘不变’与‘变’”,文章以调弦变换的有力证据说明了琉球风格的《打花鼓之歌》与中国民歌《茉莉花》之间的相似性。唐朝音乐东渡日本是多方面的,周耘(武汉音乐学院)以三首日本佛教黄檗宗声明曲考察了“佛乐东渐及其日本化”现象。另一方面,日本化的现象也非常集中地体现在唐朝音乐机构东渡之后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中,赵维平(上海音乐学院)的论文“从日本初期音乐制度的形成看其对中国音乐的接纳方式——关于雅乐寮和内教坊”,从雅乐寮的成立和乐人的构成、中日的音乐制度与乐人的比较、日本内教坊的成立及其内容、唐教坊的形成及两国的音乐制度,以及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唐朝音乐制度日本化的文化接纳和迁移现象。陈克秀(山西大同艺术研究所)则以“有关唐、宋音乐东传的若干考索”为题,以谱字、律高和文献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唐、宋音乐东传日本的论题。音乐作为文化,它的交流、容纳都与其所接触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休戚相关,任何音乐形态上的变异,事实上是观念、意识的延伸和形式化。周显宝(厦门大学)从古代东方亚细亚形态的自然环境和人群分布、社会组织与经济结构、古代中日对礼乐文化创造性和选择性三个方面“试析古代中日音乐文化的社会学背景”。王樱芬(国立台湾大学)的研究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另一方面的例子,她从“日治时期日本音乐学者对于台湾音乐的调查研究——以田边尚雄及黑泽隆朝为例”的角度,记述了这两位日本音乐学者对台湾音乐在国际上的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田边尚雄及黑泽隆朝在战争年代日本政府经济危机的情形中前来研究台湾音乐,其真正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音乐,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
中国与朝鲜的音乐文化交流也是代表们讨论的内容之一。李来璋(吉林省艺术研究所)十多年来参与对中国吉林省境内朝鲜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注意到当地的乐人无论在理念意向上,还是实践运用中都依然承袭着朝鲜半岛李氏朝鲜以来的音乐理论思维,而这又导源于李氏朝鲜在全面接受和融合由中国传去的传统音乐及其理论之后所发生的演化和变迁。因此,他提出“关于李氏朝鲜以来的宫调研究(一)——兼与中国明清以来的宫调理论比较”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解唐代音乐文化传入朝鲜的状况,以及了解朝鲜接受和融合中国音乐文化的程度,林青华(香港浸会大学)对成书于15世纪末的朝鲜音乐巨著《乐学轨范》进行了研究,从“《乐学轨范》的中国音乐史料”来看“中朝音乐文化交流”。
中国音乐与周边音乐文化交流专题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相互接触、融合问题的探讨。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总结了“中国境内藏族音乐文化与周边民族之交流”,交流体现在藏族音乐对周边其他民族的影响和周边其他民族的音乐对藏族的影响,这种在民俗民间、宫廷和宗教三方面的相互“输出”和“输入”,说明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在相互接受和交流中形成的。包爱军(中央民族大学)就蒙古佛教音乐探讨了它与汉族佛教音乐之间的交融关系,提出“经箱乐——蒙、汉宗教音乐文化交流之产物”。民族之间的交融,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相互渗透中,而且在音乐中也能看到这样的交融渗透现象。蓝雪霏(福建师范大学)以“闽东畲族排歌调与桂西南壮族诗交调的比较研究——畲族音乐与西南相关民族音乐的关系一论”,说明了畲族音乐中的多种民族因素。怎样看待和理解“小传统”和“大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介入点。杨民康(香港中文大学)以这一角度,同时从宗教文化的核心、基础和外围三个层次的文化分析模式,采用泼水节、安居节等宗教节庆仪式音乐的具体实例,探讨了“‘本土化’和‘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
香港学者论文的独特角度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兴趣和关注,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关燕儿“从古代乐妓观念看官方及民间史料应用”对大陆文工团团员的角色所涉及的古今音乐舞蹈表演者的社会角色问题进行了讨论,戴淑茵从“集体创作的粤剧《再世红梅记》”探讨了香港粤剧既具有商业化特征,也在保持传统的同时逐渐西化,结合电影和话剧的形态,与本地文化融为一体;余少华论及了香港音乐虽然以西洋文化为主体,但是不少流行文化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中国音乐的元素的现象,他“从四个港产《梁祝》版本看大陆文化在香港的本土化”中提出,在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关系之间,香港并不着意传承过程中的内容的准确性,但是在国际化、本土化及大陆化三者之间却不时地跳出了原型的藩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求存的手段,从而造就了本身文化及身份的特征。白得云(香港演艺学院)从新的音乐文化价值以及变迁中的组织机构几方面,提出了“从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观念和演出场合的变迁看现代民族乐团的发展”。
四、音乐教育
该论题当以20世纪已经形成的几种音乐教育体制与教学模式(如大陆、香港、台湾的不同教育体制以及音乐学院、师范学院和普通学校的不同教学模式)为对象,对各自的成败、得失的历史现状进行比较和研究检讨;其中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在现行音乐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及其教学方式。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推进中国音乐教育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音乐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泛,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剖析普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及其理论体系,提出我们需要结合当今全球文化发展和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作整体考虑,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建立中国传统音乐、世界音乐与文化学科的课程体系。什么是音乐艺术?它作为音乐基础教育的教习对象到底包含那些基本内容?伍国栋(中国艺术研究院)就以上的问题从三方面提出了“音乐基础教育的文化层面定位”的论述。这三个文化层面包括音乐技能、音乐史论和音乐品评,他阐述了音乐基础教育和培训中畸形地注重音乐技能操作而忽略音乐文化内容和音乐体验的片面性和潜在危机,指出这种培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若干负面影响,塑造修养全面的既能掌握音乐技能又有较高文理学识的音乐人才将是新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
乐理教学中存在的偏颇是中国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之一,重视西乐忽视中国传统乐学理论的现象非常严重。童忠良(武汉音乐学院)从音级与音体系、调式主音与音阶主音、正声相同与正声易位、之调式与为调式几个方面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论中国音乐研究与普通乐理教学——兼论中国传统音乐在现行音乐教育中应有的地位”。
重视学校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已经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主体性、基础性和开放性,这三方面的特征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以这三方面为立足点,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讨论了“(大陆)学交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政治化、技术化、审美化以及尚未建立的作为文化传承的音乐教育的主导学校音乐教育的几种观念,其次提倡了学校音乐教育应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民族音乐文化应以音乐教育为基础的认识观,最后提出了以民族音乐为基础构建学校音乐教育的系统工程。音乐现象就是音乐教育制度的直接反映。欧光勋(国立台南艺术学院)“从人文、传统、作品、演奏等面相看音乐教育体制下的中国音乐”,他指出音乐教育体系所面临的中国音乐在人文、传统、作品和演奏中呈现的问题,有的是台湾独有的,有的是海峡两岸共同面临的。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双方对中国音乐的“主体性”进行深入了解。从广义上来说,音乐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人的素质以及认识音乐的本质,以学习音乐的理论和体验音乐的感受来理解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然而,台湾的“音乐资赋优异”教育制度的价值究竟如何?赵琴(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以大量的考察材料和数据对“台湾音乐资赋优异教育的发展与现况反思”,她提倡音乐教育的改革应该从观念的改革做起,音乐教育的观念应该从培养少数音乐天才,转向“音乐应该属于每个人”的全民音乐素质的提高,从注重记忆的传授,转向艺术审美教育,这将是21世纪台湾音乐教育刻不容缓的决策。
会议除了以上四大议题的正式讨论,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工作坊讨论,与会者对各项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进一步的交流。在最后的总结会上,代表们一致表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所涉及的问题之广,学术层次之高是多年来中国音乐学研讨活动中不多见的,它将对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走向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