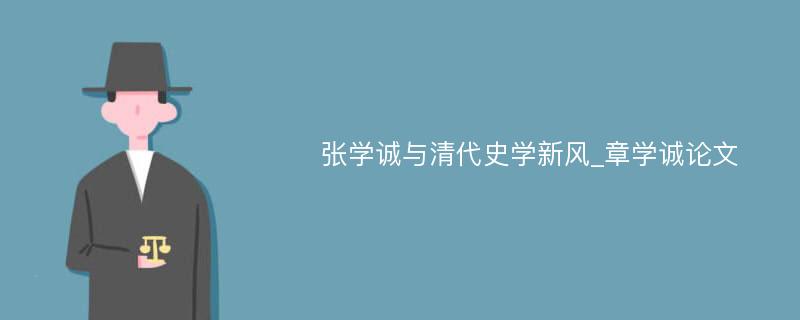
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史学论文,新风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4)02-0071-05
中国封建史学行经清乾隆、嘉庆时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考据大潮。考据之风席卷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学、历算学、金石学、舆地学等各个学科,成为整个学界的主潮。风气所趋,不用说读书人“竞为考订”,就连清室帝王、达官显宦甚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摇头晃脑地跟着学者们说几句考证的“行话”。
面对汹涌的考据潮,章学诚(1738~1801)不畏同行“隐恨”和谩骂,独立潮头,大声疾呼:“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1]。在给考据学大师钱大昕的信中,更是一针见血地说:“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2]。在章学诚看来,考据学风最大的流弊是脱离现实,专事训诂,“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如此学风,禁锢了学人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见,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使向来为安邦治国服务的史学成了“竹头木屑之伪学”[4],完全背离了史学经世之要旨。
章学诚出于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在呼唤学人奋起挽救学风的同时,自己不惜“乖时人好恶”、“逆于时趋”,以“六经皆史”为纲领,以“史学经世”为宗旨,向主宰学界的考据学风发起挑战,对考据学的观点、内容、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抨击。在毫不妥协的批判过程中,建构了以“史学经世”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体系,最后结撰成体现他全部学术思想和史学价值观的《文史通义》一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其史学理论,对史学经世思想的复兴,对清朝中、后期的启蒙思想家之变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5]
(一)
公正地说,清乾嘉年间盛行的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学术地位。许多考据学家凭借深厚的考据功底,在对古籍辨别真伪、校勘讹误、注疏训诂、补辑遗阙、订正史实、考镜典制、整齐故事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后人阅读、研究古籍扫清了许多障碍。对此,章学诚是清楚的,他严厉斥责全盘否定考据学的袁枚为“丧心病狂”[6]就是佐证。所以,章学诚批判考据学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针对繁琐考据学风给学术和社会造成的流弊。细察其锋芒所向,是多方面的,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端:
第一、尊经抑史。自西汉以降,经史分野始泾渭分明。至宋明时期,理学家崇尚心性义理,纷言“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更甚者诬读史人是“玩物丧志”,结果使“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当清考据学风盛行后,尊经俨然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史学庶几无人问津了。正如江藩所言:“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之下茫然不知”[8]。
面对如此尊经抑史的文化传统和严重现实,对酷爱史学、深谙史学经世功能的章学诚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六经皆史”,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上》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的这一学术心声。此绝非感情用事,也不是要以史抑经,而是旨在去除人为地给经书涂上的神圣光环,使人重新认识经书亦是史书的本质属性,和史学一样发挥经世作用。这一思想贯穿于章学诚一生的学术探索和学术批判之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致孙渊如的信中,他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9]继之,他花费四年左右时间,撰写了《经解》、《原道》、《史释》、《易教》诸篇,深入、系统地阐释六经本是“先王政典”的基本特征,诸如:“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0]。“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11],“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伦为世法耳”[12],等等。
很显然,在他眼里,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其是先王的“政典”,而这些政典是用以“经纬世宙”的。六经开始被称为经,并非尊称,不过是“义取经伦为世法耳”,故六经的根本价值在于“经世”。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至嘉庆五年(1800),即章学诚辞世的前一年,撰成《浙东学术》篇,他推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宏论。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3]离开现实去谈古代,离开人事而空谈义理,只是空言著述,绝达不到经世的目的。作为学者不懂这个道理,就不配谈史学。这辛辣的嘲讽表明了章学诚对脱离现实、专事训诂的考据学风和那些考据学家强烈的愤慨。
章学诚还从学术源流上详加论述“史之起源,实先于经”、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等观点,对批判考据学派尊经抑史的错误倾向也收到积极效果。
第二、“舍今求古”。这是乾嘉考据学又一突出弊病,自然也是章学诚着力抨击之点。
由于乾嘉时期文网甚密,读书人为保全性命,便远离现实,“舍今而求古”,埋头于三代、秦、汉的故纸堆中,“唯汉是尊”,“唯古是信”。久而久之,学者们无不“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14],这是章学诚极力反对的。他认为,学者们应该知古,但更应该知今,否则,对古籍即使考据得“极精能”,也毫无实际用处。他说:“君子苟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为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15]由此可见,在章学诚眼里,真正的学者必须研究现实,懂得当代典章制度。因为“涉世之文,不比杜门著述,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斯庶几矣”[16]。只有懂得现实,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章学诚在批判“舍今求古”的学术倾向时,还特别强调学术界不该盲目好古,而是通过总结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探求古今殊异的内在原因。他在《说林》篇中说:“所为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17]倡言好古者要从古今历史“因革异同”中寻找原因,总结内在规律,这要比一味好古高明得多。章学诚还进一步指出,那些一味模仿古代和炫耀博古的学者,实质上是忘记了身处的时代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18]。强调学者研究要同身处的时代紧密联系,这在封建史家中实属凤毛鳞角!
章学诚批判考据学派“舍今求古”的学风,力主学术研究要关切“当代典章”、“人伦日用”、“官司掌故”、“因革异同”等,这是他“六经皆史”、“经世致用”学术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遏止考据学风的重要举措。
第三、“皆非史学”。原来乾嘉时期多数学者主要精力是放在考订解释经学上。自钱大昕开拓了考史领域后,一时间,辨证古史之风蔚为大观。代表性成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同时,清统治者为笼络读书人,从清初就下诏开设史馆编修明史及其他史书,到乾隆朝更成就煌煌,先后修成《清实录》、《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著作在章学诚看来,“皆非史学”。他认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9]。他对当时备受尊崇的王应麟所著诸书的批判说得尤为明白:“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20]不仅如此,他还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认为自“唐宋至今”也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21]
章学诚将钱大昕等史家考史之作、史馆编修的长篇巨著及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通通视为“撰辑”,而非“著述”,这是对乾嘉史学和传统学术史空前的挑战。那么,在他眼中到底什么是史学呢?章学诚认为,“史学”的根本之点是具有“史义”(亦称“史意”)。他再三强调“作史贵知其意”[22]、“史所贵者义也”[23]。“义”是什么呢?即“史家著述之微旨”[24]。就是说,史家修史时,不仅记述史事,更重要的是以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揭示史事的本质,总结其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说”。书成后,“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5],这样的史书才具有“史意”,才可称之为“著述”。这样的著述,才是他所说的“史学”。有如此观点,在乾嘉时代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有人认为,章学诚做学问之道同前人刘知几相似,但章学诚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司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6]从这段话看,不要说“撰辑”不算“著述”,就连“史法”也不足以为“著述”,惟具“史意”之作,才称得起“著述”。
章学诚把史学成果分为“著述”和“纂辑”两大类,认为著述是独断之学,纂辑是考索之功;著述是一家之言,纂辑只是排比史料。把“著述”和“纂辑”严加区别,这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对当时学风的拨乱反正和长远的学术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当时考据学家把考据学吹得天花乱坠,倡言考据是做学问的“极则”,考索之功“足尽天地之能事”。在如此学术价值观的胁迫下,读书人“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27]。很明显,这种史学价值观是错误的。如得不到纠正,历史学就不会有创新和发展,就会失去其根本价值——经世功能,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沉湎于故纸堆中的“死学”。在如此恶劣的学术倾向严重摧残史学,阻碍其繁荣和发展之时,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超人才识针锋相对地直斥考据家们疲精劳神所取得的成果只是“纂辑”,不是“著述”,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这对史学界破除束缚,解放思想,对史学的走向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当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空谈性天”。乾嘉时代,宋学失去昔日的辉煌,汉学成为学界主潮。正如姚莹所说:读书人“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28]。尽管如此,坐而论道、空谈义理的流毒还在。所以,章学诚在鞭挞汉学的同时,对“空谈性天”的宋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言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9]章学诚批判宋学,不是不要义理,只是反对宋学家们脱离实际空言义理,“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30]。离开“经纬世宙”、“日用伦常”而高谈道德文章,背离了“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六经要旨,对这样的空头义理,章学诚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主张“义理参之于时势”,“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31]。章学诚一面批繁琐的汉学,一面批空疏的宋学,双管齐下,对肃清理学家们“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等说教的影响,对于提高史学地位,构建史与论结合的新史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章学诚以超人的学术勇气在批判汉学之繁琐、宋学之空谈的同时,以“六经皆史”、“史学经世”为宗旨,在系统清理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建构了新的史学体系,为走进死胡同的乾嘉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章学诚鉴于“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的流弊,大胆提出了“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的意见。所谓“无例之始”,就象《尚书》那样,“因事命篇,本无成法”。章学诚基于这样的主张,矢志“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其“规模”是以纪传为主,以图表为辅,而传则为包括典章制度、人物、言论、文章在内的新的史书体裁。
章学诚的史学抱负没有“载诸空言”,而在两个方面得以充分展现:
第一、花费毕生心血结撰成《文史通义》。该书是他“六经皆史”、“史学经世”、“著史贵知其义”、“义理参之于时势”、“具史识必知史德”、“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等著名史学理论的生动实践,是他对传统史学校雠得失、“斟酌艺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成果。总之,这是一部博大精深、“贵知史意”的史学理论著作,对遏制脱离现实的考据学,对廓清传统学术之得失,对推动清代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空前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33]。
第二、编修方志。这是章学诚史学理论最为精采的体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甚多,兹不赘述。简言之,章学诚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当首推论定方志的性质是历史而非地理,即“志乃史体”[34]。其次,规定志书内容应以历史文献为主。再次,论说志书体例宜立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在机构上建议设立志科。以上诸点,都是开创性的。
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和修志主张的指导下进行了修志实践。他除参与制定两湖麻城、常德、荆州等志书的体例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35]。最能体现他史学理论思想的为其最后编修的《湖北通志》,该志书体法精当,含有纪、图、表、考、政略、列传,还附有掌故、文征、丛谈等。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特别是他的修志实践,为中国方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践样板。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36]当非溢美之词。
(三)
在考据学风风靡乾嘉时期整个学界的时候,章学诚不以风气为重轻,独树一帜,向当时学界主潮发起挑战,并按自己的史学理论观点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史学实践,为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最后一部杰出的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及几种开创性的志书。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造就了这位“独胆英雄”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这里试作一分析,看来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深悉社会现实。章学诚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当是时,朝廷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可以说,在“盛世”背后,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章学诚“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于民生吏治,闻见颇真”[37]。就是说,他于谋生的奔波之中,对社会有了深深的了解,他的《上执政论时务书》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说:“近年以来,内患莫甚于蒙蔽,外患莫大于教匪,事虽二致,理实相因。……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盖事虽分三,寻原本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故但以吏治为急,而二者可以抵掌定也。”[38]他特别是对整个官吏队伍狼狈为奸、“上下相蒙”、“蠹国殃民”,致使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官逼民反”等社会问题揭露得淋漓尽致。此足见章学诚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有比较全面、真切的了解,这是坐在“四库馆”、“三通馆”的考据学家们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不能不对完全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提出尖锐的批判,不能不为史学发挥其“经世”的本质功能呼号呐喊,使之能为治国安邦服务。应该说,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了解,是章学诚挑战考据学,开创新史学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第二、承继浙东史学。任何杰出人物贡献给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少许属于原创,多数是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同样,章学诚的史学经世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是承继浙东史学而英勇前行的。章学诚生长在浙东,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浙东学派的开山鼻祖黄宗羲鉴于明亡之故力倡读史:“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39]继黄宗羲之后,浙东学派还有万斯同、全祖望等著名学者,他们都是主张史学经世的。作为这一学派的殿军人物的章学诚,极为推崇黄宗羲“以史学经济学”的治学宗旨,盛赞“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的治学风气。浙东史学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强调讲天人性命同讲历史事实相结合,这些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形成曾产生重大影响当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浙东史学是章学诚史学主张的学术渊源。
第三、明辨器道关系。关于器与道的关系,在封建社会的学人之间争议颇多。一些人认为,“道”先于“器”,即“道先天地而生”。而章学诚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认为先有“器”,后有“道”,即没有世上的万事万物,也就不会有反映这些事物的“道”。器与道二者关系密切,“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只有对事物进行具体的研究,才能得知推动事物发展的“道”,即章学诚所强调的“即器以言道”。他说:“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40]更可贵的是,章学诚不仅认识到物质是第一位的,而且认识到社会按一定规律向前运行,其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即使是“圣人”也无能为力。他说:“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41]。章学诚在强调“物”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见物不见人,时时充满人文精神。在《原道上》篇中,有这样一段精采的话语:“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行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42]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态势,而且强调人在改造世界、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强调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社会实践,其治国之“道”,才能彰明昭著,治国之制度才能日臻完善。章学诚基于这样的器道观和社会发展观,认为严重脱离历史发展实际的汉学家和宋学家“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43],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即器以明道”。很明显,正确的器道观和社会发展观是他挑战学界主潮的锐利武器,是他弘扬“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等主张的学术基石。
总而言之,章学诚之所以能勇立潮头,独树一帜,不妥协地向当时学界主潮考据学风挑战,与其说是因他具有酷爱史学之天赋,勿宁说是他深悉社会现实、承继浙东史学、明辨器道关系这三个因素起了根本作用。就是说,是社会、学术、认识三大根源造就了这位有胆有识的个性化的史学理论家,这三大根源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他的史学理论和新史学体系。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把它提出来,当与不当,切望引起同行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整个中国学术史证明,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常常泛起一波又一波的风潮,而且,有许多是学人容易识别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的恶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像章学诚那样始终坚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和信念,对错误的潮流进行针锋相对的学术批判,在批判中去开创新的理论和构建新的学术体系呢?学术史证明,只有不跟风、不媚俗、不怕讥讽谩骂、不怕穷困潦倒,决心为学术、为真理奉献一切,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上的巨人,为他所倾心的事业做出不朽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