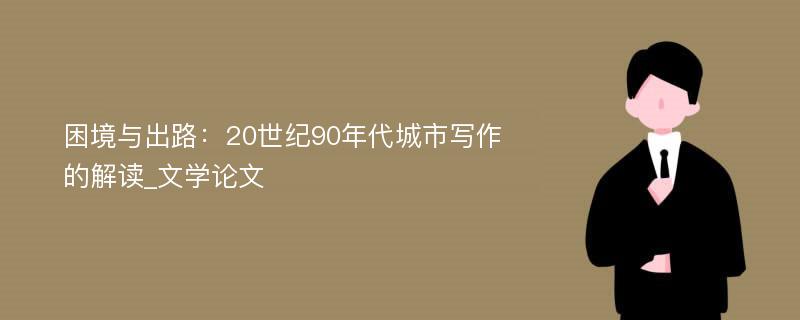
困境与出路——20世纪90年代城市写作的一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毫无疑问,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已经取代乡村成为代表中国现实的中心舞台。当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形态逐渐失去代表性地位时,文学随之出现了意味深长的转折。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城市文化的重铸和改造,城市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的主流开始呈现其自身的特色。就当下文学杂志来说,所刊登的小说至少有70%以上是城市题材作品,而90年代走上文坛的“新生代”和“70年代出生作家”,差不多清一色地全是以城市为写作对象,如邱华栋之于北京,张欣之于广州,何顿之于长沙,卫慧之于上海,一座座现代化大城市在作家笔下气象渐成、品格渐显。城市化进程中嘈杂纷乱的文化经验和欲望体验成了他们的创作源泉和叙事目标,90年代迅速变化的消费社会的现实景观成为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写作资源。在对城市小说进行客观分析之后,应该承认,90年代城市作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们提供的种种生存表象涵盖了90年代最本质的商业特征,并进而构成了物化时代城市文化景观最具特色的一面。特别是,他们以对城市生存的体认切入当下现实,使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走出了先锋派文本实验的迷宫,获得了再度繁荣的勇气和力量。
但是,在充分肯定城市小说创作实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和文本的局限。即,在迄今为止的大量以“城市”为叙事源头和归宿的作品中,除了极少数涉及较深刻的主题外(如存在、异化等),大部分描写还只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出现真正称得上是直逼城市灵魂,给人深刻心灵震撼的力作(即使是那些貌似深刻的主题也并不是新鲜独创的,早在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中,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对城市的物化以及城市人的异化等都作过描写)。在大面积的城市生活表象的包围中,作家常常盲目地认同并迎合现实生活中各种庸俗的价值观,或者干脆退守到自身狭隘的生活空间,书写各种隐秘的欲望场景。在这种陷阱式的写作中,我们看到,城市作家已无法摆脱日趋狭窄的精神视野,无法逃离日渐匮乏的叙事资源,更难以开启对城市生活本质的思考。在对前期的城市小说创作加以回味时,我们的阅读感觉是由于缺乏题材的开拓与艺术上的创新,那些曾经给人新鲜质感的作品越来越乏味;那些一度以“闯入者”姿态冲击文坛,给创作带来活力的“新生代”——作为90年代城市作家的主力军——如今已经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原有的文本模式,甚至出现作家之间的雷同现象。粗浅的叙事手段和雷同的创作理念使得他们的小说无论语言风格如何殊异却始终给人以气味相投的感觉。这样的文本更多地具有现象认知的意义,而难以承担思想提升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回顾这些文本,仍能肯定其为我们提供了转型初期城市生活的掠影的价值,却不再为阅读初期的惊异而欣喜。因为仅就“现象”而言,已随时间推移消失的部分或是已司空见惯的部分都无法再震撼我们——假如这种“现象”不再经发掘而深入到我们永恒的人性深处。
表面上,这种状态的出现似乎预示了作家创作潜力的枯竭,但当我们深究下去,就不难发现,外因是转型期读者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新景的隐形阅读期待与获知要求,内因则是叙述主体对于欲望化表象的亲历与热衷,根源在于创作主体价值判断的暧昧与小说观念的模糊。90年代作家比任何前代作家更深切地体味着欲望的张扬,更彻底地拒绝宏大叙事,消解城市生活的精神性价值,进而放弃了对形而上意义的追寻和探索。文学也由此充当了世俗生活谦卑的秘书,被欲望化的生活表象牵着鼻子忙不迭地一路狂奔。如此一来,城市书写的扩展乃至泛滥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小说世俗化趋势愈演愈烈的精神症候。这种令人担忧的精神症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世纪末城市写作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它对于文学在未来的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
实际上,90年代城市作家并不缺乏抵达深刻的能力,就意念来说,他们对城市文化、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其实已经具备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在目前,这些东西在他们的作品中,通常只作为感觉闪现于字里行间,没有成为贯穿作品情节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富于逻辑性的叙述力量,“意义”、“精神”等小说特质也随之成为被放逐的东西。棉棉曾明确表示:“我说在接近本世纪末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麦当劳,并且我要做到任何人看完我的作品都不需要再去看第二遍。”(注:棉棉:《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长春〕《作家》1998年第3期。)其实,面对日趋浮泛平庸、缺乏激情与想像的精神现场,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执着于意义的探询和理想的建构,而是选择虚浮平庸、毫无深度和力度的精神生活,因为他们觉得在一个信仰崩溃、理想破灭的时代,批判和否定大众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任何试图建构价值体系的行为更是枉费心机,只有物质性的实力原则才能引人注意,也只有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日常审美经验博取阅读市场,才能为作品的存在和作家的物质利益打通生存之路。就像海因兹·迪特里齐描述的那样,面对人类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之势,在欲望化的现实中变得尤为剧烈,特别是面对权力意志和物质利益的双重争夺,“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注: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一)》,〔北京〕《读书》2002年第5期。)。它导致的后果,便如葛兰西所说的,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注: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二)》,〔北京〕《读书》2002年第6期。)。这种毫无独立发现的、浅陋的精神征象,在艺术上的直接表现,便是本雅明所反复强调的机械复制时代的一些艺术特征——尽管它也有一些新奇的形式,但是,在本质上却丧失了艺术应有的内在“光韵”。“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注: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182页。)这种毫无创造的复制行为最终使艺术丧失了其特有的“膜拜价值”,而只留下“展示价值”。这种状态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作家不断采用重复的写实性话语,复制各种欲望化的现实生存景象,复制躯体感官的享乐经验,复制时尚化的生活标签,使小说与生活的距离不断地缩小,乃至取消。最终,写作成为与大众传媒、娱乐市场和个人休闲具有同等意义的日常生活方式,它们彼此印证、相互模仿,构成了鲍德里亚命名的“超级现实”。在超级现实中,真实被淘空了,只剩下影像间的虚假模仿与复制。作家们交出的也只是现实场景的“仿真”复制品。
这种沉溺于表象,放弃意义追问的做法无疑是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明显加强。表面上它是市场化经济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但是,更深层面的后现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入侵,包括从生活观念到思想观念,乃至小到审美观念的迅速蜕变,已经成为改变中国文学界的根本动力。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看作一个平面化世界,把人当作零乱化的主体,因而不再相信世界的本质、规律和深度,也不再相信人的完整性。“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无论如何,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注: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之路》,柳鸣九主编《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与这种世界观相联系的便是消费主义、游戏主义、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和以颠覆价值、消解意义、不确定叙述、拼贴等为特征的文学观。正如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的:“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世,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第69页。)就文学领域而言,“它是一种自由无度的、‘破坏性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表演性的文学,一种活动经历的文学。它所醉心的是语言文字的操作游戏,全然不顾作品有无意义,或者干脆就是反意义、反解释,甚至反形式、反美学的。”(注:王宁:《走向后现代主义·译后记》,佛克马著《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它使文学不断朝着两个新的极致方向发展:“一极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迈进,对传统文学和现代经典的反叛更为激烈;另一极则面对整个商品化的社会,朝着通俗和亚文化的方向迈进,历史和虚构的界限被打破,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也趋向综合,小说和非小说相互混合,甚至加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因素。”(注:王宁:《走向后现代主义·译后记》,佛克马著《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而后一种方向却有着深刻的媚俗性,是后现代主义在取消精神深度之后的一种波普式的努力,也是它利用互文性制造出来的、以迎合大众时尚为目标的审美快餐。也就是说,这种无序的后现代思潮,实际上也为表象化写作提供了一种看似合理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注解。对此,佛克马曾明确地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代码可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相联系,这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所有西方世界是常见的。文学上对无选择性的偏好与丰裕的生活条件所提供的某种‘选择的困扰’是相符的,这使得不少人可以有多种选择。后现代主义对想象的诉诸在伊凡·戴尼索维克的世界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不适应的。可以从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中引出中国的一则谚语,即‘画饼充饥’。然而,在中国语言的代码中,这一短语却有着强烈的否定性含义。鉴于此因或其他因素,在中国赞同性地接受后现代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注:佛克马:《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可惜的是,佛克马的提醒并没有引起作家们的关注。
于是,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流风遍及的时代,城市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非深度模式”写作思潮的影响。他们用个人化的叙述书写当下社会的生活状态,用直观的经验化意识构造小说情节。经验的雷同使小说变成了一部都市欲望的复印机,将不断流淌的城市经验和庸常的现实生活复制下来,一览无余、事无巨细地放大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工商业文明冲击下的城市的堕落与狂欢。可以说,90年代城市小说对城市生存的镜像式书写,构成了一幅逼真的商品拜物教与消费至上主义的时代全景图。詹明信认为“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的表面感,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0页。)“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第69页。)无论痛感与快感都属于现在的、暂时的、稍纵即逝的,90年代城市小说就类似这种情况。“……在表面多元化的掩盖下,文学的本质却愈来愈向‘后现代文化’设置的单一物质化的理论陷阱坠落。可以说,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家们正努力批判与克服的种种‘后现代文学’的弊端却毫无保留地出现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的媚俗化、商品化、感官化、物欲化、非智化、非诗化、唯丑化、唯恶化……凡此种种,正预示着中国文学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的框架中,超前预支了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弊端。”(注: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北京〕《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事实上,近年来的城市小说创作之所以始终难以出现突破性进展,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家们对后现代的文化陷阱缺乏必要的警惕,以至于在各种流行思潮的引诱下,浪费了大量的叙事才情和艺术智性。
三
任何时代的写作,都会布满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关键在于,作家如何保持清醒的意识,时刻发现并认识到这些陷阱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创作可能构成的潜在性威胁,从而自觉地规避这些陷阱,使创作沿着认定的审美理想发展。就90年代城市写作而言,作家们怎样才能跨越表象书写的陷阱,最终摆脱所面临的叙事危机呢?
首先,重建作家的主体意识。
关于当代作家的主体意识,有人这样描述:当代作家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主体意识,过去以革命的名义被剥夺的,现在以金钱的名义又被剥夺了。——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作家们是以唯政治的功利来指导创作,那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这股无形的力量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城市人主体性的被剥夺在以精神产品创造为职业的文化人那里感受得最强烈。早在80年代,作家的主体意识就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在当时的城市小说中,文化人作为新思想的代表者,往往表现出与传统思维的对抗,以及在对抗中不被世人理解的痛苦和困惑(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然而到了90年代,这种外在的对抗转化成自身的迷惘,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价值评判的迷失,表现为由于生活目标的虚幻而导致的荒诞感(邱华栋《午夜狂奔》、朱文《尖锐之秋》)。他们与其说是城市物质生活中的浪子,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漂泊者,即使居有定所,衣食有着,可心灵仍然寂寞地踯躅在城市的街头。特别是在物化情感的重压下,他们常常借用一些非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存在:回避深刻,躲避崇高,强调人面对困境的尴尬与无奈……邱华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他笔下的“拉斯蒂涅式”的青年,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每时每刻都感受着自我放逐的苦痛。在城市社会,个体的人被淹没在物欲洪流中,作家们注意到了城市人主体性的丧失,但在目前的状态下,他们还没有为城市人、同时也为自己找到精神定位的坐标。就像李洁非说的:“出于迷惘、困惑和对未来的渺茫心情,‘新生代’很难去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深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和遥远的字眼,就其精神现实而言,他们只能呆在平面化的状态里,平面化地处理创作和其中的人物。”(注:李洁非:《陌生的都市,成长的人》,〔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9抨第1期。)这是对新生代再准确不过的评价了。艾布拉姆斯曾将作家的心灵比喻为灯,灯可以照亮世界,照亮人生,构成一个文学世界。对小说家来说,只有敏感而细致的心灵,才能于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品味出人生的滋味,发现存在的底蕴,才能在习以为常的生活表面之下发现恒久的意味。可是在这个物化时代,物的挤压使人的主体意识降到了最低点,作家不再是非凡的创始者和主流话语的代言人,他们与普通大众一样,内心充满了困惑、焦灼及难以言传的无所适从,就像邱华栋说的:“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干什么都是社会的填充物罢了,作家也一样。”(注: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这种情况下,作家们自然远离主体原则和价值立场,或多或少地迎合大众心理,顺应文化消费潮流,制作有畅销书风格的文化快餐,以期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新生代对物质的占有激情和对欲望的迷恋心态超过了任何前辈作家,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已经完全被对商业社会流行心态的赞同态度所取代。90年代城市写作的困境,实际上也是城市作家主体性丧失的表现。
其次,重塑作家的虚构意识。
不可否认,90年代城市作家的作品具备良好的可读性,他们放弃了先锋作家对形式技巧的迷恋,转而追求一种朴素的与日常生活同步而行的叙事方式,强烈的现实意味和浓厚的时代气息不断召唤起阅读者对小说文本的最为直接的审美经验。这种叙事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拓展了小说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也防止了其滑向形式极端的可能性。其次,城市作家还注意吸纳畅销小说的元素,句式和情节构思趋向日常化,注意用新奇的物象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90年代城市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现实生活的逼似,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城市生活的真实图景,感受到现世生活的浓厚气息。然而,小说并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复写,不仅仅是如柏拉图所说是对生活举起的一面镜子。W·C·布斯说过:“每种艺术都只有在追求自己的独特前景时,它才能繁荣”(注: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第136页。),而“一旦艺术与现实的缝隙完全弥合,艺术就将毁灭”(注: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第136页。)。虽然小说作为一种世俗性艺术,它有着天然的形而下的表现形态,但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形而下的表现形态与形而上的思想内蕴的完美结合的艺术品。小说之所以有存在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的世界,另一种思想向度,诗性的观照立场。在本质上,小说是超越性的,它应该瓦解庸俗沉闷的现实人生,使之呈现被无情的现实所扼杀的意义,完成对人类理想精神的最高综合。小说总要超越现实生活故事,这是小说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小说区别于故事产生艺术魅力的源泉。所谓的思情寓意正是小说“说”的另一表述。这就要求作家充分调动自身的虚构意识,来表达小说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向度和价值意义。于是读者在阅读时除了获得现实生活场景和作者叙述的故事外,还能体悟到一种永久的“意味”。90年代城市作家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忽略了虚构精神对小说写作的重要性,或者干脆将虚构意识消解于对生活外部形态的铺叙之中。小说文本成了表象的罗列与细节的堆积,艺术创造成了僵化的重复。我们很难找到有深刻内蕴,在故事表层下寄寓着思想力量的作品,更很难看到所谓的“精神的最高综合”,意义的失落与语言的变质几乎成了90年代城市小说在劫难逃的宿命。正如陈晓明所言:“九十年代这些新的艺术经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最首要的不足在于艺术作品普遍缺乏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识。”(注: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可以肯定地说,物质主义的平面化写作在以低迷的姿态逼近城市生活的表象并且心甘情愿地认同城市生活平庸的法则时,城市生活不但没有激发作家的想象力,反倒变成了难以跨越的叙事陷阱,使小说彻底丧失了超越生活的精神向度、价值立场和批判态度,随之而来的便是作家正在失去对生活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书写越是贴近现实却仿佛离现实越远,在无原则的认同和妥协中,小说日渐丧失艺术品性,既不能显示精神的力量,又无法让人寻找到真正需要的东西。它消逝的不仅是它作为艺术的“形式”,更是内在精神。
强调作家主体的虚构意识,目的不在于显示虚构与写实的界限,而在于说明小说叙述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小说对于可能世界的构建和描绘的能力。当然,创作主体的虚构意识并不是一种绝对脱离客体的空泛状态,真实生活构成了小说家和读者的经验世界,虚构则是在经验世界之上的改造与变形,或者说是经验世界被创作主体心灵折射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叙述”必须与“本事”紧密相联,按“本事”提供的法则进行,否则“叙述”可能会走向虚假而导致创作失败。
有人说90年代“是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性的时代,一个美妙的‘时装化’的时代,一个彻底表象化的时代。”(注:陈晓明:《先锋派之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3期。)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道理,可是我们认为,在如今这个丧失深度的年代里产生深度并非不可能,相反,正因为深度的缺失,才显出它的可贵;越是在没有形成内在性的环境里,内在性才越有价值,才越可能成为积极的内在性,人类不可能在意义匮乏的平面上长期生存。对90年代城市小说的“非深度模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价值遁入历史盲点的“文化逆转”现象,而不是最后的精神归宿。这个文化失范、价值无序的年代,更需要一种精神价值来解释和支持生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代大众传媒与高科技主义已经被历史证明无法给出一种深刻有力的精神价值,相反的,它们倒是使原有的价值体系变得混乱不堪。唯其如此,走出平面模式,重建文学的精神向度,倾听灵魂在欲望挤压下发出的种种声音,发现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而付出的真诚努力,并以批判的态度介入现实生活,就成了文学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学自我拯救走出精神危机的安全通道。近年来,西方学者不断指出“后现代主义正在走向终结”,他们正在倡导返回历史的“新历史主义”,这是一种走出平面,重获深度的努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告别20世纪之时重新进行价值选择和精神定位,回到自我,回到存在,回到人类的内心生活,回到被欲望遮蔽的精神地带,去展示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表述人类存在的真实伤痛,让文学成为人类诗意地栖居大地的最后一个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