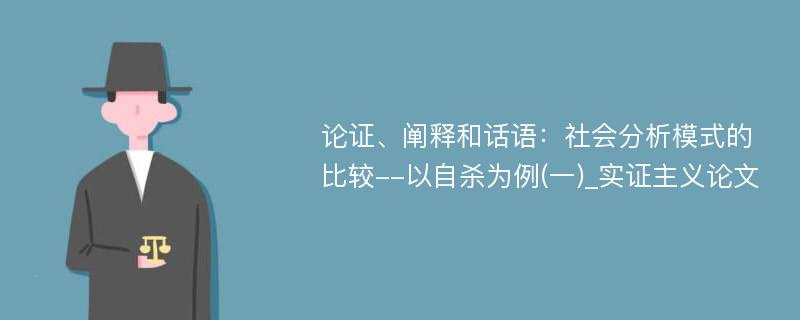
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为例论文,话语论文,现象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走向“多元话语分析”》一文中,[1] (PP1-53)笔者曾经概括和引申出了一种被称为“多元话语分析”的社会研究模式。本文拟以自杀现象的研究,将多元话语分析与现代主义社会学传统中的实证分析、诠释分析模式进行比较,来进一步具体展示多元话语分析的特点及其与后两种社会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
一、自杀现象的实证分析
这里的“实证分析”主要指的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一些分析方法。实证主义者们的理论立场虽然也是多种多样(从社会本体论的维度来看,有“社会唯实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唯名论”的实证主义;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也有经验论或归纳论的实证主义、唯理论或演绎论的实证主义、“分析实在论”的实证主义等),但其共同点就是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完全由客观规律所支配的现象,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加以研究。而所谓的“实证”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一项科学命题必须是建立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而所谓“客观事实”,就是一种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事实”,它应该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可以被人们以直接(借助于各种感官)或间接(借助于各种作为人体感官之延伸的工具如显微镜、望远镜等)的方式从外部特征上感性地加以观察(可观察性);二是这种观察的结果具有不依观察者个人主观意识状况为转移的特性,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个观察者就同一“事实”所进行的每一次观察所得到的观察结果都应该是相同的(可重复性);三是这些观察结果还要能够以相同的、所有人都能够以惟一的方式加以理解和确认的形式来进行表述(可操作性)。
在实证分析那里,自杀研究就是要对“自杀”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及其背后支配其存在和变化的规则进行科学地描述和分析。对于一个实证主义者来说,无论其在事实观察和理论建构之间的时间顺序等程序问题上与他人有何分歧,以下这些研究程序及其原则是他必须遵守的:
1.他必须根据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来对“自杀”行为作出一个“科学”(而非常识性)的界定,并据此来对可能符合该定义的那些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调查),将其中真正符合该定义的那些事件归属到“自杀”这一范畴之下;同样,他也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对与“自杀”行为可能相关的那样一些“事实”(“自杀”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职业、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等)进行科学的(而非常识性的)界定,并据此对按照上述定义被归入到“自杀”这一范畴之下的那些事件的当事者进行观察(调查),将相关的一些事实按照定义一一记录在案。
2.将按照定义搜集到的那些自杀行为确立为需要加以解释的因素,将同样按照定义收集到的那些与“自杀”行为可能相关的“事实”资料确立为可能可以用来对自杀行为加以解释的因素,然后同样根据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来对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推断出两类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在进行上述第二项工作时,采用的分析方法既可以是统计分析方法,也可以是个案分析方法。一般来讲,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社会唯实论”者们更倾向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社会唯名论者则可能更倾向于采用个案分析方法。
涂尔干关于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中持“社会唯实论”立场的学者们以统计分析方法来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
众所周知,涂尔干不仅是一个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唯实论”者。作为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始终坚持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本质上的一致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本质上的一致性以及科学命题必须是建立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些基本原则;而作为一个“社会唯实论”者,他更进一步认为“社会现象”是一种外在于、独立于个人之外并对个人具有强制力的集体性的“客观存在”。因此,涂尔干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即不仅“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 (P13),而且要“通过社会去解释社会现象”[2] (P85)。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正是试图努力遵循他自己确立的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
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首先试图按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一类的原则来把“自杀”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来加以界定。他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加以界定的“自杀”范畴“必须具有客观性,即与事物某些确定的方面相吻合”;“我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死亡中,探究到底是否存在具有非常客观的共性的死亡,以致任何悉心的观察者都能辨别出来”[3] (P2)。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根据自杀者的行为动机(如具有自我毁灭的主观意图)等主观因素来对自杀进行定义,因为一来行动者的主观动机很难准确地加以观察和把握,二来在自杀行为及其后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自杀者的行为动机却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一定要以“具有自我毁灭的主观意图”之类的因素来界定自杀,那么就会把很大一批实际效果与自杀相同的那些现象排除在自杀范畴之外。据此,涂尔干先是将自杀界定为“如下的任何死亡,即由死亡者本身完成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结果”[3] (PP2-3);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又进一步将其界定为“任何一桩直接或间接导源于受害者自身主动的或被动的行为,且受害者知道这一行为的后果的死亡事件”[3] (P4)①。
从表面上看,自杀完全是一种个体行为,它的发生完全取决于一些个体性因素,因而人们往往认为它只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试图用性格、脾气、经历和个人生活史来解释自杀行为。然而,涂尔干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来考察单个的自杀者,“而是将一定时期发生在一定社会中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简单集合,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新事物,有着自己的整体性,自己的个性,甚至于自己的本质特征。而就其本质来说,它具有社会性质”[3] (P8)。为了更好地揭示自杀现象的这种社会性质,涂尔干又提出了“自杀率”(自杀死亡的人数占其所属的统计群体人口的比例)这一概念。利用自杀率这个概念来去观察和分析19世纪中期欧洲主要国家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涂尔干发现自杀确实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譬如,每个国家的自杀率在短期内变化幅度虽然很小,但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不同国家的自杀率之间以及同一个国家里不同群体的自杀率之间却有较大的差异。并且,不论是哪个社会或群体,始终都会有一部分人死于自杀行为。这表明自杀的确是一种社会性的事实,它既会随着各个社会或群体某些共有特征的变化而变化,也会由于各个社会或群体属性之间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论是哪个社会或群体,始终都会有一部分人死于自杀行为。自杀现象的这种社会性质使得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研究课题。
那么,影响一个社会自杀率的主要因素到底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涂尔干将人们通常可能提出来作为解释自杀现象的那些因素区分为非社会因素(包括人的生理-心理特性如精神失常、种族特质和遗传、模仿心理等,以及外部环境如气候、气温等)与社会因素(主要是社会整合的程度)两大类,并且也尽量按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一类的原则来把这些因素当作客观事实来加以界定,然后再对这些因素与自杀现象之间的关系一一加以考察,结果表明所有非社会因素的变化与自杀率的变化之间都不存在着紧密的共变关系,只有社会因素的变化才与自杀率的变化高度一致,从而证明了影响自杀现象的主要因素不是各种非社会因素而是其他某种社会现象这样一种看法。
涂尔干用来对自杀率和可能影响自杀率的那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进行推断性分析的主要方法是所谓共变法。当他提出各种非社会因素都不是影响自杀率的真正原因这一论断时,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些因素与自杀率之间不存在着统计上的共变关系(如精神病比率高的群体或地区自杀率反而低、同一种族的人其自杀率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宗教中有着很大的差别、自杀率并未与模仿理论预期的行为变化而同步变化、自杀率的变化并不与气候及气温的分布严格保持一致等);同样,当他提出影响自杀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整合程度一类的“社会因素”时,其主要依据也是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统计意义上的密切共变关系:(1)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率与群体成员之间的整合程度成反比关系: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整合程度越高,其成员的自杀率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例如,对其信徒的控制或整合程度越高的宗教(如犹太教和天主教),其信徒的自杀率相对就会越低;反之(如新教徒)就会越高;同样,成员越多、内部整合程度越高的家庭,自杀率相对也就越低,反之就越高;已婚者的自杀率则也要低于未婚者的自杀率;在政治危机时期社会的自杀率往往会降低,这也是因为政治危机在许多情况下激发了全民族的集体情感,使全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动起来,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较紧密的民族团结。而群体内部整合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兴盛的结果。正是个人主义的兴盛削弱了个人依附的集体力量,使个人把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凌驾于群体的目标和利益之上,从而降低了团体的整合程度,提高了自杀的概率。所以他把这类自杀叫做利己型自杀。(2)经过仔细分析也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率与群体成员之间的整合程度成正比关系:以利他型自杀类型而言,经过分析则可以发现与利己型自杀相反的倾向:一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整合程度越高,此类自杀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涂尔干认为这类自杀主要是因为社会把个人过于严格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造成的。在利己型自杀中,社会禁止选择死亡,而在这一类自杀中,社会却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死亡。在这一类自杀盛行的地方,自我完全不属于自己,个体的生命本身毫无价值,它只是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已。涂尔干将此类自杀叫做利他型自杀。(3)经过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有一类自杀其比率与群体内部规范约束的有效程度成正比关系:在规范约束有效程度高的时期或地方,此类自杀率相对较低,反之则较高。涂尔干把这类自杀叫做失范型自杀。这类自杀无论在贫困还是富裕阶层中、也无论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还是经济骤然繁荣时期都会发生,因此它与人们的贫困程度无关而主要是与社会秩序的重大变更有关。在社会正常运行时期,各种社会规范能够对人们发挥有效的约束力,人们安心于自己的所得。但当社会被严重的危机或幸运的骤变打乱时,其约束作用便暂时地消失了,因而便可能扰乱人们的精神平衡,导致自杀率上升。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主要以统计上的共变关系为依据的推断和分析,涂尔干试图表明,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自杀,本质上都是由于某种社会原因(社会整合不足、社会整合过度、社会失序等)而造成的。
涂尔干不仅是实证主义阵营当中的“社会唯实论”者,而且还是“社会唯实论”阵营当中的“功能主义”者。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他始终把社会整合当作自己关心的一个核心主题。他在对自杀现象进行分析时力图把社会整合程度当作解释自杀率变化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即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所持的这样一种理论立场。但除了功能主义学派之外,在实证主义的“社会唯实论”阵营当中还包括有达伦多夫一类的社会冲突论者。这些人在对自杀现象进行分析时,自然将把重点放在自杀率与社会不平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以社会不平等等因素来作为解释自杀率的主要自变量。但作为实证主义及社会唯实者,他们在把自杀现象当作是一种由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客观事实这一点上与涂尔干等功能主义者之间不会有什么重大差别。因此,上述以统计推断的方法来从总体上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也当是他们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
然而,对于霍曼斯一类持社会唯名论立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对于这些学者来说,“社会”(家庭、公司、国家、群体等)确实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是许多个体行动的不同组合。因此,要理解由个体行动建构出来的某种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返回到个人,通过对个体行动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来达到对作为个体行动之产物的某种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从这样一种主张出发,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主要的分析方法就应该是个案分析而非统计分析。但与韦伯等诠释社会学家们不同的是,对于霍曼斯一类的学者来说,作为实证主义者,他们反对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方面去描述和理解行动者的行动过程(因为他们认为个体的主观意向是无法客观地加以把握的),而是主张要用行为主义心理学常用的实验等方法,通过对个体行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之外部特征的考察,来总结出支配着个体行为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然后以此为前提应用演绎逻辑来对包括特定个体的自杀行为在内的各种具体社会事件客观地加以说明。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说明。
二、自杀现象的诠释学分析
本文所说的诠释学分析包含了由韦伯创立的早期诠释社会学、舒茨提出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学”、布鲁默提出的“符号互动主义”、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等社会学流派所使用的那样一些社会分析方法。这些流派所使用的社会分析方法之间尽管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共同特点是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认为社会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外在于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东西,而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那些个人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现象就不能像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从对现象外部特征的观察入手、以现象之间可从外部加以观察的那些联系为依据,而必须采用一种与实证科学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它们还原为建构了它们的那些意向性的个体行动,通过对这些行动之主观意向及其过程的诠释或理解来达到对作为行动之产物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理解。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现象学社会学家J.D.道格拉斯(J.D.Douglas)、J.M.阿特金森(J.M.Atkinson)、J.雅可布(J.Jacobs)等人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来作为对自杀现象进行诠释学分析的范例。
道格拉斯和阿特金森等人认为,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属于自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具有的什么“客观属性”以及根据这些“客观属性”而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对“自杀”范畴的主观认定。阿特金森由此彻底否定有一个客观的自杀率的看法,认为“以这种假设(有一个像客观现实那样存在着并等待人们去发现的‘真正的’自杀率)作为前提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结果只会发现与他们企图弄清楚的社会现实毫无关系的自杀的‘事实’。通过建立一整套对自杀进行分类和测定的标准——用科学的语言讲就是通过将自杀概念的操作化——他们仅仅是把他们的现实强加于社会世界。这就比如会使那个社会世界遭到歪曲。”其实,社会学家真正应当提出来加以研究的问题是:“某些死亡是怎样被人们划入自杀范畴的?”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那些试图解释被看作是非自然死亡的原因的人所使用的意义进行调查。这样的方法最不会歪曲社会世界,因为它试图探究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成员们用来构造他们的社会现实的程序”[4] (PP39-40)。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道格拉斯和阿特金森等人对涂尔干一类社会学家主要以官方统计资料为依据来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表面上看,涂尔干等人这样做,似乎主要是便于获取数据,但其实更主要是这一派社会学家所持实证主义观点的逻辑产物。因为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自杀”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体意识之外的客观事实。具体到“自杀”这一社会现象,称它为一种“客观现象”,即意味着:(1)不同的人对于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属于“自杀”尽管开始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但只要按照科学的准则进行讨论,最终将会有完全相同的判定标准;(2)不同的人来对同一“自杀”事件进行观察和界定时,只要采用的方法得当,最终都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官方人士(验尸官)、医生、研究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家,还是其他普通社会成员,在“证据”充分的条件下,对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可以归入“自杀”这一范畴之下应该不会有重要分歧。而出于便于获取数据方面的考虑,采用官方现成的自杀统计数据来对自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就显然是一种合理的行为。道格拉斯和阿特金森等人则从上述诠释社会学立场出发认为,官方的统计资料其实仅仅是官方工作人员这类社会行动者对于某些死亡事件的意义所做理解和解释的结果,它并非是什么“客观事实”的再现。
在一篇讨论自杀统计的论文中,阿特金森指出,一个社会学家在决定是否使用官方统计资料来研究自杀现象时,有两个决定他必须首先做出:第一,他必须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官方的各种相关范畴作为其理论工作的有效指标;第二,是要确定与这些官方范畴相应的统计资料的有效性与精确性。阿特金森说,那些决定采用官方范畴来进行自杀研究的社会学家事实上是默认了以下两个基本的逻辑前提:(1)官方的“自杀”的范畴是一种与社会学家们的“自杀”范畴完全一致的方式来加以界定的,因而是一个可接受的指标;(2)官方对这种官方定义的使用是持续不变、始终一致的,以至于所有合乎定义的死亡事件都能被包括在统计范围之内。[5] (P88)阿特金森认为,这两个逻辑前提其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一次死亡事件是否属于“自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观察、记录、界定这一死亡事件的那些人们(如验尸官、医生、记者、死者的家属和朋友等)对这一事件的理解或诠释。因此,我们在利用这些官方资料来描述和分析自杀现象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客观现实的再现,而必须意识到它们是官方人士对某些死亡事件进行理解和诠释的产物,必须深入到这些官方人士的主观意识过程当中去,了解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些死亡事件的含义,如何将它们建构成一种被称为“自杀”的现象的。
在持实证主义观点的研究人员内部,人们也已经意识到以往以官方统计资料为依据来进行自杀研究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可能具有严重的不准确性、实际的自杀率往往被有意低估等。但是,尽管如此,许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者仍然认为:“经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技术的改进,还是可望得到‘真实的自杀率’,或至少可以得到十分接近的近似值。他们认为,一旦发现了‘真正的事实’,也就能够解释形成这些事实的原因了。”[4] (PP40-41)但阿特金森等诠释社会学家们则认为,实证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自杀等社会现象的描述可能不精确,而在于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世界只能根据其不同成员的意义诠释过程去理解,只将其中部分成员的意义诠释当成了客观世界本身,因而“粗暴地对待了他们企图了解的社会现实”。
出于这种考虑,阿特金森将自己有关自杀的研究“集中在验尸官将某些死亡划入自杀范畴时所使用的方法上。他曾与验尸官进行了讨论,在三个不同的城镇在场旁观验尸,观察了一个验尸官进行工作,查看了一个特定验尸官的部分记录。阿特金森认为,验尸官对于自杀率都有一种‘常识性理论’。假如有关死者的情况符合这个理论,他们就很可能把他(或她)的死亡划入自杀范畴。依据这个理论,为了能够就自杀的问题作出裁决,验尸官所考虑的是下述一些有关证据:第一,死者生前是否写下了企图自杀的遗书或曾有过这样的凶兆?第二,某些特殊的死亡方式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杀的表示。在马路上的死亡很少被解释为是自杀的一个迹象,淹死、吊死或因煤气中毒及用药过量而死亡则很可能被看作是自杀的迹象。第三,死亡的地点和环境被认为是有关的因素。例如,同发生在有组织地进行狩猎的农村相比,发生在偏僻荒凉地区的枪杀更可能被解释为是自杀。在煤气中毒而死的情况下,假如窗户、门和通风装置都被关闭以防煤气溢出,就更有可能作出自杀的定论。第四,验尸官还考虑死者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关于他(或她)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处境。例如,精神病史、动荡的童年生活和意志急剧消沉的迹象,这些常常被认为是自杀的证据。一次新近的离婚事件、近亲的死亡、没有朋友、工作中的挫折或经济上的严重拮据,都可能被认为是自杀的理由。因此,阿特金森认为,“那些从被官方归入自杀一类的死者的社会处境或心理状况来寻求自杀原因的社会科学家们,可能只是在表达验尸官的常识性理论而已”[4] (PP41-43)。
在《自杀之社会意义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道格拉斯也对涂尔干一类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来展开的自杀社会学研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道格拉斯认为,涂尔干等人在自杀研究过程中对于官方统计资料的这种信任和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一个非常绝对的基本假设为前提的,这就是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自杀范畴的含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决不会有任何变化(否则的话“自杀率”的变化或许就可以由那些意义的变化而不是由所谓“社会整合”一类的因素来加以解释了)。[6] (P131)道格拉斯也认为这种假定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人们对自杀含义的主观界定往往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意味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条件下被归入到“自杀”范畴之下的那些死亡事件其实并非完全是同质的,在内涵和外延上可能存在着重要差别。
除了在使用官方统计资料时所隐含的上述问题之外,道格拉斯还指出,使用统计方法来分析所得到的关于自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当他们想要进一步弄清楚这些相关关系当中到底哪一些属于因果性关系时,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只能够是根据常识来推断。例如,当涂尔干在解释为什么新教徒的自杀率常常高于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时,他同样运用共变法比较了各种教徒人口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大小给其造成的社会压力、各教派教义对待自杀的态度以及各教派团体对其内部成员个人的约束(或整合)程度等因素对自杀行为可能造成的作用,结果发现前两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都不存在严格的共变关系(新教徒比率小的地方其自杀率依然很高、新教和天主教教义对自杀都相同的排斥态度),只有内部约束(整合)程度这个因素与自杀率之间有较严格的共变关系(自杀率高的教派团体其内部整合程度也高,反之亦然)。这种比较严格的共变关系自然使人想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单是这种严格的共变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想弄清楚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因果关系,就应该对自杀者的主观意向进行大量的个案分析,从自杀者的意向活动中来考察团体约束或整合程度是否确实是造成自杀率高低的主要因素。但涂尔干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借助于一些常识性的推论(如“一个宗教团体对个人判断作出的让步越大,它主宰生活的力量就越小,它的聚合力和生命力就越弱”等)最后得出结论说:“新教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它不象天主教结合得那样紧密。”[3] (P115)
道格拉斯呼吁采用一种可以用来对在真实世界的自杀事件中可观察到的沟通行动进行分析的全新的社会学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利用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自杀者等)记录下来的有关资料,来对自杀事件中有关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一些有共性的意义建构模式。道格拉斯用了几个比较简单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1:F.B.先生,生于1902年,在进入医院之前有好几年显示出日趋增强的易激动、多疑和缺乏自制的倾向。1945年他成为明显的妄想狂和抑郁症患者,并同时有一种超常的性要求。他害怕自己会自杀(他的家族已有三位成员死于自杀),并常常威胁他的妻子和孩子。当他妻子开始启动离婚程序时,他变得极度抑郁和自责。一天晚上,他企图饮酒自杀,并将事情告诉了妻子。他被立即送往一家总医院,然后被转往一家观察所,最后又被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的妄想狂和抑郁症症状虽然维持未变,但渐渐平静下来趋于一种呆滞状态。担心他可能再度尝试自杀,他的妻子不仅未再继续要求离婚,且有规律地去探访他,告诉他不会再提与他离婚的事。自此以后数年里,他一直呆在这所精神病院中。[6] (PP137-138)
道格拉斯分析说:“在此案中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位妻子将他丈夫的自杀行为解释为她启动离婚程序这一行动的直接产物。即是说,对她而言,非常清楚的是,这一特殊的、直接的程序性情境是其丈夫自杀行动的一个原因。伴随这样一种解释以及她不愿意丈夫再度自杀的愿望,她改变了情境,使之回复到从前的情形。”[6] (P138)
案例2:一个22岁的年轻职员杀死了自己,因为其新婚四个月的妻子不再爱他,而移情别恋于他的兄长,并宣称要与他离婚,以便能与后者结婚。他留下的一堆自杀手记清楚明白地显示了他要通过自杀来使其妻子和哥哥声名狼藉,以及将注意力引向自身的愿望。在这些手记中,他追述了自己那被损毁了的浪漫故事,并且劝告记者去找一位朋友以获得更多的详情,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日记给了这位朋友。
一份手记的开头是特别写给其妻子的:“我一直都爱着你;但是现在我死了也憎恨你和我的哥哥。”这是用坚定有力的手写下的句子;随着自杀手记的展开,手迹变得漂浮不定起来,然后更由于其陷于无意识状态而变得几乎不可辨认。在打开煤气后不久,他写道:“把我的‘万灵妙药’推荐给所有患有疾病的人吧。时间不会太长了。”一小时过后,他继续写道:“还是一样,希望我能在上午2点离去。呵,我如此地爱你,佛罗伦丝。我觉得非常疲倦,有一点眩晕。但我的大脑非常清醒。我能看到我的手正在摇晃……一个正值年轻之时的人要想死去是多么不容易啊。现在我希望遗忘会快点到来”。这份手记在此终结。
另一份手记则对使用房东的屋子自杀而为后者可能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另一份则写着:“对有兴趣阅读此手记的人:所有事件的起因:我曾经热爱和信任我的妻子并且也信任我的哥哥。现在我憎恨我的妻子,藐视我的哥哥,并且由于一直愚蠢地爱着像我妻子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而宣判我自己死刑。他们两人今天下午都知道我今晚自杀的企图。他们对此前景感到非常愉快。他们有无数的理由来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23岁的哥哥向警察坦承了他与弟媳之间的友谊。由于父母离异,幼年时兄弟两人曾经分开,但直到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而导致这场悲剧发生之前,兄弟两人还是成了难分难舍的好伙伴。当弟弟因爱心未得回报而企图以自杀相要挟时,姑娘出于怜悯而同意了与他结婚——但后来她发现难以实践自己所许的诺言。婚后不久,弟弟便发现了妻子与兄长之间的关系。他陷入了极度的抑郁,并威胁说要自杀。在他死前的一天,当他看到的一些场面使他确认那两人的确深深地陷入了爱河时,这位职员恨恨地说:“好吧,让我以死来还击你们。”[6] (PP138-139)
道格拉斯对此案例进行了如下分析:“这个案例清楚地表明了在自杀者和他人心中通常赋予自杀行为之上的‘复仇’含义的一般结构:首先,在此案中,最为明显的是指出人们认为应该受到谴责的那个人(人们企图让他人及被谴责者认为此人应为自杀者的行为负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此例中,对自杀者准备加以谴责、并且他认为应该受他人(包括他们自己)谴责之对象的揭示是非常清楚的:他留下了大量笔记,提供了许多陈述,以便使他所谴责的那些人变得非常明确。但光是指出这些他试图视为罪犯的人还是不够的;要想使他们被其他人(或被他们自己)界定为是原凶,他必须表明存在着某些典型的情境,这类典型的情境会被人们典型地相信为是引发某种典型动机的原因,后者又被典型地相信为是引发某些典型行动(比如自杀行动)的原因。在此例中,自杀者试图通过显示他已经被其妻子和兄弟的不道德行为所背叛来达到这一点。”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他人(例如警察)而言,在诠释或理解这一自杀事件时,光听自杀者个人的简单陈述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需要观察其他当事人对自杀者的指控所做出的反应。“在此例中,被谴责者表现出很诚实的样子(与警察自由的交谈),并显示她从未真正爱过他(自杀者),这些尝试给人一个行为良好、全然只是出于爱的力量而被迫背叛兄弟(也即意味着这并非是种真正意义上的背叛,尽管从自杀者的立场来看确是一种背叛)。”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自杀行为的选择也意味着一个人对其所说之言的高度承诺(他是严肃的、诚实的,正如这一终极性的承诺行为所显示的那样),以及他值得‘同情’,因为他的自杀行为是由外部情境的压力所迫。在这样一种情境下,那些遭受谴责的人很难以一种对他们自己来说更可接受的方式来界定事件(尤其是如果他们‘知道’自杀者所说的是‘真的’的话)。他们几乎无法争论说他们是更为正确或更值得同情。他们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重新界定所发生之事(事情并非是像自杀者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此例中自杀者的妻子与兄长所选择的道路;或者,重新界定自杀者(他是一个‘疯子’,或者他试图伤害我们等),以使自杀者看起来不那么值得同情。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那么多的自杀者被人当成疯子来看待,以及为何那些企图以自杀行为来谴责他人的人常用一些不那么直接的谴责手段。”道格拉斯总结说:“这一分析也使我们看到,就像‘自杀’本身一样,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真实的或想象的)参与者之间发生的‘自杀争议过程’的一个结果。”[6] (PP139-140)
道格拉斯认为,上述几个案例中的采取“自杀”行动的行动者赋予自身“自杀”行动之上的意义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把“自杀”行动当作是向自己怨恨的某些人进行复仇的一种手段。“复仇”是促使自杀者走向自杀的直接原因。因此,可以将它们抽象概括为有关自杀意义的一种模式,即自杀的“复仇(revenge)”模式。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案例中抽象概括出有关自杀意义的其他一些模式,如“求助(the search foe help)”模式、“同情(sympathy)”模式、“解脱(escape)”模式、“忏悔(repentance)”模式、“赎罪(expiation)”模式、“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模式和“危机(seriousness)”模式等等。参照这样一些意义模式,我们就可以根据自杀者自己赋予其自杀行为之上的主观意义来对自杀现象的形成原因做出比实证主义者的解释更为合理的一些解释。
道格拉斯的上述思路在雅可布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自杀笔记的现象学研究”一文中,雅可布对一些自杀者自杀前留下的笔记材料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发现许多自杀者在对自己的自杀行为赋予意义时,都拥有一个大致相同的非常接近于道格拉斯所概括的“解脱”模式:这些自杀者在笔记中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定自己正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困境,惟有一死才能够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7] (PP332-348)
总而言之,在道格拉斯、阿特金森、雅可布一类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看来,“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在那意义的背后没有客观现实。”对于那些不把犯罪和自杀看作是意义构成物的社会学家来说,他们是在把自己的现实强加于社会世界,从而歪曲了他们试图理解的真正的现实。”[4] (P44)(未完待续)
注释:
①与前一个定义相比,后一个定义的好处是可以将由于行动者的幻觉所造成的一些死亡(“如某人从很高的窗户上跳下去,自己还以为是在一层楼上”)排除在自杀定义之外。涂尔干认为这一定义要更为科学。但实际上前一定义更符合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原则(或涂尔干自己表述的“从事物的外部特征来界定事物”的原则),因为后一定义涉及了行动者是否“知道”自己行动后果这样一种主观意识状况方面的因素。涂尔干对后一定义的肯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涂尔干社会学及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局限。涂尔干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书中为这一定义辩解说它不会导致研究上的困难,因为“很容易辨认”这种主观意识状况,“人们并非不可能发现个人事先是否知道他的行为的必然后果。”这一辩解有点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