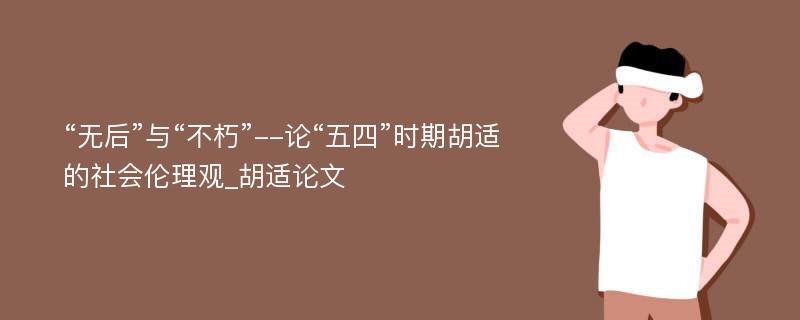
“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伦理论文,试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胡适不但在白话诗文运动中首举义旗,冲锋陷阵,而且在思想哲学、社会伦理范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传统旋风。他的“无后”主义和“不朽”观在强烈地摇撼3000年来封建伦理传统和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新文化”及其价值体系注入了深刻的理性内涵与郁勃的现代气息,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7月30日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的诗:“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那里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将来你长大时,/①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的文艺栏上。过了几天有一个叫汪长禄的人写了封长信给胡适,对这首诗表达的思想内容提出异议,汪氏认为胡适在诗中把“亲子的关系一方面变成了跛形的义务者,他一方面变成了跛形的权利者”。“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帐’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汪长禄着重对胡适诗的末二句“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强调做孝子与做堂堂的人是可以统一的,生怕根柢浅薄的青年人盲目崇拜名人名言,割裂甚而对立两者,“肆无忌惮”做起不仁不孝的事来。胡适的回信重申了“父母于子无恩”的观念,犀利地攻击了“孝子”这个概念的荒诞空泛,明确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并分别就儿子与父母两边的社会功罪上发议论,精神主旨都集中在一点: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应是一个“堂堂的人”。如果是一个“堕落”的“祸根”,甚或是“军阀派的走狗”、“卖国卖主义”的“一国一世”的大罪人,儿子大可不必爱敬这样的父母,父母也决不要这样的儿子的孝顺。胡适的《我的儿子》诗以及他的答信旨意显然已溢出了家庭伦理的范畴。
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胡适这一伦理——社会范畴的思想观念变革之由来及其发展脉络。
早在留美期间,1914年,胡适就对我国“家族的个人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抨击——为断绝家族成员间变态的依赖性,他提出“无后主义”的新观念:他在1914年9月的一则日记中说道,“吾国家族制度以嗣续为中坚”(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六个流弊:一、“望嗣续之心切,故不以多妻为非”;二、“父母欲早抱孙,故多早婚”;三、“唯其以无后为忧也,故子孙以多为贵,故生产无节”;四、“其所望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五、“父母之望子也,以为养老计也,故谚曰‘生儿防老’,及其既得子矣,既成人矣,父母自视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养矣。……其为社会之损失,何可胜算?”六、“父母养子而待养于子,养成一种牢不可拔之倚赖性。”——胡适说:“吾所持‘无后’之说,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则世界人类绝矣。吾欲人人知后之不足重而无后之不足忧。”他特地标举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之两段言论:一、“夫人最大事功为公众而作者,必皆出于不婚或无子之人,其人虽不婚无后,然实已以社会为妻为子矣”(《婚娶与独处论》);二、“吾人行见最伟大之事功皆出于无子之人耳。其人虽不能以形体传后,然其心思精神则已传矣。故惟无后者乃最能传后者也”(《父子论》)。由培根的“无后”言论胡适联系起中国古籍《左传》中叔孙豹答范宣子的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胡适禁不住发挥道:“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谓‘无后之后’也。释迦、孔子、老子、耶稣皆不赖子孙传后,华盛顿无子,而美人尊为国父,则举国皆其子孙也。李白、杜甫、斐伦(拜伦)、邓耐生(丁尼生),其著作皆足传后,有后无后,何所损益乎?”
正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正是“以社会为妻为子”,正是看重“心思精神”之永远传后,胡适认识到只有做一个社会功臣才是不朽传后的最可靠手段,而“社会功臣”的基点就是做一个“堂堂的人”。——首先做成了一个“堂堂的人”,进而做成了一个“社会功臣”,才会有“有后无后何所损益”的境界。这也正是胡适要儿子首先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的哲学出发点,也正是他在《竞业旬报》时期向世人推荐一个最可靠的儿子——“社会”——逻辑上的必然发展。胡适把这一层思想哲学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三W”便是英文中Worth、Work、Words的第一字母,其涵义正落实在“立德、立功、立言”三点之上。
母亲逝世后,胡适悲痛之余,又重新想起了这个哲学问题。他母亲的平生活动从未超出家庭琐屑细事之外,但他的精神上的左右力与人格影响却是伟大的、深久的。胡适想到他父亲对他母亲一生的影响,他母亲对他自己垂久的影响,终于相信,一切事情,极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有垂久的巨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觉得“三不朽论”有修正的必要,它原来的涵义至少有三层不足:一、只限于极少数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绩言语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世界上能有几个墨翟、耶稣,几个哥伦布、华盛顿,几个杜甫、陶潜,几个牛顿、达尔文呢?”这“岂不成了一种‘寡头’不朽论吗?”二、没有消极的制裁。“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恶又怎样呢?”“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恶德又怎样呢?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或地狱之火吗?”三、“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怎样的人格方才可算是德,怎样的事业方才可算是功,怎样的著作方才可算是言呢?”“一个人应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胡适认为,积极方面的“立德立功立言”应与消极方面的犯罪作孽、遗臭贻患同样获得“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恶”的制裁尤为紧要。以修正“三不朽”说为契机,胡适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的“社会的不朽论”;‘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即“大我”)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恶,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不朽——我的宗教》)
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日积月累而成就“小我”,“小我”对于其本身的作为,对于社会、人类世界的“大我”的作为都必然留下抹不去的痕记。“小我”是会死的,但是他还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这个“大我”乃是不朽的。“小我”的一切善恶是非功罪,一切言行思想著述都在“大我”上必然要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为之胡适说“这个‘大我’永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胡适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它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他的根本一点就是“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见《我的信仰》)
由此胡适又引导出了“对于大我负责任”的观念:“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每个“小我”的“负责”都是绝大绝严重的。胡适反复强调“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社会不朽论”的最根本的教旨便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小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社会不朽”思想的核心精神便是个人对社会的负责,“小我”对“大我”的负责。个人,不论地位贵贱,不论才智高下,不论身份职业都应该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演好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德功言(也无论是伟大的崇高的或是平凡的细微的)为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共同扶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的幸福事业。只要社会的每一分子即每一个个人都尽了自己的职责,都认真地“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多积德,不作孽,那么整个社会便会协调地朝前发展,“大我”人类便会不断地趋向光明。——这是胡适留学时期形成的“执事者各司其事”为“七字救国金丹”的理论发展。甚至可以追溯到《竞业旬报》时代他本人的思想启蒙。②在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的矛盾运动完善协调的同时,胡适又系统提出了他对于中国传统的观念形态有巨大变革意义和冲击力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哲学。
“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哲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五四前夕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中。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的“写实主义”,易卜生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救世精神。胡适详细地介绍易卜生戏剧中对资产阶级陋俗陈规的批判,锋芒直指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法律、道德、宗教,强调了“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并由此过渡到以人格自由独立、个性价值尊严为精神核心的“救出自己,完善自己”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胡适悄悄修正了易卜生的批判对象,直接用这位“人的精神的反叛的最伟大教授之一”(普列汉诺夫称赞易卜生语)的哲学精神,对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对儒家伦理道德与社会观念形态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于易卜生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强烈现实意义,胡适有一段名言:“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为什么“不得不说”,因为易卜生觉得自己有责任,自己的这个“小我”对社会的“大我”有不可推卸的救治的责任,不能袖手旁观。只有尽了自己的这个责任,才能做到良心平静。
胡适认为几千年的文明史是螺旋型发展进步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个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1921年4月30日日记)。其中的关键便是社会需要不断有百折不挠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个人或少数党。而这些个人和少数党能悲壮地投身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寻求真理的事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须要如易卜生指出的那样“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这里胡适引导出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主旨。
胡适指出,“个人须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是“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跟着眼前的社会一起堕落,不肯救出自己乃是最大的罪孽。胡适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抑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但他又指出“要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胡适认为,“自由意志”与“负责意识”是组成个人独立的人格、自由发展个性的必备条件。③而具备了独立的人格,充分发展个性的一个个的个人乃是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动力。这也正是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核心。
“负责”是对社会的,更是对个人自己的。对自己尽了最大的责任,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了器,就是最高意义的对社会负责。反之,对自己不负责,不想救出自己,跟着世界堕落,他也决不配谈对社会的负责。对自己要充分自信,要绝对忠诚,唯这一点上决不容许半点含糊。胡适在1914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曾说:“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护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行乎?”此“不容忍”说也。其所根据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白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
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这里胡适强调对自己负责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对真理之孜孜追求上,所谓“不容忍”之说,就是为真理而战不容丝毫的含糊,决不因他人之故而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认识与服膺,放弃自己的人格独立自由的根本原则。④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集中赞扬了易卜生戏剧的《国民公敌》中那个斯铎曼医生的人物典范,把斯铎曼医生看作是对自己高度负责、对自己绝对忠诚,孤身一人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不容忍”的形象代表。——斯铎曼医生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被社会容忍,反被社会全体一致看作为“国民公敌”,遭受无数的打击与磨难。但他坚认自己主张之正确,不肯放弃真理,不肯妥协调和,与整个堕落的社会、全体迷误的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坚韧不拔的斗争。——胡适与易卜生一样呼唤社会上生出千百个斯铎曼医生,号召独立特行的理想志士敢于做被社会大众误解甚而被迫害的“国民公敌”。胡适与易卜生都借斯铎曼医生的口向世人宣告:“世人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只有绝对地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才能最孤立,也才能最强大。这正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谛。12年后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又重提“易卜生主义”和集中体现了易卜生主义精髓的斯铎曼医生:“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暗,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胡适之所以大力宣传“易卜生主义”,宣传“斯铎曼精神”,其主旨便在号召人们学习斯铎曼的那种“白血轮”即白血球精神。他说:“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数量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这一层思想几乎贯串了胡适一生的言论,1935年5月胡适写的一篇叫《再谈五四——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50号)还提到:“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在胡适眼里不仅列宁是“爱自由、爱真理”的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胡适认为眼前这个时代亦应该涌出无数个“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宣布:“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大的担子?”⑤胡适再三强调“一个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特别重视造孽、积德之辨,他说:“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么?你能种什么”——胡适从五四时代起即在播种着爱自由的种子,爱真理的种子,都在为新时代新国家培养着不屈奋斗的白血轮分子。他的口号始终是救出自己进而救国家;对自己的现在负责,进而对社会的未来负责。这是他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哲学,也是他积极的淑世主义的宗教。但是,由于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毕竟其核心是为我,与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与当时我们党倡导的革命的集体主义相比,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视为一个先进的口号。
正因为胡适积极倡导他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哲学与淑世主义的宗教,他把“独善的个人主义”看作是对青年人思想最有危害的一种错误思潮和糊涂观念。“独善的个人主义”思潮的根本性质是:“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思潮以当时的“新村运动”为主要实践代表,它们实质上是放弃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对眼前的充满罪恶的龌龊社会采取逃避主义的态度,它在性质上同宗教宣传的极乐园、神仙生活及古时的山林隐逸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主张让步,放弃责任,与世无争,逃避社会,寻求人生社会外的所谓世外桃源。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对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再次呼吁人们对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宏伟事业负起责任,不退缩,不躲避,积极入世,坚韧奋斗。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步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息奋斗,把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旧生活变为新生活。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生活的奋斗中得到改造与完善,成为一代新人。
注释:
①这句诗在1920年3月《尝试集》初版中改为:“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②当时在《竞业旬报》上有一位叫吴铁秋的作者曾写过几篇对胡适思想有很大触动的文章,其一篇为《说我》,主旨说,中国第一大病,坏在不知有我,人人能知“有我”就好了。他主张:“世界所有事,皆我所有事”。一篇为《说自治》,主旨说,看重“自治”的“自”字,认真读,使劲读,自己唤醒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不可躲避自己的责任,不可放弃自己的事功,一刻也不可因循玩乐。一篇为《但问问现在是什么人》,更是强调做官的认真做好官,做民的认真做好民。士农工商,所谓“各有责任,各营其业,各司其职,装龙象龙,装虎象虎”。“到了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时候,大家总要醒醒迷,回回头,说我是什么人,我应该办什么事,我应该担什么责。做官的死心塌地去做官,说我不办这等事还了得,做民的死心塌地去做民,说我不办这等事还了得……各人要照各人本份办事。”又说:“中国有一种大毛病,是人人的通病,是特殊的奇病……就是善忘”。“善忘的到了妙处就是将自己身子忘记了。不知自己身子,现在处了什么时候,当了什么地位,做了什么人物。”“中国所坏的就坏在上无官,下无民,做官的不晓办做官的事,做民的不晓办做民的事。一旦大家都改了习惯,换了心肠,认了本来面目,从家而忘国的时代变而为国而忘家的时代,从私而忘公的时代变而为公而忘私的时代。”——吴铁秋这些言论无疑对当时的少年胡适有相当深刻的启发与影响。
③这一层思想也有杜威的渊源,胡适曾反复宣讲过。如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就介绍引用杜威的《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讲演中的一段话:“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④胡适于1914年11月2日曾给美国女友韦莲司写过一封长信,信中已经与韦莲司女士讨论到易卜生的戏剧与易卜生的哲学。其中有两条显然与这里的“易卜生主义”的意旨相通:一,“我们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对自己忠实。……并且绝不可以妨碍我们的个性与性格。我们幸运地能够在新的启示之下看见真理的人,必须坚持我们所见到的真理。我们绝不可妥协,为着我们的思想——真理——不容有任何妥协。”二,“个人应该有发展到极限的充分自由,对于社会的利益也最有好处。只有每个个人坚持紧守他所相信是真的与善的东西,而不肯满足于‘事物的既成秩序’,人类才可以有进步。换句话说,我们的进步是靠激进派和反叛者的”。
⑤胡适往往将这个“绝重大的担子”与“青年的救国”的事业联系起来,如《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他就宣传道:“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在引用了易卜生“铸造成器”,“救出自己”两段的语录之后又说:“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又说“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大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根,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所谓“任重而道远”,所谓“绝重大的担子”便是要求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培养成人才,才是救国事业的最根本的基础,才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必要前提。——而这个“器”,这个“人才”的两个标准便是爱自由、爱真理,具有独立的人格,有负责任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