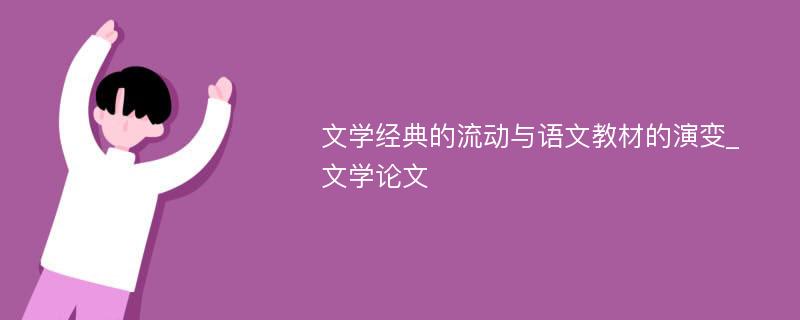
文学经典的流动与语文教材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材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教育部《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与实施,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相继实验,给中小学基础教育带来了百花竞放的新景观。但是教材编写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语文教材(指“文字教材”)也是人们期望值最高,非难最多的一种文本。而在语文教材的编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是教材的选文。哪些作品可作为课文,怎样才能突出“新”字?不同的编者由于鉴赏水平、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文标准。除客观标准(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和思想的深透性与影响等)外,主观上的标准也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与文学经典有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一、如何认识“经典”的恒定性与流动性
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化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多媒体网络文学、卡通漫画、影碟光盘(其中有健康信息,也有垃圾信息,如暴力色情)等,像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无遮拦地向学生涌来,迎合了学生们追求轻松与时尚的心理需求。然而一谈及经典名著,学生们就有一种距离感、沉重感。有的甚至提出“看名著能管考大学吗?”对此,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引导学生了解文学经典,接受文学经典,它对提升学生审美情趣,陶冶情操,学会感受与思考,将产生终身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读书兴趣,单靠推荐书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在教材编写上下工夫,突出一个“新”字,但不是赶时髦。那么中学语文教材应选哪些作品?哪些作品既是经典的又是典范的?教材编写者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标准。
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精髓,是一个时代文学成熟的标志,是垂范后世、被众多读者所传诵、历久弥新的文本,有恒定的文学价值。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指出:“经典不是指一本书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经典是指一本被世世代代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的推动,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所阅读的书。”(注:[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倪华迪译:《作家们的作家·论经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3页。)英国诗人艾略特也曾指出:“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成熟的文学背后有一部历史:它不只是一部编年史或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手稿和作品,而是一种语言在自己的限度内实现自身潜力的进程。这一进程尽管是不自觉的,但却很有秩序。”每个时代过后都会有被人们所认同的、符合人们思想需要的、具有跨越时空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的文学经典产生。它的产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的结果,是读者与作者共鸣的产物,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在一定的时期,有约定俗成的、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从语文教材的编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课文是作为“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名篇保存下来的,它们是编者一致认同的作品。如:《皇帝的新装》《春》《荷塘月色》《济南的冬天》《祝福》《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促织》《美猴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等。除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外,其教育价值也是决定这些作品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文学经典有着它“恒定”“稳定”的特征。
文学经典,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总结、代表、隐喻了一个时代。同时,它又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发展的。所以,我认为文学经典又具有“流动”的特征。其“流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经典”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具有一种构造性;二是“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更改变动和再选择的特点。它的变动符合变化了的时代与人们重新审视经典作品的需求,并被多数人所认同。正如清代赵翼在《诗论》中所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经典,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发展和积淀的结果,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费振刚教授在《〈诗经〉的经典性》一文中指出:“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应当说它总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人的生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来接受它。”(注:《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第295页,2000年7月版。)正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经典又经历着“确立——打碎——重组”的过程。
作为诗歌总集的《诗经》,其经典地位至今都是不可动摇的。但在不同时代,受政治观、文学观、价值观的影响,中学语文教材篇目的变化是很大的。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可略见一斑。1956年人教版汉语、文学分科教材中《诗经》的选篇是初中第三册:《木瓜》《采葛》《君子于役》;高中第一册:《关雎》《氓》《黍离》《伐檀》《蒹葭》《无衣》。选篇基本上是反映当时人们劳动、爱情、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对生活的感受等内容。1957年“反右”斗争后,对汉语、文学教材进行了批判。认为教材编写上是“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并质问“今天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现行教材却编选了一些消极避世、闲情逸致、儿女情长的作品教育学生,这与今天轰轰烈烈的时代合拍吗?”(注:顾振彪:《人教版1956年初中、高中文学、汉语分科课本介绍》,《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516页。)于是一套以经典作品为主的教材被停用了。此后的教材则变成了政治性读本。在那个年代,不仅是重视不够的问题,而是彻底否定。1958年和1960年人教版语文初、高中教材把《诗经》的篇目都删去了。1963年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1978年第一册、1982年第一册、1990年第五册《诗经》的选篇都是《伐檀》《硕鼠》。看来反映阶级压迫和剥削内容的课文,则成为以不变应万变的保留篇目。直至1996年以后,新语文教学大纲的出台,语文教材的面貌才得到改观。人教版高中教材除了保留《伐檀》外,还增加了《静女》等篇。
再以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例。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经典的,他们的地位也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政治观、文学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其经典的地位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语文教材中这种变化更为明显。1952年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的选篇是:白居易诗四首:《重赋》《轻肥》《买花》《卖炭翁》。第四册古诗二首,有杜甫一篇;绝句八首,有李白一首。第六册选篇:杜甫的《羌村三首》。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材高中版第二册的选篇是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子夜吴歌二首》《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杜甫诗:《兵车行》《羌村三首》《旅夜书怀》《登高》;白居易诗:《琵琶行(并序)》《买花》。此时,三大诗人平分秋色。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篇:第三册,白居易诗二首:《杜陵叟》《缭绫》。第四册,杜甫诗:《羌村三首》。在这轰轰烈烈的年代,是不需要李白诗中浪漫主义的“闲情逸致”的。所以,教材中删掉了李白的诗篇。1960年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选篇是杜甫:《羌村三首》;第四册选篇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岳阳楼》;李白:《蜀道难》。1963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选篇有白居易:《杜陵叟》;第五册选篇有白居易:《琵琶行》;第六册选篇有杜甫:《羌村三首》。从以上课文就可看出,1956年以前的教材基本上是三大诗人地位均等,在课文分析上,既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又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过分强调思想教材,经典作品少得可怜,大量的政论文,时事性强而缺少文采。课文几乎变成政治读物和报刊集锦,极左思潮在教材中随处可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映人民对剥削压迫的反抗,以及对杜诗人民性的阐释成为教材的主流。此时,杜甫、白居易的地位居于李白之上,“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得到了空前的体现。到1978年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李白诗的地位才开始上升。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观、文学观,就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对文学作品的阐释甚至大相径庭。
二、如何理解“经典”与“典范”
经典的作品一般都具有典范性。“典范”是指“可以作为学习、效仿标准的人或事物。”(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修订本,第280页。)扩大一点,还可包括诗文、艺术品等。“典范”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次经典”,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准(这里不是指它有缺陷,而是指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更多读者的普遍认可);二是,强调“对象”,即谁的“典范”。就语文教材编选而言,它包含了年龄、文化知识水平、理解和接受能力、可感性等复杂因素。从“对象”的角度看,“典范”显然还包含着“可供效仿”的含义。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而言,经典的作品不一定都具有可读性和可感性;反之,可读性和可感性强的作品,虽然是典范的、可效仿的,却不一定是经典的。在语文教材的选文中,不能过于强调“经典性”,而忽视现当代一些好的文学作品的进入。这里所说的文学作品是广义的,它还包括除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外的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好文章。这些作品应该是经得起咀嚼的、有一定难度的作品。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年龄,学习阶段上不同“典范”的区分,并注意选文的趣味性。
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够经典的,同时,也是典范的。已有不少片段被编选进教材,如,《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曹操煮酒论英雄》《促织》等。这些作品中学生是可以接受的,小学生则不适合。教材的编选强调经典性、典范性,还要看“对象”。一些热心于语文教育的专家、教授曾为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篇目,包容了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名著,扩大了编选的范围。但教材编写者则应从中学生的接受能力上考虑,并不是所有的经典作品都适合中学生阅读和欣赏的。有些作品虽是经典的,但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却不适合。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以及《金瓶梅》等。另外,选文标准也不能走极端。虽然过去是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思想性、教育性,但是现在也不能完全以作品的艺术价值定取舍而不考虑思想内容。如:很多人提议周作人的作品应选进教材,如果作为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本,没有周作人的作品,可以说是个缺憾,但中学语文教材却不宜选用。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就中学生的阅历、认知水平来看,他们还理解不了周作人“屈节仕敌”的问题,放到大学再学习就较为适合。因此,教材编选应是文质兼美的、典范的、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文道统一”,防止顾此失彼。
有些作品虽不是经典,或现在还没有成为经典,但却是典范的,能够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能够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这一类作品应属于“次经典”的范畴。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选编进高中语文教材就比较合适。这是一篇在当代难得的、感人至深的、风格独特的优美散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作品可选入教材。以诗歌和散文为例,如:冰心的诗《纸船——寄母亲》,徐志摩《沙扬娜拉》,艾青《我爱这土地》,冯至《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流沙河《我是那一只蟋蟀》,戴望舒《乐园鸟》,卞之琳《断章》,余光中《白玉苦瓜》,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辛笛《风景》,牛汉《悼念一棵枫树》,曾卓《悬崖边的树》,穆旦《赞美》,纪弦《一片槐树叶》。还有汪曾祺的散文《葡萄月令》,梁实秋《雅舍》,郁达夫《故都的秋》,冯骥才《珍珠鸟》,林斤澜《春风》,林希《石缝间的生命》,余秋雨《阳关雪》,宗璞《送春》,梁衡《壶口瀑布》,[法]布封《天鹅》,[美]莫利《门》,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日]东山魁夷《一片树叶》,江口涣《鹤群翔空》等。以上这些作品,对于中学生来说是完全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和效仿。
三、如何正确使用和阅读“经典”
“经典”是一种被使用、被阅读的经典。因而,对经典不断加以阐释、加入新的理解,发现过去未发现的“经典”的潜在因素(思想的、美学的、语言的),是使用“经典”的正确途径。在使用上,我们不仅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多种理解的方式,拒绝僵化的“一种标准态度”的方式,而且要考虑学生年龄段和可接受性,不能盲目的标新立异,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在提倡学生阅读经典作品的同时,还要考虑其可读性和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既要强调作品“反映了什么?”“揭示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又要强调读者“我”“读什么?”“怎么读?”突出接受者的主体意识。这样有利于学生对新作品的理解,更有助于学生对传统的、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进而培养学生的阅读想象力,扩大文学作品的阅读空间。语文学习是需要悟性的,它本身有一定的“模糊性”,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就不能是简单的“好”与“不好”。阅读和鉴赏作品是读者一次心灵游历的过程,也是发现作品意义的过程,其结果是千差万别的,它的答案也不止一个,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经典名著《红楼梦》,就其阅读和鉴赏来说,就有很大的探讨和想象的空间。在作品的分析和评价上,就不能一个标准、一种答案。文学鉴赏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认识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与认识,而不同身份的人,又从不同的角度看《红楼梦》。所以,了解作者创作的本意是很重要的。学生对作品真正意义的理解,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完成的。
今天我们指导学生阅读经典作品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经典的被误读。作为教材、教参的编选者,应客观地分析文学作品,正确对待和解说经典,不能用某种主观的认识去肢解作品。如: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学语文教材选取了第四幕第一场“法庭审判”。在教参和许多文章分析夏洛克这一人物时,都有这样一个定义式的评价:“这是一个贪婪、冷酷、阴险、凶残、报复心极强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的形象”。“他集贪婪、吝啬、狡猾和残酷于一身,他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归结为对金钱的贪欲”。对这一形象的评价不仅是多侧面的,同时又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把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简单地脸谱化了。剧中商人安东尼奥和高利贷者犹太富翁夏洛克的矛盾冲突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包含着一个种族矛盾和宗教偏见的问题。这一点在剧中第一幕第三场交代得十分清楚,说明了他的“复仇”既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的内容,又表现了这个人物思想、心理、性格上复杂的多面性。绝不是用简单的“贪婪、冷酷、凶残、吝啬、狡猾”等判断词语能够概括的。我们在指导学生学习经典作品和教材编写过程中,都不能把作品的分析简单化、脸谱化。
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并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着。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地在历史长河中流动、变化,正是这种流动、变化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筛选出符合时代和人们精神需要的经典作品,成为人们提高文学修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教材编写者和语文教师有责任指导学生正确学习、认识、理解、使用经典作品,亲近大师,走近经典,加强文学教育,这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十分有益的。面对中学生远离文学名著的现象,我们应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并抓住教育改革的契机,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除语文知识外,要大量选取经典的、贴近学生生活的、有时代气息的、古今中外的、文质兼美的、题材、体裁风格各异的作品,让语文课充分展示丰富的人文内涵,把学生的兴趣吸引过来,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语文学习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