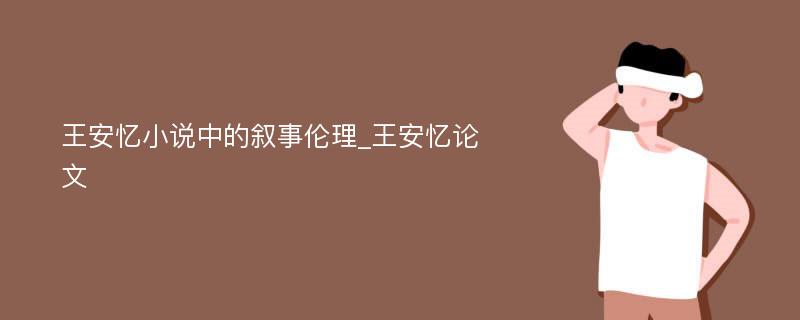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王安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3-0052-05
如果不沿袭评论界将女性-上海-城市重叠的文化批评的路径,回到王安忆小说中的女人形象系列,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世界不复有张洁式的不羁狂放的知识女性的悲怆,亦不复有徐小斌式的特异独立的女性塑型,没有陈染的面对女性自我独吊式的决绝。她们出入她的笔下,或凄艳吊诡,如阿三(《我爱比尔》)、米尼(《米尼》);或凭着不安分的心性改变命运,如张达玲(《流水三十章》)、妹头(《妹头》)、妙妙(《妙妙》);或顺势而为寻一份属己的生活,如富萍(《富萍》);或隐忍而承担终至福降,如郁晓秋(《桃之夭夭》)。早期的“雯雯”故事、“三恋”系列,以及90年代以后的作品在对人性细部的体察中,叙写一个女人经历外在的与内心的一系列的磨难。并非大悲大恸,亦不直指男权文化压抑的要害,抛开性别权利之争,回到经验,回到个体,于观念与故事之间,只提供“形象”让她们来演绎,理智与情感,卑微与琐碎,激烈与失望,也有性、欲望,有一味地隐忍、善良与不甘。而在这些故事背后是一位具有足够理性、智慧,内在力量与平衡力量都健全的知识女性的自我,或者说,是作家的自我与她的人物一起被创造出来,并在女人的经验、命运之处支撑起小说叙事的伦理向度。
刘小枫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观点论述西方现代小说兴起的原因时说:“在近代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而小说“叙事伦理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1] 132相比较而言,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自发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启蒙、政治、知识、学术、教育等意识形态问题相纠缠,已充分地形而上学化了。直到90年代,商品消费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多元状态与零碎经验充斥个人生活,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归个人经验,在对日常性、个体性、私人性的发掘描摹中完成它在框架设定内的一系列的人性目的。王安忆的小说亲证并实践了这一变化过程,她说“我是说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经验。所以一定带有片面性的。这是它的重要特征。”[2] 12王安忆从不以新时代的启蒙者自居,而是在作品中与读者一起体验平实生活中那些让人心悸的瞬间,体味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在《寻找苏青》一文论及大历史与女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时,王安忆说苏青“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是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的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3] 112毕竟在历史前进的大背景下,人的存在是渺小与脆弱的,人一旦被裹挟进历史前行的浪潮中,无论是好是坏,是乐是悲,难以抗拒的宿命是彻底的。而文学与历史记述不同,它对一个时代的见证只能从人生的“边角料”中去触摸,只能从历史背阴处人的身影处搜寻。从性别来说,女人与自然、生命有着更紧密的血缘联系,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以她教育,使她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生命、生活的意义,也更注重自我情感的依托,更侧重于自我生命的体验。这样,“女人与文学,在其初衷是天然一致的。而女人比男人更具有个人性,这又与文学的基础结成了联盟,在使文学回归的道路上,女作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女作家赖以发生并发展的自我,应当如何达到真实?如何表达真实的女性形象?“一个人非常容易将自己想像成为另外一种形象的,而女人又更加倍地多了这种误入歧途的危险。……还因为女人更重视更能体察她的自我,因而也更爱护自我。她们如同编织人生的理想一般精心地编织自己的形象,弄到头来,她们竟瞒天过海,将自己都骗了,以为那编织的自我,就是她们的自我,而实际上却不是。”[3] 79基于上述认识,王安忆将她的人物置于这样的生存纬度:一是女人“此岸”的“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事”,日常性、世俗性是女人的生存背景,其特点是较多的自然成分,而较少修饰,这也是她们天性的基质;二是女人的自然人性要求,比如身体感觉,生命体验,还有如张爱玲所说的女人天性中地母的根芽;三是女人心性中对“彼岸”的执著追求,所谓的“英雄心在平凡的人世间的存在形式”。在此,王安忆为她的人物“寻找与发现”(汪政语)了更为稳定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并以一种近于自然主义的写实笔调书写,但这并不同于19世纪西方文学的自然主义,不是将人生的琐碎、丑陋放大,冷静地解剖,而只是借鉴自然主义的科学精神来观察、研究、收集、记录,运用收罗观察到的人性材料,以一种平实、细密的语言叙述女人个体存在的内在事件、琐屑主事,形成关于女人叙事的伦理基础。
王安忆小说叙事伦理的第一方面内容,是女人在“此岸”日常的柴米油盐的经营,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性情,“幸福”于她们是生存第一位的。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历来将女性生存的权利,改变女性历史文化中“缺席”处境,寄希望于女性的经济独立、人性自由、平等的文化诉求上。西蒙·波伏娃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据自由而不是根据幸福,对个人的命运予以界定。”波伏娃还说“快乐这个字的真正意义是很难捉摸的,仍然有不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隐蔽,永远不能去决定快乐与否”,因此她称,对女子命运问题“我着重的是自由而不是快乐。”应考虑的是女子“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得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4] 6-7但是一些权利要求、宏大话语只能提供社会层面的批判价值,具体到普通、边缘的生存事件,偶发的、局部的个体经验总是难以用文化的构建去囊括,文学也就只能从绝对统一中分离,走向局部、个体。伦理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一些理则,让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养符合这些理则。叙事伦理则是重新描摹人的道德的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尽力谋求它。”[1] 3“自由”、“独立”诸理念相对于王安忆的女人是过于遥远,她们生活于社会边缘,虽非贫贱,但在一个物质的社会里,无论经济地位、受教育的程度,都使她们受到过多的约束。而社会在组织建构、经济状况、社会福利及婚育制度等方面,都还没有为女人的自由和独立做好相应的硬件支持。不仅如此,女性的“生理”、“心理”以及经济情形,使得她们更看中对幸福、快乐的谋求,在更宽泛的道德谱系里,一个按传统方式生活的女人,只要是她心甘情愿,并在其中得到快乐,都不能概言她一定是落后或愚蠢。王安忆的叙事回到女性自身的经验、声音、欲望,有一种知根知底的现实情怀。
小说《桃之夭夭》书名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适家。”言家庭兴旺,贺婚嫁之歌。小说写笑明明,一个滑稽剧团演员,一切生计全靠自己打点,虽难免俗气,但“终是性情中人”。在笑明明眼里,郁子涵纵是百无益处,无一技之艺难以自立,外加破落子弟好吃懒做的习性,但仅为郁子涵躲在窗帘后那怯怯地注视;仅为他敢于弃家追随笑明明的剧团至无锡;仅为再次相见他拿出夹在笔记本中的红叶黄叶,郁子涵就“依然是梨花影中的少年”。随后,笑明明与安稳富裕的生活前途告别、嫁给了郁子涵。笑明明在与郁子涵离婚一年半后果敢地生出郁晓秋,可见其自在自为、处变不惊的品性。母亲一时的任性造就了郁晓秋一生的阴影。私生子的身份,母亲的出气筒,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整个视她为一个“无”,连家里的保姆也歧视她。长大后,工厂里劳作,日里操持家务,甚至后来的失恋,养育姐姐的孩子,她似乎都没有多少怨怼。她一味地付出类似于铁凝笔下的白大省,可与白大省不同的是,郁晓秋一切的行为更多的出自天性、本色。小说写道,“在这个凄凉的时代里,她显得格外鲜艳,而且快活。这是生长本身滋养出来的,多少是孤立的,与周遭环境无关,或者有关,只是不那么直接。健康的生命,总是会从各样环境里收取养料,充盈自己。”[5] 而白大省的“善良”、“仁义”一开始就被文化锁定,她最终没有躲过那小女孩丢下的脏手绢带来的道德叩问,其实她躲不过的是十岁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在她心里的“仁义”,她为这“仁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女人确实是“变成”的。郁晓秋“似乎天生信赖人生,其实不是无端,她是择善,就不信会有大恶”,[5] 凭着勤劳付出,精打细算的心性,郁晓秋为自己寻找快乐,为两个忧伤的家庭传送热闹,为自己谋得幸福。富萍在50年代来到上海,投靠做保姆的奶奶,由此进入奶奶东家的住处——上海淮海路的弄堂,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客厅里的钢琴声、爬满藤叶的旧式洋房。而富萍偏偏从这里的后门溜出,后来干脆不辞而别,直接去了水上工人居住区,最终落户梅家桥。表面上看,富萍是不愿意回乡下与奶奶的孙子成婚,要逃避乡下生活的艰辛。其实不然,她选择的梅家桥,是在一片垃圾场上建立的破旧的棚户,居民生计很卑微,过去拾荒,现在磨刀、贩小食、折锡箔,还有人继续拾垃圾。富萍对婚姻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对安稳、幸福生活的愿望。孤儿寡母,一条腿残疾的青年,阴湿的披屋,靠糊纸合为生,其经济贫困至极,但梅家桥-孤儿寡母让富萍感到“心境很安谧”。在这里,王安忆尽可能地伸展小说的触角,破“壳”而入,汲取实际延续着女人的生存的智慧和幸福观——一种凭感性的而富有诗意的生活方式。
基于女人身体感觉、具体而微的体验,构成王安忆叙事伦理第二方面内容。小说伦理叙事有一个前提,承认个体身体感觉偏好及其差异为人的平等、自由正当性的基础。就个人的身体感觉而言,没有公共道德插手的余地,身体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因而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善恶之分——每个人在自然天性上都是享乐主义者,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寻求的享乐方式之分,粗俗的,或优雅的,“这是人与人之间能找到的唯一区别”[1] 23-24。人类文明的教化使得身体的本能冲动不再像动物那样直接、纯粹和一丝不挂,但人也秉承了进化史上不可讳言的原始的动物性。所以,人的秘密决不仅仅是如传统文化所界定的那样只能从自我意识中去发掘,相反它埋在身体与理性的自我意识对决的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情欲经验中。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将身体的冲动置于存在的醒目位置,叙述人的情欲在挫折中前行,踉踉跄跄,既欢乐又发抖的非理情状。这种身体的冲动有效地锻造了他/她的生活实践,也显示了他/她的性别差异性。
《小城之恋》将“爱”与“性”分离,直接写“性”。他/她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灰色暗淡的小城生活,单调、乏味的练功,他/她由身体接触引发生理的冲动,就好像踩到了以红花绿草伪装的陷阱,无可阻止地往深渊堕落……好比命中的劫数还没有完,他们是逃也逃不脱的。女人最终在孩子的一声哭啼中拯救了自己,女人的性欲被做母亲的天性所洗涤,而男人则一味地颓废下去。小说《荒山之恋》叙述他/她由“性”走到“爱”的过程。大提琴手,一个阴性气质的男人,他天性中的激情给了音乐,现实需要、责任给了家庭,而作为一个男人本能的“性”一直蒙昧未开;金谷巷女孩,因为美丽,因为过早地知晓男女情事,反而没有真正的情爱体验,她鲜活的生命激情是在遇到大提琴手之后才被激发出来。小说采用逐层剥离的叙事手法,先是除去附着在人物身上社会家庭应承担的责任、道德规约,然后剥除传统性别文化制约下,他/她主动与被动角色认定,让他与她相遇由身体感觉的引领走向性,由性发展为爱情,最终走上爱的祭坛。《锦绣谷之恋》的开篇展现在叙述人的“注视”下家庭生活隐秘的一幕:睡眠、早起、洗漱,而这一切经由那位妻子探究式的“审视”,形成双重视角,对日常作出判断:婚姻生活的惯性,使得身体麻木,情欲休眠;女主人公从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孩渐变成一个喜怒无常的少妇,成为耽于形而上感情追问的“精神单身”。一次“出差”仿佛是对女主人公“精神单身”的一次事实求证。出差的“她”恰遇作家的“他”,在另一位陌生的、令她心仪的男性目光“注视”下,她身体的感觉开始复活。锦绣谷缭绕的雾气隔开了他/她与世俗生活的联系,也遮蔽了彼此在尘世中的面目。他们当真沉醉其间,心与心交流,信誓旦旦。但拥有浪漫情怀的他们毕竟身处尘世,况且,她与丈夫的关系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淡漠,丈夫送行时随火车奔跑的身影,不时时出现在她的脑际中么?由游移于浪漫到最终返身红尘,以至安定,仍会有内心的不安、躁动,仍若有所思的等待,但已不是为了某个男人,某一段情感。她找回的那一种原生状身体感觉,被置于闲闲淡淡的婚姻生活中考量,可供她清除日常淤积于胸的情绪“垃圾”。其实,在社会文化、教育、世俗规约中,生命的意义被各种观念加以解说、阐释,带上理想神圣的光环,但却忽略掉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身体是生命的基本物质形态,各种生命意义的言说,都必须通过身体的体验转化为身体的感受才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王安忆在小说中试图把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还原为身体的具体感受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具有的意义上。
女人的身份比男人更多伦理色彩,诸如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朋友(情人)等,尽管启蒙运动以来一直鼓吹普遍的人性解放、自由、平等,但实际情形是,女人只有在家庭获得伦理定位,才能确立作为人存在的正当理由。女人的情欲正如其服装,被繁复的装饰物遮蔽,幸福美满是爱情与婚姻的允诺,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和不以爱情为目的的情欲,都被标示为不洁、卑下而清除出女人的意识。女人的情欲常常是以别样的方式成为性货币,在婚姻和商业市场流通。同时,在人们的性别认知上,身体的权利,一直姓“男”,身体书写者也姓“男”。女人或女人的欲望围绕男人行事,女人要么是祸水,总是将男人导向毁灭,如果他正仕途畅达、春风意满之时;要么是圣母,如果他正遭遇权利社会的排斥,倒霉、沦落之时;要么把女人物质化,在商业社会女人并不是更自由、更“人”性了。这里涉及到一些问题的对立,男人-女人,人-身体,爱情-情欲,形成积极与消极,高贵与低贱,赞美与诅咒,而所有的判断是出自我们思考的偏狭对后者的盲视。王安忆小说的思考对象发生了转移,她首先从性别立场上调整了对于人的身体的态度,在转换中发现女性生命的无限秘密,在经验上丰富了女性的内在感受。所以,王安忆说“其实我的小说确是回到了写人自身了”[6],更确切地说是回到女人自身。
呵护现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感觉的叙事本身就建立了小说叙事的伦理道德,但这里的伦理道德,与公共领域里与国家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道德秩序是不同的。其差异性在于,由国家意识形态、公共道德等一切形而上道德指令共同打造的是一套“通用语汇”,为人们的生活指示方向,判定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合乎规范,它有以下三个特点:确定性——因为有一个确定的本质实在;可以提供价值判断的尺度;可以为人处于安稳状态提供依据。而王安忆将“个人”、“心灵”、“片面”这些词叠加形成小说的“个人语汇”,与“通用语汇”相对,悬置价值判断,让叙事在道德判断之前展开,建立一种关于小说叙事的模糊伦理学,即是寻求道德的多样性和生活信念、生活方式的新奇性,拒绝进入明确的道德世界——形成自己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
王安忆探讨人的道德困境的小说起始于80年代末,在对这个世界既欲亲近又欲逃离的矛盾中,她想揭开文化与人性的层层覆盖与辎重。《流水三十章》中的张达玲三十年的人生是扭曲的三十年,这源于她与现实的不合作。其实,大多数个人的生活都是普通而又低层的,但若像张达玲那样灵魂生出太过活跃却又不合实际的念头,并且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获取符合自己过高心志的社会地位,这样她的人生必然陷入悖论。王安忆自言“我在《流水三十章》所做的,即英雄心在平凡的人世间的存在形式。所谓‘前面是光明的颂歌’其实就是汇了大多数人的世界,那世界着实是温暖的,我让张达玲做了妥协,因为我不忍让她承担残酷的英雄的命运。”[7] 2-4米尼、阿三有类似于张达玲的极端,但却没有张达玲那样幸运,能够找到安全的舢板,渡出人生的险滩。米尼在偶然的机遇认识阿康,此后的十几年她身不由己地进入了一个丑陋、黑暗、无廉耻的罪恶世界。回首过去,米尼总是在问自己:阿康,你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呢?“如果不是这一天回家,而是早一天回家或者晚一天,那将会怎样呢?这一天就好像是一道分水岭,将米尼的生活分成了两半。”[8] 5这纯属于偶然,米尼的命运在那一刻就决定了。“她记得她回过头去的时候,明亮的三星忽然向西行走了数十米。由于她们是在向东行走,那三星就好像是划过了米尼的头顶,在天空走了一个弧度,向后去了。这一瞬间,米尼无比清晰地感觉到地球是由一个巨大的弧形苍穹笼罩。她觉得,以后发生的一切,在这时是有预兆的。”[8] 4那三星是米尼的幸运星么?是它把米尼的一生幸福带走了么?
阿三的故事其实是米尼故事的重写,不同的是故事的表面,相同的是内里命运的底色。学美术的大学生阿三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美国外交官比尔。比尔爱中国,喜欢阿三的“特别”;阿三爱比尔,却有着祭奠般的壮烈。当阿三脱去层层叠叠、重褶中裥的衣服,那层象征古老文化的符号蜕去,以处女之身与比尔完成初夜时,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点共同的人性。一旦俩人穿上衣服,他们的关系就变得不平等。比尔走了,比尔带给阿三的异国气息,一种文明的氛围,一种西方男性的身体魅力,永远留了下来,结纠于阿三内心萦绕不去。命运给了阿三一个机会让她深陷其中,又不让她实现爱与被爱的愿望。阿三一步步走来,不知不觉得已走到了深渊的临界点。性与爱可能只是一个题材问题,它们只是喻体,而本体则是人们自身也无法左右的性情和那些总是悖逆着人的意愿的不可知的力量。这一类小说真真打动人的地方也许是:一个人经历深度的情感裂伤后如何生活?什么叫做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无助与无奈?“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的基本元素。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其实相当片面。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生活。对这一个人来说如此轻逸的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比死还不如。”[1] 206-207阿三们的无奈感是其个体性情的必然。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人的伦理问题与社会、道德没有直接的关系。王安忆在采访记实中写道:“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是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可能性!”[3] 73人生来都想做好人,可如果人本性善,那么恶从何而来?对个体而言没有一个合乎逻辑、又明确的答案。恶所以会滋生,是因为人总会在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时刻失去方向,或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能力行善。恶导源于人的挫折感。无论人的改变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也不可能对人为什么会无力行善作出结论,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女性”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没有被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性别问题,其人性诉求、生存选择与命运走向也不外乎是某些个人的幸福或不幸,但关于“她”的叙事总是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与个人的性情意愿及价值意愿编织在一起。因而,“她”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拒绝流行的概念的夹带,整饬属己的生存经纬,作为生命实体的女性得到了某种更接近原貌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