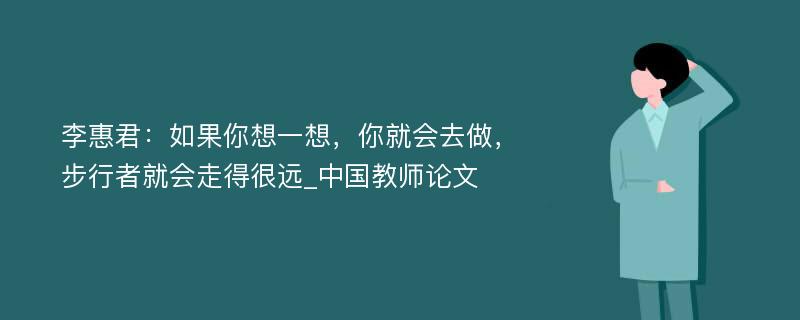
李惠军:思者行,行者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者论文,李惠军论文,思者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没有创意,历史课就没有灵魂
《中国教师》:有人评价,“广博”“深刻”是您突出的教学风格,您怎么看?
李惠军:很难说我有什么教学风格,但我一直在追求教学个性。历史最大的特点是讲究论从史出、史从证来,所以人们想象历史教学永远穿着中山装,迂腐呆板、亦步亦趋。其实,历史教学的严谨、规范,恰恰需要教师的灵感和创意。
文学家杰克·伦敦说过:“我的天地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创作需要天赋,它首先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灵魂的搏击和生命的燃烧。”他讲的是文学创作,但时常是我进行教学创意并突来灵感的体会。创意决定教学品质,是形成教师教学个性的前提条件。我认为,历史教材并非历史,历史不是一串串干瘪的教条,它应在教师深刻的哲思与生动的表达中得到还原和丰富。
《中国教师》:形成历史教学要追求创意的理念,您受谁的影响最大?
李惠军: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老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是著名史学家赵俪生的学生和女婿——孙达人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并非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而是农民战争》的文章,挑战了传统的观念,毛泽东同志曾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上课从来不带任何教材和讲义,他将全新的理性思考与丰富的史学材料无缝连接,似行云流水,洋洋洒洒数万言,常给人以猛烈的震动。在我几十年的历史教学中,他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一直以他为顶礼膜拜的楷模。
《中国教师》:您刚登上讲台时背下教材、不带讲义上课,是否就源于对孙老师的崇拜?
李惠军:有关系,但也有触发事件。我是77级大学生,大学毕业时23岁。因为那时大学毕业生非常稀有,所以我一工作就被安排教高三。第一次家长会,家长们见到脸上没有皱纹、满头乌发的我,流露出相当的惊异、怀疑和担忧:这么年轻的教师能教好吗?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怎么才能赢得家长的信任呢?我要用娴熟的教学让他们放心,于是我一字不落地背下了6本中学历史教材,包括图表,并把全部教材内容按照时代、专题和国别,用“纲要信号图式法”归纳为复习大纲,甚至把全部教材刻成填空题,若干填空题组合为一道问答题,油印后发给学生进行自我测试。除了上课与学生“摸爬滚打”之外,我还把行李搬进学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上晚自习。昏昏沉沉地带了一年,直到第一届毕业生在历史高考中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班里出了全疆文科状元,我才感到那次危机过去。那次信任危机让我将对孙达人老师的内心崇拜转变为现实的仿效行动。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习惯。
《中国教师》:您觉得历史教师都应做到这点吗?
李惠军:我倒不主张别人都像我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经历和性格都是不同的。有些教师性格内敛,他可以像一把刻刀一样,细细地雕琢课堂。有些教师属于激情型的,他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忽入高山深谷,忽入平静的港湾。但无论各人差异如何,历史教师都要赢得学生心灵的共鸣,使师生共同沿着时间隧道回到当年的现实去观察历史、思考历史。教师要有自己的教学创意,否则,历史教学就成了对城南旧事简单的追忆和回顾,对过去琐事的堆砌。
《中国教师》:您背教材是为了创意吗?
李惠军:那不是为了创意和设计,只是为了模仿老师的洋洋洒洒,赢得家长的信任。那个时候连设计的理念都没有,教学就是把课本交给学生,学生上了高考战场赢了分数就行了,所以教学只要有执行力就够了,而执行力和设计力、创意力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教的是教材,而不是历史。教材绝不是历史,只是历史的一种呈现方式,如果仅仅教教材,那么完全达不到让学生听历史、想历史、懂历史的目标。如何让学生进入历史,让一节课有自己的立意、境界、品位、格调?那需要创意。如果没有创意,教学就成了千人一面,无论哪一课、无论哪个教师教,都是把背景、内容、过程、影响、意义按部就班地讲一遍。
2000年前后,上海市举办4年一度的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作为评委我先后观摩评议了20多节课,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人用倒叙法,有人用中心开花法,有人师生共研,有人慷慨陈词,但却大同小异,严重缺乏一种品质、缺少一个灵魂。一节课如果没有灵魂就很难有个性,教师就不得不遵循教材的格和序来完成,这样的历史课实际上是没有味道的。那时候我就在思考:如何让历史课上出品质来?要有创意,要在科学和艺术思考下创意出一节课的灵魂。
《中国教师》:你所说一节课“灵魂”的创意,到底指的是什么?
李惠军:一节课的灵魂是整个教学设计的主轴,是教学活动的主线。例如,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工作室从国家意识、主流观点出发设计了这一课。第一环节:辛亥革命的酝酿。我们给学生讲了4个故事:暮鼓晨钟——革命党的成立;壮怀激烈——“苏报案”的故事;大义诀别——林觉民的《与妻书》;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即将成熟。这一环节以人物(孙中山)为主线,以故事为载体,以动情为落脚点,这就是这节课的主线。其中,故事是主线的素材,手段是主线的工具。
如何创意灵魂?灵魂的发掘需要逻辑性思维和意象性冥想的结合。我认为,历史教学固然需要严谨的逻辑、细密的推敲,但课堂教学绝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逻辑推理是思维的骨架,它规定了历史教学的边框和疆界,这是不能逾越的。但我们更需要怀着对历史的崇尚和敬畏之情,展开历史的想象,有血肉地建构历史推论,形成有情、有神的外形。这样,历史意识才有了从教师向学生传达的载体。一位教师连自己都没有在演绎思维中使历史过程的碎片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还怎么指望学生能辩证、完整地体验历史呢?
在这节课的第二环节——辛亥革命的发展,我们就刻意在历史边框内“着色”:楚望台上的枪声;大清帝国的坍塌;南京城头的盛典;《临时约法》的颁布。辛亥革命的发生如何从必然演绎成实然?辛亥革命的必然、偶然、实然就是这节课的灵魂。历史课有了灵魂才有了生命,课堂组织才有了个性。
《中国教师》:在论坛上,有教师和学生说,错过您的课是终生遗憾,但也有教师质疑,新课改的形势下不是讲究教师少讲学生多动吗,那您在课上怎么讲那么多?
李惠军:课堂教学是双边活动,新课程理念强调的是互动。教师在呈现历史的同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共鸣或质疑?我们在热烈讨论、执著实践之余,必须理性、冷静地思考一个最简单、最原初,但却最起码、最关键的问题:学生“动”起来的前提是什么?那一定是学生首先要“听”,乐“听”、善“听”。学生听清了、听懂了才谈得上真正的互动。历史学科是公民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一个“小”学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样让学生喜欢听?那需要创意。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教师对丰富历史的呈现力和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再现力正日益消退,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像孙达人先生那样,充满哲思,行云流水般地表达历史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语言大师了。
学生动没动?不是看学生有没有“声动”“行动”“群动”,而是看学生是否在“心动”“情动”“神动”“思动”。孙达人老师就带一支粉笔上课,我们经常被他的哲思和悬念打动,我们看似没动,但一下课我们还要查资料、追着老师探讨,那不是“动”吗?
还以辛亥革命为例,学生在前两个环节中听了很多故事,学生光听没动吗?我们先不急于找答案。第三环节,该讲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了,很多教师直接就把辛亥革命的意义、局限性拿给学生,学生虽然当时得了100分,但可能多年以后还是不明白书上辛亥革命的意义那几句话。
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将教学设计为“走进先烈的精神世界”的交流和探讨。我建议给学生播放胡锦涛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视频。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听,兴致勃勃地发表看法。为什么学生能喜欢听政治家的讲话?是因为前边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已经打动了他,这是情感的内化过程。他听完想说,这是外化过程,因为他对孙中山有自己的认识,他想寻求共识。他们从胡锦涛的讲话中得到了情感的共鸣。
在课的结尾,我建议教师引入了一个材料。著名的《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烈士是福州人,1996年他的家乡在仓前公园为他树立了一个雕塑。不想几年之后,斑驳风化的雕塑倒在一个公共厕所旁。就是这尊革命志士的雕像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变成了不愿意交3毛钱如厕者的小便槽。雕像除了头部完整,身体出现了大洞,里边全是乌七八糟的垃圾。我建议教师就介绍这张让人揪心的图片,让学生看清雕像的眼睛,配一句话外音:“雕像静静地躺着,目光坚毅地看着前方。”如果林觉民有在天之灵,这位革命志士会作何感想?学生看着图片一动不动,眼睛里闪着亮,透出一种无奈、遗憾。
激烈的情感冲突带来了深刻的思考,课后学生们的问题蜂拥而至,我建议又加了一节课:“回首百年前的思考”。这节课突出哲思,解决两个问题:辛亥革命该不该发生?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这也是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的一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该怎样地发生?
学生查了资料,讨论非常热烈,师生与历史在对话中产生了多元碰撞,最后达成了共识,通向革命的道路要从广域视野下进行历史叩问。一方面,这场革命要放眼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的屈辱和阵痛看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定格于辛亥革命前的10年发生了什么来看它的偶然性。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讨论前我们给了学生各方面材料,包括教材观点、政治报告、时事新闻(如马英九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网络评价,甚至包括李泽厚一针见血地说辛亥革命搞糟了,让学生在讨论中去辨别。
从以上学生情感“内化——外化——共鸣——冲突”过程的创意中,我们没让学生动起来吗?课堂教学首先要让历史在学生心中留下烙印,唤起哲思才能谈到学生真正的“动”。认为互动必须是什么形式的“动”,多长时间的“动”,都是对新课改理念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另外,我们不能把思想家的观点写进教材变成天条语录,让学生无论懂与不懂都要接受,在教学中又让学生轻易地渡越一个本来难以跨越的思维空间,轻易地接受一个本来难以感受的情感过程。
二、“求新、求奇”“求实、求用”相辅相成
《中国教师》:有教师会关心,您这种“求新、求奇”的创意对高考成绩的贡献有多少呢?
李惠军:虽然我认为高考不是成材的唯一基点,但我能理解中学教师最现实的任务,教师必须面对社会对学生的评价,包括高考。其实,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拓展和高考命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性评价和选拔性评价已经变得密切相关。例如,2001年上海高考题“老山汉墓走出了西域美女”,它给出对墓主人身份的各种猜测,问考生对各种猜测持什么观点及理由,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及用哪些方法去搜集证据。从这道题的立意和指向来看,这明显是在考查学生对历史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和学科意识。悄悄变脸的高考命题已经不容我们再为是否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而迟疑了。
在这点上,我早已受过强烈的震撼。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已经教书10余年,对高考来讲我感觉已驾轻就熟。我不仅用两年时间把课本背下来了,而且后来一两年我还建立了教材结构系统和纵横联系。那时是沾沾自喜的,以为把历史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后来突然出现一道没见过的题。恩格斯1895年去世前有个政治遗言,从当时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搞无产阶级革命时机还不成熟。当时教材可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无产阶级从产生以后就变成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了,让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发抖吧,我们要打破枷锁。怎么恩格斯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到时候呢?这不是教材中批判的“修正主义”观点吗?恩格斯怎么成了“修正主义”?别说学生,连教师都懵了。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把历史看清楚。这给了我两个启示。一是我必须走出沾沾自喜的教材,去了解一下史学界研究的动态。我不是历史研究者,但我必须是个涉猎者。二是学生没有研究过,就没有问题意识,更谈不上研究的规范和研究的能力。将来走上社会以后,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容器,而不是一个挖掘机。或许当年像我这样受到震撼的少有的几个人先有了这样的启示,从教学行为上早走了半步,从那以后我们在高考上基本上是不败者。
我们的学生研究辛亥革命该不该发生,从近60年看必然、从近10年看偶然的学习过程,就是给了他以后从长时出发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所以教学不但要求新、求奇,还要求实、求用。
《中国教师》:您的工作室有什么“求实、求用”之法?
李惠军:我提出,我们不仅要有立足于“求广、求博”的素材库,包括符合课改精神的各种创新手段,而且还要有立足于“求实、求用”的基本课件库,力求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对历史的系统获得结构性认识,并把每一个历史现象在系统中各就各位,进而将派生出的问题建立题库。对于学生评价来说,学生理解了结构,就会把历史信息在问题情境下激活,变成回答问题的素材,最后转化为分数,如此而已。但问题绝不是简单地对应某些知识,做题库并不是让学生陷入题海,而是用适切的、经典的、相关的问题,让学生悟出方法,这就是问题方法化。
为什么很多学生做了很多题之后不会做题了,读了很多书之后不会读书了?关键是教材没有问题化,问题没有方法化。“求实、求用”要有工具,题库就是一个将教材问题化、问题方法化的工具。除此之外,我们为教师培训还组织了很多经典案例,建立了电子教案库。
《中国教师》:在教师培训中是否有人提出过困惑,学生除了上课、做题,哪有研究性学习的时间啊?
李惠军: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固然可以通过独立的研究型课程加以体现,但是,实践中研究型课程是“杯水车薪”。在中学里,历史这个“小”学科如果每学期能有5次(每次2课时)研究课的机会,那真是阿弥陀佛、无量天尊了。
但这并不等于历史教师就束手无策了,历史教师完全可以在创意中向常规教学渗透,让研究性学习在必修课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是在“求实、求用”前提下自然流露和适切融入的过程,它就不是刻意附加的第二件事情,而是一揽子工程。
我徒弟来问清朝闭关政策怎么讲,我建议不要增加负担,但要有研究性的氛围。我们现在都在批评清朝闭关,认为闭关是非常愚蠢的,教材也是这样评价的。当时的康熙、乾隆是多么聪慧、阅历丰富,但为什么作出了一个让我们今天这些凡夫俗子都感到极端愚蠢的决断?西方国家不能闭关,我们为什么能闭关?明朝没闭关,为什么清朝就闭关了?关是闭不住的,但我们如何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闭关?这节基础课中没有另加东西吧?但符合课改精神吧?有研究性因素吧?而且,高考完全可以出这样的题呀。实际上,3年前我在给上海某个区命题时已经把这道题出了。
三、思想着,思想着,收获生活
《中国教师》:就您的经历而言,什么促进了您的专业成长?
李惠军:外在的冲击和内在的困惑给了我力量。例如,初登讲台家长的不信任,给了我打击,我背下来了教材。20世纪90年代,我已经成为特级教师,那几道高考题打懵了我,我开始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读刘宗绪、黄永年等专家编的大学历史教材。
到了上海之后,赶上一期课改,历史教材中外混编,不能适应上海的历史教育文化和课堂教育生态,我不断地追问历史教学的有效性。进入二期课改后,历史教材由按社会形态结构变成了文明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文明史结构下,我该教学生什么?我茫然不知。这些一次次挑战和冲击,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困惑和贫乏,迫使我不断思考,把危机变成转机。
教师都是践行者,而任何践行都需要思想,任何时候教师的践行都应该是进行时态——思想着,思想着,一直思想着,哪怕你的思想碰到一个鸿沟,也比你不去劳动,轻易获得一个看似真理的思想要好得多。
当然,开放的心态很重要。一种文明如果是封闭的,不和其他文明相交流,注定是要死的。中学教师要想发展必须与他人广泛交流,接受异质文明,获得新的文化。例如,前几天我和华东师大的余伟民教授交流,他偶尔说到一本书《带一本书去巴黎》,我找到一看果然不错。如果历史教师都读过这样一本书,那么再讲法国大革命就会别有情致。
我有工作室以来进步很快,因为我与很多徒弟交流时有了重新修炼的机会。我晋元中学的一个徒弟讲“唐朝的制度建设”。他采用了我的一些思路,但有的他否定了。唐朝为什么是蒸蒸日上的?他从关陇集团的胡人血统,唐朝三省六部制度已带有权利制衡要素等史料中找到一些根据。这个确实让我提高了。我跟徒弟讲,我一辈子没教过几次好课,但我的教训、我的创意都可以让他们少走弯路。徒弟们尊重我,用我的思路去研究,发现我的弱点,让我进步,这是对我的爱。我也非常自豪,教出了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的好徒弟。
《中国教师》:您从教30多年,除了教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徒弟和高考状元,还有其他收获吗?
李惠军:我大学毕业时,著名史学家史念海先生曾给我赠语:“宁可劳而无获,不可不劳而获。”这句话对我鞭策终身。30多年来,历史教育是我最大的收获。有了历史教育,我的生活就是完全的,有了历史教育,我的生活就是有品质的。
(李惠军,上海晋元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