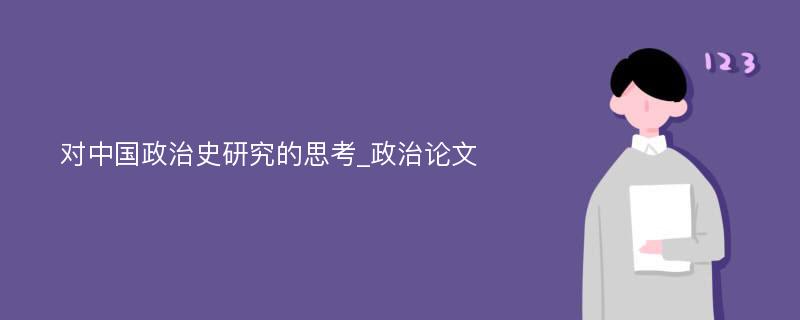
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9)02-0108-05
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这恐怕早已是学界的共识。反思不仅是归纳以往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为今后研究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路。笔者不揣浅陋,以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就教于大家。
一、重提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努力:从社会史到政治史
本文先从政治史地位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谈起。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引进了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诠释框架,它将人们的研究领域从作为上层的国家,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基层社会,从而让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新鲜感”,各家研究纷纷转向。这种形势进一步发展,直接推动了基层社会史研究“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1](52),逐步占据了“显学”的交椅。然而,由于发展不平衡,随着研究范式向“微观叙事”(姑且以此称谓区别于“宏大叙事”)转型,人们过分偏重“社会”的同时,却忽视了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淡化。继以往“革命叙事”、“宏大叙事”所走极端之后,史学研究大有走向另一极端之势。这种趋势对政治史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作为传统研究重点的政治史不仅退居社会史之后,甚至走向被人遗忘的边缘①。
不可否认,造成政治史研究衰落的关键在于自身原因。长期单一的研究套路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无法给人们展示出更为鲜活的历史画面,特别是在人们试图绕开“帝王将相”的历史,日益关注大众历史之时,以往政治史研究内容及方法捉襟见肘。正如赵世瑜所批“事件史”(即重大政治事件)和“制度史”软肋时指出的:处理其他相关问题,特别是其社会情境和实践层面问题软弱无力从而限制了在对深层次问题的解释力[2]。而“微观叙事”则有利于转换思维方式,打破传统“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模式的束缚,将“帝王将相”的历史变为“人民群众”鲜活的历史,其不同的方法与取向使人耳目一新。
尽管如此,有一条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国家与政府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实体所无法取代的,特别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政策的出台直接或间接影响、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并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至深且远的影响。正因此,在我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是皇帝、官僚,“大政府”的观念历来根深蒂固,人们始终怀着“由一个强有力的好的政府出面包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期望”[3]。可以说,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即是国家政治在不同维度的延伸或扩展。因此,政治史研究不仅不能被弱化,反而应该大力加强。这一点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面对政治史式微的局面,杨念群发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表示了“同情”。文章指出:“此文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因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政治’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和许多血泪横飞的苦痛记忆密不可分,它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上层的实践,也是下层的感受。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由于现代国家建设的不断介入,具有了远较古代更加复杂的涵义,也非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手段所能胜任。”[4]显然,杨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思政治史研究中“革命叙事”和“制度史”的弊端,而为政治史开出一剂药方。然而,此方明显存在缺陷,即其并非以政治史研究自身的升华为根本,更多强调了汲取政治史之外有关内容,主要是社会史的“营养”,使得政治史的主帅地位并未因此得到相应突出。
正基于此,赵世瑜对其亦直接表示异议,他认为杨念群重提政治史,是在“试图关注近代政治的强烈渗透性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意味何在。在我看来,这种问题意识与其说是政治史的,不如说是社会史的,至少,它体现了被社会史取向改造了的政治史。”他提出,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史如何“介入政治”。赵世瑜借鉴了法国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勒高夫对政治史地位评价的经典话语——“在从解剖学时代走到原子能时代以后,政治史不再是史学的支柱,而是史学的核心”,以此作为社会史“介入政治”的基本理论依据,指出“社会史并不因‘政治’在近代以后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力量而需要对它特别关注,它始终应该成为社会史力图说明和解释的对象,关键在于这说明和解释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同时,他以孔飞力的《叫魂》为例,举证了社会史“介入政治”的具体方法,就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地位进行了界定:“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1](62-65)。这一点如从“搞活”政治史研究角度加以审视,与前引邓小南所述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对政治史核心地位不同程度的强调,在当前人们对社会史趋之若鹜之时是难能可贵的。以上论断,亦成为学界部分学者意识到研究的非正常倾向,并尝试作出部分纠正的体现。遗憾的是,杨念群提出的关注近代以后政治对民众生活渗透的建议,其初衷不无道理,但如赵世瑜所评,他所重提的“政治史”乃是社会史改造的政治史,仍不出社会史的势力范围。而赵世瑜的“介入”法,尽管亦有合理之处,如全面分析,充其量也只是为研究政治史提供了一种路径或角度,因为“介入”一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方向性意义。我们可以同样方式,从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领域“介入政治”。赵世瑜等对此还有更明确地表露: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5]。由于其研究基础在社会史,以基层社会的视角透视政治史内容,这对政治史无疑是一种推动,但是就根本而言,仍走了政治史的外围,只提供了从外部窥视“政治”的角度,并未深入到政治及政治事件的内部;只提供了认识政治史内容的条件和手段,并未将政治史探讨的“政治”的真正内涵和灵魂阐发出来,充其量是从政策、事件等政治问题的反响层面作出了一定诠释,究竟国家政治运作呈何态势仍不得而知。一言以蔽之,他们仍未逃脱社会史的“掌控”,并未找到政治史的“核心”地位到底应该如何体现。
二、中国政治史究竟该如何研究
在笔者看来,政治史的本质内容在于“政”与“治”两方面,即国家(政府)政策(包括制度、方案)的制定与执行(即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两个层面。按照《辞海》的解释,“政治”有两种含意:其一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其二为“国事得以治理”[6](1773)。前者为传统意义上抽象的政治概念,后者则为现实中的具体政治概念,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国家如何得以治理、治理的成效及影响如何等等。围绕“政治”本身来展开,这些内容最为接近现实生活,是能够为人们所“亲眼目睹”的实践过程和结果。因此,我们借鉴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背景知识的同时,若将政治史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就不能只为政治史谋求某一角度的背景,或单从某一视角来诠释政治,更遑论完全脱离政治史闭门造车,“自成一家”。如社会史比较关注基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但是这种关注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只顾基层社会,反而置国家、政府层面的问题于不顾,这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不相合。如果纯粹为了克服以前只看上不看下的弊端,反而只看下不看上,那将同前者一样,均将走入歧途和极端②。当然,本文并非反对开展对基层社会的研究,只是反对那种钻牛角尖似的刻意追求,尤其是套用西方理论,执意建构起以西方为模板的中国社会架构。相比之下,史学研究的进程仍应保持政治史的主帅角色,深入国家政治的内部,开展对国家大政及其国家治理等课题(即侧重政府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的实施及其实际反响与效果,用现代词汇讲就是国家治理与“政府绩效”)的研究,探讨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及思想、现实的逻辑,学术路径上则以政治史向其他领域发散,而非单纯相反由其他领域向政治史集中。以此为前提,各领域的研究才能更符合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实际。
政治史究竟应该如何研究?除传统思路外,研究如何继续深化?许多前辈学者已多有阐述。1940年,周谷城在其出版的《中国政治史》弁言中指出:“本书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制度史;更与一般专讲理乱兴衰的政治史绝不相同。”[7](弁言)周氏显然是在试图避开所谓的政治现象(即理乱兴衰),专注于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如氏族、门阀、藩镇商人与地主等等),因为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主题不外乎政治斗争(如君权与相权、君权与外戚、宦官、中央与地方官员等权力与利益之争)与政治制度(如选官制度、监察制度等),因此周著不可不谓为政治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若论对政治史研究阐述较为系统者,当属梁启超、钱穆二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政治史应研究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民族、国土、时代、家族和阶级,这是政治史的基础,“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变迁。”第二部分是“政治上制度的变迁”,其中包括中央政权的变迁,具体而言,除政体外,“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各种政权如何分配?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这样中央的政治组织和中央权力的所在,须分类研究其变迁,详述其真相。如司法、财政、外交、民政等。”第三部分则为“政权的运用”,即政治的实际运作[8](269-272)。钱穆则指出:“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9](18)从表面上看,钱穆关注的重点在于今天所谓的政治制度史,但是如果详细分析他在讲述政治史研究所参考、引用的例证时便可发现,他所谓的“政治史”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其一,制度史,即所谓的政治制度,如监察制度等。其二,政府政策,如他在文中所举汉武帝时代的盐铁政策,“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9](33~34)。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政治制度明显包含了政府政策这一层面。其三,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他提出:“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理论之存在……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9](33-34)
若就梁、钱二家高论而言,梁氏长处在于综合概括,但仍将历史划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研究,政府政策亦分散见诸各方面。钱氏优点正在于具体地从中抽绎出了“政策”这一命题,打破了以往分头进行“割裂”式研究的做法,更非仅以“权力”及纯粹的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于对“政治史中的政策”、“经济史中的政策”等命题的简单描述及表面性主观概括与评论(如“规模大”、“涉及面广”、“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更忽略了政府作为历史性实体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未能将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作为独立的问题和线索抽绎出来予以关注,更遑论将其上升到政治史研究主线的高度。需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王凌明确将人们一度忽视的“国家”和“政府”纳入研究范围,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③一书,从经济史到政治史实现了一个转变,并把几种历史联系起来;此后又抓住“国家的视角”,达到了新的近代史观的转变[10]④。在这中间,政府问题无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研究思路值得关注。
法国学者魏丕信指出:“我的研究重心着眼于分析和理解这个官僚系统,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下,用什么样技术上的办法和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来控制和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管辖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正是‘教养’一辞的微言大义,也可说是传统中国政府计划中最核心的课题。换句话说,皇帝、朝廷、中央政府、地方行政单位直接负起的责任不仅是保障人民的生计,还包括了教化民间的时尚、道德观念、礼仪、风俗,从而建构宇宙和人间的秩序,也就是臻于‘太平’境界。”[11](222)因此,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被纳入国家政治“改造”的范畴。黄仁宇所谓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职能主要侧重“管理”,而非“服务”,也正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插手,从而将其纳入政府“控制”之下[12]。作为一国治国大政的取向,为达到教养子民的目的,政府制定和执行种种政策措施以施加国家的意志和影响。如此,国家意志和行为自然引起了民众生活或深或浅的改变。这些在18世纪的中国表现得尤其突出(当然并不仅限于此)。面对人口急剧膨胀的现实,政府积极、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农业、粮食、赈灾、矿业、慈善事业、河工、塘工等各领域均出现了重要的政策调整,许多历史性难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和解决。政府职能加强,因此与人口持续增长、边疆开拓共同成为18世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产生“共时”现象的三大标志。政府的这种行为态势是我们绝对不能漠视的,而这些鲜活历史的创造除人民的参与外,政府发挥的主导作用又是任何个人及社会实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图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别以上“政”的下达为主导,加之由此折射出的政治文化等共同组成了政治史研究的主流内容。这正是政治史作为历史研究“核心”地位的体现。
总之,政治史研究欲图重振,不仅要克服“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4]的弊端,在方法论上注重强化“问题意识”,做到言之有物,具备洞察力,致力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实在逻辑,而非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13](3)。另一方面则要在研究对象及研究主线问题上作出更加明确的判断与选择,即在传统的政治斗争、政治制度等内容外,将治理国家的各项“实政”,不仅有以往研究较多的政治、民族、文化方面的政策、行为,还应将经济政策等,如盐政、漕政、农政、粮政、矿政、财政等等均作为研究的重点,既关注大政制定的背景、经过等内容,又要探索其实际运作的各个环节,如皇权与官僚在政策推行中的关系变化、地方高级官员与中下级官员的态度反应、政策推行的方式、政策与基层民众产生的摩擦与融合(政策推行的社会效应,或言政策的渗透性)等等,凸显社会事务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问题,并以此为依托,研究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阶段性或整体性特征。这样,我们的政治史研究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真正得以深入。
注释:
①邓小南曾以宋史为例,对政治史研究的导向及讨论的对象重新进行了阐释。前者要求超越描述性研究,更加注重所谓的“问题意识”;后者则应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过程、行为和关系的探讨,突出人的行为。(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下同,第2—8页)不难看出,邓的核心观念在于将政治史“做活”,做得有思想、有内涵、有体系。这一点值得我们加以思考。但是,此论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入,尽管其中提到了研究的对象。不过,前书所引日本学者寺地遵的著作则对政治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了概括,即国家的统治机构、制度、国家意志与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政治势力等。这种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具体、合理的。本文的出发点与之有相似之处,但将更加突出和提升政府政策与政府行为的地位。
②杨念群在《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一书中,曾对“国家一社会”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社会史研究“并非包罗万象,也非包治百病的药方”,美国学者罗威廉研究主题的转换,特别是《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的出炉,更是反映出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即存在一种“过于注重下层历史解释而相对忽略对上层社会进行重新研究的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8页)。我认为,这一评论是比较客观的,社会史的研究似乎又走了政治史以外的另一个极端:以往政治史是只看上不看下,现在社会史是只看下不看上。
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书以《活着的传统》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再版。
④高王凌在“社会政治史”方面的努力,见见"Controcomportamenti",dei Contadini Cinesi nel Periodo della Collettivizzaione Agricold,(意大利)《Momdo Cinese》124期,2005;On a Slippery Roof,Chinese Farmers And The Complex Agenda of Land Reform,(法国)《éTudes Rurales》179期,2007;在他看来,所谓“上层政治”与“基层社会”可以互为视角,但仍各有各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