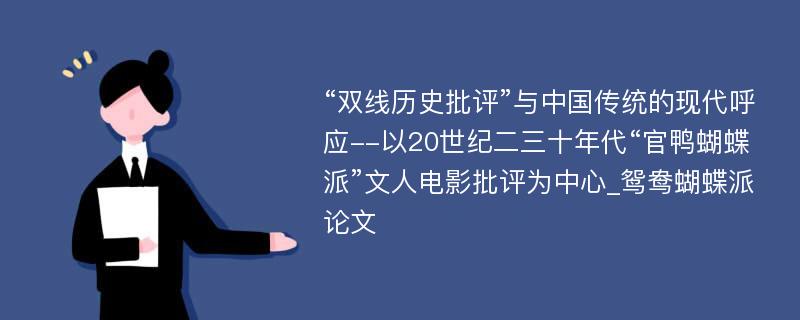
“复线历史批评”与中国传统的现代回响——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批评论文,复线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指出:“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1)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这部著作并没有对“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制作的史实给予相应的重视。2004年以来,在“重写电影史”的呼声中,“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开始引起研究者关注,显现出一种更开放的史学视野,预示着试图重新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趋势。(2)
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编导这一范畴,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这派文人不仅做编剧、当导演,而且自20世纪10年代末以来,他们撰写的电影批评、电影小说和以电影为噱头的小品文就随着各种电影杂志和其他各色报刊游走于现代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了。(3)可以说,“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印刷媒体上构建起一个相当重要的电影书写网络,而且,在他们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都参与到电影写作中来,支撑起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电影世界的一片天空。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鸳鸯蝴蝶派”文人就遭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4)新文化作家指陈“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戏谑、笑闹和色情,固然是事实,但他们对通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高蹈的道德姿态和“扣帽子”式的大话语调。如果我们放弃攻击式的论述,仔细阅读通俗文人的作品,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文字,就会发现通俗文化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深邃思想和人间情怀,并不是简单地“扣帽子”就能抹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不仅是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需要,也是思考“早期中国电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关系”的史学要求。⑸)
本文难以对民国时期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作全面系统的论述,我将以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为中心,择取有代表性的文本来集中讨论:“鸳鸯蝴蝶派”文人如何将中国传统负载于电影批评之中来回应现代社会?传统文化营养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里的回响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电影文化事业和城市平民大众的影响与意义何在?我将援引芝加哥大学的印度裔美籍中国现代史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观念,尝试以“复线历史批评”(bifurcated historic review)来概括和阐释“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批评的一种思想风貌,并从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电影批评对后“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平民的思想启蒙、电影批评对历史片创作的深远意义、电影批评对早期中国电影史述的多元开拓。
一、“说伦理影片”与后“五四”时期的再启蒙路径
如果我们稍稍检视一下“五四”以后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引起震动的影片,就能从中窥测出“伦理道德”确是那时中国城市平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从1921年的《阎瑞生》到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甚至包括1922年以来数度映演而轰动中国的美国影片《赖婚》(Way Down East,David Wark Griffith,1920),(6)其中所触及的无论谋财害命,还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等等,都映照出后“五四”时期中国平民生活里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1915年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所呐喊的思想文化启蒙,还远未深入大众民心。或者说,在实际接受层面,由于平民阶层对精英启蒙话语的误解和盲从,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当然,1912年中国封建帝制崩塌后的文化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只靠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游走于校园街头的青年学生就能完成。但遗憾的是,20年代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对电影这一拥有相当广泛的城市平民接受群体的文化事业的扶持。(7)反观20年代的中国电影,真如新文化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只是充斥着旧道德和黑幕的没落世界吗?虽然柯灵(1909-2000)先生曾说“‘五四’运动发轫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电影领域基本上处于与新文化运动的绝缘状态”,(8)但毫无疑问,启蒙的气息仍然浸润着电影圈。(9)
不像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有着教授职衔,“鸳鸯蝴蝶派”文人大多必须依靠写文章、做电影、办杂志来谋生,这决定了他们的种种文化活动都必然心系城市平民大众的所思所想。当然,“鸳鸯蝴蝶派”本就是一个偏狭的称谓和相对松散的群体,其间鱼龙混杂。在上世纪20年代无序竞争的中国电影市场,各色文人参与编导的粗制滥造的影片恐怕不在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鸳鸯蝴蝶派”的一拨中坚人物,在后“五四”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传统文化营养为渊源,借助电影和电影印刷文本对抗着涌入中国后变质了的某些西方观念。上世纪20年代中期,正当伦理电影兴盛之际,“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1895-1968)(10)刊发了一篇重要影评:《说伦理影片》。(11)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其论题重要、论述充分、论域广泛,实可作为后“五四”时期中国电影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而且,类似这样的文章,在包天笑(1876-1973)、范烟桥(1894-1967)、程小青(1893-1976)、陈小蝶(1897-1989)、江红蕉(1898-1972)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中,并不少见。
与轰轰烈烈呐喊“反传统”、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不同,上世纪20年代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切身体会到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涌入中国后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种种问题,他们力求找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营养经转化后而承传到现代社会中来的药方。1926年,周瘦鹃在《说伦理影片》中,针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儿女们“几乎将父母抛在脑后”的不孝现状和大吹大擂的“非孝之说”,郑重地将“孝”提出来讨论,并明确指出要分清“孝”和“愚孝”的不同。他对现代中国社会儿女的要求并不是“王祥卧冰”、“孟宗哭竹”,而只是“使父母衣食无缺,老怀常开”而已。这难道不是对那些打着“解放”和“自由”旗帜,而扔掉传统、抛弃父母的某些所谓“新青年”们的反讽吗?
周瘦鹃谈论孝道,追忆传统,但他并不是个泥古主义者,他将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洋文字(“filial”孝)、西人行为和西方电影结合起来谈影论道。他尤其谈及《慈母》(Over the Hill)和《吾儿今夜流浪何处》(Where Is My Wandering Boy Tonight?)描写父母爱子女,其中孝与不孝的强烈对比,竟使他不知不觉落泪不少。此外,几部国产伦理片也足以拨动心弦。实际上,周瘦鹃在《说伦理影片》中提出的,是尚未被“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认识到的电影这一独特的现代文化形式在“感化人心”方面所可能具有的强大社会功效。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更多地从思想和行动上“解放”了一部分中国的“新青年”,那么,针对后“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周瘦鹃则试图将传统文化营养融入涌进中国的西方浪潮,并借助现代文化形式来寻求解决之道。这种将观念和思想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念建立在情感心理的根基上,从而达到理智与情感之交融的设想,实际上源自中国儒家强调建构人性和心灵以达到人际关系的情感认同与和谐一致(由“礼”而“仁”),从而稳定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12)这正是针对“五四”启蒙之后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诚恳地想要通过挖掘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营养并运用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形式,去对更大面积的平民大众进行“再启蒙”的努力。
上世纪20年代中期,针对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很多人又在反弹式地激烈呐喊恢复“旧道德”,但只要我们追溯西方启蒙的精神内核,就会发现:启蒙决不是一会儿猛烈地打倒传统,出了问题,却又同样激进地搬出传统。在18世纪的欧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就断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并将“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为启蒙的座右铭。(13)周瘦鹃之所以既不同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又不同于后“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就在于他能够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智,针对中国本土的问题,去寻求在秩序混乱的时代中可以操作的面向平民大众的“再启蒙”路径。周瘦鹃并不以启蒙者自居,但他选择的是渐进改良的启蒙路径,这与郑正秋(1889-1935)倡导以电影来“改良社会心理”(14)的观念相合,只不过,周瘦鹃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更具体,开出的药方更有针对性。他不仅倡导将传统营养注入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电影文化形式中,而且,实实在在地为扶持中国电影事业和净化媒体舆论添砖加瓦。他既对同属“鸳鸯蝴蝶派”的友人朱瘦菊“很想借银幕感化人心”而连续摄制劝善惩恶的《马介甫》和伦理巨作《儿孙福》的实际行动大加鼓励,又对《儿孙福》的导演史东山(1902-1955)能深入浅出地将父母子女的心理表现于银幕之上,让观众感同身受的艺术手法予以赞赏。周瘦鹃之外,陈小蝶在《影片之国民性与音乐之号召力》和《电影作风与文学之倾向》等文章中从“国民性”、“中国音乐”、“中国文学历史”来追忆传统,扶持现代中国电影的思路也颇具特色。(15)
周瘦鹃、陈小蝶、朱瘦菊等“鸳鸯蝴蝶派”文人透过电影和现实生活所深切体悟到的是:过去的历史和传统正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消逝,受西潮冲击的中国社会、中国电影和中国人已病症重重。因而,他们试图将失忆的传统和消散的历史重新捡拾起来,并融入电影这一拥有相当广泛的城市平民接受群体的现代文化形式,来创造“过去”,疗救“现在”。这即如杜赞奇教授所说:“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16)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周瘦鹃为代表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撰写的电影批评,正是以“复线历史批评”来“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传播(transmission)的历史”。(17)
二、“历史影片之讨论”与迟到的历史片高峰
如果说,周瘦鹃、陈小蝶等“鸳鸯蝴蝶派”文人,无论追忆传统伦理道德,抑或发扬古代音乐和文学以扶持现代中国电影事业,以图寻求“感化人心”、“拯救历史”的“再启蒙”路径,都还显得有些势单力薄,那么,1925年底,由包天笑领衔“鸳鸯蝴蝶派”文人掀起的“历史影片之讨论”和后续跟进的关于历史片的诸多影评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不可小视。其中,关涉到的中国传统赓续与现代转化、电影创作与审查,以及“鸳鸯蝴蝶派”文人因这场讨论所带来的评价问题等等,实可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案例,但尚未见详细研究。(18)
上世纪20年代中期,针对中国电影勃兴繁荣背后所潜藏的危机,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友人围绕历史片问题,展开了一场追问中国电影事业前途的讨论。(19)据包天笑和友人们的观察,1925年以前的中国影片大多数都“就事敷衍”,“曾未见一片之关于历史者”。于是,包天笑执笔将他与友人们关于历史影片的讨论撰写出来,从1925年11月到1926年2月分三次连载于《明星特刊》。(20)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人们对历史的观念本来就很深,无论京剧、院本,还是新剧等等,无不截取历史片断来进行排演。因而,中国电影事业要想发扬光大,绝不能靠时髦的男女明星饰演的扭扭捏捏的爱情影片,而必须拍摄历史影片。
包天笑等人倡导历史影片的出发点固然是试图通过承传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观念和中国传统戏剧的历史经验来拯救中国电影事业,但他们的视野和抱负,更有着强烈的回应全球社会的现代意识。他们认识到“电影事业,不能局于一国中,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中国电影要想昂首走出国门,就应摄制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影片。在他们看来:“欧美各国,无不知中国为古国,无不欲知中国历史上雄大之名誉,正苦于无从取资,无从证信,今忽有中国历史上规模闳大之影片,……匪特使欧美之人,群相欢迎。吾国古代历史之精神,英雄豪杰之继起,岂让彼后进文明之国?”而且,欧美人倘若“多观中国历史影片,将对于中国人之观念,易侮慢而为钦仰”。可以看出,包天笑等人试图通过摄制历史影片想要拯救和拓展的不仅是中国电影事业,更要通过历史影片来拯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全球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试图通过电影来拯救中国传统和中国历史,从而通过中国传统和中国历史来拯救现代中国文化。即使就当代中国来看,这种意见和雄心也仍然有效!
现代中国的一拨“鸳鸯蝴蝶派”文人在参与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过程中,面临西方电影的大量涌入而被迫但却又能动地做出反应,从而试图引发电影文化事业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他们发现了繁荣背后的中国影坛的问题所在,也深知摄制历史片在演员、导演、布景、服装等各方面的艰难,但却仍然抱着“辟此先河”的勇气来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出药方,提出并详细解释“不可太苟简”、“不可太精审”、“不可太根据正史”和“不可太根据小说”的历史片拍摄建议。与前文所论周瘦鹃、陈小蝶一样,包天笑等人说传统、谈历史,却并不泥古,也不空谈,而是将传统诉诸“新道德、新观念”来实实在在地谈论现代历史影片的编创。
我们反观1925年以来的中国影坛,虽已出现拍摄历史片的动向,但创作状况却与“历史影片之讨论”的期望相距甚远。天一公司的《女侠李飞飞》(1925)已投入市场,给此后的武侠片潮流开了个头,《梁祝痛史》(1926)更揭开了古装片竞争浪潮的序幕。(21)电影作为一种昂贵的工业和商业文化形式,在其资本积累初期,尤其需要遵循市场运营规律,否则将难以为继。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的古装武侠神怪片无序竞争的状况,是文化商业市场得以成熟之前必经的初始混沌阶段。一方面,市场有其去粗存精的淘洗能力;另一方面,行业规范和自律、政府督导和扶持(而非查禁)以及舆论批评和引导,这些能动调控手段是让电影市场更有效地走向健康和谐的重要保证。面对无序竞争的中国影坛,电影舆论批评呈现出对国产片前途的极大担忧。孙师毅(1904-1966)在1926年就大声疾呼:电影界的古剧疯狂症“实在是今日将致中国电影事业于毁灭的一大危机。这种危机之能否避免,就完全要看对付这种制片公司的公众制裁力量的程度怎样!”(22)
如果我们将“历史影片之讨论”与郑正秋的电影取材主张做个类比,就会发现:包天笑等人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营养输入历史影片来回应现代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的期望,更符合郑正秋所说“第二步适应社会心理”和“第三步改良社会心理”的电影创作阶段。换句话说,中国影坛实际发生的古装武侠神怪片无序竞争的恶性状况,并不能作为否定“历史影片之讨论”的倡导方向和意见建议的根据,相反,经过电影创作“迎合社会心理”这第一阶段的积累,优秀的历史影片就有可能逐渐在电影市场上脱颖而出。然而,制裁和取缔古装武侠神怪片的呼声,导致的却是舆论批评呈现出要将历史影片都统统打倒的气象。针对舆论批评一边倒的气象,能够跟进“历史影片之讨论”的眼光与思路,而继续支持历史片创作的,仍然是范烟桥、程小青等“鸳鸯蝴蝶派”文人。他们不盲目跟风批判,而是更理性地剖析现状,找出根源,给出建议。(23)舆论认为中国电影界在退步,但范烟桥在1928年明确提出:“历史影片自有其真价值,中国电影界渐趋于历史的途径,尚非退步!”他深感中国电影“萌芽甫茁”,“在此数年间已经过若干阶段,最近则渐趋于历史”的难得状况,一方面谨慎批评已上映的中国历史片;另一方面,援引何炳松翻译《新史学》中所述“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和“描写个人的性情动作”作为摄制历史片的条件和衡量历史片的标准。范烟桥、程小青等人对历史片采取的是批评、扶持和引导的态度,是从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的“职业影评人”态度。
遗憾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倡导和扶持历史片的持续努力难以阻挡制裁和取缔古装武侠神怪片的呼声和禁令。自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11月3日抄发《电影检查法》训令和1931年2月3日颁布《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之后,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古装武侠神怪片实施“严格之取缔”,从1931年6月15日到1934年2月20日查禁的国产片,基本上全部都是古装武侠神怪片。(24)国民政府的查禁固然遏制了神怪武侠片的泛滥,但另一方面,在我看来,1930年以后国民政府持续几年时间的严格审查(实际上跟禁绝差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中国历史片拍摄的动向和潮流。也就是说,在几年的严厉审查下,各影片公司再也不敢花费钱财去铤而走险地拍摄古装武侠神怪片,连带到不敢再拍摄关涉历史题材的影片了。
颇为有趣的是,连品味高尚的“新月派”诗人邵洵美(1906-1968)都曾对国民政府查禁神怪电影的行动发出过质疑。(25)在上世纪30年代上半期,明星公司和联华公司固然拍摄了大量优秀的现实社会问题影片,然而,“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的中国电影界,却再也看不到本该出现的类似1927年民新公司和天一公司竞相拍摄历史片《木兰从军》的现象了。(26)到了国难当头的1936年,电影市场上几乎见不到历史片了,能再次站出来呼唤历史片的,还是范烟桥。他极为感慨地以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作比较,坚持申述历史片的价值,强调历史故事兴奋民族的力量和对时代的刺激。(27)
虽然“鸳鸯蝴蝶派”文人始终坚持倡导扶持历史片,但盲从的影评舆论和国民政府的禁令却“人为切断”了中国历史片的动向和潮流。这一潮流,颇为讽刺地被延迟到上海“孤岛”时期,才得以复苏,随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39年2月春节期间,有三部新国片(《木兰从军》、《楚霸王》、《孟姜女》)同时在上海首轮豪华影院上映。(28)当此之时,范烟桥又撰文《孟姜女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影响》对孟姜女传说在银幕上与时代精神紧密勾连的现代创造和传统道德在战乱时代的意义予以阐释。(29)讽刺的是,在“孤岛”叫座又叫好的《木兰从军》这一延迟到来的中国历史片经典作品,被拿到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放映时,仍被谴责批判,甚至出现40年初“焚烧《木兰从军》”的恶性事件。(30)由此,我们再来对照、叩审“鸳鸯蝴蝶派”文人从1925年集体倡导“历史影片之讨论”直到30年代持续跟进扶持历史片的电影批评史轨迹,就能发现这一脉电影批评所潜藏的深远意义。
三、“地域批评”与多元的早期中国电影史述传统
无论周瘦鹃谈论伦理影片,还是陈小蝶追忆中国古代音乐和文学,抑或包天笑、范烟桥等人倡导扶持中国历史影片,“鸳鸯蝴蝶派”文人批评电影的重心基本上都集中于如何从散失的历史和传统中汲取文化营养输入现代电影,以期感化人心、改良社会。与此同时,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还能为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拓展和中国电影文化史述传统的建构,而默默耕耘在撰述、编辑、出版、传播的民间文化岗位上。除前文提及周瘦鹃、范烟桥、包天笑外,为中国电影拓展而奔走南北的《电影月报》编辑徐碧波(1898-1992)、合力编纂《中国影戏大观》的五位“鸳鸯蝴蝶派”文人,还有“补白大王”郑逸梅(1895-1992)等,都是重要代表。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的电影公司和影片产量猛增,加上每年涌入上海的外国影片,导致上海本地电影市场过于饱和。各电影公司无序竞争的恶性状态,促使“明星”等影片公司建立起旨在“集合会员出品,以期推销国内外之营业”的六合影片影业公司。(31)1928年《电影月报》的创办,就成为六合影片公司整合资源、拓展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重要文化平台。作为《电影月报》的编辑,徐碧波携带影片亲自奔走各地考察,撰写调查报告。在六合影片公司和《电影月报》的努力下,从1928年开始,更多的通俗文人参与到考察中国各地电影事业的行动中,《电影月报》连续刊发《国产影片与天津》、《济南之电影》、《电影在苏州》、《电影在常熟》、《电影在常州》、《电影在北平》、《北平的电影界》、《电影在青岛》、《电影在厦门》、《电影在杭州》、《电影在漳州》等文章。(32)文章作者考察各地电影状况,品评各色风土人情,他们会对当地没有像样的影院和正当的娱乐而忧心,会对当地电影观众的欣赏程度急需提高而焦虑,更会对当地频繁上映《白蛇传》、《忠孝节义》、《立地成佛》等“上海滩上三等以下之东西”而直言不讳地指出:“影片之内容,一蟹不如一蟹,几使观众不信中国更有较好之影片。则中国电影前途不将受一重大之打击乎!”(33)这些鲜活的记录、报告和批评,都成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各个地域的影业状况、影片质量、放映场所,甚至风土人情等文化状况的第一手史料。
实际上,以“鸳鸯蝴蝶派”文人为中心而建立和拓展开来的现代中国电影“地域批评”的史述传统,在当代中国也得到了回应。近年来,不仅出现了一些类似“鸳鸯蝴蝶派”文人将记录、报告和批评相结合的研究中国各地域电影状况的论文,(34)更出现了《苏州与中国电影》、《厦门电影百年》、《宁波电影纪事》、《宁夏电影史话》、《大连与中国电影》、《北京电影百年》、《哈尔滨电影地图》等中国各地域的电影史研究专著。这其中,苏州、厦门、北京的电影史述较为完善,这并非偶然。文化需要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建构和传承,中国各地域的电影文化传统同样需要各代人的努力,才能更好地回应现代,把握当代,展望未来。李道新教授就将北京电影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研究,分析阐发北京影业之于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持续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影北京”的发展战略。(35)
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早期中国电影“地域批评”是在拓展电影事业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附带成果,那么,1927年,徐耻痕、王西神、严独鹤、赵苕狂、徐卓呆五位“鸳鸯蝴蝶派”文人合力编纂的《中国影戏大观》则是一次高度自觉地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整体观照。(36)“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文人身份使得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史学意识,他们不仅能够自觉地集体合力编纂电影史,也能以个人之力主动搜集史料进行撰述。范烟桥写过《徐卓呆的滑稽史》,1937年,他更将中国电影自起始以来的重要史料加以搜集,撰著《中国电影史料》一文,其中统计的影片公司的地域分配、影院放映的地域情况、各年度影片数量等等,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统计学数据。(37)
国有国史、家有家谱,构建历史和传统的意义正在于更好地面向人类文明的“今天”和“明天”。如果将中国电影史看作中国传统史述家族中的一支,那么,《中国影戏大观》、《中国电影史料》都类似“正史”,但同时,尤为重要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早期中国电影史述实践同样承传了中国另一种鲜活的修史传统,即“野史笔记”传统。很多“鸳鸯蝴蝶派”文人都直接参与电影制作,他们的“圈内人”身份使得其撰写电影批评和电影史料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对参与电影活动的过程、影坛内外的见闻等形形色色、点点滴滴的人和事都悉心记录下来。因而,我们能够看到散见在各色报刊上的大量关于电影的“影坛见闻”和“野史笔记”。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就以“电影漫谭”、“电影杂碎”、“银灯琐志”、“电影琐话”等名目在《紫罗兰》、《红玫瑰》等各色刊物上发表了诸多关于电影的“补白”。这其中,既有受邀观片所写的笔记,(38)也有根据电影见闻所演绎的笑话小品,(39)既有揭露日本人窃印影片的电影琐话,(40)也有对电影特刊制作的美术化和兴味提出意见的电影杂碎,(41)既有听但杜宇(1897-1972)所说的法国电影新闻,(42)更有以花为喻品评电影女明星的银灯琐志,(43)真是包罗万象!此外,张碧梧、朱瘦菊等人也都是“影坛见闻”和“逸闻轶事”的好手。(44)晚年的包天笑、郑逸梅、陈蝶衣等人更给我们留下了《我与电影》、《影坛旧闻》、《影坛秘史》等回忆录。(45)这些声情并茂、戏谑轻松而又不乏谨严考辨的电影文字,实在是电影“正史”之外弥足珍贵的别样的电影风景,有了这些,往昔的中国电影岁月才有可能活灵活现地跳脱出来。
依靠“鸳鸯蝴蝶派”文人珍贵的地域批评和鲜活的史述实践,我们才可能得以认识上世纪20年代上海以外的中国各地域的电影状况,才可能丰富早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图景。正如陈墨先生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一文中强调的“整体观照”和“细节”对于电影史建构的重要性。(46)恰恰是这一拨儿“鸳鸯蝴蝶派”中关注电影的文人,为我们建构起一个观照整体、记录细节的多元的早期中国电影史述传统。
“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及史述实践,丰富而驳杂,但其中有一个核心的灵魂:以中国传统文化营养来建构现代中国电影书写。追忆和接续传统、挖掘和建构历史,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电影书写来回应现代中国社会,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路径。“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呈现出一派转化传统、拯救历史、创造现代的“复线历史批评”(bifurcated historic review)的思想风貌,这一“复线历史批评”,在对后“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平民的思想启蒙、对中国历史片创作的深远意义、对早期中国电影史述的多元开拓三方面形成了三条相互交织又各具特色的现代中国电影批评的重要轨迹。
后“五四”时期在西潮激荡下的现代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做诊断、开药方。他们试图寻求将传统文化营养注入现代电影之中来“感化人心”,来对更大面积的现代中国平民大众进行“再启蒙”的路径;他们更将中国传统文化诉诸“新道德、新观念”来实实在在地谈论现代电影的编创,为扶持中国电影事业和净化媒体舆论添砖加瓦。他们既以追忆和维护的方式去重拾“散失的历史”,更以批判和创造的方式来回应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既是在人们打倒传统、忘掉传统时所进行的历史启蒙,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启蒙的双重现代性批评。
倘若打开历史的“长镜头”和文化的“宽银幕”,将包天笑、范烟桥等“鸳鸯蝴蝶派”文人倡导和扶持中国历史片的一系列影评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关联起来,就会发现:从1927年《木兰从军》的竞拍,到30年以来国民政府查禁古装武侠神怪片,再到1939年“孤岛”时期以《木兰从军》为代表的迟到的历史片高峰,在现代中国历史片十余年坎坎坷坷的跌宕轨迹中,当喧闹、泡沫、批判、谩骂、查禁、焚烧都过去之后,我们再来对照、叩审“鸳鸯蝴蝶派”文人从1925年集体倡导“历史影片之讨论”直到30年代持续跟进扶持历史片的电影批评史轨迹,这一脉电影批评的人文价值和史学意义,以及影评人的开创眼光和职业精神便凸显出来。首先,“鸳鸯蝴蝶派”文人始终倡导和扶持中国历史片,映照出的是他们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营养以图回应现代社会的民族自信心和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情怀。其次,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片的批评资源和文献,尤其是“鸳鸯蝴蝶派”文人运用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资源(何炳松译《新史学》)提出的关于历史片的诸多意见、建议和标准等,现在看来,仍有参考价值,值得再做仔细挖掘和研究。再次,关于“鸳鸯蝴蝶派”文人在中国古装片浪潮中的评价问题。1939年“孤岛”时期的历史片高峰与1925年的“历史影片之讨论”虽相距14年,显得有些迟到,但却仍然足以昭示出“鸳鸯蝴蝶派”文人始终倡导和扶持历史片的开创眼光和职业精神,更反衬出政府文化政策和电影舆论批评的种种激进问题。“鸳鸯蝴蝶派”文人不仅不应该为古装武侠神怪片无序竞争的浪潮负责,相反,他们坚持并提出的历史片创作途径和建议正是引导当时中国电影创作走向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只不过,他们的前瞻性意见被取缔的呼声和政府的禁令所淹没、所阻断。但是,“鸳鸯蝴蝶派”文人能够顶住舆论风潮和政府查禁,而始终坚持倡导、扶持历史片,这种对中国电影文化事业的执著与勇气、态度与精神,现在看来,更值得肯定和珍视。
2009年,在《当代电影》围绕“中国电影史研究:重写的艰困与创新的呼唤”主题组稿中,虞吉教授引用吴冠平先生的说法,“在以往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如何还原有人的历史场景的质感与细节是被忽略的”,并认为:“以‘心态史’、‘问题史’、‘方志史’、‘区域史’、‘地方史’、‘社区史’等命名的所谓新‘电影史’不仅是电影史学观念学理性嬗变所体现的新向度,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电影史学科向前推进的新的增长点。”(47)从这个意义上讲,徐碧波、郑逸梅等“鸳鸯蝴蝶派”文人开创的中国电影“地域批评”和多元鲜活的电影史述传统,正是把握“区域史”与“地方史”,还原“有人的历史场景的质感与细节”的一个传统基点。透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和史述实践,早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图景丰富鲜活起来,这种批评和史述的传统正为当代中国电影人所承传。
注释:
(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2)参见盘剑《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125—131页,张巍《“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中国电影情节剧观念的确立》,《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第69—75页;梅雯《破碎的影像与失忆的历史——从旧派鸳蝴电影的衰落看中国知识范型的转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
(3)范伯群教授甚至认为通俗作家“几乎包揽了20世纪20年代各电影杂志的评论文章”,见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4)参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8、59页。
(5)石川《后编年体史述:多元体裁与深度阐释》,《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第85页。
(6)《赖婚》于1922年5月先在上海献映,后至天津和北平,《赖婚》在上海前后映演5次。参见陈建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第114页。
(7)毕克伟教授(Paul G.Pickowicz)甚至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根本也瞧不起电影。尽管他们口头上大讲文艺的民主化、大众化,但30年代以前,他们对电影只有轻蔑,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将五四精神贯彻到电影界。”毕克伟《“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萧志伟译,见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柯灵《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电影回顾录》,香港中国电影学会编《中国电影研究》第1辑,香港中国电影学会1983年版,第5页。
(9)参见李道新《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涵义》,《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石川《作为早期大众文化产品的郑正秋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
(10)1919年6月20日至1920年7月4日,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连续发表16篇“影戏话”,参见陈建华《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影戏话〉读解》,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2007年7月第9辑,第53—76页。
(11)周瘦鹃《说伦理影片》,《〈儿孙福〉特刊》1926年,参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78—680页。
(12)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13)[德]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美]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4)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载1925年明星公司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参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290页。
(15)参见陈小蝶《影片之国民性与音乐之号召力》(上),《电影月报》第1期,1928年4月1日,《影片之国民性与音乐之号召力》(下),《电影月报》第2期,1928年5月1日;《电影作风与文学之倾向》,《电影月报》第5期,1928年8月10日。
(16)[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7)同(16),第39页。
(18)李道新和张英进教授分别在《中国电影批评史》和一篇序言中对此有所论述和提及。可参看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张英进《文化史语境中的“海派”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见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9)此前的1924年,天津的《电影周刊》上也出现过关于“电影与历史”的零星文章。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第30页。
(20)天笑《历史影片之讨论》,《明星特刊》第6、7、9期,1925年11月、1926年1月、1926年2月,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629—632页。
(21)参见李少白《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22)孙师毅《电影界的古剧疯狂症》(载《银星》1926年第3期),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643—645页。
(23)烟桥《历史影片之价值》(《电影月报》第4期,1928年7月1日出版)程小青《历史影片的利用及难点》(载1927年大中华百合公司特刊《美人计》),参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633-634页。
(24)参见《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三年来工作述要(1934年)》、《电影检查委员会查禁国产影片一览表(1931年6月15-1934年2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397页。
(25)参见邵洵美《神怪的文学》(原载1935年12月20日《时代图画半月刊》第9卷第1期),陈子善编《洵美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26)参见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郦苏元《黎民伟与中国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
(27)烟桥《半月闲话:历史的影片》,《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6期。
(28)参见[美]傅葆石(Poshek Fu)《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9)烟桥《孟姜女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影响》,《金城月刊》1938年新生号,上海金城大戏院1938年11月。
(30)同(28),第72—83页。
(31)参见徐碧波《电影在常熟》,《电影月报》第4期,1928年7月1日。
(32)所列文章依次见:《电影月报》第1—10期、第11、12期合刊,出版日期从1928年4月1日至1929年9月15日。
(33)烟桥《济南之电影》,《电影月报》第2期,上海,1928年5月1日。
(34)参见汪朝光《20世纪初叶电影在东北边陲之兴——哈尔滨早期电影市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徐文明《一座城市电影放映的历史记忆书写——关于宁波1910—1930年代电影放映及影院经营状况的研究》,《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
(35)李道新《都市功能的转换与电影生态的变迁——以北京影业为中心的历史文化研究》,《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36)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开端》,《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37)范烟桥《中国电影史料》,《明星月刊》第8卷第2期,1937年3月1日。
(38)郑逸梅《观〈山东响马〉试片之零话》,《友联特刊〈山东响马〉号》,1927年8月。
(39)郑逸梅《乡人看影戏》,《红玫瑰》第1卷第18期,1924年11月29日。
(40)郑逸梅《电影琐话》,《友联特刊·〈山东响马〉号》,1927年8月。
(41)郑逸梅《关于电影之杂碎》,《友联特刊〈红蝴蝶〉号》,1928年2月1日。
(42)郑逸梅《记两个为电影而牺牲者》,《紫罗兰》第2卷第16号,1927年8月27日。
(43)郑逸梅《银灯琐志》,《紫罗兰电影号》第1卷第12号,1926年5月26日。
(44)比如:张碧梧《摄制马振华影片之琐录》,《电影月报》第3期,1928年6月1日;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海誓片中之FF》、《〈古井重波记〉中之AA》,《电影杂志》第1卷第1号,1924年5月。
(45)包天笑1973年撰写的《我与电影》一文,收于《钏影楼回忆录》;郑逸梅《影坛旧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陈蝶衣的《影坛秘史》于1984年在香港出版。参见魏绍昌《艺苑拾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46)参见陈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47)虞吉《“开放的电影史观念”主导的路径标识》,《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第79—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