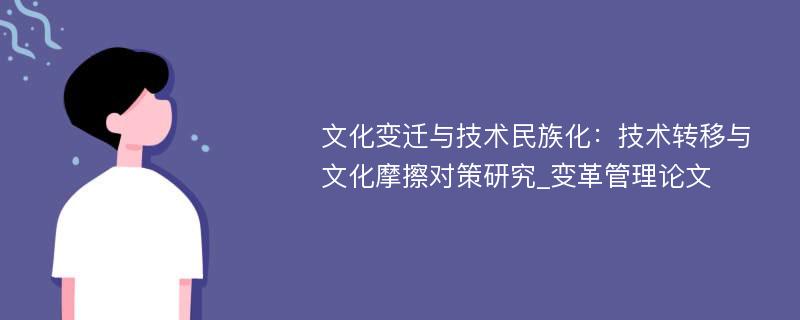
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关于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技术论文,摩擦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技术转移问题,笔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论述[1-6],并且指出,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必须同时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它是消除在技术转移中出现文化摩擦的实践对策。对此,笔者将作如下进一步探讨。
1 概念的界定
文化变革概指文化(广义)通过一定的方法或途径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及其结果。它是指整个文化系统即“技术-文化”系统的变革,但在这里,它主要突出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其中,文化制度的变革是核心,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是根本。技术民族化概指在引进外来技术中,依据本民族气候风土、民族文化,对外来技术加以改造或创新,使之成为本民族“技术-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实现外来技术与本民族技术相融合的过程及其结果。
理论上,根据“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可知,技术与文化各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并且,技术的特殊性除了受到区域气候风土的影响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文化特殊性的影响,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化特征。文化变革主要解决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双方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技术民族化则主要解决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双方技术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样,技术特殊性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自然就决定了技术民族化与文化变革密切相关,互为一体。
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与文化相关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上。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使得技术转移滞后,并由此产生文化摩擦。为此,需要通过文化变革来解决。然而,文化变革并非是全部变革,它只是改变传统文化中那些陈旧的甚至反动的特殊性因素,还要保留其中的优秀成分,另外,还要保留传统技术的特殊性。这样,在通过文化变革,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技术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同时,还要根据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成分,以及传统技术的特殊性,对外来文化、技术制度及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取舍、创新,使之与本民族传统技术、文化融为一体。这就是说,在进行技术制度及意识形态转移过程中,要同时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包括文化)的民族化。否则,只进行文化变革就有可能导致全盘西化,使民族“技术-文化”系统丧失独立性;而只实施技术(或文化)民族化就有可能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
2 文化变革的艰巨性和迫切性
近代中国在技术转移中,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变革,但是,其结果或失败或半途而废。这表明了文化变革的艰难,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都要流血,而且,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用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7]。可见,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比技术民族化更为艰难和迫切。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文化制度的变革。然而,封建思想依然存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仍未完成。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也制约了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可见,文化变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文化变革问题是自“五四”以来在文化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其中,一方主张应当进行内在变革,即所谓“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由“儒家的道德主体转换出支撑工业文明的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另一方主张应当进行外在变革,如,或主张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主张“外在批判性重建”[8],即通过引进外来文化,重建本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从技术转移角度看,随着转移进程的深入,外来技术、文化必然被转移进来,如果不顾及这些,只注重“内在创造性转化”,这虽然也需要,但也很难“开出新外王”。这正如江泽民所说:“在长期闭关锁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陈旧、保守、固步不前的价值系统,仅仅依靠内部制度变更或内部思想解决是难以打破的,必须借助于域外文化的冲击”。然而,如果只依靠外来文化完成文化变革,而不注重“内在创造性”,不注重依据本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改造吸收,那么,一则将会欲速则不达,二则将可能丧失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因此,应当在吸收外来文化改革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依靠自己的创造性,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民族化。这又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中国不能蹈袭西方文明的方法来进行改革。如果想抛开自己的文化基础,去实现西方化,中国必然会崩溃消亡”[9]。因此,只有做到“内在创造性转化”与“外在批判性重建”相统一的文化变革,才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之路。
在笔者看来,我国文化制度改革将是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可能是制度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制度,它代表社会制度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方向。当代中西社会政治制度已远非近代中西社会政治制度可比,已发生了逆转。因此,当代中国不可能再像晚清封建政府那样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改革本国没落腐败的封建制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无需也不能再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替代它。然而,制度优越并非意味着体制一定优越。长期封建残余思想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致使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发生了偏差。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变革的着眼点应是针对体制变革,即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包括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来改革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同时,应当注意使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因此,在政企关系问题上,改革的方针则是,既不能像美国自由经济体制那样完全实现政企分开,也不能再像计划经济体制那样政企不分。即应当是既保持企业的相对独立,又不能离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做到二者的统一。此外还应做到把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党的领导体制相结合;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与加强企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即达到在体制改革方面实现“内在创造性转化”与“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有机统一。
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革(或更新)则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封建思想,增强了市场、商品、竞争以及科技意识。然而,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主义的人生观、金钱观、道德观与封建思想一起不断地冲击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价值道德观,并以假、冒、伪、劣以及贪污腐化等行为显现出来。有的论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原故。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并将由文化制度变革来解决。然而,即使体制健全,如果个人不具备抵御各种不正确、不健康思想的素质或能力,也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那种以此措责改革开放过度或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则只是一种空发议论,只能是理论上的谬误和实践中的误导。应当在文化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传统优秀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竞争意识、科技意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用祖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加强教育,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抵制一切腐败思想侵蚀的能力,并配以法制建设,这应当成为文化意识形态改革实践中的一种指导。
3 技术民族化与技术创新
技术民族化包括技术器物的民族化和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民族化。
实施技术器物的民族化,一是要依据本民族气候风土,对外来技术器物实施民族化;二是要根据本民族的审美爱好对外来技术器物加以改造,使之民族化。
历史上,不考虑气候风土的影响,不对外来的技术器物实施民族化而带来损失者,不乏多例。例如,近代英国人贝塞麦因到藏有酸性矿石的国家建造自己所发明的本来只适于藏有碱性矿石地区的酸性炼钢炉而导致失败,受到攻击。近代中国实业家张之洞在没有事先考察我国的矿石性质的情况下,因善自引进英国的酸性炼钢技术,建造酸性炼钢炉而造成重大损失。古代日本人在引种中国棉花时,因未考虑到两国气候土壤的差异而导致失败[10]。近代日本在设计建造釜石炼铁厂和八幡炼铁厂时,不考虑本国与外国自然资源状况的差异,只依赖于英国人的教条式指导,终因“原材料不足”,“贪大求全”而致失败[11]。美国最初在引进欧洲大型机车时,不考虑两地区自然状况差异,对其不进行二次创新,直接使用,其结果,由于这种大型机车在使用中,它们不适应于美国森林密集、道路狭窄、转弯过多的自然环境,或多出事故或易燃发生火灾[12]。
当然,也有许多成功的事例。例如,1884年,两位匈牙利工程师布拉蒂和齐裴诺斯依据英国发明家高拉德和吉布斯所发明的变压器的基本原理,根据本国国情,又重新设计制造出了结构简单、功能完备的“匈式变压器”。后来,美国威斯豪斯公司又设计出适于美国国情的具有“美国风格”的美式变压器。日本土木技术专家摩勒鲁(1841-1871)在设计铺设铁路时,根据本国木材和砂土资源丰富的特点,没有采用英式铁制枕木,而改用木制枕木铺设铁路,从而达到了既充分利用资源又节省了资源的目的[13]。日本在炼铁技术方面,曾经综合了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生产铸铁用的高炉设计技术,根据本国的铁矿石原料的特点,设计建造了适应于日本频繁地震、地质地基和用海水冷却等特殊情况的炼铁高炉。瑞典没有机械地效仿英国的以煤炼铁技术,而是发明了既能炼出高质特种钢,又能充分利用本国矿产资源,还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的电气化炼钢高炉建造技术[14]。
在根据本民族文化对外来技术器物实施民族化方面,日本做得比较突出。
例如,古代日本人在接受到中国的铜镜时,在对其进行大量地仿制(制造出了诸如“方格规矩镜”、“内行花纹镜”等许多仿制品)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的审美爱好,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画像镜和神兽镜结合起来”,创新制成了兼有中日两国民族文化特征的“三角缘神兽镜”[15]。日本民族崇尚自然,喜爱精致、灵巧型的器物产品,他们依照这种审美意识,创制出了以精致、小巧为特征的“盆栽”、“花道”、“茶道”等各种民族艺术及其民族产品。现代日本在引进西方发达的技术器物时,他们也把上述审美意识渗透在对外来技术器物的创新实践中,创制出显示日本民族特色的各类技术器物,如微型计算机、精密高容量的光导纤维、精密善用的各种磁带录像机、小轿车等。日本人就是这洋,把技术器物创新与本民族的审美文化相结合,创制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技术产品。
实施技术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民族化,一是要根据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外来技术组织、制度加以创新,使之民族化;二是要注重把外来技术意识形态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其民族化。
例如,日本根据本民族的集团主义以及“和”的文化传统,对欧美泰勒制的企业经营管理及生产制度进行创新,创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诸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QC管理小组、看板管理等日本式管理制度。另外,日本还综合引进德国的帕德休公司多种经营(即从生产染料合成开始发展到医药品和化学肥料)和美国的杜邦公司的多种经营(即从生产火药开始发展到研制赛璐珞、玻璃纸、漆涂料和合成纤维)管理技术,分别成立了染料、医药品等多种行业,从而建立了日本式的化工企业多种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了外来技术制度的民族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企业技术创新所进行的制度创新,除了对传统技术制度进行改革以外,主要是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对外来技术制度实施民族化,它指的就是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对于西方关于技术决定论、技术政治论、技术价值论等技术观,应当在承认其合理性的同时,注重与本国文化相结合。即把技术决定政治论与传统的文化决定政治观相结合。把技术中立性,工具理性与文化主体(人)相结合,达到在政治活动中,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把技术效用性的中立性与技术应用的非中立性结合起来,实现技术价值与其使用价值相统一。把由技术应用及其后果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后人类中心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结合起来,正确认识人-技术-自然三者的关系,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意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民族化的过程与对外来技术的综合创新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民族化是由引进技术创新来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民族化也就是对外来技术的引进综合创新。另外,随着技术转移的持续进行,转移双方技术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出现。因此,技术民族化也是一个持续实施的过程。
4 技术民族化与文化民族化
强调技术民族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狭义)民族化不存在或不重要,随着技术转移的持续深入,将会带来文化传播。这样,技术民族化又将涉及到文化民族化。如果不考虑或不实施文化民族化,那么,技术民族化将受到阻碍,或者,即使实施技术民族化,也很难保证整个“技术-文化”系统保持其民族特色或相对独立性。这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在亲自选择并吸收其他国家文明之时……,如果缺乏选择能力,则反而使其失掉自己民族所固有的东西”[16]。
日本在技术转移中不仅注重对外来技术实施民族化,而且还注重对外来文化实施民族化。这突出表现在,日本吸收了中国儒学中“和”的思想,抛弃了其中的重文轻武,轻视科技、科举制度成分,并将其与本国传统的“神道教”结合,形成了日本的“和道”文化。这样,日本经过对中国儒学的选择、创新,形成了具有“疏于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考;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17]等特征的日本儒学。日本儒学不仅在近代技术与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战后经济、技术振兴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以致于世人把日本资本主义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引进中国技术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国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其技术民族化创造了条件。可见,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民族化促进了对外来技术的民族化,两者相辅相成,互动发展。正因如此,才使得日本由古至今,尽管先后引进中、西方技术与文化,但又不丧失民族特性,从而能够保持本国技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5 技术民族化与中国民族工业的振兴
技术民族化问题在战后中国的技术引进初期曾被人忽视。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不仅引进了苏联的机械设备,而且从行政机关、制度和规章、行政上的管理方法,直至科学技术体制都引入了苏联的模式”[18],不注重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技术民族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考虑本国的技术基础(如设备、原料、资金、管理)和人员技术素质,“跨越那些中间技术”[19],盲目引进国外的高、精、尖技术,以便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中国在引进日本的摄影机过程中,不是首先引进自动摄影机,再引进电子分色机,而是一开始就引进电子分色机。其结果,使得中国人不会运用其中的全部性能,只能把它当作普通摄影机使用,并且,一旦机器出现故障,自己又不能修理,只能依赖于外国,受制于外国,从而陷于被动。
上述现象在迄今为止的技术转移过程中是不少的,它降低了技术转移效率,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而且,随着技术转移的深入(一旦中国加入到WTO以后),将会给那些原来只靠技术引进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带来很大冲击,严重威胁着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可见,实施技术民族化,振兴民族工业已经迫在眉睫了。
实施技术民族化要与技术支持力相适应。技术支持力概指传统技术基础,它包括物力、财力以及技术人员素质与能力等。如果“已有的传统产业和原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差太远,超过了原有技术吸收能力的范围,这种技术引进来也固定不了,因为需要引进的新技术几乎与原有技术无关”[20]。上述中国出现盲目引进与超越引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技术支持力。
实施技术民族比,重要的是引进那些与自身技术支持力相对应的外来技术,并在其中对其实施民族化。例如,近代日本根据本国所具有的用风箱炼铁的原有技术,引进并创新来自荷兰的高炉炼铁技术;日本依靠自己所具有的雄厚的纺织技术基础,引进法国的“贾卡透纺织机”技术。现代日本依靠其在近代就已经掌握了的木偶人的制造技术基础,引进西方的计算机技术,并成功地实施了技术民族化。另外,还要通过开办技术学校,成立技术培训中心机构等,提高技术工作者的科技素质,使之既能引进外来技术,又能根据本国国情加以创新,使之民族化。
我国许多企业在实施技术民族化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成就。例如,“海尔”等集团能在引进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创新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增强自己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实力。此外,我国企业还自行设计制造出诸如微机控制电梯、数控电火花切割机、高速动平衡试验机等高技术产品,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竞争能力,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上述还只是对外来技术器物实施了民族化,还要积极地实施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民族化。为此,需要我国企业通过改革本企业传统的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建立现代生产管理、人才管理、质量管理、技术开发管理等企业制度,建设适合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以此来完成技术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民族化。
目前,我国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进行的宏(微)观改革,成为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同时,技术器物、组织管理创新和创新管理以及观念更新则又是技术民族化所要做的重要工作。可见,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则成为我国目前开展技术创新的两个重要内容,它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1-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