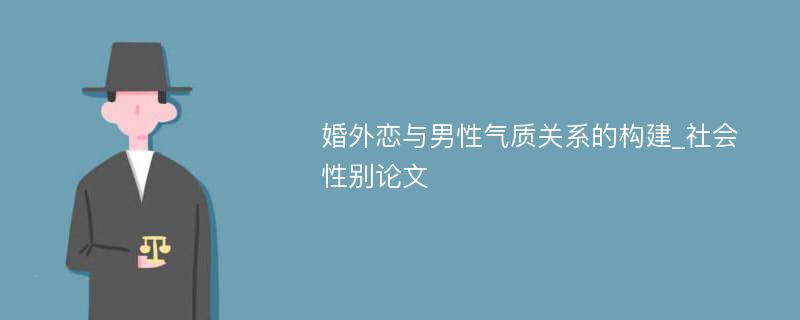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养论文,气质论文,男性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阿菲正在家中看肥皂剧。百无聊赖,她玩起自己的假睫毛,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取下。阿菲住在广州城郊一套70多平米的两居室中,这是她的男友阿东六个月前给她买的。我到阿菲家的时候,阿东刚离开,阿菲说:他已经三天没来过了,这次呆了两个小时。我调侃阿菲“是不是小别胜新婚啊?”阿菲说:“我们没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有些不信,阿菲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性欲)不是很大,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①在阿东开始表现出不太想和她做爱的时候,阿菲曾担心男友会抛弃自己,然而让她感到欣慰的是,阿东仍然给她钱,供养她。“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阿菲说。
阿菲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奶”,她是广州本地人,31岁,三年前和建筑公司老板阿东——一个37岁的已婚男人——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方供养。然而与“包二奶”是“以性交为目的和首要目的”②常识不同,在阿菲/阿东这一案例以及笔者调查的其他部分婚外包养案例中,“性”并非是最关键的因素: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包养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本研究对婚外包养的分析将突破“性”的局限,而将其置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男性气质(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来考察。文章指出,“性”是这个时期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行为”层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符号”层面。
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不少学者注意到性别关系的重塑运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领域积极地开展起来,尤以批判和背离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去性别化”的性别实践为重要特征。③从80年代开始,以男性作家和男性学者为主要代表的知识精英抨击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中过分强化女性的权力和自主性,让男性完全服务于国家,从而使男人不像男人。这是对男性心理和精神上的阉割,④最终会导致国家的虚弱和现代化的无法实现。⑤市场改革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提倡“素质”和“欲望”的“市场话语”为主导,与以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⑥
在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性别话语中,关于男性气质的主流表述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性和欲望的显性化。在“后社会主义寓言”中,释放和彰显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压抑的个体欲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性和情欲作为最本质的人性获得表述的合法性,⑦而男性的“性”欲、“情”欲又因与传统性别规范暗合,获得更多的社会接纳和道德合法性。其次,财富的核心地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男性越来越多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⑧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现,这种能力可极大的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⑨最后,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⑩
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凝结着性别与社会阶层这两种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当经济水平与男性个体素质和吸引力、养家能力紧密捆绑在一起时,低社会阶层的男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去男性化”的危机;同时,当(异性恋的)性和情感的欲望成为市场改革时期男人本性时,女性身体、性和情感就会成为实现男性气质的重要途径,进而转化为表达某种阶层优势的符号。在本文中,笔者将引入“关系化”的视角——即男性性别身份的完成如何依赖于(亲密关系中)女性的劳动——来考察婚外关系与男性气质的建构;除此以外,本文对男性气质关系化建构的讨论还将保持对社会阶层的敏感性,探讨婚外包养关系对不同社会阶层男性的社会意义。
二、性别建构的理论视角转换:从个体的实践到“关系化”的建构
自女性主义者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来揭示性别的社会建构本质及背后的权力结构和等级体系以来,性别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从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角度进行性别认知——如“性别角色(sexroles)”的概念——转向从动态的、实践(practice)的角度去把握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在美国性别社会学权威刊物《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的创刊号中,Candace West和Don Zimmerman发表了《创造性别》(Doing Gender)一文,指出“性别不是某种一个人的所是(being),而是一个人的所为(doing)”。作者将具有模糊性的生理的性(sex)、社会文化界定的“性别类属”(sex category)和实践取向的社会性别(gender)区别开来,认为社会性别不应被视为固定、静止的角色,它其实是在社会生活和关系中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社会性别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反复进行的一系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以“准确”地把自己放入相应的性别类属。“创造性别”看似个体的行为,其驱动机制则具有社会制度和互动属性。比如在多数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本质分化的性别类属是区分人群的最基本标准之一,并约束着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各种互动情境,那么个体“创造性别”不仅无法逃避,而且带有强制性。社会文化和制度性安排(例如性别的劳动分工、强制的异性恋)规定合适的性别展示的方式和内容,界定了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符的规范性行为,并接受不同社会关系和互动情境的调适;(11)反过来,人们通过日常的、有序的和重复的“创造性别”,不仅完成了个体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的建构,而且实现了对“性别类属”的表述,并完成相关制度安排的再生产。由此可见,“创造性别”的概念将社会结构、文化符号与个体身份有机的串联起来。(12)
几乎与此同期,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Judith Butler提出了“性别表演”(gender as performance)的概念,进一步挑战了关于性别的本质主义论述。Butler认为性别是一种重复性表演的效应(effect),这种表演在遮掩了个体性别行为矛盾性和不稳定性之时,生产出一种静止的、正常的性别效应;所谓的“真实的性别”只是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是通过策略性的集体协议去表演、生产和维持不相关的、两极分化的性别得以维系;正是性别生产的可信性模糊了性别作为一种文化虚构的实质。在Butler看来,正是这种表演性,给性别身份带来了多样性空间,开启了对性别规范进行挑战和反抗的可能。(13)
在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所为”和“表演”视角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经验研究探讨社会性别的多样性和情境化的建构,阐述个体和群体的性别“创造”或“表演”如何在各种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进行实践,这些合力包括总体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地方性的性别文化、具体的机构环境、社会关系规范以及其他的社会力量(比如阶级、族群等)。(14)然而,尽管学者们通常在社会互动中观察性别建构的过程及其机制,并从理论上指出不同社会性别建构之间的相关性,(15)但在研究中经常陷入“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的“个体主义”陷阱——从个体认同的视角强调个体为建构其自身的性别身份、性别认同的所作所为,以及个体对这些行为的主体认知,却忽略了性别建构的互动性内涵。
近年来,一些反思开始出现。Connell和Messerschmidt在关于男性气质研究的评述文章中提出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的研究需要引入“关系化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强调女性在社会关系和互动情境中的实践“在许多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对男性气质的理解“需要整合对性别等级的更为整体性的认知,对从属地位群体的能动性和占主导地位群体的强力给予同等的关注和承认,并意识到性别动力和其他社会动力的相互影响”(16)。
Jane Ward进一步对如何从“关系化”的视角去理解社会性别进行理论化尝试。她认为社会性别不仅仅是个体在互动中完成的、反复表演的各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姿态”(gestures),而且还包含了大量由他者承担的繁复的情感的、身体的和性方面的“支持”行为,这些行为共同生产出个体性别的完整性。由此,她提出了“性别劳动”的概念,以形容人们为他者“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情感和身体的各种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需要指出的是,为他人进行“性别劳动”是一个包含大量训练、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愉悦、有表演性和充满活力的,也可能是令人生厌、挫折累累和受强迫的。(17)
Ward指出,所有的社会性别(男性、女性、跨性别、酷儿等)的身份建构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承认、肯定和协助;然而,性别劳动的要求和给予却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某些社会性别身份,更“理所应当”地期待、要求他人为其提供性别劳动,也更能通过强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实现。这些性别身份通常是男性(包含异性恋、同性恋和跨性别中男性取向的那一方),特别是当这些性别身份和其他类型的权力形式(比如优势阶层和种族)结合之后。这是因为,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则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制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与各种通常由女性承担的围绕他人诉求而开展的“关爱工作”(care work)和“亲密劳动”(intimate labor)很相似,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
然而,除了Ward利用性别劳动的概念分析“跨性别”身份建构中他人的贡献以外,从“关系化”的视角去系统考察性别建构的经验研究为数寥寥。一些优秀的民族志作品虽然记录了女性如何帮助男性建立性别认同、男性尊严和优越感,但因为缺乏理论自觉,显得比较零散。如Anne Allison在其著作Nightwork中指出,东京的酒吧女招待对日本企业职员进行一系列的亲密举动,如敬酒、点烟以及恭维和挑逗,以此帮助那些男性塑造一种性感、成功的男性形象。(18)Arlie Hochschild在Second Shift中提到一些收入高于丈夫的职业女性,她们往往通过承担更多的家务,以不断确认丈夫的男性尊严——因为被“剥夺”了家庭主要供养者的角色,丈夫们感受到男性权威受到了挑战。(19)
本文将借助性别关系化建构的视角,特别是性别劳动的概念,分析亲密关系与男性气质的建构,阐述二奶在家庭内外所承担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在婚外包养这样一种很不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经济上的依赖、社会文化上的压力以及缺少法律的保护,帮助男性实现某种与阶层相关的男性气质,成为被包养女性维护自身地位的一种有效策略,这也使得她们的性别劳动更有迹可寻,便于我们考察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通过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婚外包养案例的分析,本文还将更好的展示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性别劳动在特定亲密关系中的运作。首先,二奶们给男伴提供的性别劳动远远多于从她们的男伴那里得到的性别劳动,这与社会的性别期待有关,也与她们对男伴的经济依附有关;其次,二奶和妻子不同,妻子拥有法律和社会承认所赋予的“地位”作为保护伞,一定程度上免于陷入繁琐的、不对等的,甚至痛苦的性别劳动中,然而二奶却会因为自身地位的不确定性而将取悦对方当做一种维系关系的策略;再之,二奶也与陪酒女等商业性情色服务不同,陪酒女一定可以将她们的真实情感和逢场作戏的工作区分开——当她们在一个商业场合努力奉迎男性的时候,她们可以在此过程中不用表演得那么真诚,但在私人的亲密关系中,二奶们不仅主动承担肯定、保证和强化其伴侣男性气质的工作,而且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使得这些工作看上去是真实的,甚至是毫不费力的;最后,当男性的性别与商人阶层相结合时,二奶们为男伴制造性别的劳动往往从私人场所的私密互动拓展到特定公共场合的公开呈现,这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亲密关系的表演来彰显特定的男性气质已成为传递新贵阶层优势的重要途径。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分析材料主要来自于笔者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以及2007年6-8月在广州和宁波进行的关于婚外包养的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笔者对婚外包养的定义采取“社会生成”的方式,即由知情者给笔者介绍或推荐他们认为的处于婚外包养关系的当事人,然后分析这些当事人(及关系)的特点,总结他们对于婚外包养的理解。虽然对于包养关系的理解各有差异,但收集到的个案具有三方面的相似性:(1)相对长期的同居关系,往往有固定的共同居所;(2)同居关系中一方为已婚男性;(3)另一方为男方合法配偶外的女性,并在经济上依附于该男子,即该男子是女子当下生活最根本的经济来源。
研究一共收集了19例个案,其中11位女性是外地打工妹,8位是广州本地女性,调查时年龄最小18岁,最大38岁,最高学历为高中;男性的年龄跨度为35到50多岁,17位是中国大陆的,2位是香港人,11人经商,3个是高级白领(技术总监、总经理、建筑设计师),另外5个属于广义上的工薪阶层(办公室行政、工地工头、销售)。笔者对19个案例中的16位女性、4位男性和1位男性受访者的前妻进行了1~3次、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的深度访谈,对另外3位男性以及其他知情者(比如朋友、邻居、亲属、熟人等)进行多次非正式的访谈,每次谈话时间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笔者还对三分之二的当事人进行参与观察的研究,主要包括去受访者家串门以及参加他们日常娱乐和社交活动(比如朋友聚会、泡吧、唱卡拉OK、逛街、美容美发),笔者获取的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于这种参与观察。为保护受访者,本文中所采用的人名和地名均为化名。
四、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建构
(一)家务劳动的情感与符号意义
40岁的阿才是浙江人,供职于当地的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作为一名基层销售人员,他每月去广州出差两周。三年前,他在广州市郊城中村同38岁的阿润同居。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有一个10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前夫因逃债失踪后,阿润为供养儿子并偿还债务,来到广州打工。她起初在发廊做洗头工,兼做“小姐”,与阿才相遇并同居后,阿润便不再工作。
阿才支付每月350元的房屋租金和他逗留广州期间两人的花销,此外他还给阿润每月800元的生活费;阿润照顾他在广州期间的日常起居。她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井井有条,阿才换下的衣服当天就洗净晾干,一日三餐也都照着阿才的心意做。这其实与阿才在老家的情况很不同:阿才的妻子在公司做财务,靠着夫妇俩的收入供着房子的贷款和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因为心疼妻子在他出差期间又当爹又当妈,他回到老家就把所有的家务几乎都承包了。但在广州,他很享用阿润无微不至的照顾,回家往床上一躺,闻着饭菜飘香。有时在做饭间歇,阿润还会进来给他揉肩搓背,帮他解乏。阿才常说:“照顾人是阿润的强项。”
如同阿润,工薪阶层的二奶们大多承担大量的家务和照料劳动,而且大部分二奶都会留意男伴的需求与喜好,以在提供家务和照料时投其所好。在笔者调查的案例中,所有工薪阶层的二奶们都会学做她们男友最爱吃的饭菜,有些二奶还学着做有营养的可口饭菜,以此表明对男友的关心。这为阿才这样经常出差的工薪男性提供了很多现实的好处:从纯粹经济计算的角度来看,包养阿润这样贤惠女子比从市场上购买家政服务更划算。(20)更重要的是,对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往往,这些个性化的、带着爱意的照料是对他们作为家庭供养者身份的肯定和回馈。正如当过出租车司机的老王所言:“现在这社会赚点钱不容易,还不是为了老婆小孩。回到家老婆(要能)做一桌子菜等着你,再说两句体贴的话,心情就不一样,感觉就不怎么累了,觉得值得。”
然而,很多工薪阶层是双职工家庭,妻子的工作对家庭经济条件至关重要。在工作、家务的双重负担下,妻子无暇时时照顾丈夫的需求。夫妻俩也会就家务分工中产生争吵,比如在老王看来,自己赚钱养家就是尽到了丈夫的职责,做家务、照顾儿子主要是女人的事儿;而妻子则认为自己也工作,老王也应该多参与家务。因此,对一些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包养便宜贤惠的二奶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幻象,二奶们所给予的服务和照顾不仅再生产了工薪阶层男性的劳动力,还再生产了他们的尊严感,完成其“养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构。
比较而言,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则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在14个商人和高级白领包养案例中,有12位男性的两个“家”在同一个城市;另两个香港人,一个是珠宝商人,一个是建筑师,他们去大陆主要是去休闲和见二奶。这些男性几乎每天都会在外应酬,而其他家务则由他们的妻子或家里的保姆来承担。不少商人的二奶也请小时工来料理家事。家务照料在商人的包养关系中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但其符号意义却不容忽视。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遇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情形:这些二奶在和其他人外出吃晚饭时匆匆赶回家,因为他们的男人临时决定回“家”吃饭;还有二奶会特意从自己的住所——没有电梯的8楼——跑下楼去为男伴买他随口提到想吃的点心。通过恰当甚至略带表演性的家务劳动,二奶们给这些男人们传递了重要信息——他们在家中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因为他们的要求可被无条件满足。
(二)多维度的情感劳动
除了符号化的家务劳动外,二奶们也通过情感管理来帮助男伴完成他们所希望的男性形象。工薪阶层的二奶经常需要控制不满、不悦等负面情绪,比如,阿润这么描述男伴:
他就是性格急躁一点,别的都没有什么。我就是忍得住,随和他。有一次,他说要11点半吃饭,让我去煲汤,后来还没煲好,他就会说:怎么还没煲好啊,怎么那么久啊?他就不高兴,说11点半要吃饭。我就随和他了,说老太婆了,不中用了……后来他也就好了,如果顶的话也合不长的。
这些常被描述成“温顺、善解人意”的女性美德,事实上包含了大量的被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称为“情感管理”的工作——激发或压制情绪从而保持一种使对方产生合适心理状态的外部表情。(22)阿才的急躁易怒令阿润心里不满,但阿润的策略是“忍”——不从情绪和言语中表露出内心的不满,甚至采取一些自嘲的方式消解他的烦躁情绪,从而使对方的要求显得正当合理。阿润的“忍”一方面符合传统的女性规范——女性通常被期待控制愤怒、不满等情绪以表现“温顺”,另一方面也是她维系这段关系的重要策略,她深知“顶是合不久”的,在经济依附和“无名无分”的双重弱势下,她通过帮助阿才确认在家中的权威感以稳固自身地位。
一些二奶还给予男伴肯定和鼓励,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这对于在社会和家庭中缺乏认可的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尤为重要。50岁的老王曾是出租汽车司机,后来在妻子方荔亲戚的帮助下调入办公室做行政。三年前和一个比他年龄小20岁的打工妹小梅好上了。老王说:
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就是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但是方荔觉得这是赌博,坚决不同意,反应特别激烈……她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说人家开公司,赚钞票,我一点没上进心,一点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将。(我)在家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很压抑……(我)和小梅就很谈得来,每次我去她那里,觉得很放松,很愉快。她对我很好,给我做饭,陪我聊天,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她知道我跟我老婆的事情,她也很同情我,觉得我是很好的男人,应该有个幸福的婚姻……我跟她说过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照样对我很好。说实话,我蛮感动的。
方荔发现了老王的私情并愤怒地砸了小梅的住所,两人结束了25年的婚姻。离婚后,老王发现,小梅对他不会娶她感到很难过,并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她内心深处的感受。通过压抑自己的失望、不断给予支持,小梅让老王获得了一种“很好的男人”的自我价值感。(22)
与工薪阶层的二奶相比,商人阶层的二奶则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语伤害并抑制愤怒来迎合男伴。许多商人的二奶告诉笔者,在关系稳定之后,她们的男友经常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这些情绪发泄很多时候是一种“迁怒”。男性在工作、应酬、以及家庭生活中遇到压力或者不顺,经常会演变成在二奶处“找茬”,并将后者的忍受当作一种理所当然。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婚姻关系不同,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缺乏社会约束,完全依赖于包养双方的互动和牵制,只有在男性情感高度投入(比如关系初期或对二奶有强烈情感依赖)的情况下,男性才会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23)
比如,一次阿菲因为许久没见到阿东,在电话里对他娇嗔抱怨,没想到阿东在电话那头吼道,“你个婊子,你被那么多男人屌过了,你以为你还是处女啊,还说我对你不够好?!”阿菲很受伤害,但并没有回击。她说:“我这个男人就是粗鲁。跟他吵没用啊,他更气啊,骂得更难听,还关水喉(停止供养),费什么事呢?”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外,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使得他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比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阿英是一名香港珠宝商的二奶,她说,“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就说生意上的事情,我对他的生意没兴趣。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只好在那边听,假装听得很认真,有时候说几句,说这个真有意思啊,他听着高兴点。”通过专注的聆听、赞赏的笑声和肯定性的评论,阿英不仅满足了男友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情感需求,而且从她的反应中,男友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趣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商人的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相处中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感叹:“她让我感觉像个皇帝”。感觉像个“皇帝”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通过包二奶而获得的“好男人”。皇帝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拥有资格享受别人提供的各种服务,可以随意下达命令并期待这些命令总是能够得到执行。
(三)私人关系的外显
除了在私人空间彰显男友的地位,商人的二奶们还需要帮助男友在其社会圈子里获得“面子”。在新兴的商人和企业家圈子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常常被视为是最有价值、最值得拥有的男性战利品。在私人浪漫关系的光晕下,能够拥有值得艳羡的女伴一方面标志着男性个人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折射出男性的个人魅力和地位。
许多商人和企业家的二奶为了维护男人的荣誉和地位,会进行大量的身体劳动,(24)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场合呈现出“恰当”的女性身体。许多人会根据她们男友对伴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外表打扮,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一定想要他的二奶看起来是更年轻或时髦。例如,笔者访谈的两个二十岁左右的打工妹就常被比她们年长几十岁的男友要求穿昂贵的套装,而不要穿便宜、时髦的衣服,而且尽量少化妆。这种装扮可以使她们看上去更成熟,免得两人被误认作祖父和孙女。这样的装扮也可以掩盖她们的农村身份,让她们看上去更有文化和品味,不会被人当成酒吧陪酒女。相反,对那些30岁左右的二奶们而言,“装嫩扮靓”则是首要任务,这些女性会追逐最新的时尚并浓妆艳抹,甚至去整容以淡化年龄的痕迹,她们告诉笔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持形象上的优势,因为男人不会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又老又丑”。
商人们的二奶经常被要求陪同男友出席各种应酬活动。在这些男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中,对女色的消费构成男性缔结兄弟纽带的重要内容。这种应酬活动通常被建构成(有权势的)男人可以摆脱道德约束、满足一己私欲、寻找乐趣和刺激的场合,这与妻子的形象——去性化的贤妻良母和家庭的守护者——格格不入。所以,妻子的出现会被认为既玷污了家庭的清誉,又坏了男人的“性/兴致”;相反,二奶的陪同则能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她们被视为私人欲望满足的对象,所以在这些场合出现被认为是怡情的。
在这些应酬场合,二奶们要尽量使她们的男友看起来很有男性吸引力。比如,一天晚上,笔者跟随阿雪去她男友阿海开的夜总会。我们的包厢里还有阿海的两个朋友和他们的女伴。不一会儿,阿海来到我们的包厢,阿雪忙迎前挽住他,阿海笑着对大家说:“(刚才)碰到几个老朋友,来来来,喝一杯。”阿雪从茶几上拿起一只空杯,给他倒上啤酒。一个朋友递上一杯芝华士,说我们都喝芝华士,你喝啤酒不行。阿雪忙接过杯子说:“我男朋友胃不好,喝不得啊!”朋友们听她护驾,对阿海说:“女朋友体贴啊,你不能喝,她来喝一杯吧?”阿海看了阿雪一眼,阿雪娇嗔道:“哎呀,你们不要为难我男朋友,为难我啦。”看大家不依不饶,她接过酒杯:“好吧,只能喝一杯哦。”喝过了酒,大家坐下。阿雪紧紧倚着阿海,轻抚着他的手,柔情地说:“怎么去这么久啊?有没有累啊?”身边的朋友打趣阿海说:“你女朋友想你了,等不及了。”大家一阵哄笑,阿雪害羞起来,轻搡边上的男生:“不许欺负我!”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不同,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进而消解商品化性消费所建立起来男性魅力的廉价感,同时和陪酒女郎相比,二奶们的表演也要更为自然真实。因此,对很多被商人包养的二奶而言,出席这种应酬活动具有一定强制性,她们不得不去。
与商人的二奶们费尽心思给男人在公共场合“挣面子”不同,工薪阶层包养二奶的行为则更具私密性,包养二奶通常是工薪男性个体化的、修补男性尊严的方式,而并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亚文化。一般而言,工薪阶层的男性不需要参与半制度化的、充斥着情色消费的社交应酬活动,他们的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或者干脆排斥女性参与(比如喝酒、打牌)。二奶们很少被邀请参加他们社交活动,一些二奶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男人们的活动而使自己显得像个“贤妻良母”。
五、结论:性别的关系化建构及其本土意义
在当代中国,为了使男人的自我价值感、男性尊严和男性权威得到承认和确证,二奶们从事着巧妙而辛苦的家务、情感及身体劳动。家庭的私人环境以及情人关系的亲密性容易使男性将二奶所承担的繁琐的、往往是强制性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劳动视为是自愿的、甚至是非常乐意的;这一认知使男性进一步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是对自身男性气质的真实肯定和赞赏。
二奶们所承担的劳动对于其伴侣的意义,根据男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通过提供自愿而体贴的家务服务及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工薪阶层的二奶不仅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合理支出的家,为男伴们提供生活上的便利,而且还试图为他们制造“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价值感;商人们的二奶则需要进行大量的性别劳动以帮助她们的男友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一个优越而强有力的自我形象。这两种不同阶层的男性气质形式与市场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工薪阶层男性在新的市场经济时代被逐渐边缘化,因此,被承认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所带来的尊严感和价值感是其男性气质的核心;另一方面,商人阶层的男性在市场化改革之后逐渐拥有了经济能力,并试图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将女性身体商品化和男性欲望显性化的性别话语支持下,通过拥有漂亮女人来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构成了新贵阶层男性气质的核心。
必须强调的是,为他人制造性别的劳动不仅仅发生在亲密关系和异性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由于性别劳动需要以他人的意愿为中心并压抑对自我的关注,性别劳动的提供与获取往往呈现出某种权力和地位等级关系。居高位者往往将他人对其(性别)身份的确认和尊重视为理所当然,而居低位者一方面承受着性别劳动的重负,另一方面也将为他人制造性别策略化为获取资源、调整关系状态的手段,从而使得一些优势社会阶层可以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获得性别身份的确认及阶层地位的彰显。此外,关于特定社会关系中情感互动的社会文化准则也会制约性别劳动的方向和程度。
关系化建构的视角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性别身份的建构尤其有用。首先,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对于性别的界定既不是男女二元的,也不具有西方那种以性为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认定,而是基于人伦关系中的名分。(25)在人伦关系中,不同角色是互相依存的,一种身份的确立需要相关角色的扮演。即便在近代,“男女二分”的性别界定已深入人心,但特定性别角色依然包含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相关角色要素,比如,男性气质往往融合“夫”、“子”、“父”、“友”等多种角色要素的组合。再之,在社会转型时期,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多种话语的交织下,个体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被大大增强,更加需要来自他者的肯定和协助。此外,依赖人伦关系的性别观与多样化的性别话语也带来了性别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简言之,上述因素为我国学者突破西方个体主义倾向的局限进而更全面考察主体身份建构提供了契机,也让人期待出现更多融合“关系化”视角的性别研究佳作。
注释:
①阿菲解释说阿东留着跟老婆做爱是为了避免被怀疑有外遇。
②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184页。国内对婚外包养的媒体报道很多,但系统研究较少。潘绥铭在1990年代后期对于国内的“性产业”的研究中也记录了少量的“包二奶”的案例,并对包二奶的现象阐释了他个人的观点。潘绥铭认为“包二奶”属于广义的男性购买性服务行为……是以“包娼”为基础的、摹仿纳妾的、新的购买性服务的形式。包娼和包二奶,虽然不排除而且往往寻求双方共同生活,但是仍然以性交为目标和首要目标。潘绥铭从性产业入手接触包养情况,接触的案例也基本都是小姐变为“二奶”的案例,不难理解他把“包养”直接归为性产业的一种,把包养者和包养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与卖淫同质的“性与钱的交易”。这种观点也大体上是社会大众对婚外包养关系的认识。
③⑤Brownell,Susan.“Strong Women and Impotent Men:Sports,Gender,and Nationalism in Chinese Public Culture.”In 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edited by M.M.Ya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Yang,Mayfair M.“From Gender Erasure to Gender Difference.”In 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edited by M.M.Ya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Zhong,Xueping.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④Zhang,Everett Yuehong.“Goudui and the State:Constructing Entrepreneurial Masculinity in Two Cosmopolitan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in Gendered Modernities,edited by D.Hodgson.New York:Palgrave,2001.
⑥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2)。
⑦[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Zhang,Everett Yuehong.Birth of Nanke(Men's Medicine) in China:The Making of the Subject of Desire.American Ethnologist,2007(3).
⑧[澳]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⑨Farrer,James.Opening Up: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Osburg,John.Engendering Wealth:China's New Rich and the Rise of an Elite Masculinity.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2008.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6)。
⑩Yang,Jie.“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Class,Gender,and Kindly Power in Post-Mao China.”American Ethnologist,2010(3).
(11)West和Zimmerman提出,个体并非总是遵循性别的社会规范,有时甚至刻意违背和挑战,但往往需要为背离行为付出代价。
(12)West,Candace,and 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Gender & Society,1987(1).
(13)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14)比如,Barber,Kristen“.The Well-Coiffed man:Class,Race and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in Hair Salon.”Gender & Society,2008(4).Bettie,Julie.“Women without Class:Chicas,Cholas,Trash and the Presence/Absence of Class Identity.”Signs,2000(1).
(15)Connell,R.W.Gender and Power:Society,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6)Connell,R.W.,and James.W.Messerschmidt.“Hegemonic Masculinity:Rethinking the Concept.”Gender & Society,2005(6),p.848.
(17)Ward,Jane.“Gender Labor:Transmen,Femmes,and Collective Work of Transgression.”Sexualities,2010(2):237.Ward 对劳动(labor)概念的运用延承了女性主义者将由女性承担的家务、照料以及情绪渲染、情感抚慰等事务视为“劳动”的传统。
(18)Allison,Anne.Nightwork:Sexuality,Pleasure,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19)Hochschild,Arlie.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New York:Viking,1989.
(20)以在汽配公司当销售员、40岁的阿才为例,他每个月在广州出差两周。他在广州期间若外出吃饭和使用家政服务,支出大约是每个月1200-1300元。而他和38岁的广西打工妹阿润同居后,每月给阿润的生活费800元,支付他在广州期间的两人的开销500元,阿润为他做饭洗衣、收拾房间,此外他还能享受其他的免费“服务”,比如按摩和性生活。
(21)Hochschild,Arlie.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2)方荔和小梅对老王的期待是不同的。方荔比老王小两岁,宁波本地人。两人于80年代初结婚,婚姻最初几年情投意合。90年代初方荔的姐夫和妹夫都下海了,收入倍增,她和老王的所在单位的效益却越来越差。她希望老王多跟姐夫妹夫学习,改善家里经济条件,而老王却逐渐排斥去她娘家,认为“每次去总感觉低人一头”。他更愿意与和原来的同事和邻居们相处,并迷上了麻将。在90年代,麻将被认为是“赌博”,方荔爱之深,责之切,采取“劝说”、“责备”和“惩罚”等方式帮他“改邪归正。”在方荔看来,“眼看他染上坏习惯,随他去,那就不是自家人了”。小梅则是一名比老王小20岁的外地打工妹,她的第一次婚姻却以失败告终——丈夫是老家人,婚后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闲,还对她拳脚相向。来宁波后,小梅先后在洗衣店、餐馆和洗车房打工,生活清苦孤单。老王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男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养家,而且性格随和,会关心人。所以她愿意象一个“贤妻”一样——默默忍受、不抱怨、支持鼓励以帮助他“活得像个男人”。
(23)在追求和关系初期,男性通常不会随意发作,反而会忍受女伴的小性子和脾气。在他们看来,能追求到“难搞定”的女性是他们男人味的表现,他们甚至也享受这种调剂。
(24)Lan,Pei-chia.“Working in a Neon Cage:‘Bodily Labor’of Cosmetics Saleswomen in Taiwan.”Feminist Studies,2003(1).
(25)Tani E.Barlow,“Theorizing Woman:Funü,Guojia,Jiating (Chinese Woman,Chinese State,Chinese Family),”in Angela Zito & Tani E.Barlow,eds.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王政:《跨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