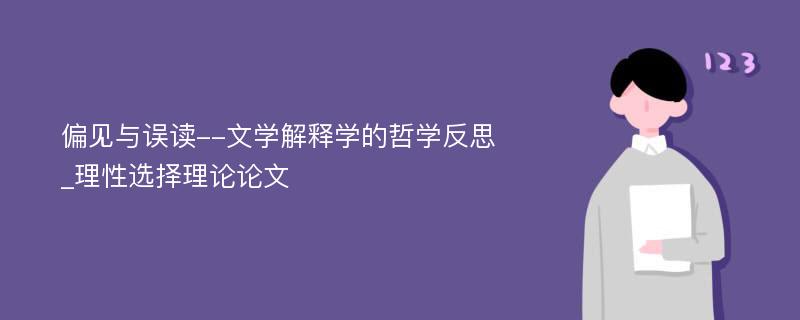
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偏见论文,哲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阐释学的根本问题还是哲学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阐释主体与文本原初意义(Original meaning)之间的纠缠问题。人的终极关怀总是诱逼着人在信仰上追寻一个恒定不变的本体,这种本体的终极关怀转向人的理解之后,则延伸为一种追寻文本恒定不变的原初意义的生存渴望。那么,人作为思者,为什么要如此渴切地追寻文本的原初意义呢?
在古希腊,思者曾塑造了向人传达诸神旨意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企图以赫尔墨斯对诸神神谕原初意义的理解和传达铸成思者自我的权威性,因此思者成为诸神神谕的有效代言人。在西方的中世纪,《圣经》文本的解读者企图以对《圣经》文本原初意义的理解,把自己塑造为上帝的代言人,因此每一位主教都以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来装饰着自己的尊严,从而企获教诲芸芸众生的权威性。在东方的中世纪,两汉的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对“六经”文本原初意义追寻的争执,在骨子里也是企图以“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来支撑自己的权威性言说,使自己成为孔子或周公的代言人。原来这些思者在他们的阐释行动表象下掩盖着一种窃夺权力话语的野心。可以说,在东西方漫长的中世纪, 正是这些苟于功利性的思者对《圣经》和“六经”经典文本原初意义的追寻中,在方法论上推动了东西方古典阐释学的生成。[①]倘若我们拂去这些思者在阐释中追寻经典文本终极意义的智慧,裸露在我们视域的即是思者的阐释无非是强借经典文本而追寻所谓原初意义来维护传统及传统的权威性,以此最终满足自我庇荫于传统与权威之下的权力话语表达。
这,就是东西方古典阐释学在解读经典文本中的共同价值取向。
东西方古典阐释学在运作的目的论上曾各自有过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标志着古典阐释学从宗教的层面带着极端的功利性向人文科学渗透,最终成为阐释主体以经典文本以外的普泛文本进行解读的一般方法论。在西方,这一转机是在阐释学之康德——施莱尔马赫调合文献学和经典注释学的努力下完成,并以狄尔泰为开端的;在东方,这一转机是在经学大师郑玄在调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努力下兑现的。但遗憾的是,古典阐释学的转向并没有在一般方法论上给文本意义的追寻带来理解上的澄明,反而在时空的分隔中把文本作者的原初视域和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置放于历史的两端,给文本的理解障设了非历史感的不可解读性。倘若我们从顾颉刚的历史理论反观文本,实际上文本就是层累地造的历史积淀,阐释主体对文本的理解在理论上即是对文本生成的原初视域的历史追溯。而古典阐释学在非历史感的迷误遮蔽下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阐释主体通过文本的透镜追溯逝去的历史,而最终却导致了自身存在历史的自我遗忘。可是,对于经典文本终极意义的有效追寻,古典阐释学从来就没有在方法论上怀疑过自己不可奏效。因此,古典阐释学趋使着阐释主体把在文本读解中获取的相对意义在历史的虚无感中转换为绝对命令,仰仗着传统和权威趋赶着历史行进,因此阐释主体全然在失落自身存在历史的真空语境下宣称:我就是历史!作出一副“我就是历史代言人”的姿态自欺欺人。罗兰·巴特曾在《历史的话语》中企图借助符号学的分析消解历史话语中的“事实”概念本身,为他的虚无主义历史观张本。这虽然是一种首先攻击他人无能再承认自己不行的理论软弱,但这种理论的软弱毕竟还是表达了当代西方学者对古典阐释学历史虚无主义的嘲解。
然而罗兰·巴特对古典阐释学进行的嘲解却比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张扬的理性对传统与权威的取代延误了两个世纪。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推动了思辨哲学以理性取代经院哲学铸成的传统与权威。笛卡尔曾在怀疑一切中最终找到他认为无可怀疑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大自然在”。笛卡尔曾以天赋理性把上帝推下了本体格位,理性作为生命主体天赋的普遍原则与上帝的天赋观念同在,在笛卡尔的逻辑推导中,上帝虽然在本体论上失去了以往的宗教尊严,但是笛卡尔在哲思中还是被迫认同了上帝在非本体格位上存在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人文精神对理性崇拜的狂热使其成为取代上帝后的新的权威。从此理性便以自身的智慧和不可一世的傲慢遮蔽着阐释学的发展。不啻笛卡尔,在这一时期的欧洲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的力量就在于它以普遍性原则给予每一生命主体追寻客观真理的平等权力。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平等权利的设置是以承认文本融涵客观真理为大前提的。但是理性恩赐于人的公允向阐释学的渗透着实地给主体对文本的阐释凝铸了一个无尽的困惑,因为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对阐释学的浸淫,在逻辑的推导程序上不容置疑地给任何一个文本设定了一个客观的可以有效追寻的原初意义,即在客观真理的层面上为文本无容置疑地设定了原初意义,并且这一原初意义在理论上阐释主体与文本作者共享的权力。因此,理性要求此时此在的阐释主体可以超越自身存在的当下历史视域去收览彼时彼在的文本作者创建文本的原初意义。的确,理性的普遍性原则在阐释的逻辑上打通了阐释主体与文本作者可能共享原初意义的契合点,但这一切是以阐释主体遗忘自身存在的历史为替换代价的。这就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一针见血点破的阐释主体“自身存在历史的自我遗忘”症。
人不可抛弃历史!但随着历史的逝去,一切理论的狂热在冷却之后都给后来者留下了反思的鉴照。让人倍感无尽嘲讽的是,在西方阐释学发展的历程中,理性与宗教在对文本的阐释中似乎共同执行着共同的解读原则,两者都以追寻到文本的原初意义而彰现阐释者的权力话语。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依仗上帝的威严追寻到宗教经典文本的绝对教义,而后者凭借理性不可一世的傲慢收览了被阐释文本中的绝对原初意义。我本人在思考中绝然不愿把终结中世纪而启蒙一个精英时代的理性与失魂落魄的上帝相提并论,但理性在历史中渴求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功利性逼使我的思路只有归此而然。倘若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伽达默尔在其哲学阐释学体系的建构中为什么以“合法的偏见”来拒斥理性的深层心理。无论如何,理性的权威性向阐释学空间中的转移最终表现为阐释主体借助于理性而达向对文本原初意义的追寻,因此阐释主体往往一旦成为文本原初意义的绝对理解者,便带挟文本作者的权威意志而逼视此在空间的他者向其就范。在文学艺术的阐释空间中,这种逼视他者向其就范还仅仅是审美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的问题,而政治文本的解读者则可能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文本霸权主义解读精神中欺世盗名地遮蔽一个时代。
那么,文本究竟有没有原初意义呢?这是当代阐释学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想即便承认有,文本的原初意义也只能在理论的假设上成立。90年代是一个理论多元主义的时代,任何一种理论的张本者企图以自己并不受别人尊重的自以为是欺行霸市都显得极为不明智,因此应该允许在理论上自由地论证文本原初意义的存在或不存在。但是从前者来看,在人类文化演进的3000年来,又有谁在阐释中真正捕获到作者赋予文本的原初意义呢?恐怕作者是脱离自身写作的那个特定语境,他自身也无法有效地再度拾寻自己赋予文本的原初意义。从当下学术界讨论阐释学的多元理论视角看,我想可以这样综述:文本的原初意义是人类精神视野的盲点,从理论上可以设定它的存在,但主体在文本的阐释中又不可能对他明视,即然不可能对它明视,在理论上又可以放弃追寻它的存在。康德曾以四个二律背反告诫芸芸众生:人类文化就是在二律背反中行进的。据说,这就是阐释学关于文本原初意义追寻中的一个二律背反。
文学理论界存在着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那些思考极为至深的精英人物在对繁琐而复杂的命题解析中,其艰难而痛苦的思考一旦莫明其妙地陷入一种理论悖立的紧张,他们大都以“二律背反”为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寻找终极解答的归宿,这样“二律背反”就成为思者中的弱智者逃避思考的一种展览智力无能的理论范式。这大概是康德之后的智者在面对两类悖立同时又各自成立的现象所表现出的无奈。然而在东西方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位思者最终没有就范于阐释学的“二律背反”,他“以偏见反对偏见”的阐释学命题终结了阐释学史程上的两个时代:具有宗教性的古典阐释学时代与启蒙理性的阐释学时代。他驻足于“视域融合”(Horizont verschmelzung)的高度制造了文本阐释理论中的历史碰撞,从而消解了文本的原初意义,并出语惊人地向历史宣称“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④]把“理解”打入“合法的偏见”中,最终使学术界的思者在折服于他的强大理论能量的威慑下触摸到这样一个潜在的真谛:人类文化创生的初始即是在理解的“误读”(Misreading)中行进的,且最终走向了历史建构的精深博大。
此人,就是伽达默尔。
二
如果我们顺延着伽达默尔思路成立这样一个命题:一部人类历史的集成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误读史;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无论如何先让我们的思考沿着伽达默尔走下去。
伽达默尔是幸运的,他前有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他一手挟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一手牵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本体论,顺理成章地步入了阐释学的思考空间。在这里,我们用胡塞尔的悬置理论先把胡塞尔本人与其现象学理论悬置于括号中暂且不论,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关于“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理论给伽达默尔支撑自身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杠杆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
在西方,阐释学的发展曾在海德格尔思考的左右中完成了一次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巨大转向。海德格尔把理解认同为“此在”的人把握自身存在的方式,把理解置放在生命存在的本体论高度。但海德格尔又没有把企图在理解中证明自身存在的“此在”的人——阐释主体设定为理解的起点,而是把理解的起点辅设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个起点就是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前理解”这个概念的容量是巨大的,它以“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和“先知”(Vorgriff)三个层面,涵摄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和精神物化物。海德格尔以为,主体只要在阐释中进入“理解前”,就被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所侵占,因此主体绝对不可能再是一个通体透明的文化处女,再因此主体也绝对不可能在贞洁的状态下不带任何失贞的偏见追寻主体的原初意义。说到底,理解是不可能从阐释主体自身的贞洁开始的。这也正如德里达在《回忆保尔德曼》一书中所言:“我们只能是先于我们知识景观下的我们。”[⑤]实际上,海德格尔在智者千虑中忽视了这一点,无论主体是否进行理解,它都必须处在“前理解”的状态中。人只要存在于历史中就必然失去自身的贞洁而不是一具文化处女。但海德格尔的思考的确又有出人之处,他在理解的本体存在——人与“前理解”之间设置了一个具有张力的时空跨度,我想任何一位对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投入致深思考的学者都可以体验到这样一个在拉开的时空跨度中所带来的理论紧张。“此在”的人渴望以理解证明自身的存在,而理解的起跑线却又不设置在理解主体自身的脚下,理解主体只能从距离自身遥远的历史地平线——“前理解”起步达向对文本意义的获取。这种极度紧张的理论体系结构设置绷得人喘不过气来。理论体系内部构设的紧张恰恰是理论的生命张力。而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拉开的时空跨度中置入了历史和理解的历史感从而缓解了两端的紧张。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启步达向文本,必然带着历史的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所以阐释主体怎样也无法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威慑,而带着本质的贞洁与文本的原初意义相结合。在海德格尔这里,为了张扬理解中的历史性只有把历史贬损为主体理解文本的有色眼镜了。历史为在阐释中突凸出自身的价值——历史性,在名誉上为此负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文本意义获取中的“偏见”。
“偏见”(PrejudicesNoruteile),就是由海德格尔率先提出的。
如果说,海德格尔关于“前理解”思考的主旨还是在于为了论证他的“此在”的存在做本体论意义上的辅设;那么,伽达默尔则把“前理解”径直带入他的哲学阐释学体系的建构中,推出了他的一系列命题,使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存在的本体论思考走向了深化和体系化。
伽达默尔是偏激的。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过“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内涵,在阐释学的理论上把其统统打入文本解读的“偏见”中,又把“偏见”合法地归置在主体解读文本时其视野得以展开的历史地平线上。这个“历史地平线”就是伽达默尔所言称的主体在阐释中得以展开的“视域”(Horizont)。伽达默尔给人启示最为深刻一个理论切入点就是“视域融合”。提及“视域融合”,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判一下当下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
殷鼎在《理解的命运》一书中是这样理解的:“当我们带着自己由历史给予的‘视野’(视域)去理解历史作品、哲学、或某种文化时,就一定会出现二(两)个不同的‘视野’或历史背景的问题。我们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这是我们的‘视野’,但我们却又是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解释的对象。如历史典籍、历史事件,某种哲学,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历史的特定内容,限制了我们的‘先见’(前理解),只接纳它可能接受的理解。无论是去解释历史、文学作品,以及他人的言谈,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的相互限定的历史背景。只有当这两个历史背景,即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溶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加德默尔称这种过程为‘视野的溶合’(视域融合)。”[⑥]根据殷鼎对伽达默尔“两个不同的‘视域’”的所谓理解,第一“视域”是指称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及三个层面的内涵(“先有”、“先见”和“先知”)。这个“视域”是历史通过语言的代际传递对阐释主体进行渗透、占有的文化侵蚀和文化压迫,是历史强加于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第二“视域”是文本的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这一历史语境渗透、占有了作者的理解及文本意义的生成。由于第一“视域”作为历史对阐释主体浸淫而行成了理解的起点,因此理解不可能从主体未受历史侵占的贞洁状态起步而达向对文本原初意义的获取,理解只能从第一“视域”起步而达向第二“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最终导致了两个视域的融合。注意:第一“视域”是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就我本人理解其特点是“历史的当下”或“当下的历史”。因此主体对文本的理解无法摆脱历史的引力而必然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视域融合”中产生的“偏见”。
而王岳川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中这样理解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本文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亦称‘初始的视界’),而去对这本文进行理解的人,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亦称‘现今的视界’)。蕴含于本文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本文进行解读的理解者‘现今的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理解正是从现今祝界起步达向初始视界,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⑦]根据王岳川关于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所谓理解,作者创建文本而存在的历史构成了作者的初始视界,因为“理解者的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⑧]主体理解文本而自身存在的“现今时代氛围”构成了阐释得以起动的现今视界,从而营造了阐释过程中的“视界融合”。因此主体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带着“现今时代氛围”的当下历史感去解析文本的意义,使文本意义的理解走向了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视域融合”中的“偏见”。
比较一下殷鼎与王岳川对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对“偏见”内涵的理解有着极大偏失。
殷鼎理解的第二“视域”与王岳川理解的“初始视域”有着一致性,均是指涉文本的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殷鼎理解的第一“视域”与王岳川理解的“现今视域”则有着极大的意义偏失。殷鼎理解的第一“视域”是指涉历史逝去的彼端通过语言的代际传递与历史当下的此端携手的整个历史语境,而王岳川理解的“现今视域”则纯粹是指涉主体阐释文本时自身栖居的当下历史。当然从顾颉刚“历史的层累地造说”观审,当下历史也是从逝去的历史积淀而来的,但王岳川在理解中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难见出,前者把理解的历史及历史感置放于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而后者把理解的历史及历史感置放于阐释主体的当下历史与文本创建的原初历史语境之间。因此前者理解的“偏见”是在从逝去到当下的整个历史与文本创建的特定历史语境的逻辑问答中发生的,而后者理解的“偏见”仅是在当下历史与文本创建的特定历史语境的逻辑问答中发生的。那么,究竟谁理解的“偏见”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体系中的那个原初意义的“偏见”呢?殷鼎的《理解的命运》一书基本上是在多本关于介绍阐释学的原著的翻译上而完成的,在自身没有投入多少主观的理解下,其对文本阐释的“偏见”的理解最接近伽达默尔的原初意义。而王岳川对文本阐释的“偏见”的理解则是在理解的“偏见”中完成的。这实际上构成了西方阐释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理解偏见,这是一种跨文化的阐释学理论误读。最有意思的是,两位研究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人在对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的理解上却没有达成理解的共识,这只能说明阐释学无法使自身的阐释理论在阐释学研究者对自身的阐释下走向理解的澄明。
阐释学最终无法回避理解的“偏见”。
本文对“视域融合”理解的审判无意于褒贬任何人,“理解”本身就无法用“好”与“坏”来区别对待。本文只想从“审判”使自己的思考向前递进一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从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到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两者在联手清算古典阐释学与启蒙时期的思辨理性关于阐释主体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症时,把“历史”与“偏见”作为两颗等值的法码置于同一樽价值天平的两端,在两者的价值平衡中,“历史”使文本阐释中的“偏见”成为了“合法的偏见”。古典阐释学与启蒙理性时期的阐释学在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力时,往往总是以追寻到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敌视理解中的偏见,但伽达默尔正是以“合法的偏见”把两者统统打入“以偏见反对偏见”的误读中。在伽达默尔的思路延伸下,于是,人在历史的无可回避中建构的只能是效果历史,一切文本的读解均是在“合法的偏见”中行进,再于是,伽达默尔崇尚“合法的偏见”在极端中抽去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有文本的原初意义、消解了古往今来的一切阐释主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话语、治愈了阐释主体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症,把理解中的“客观真理”、“绝对命令”、“根本原则”等等从人类思想的圣殿中清扫出去,为理解中的多元阐释主义精神张本……
最终,历史与文化也正是在被理解的“偏见”中呈现出人赋予他的宽容与尊严。
三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为了给文本读解的多元阐释主义精神留一块合理的本体地盘,曾把他的视野谨慎地投入到法律的语境中寻求“偏见”的合法性。当“偏见”在伽达默尔那里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后,我们不禁要设问:“偏见”与“误读”又有怎样的不同呢?照我看来,“偏见”与“误读”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在国语的表达中,两者只是以不同的能指来涵盖同一所指罢了。我们完全可以用“误读”这样一个概念统领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赋予“偏见”的全部理论内涵。曾几何时,伽达默尔在他的思路困惑中倍感有必要界分“偏见”与“误读”的不同,因此在《真理与方法》中,他曾对“偏见”这一概念做出了二元界分,企图从“合法的偏见”与“盲目的偏见”的悖立中分离出作为“误读”的“偏见”。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体系中,“合法的偏见”相当于康德的十二理性认知范畴,是历史“先验”地给定予阐释主体的具有正面价值的渗透和侵入,“盲目的偏见”则是阐释主体栖居于文化语境中后天地对历史的获得性接受。伽达默尔的思考蹒跚到这里后显得很疲惫而苍白了。我们不禁要设问:逝去的历史对当下存在的阐释主体而言,其是否构成先验的认知范畴呢?是否能用“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来界说历史的先验性渗透与历史的获得性接受呢?在阐释主体的文化心理成分中,又怎样明晰地界分哪些是先验性渗透与哪些是获得性接受呢?又怎样把阐释过程中产生的“偏见”明效大验地归类于“合法”或是“盲目”呢?设问不能再进行下去了。伽达默尔穷尽了自己的智慧,最终没有使自己的哲学阐释学理论在体系的建构上走向自恰。“盲目的偏见”的设定在理论上取消了人对历史接受的选择性与主体性,使人处于遮蔽状态,而“合法的偏见”又取消了文本理解的原初意义,使人固执阐释的主体性处于敞开状态。
年迈的伽达默尔一头撞在悖论上瞢然不知所措。
严格地讲,伽达默尔对“偏见”的再度二元界分是从思考的误区中走来的理论徒劳。既然伽达默尔无法使他的“盲目的偏见”在理论上对立于“合法的偏见”而奏效,就没有必要从“合法的偏见”中分离出“盲目的偏见”,否则,人在历史的浸淫下永远是一个纯粹的受动符号而已。实际上,伽达默尔在理论上论证“盲目的偏见”的失败在总体上承认了“偏见”就是“误读”。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偏见”把“误读”限制在“非合法”的负价值取向中,所以“误读”,只有对“合法的偏见”敞开。因此毫无疑问,“偏见”就是“误读”,“合法的偏见”就是“合法的误读”。
当我们思考到这里后,不禁感到一种莫明的恐惧,难到一部人类历史的集成真的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和人类文化的误读史吗?难到一部人类文学批评史也是一部人类情感和人类审美的误读史吗?其实在“偏见”与“误读”之间,我们仅仅只是在情感色彩上不愿选择后者这样一个具有贬意的概念来替换前者而指称这一事实罢了!
语言是信息的交换媒体。实际上,当东西方的第一位哲人在本体论上用语言读解自身栖居的那个自在的宇宙时,人类就开始了漫长的误读历程。在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巴门尼德乘坐着驷马高车驰骋于女神大道,圣哲般地告诫芸芸众生:“要用你的心灵牢牢注视那遥远的东西,一如近在目前”,[⑦]那就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的终极“存在”(Bing)。[⑧]在中国哲学史的源头,老子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体猜想中,[⑨]把“道”比附为创生宇宙的“众妙之门”。[⑩]难道宇宙的本体真的就是巴门尼德读解的“Bing”和老子阐释的“道”吗?只要宇宙的本体对上述两位哲人的本体论猜想不给予自明的验证和回答,巴门尼德与老子的本体论读解只能是两个亘古历史的“误读”。语言的代际转递能力是可怕的,其往往以一种巨大的惯性推动着那些奔命于思考的哲人们从第一次“误读”走向无尽的“误读”。语言把巴门尼德与老子在猜想中对宇宙本体的“误读”在历史的积淀中承传下去,使一代又一代的智者哲人耗尽终身的精力在“误读”中承继着形而上学的本体思考,从“误读”走向“误读”,再度走向“误读”……,因此东西方哲学史上才有了那些虚妄而又极富于思想的一系列本体概念和本体范畴:巴门尼德的“存在”(Bing)、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logos)、柏拉图的“理念”(ldea),圣·奥古斯丁的“上帝”(God)、康德的“物自体”(Thing in itself)、黑格尔的“绝对理念”(Absoluteldea)、老庄的“道”、《周易》的“太极”、杨雄的“太玄”、二程的“理”、陆九渊的“心”等等,他们每个人都以其惊人的思辨能力在“误读”的本体概念和本体范畴上建构起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一哲学行为的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谁也没有能够以自己的读解使那个自在的宇宙本体走向澄明,因此可以毫不偏激地说,他们对宇宙本体的哲学阐释统统都是在“误读”中建构起自己庞大的理论体系的。无论是古典阐释学还是现代阐释学,它们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还是本体论的问题,当东西方的第一位哲人在“误读”宇宙本体中推动人类的哲思启程后,不啻后来的哲人走向误读,作为哲学分枝的阐释学也正是在哲人“误读”的历史中发生,并带着人自身无可逃避的“误读”企图去解决“误读”的困惑。
这,就是阐释学自身无法回避的悖论。
狄尔泰把整个人文世界景观“误读”(阐释)为一个硕大的文本,在这个世界景观的背后没有绝对客观真理,文本也没有原初意义,因此“误读”永远合理。当我们的思考延伸到这里时,我们再也不恐惧理解中的“误读”了,似乎体验到人通过语言进入他存在的世界,又通过语言的“误读”赋予这个单调的世界以多元的思想色彩,又体验到只有“误读”才可能使人成为他自己,只有“误读”才可能使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充满了意义,只有“误读”才可能消解文本阐释中的权力话语。施莱尔马赫有句名言:“哪里有误读,哪里就有阐释学。”[①①]我窃以为应该调换一下这一命题表述的语法逻辑位置:“哪里有阐释学,哪里就有误读。”因为人只要从语言进入阐释就必然走向“误读”。这是人命定如此的劫数!
因此,“阐释”就是“误读”,而“误读”又是思者的思想源泉。
最后,让我们的思考驻足于哲学阐释学企获的真理观和知识观来结束我们的思考。由于几千年来,人在对文本的阐释中从未获得过文本的原初意义,文学阐释主体在对文学现象的阐释中也从未获得过文本的原初意义;可以说人与人之间、阐释主体与文学现象之间,从来就没有过本真而澄明的理解,人总是借助阐释而费尽心机地揣度他者。人,在阐释中从来就没有追寻到客观真理,也从来就没有收获到文本的原初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人最大的幸运。顾颉刚曾在《古史辨·自序》中一语道出这一命题的真谛:“(我)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①②]“阐释”的“误读”使人永远置身于彷徨觅路之中寻找着真理,而人类思想总是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产生,而不是在寻找到真理的行为终结中产生。人的本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阐释的主体意识,而动物没有阐释的主体意义,因此动物所面对就是一个恒定的、绝对的客观世界。因此,任何非生命的客观存在对于没有主体意识的动物来说都自然障设的“绝对真理”。可以说,“误读”是阐释主体——人的意识的根本内涵,因此任何终极真理的获得都意味着人类思想的毙命和终结。
“误读”又可以界分为自觉性误读和非自觉性误读两个维面,因此“误读”始终是在知识的建构与解构中以其极端的破坏性与创造性推动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反思中国思想史,几乎每一次思想巨潮的涌起都是肇事于那些思者“误读”的推波助澜,魏晋玄学以道家思想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破坏性读解是在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的自觉性“误读”中完成的,这些玄学大师以援道入儒的“误读”轻而易举地读破了两汉经学大师“皓首穷经”构筑起的儒家学术宗教世界,终结了汉代,创造性地开启了一个思想的魏晋时期。宋明理学和心学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中援佛老入儒,从而构成一种极端的破坏性“误读”,陆九渊一扫汉唐经学大师“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的封闭性阐释尊严,[①⑤]狂妄地叫嚣:“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①⑥]“误读”在宋明理学与心学这里把自己的两个维面在阐释中演奏得淋漓尽致,因此理学家与心学家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误读”才可能在最大的破坏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思想。
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那些有识之士的翻译和阐释下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指导着中国革命。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如毛泽东等人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语境下以自己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阐释的,[①⑦]这种阐释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营造的那方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撰写的西方近代革命历史那方视域的跨文化融合,而不是遗忘中国革命自身存在历史的对马克思经典文本原初意义的绝对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任何经典文本一样,任何阐释者都不可能从其文本空间获取绝对的原初意义。五、六、七、八十年代那些书斋式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的阐释者,都曾武断地认定自己的阐释达向了对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原初意义的绝对理解,殊不知太可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阐释学空间,恰恰就是要求主体在文本阐释中遵循自身存在的历史语境,这才是阐释学中的历史主义者。因此上述阐释行为从骨子里讲,也就是企图假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从而获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空间的权力话语表达而已。无疑,这是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阐释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不啻是文学理论空间,可以说在哲学、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空间,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阐释中,谁也没有本真地触摸过马克思的亡灵,包括马克思本人脱离了他的经典文本撰写的特定语境,他也无法再度获得他曾赋予文本的绝对原初意义。因此,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阐释是在创造性“误读”中完成,才可能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才是阐释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这也才是文学阐释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态度。从现代阐释学意义上观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经典文本在当代中国当下实践语境中最大“误读”的理论成果。也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发展。
就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现象,乐黛云曾在《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一文中指出:“总之,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于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吸取新义,还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的立场上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①⑥]的确,只要历史在碰撞、文化在交流,“误读”与人类将同在。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大陆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正浸淫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经典文本的“误读”中,伽达默尔、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杰姆逊、哈桑、佛克马他们著作文本的支言片语被解译到中国大陆来,与当下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碰撞着。当一批中国学人中的有识之土屈就且委身于西方后现代理论支言片语的语境下,带着西方后现代的视域阐释当下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现象时,于是在阐释中,中国不仅有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也终于有了中国自身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理论。实际上,当我们目睹中国大陆的后现代主义阐释者在圈子内就后现代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本真获取进行相互攻讦时,这不禁引起我们这样的思考:他们之间的攻讦大都是非常刻薄的,都企图以指责对方没有读懂西方后现代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而张扬自己。实际上,他们都忘却了这一点,当西方的阐释学走向后现代之后,在理论上已经取消了文本阐释的原初意义,支撑在阐释背后只有“误读”。问题在于,不管他们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是想违背阐释学在后现代时期的理论内涵,在大陆中国获取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绝对表达权力而已。我想大概他们谁也没有本真地触摸过西方后现代主义经典文本的绝对原初意义。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些明白人为什么把大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尊称为“伪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这里有一个使大陆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处境很惨的二难推进,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那么你就不要声明你获取了后现代主义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如果你声明你获取了后现代主义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那么你就不要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但无论如何,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当下大陆中国的“误读”使经济发展而思想贫脊的90年代充溢着思想,其结果就是当下国内的文学艺术现象在“误读”中的“后现代化”。可谓是饥不择食。可以说在80年代初,袁可嘉在《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中最早介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①⑨]从那时起他便给90年代的学人爆炒和“误读”西方后现代主义埋下了伏笔。那么,又是谁承继了袁可嘉,成为90年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最大“误读”的肇事者呢?
思考到这里后,我倍感困惑,不禁设问:还有什么文化现象不是“误读”或不是被“误读”呢?一位颇有才气和思考的学者回答我道:“大概没有了!”其实未必然,我在困惑中还是极度清明的。我说有:那就是王朔小说中连篇累牍的脏话即“我是你爸爸”或“操你妈”什么的,大概只有这些“伪后现代”文学话语的表述不会引起误读了,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解读它的原初意义。[①⑧]
注释:
①经学既是中国古典阐释学,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宗教,经学以注疏、训古、诠释、考证而达到对儒家经典文本意义的理解。这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对《圣经》经典文本的读解在方法论与目的论上有着一致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都是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延伸出来的学术思潮。
②H.G.Gadmer and G.Boehm eds.Philosoghical Hermeneu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55
③Jacques Derrida.Memoris for Paul de M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6.P.34
④《理解的命运》殷鼎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2页。目前学术界关于阐释学一些概念的翻译比较混乱,如“Horizon”有“视界”、“视野”、“境界”、“境域”等几种翻法,本文以为应该译成“视域”为恰当。
⑤ 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⑦ ⑧《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上卷,第31页。
⑨ ⑩《老子》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5、1页。
①①F.Schleiermacher.Hermeneutik.Hrsg.von H.Kimmerle,Heidelberg.1959.p.15
①②《古史辨·自序》顾颉刚撰,见于《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①③《经学历史》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页。
①④《陆象山全集》陆九渊著,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252页。
①⑤毛泽东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阐释不是书斋式的,而是主体走出书斋的一种思想加实践的阐释行为。
①⑥《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乐黛云撰,见于《独角兽与龙——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乐黛云、勒·比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①⑦袁可嘉曾在1982年撰写《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该文见于《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袁可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实际上在80年代初,袁可嘉最早介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当时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正急食于“伤痕”、“反思”、“寻根”、“文化热”和“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而不可消化,的确没有更多的胃口吞食“后现代主义”什么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90年代“后现代主义热”的独领风骚恰恰说明了当下国内文学理论界正处于自我思想的贫困状态和自我精神的饥饿状态。
①⑧Project Supported by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标签: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伽达默尔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本体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