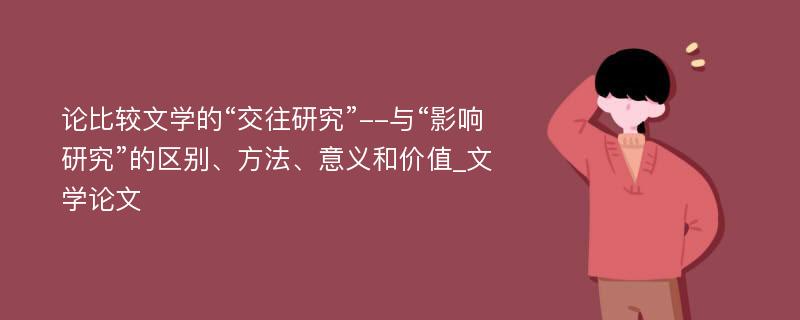
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它与论文,区别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2-129-06
一 “法国学派”的方法是“传播研究”而不是“影响研究”
在对传播研究方法进行阐述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与传播研究方法有关的“法国学派”及“影响研究”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将“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看成是一回事,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影响研究”是“法国学派”,又在这个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文学传播与文学影响等同起来,把“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等同起来。然而,如果我们将法国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和主张,及法国学派的研究特色做一必要的检讨和辨析,就不难看出,“法国学派”实际上并不赞成“影响研究”。
第一位阐述和总结法国比较文学百余年研究经验的理论家是梵·第根,他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多国(仅在欧洲范围内而言——引者注)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所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进一步解释说:“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界限之外这件事实。”梵·第根把这种“经过路线”分为放送者、接受者和媒介者三项进行研究。从放送者的角度来看,考察一个作家在国外的影响与声
誉,梵·第根称之为“誉舆学”;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的来源,即源流学(今译“渊源学”);研究文学传播的途径、手段,包括翻译、改编、演出、评介等,即媒介学。由此看来,梵·第根所阐述的实际上是文学的“传播”关系,那时梵·第根没有直接使用“传播”一词,但他所谓的“经过路线”,其意思和“传播”完全相同。当然他也使用了“影响”一词,但他所说的“影响”与“经过路线”实际上是同义词,并没有对“影响”加以严密的界定,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经过路线”与“影响”两个概念的混淆。
此后,法国学派的另一个著名的理论家J-M·伽列(一译卡雷)在为他的学生马·法·基亚的《比较文学》初版所写的序言中,则开始对“影响”研究与法国学派所推崇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做明确的区别。他认为,比起有事实为据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来,“影响研究”是不可靠的。他写道:
人们或许过分专注于影响研究(Les études d'influence)了。这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相比之下,更为可靠的则是由作品的成就、某位作家的境遇、某位大人物的命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旅行和见闻等等所构成的历史。[1](P43)
和伽列一样,基亚也对“影响研究”持怀疑态度。他在流传甚广的《比较文学》(1951)一书中写道“有关影响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当人们想把问题提高到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影响时,那无疑很快就会落到抽象的语言游戏中去了。”[2](P16)因此基亚更明确地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做了界定,即“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认为比较文学家也应该是文学关系史家。他把“文学世界主义的媒介因素”——即国际关系的媒介工具(翻译、旅行)和使用这些工具的人(译者、旅行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基亚举例说:研究法国作家伏尔泰与英国的关系,“主要的还得说明这位流亡者(指伏尔泰——引者注)是怎样熟悉这个国家的、是怎样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的,又是怎样交朋友的。他回法国后又让人们了解了英国哪些方面的情况,为什么让人了解这些情况而不是另外一些”,认为“这些工作的优点是可以避开‘影响’这个暗礁”。[2](P16)
上述法国学派几个代表人物的观点足以表明,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影响研究”学派。毋宁说,法国学派对“影响研究”是持怀疑的、或者是不赞成态度的。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将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混为一谈。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人们意识到了“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例如看出“法国学派”仅仅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欧洲,看出“法国学派”对“接受者”的研究重视不够,看出“法国学派”反对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主张以“确实的事实”来证明“影响”之存在的不可行性。但是,现在我们确认法国学派不是“影响研究”,而是“传播研究”的学派,那就很容易看出,人们对“法国学派”的批评,是站在“影响研究”的立场上,用“影响研究”的学术标准来批评“法国学派”的。而倘若从“传播研究”的立场来看,“法国学派”的学术主张就显出了更多的合理性。法国学派仅仅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欧洲,除了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法国中心论的意识在起作用外,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国学派”知道,只有欧洲内部的文学传播才有大量可以实证的确凿的事实可以收集,可以画出清晰的文学传播的“经过路线”。而跨出欧洲的范围,确凿的“传播研究”的事实就少得多,“传播研究”就显得很困难,就势必要使研究跨入他们所怀疑的“影响研究”的范围。“法国学派”反对推理与分析的方法,这对于“传播研究”而言,也是合理的。因为“传播研究”必须实证,推理和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但“影响研究”用实证的方法就未必可靠,很大程度上要在有限的事实的基础上,依赖于分析、推理的方法。
说明“法国学派”不是“影响研究”的学派,说明“法国学派”的实质是“传播研究”,对于区分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及其分野,是非常必要的。
二 从“影响”与“传播”之不同看传播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国际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影响”的研究和“传播”的研究混为一谈。诚然,“影响”与“传播”有共通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影响”也是“传播”的,或者说,“影响”也有“传播”的性质。但是,为了科学地区分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方法,我们必须搞清文学中的“影响”与“传播”这两种现象的本质不同。在比较文学中,“影响”不是一种物理的事实,甚至不是一种本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影响”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影响(influence)一词,在西文中起源于古代占星学,本指星体对人类的感应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难以觉察的,具有神秘的形式,后泛指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微妙的影响关系。中文的“影响”两个词素,恰切地表明了这种关系是“影”(影子)和“响”(响声),“影响”的存在恰如“影子”和“响声”一般难以把握。
文学的“传播”与文学的“影响”则有多方面的不同,首先,从途径与手段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学信息的流动过程,必须借助有形的媒介手段,如翻译、新闻报刊、团体组织、人员交流等等。虽然“影响”的实现也依靠“传播”,但影响的传播不一定需要有声有色的媒介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部作品受到另一个作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并不像“传播”那样有一个明晰可寻的“经过路线”,难以找出一个有形的过程、环节和途径。接受影响可以不通过任何媒介因素,而直接与影响自己的对象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影响”的实现方式和途径的复杂化、暖昧化,形成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瞬间影响和持续影响、有意识的影响和无意识的影响等等不同的情况。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作为,是有意识地向外“放送”的行为,或有意识地由外向内输入的行为。如80年代日本政府鼓励有关机构组织和作家积极向国外传播自己的作品,以便表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日本人只是个“经济动物”的看法是不对的。可以说,80年代日本文学在国外的普遍流行,与日本人的主动向外推广有密切关系。
从文学的接受效果来看,一个国家的作品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之后,尽管也被改造和利用,但仍然基本上、大体地保持着它原来的本体状态。例如中国小说集《剪灯新话》在1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曾广泛流布,并被一些文人作家翻译、改编和摹仿——日本人称为“翻案”,即保留其基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只是把人名、地名和部分细节换成日本的。现代日本学者对这些“翻案”小说的“出典”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是哪一部中国小说的“翻案”。严格地说来,这种“出典”的研究实际上是文学“传播”的研究,而不是文学“影响”的研究,是对被“传播”的作品的状态和结果的研究。因为,仅仅是翻译、改编和摹仿,还只处于对外来文学的“输入”和“利用”的阶段,还不能达到将外来的文学消化、吸收、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的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播”和“影响”的联系与内在区别:“传播”是“影响”的一种基础,“传播研究”可以成为“影响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影响”研究和“传播”研究的立足点就有不同。“影响”研究是一种探讨作家创造的内在奥秘、揭示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作品的成因的一种研究,它本质上是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不是外缘的、外部的研究),是立足于审美判断、特别是创作心理分析、美学构成分析上的研究。与“影响”密切相关的范畴是:“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独创”;它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不是实证,而是审美判断和创作心理分析。它主要研究“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独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不同。它是建立在外在事实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关系研究,像“法国学派”所做的那样,本质上是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上的基本事实,特别是一国文学传播到另一国文学的途径、方式、媒介、效果和反应,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统计学的、实证的方法,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属于文学的外部关系研究的范围。在“传播”研究中,除非特别需要,它一般不涉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判断,而只关注其传播与交流情况。与传播研究相关的重要概念是“渊源”、“媒介”、“输入”、“反馈”等等。
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来说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两种方法的立足点的不同。例如,中国的“龙”和印度的“龙”(音译“那伽”)两种文学形象的比较研究。瞿世休、台静农很早就提出:“龙”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从印度“输入的洋货”,季羡林也肯定了这一观点,说:“这东西(龙)不是本国产的,而是印度输入的。”[3](P106)但是,后来阎云翔在硕士论文《论印度的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的故事的影响》[4](P413)中,经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不能说龙王龙女故事是外来的洋货,也不能简单地说龙王龙女故事是从印度输入的。影响与输入,一词之差,具有本质区别。……龙王龙女故事绝非那伽故事的复制品,更不是舶来货,而是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国创作。”我们可以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结论中,看出他们所包含的两种不同的立场、木同的研究方法。“输入”说的立场和方法是“传播研究”,“影响”说的立场和方法则是“影响研究”。所以,阎云翔深刻体会到:“影响与输入,一词之差,具有本质区别。”这个研究实例有力地说明:“传播——输入”与“影响——接受”在国际文学关系中,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形态。如果对这两种形态不加以区分,就很容易将“影响——接受”的关系与“传播——输入”的关系混同起来,那就会妨碍研究者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区分“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比较文学方法非常重要和必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它能够有助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划分的科学化。现在流行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分法,在理论上存在盲点。通常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不同,在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有事实关系。“影响研究”是有事实关系的研究,“平行研究”则没有事实关系的研究。然而,问题正出于“事实”这个词本身。如上所说,“影响”作为“事实”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事实”。凡是“事实”,都应该是“铁证如山”、实实在在、有案可稽的东西,而那些似是而非、暖昧模糊、难以把握的东西,通常不能被看作是确凿的事实,至多不过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准事实”罢了。但是,文学中的“影响”恰恰是这样一种难以把握的“准事实”。这就使得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遇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惑——“影响研究”不是建立在事实关系基础上的研究吗?那好吧,现在让我收集事实,并且我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我证明了不同的国际文学之间的交流、指出了一个国家的某个作家、某个作品、某种文学思潮流派和理论主张,如何流传到了另一个国家。但是,即便如此,让我用这些材料和事实进一步证实某某作家、某某作品,是否受了另外某个作家作品的影响的时候,就觉得光有这些事实还不够,还不能说明问题。例如,在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说俄罗斯文学传播到了中国,鲁迅曾经赞赏过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还写了与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同名的小说。事实就是如此。这些事实能够说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对果戈理的接受,但能不能证明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受到了果戈理的影响?如果说有影响,那么进一步具体说是如何的影响,多大程度的影响?那就难以回答了。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即由“传播”问题,到了“影响”问题。这是两种相互关联的、但又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就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所谓“影响研究”原来并不能证实“影响”,那么“影响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呢?由于没有分清“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性质的不同,他们对通常所谓的“影响研究”抱着过多、过全面的要求,一方面期望“影响研究”能够理清文学交流的事实,一方面也要求“影响研究”能够深入探得作家创作和作品构成的内部机制。当通常所谓的“影响研究”已经一定程度地达到了理清文学交流事实这一目标的时候,人们便不再满足于此,批评“影响研究”只是画出了影响的“经过路线”,只是“文学的外贸关系”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能切入文学的本体和本质;另一方面,当他们试图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影响”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实证方法的不适用,因为实证方法无法证实“影响”的存在。所以就认为“影响研究”不可行、“实证研究”不可行,并由此全面否定“影响研究”,提出对影响研究进行“颠覆瓦解”。这就是主流的“美国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贯看法,9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也有人进一步回应着这种否定影响研究的主张。
这种偏颇的主张的根本症结,是将“影响”与“传播”混淆起来,而没有将“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区分开来,没有将“传播研究”所使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与“影响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区分开来。以实证研究的效果来要求和衡量影响研究,以实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来全面否定影响研究的价值,以实证研究不能确证“影响”是否存在,来否定“实证”研究方法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以“传播研究”不能揭示作家创作的内在成因为由,而轻视了国际文学关系史(文学传播)研究的价值。
这些都表明,将“传播研究”方法从通常所说的“影响研究”方法中剥离出来,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由“法国学派”所开创的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方法,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如自觉不自觉的欧洲中心论、法国中心论等),但它所奠定的方法论基础,今天并没有过时,特别是在中国,“传播研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非常紧迫和非常需要。
三 传播研究法的运用、意义和价值
“传播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适用对象、运用价值和操作方法。
“传播研究”法的适用对象是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
从纵向的、历时的角度看,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谓“国际文学关系史”是一个大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例如,各国的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是站在自身国家的独特的立场上,研究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传播关系,如法国学者热衷于研究法国文学在欧洲国家文学的传播,或研究其它欧洲国家在法国的传播。而中国的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研究中国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传播关系。在我国,近2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传播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且大都是以“中国文学在国外”或“外国文学在中国”之类的名称形式出现的。1989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编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书中收集的世界各国学者撰写的十七篇文章,分别论述了中国传统小说在朝鲜、日本、蒙古、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马来亚等亚洲各国的传播情况。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一书,描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概况。学林出版社1997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的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和韩国学者闵宽东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分别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英美等英语国家和在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传播情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饶芃子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研究了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情况;还有研究一部作品的对外传播的,如胡文彬的《〈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何香久的《〈金瓶梅〉传播史话——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等。以外国某一作家在中国的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如杨仁敬的《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等等。90年代初,广州花城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中国文学在朝鲜》、《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学在英国》、《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文学在美国》等传播研究的专著多种。这些传播研究著作的特点,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来看,很有自己的特色。它们把研究的重心不是放在被传播者身上,而是放在传播过程,传播媒介、特别是接受者的理解、评论和评价上。对传播媒介,如翻译家及翻译、报刊杂志、文学团体和社会团体等,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对接收者的研究,也不限于作家的接受——这是和影响研究相区别的重要特征——而是对所有身份、所有阶层人士的不同的接受情况都进行分析评述。如杨仁敬的《海明威在中国》,用了不少的篇幅谈了当时的蒋介石等政治家对海明威的接待和欢迎。可见传播研究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研究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而是研究被传播者的传播过程和流转际遇。传播研究所侧重的,不是文本的、作家本体的影响分析,而是关于传播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和资料分析,所凸现的是研究的历史学、文献学的价值。如果说“影响研究”主要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文本分析,那么,“传播研究”主要就是文学的文化史学的研究。
从横向的、共时的角度看,传播研究法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今日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的世界,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也是一种信息,文学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比较文学的“文学传播”研究,就是要注意研究什么样的外来文学、外来作品文本,传播过来后容易被转化为受众普遍接受的信息。历史上的文学传播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自然的、甚至是偶然的过程,例如为什么是《赵氏孤儿》,而不是其他更优秀的元杂剧在法国及欧洲普遍传播?为什么在中国淹没不闻的《游仙窟》,而不是其它更优秀的唐传奇在朝鲜和日本备受重视并对他们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里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运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法,就不能只是被动地陈述过去的事实,而是主动地分析接受传播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条件,指出什么样的外来作品与国内读者的阅读期待相适应,从而成为文学传播的向导,并使精明的出版商和广大的读者受益。例如当代美国小说《廊桥遗梦》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传播甚广,译本发行量惊人,盗版本猖獗,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场场满座,VCD光盘走俏。小说使用的是传统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手法讲述了一个婚外艳遇的故事,手法和故事都平淡无奇。然而这样的小说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却备受读者青睐,而其中的主人公却受到了一贯恪守传统性道德观念的中国读者的宽容与同情。有媒体分析说,《廊桥遗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表明在当代中国许多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中,家庭和性爱的传统道德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倾斜,并预料此类作品,今后仍将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果然,90年代末,当国内几家出版社推出了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一系列以背德的婚外恋为题材、宣言情感至上的小说时,又同样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罕见的畅销书。出版渡边淳一作品的几家出版社不仅为盗版所苦,而且还出现了究竟哪家出版社才拥有真正的中文版版权的纠纷。诸如此类的现象就是比较文学传播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课题。传播研究可以为翻译家和出版商提供传播情况的预测。以当代世界文学为对象的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当代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的研究。它既是国际文学交流的研究,也是国际文学消费周转“大市场”的研究;它既是一种历史的、“事后”的研究,更是一种前瞻性的、预测性的研究。因此这种研究对于推进、引导国际文学的交流,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3](P318)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季先生所说的那种“实用”和“功利”的价值。我们不能同意那些“审美至上主义”的看法,那种看法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性”的研究是至高无上的,而所谓“文学性”就是对文本的审美分析和判断。在我们看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传播研究和以审美的比较分析的各种研究,具有同等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没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高低之分,只有研究质量和水平上的优劣之别。我们把“传播研究”从“影响研究”中剥离出来,其目的也就是在学科理论上明确“传播研究”的独特性和它的价值,以便使它与“影响研究”互有分工,又互相补充,也是为了使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与方法的划分更为科学化,在实践上更具有可操作性。
收稿日期:2002-0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