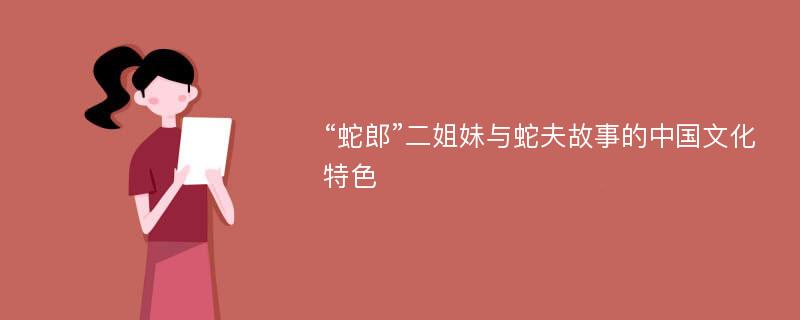
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两姐妹论文,丈夫论文,特色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1)01-0017-05
在人与异类婚恋的故事中,那些作为异类的动植物精灵多扮演女性角色,如蛇女、狐女、螺女、虎妻、天鹅处女等,在她们身上,闪耀出浪漫主义的奇光异采。异类充当男性角色,让普通女子同神奇男人结合构成美妙故事的,则以“青蛙少年”和“蛇郎”这两个类型最为流行。少女嫁给一条蛇,它脱去蛇皮即变形为美男子,富有、神奇而且有情有义,由此生发出饱含人生意趣的纠葛冲突。这个看似荒诞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深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喜爱而传承至今。
中国的蛇郎故事数量极为丰富。1930年钟敬文先生写作《蛇郎故事试探》时,引述当时采录发表的蛇郎故事30篇,丁乃通于70年代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时,所列出的蛇郎异文已增加到60余篇。刘守华于1986年发表《蛇郎故事比较研究》一文,使用本类型的新异文约40篇。随后全国开展民间文学普查,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地采录的蛇郎故事数量激增。仅从近几年间问世的几部故事集成来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及地方资料本所载就有9篇[1](P398,P99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载有2篇[2](P419),《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载有2篇[3](P55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及地方资料本载有23篇[4](P605,P896),《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及地方资料本载有12篇[5](P607,P89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及地方资料本载有53篇[6](P367-P1510),以上合计共101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祖国宝岛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的鲁凯人、卑南人中间,近几年来也采录到好几篇关于《蛇郎君》的优美传说。这几部分材料加起来就有220余篇了。还有许多篇散见于各地编印的资料本中,实际上记录成文的中国蛇郎故事的异文已达数百篇,它们分布在祖国大陆东西南北中及海峡两岸21个省区的25个兄弟民族之中(注:这些故事流传的地区有: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河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台湾等。来自以下民族:汉、满、朝鲜、回、维吾尔、藏、撒拉、羌、东乡、壮、傣、布依、水、侗、黎、高山、仡佬、傈僳、德昂、基诺、怒、彝、苗、瑶、土家等。),其广泛影响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脍炙人口的民间童话精品。
(一)
AT分类法将神奇故事433型《蛇王子》分做433A、433B和433C三个亚型。其中收录中国材料甚少,这三个亚型,主要是从印欧故事中抽取出来的。丁乃通先生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依据他搜罗的中国蛇郎故事异文的普遍形态,另立了一个433D型:蛇郎和两姐妹。这个亚型的故事最为流行。还有不常见的另外两个亚型,我把它做为433E和433F型。中国特有的433D型蛇郎故事的梗概为:(1)一老汉因得到蛇的帮助,答应嫁一女给蛇。蛇上门求亲,为大姐二组所拒绝,只有三妹愿遵父命,远嫁蛇家。(2)三妹与蛇郎成亲后,蛇郎变形为人,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大姐心怀嫉妒,害死了妹妹,冒充三妹与蛇郎同居。(3)三妹灵魂不灭,变成小鸟;小鸟被大姐杀死后,变成竹子或枣树;竹树被砍后变成竹床或木凳,不断揭露真情,表示对蛇郎的亲爱和对大姐的仇恨。(4)大姐烧了竹床或木凳,三妹的灵魂变成火炭、剪刀、金戒指等物,随后复活,夫妻团聚。大姐丑行败露,被蛇郎撵走或羞愧自尽。
本篇故事虽然以蛇郎为男主人公,蛇郎直接出面积极活动的时候并不多,它着重在叙说两姐妹围绕蛇郎所产生的纠葛冲突。试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所载《蛇郎》的后半截:
没过几天,蛇郎和三姑娘就成了亲。小两口和和美美,日子过得要多好有多好。
有一天,大姑娘和二姑娘上小妹妹家来串门。她们见小妹妹家吃得好,穿得好,要啥有啥,那蛇郎模样俊,脾气好,对小妹妹亲亲热热。这阵儿,大姑娘有点儿后悔啦,她寻思,当初我要是嫁给蛇郎,这福不就是自个儿的了吗?
…………
这天早晨,大姑娘和小妹妹一起照镜子,她看镜子里自个儿小脸上就多了几个浅麻子,剩下哪儿都和小妹妹长得差不多,眼珠一转,就起了歹意啦。她对小妹妹说:“这镜子走模样,咱俩换换衣裳和首饰,再到井台上去照照吧!”
大姑娘和小妹妹换了衣服和首饰,来到井台上。小妹妹刚对着井口哈下腰,大姑娘一把把她推到井里去了。
大姑娘赶紧回小妹妹家,装起小妹妹来。那蛇郎也没大理会。
天要黑了,蛇郎去井台挑水,忽然从井里飞出一只小鸟来,落在蛇郎的肩头上。蛇郎见这小鸟挺稀罕人,就把它带回家去,养在笼子里,挂在窗户上。
大姑娘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梳头,那小鸟就唱起来:“麻丫头,不害羞,对着镜子照狗头;麻丫头,不知臊,跟着妹夫睡了觉。”
大姑娘气得把小鸟一把摔在地上,摔死了。蛇郎见笼子里没了小鸟,就问大姑娘,大姑娘说是叫猫给抓死了。蛇郎挺心疼,把小鸟埋在家门前。
不久,埋小鸟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树上开满了花,结满了果。大姑娘走到树下,树上的果子就叭叭地往下掉,个个打在她头上。
大姑娘气得把树给砍倒了,劈巴劈巴当柴禾烧。
大姑娘正蹲在灶前往灶坑里塞小树枝子,忽然从灶口里喷出一团火来,把大姑娘烧得有皮无毛。大姑娘觉得自个儿这样子没法见人,就一头钻进灶坑里,烧死了。[1](P399)
从这里可以看出,《蛇郎》故事的艺术构思特点不在表现蛇郎怎样以他的神奇手段获得人间的美好爱情,如同《青蛙少年》那样,而是“以蛇之变形来象征人的境遇变幻,将蛇郎塑造成一个由贫贱走向富贵的男子,在他命运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将两姐妹——实际上是两种女性的思想性格进行鲜明对比。心地善良淳朴的妹妹不嫌蛇郎贫贱,终获幸福。开始嫌弃蛇郎的大姐后来又以卑劣手段害死妹妹,企图攫取富贵,落得可耻下场。中国蛇郎故事大都具备三妹灵魂不灭,连续变形抗争的情节。妹妹不仅有着善良的品格,还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从而成为一大特点。”[7]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姊妹易嫁》,以写实手法,叙说两姐妹围绕一个由放牛娃出身经科考而获得功名富贵的男人所发生的婚姻纠葛,体裁不同,而艺术构思和文化内涵却完全一致。《蛇郎》的主题,正如一首情歌所表达的:“茄子开花球打球,心愿嫁郎不怕穷,只要两人情意好,做来做去天会红。”故事中被人们称颂的小妹妹同蛇郎的婚事是由父亲许婚、蜜蜂做媒而实现的,这些描述不用说是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缔结婚姻的旧时婚俗的写照,含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老蛇坐地守”的思想局限性;同时它又表现出女性对美好婚姻和婚后奇迹的热烈憧憬;尤其是妹妹不屈不挠捍卫自己人生权利的执着表现,更使人们受到深刻有力的感染,它也就成为本类型故事中最能牵动人心的核心母题。
(二)
在中国蛇郎故事中,还有一个亚型为蛇始祖型,即那位娶人间少女的蛇郎后来成了某一民族或氏族的始祖,它在体裁上属于始祖传说。台湾卑南和鲁凯人讲述的蛇郎故事,就以蛇始祖型为主,如卑南人的《蛇郎君》。
大南村有一位漂亮少女,很多头目的男孩向她求婚她都不接受,因为她爱上了一条蛇。后来蛇向少女的父母提亲,把少女娶回家去。蛇的家在深山的一个湖里,他们生了很多鸟、蛇等动物,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各种禽兽[8](P165)。
口述者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梗概,原故事无疑要丰满很多。
鲁凯村的《蛇郎君》是一位名叫杜玉英的女性用汉语讲述的,属同一类型,而情节和细节却十分生动,引人入胜,梗概如下:
从前有一位头目的女儿叫玛嫩,爱上了一条百步蛇。别人看到的是一条蛇,她见到的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是从外地特地来向她求婚的。他俩决定结婚,男方送来聘礼。婚礼依照平时习俗举行。玛嫩嫁给高山上的蛇家。她看到自己进去的地方是一座宫殿,别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湖。后来,人们在每年举行丰年祭之前,都要请祖先来尝一尝,我们的头目看到蛇尝过小米饭以后慢慢地回去了,便向大家宣布:“我们的祖先已经回来尝过小米饭了,现在可以举行丰年祭了。”[9](P55-60)
《鲁凯族口传文学》一书中还附录了由另外两位老人所讲的蛇郎君故事,内容与之大同小异。
卑南族故事中,少女嫁蛇之后,“他们生了很多鸟、蛇等动物,于是世界上就有了各种禽兽。”鲁凯族故事中,少女嫁给百步蛇之后所生的子孙,成为“我们的祖先”以及人们一年一度举行丰年祭必须祭拜的对象。它们属于始祖型传说的特质十分明显。罗香林先生四十年代作《古代百越分布考》[10],首次提及古代越人的蛇图腾崇拜遗存于有关蛇郎的口头传说中,他认为:
此传说之最足令人玩味的,为以年少貌美之女子,出嫁恶蛇,而恶蛇为能呈现人形之王子。此与远古图腾社会之组织与信仰,有其承袭演进之关系。盖远古之图腾社会,每选择貌美女子贡献与图腾祖,为能使种人繁殖,而其贡献仪节即为以巫术形式缺与图腾祖婚配,图腾之标志虽常为非人形之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然实际所与接触之对象,则常为巫者或属于部范首领之真人。
这里说的奉献少女与图腾祖婚配,是采取由巫者扮演图腾祖的象征形式。是否有更野蛮的形式,即将少女直接奉献给作为图腾崇拜的蛇,以完成这种仪式的呢?看来也是有的。晋人干宝所撰《搜神记》中,有一篇《李寄斩蛇》的著名传说,说闽中某山谷中有大蛇,“土俗常惧”,人们每年要给它奉献十二、三岁的少女,“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结果都被蛇吞吃了。后有一个叫李寄的女孩子奋力斩蛇,才废除这一陋俗。为什么一定要用女孩子来祭蛇,显然正是越族人以蛇为图腾祖,名为给蛇王娶妇,实则为以人作牺牲献祭的更原始习俗的表现。在李寄斩蛇故事流行之前,应当是有肯定这一图腾婚的蛇郎故事生于民间的。在云南地区白族、怒族所属的那些崇蛇的氏族中,关于蛇始祖的传说一直传承至今。《三姑娘和蛇氏族》就讲,三姑娘上山割茅草,嫁给了一条青蛇,她给蛇郎生了两个儿子,“两弟兄都有好几个儿子,有的说怒族话,有的说傈僳话,还有的说别的话,他们就叫蛇氏族。”[11]
古代闽中是闽越人居住的地方,闽越人以蛇为图腾由来已久,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闽”字道:“闽,东南越,蛇种。”早期的蛇郎故事就是蛇图腾崇拜的伴生物。关于台湾的卑南、鲁凯等高山族的来源,有关学者指出:
高山族的来源是多样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以及民族学资料证明,高山族先民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是古越人的一支——闽越的后裔,但也融合了少数来自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等地的居民[12](P5)。
卑南、鲁凯人在口头文学中传承不息的始祖型“蛇郎君”故事,只能从越族崇蛇的古老文化因子中求得合理的解释。
以上几篇《蛇郎君》故事异文,在叙述中都强调,第一,“她看到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是一位从外地来向她求婚的王子,而别人看到的则是一条百步蛇。”第二,别人看见女主人公进去的地方是一个湖,而她本人“看到她就要进去的那幢房子是一座宫殿”;众人都为女孩子为蛇王子所喜欢而感到高兴。第三,结束故事叙述之后,讲述人告诉听众,这位迎娶少女的蛇王子就是他们民族的祖先,“我们把百步蛇看作是早先头目的子孙”。总之,故事中把人们尊崇蛇王的心态表现得十分突出,口头叙说显然是古代以少女奉献蛇图腾祖先这一仪式留下的遗迹。关于接受聘礼、按流行习俗操办婚事等等,则是后来添加的细节。就整体而言,它们保持着十分古朴的风貌,是关于图腾婚和古代越文化的极为难得的口碑资料。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中告诉我们:“台湾蕃族(高山族),每一蕃社必有他们祖先起源的历史传说,鸟蛇化身而为其社祖者甚多。”[13](P20)这一论断在卑南、鲁凯人的口传文学中得到完全证实。
大陆民众广泛传诵的蛇郎和两姐妹故事,在台湾汉族和高山族口头文学中也照样很流行,如在台中县东势镇采录的客语故事《蛇郎君的故事》[14](P71-77),在云林县采录的闽南语故事《蛇郎君》[14](P141-151),不仅整体形态,甚至许多细节和用语也和福建的《蛇郎君》十分接近。台东卑南人所讲的《虎郎君》,除将作为男主人公原型蛇换成老虎之外,其他部分均沿用蛇郎和两姐妹型故事的情节结构。至于鲁凯人所讲之《蛇郎君》,后半截没有姐妹争夫、妹妹变形复仇的叙说,表明这一情节不适合鲁凯人的生活习俗因而被排斥,但开头关于百步蛇以山花向家有三个女儿的老汉提亲的叙述则显然受了汉族故事的影响。正如一位台湾民间文艺学家所指出的:“从历史的地域的角度看,这一型的故事传入鲁凯族,应当是经由居住在台湾的汉族。……鲁凯族显然只取了这一型故事的第一部分,因为它是可以独立的一个单元,而且也有孝心女儿结果有好归宿的正面意义。”[16]基于蛇崇拜的民俗文化背景所构造的同型蛇郎故事在海峡两岸众口相传,从一个特殊层面,昭示出中华文化根基的深厚有力,这是耐人深思的[17]。
(三)
蛇郎故事就其大体结构而言,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其普同性,因而它是一个著名的世界性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在世界广大地区流动的巨大“故事圈”。可是就它的具体形态来考察,又有着很鲜明的民族性。433F始祖型蛇郎传说,特别是433D型蛇郎与两姐妹故事,为中国所特有,其地理分布范围与界限泾渭分明,绝少混杂。造成这种情况的奥秘何在?答案只能从不同民族的古老文化因子中去追索。中国的两种主要类型的蛇郎故事,尽管具体情节很不相同,却都是建立在尊崇蛇,以蛇作为神奇美好男子形象的文化心态基础之上,而这一文化心态根源于古代越人的蛇崇拜,历经千年沧桑未能磨灭。
印度虽然也有一些地方流行蛇崇拜的习俗,但因崇信佛教,讲究“轮回转世”,包括蛇在内的各种畜类,常被看作是人类前生作恶的回报。所以印度流行的蛇王子故事(433A、433B),主人公不是被人施魔法,就是自己作恶遭惩罚而获得蛇的丑陋外形。流行的情节模式是女主人公用自己的美好爱情,帮助这位王子摆脱厄运,恢复人的本相。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的《美人与兽》,也保持了这一构思特点。
我国的东邻日本所流行的蛇婿故事大体上都属于蛇精作祟型(433E)。由蛇精幻化而成的小伙子主动上门寻求意中人,后来不是被女孩子本人就是被她的父母设计害死,结局十分悲惨。许多日本学者都曾揭示这一特点,如柳田国男就说,按一般民间故事叙述逻辑,“嫁给大蛇的孝顺孩子”理应得到好报。可是在日本,“这非常不符合民意,所以人们总是把故事的结尾部分给改成了不是讨伐,就是诛灭,置之死地而后快。”[18](P25)还有一位年轻日本学者将中日蛇郎故事作比较之后说,日本的蛇郎从来就不曾得到中国蛇郎那样的好运气,他们都是死于自己所钟爱的女人之手。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因为日本人把蛇看作邪神,由此便形成了“日本民间故事中的蛇郎故事恐惧成分多,并与击败邪神故事相联系”的民族文化特征[19]。
中国大陆也有蛇精作祟淫人妻女被人识破或予以斩杀的故事,《李寄斩蛇》就是它的早期形态。佛教和道教兴起之后,由高僧高道来斩除蛇妖逐渐构成为一个大的故事类型。与此同时,按传统婚俗模式所编织的“女嫁蛇”故事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由于受“龙蛇一体”观念之影响,越人崇蛇的心理扩展到中华大地上许多兄弟民族中间,赋予蛇族以神奇、高贵品质的口头文学也渐流行起来。在晋代大文学家陶潜所撰《搜神后记》中,就有《女嫁蛇》一篇,宋人录入《太平广记》,改题为《太元士人》,现全文照录如下: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庄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则是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20]
这里的蛇家,已拥有可以与王侯相比拟的豪华宅第,而且完全是按世俗礼仪来操办婚事。小蛇均化身为奴婢各司其职,那蛇精显然也以人世间新郎官的姿态,在婚礼上出现过。只是进洞房以后现出原形才使乳母惊骇而逃。这个情节结构并不完整的故事似乎就是中国蛇郎的雏型。将少女献祭给蛇神以祈福消灾的传说,是基于原始信仰和习俗而构成的,这个女嫁蛇故事,将这一神奇婚姻世俗化、文学化,已开始具有后世民间幻想故事的艺术特征。沿此线索,口头文家进一步将人们的婚姻生活理想和现实的婚姻家庭纠葛同蛇婚传说相融合,精心缀合,巧妙穿插,就构成近现代蛇郎故事的优美形态了。
在口头传承过程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蛇郎与两姐妹故事,具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形式。它由嫁蛇、遇害、变形和团圆四个情节单元,构成首尾完整、富于波澜曲折的故事情节;而且三个人物分别在不同情节单元里得到展现他们思想性格的活动空间,因而各有其神采。情节发展神奇莫测、出人意外,如蛇提亲,女嫁蛇,蛇变形为人,人死后灵魂不灭,幻化成动植物复仇泄恨,最后起死回生等;可是它在细节上又充满日常生活情趣,活泼动人,如对蛇接亲场面的描绘:“牛驮胭骆马驮粉,骆驼驮的十样锦,雀儿衔上红头绳,燕儿抱上花洒瓶,绵羊驮上洗脸盆。”又如对妹妹变形复仇的叙说:“二女子生气把树砍了,砍了做成个板凳,说‘我坐你一世,坐你一世!’她男人往上一坐,又平稳,又光滑;她一坐,上面有刺哩,扎的她龇牙咧嘴。”[21]在用大胆想象构造的艺术间里,倾注丰富情感与智慧,由此获得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它的众多异文均保持着主干情节的一致性,和其他故事类型相比较,形态显得更为稳定;然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流传时,又被故事讲述家灵活地渲染上本地风光,显得多姿多采。如一般地区均以蛇郎为主角,海南黎族却以他们常见的海龟来扮演这一角色。开头部分老汉因想摘取几朵山间野花送给女儿从而遭遇蛇郎的情节,在众多异文中只是一种无名野花,并无特别含义,台湾鲁凯族讲述的《蛇郎君》中,却限定为百合花,因在鲁凯人中,百合花象征女性的贞洁,而且戴百合花是贵族才有的特权,它在鲁凯人习俗中特别受到尊敬和喜爱。让蛇郎用百合花讨亲,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16](P136)结尾部分分辨真假妻子的情节,安徽故事是把夫妻两人的头发打开,看能否交纠不脱,这一构想来自汉族结发成亲的传统习俗。广西壮族故事则让两姐妹来跳火堆,它从用“神判”来分辨善恶的古老习俗中吸取而来。这些因地制宜的局部变异,使故事更能适应人们的多种审美情趣从而增强了它的艺术活力。
蛇郎也是吸引众多民间文艺学家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周作人很早就提出,它在文化史研究上,“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故事之一”[22]。专门研究文章,有钟敬文于30年代发表的《蛇郎故事试探》[23](P192-208),刘守华于80年代发表的《蛇郎故事比较研究》,以及刘魁立于90年代发表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24](P134-147)等。它们或着重于故事中所含民俗文化母题的阐释,或着重于叙事形态的解剖,或着重于不同国家间蛇郎故事的比较研究,均有各自的新发现与独到成就。
收稿日期:200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