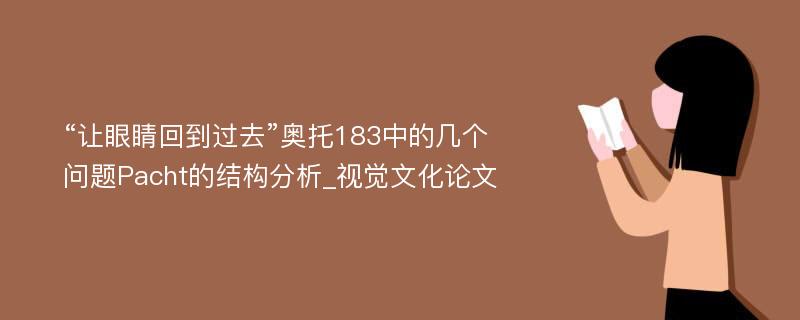
“让眼睛回到过去”——奥托#183;帕赫特“结构分析”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奥托论文,眼睛论文,结构论文,帕赫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也纳艺术史家泽德迈尔[Hans Sedlmayr]自然是一位在战后学界引起较多争议的人物,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事件是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引言和《19世纪艺术史和艺术理论》[Kunstgeschichte und Kunsttheorie im 19.Jahrundert]①充满敌意的评论中,就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的批判。相形之下,他的维也纳大学同事,奥托·帕赫特[Otto Pacht,1902-1988]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也没有那么多的争议。他比泽德迈尔年轻6岁,大学时代跟随德沃夏克、斯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和卡尔·斯瓦巴德[Karl Maria Swoboda]等新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学者从事中世纪艺术研究。早年曾与泽德迈尔合作编辑出版他们的艺术史理论刊物《艺术科学研究》[Kunst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但在1932年泽德迈尔加入奥地利纳粹党之后,两人就不再往来了。 帕赫特是犹太人,1937年之后,就移居英国和美国,曾在“瓦尔堡研究院”(1937-1941)、“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956-1957)和纽约大学美术学院工作过,1963年,回到了维也纳大学,1972年退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主要是在从事中世纪手抄本的研究,话题比较专门,没有像泽德迈尔那样写过诸如《走向严谨的艺术科学》[Toward a Rigorous Study of Art]或《艺术危机》[Art in Crisis:the Lost Center]之类的谈论一般艺术史方法论或理论的文章,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影响并不大。20世纪60年代,他回到维也纳大学担任教职,开设的课程广受欢迎,他的思想和著作也开始在英美国家受到重视,到了90年代,学界就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和李格尔的思想的讨论进一步让他成了关注的对象,他本人也参与了其中②。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S.Wood]③1999年把帕赫特1970/71年间在维也纳大学的演讲文本《艺术史的实践:方法论的反思》④翻译出版,并为该书撰写了一个导言。在这些演讲中,帕赫特澄清了他的早期艺术史研究中的结构分析的思想。 帕赫特的另外一本著作《凡·艾克和尼德兰早期绘画的起源》[Van Eyck and the Founder of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也出自他1972年维也纳大学开设的课程“尼德兰绘画的创建者”⑤的讲稿文本,1994年出了英文版。事实上,凡·艾克兄弟是帕赫特研究得最为深入的艺术家个案。这本书表达了他对60、70年代流行的艺术史图像学研究方法的怀疑,与1953年潘诺夫斯基的哈佛大学诺顿讲座《尼德兰早期绘画》[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的方法论形成鲜明对照。潘诺夫斯基的著作是一种细致入微的图像学探索⑥,试图阐明基督教的观念是如何在尼德兰的视觉写实主义当中获得象征形式的。而帕赫特是着眼于一种不同于图像志和图像学的文字解读的方式来理解作品。他对凡·艾克绘画的解释是围绕着画家的观察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是如何转化成形式的问题而展开的。 比如,在论及《根特祭坛画》绘画空间存在的频繁断裂和视点转换的情况时,他不是从主题叙事或图像志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是着眼于凡·艾克的观看活动本身,比如《羔羊的礼拜》中,顶部风景的视点是水平的,到了中间的祭坛,就变成俯视的角度,底部又恢复成平视,这种自上而下的高低视点的突兀转换,是不应从主题内容的叙述上去理解的,而需要立足于一种对画家的眼睛活动的特性的认识。画中的低视点是固定的,高视点处在持续变动当中,画家的眼睛好像是在追踪整个场景,从前到后,从近到远,眼睛凭依着那些次第排列的物件摸索着通向深处的道路,或者是从远处的平面向近处的日趋强化的三度空间的转换来构架空间感⑦。所以,凡·艾克画作的形式感是来自于一种眼睛从不离开对象的原则,即眼睛始终附着在对象的表面,它的持续的观察和追踪对象的活动构造了空间的形式,形成一种让眼睛的观察活动静态化的效果。帕赫特的这种基于艺术家的眼睛的活动的形式问题的探索,显得比较单纯,浸润了一种对艺术家的天才的信仰。相对于传统艺术史的那种繁琐的历史语境的重构,他的著作旨在引导读者透过艺术家的眼睛,一种对艺术家的“观看习惯”或“设计原则”的理解,进入到历史的场景当中。这是一种致力于还原过去时期的观看方式、回归艺术本身的理解尼德兰艺术的方式,因此,“帕赫特的分析视觉资料的能力,以及他的把原因和效果联系起来的能力,成为了一种艺术史话语的范式。艺术史必须坚持在自己的基点上发展”,这种写作类型也被称为是“非编年的”[anachronistic]⑧。 帕赫特显然更多地关注艺术表现问题,他的视觉结构和观看习惯的分析是以个体艺术家的创作为出发点的,并没有刻意突出其作为种族精神的传承的意义,他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于泽德迈尔的那种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态度。二战之后,他的回归艺术本身的主张主要针对当时以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和温德为代表的瓦尔堡艺术史学派的。他觉得,60年代贡布里希对李格尔的批判,是基于一种波普尔式的对所有的演变论、历史主义、集体主义和决定论的攻击,是一种对泽德迈尔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危险的意识,“艺术意志”就此也成了驱动艺术前进的车轮的机器。但实际上,艺术意志的问题要远为复杂,在他看来,贡布里希的种种说法是有点离题的。⑨ 作为新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帕赫特的研究和写作聚焦于那些与现实政治、宗教和文化问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中世纪手抄本、早期北方文艺复兴绘画等领域,他的政治履历无懈可击,所以,一些学者倾向于突出他在新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中的地位,而尽量回避或弱化泽德迈尔的角色。伍德在为帕赫特《艺术史的实践》撰写的引言中,直接把他与贡布里希和潘诺夫斯基相提并论⑩,代表了战后欧美艺术史的一种重要学术方向。在他看来,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虽然建构起了艺术史的两种规范模式,但几乎都只适用于再现绘画,并没有给二十世纪的艺术留下概念空间,中世纪艺术也基本处在这两种阐释模式之外,情况正像帕赫特所说的,“十世纪的细密画中,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的背景不应被读解为文艺复兴艺术的那个深度空间,那么,城市就不会像潘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飘浮在空中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依存于奇迹,所以,它必须创造一个自己的图画世界,其视觉逻辑是独立于我们所称的自然法则的。”(11)同样,他的这种从观看结构或逻辑来理解作品的主张也打开了现代艺术的大门。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1983年出版的《描述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Seventeenth Century]的引言中也谈到了李格尔和帕赫特,并以他们的思想来反对瓦萨里以来西方艺术史学中的那种对于叙述性绘画的偏好。(12) 一 “设计原则”和“结构分析” 与泽德迈尔一样,帕赫特主张艺术史需要回归到艺术本身,研究者要在观看方式和视觉习惯上回到过去,达到与过去时代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同步。相对于图像学和图像志的文献性关照,帕赫特觉得,对于艺术史家来讲,调整眼睛,理解作品本身的意图,要比把握它们的视觉图像的结构更加重要,也更为困难一些。 把艺术史的基本问题归结到观看的层面,是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形式的“艺术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不过,帕赫特所说的观看和视觉习惯,更多指向个体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性的直觉,而不是沃尔夫林风格史中的那种群体性的“视觉模式”。对于艺术创作的表现性直觉的定义,帕赫特在《艺术史的实践:方法论的反思》中是提出了一个“设计原则”[Gestaltungsprinzip or the design principle]的概念,即一种控制绘画和建筑的视觉结构的隐在逻辑。它不仅是一种可视形式,还涉及更基础的层面,一种由作品的组织关系构成的系统,一个以图像为基础的对比、框架和平面构成的视觉整体(13)。这个“设计原则”是进入作品的历史意义的钥匙,要比传统的图像学和风格方法都更加切实和有效。 帕赫特的“设计原则”的概念与泽德迈尔的基于整体心理学[holistic psychology]、格式塔心理学的“结构分析”或“格式塔观看”[Gestaltetes Sehen,Gestalt vision,configured seeing]的思想一致,都涉及对观看本身的认识。他们否定所谓的纯洁无瑕的视网膜形象,而认定观看总是伴随先前的经验,也会被固有的知识和记忆所控制,就像泽德迈尔所说的,眼睛在辨识出对象是什么之前,它的原初视像就已经是一个“马奇奥”[Macchia]了,是一种包含了直觉的结构。 因此,理解艺术品的“设计原则”就是理解它的表现性的直觉结构,正是这个结构让艺术之物变成了艺术品。绘画、建筑和雕塑的物理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艺术品,而只是一些前美学的基质。艺术品必须在观者的身体的和思想的眼睛里经历一个再生产过程,即观者的眼睛经由作品引导而进入一种不同于日常的直觉感知当中。当然,从观者角度出发,了解作品隐含的一种陌生的观看方式或视觉习惯,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单纯依靠理性思考就能实现的,而需要让眼睛有所适应,得到某种训练。(14)在一系列浸润过程中,形成与作品匹配的直觉把握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性的观察训练和个人直觉能力的形成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达到对作品的视觉习惯的理解之后,直觉的把握与学术观察间的对立才能瞬间地具体化。(15)帕赫特进而认为,作为艺术史的基础训练,学习观看就像掌握任何一门技艺一样,需要依靠观者自身的努力,在作品的引导下,不断地塑造自己的观看习惯,让眼睛进入状态,最终达到理解。(16)观看过程就是视觉地把握作品的特性或艺术家的特性,这基本是一个不断区分和辨析的过程。 在一种视觉的意向性和表现性上理解与认知艺术品的观念,在帕赫特的中世纪和北方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凡·艾克与尼德兰早期绘画的起源》中,他对凡·艾克兄弟绘画特点的论述,不是像通常那样着眼于两位画家推进或完善油画技术和材料的发展,而是聚焦于两人在绘画表现观念上的突破,即他们对光和影所致的色彩共生现象的新认识。事实上,帕赫特是认为,凡·艾克兄弟画作的真正主题是光的活动,颜色因光而变得灿烂。光吸收到各种颜色当中,服务于再现的目的。他们因此不再需要像中世纪时代的画家那样,直接把黄金用到绘画中,而可以借助细致入微的光色关系的经营来表达黄金的色泽。他们还把真实世界的光当作了绘画的一部分,光投射到画作表面,散发光芒,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层次。这种珠宝般的光感常被说成是为了匹敌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两位画家热衷于颜色的透明效果本身,是为了创造一种透过绘画表面而浮现的神奇光芒印象,这就是凡·艾克兄弟绘画的“设计原则”或“视觉习惯”的成果,也是他们对艺术史的真正贡献所在。 因此,帕赫特主张的是一种对作品的个体化“设计原则”而非时代风格特征的发现。在他看来,传统风格史的问题在于,观者认识的不是拉斐尔本人,而是拉斐尔的样式。在面对一件特定作品时,总是尝试在它的风格的前辈那里推导它,这实际上是一种迂回方式:即通过说明某人来自于哪里,去往那里,来回答他是谁的问题。(17)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首次遇见一件作品时,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它的特性,而是它与我们已经了解的一切的相似性。人们第一次看到的是教师和学生都知道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可以定义它的个性的东西。”(18)但实际上,任何作品都是包含了自身的表现的逻辑,这个逻辑完全不是一种共性的感知方式或理论模式可以解释得清楚的。比如,布鲁涅列斯奇的建筑,尽管包含了复杂的数学关系,但数学只是构成他所设计的建筑物的自身逻辑的一个要素,建筑本身并非是按照数学法则设计的,数学和几何学的公式是不能说明他的设计的艺术意图的。帕赫特认为,理解这一点对于真正的“艺术科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身为中世纪的学者,面对大量的无名作品,帕赫特也势必表现出对作品的共性视觉形式结构的关注,这种共性结构,以他的理解主要是指作品中隐含的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比如,他在罗马式手抄本插图中,发现了一种以空间穿插和交织为意向的平面化的形式设计原则。为让读者能够领会和理解这种共性的设计意图,他在描述的过程中,避免使用诸如山、云之类的可辨识对象的名称,引导观者从再现景象的关照中走出来,而进入到一个抽象的形式结构世界。他说,之所以人们会感到中世纪艺术作品难以理解,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图画想象所服从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不同于我们所尊崇的视觉和思想的习惯。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中世纪的语言,这样才能让遥远年代的作品向我们说话。(19) 他是用“入眼”[getting one's eye in]来形容让陌生作品说话的过程的,简单地说,就是比较和辨别,比如说,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幅主题相同的出自托斯坎尼和威尼斯地区画家之手的作品,来辨别“素描的”[disegno]和“色彩的”视觉表达的差别;通过分析达·芬奇和提埃波罗的画作,来认识佛罗伦萨画派的着眼于个体人物戏剧性动作的经营的画面与威尼斯画家的热衷于群体事件描绘的差别。(20)但是,帕赫特所主张的比较并非是沃尔夫林的“无名美术史”,他的“入眼”的最终目标还是在于对个体艺术家的直觉表现的结构的认识,至于时代的或地区的视觉表达的共性的“设计原则”只能在这种对个体艺术家的认识当中才可能存在。他显然是维护了艺术家的天才的概念的,与斯洛塞尔的思想保持了一致。总体上,帕赫特在英语国家是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回应的,尤其是近些年,诸如克里斯托弗·伍德、亚历山大·奈格尔这样的学者,尝试一种基于现当代艺术概念的对传统艺术的反思和重述,希望跨学科的艺术史能够回归艺术的本位,而这也可视为对美国移民艺术史传统的过分强调知性内涵的反拨。与帕赫特一样,这两位美国当代的艺术史学者,在艺术史写作中是保持了一种美学标准的,并且也不刻意地回避批评视角,他们既不认同那种把艺术史当作同质的和价值中立的艺术品目录的做法,也反对把作品仅仅当作历史文献。他们试图在艺术史的世界里拯救艺术的价值,坚信艺术的成就是与图像的再现、诱导的或辨识的目标没有关系的。 二 “形式机会” “形式机会”[formal opportunities]也是帕赫特艺术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初,他是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所处环境的建筑构架,诸如祭坛[Altar]、布道坛[pulpit]、壁龛[tabernacle]、诵经台[lectern]、洗礼池[font]、陵墓和风琴架等,这些建筑的设置就是“形式机会”,它们相对独立;另外,像一些建筑构件,比如门把手、烛台、入口和钟楼等,也给一些纪念性的绘画和雕塑提供了场所或形式机会。所有这些要素都有明确的社会和实用的功能,附属于它们的绘画和雕塑的形式也无法从这些功能中分离出来。他谈到的一个“形式机会”的例子是唐纳泰罗的雕塑《朱迪思》[Judith],一直以来,大家对这件作品的认识总是局限在纪念的永恒性和瞬间的叙事的矛盾上,但实际上,这件作品的视觉设计是考虑到它摆放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Pizza della Signoris]的情况的,观者会从多个角度观看它。从正面看,人物动态是有些怪异的,没有一般叙事或纪念雕塑的那种稳定和清晰的形式感,但是,如果是从多个角度观赏它,就会形成对这件作品的视觉表达的整体性的理解,就不会轻易地得出结论说,这件作品代表了唐纳泰罗个人艺术风格的转换。(21) 另一个例子是“布列斯劳地区佛莱堡的石棺雕像”[Freiburg im Breisgau],主题虽然是“基督复活”,但雕像布局并非按叙事或讲故事方式展开,而是与当地纪念基督受难“涤足节”[Maundy Thursday]的祝圣仪式相关。所以,在读解这个中世纪石棺图像时,需要祛除主题内容的知识,然后才可能在石棺的那些相互分离的形象之间找到一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引入复活节仪式的知识。帕赫特说,这种演绎的方式仍旧是历史的,却是着眼于理解视觉表达的逻辑,在这件作品中,就是去理解结合特定仪式秩序的非叙事的和超时间的视觉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复活节的视觉概念,一场复活节盛宴的纪念碑,而不是展现“基督复活”主题的图像,不是历史瞬间的视觉记录。在这场戏剧中扮演角色的人物,与死去的基督一样被永恒化了。所以,在这个石棺雕像中,时间和非时间性、象征和事实记录相互穿透,让人们难以理解它。(22)帕赫特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图像志的知识不应孤立使用,只有在这些知识可以对风格感知有所贡献时才会有意义。(23)简单地说,在了解隐含在整体中的组织原则之前,图像再现意义是不会变得清楚的。仅从图像志的角度来解释作品并不充分。发现正确读解作品的人,就是能见其所欲的人,也就可以把它安置在恰当时间节点了。(24)帕赫特因此而坚信,可以通过纯粹的视觉证据,确定作品的年代和出处。 三 描述 用文字来描述对艺术品的视觉理解和感悟,是艺术史家的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帕赫特认为,那种以为图像能够自己说明自己的论调基本上是推卸责任,或者是无力描述视觉经验。(25)艺术史家一方面要确认视觉创造和表达的自足性、结构和超越文字表达的特质,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对艺术的“设计原则”的理解通过文字而提升到意识层面,文字要能阐明图像,而不是倒过来,用图像来说明文字。 帕赫特所说的用文字说明图像,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外在的,比如图像志和图像学的阐释,认定任何图像都是以文字为依据的,是服务于经文的内容的,这种从图像主题内容出发的描述,比较容易转换成客观的文字表达,还有就是风格或形式的外部特征,视觉描述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外在的层面,就意味着对艺术本身的抹杀。帕赫特断言,持这种想法的人,是无法抓住视觉艺术的表现结构的。(26)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第二个层面的描述,用文字传达艺术的非叙述性特质,也就是作品的“设计原则”。艺术史家只有让自己的眼睛真正进入作品中,达到一种“具体的观看”[configured seeing],理解作品的视觉表现的统一性,陌生的作品才会显示秩序,这时,用文字传达印象的任务就变得容易了,清晰的语言表述也变得可能了。这基本是一个发现绘画创造的语言对等物的“词画”[word painting]的过程,而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崇高的新柏拉图主义或经院哲学的理念。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新的视觉经验都能找到现成的词汇表达,所以,艺术史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个体的语言能力。与帕赫特持相同观点的平德也说,形式的历史,总是思想和精神态度的历史,但不只是这种精神态度和思想的图示:它是一个在思想和精神态度一般历史中的自足表达的领域。(27)因此,艺术史的真正目标不是确认作品的物理存在,而是通过观看,从物质存在中抽取某种东西,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过程与艺术创作一样,是一种创造的活动。 为说明自己的这种基于艺术内部的“设计原则”的艺术史的效用,帕赫特在《艺术史的实践》中列举了两个当时学界引起巨大争议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提香的著名画作《世俗的爱与神圣的爱》。在1910年之前,学界是认同这幅画作的标题的,但在这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其中包括阿道夫·文图里[Adolfo Venturi]、克劳德·菲利普斯[Claude Phillips]等人,而陶辛[Moritz Thausing]也说,画中看不出哪个人物代表世俗的爱,哪个是神圣的爱。潘诺夫斯基认定这幅画作是属于一种标徽式的图像。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提香时代,人文主义哲学中所流行的“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他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费利奇诺[Marsilio Ficino]那里发现了所谓的“孪生维纳斯”[geminae Veneres]的概念,即思想的永恒之美和眼睛的瞬间之美的对比。他提到的另一个证据是里帕[Cesare Ripa]编写的文艺复兴晚期的《标徽之书》,在里面也找到了一对人格化的女性,与提香画作中两个人物惊人地相似。裸体人物右手的法器是火焰,代表“神的爱”;另一位女性的奢华服饰代表世俗性,画作标示出两种不同的道德。里帕[Ripa]的书中,称她们为“永恒之福”[Felicita eterna]和“瞬间之娱”[Felicita breve],并且,稍早一些的画家曼坦纳也创作过类似的作品。 但是,这件作品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来自于一位法国学者路易·哈提卡[Louis Hourticq],他的观点与潘诺夫斯基不同。他认为那个着衣女性应该是当时威尼斯的一本流行小说(28)中的人物,名字叫鲍利亚[Polia]。在小说中,这个人物逐渐从原先忠于纯真的狄安娜转向了美神维纳斯。他的这个观点的关键证据是石棺的浮雕,潘诺夫斯基的解释里面并没有涉及这一点。石棺右侧画面表现出了与小说情节的一致性。阿多尼斯[Adonis]因为与维纳斯的暧昧之情而被战神玛尔斯鞭打,维纳斯急切地想要帮助她的爱人。画中的石棺所在正是阿多尼斯的陵墓,维纳斯每年都会到访凭吊。据说在营救阿多尼斯的时候,维纳斯在石楠树上擦伤了腿,血流了出来,被年轻的丘比特收集到了一个贝壳(容器)里,放在墓中。每年春天,维纳斯到访,丘比特都会挖出这个装有女神鲜血的贝壳,这时,玫瑰的颜色就会由白变成红色。石棺浮雕上的那个没有骑手的马是冷漠和贞节符号,在小说的木刻插图中也有所表现。这位学者的解释显然可以说明这个场景特点。如此这般,画作的主题就不是世俗的爱与天上的爱了,而变成了维纳斯的祭奠。(29)这种对主题内容认识的差别,必定影响到观者对这件作品原初视觉表达结构的恰当理解。如果潘诺夫斯基的解读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也会导致观者对作品的真实意图的误读。 ①这篇评论发表在Art Bulletin 46,no.3(September 1964),pp.418-420. ②Otto Pacht,"Art Historians and Art Critics-vi:Alois Riegl",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05,May 1963,pp.188-193. ③他在2003年编辑出版了《维也纳艺术史读本:1930年代的政治和艺术史方法》[The Vienna School Reader:Politics and Art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1930s]中收录了帕赫特的两篇文章,《图像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Image Theory,1930/31]和《15世纪北方绘画中的设计原则》[Design Principles of Fifteenth-Century Northern Painting,1933]。 ④Otto Pacht,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Reflections on Method,Harvey Miller Publishers,translated by David Britt,1986. ⑤最初文本是1965-1966年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尼德兰绘画为主题的两个学期的课程。 ⑥阿尔珀斯在《描述的艺术》中,谈到潘诺夫斯基在关注尼德兰绘画的图像叙事的同时,也是注意到了其中包含的叙事与描述的矛盾的,即那种对于世界表面的描述和关照是以牺牲叙事的再现活动为代价的。关于凡·艾克,潘诺夫斯基说,他的眼睛的活动既像显微镜,又像望远镜,观者必须协调远观和近看的关系。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Seventeen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xxi. ⑦Otto Pacht,Van Eyck and the Founders of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trans by David Britt,Harvey Miller Publishers,1994,p.136. ⑧Mark Evans,Review for Van Eyck and the founders of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38,May 1996,pp.332-333. ⑨Jas Eisner,From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Big Picture:Some Reflections on Riegl's Concept of Kunstwollen,Critical Inquiry,Vol.32,No.4(Summer 2006),pp.741-766. ⑩Otto Pacht,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Reflection on Method,Harvey Miller Publishers,translated by David Britt 1986,p.9. (11)Ibid.,p.45. (12)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Seventeenth Centu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xx. (13)Christopher S.Wood,"Introduction",from Otto Pacht's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Reflection on Method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translated by David Britt,1986,p.11. (14)Otto Pacht's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Reflection on Method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translated by David Britt 1986,p.86. (15)Ibid.,p.40. (16)Ibid.,p.23. (17)Ibid.,p.23. (18)Ibid.,p.65. (19)Ibid.,p.46. (20)Ibid.,p.91. (21)Ibid.,pp.46-52. (22)Ibid.,p.43. (23)Ibid.,p.43. (24)Ibid.,p.61. (25)Ibid.,p.97. (26)Ibid.,p.84. (27)Ibid.,p.85. (28)小说名称叫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1499)。 (29)Ibid.,pp.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