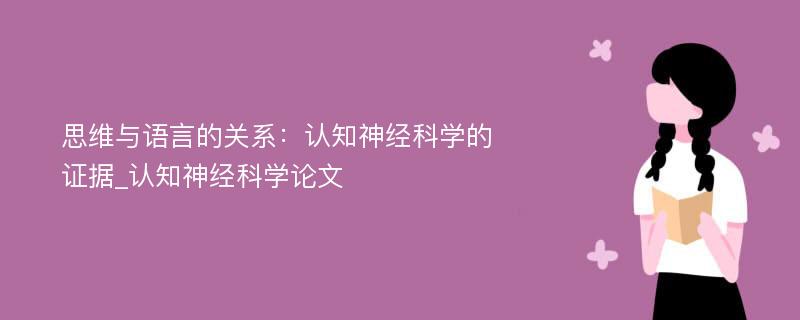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证据论文,思维论文,神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始终是人类心智研究中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课题,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到爱因斯坦的名言“那些思想不是以语言的形式来临的,我极少用语言来思考,一旦思想来临,我事后也许会想到要用语言去表达它”都涉及到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而事实上,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对生命与宇宙的终极真理的思索上,它还更普遍地表现在人们日常的思维活动中。比如当你计算一道简单的算术题“12乘6等于几?”时,你会用家乡的方言来计算,还是用普通话来计算?或者,如果你有很好的英文水平,你会用英文来计算吗?一般而言,人们会用他们在中小学课堂上所使用的那种言语来进行算术运算,即使一个人有很好的外文水平,他们也不大可能用外文进行计算,这说明正常成人的数学思维对于其言语习惯的依赖;再比如请你做下面这个推理:“张三比李四高,李四比王五高,张三比王五高吗?”答案很简单,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推理的结果,而在于你在完成推理任务时是否依赖了空间的表征方式,尽管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的推理过程多少都借助了空间表征,但也有学者认为推理过程其实只是依靠抽象的语言形式的逻辑规则来完成的,无须诉诸空间表征。上面的例子说明,即使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常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我们的思维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研究者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比如探讨经验如何塑造特定的语言文字表达和思维方式),但这个问题始终是心理学领域最重要而又最错综复杂的难题之一,它涉及人类思维和心智的本质。借助于脑成像技术,认知神经科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话题。其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某种特定的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语言的”,那么,在进行这种思维活动时,大脑中负责语言信息处理的区域就会参与;反之,如果某种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空间的”,则大脑中负责空间信息处理的区域就会参与其中。结合直观的脑功能图谱证据与其他的跨领域证据(如来自行为实验和脑损伤研究的证据),人们就能推测语言与空间信息加工过程究竟是怎样编织在我们瞬息万变的思维与意识之中的。下面,本文以3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过程——运算、推理和顿悟为例,说明新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能为人们理解这个古老的难题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1 运算与语言
有关运算的研究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一个“运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即:人们的运算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受制约于语言,又在何种程度上独立于语言。
例如,第一项探讨运算的脑机制的研究是1908年由Lewandowsky和Stadelmann做出的,他们在研究中强调,应该将运算能力与语言能力分离开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只有借助于研究那些表现出运算障碍但不伴随失语症的病人,才能正确地推知负责运算的大脑中枢。Lewandowsky和Stadelmann研究了一例不能进行加减和十进制运算的病人,该病人脑损伤的部位在左侧的枕叶,据此,他们推测人脑内负责运算的中枢可能在左侧的枕叶。1919年,Henschen发表了一项系统探讨运算障碍的经典报告,在总结了文献中的305例运算障碍的病人以及他自己遇到的67例病人之后,Henschen得出结论说,人脑中存在相互独立的文字处理中枢与数字处理中枢,因此,运算能力应与语言能力及其障碍分开来加以研究。继Henschen之后,Berger初级运算障碍与二级运算障碍之间加以区分。所谓二级运算障碍是指由其他的脑功能障碍(比如注意障碍、记忆障碍以及语言障碍)所引发的运算障碍,而初级运算障碍则是原发性的运算障碍,并不是由其他的脑功能障碍所导致的。Berger研究了18个运算障碍的病人,发现只有3例是属于他所谓的初级运算障碍。
与较早的理论不同,后来出现的运算理论更注重运算的内部知识表征,比如McCloskey等人提出的运算的抽象—模块模型(abstract-modular model)是目前较为重要的运算的理论之一[1],该理论假设了一个抽象的内在数字表征系统的存在,认为无论是阿拉伯数字(如1,2,3)和言语数字(如一,二,三)的输入或者输出,都以抽象的内在数字表征系统为中介。抽象—模块模型关于抽象的内在数字表征系统的假设与那些对于尚未获得言语能力的婴儿的运算研究是一致的。比如,Starkey等人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表明[2]:如果在实验中给婴儿看一边含有两个常见物体而另一边含有三个物体的一个屏幕(在实验中,左右数目以及物体排列方式被充分随机),并在呈现屏幕的同时(从屏幕背后)发出两声或者三声的节拍,则婴儿更倾向于注视其物体数目与节拍声的数目相同的那一侧。这一观察说明,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婴儿,也具有一种“数字感”。而Wynn等人在Nature杂志上的研究报告也发现[3],在5个月的婴儿事先知道小舞台上的玩偶的数量的情况下,用幕布遮住舞台,然后在婴儿能看见的情况下往被遮住的舞台上添加玩偶,或者从舞台上拿出玩偶,最后,掀开幕布。结果发现,当舞台上玩偶的数量与加或者减所得的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这种不一致其实是因为主试从一个儿童看不见的角度偷偷增减了玩偶),儿童注视舞台的时间明显增长,这说明尚未获得语言的婴儿也具有进行简单加减运算的能力。
但抽象—模块模型仍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反驳性的证据包括:(1)既然存在一个抽象的内在数字表征系统,那么,为什么人们的乘法作业会受到物体命名作业的严重干扰?(2)既然所有的数字加工都必须以抽象的内在数字表征系统为中介,那么,为什么有的脑损伤病人会在计算能力障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有读写阿拉伯数字的能力?(3)同理,为什么有的病人会出现一种运算能力(比如减法)有障碍,而其他运算能力(比如加法和乘法)没有障碍的现象?(4)为什么会出现有的病人能够进行简单的口头加减运算,但却不会做笔算的现象?(5)尽管有证据显示即使是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儿童也能具有某种运算能力,但为什么儿童的运算能力会随语言能力的发展而大大增强?
比如,Dehaene等人采用熟练掌握英、俄双语的被试为实验对象[4],质疑了抽象—模块模型,他们首先用某种语言(比如俄语)让被试进行精确计算(呈现“4+5”,令被试判断“9”和“7”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和粗略估算(呈现“4+5”,令被试判断“8”和“3”哪一个更接近于正确答案)的训练,然后,分别用两种语言测试运算训练的迁移情况,结果发现,对于粗略估算而言,无论训练时所用的语言与测试时所用的语言是否相同,正迁移的成绩都一样好,而对于精确计算而言,如果训练时所用的语言与测试时所用的语言相同,则正迁移的成绩较高,反之,则迁移的成绩较低。这说明有的计算过程(如精确计算)较大程度地依赖于特殊的语言形式,而有的计算过程(如粗略估算)则依赖程度较小,这是McCloskey等人的抽象—模块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根据上述考虑以及其它的研究结果,Dehaene和Cohen提出了所谓计算的三重编码模型(triple-code model)[5],他们假设数字有3种类型的心理编码,即听觉编码(由通用的语言模块生成和操作),视觉编码(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进行空间性的内部表征)和模拟幅度编码(analogue magnitude code,指数量被表征为一种类似于在坐标轴上分布的数据点)。三重编码模型假设每一个运算过程都是与特定的符号输入或者输出形式捆绑在一起的,并不存在McCloskey等人所说的独立于言语或者阿拉伯数字符号之外的抽象内在数字表征系统。
在其脑成像研究中,Dehaene等人令被试分别进行精确计算和粗略估算[4],结果发现:相对于精确计算而言,粗略估算激活的脑区包括双侧顶内沟及中央后沟和顶下小叶、右侧楔前叶(precuneus)、双侧中央前回、左背侧前额叶、双侧额上回、左侧小脑以及双侧丘脑等;而相对于粗略估算而言,精确计算激活的脑区包括左侧额下回、左侧扣带前回、左侧楔前叶、右侧顶枕裂、双侧角回以及右侧颞中回等。在粗略估算中观察到的顶叶(特别是顶内沟)和楔前叶的活动为粗略估算借助于一个视觉—空间表征过程来实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为这个区域曾经在眼动、心理旋转以及空间注意导向等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过程中被广泛地观察到。而在精确计算中观察到的左侧额下回的活动,则为精确计算借助于一个语言信息加工过程来实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因为左侧额下回通常参与语义选择一类的信息加工过程。Dehaene等人的上述结果从一个新的角度证明了运算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可能是由运算的任务来决定的,粗略估算之所以更多地伴随脑内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的活动,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头脑中借助了类似于解析几何的坐标轴一类的空间信息表征方式来估计和比较数值的大小,而精确计算之所以更多地伴随语言区域的活动可能与精确计算需要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而左侧额下回的言语区域参与工作记忆中的言语信息的静态保持和动态比较有关。
2 演绎推理与语言
有关演绎推理的理论或模型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人们在进行推理时的内在心理表征问题。心理逻辑(mental logic)理论认为,人们在推理过程中使用抽象的、没有内容限制的推理规则来进行有效的推理,就像在逻辑学中根据大、小前提推演出结论一样。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能够使用一套逻辑语言(如“所有”“一些”等)来进行推理。因此,演绎推理是一个由推理规则约束的句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或心理表征保持着命题表达语言的结构特征。心理逻辑理论假设推理是由语言信息加工过程实现的。
而与此不同,心理模型理论(mental model)则认为:人们通过建构心理模型以表征外部世界那些可能的事物状态,并通过描述和证实这些模型来推导有效的结论。该理论假设:在推理过程中人们保持和操作的乃是事物的结构特征(即各要素在问题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而并非语言(即陈述命题的语言)的结构特征,因而,尽管心理模型理论在其理论阐述上并不绝对地断言演绎推理是由一个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来实现,但是该理论无疑更加倾向于这样的解释。行为研究在关于演绎推理的表征方式问题上仍未获得统一的结论。比如,De Soto等人在一项早期研究中发现[6],让人们判断“A比B矮,B又比C矮”要比判断“A比B高,B又比C高”更加困难。对此,主张推理是借助于空间关系表征来实现的研究者的解释是:因为“高于”的关系比“矮于”的关系更易于被视觉—空间地表征,因此,“高于”要比“矮于”更能促进线性三段论的推理。但是,另一派意见却认为,无论是“高于”关系的推理,还是“矮于”关系的推理,都最终将通过一个言语过程来实现,所不同的是“高于”是一个未被明确地标记的词(lexically unmarked term),“矮于”却是一个其意义被明确地标记的词(lexically marked term),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谈论“矮于”的时候,一定是相对于某一个标准而言的,因而加工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自大脑研究的证据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以往的研究表明:大脑右侧半球以及顶叶可能是支持空间信息加工的关键性区域,因此主张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的Johnson-Laird等人1994年曾经预测:右脑以及顶叶将参与推理[7]。1997年,Goel等人发表了一项有关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脑成像(PET)实验[8],在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下列演绎或归纳推理的结论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可能。实验包含了4种不同的推理任务:
条件1
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条件2
如果苏格拉底是一只猫,那么,他就有9条命//苏格拉底是一只猫//所以,苏格拉底有9条命
条件3
苏格拉底是一只猫//苏格拉底有32颗牙齿//所以,所有的猫都有32颗牙齿
条件4
苏格拉底是一只猫//苏格拉底有一颗坏牙//所以,所有的猫都有一颗坏牙
研究结果表明:演绎推理(条件1和2)激活左腹侧额叶(BA[布罗德曼]47)和左枕上回(BA19),而归纳推理(条件3和4)激活了左侧的额内侧回,扣带回和额上回(BA8,9,24,32)。相对于进行归纳推理而言,人们进行演绎推理需要额上回的内侧面(BA8,9)的参与。Goel等人认为,这个实验结果与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预期不符,因为推理不但没有激活以往在空间工作记忆中观察到的右腹侧额叶(BA47),右侧顶叶(BA40)和右侧枕叶(BA19),而且也没有激活在物体的空间位置表征中至关重要的后部的顶叶。但是,推理活动中没有观察到参与空间信息加工的区域的活动,也可能是由于这项所用的实验任务本身不包含明显的空间关系。为了检验包含明显的空间关系的推理活动是否会激活空间信息加工的脑区,Goel等人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比较了下列推理[9]:
条件1:范畴三段论推理
有些军官是将军//所有的列兵都不是将军//有些军官不是列兵
条件2:含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
军官站在将军旁边//列兵站在将军后面//列兵站在军官后面
条件3:不含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
军官比将军重//将军比列兵重//列兵比军官轻
除了上述推理任务之外,在实验中还有一种基线条件作为参照,在基线任务中给被试看的句子是一样的,但是信息加工的任务却是要求他们理解句子的意思并判断推理过程涉及到几个人。研究结果表明:(1)与基线任务相比,三种推理任务都激活了大致相似的脑区,包括左腹侧额叶(BA45,47),左侧额中回(BA46),左侧颞中回(BA21,22),左侧颞下回和颞上回(BA22,BA37),以及左侧扣带回(BA32,24)等。(2)含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与不含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所激活的脑区相似,二者没有显著的差别。(3)范畴三段论推理比含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双侧颞中回(BA21),左侧额下回(BA45)和左侧额上回(BA8);而含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则比范畴三段论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右侧楔前叶(BA31)。(4)与(3)相类似,范畴三段论推理比不含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左侧颞中回(BA21),左侧额下回(BA45),左侧额上回(BA8,9)以及前部的额中回(BA10);而不含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则比范畴三段论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左侧顶枕裂(BA7)和楔前叶。(5)研究者还根据被试的韦氏智力测验成绩,将被试分为高空间能力组和低空间能力组,但比较这两组被试进行推理时的脑活动,却没有发现任何差异。
根据以上观察,Goel等人总结说推理似乎是一个言语信息加工过程而非一个空间信息加工过程,其核心依据有二:第一,线性三段论推理,无论其包含明显的空间关系与否,激活的脑区都相似;其二,不同空间能力的被试在解决推理问题时其脑活动没有明显的差别。但Goel等人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当含有或不含有明显空间关系的线性三段论推理与范畴三段论推理相比较时,激活了楔前叶和顶枕裂,这个区域典型的功能是负责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这一事实可能说明了所有的线性三段论推理通常都是通过一个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来完成的。
Knauff等人站在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的立场上,主张推理过程其实最终都是通过一个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来完成的[10]。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在推理过程是否依赖于视觉-空间信息加工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研究者错误地将“视觉表象”和“空间表征”混为一谈。“视觉表象”是一种对具体的物体的生动的表象,它与人们的真实知觉十分相似,比如当我们想象一个苹果时,苹果的颜色、形状以及确切的大小都会被准确地表征出来。而“空间表征”则远远没有这么具体,它表征的是一种抽象的空间关系,是一种“示意图”式的表征,比如当我们说“苹果在橘子右面,梨在橘子左面”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将苹果等具体物体简化为一个抽象的圆圈或者点。Knauff等人认为,人们的推理过程所真正依赖的是抽象的“空间表征”而非具体的“视觉表象”,事实上,“视觉表象”非但不能对推理过程有所促进,反而会干扰推理。在其实验中,Knauff等人比较了以下的4种情况:
条件1:既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线性三段论推理
狗在猫的上面//猫在猿的上面//狗在猿的上面吗?
条件2: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线性三段论推理
狗比猫干净//猫比猿干净//狗比猿干净吗?
条件3:容易形成空间表征,但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的线性三段论推理
狗比猫更靠北//猫比猿更靠北//狗比猿更靠北吗?
条件4:既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线性三段论推理(参照水平)
狗比猫好//猫比猿好//狗比猿好吗?
行为结果显示,4种推理任务的反应时依次为: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最长;既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次之;既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再次之;容易形成空间表征,但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的推理最短。Knauff等人认为,既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线性三段论推理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参照水平,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视觉表象还是空间表征都不容易形成。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的反应时比参照水平的长,而既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与容易形成空间表征但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的推理的反应时比参照水平的短?Knauff等人对此的解释是,所有的推理过程最终都是通过一个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来完成的,即使是在既不容易形成视觉表象,又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但是,“视觉表象”非但不能对推理过程有所促进,反而会干扰推理,因此,在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条件下,推理的反应时反而比参照水平的长。与“视觉表象”的作用相反,“空间表征”是真正的推理过程的促进者,因此,在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条件下,无论视觉表象是否容易形成,完成推理的所用的时间都会比参照水平的短,而“空间表征”对于推理过程的促进作用,以在视觉表象不易形成的条件下尤甚。
Knauff等人的脑成像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他们的推测。他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静息状态而言,4种推理活动都激活了双侧楔前叶(BA7),右侧顶上小叶(BA7),双侧颞中回(BA21),左侧颞上回(BA38),左侧额中回(BA46),额下回(BA47)以及右侧额中回(BA6)等区域。其中,顶叶和楔前叶被认为是典型的参与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的脑区。研究者进一步用参照水平去分别与其他三种推理任务相比较,结果发现,参照水平与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两种条件相比均无差别,而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任务则比参照水平更多地激活了视觉区域(BA18/31)与左侧岛叶。视觉区域的活动可能与视觉表象的形成有关系,而左侧岛叶的活动则与语义信息的加工有关系。
如果我们将Goel等人的实验和Knauff等人的实验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可以发现:线形三段论推理似乎总是需要空间信息加工过程的参与——无论是在Goel等人的实验中当线形三段论推理与范畴三段论推理相比较时,还是在Knauff等人的实验中当线形三段论推理与静息状态相比较时,情形都是如此。而范畴三段论推理则有所不同,在Goel等人的两项实验中,范畴三段论推理都没有激活空间信息加工的脑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对于进行线形三段论推理,人们在进行范畴三段论推理时,更有可能借助于以往的知识。这就涉及到了推理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过去的知识对于推理过程的影响。
Goel等人2000年的一项脑成像研究中直接比较了参与两类三段论推理的脑区[11],一类是包含具体名称的范畴三段论推理,比如,“所有的狗都是宠物,所有的卷毛狗都是狗,所有的卷毛狗都是宠物吗?”;另一类是只包含抽象符号的范畴三段论推理,比如“所有的P都是B,所有的C都是P,所有的C都是B吗?”。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具体的三段论推理还是抽象的三段论推理,都会激活双侧的基底节、右侧的小脑、双侧的纺锤状回以及左侧前额叶在内的脑神经网络。而相对于抽象的三段论推理而言,具体的三段论推理会激活包括左侧颞中/上回以及左侧额下回在内的语言加工区域;相对于具体的三段论推理而言,抽象的三段论推理会激活包括双侧枕叶、双侧顶上小叶、双侧顶下小叶、双侧额中回以及双侧中央前回在内的视觉-空间信息加工区域。抽象的三段论推理之所以会激活一个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是因为在没有具体实物的情况下,人们在其头脑中可能会用圈图来表征包含、相交或者分离的关系;而具体的三段论推理之所以会激活语言信息加工区域,可能是因为思维的对象(比如“狗”,“宠物”等)涉及具体事物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语义加工和分析。Goel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之所以他们在以往的两项研究中没有观察到空间信息加工脑区在范畴三段论推理中被激活,可能是因为在那两项研究中采用的都是具体概念。
上述实验结果被认为是支持推理的双重机制理论(dual mechanism theory)的实验证据,按照双重机制理论的观点,人们既可以基于形式逻辑结构进行推理,也可以基于以往的经验进行情景-特异的启发式(situation-specific heuristic)的推理。该理论认为,只有在没有适合的背景知识可供参照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基于形式逻辑结构进行推理。Goel等人进而假设:基于情景-特异启发式的推理依靠一个额叶-颞叶系统来实现,而基于形式逻辑结构进行的推理则推理借助于类似Venn图的内部表征,通过一个额叶-顶叶系统的空间信息加工系统完成。
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Goel等人令被试做两类不同的包含明显空间关系的推理任务”[12],一类涉及人们所熟知的环境,比如:
Paris在London的南面//London在Edinburgh的南面//Paris在Edinburgh的南面
另一类则涉及陌生的环境,比如:
AI lab在Roth Centre的南面//London在Cedar Hall的南面//AI lab在Cedar Hall的南面
Goel等人预测,人们在对熟知的环境进行推理时会采用情景-特异的启发式策略,而在对陌生的环境进行推理时,则会基于形式逻辑结构进行思维。为了控制和估算人脑对熟悉或者陌生的环境本身的反应情况,研究者还设立了两种含有熟悉或者陌生的环境,但却不涉及逻辑关系的条件作为参照。
含熟悉环境但不涉及逻辑关系的控制条件:
Spain在Italy的西面//Italy在Greece的西面//Ireland在Sweden的西面
含陌生环境但不涉及逻辑关系的控制条件:
AI lab在Roth Centre的北面//AI lab在Cedar Hall的北面//Tate Hall在Scott Library的北面
实验结果显示:含熟悉环境的推理比含陌生环境的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双侧的中下部的枕叶(BA18,19),右侧的颞下回(BA37)以及双侧的后部海马。而含陌生环境的推理比含熟悉环境的推理更多地激活了双侧顶叶(BA7)和双侧额上回(BA6)。为了确保在实验中所观察到的脑活动是由熟悉或者陌生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引起,而不是由熟悉或者陌生的环境本身所引起,研究者还分别用与上述两种推理条件相对应的控制条件先过滤掉熟悉或者陌生的环境本身所引起效应,然后再对两种推理条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上述差别仍然存在。这项研究说明,人们可能采用不同的信息加工策略解决不同的推理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逻辑的角度看是相同的。
推理是人类思维最为基本的过程,尽管早期关于范畴三段论推理的脑成像研究表明推理过程主要由负责语言信息加工的脑区来实现,但其后的研究表明线形三段论推理以及只含有抽象概念的范畴三段论推理都有可能借助于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来实现,这可能意味着人们采用不同的信息加工策略解决不同的推理问题,在有现成知识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人们会采用启发式策略,靠与语义记忆有关的额-颞叶系统来进行推理,而在没有现成知识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人们会利用形式逻辑规则,靠与空间信息加工有关的额-顶叶系统来进行推理。因此,我们似乎并不能抽象地谈论参与推理的脑区,而应该在明确人们所采用的具体推理策略的前提下谈论推理的大脑机制。
3 顿悟与语言
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灵感,顿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典型例子。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发明或者发现的提出过程往往是非言语性的,詹姆斯说:“伟大的思想家会预见性地在一瞬间窥见事物之间的全部关系,整个过程发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无法言表”。人们在实验室条件下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比如,Darkin在早年的研究中观察到人们在顿悟地解决问题之前常常表现出沉默,Darkin要求被试在解决顿悟问题时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结果发现在突然来临的顿悟之前人们通常会停止其言语过程。而Schooler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口语报告不但不能促成顿悟,反而会抑制顿悟过[13]。
但Fleck和Weisberg近期的一项研究却对Schooler等人的上述观察提出了质疑,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在解决Duncker的蜡烛问题时,口语报告似乎并不会干扰问题的解决过程[14]。借助于脑成像手段人们可以直接地观察到人们在顿悟地解决问题时大脑的活动状况。
在Luo和Niki的脑成像研究中[15],研究者让被试猜一系列谜语(比如“你杀死了她,但却得流你自己的血”——谜底:蚊子)并选择了那些被试能够良好地理解、但却不能解决的谜语作为正式的实验材料,然后向被试呈现谜语的答案以促成其顿悟。结果发现包括双侧的额上回、额中回和额下回,扣带前回,双侧的颞上回及颞下回,以及楔前叶和海马在内的广泛脑区参与了顿悟过程,其中的楔前叶(BA7)是典型的空间信息加工区域,这为顿悟的实现可能借助于空间信息加工过程提供了证据。罗劲等人还在后继的研究中比较了脑筋急转弯问题(如“有一条毛毛虫想过河,但河宽水深,又没有桥和渡船,也没有谁能帮助它,请问这条毛毛虫如何渡河?”——答案:变成蝴蝶飞过河)和普通的百科知识问题(比如“老话说:‘男女七岁不能……’不能怎样?”——答案:不能同席)的解决过程[16]。结果发现相对于顿悟的问题解决,百科知识问题的解决激活一个以左侧前部颞中回(BA21)和左侧岛叶(BA13)为中心的“知识语言信息加工网络”,而相对于百科知识问题的解决,顿悟的问题解决则激活双侧的后部颞中回(BA39)、枕中回(BA19)、楔前叶(BA19)以及左侧海马旁回。
这一结果与前述Goel等人比较具体和抽象三段论推理的脑成像研究具有一定的可比性[11],它表明人们在解答百科知识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与解决含具体名称的范畴三段论推理一样的信息加工策略,依赖于具体的知识存储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在解答顿悟问题时则有可能像解决抽象的范畴三段论推理一样,采取更加空间化和抽象化的信息加工策略来实现问题表征方式的根本转换。
那么,会不会是“脑筋急弯问题”的中包含了某些特殊的可视形象(比如毛毛虫与蝴蝶)激活了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有两个事实可以反驳上述的推测:其一,实验所使用的百科知识性问题的可视觉化程度与“脑筋急弯问题”相当,比如“男女七岁不同席”也是可以视觉化的。其二,研究者进一步在两类“脑筋急弯问题”之间进行了比较,一类的问题的视觉化程度较高,比如“夜里,一个穿白长袍的女人在海边的沙滩上行走,可她的身后却没有脚印,这是为什么?”(答案:她在倒退着走);另一类则视觉化程度较低,比如“诸葛亮是大智者,如果他还活在世上,我们现在的世界一定会有所不同,请告诉我那个一定会有所不同的地方”(答案:世界上会多一个人)。结果表明:比之于低视觉化的问题,高视觉化的顿悟问题的解决激活了位于左侧额叶的语言区以及双侧的舌回(lingual gyrus)和梭状回(fusiform gyrus),这些区域的活动可能与在高视觉化条件下被试将对问题情境的语言描述转化为视觉表征,并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保持这种表征有关。高视觉化条件下所激活的脑区与Knauff等人实验中的容易形成视觉表象,但不容易形成空间表征的推理任务相似[10],这提示在顿悟问题中的可视觉化可能与Knauff等人提出的“视觉表象”相当,但却与顿悟中实现问题表征方式的转换的视觉空间信息加工网络的活动没有关系。
与罗劲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16.17],Jung-Beeman等人用另一种方法研究顿悟的大脑过程但结果却并未发现空间信息加工区域的活动[18]。他们采用的实验方法是给被试三个互不相干的词,比如pine(松树),crab(螃蟹),sauce(调味料),要求被试找到一个词,这个词与上述的三个词中的无论哪一个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形成一个常见的合成词或者短语,比如apple(苹果)与上述的三个词结合,会产生pineapple(菠萝),crab apple(山楂)和apple sause(苹果酱)。Jung-Beeman等人的研究小组以往的结果证明,被试在解决有些项目时,会产生一种“啊哈!”反应。研究者将被试能够成功解决的项目分成两类,一类项目被试在解决的时候伴随有“啊哈!”反应,而另外一类则不伴随有“啊哈!”反应。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不伴随“啊哈!”反应的项目,伴随“啊哈!”反应的项目明显地激活了右侧的前部额上回,但却并未观察到顶叶空间信息加工区域的活动。尽管我们目前尚不清楚为何会有上述的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说明了在不同任务条件下、不同实验材料的顿悟对空间或者语言信息加工过程的依赖程度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4 脑成像的证据:究竟能走多远?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脑成像研究为研究思维的要素和组成提供了直观的脑活动数据,在事先假定各脑区的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研究者就有可能借助于这些数据来推测思维过程中言语活动的参与状况和及其作用。整体而言,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提示,在普遍意义上谈论“思维”是否依赖于“语言”是不恰当的,思维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活动与思维的具体内容有关,即使是同一种类的思维过程,所涉及的内容不同,其对语言过程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这样的证据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增进我们对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理解?乐观者认为,直观的脑成像为我们揭开人类思维的本质之谜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比如,对于心理表象在本质上是图像的(pictorial)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心理学家们有着长期的争论,但新近的脑成像研究显示:人们在形成心理表象时有视觉区域的活动,这为心理表象的图像本质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对此,著名心理学家Kosslyn乐观地认为,脑科学证据的出现有可能使长期的“心理表象之争”以“图像说”被证实而结束对此问题的争论[19]。但反对者却认为:无论是真实的视觉所引起的视皮层的活动,还是由心理表象所引起的视皮层的活动,可能都与内在信息表征本身的“形式”无关,即使是视觉区域的活动,也不能保证其信息加工的本质是“视觉的”[19]。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只根据思维过程中是否有语言区域或者空间信息加工区域的活动似乎是不足以用来推论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言语的”还是“视觉空间”的。因此,如何看待脑成像的证据的推论力,仍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标签:认知神经科学论文; 信息加工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信息加工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线性空间论文; 认知障碍论文; 线性思维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