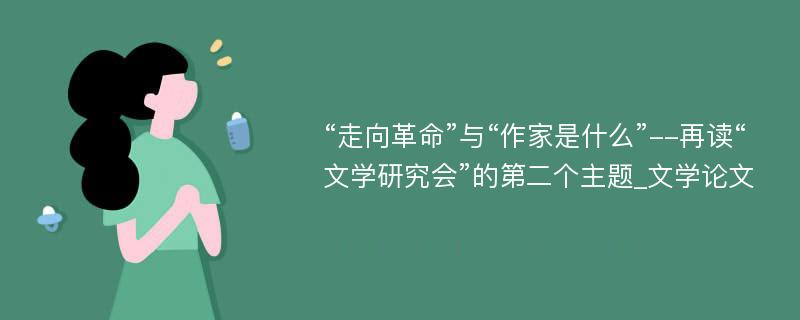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会论文,何为论文,走向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042-05
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按正式的记载共12人。其中周作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文研会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在当时威望最高。郑振铎、沈雁冰是中坚,也是其文学思想的主要阐述者。“文研会”这个名目,在今天看来不像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文学社团,而更像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机构。其实,文研会在最初筹划时就是为了“研究”文学而非从事文学创作,郑振铎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一文中就曾这样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我们五个人(引者按:指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都是发起人。”[1]因此文研会成立后非常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文学思想的阐发,“五四”年代并未涉足“创作”但却倾心“研究”的沈雁冰竟成为文研会的首席代表,于此不能无因。因此,从文学理论或文学思想角度研究文研会,应该是颇有必要的。本文拟就近年来“重读”文研会时感触最深的两点略陈管见,期望能对“重写”20世纪文学史或指点当下文坛多少有所裨益。
一、走向革命:“为人生”文学观的别一读法
文研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其具体的表述是《文学研究会宣言》中的如下一段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
“为人生”的文学观在1921年由文研会正式提出,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来说,具有总结以往、面对当前,开拓未来的多重意义。“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自发动以来,先驱者们在批判封建文学、倡导“人的觉悟”和成功地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着新文学思想内容方面的建设。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指斥封建文学“其内容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认为易卜生揭露了家庭和社会的黑暗,“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4]。显然,上述观点中已蕴含着新文学应关注现实人生的思想。至周作人1918年末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反映人生,“为人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已基本形成。就在周作人写《人的文学》的同时,他还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5]这无疑是对“为人生”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到1920年周作人写《新文学的要求》时,他已经以明确的语言表示:‘“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的惟一需要。”[6]因此,以新文学第一个社团的名义将这一文学思想正式昭告天下,无疑是对以往的探讨做了一个集体性的肯定和总结;而1920年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五四”新文学阵营又面临着新的对手和挑战。此时,正统的封建旧文学已溃不成军,但以游戏、消遣为宗旨的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却仍然存在,新的受西方影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也开始露头。这两种文学都披着时髦的“现代”外衣:鸳派文学也用白话并标榜“写实”;“为艺术而艺术”者更以新潮自居。但他们都缺乏“五四”先驱者对社会人生那种崇高的启蒙主义的关怀。如果听任这两种文学泛滥,无异于听任“五四”启蒙主义精神自挫其锋。因此,文研会正式举出“为人生”的文学大旗,无疑是新文学阵营面对当下文坛的疲软现状再次宣示自己的文学立场;1920年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已经走过了“破坏期”而步入“建设期”。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学?怎样建设新文学?这正是文学界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文研会及时揭橥“为人生”的文学观,无疑也是“五四”先驱者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响亮回答。自然,这种回答不一定是很全面的,惟其如此,尊崇个性主义的创造社随后与文研会发生论争。但文研会基于人道主义思想所作出的这种回答,又毕竟是及时、必要和切合中国启蒙任务需要的。
如前所述,文研会成立之前,周作人对文学如何“为人生”已作出过初步的解释。文研会成立以后,沈雁冰、郑振铎等核心成员又对这一文学观作出新的探讨和阐述。这种新的探讨和阐述有如下新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五四”逐渐落潮社会又复归黑暗;二是随着共产党的成立政治意识逐渐置换文化意识而再次走向历史的前台;三是沈雁冰参与共产党的筹建逐渐由单纯的文化人向政治和文学兼顾的政治文化人转变。因此,沈雁冰和受到沈雁冰影响的郑振铎等人就“为人生”发表的见解,不仅使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显出一条发展的脉络,由开始时的略带全人类性的“为人生”向略带阶级性的“为人生”转化,而且使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和周作人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呈现出“蜕变”迹象,由周作人的更关注普通人精神上“非人的生活”向更关注普通人物质上“非人的生活”转化。此中所体现的本世纪“救亡”主题对“启蒙”主题的制约和压挤再一次显现出来。
由沈雁冰、郑振铎等阐述的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首先对文学上的“平民主义”作出了新的探讨和解释。“平民主义”正如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文所说的那样,它反对“一切特权阶级”,张扬“自由平等的个人”,是当时“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的一种文化思潮[7](P5)。周作人之所以写出《平民文学》一文,显然也是受了这种思潮的鼓舞。正因为这样,周作人有意作了两个强调:一是所谓“平民”,指的是非贵族的“世间普通男女”,亦即世上“一律平等的人类”。二是“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5]。沈雁冰、郑振铎等人最初宣传“为人生”的文学观时,显然还继承着周作人的说法,如沈雁冰在1921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就曾这样说:为人生的文学“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8]。但在1922年7月发表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沈雁冰就传达出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新文学的作者们应该“注意社会问题,同情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沈雁冰还结合对旧小说的批评指出:真正的新文学的作者应该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的头脑”,否则,“他们虽然也做人道主义的小说,也做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而其结果,人道主义反成了浅薄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的穷困反成了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了。”[9]显然,所谓“平民”已具体化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了。
由沈雁冰、郑振铎等阐述的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同时对文学反映人生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新的探讨和阐述。他们显然不满足于周作人讲过的“人的文学”既可以写人的“理想的生活”,也可以写人的“非人的生活”和“平民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等说法,而特意强调写社会的黑暗与劳苦大众的痛苦。沈雁冰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而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10]郑振铎更有一文,题为《血和泪的文学》,其中写道:“萨旦日日以毒箭射我们的兄弟,战神又不断高唱他的战歌,……忘了么?虽无心肝的人也难忘恩负义了吧!”因此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11]
由沈雁冰、郑振铎等阐述的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还对文学如何“为”人生作出了新的探讨和阐述。应该说,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阐述,还是首先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情感性及其感人功能的。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曾指出:文学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作者只要把他的观察、感觉、情绪写出来,“读者自然的会受他的同化,受他的感动。”[12]但沈雁冰、郑振铎们显然担忧反映人生的文学陷入批判现实主义的悲观与绝望之中,因此他们更注重文学以其理想性或理性精神指导人生的功能。沈雁冰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中指出:进化的文学应“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13]郑振铎在《光明运动的开始》中也说:文学在揭露罪恶社会的同时,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14](P151]。
总之,由沈雁冰、郑振铎等阐述的文研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既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的基本精神,又显示出新的进展。“为人生”,可以说是“五四”文学自《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以来就已揭橥于世的最基本的文学精神,文研会既然也高举“为人生”的大旗,说明它确实继承了“五四”文学这一最基本的精神,不愧为“《新青年》派”的嫡传(事实上,创造社和文研会论争时也是这样“理解”文研会的)。但以沈雁冰、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研会在现代文学思想建设史上所作的工作,实际上是既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又依据社会和政治思潮的变迁对之实行某种程度的“革命性”改造。就此而言,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文学“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又可以看到在“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精神中已悄无声息地孕育出了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同时还会看到以“启蒙”为基本性质的“五四”文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日渐高涨和活跃的‘“救亡”意识的导引下,是怎样逐步偏离原有的性质和航向,由“人生型”的、“文化型”的启蒙主义文学向“阶级型”的、“政治型”的“革命文学”转变。在这一转变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沈雁冰、郑振铎个人当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从根本而言这一切又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斗争的高涨,使得“五四”落潮后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固然使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陷入苦闷、伤感和彷徨之中,另一方面却是激进知识分子中政治意识的增强和新的革命斗争的酝酿。沈雁冰、郑振铎对“五四”文学“为人生”主张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正是文学思潮面对时代变迁所作出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式的感应。正由于这样,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对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生活和命运的关心,以对文学反映时代批判现实改造社会的意义的关怀,以对文学唤醒民众指导人生的功用的关注,为新文学开辟着一条源自“五四”又不等同于“五四”的有着新的宗旨和追求的道路。应该承认,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传统。这种“为人生”的文学,不久以后又接受了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灵魂的革命理论的影响,向着无产阶级文学前进。事实上,“五四”时代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为人生”再到“同情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被侮辱者”等口号或主张的演变,已经预言了现代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势。
二、作家何为:对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强调
文研会成立以后曾参与多次文艺论争。其中有的属于新旧文学之争,如对“学衡派”和“甲寅派”的批判,这种斗争的主要意义是维护新文学的生存权(“学衡派”实际上是一个受到美国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并不能简单定性为“复古派”或“旧文学”,但保守立场使其站在“五四”新文化的对立面。这里姑沿用旧说,以看出当时文学论争的类别)。有的却更多地属于文艺思想之争,如对鸳鸯蝴蝶派、名士派和唯美派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文艺思想之争中,文研会的理论家们一方面继续阐述了他们的“为人生”的文艺观,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作家应具备神圣的社会责任感。
鸳鸯蝴蝶派在民国初年盛行一时,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了当时都市青年在爱情上渴望自由却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时代的苦闷,在艺术上也有一些翻新之处,因而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地位未可全盘否定。但该派的致命缺陷是不具备“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关于“人的觉悟”的现代意识和用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不仅其作品内容中依旧充斥着“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陈旧观念,而且作家编造种种“哀情”、“惨情”故事的动机,又不外以下两个:或者借此抒发作者个人那种与封建时代落魄文人颇为类似的关于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感喟,并以此迎合市民阶层读者的消极心理;或者借此类作品在市民阶层中有广大读者而扩大销路,以牟取商业上金钱上的利益。总之,鸳鸯蝴蝶派作家真正缺少的不是文学才华,而是缺少对文学事业的严肃态度和作家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批判鸳鸯蝴蝶派时,除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外,还进而剖析了该派作家人生观的不健全和由这种不健全的人生观所决定的对文学事业的不忠诚。他指出:鸳鸯蝴蝶派作者“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他们从事小说创作,或者只是“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来“游戏笔墨”,结果“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札”;或者“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对于艺术不忠诚的态度,再没有比这利害些的了。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沈雁冰在这篇文章中特意说明:区分新旧小说的“惟一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凡抱着“表现人生”这种“严正的观念而作出来的小说,我以为无论好歹,总比那些以游戏消闲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8]显然,沈雁冰所说的“严正的观念”是包含作家对艺术事业的忠诚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内容的。
名士派古已有之。凡有名望而不作官甚至鄙视作官者,或有知识而不拘小节甚至以自由散漫自赏者,皆属名士派。“五四”时代文研会所抨击的名士派有两种人:一种是旧派作家中以才子自命而风流自赏者,当时不少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文章都径称该派作家为名士;一种是跻身新文学家中却颓唐自放而卑视功利者,这种人常常引西洋的浪漫派颓废派文学为同道。两种人的人格成因固然有很大不同,但都表现出对文学的社会使命和作家社会责任的放逐。因此沈雁冰在1923年的《“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对名士思想也提出严肃批评。他指出:“中国名士最坏的习气是,狂放脱略。他们狂放到极点,以注意政治现象为卑琐;他们脱略到极点,以整饬治事为迂俗。他们把国家兴亡大事,等之春花秋月。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总是一笔糊涂账。中国知识阶级所以缺乏组织力与活动力,就中了这些名士思想的毒。”沈雁冰特意说明:“西洋的浪漫派颓废派的文学家的思想和行事,原与中国名士派根本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西洋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一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名士派的余孽认了同宗。”[15]因此沈雁冰在这里批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漫派颓废派文学,而是强调一个作家不能“狂放脱略”到不关心国家兴亡大事,不注意政治现象,不能忘却了文学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神圣使命和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唯美派是“五四”时代滔滔输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中的一种。“五四”先驱者和文学研究会一开始并未对唯美派表示完全的拒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盛赞的西洋作家中就有英国唯美派的巨子王尔德。文研会接编《小说月报》后发表的《改革宣言》中也称:欲创造中国的新文艺,就必须认真研究西洋文艺。这种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材料。”[16]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文研会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唯美派的立场。沈雁冰1921年作《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好的西洋文学都该介绍这办法,于理论上是很立得住的,只是不免不全合我们的目的。虽则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于成就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很不经济的。”[7]显然,在文研会理论家中沈雁冰是最富于战略头脑的。他不否认王尔德的作品是“好的西洋文学”,但却不赞成盲目引进,因为它不适合“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主潮的要求。惟其如此,当1923年随着“近年来政治的愈趋黑暗”文坛上遂普遍反对唯美主义时,他热情洋溢地写下《“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这篇论文,一方面指出当时醉心于唯美的作家“并未曾产生实在伟大的值得赞美的作品”,他们或者“只能使中国文人用旧的几句风花雪月的滥调”,或者“只能拾几个舶来的已成滥调的西洋典子”;另一方面热情呼唤新文学创作“大转变时期”的到来。所谓“大转变”,即由“吟风弄月的、‘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文学”转变为“激励民气的文艺”。他说:“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15]毋庸多言,沈雁冰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是文研会文学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早在1920年文研会成立之前沈雁冰就写有一篇题为《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的论文。他指出:“自来一种新思想的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中国现在正是新思想勃发的时候,中国文学家应当有传布新主潮的志愿,有表现正确的人生观在著作中的手段。应该晓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哲理?什么是文学的艺术?什么叫做社会化的文学,什么叫做德谟克拉西的文学?”[17]以后在与对立文艺观的斗争中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作家社会责任说。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统领和深化了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论。因此,文研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不仅反映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作家人格精神的基本要求,而且体现了文研会作为一个“同情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的“为人生”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的确,“责任”是文研会理论家笔下出现最多的字眼之一。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对成就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而且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01-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