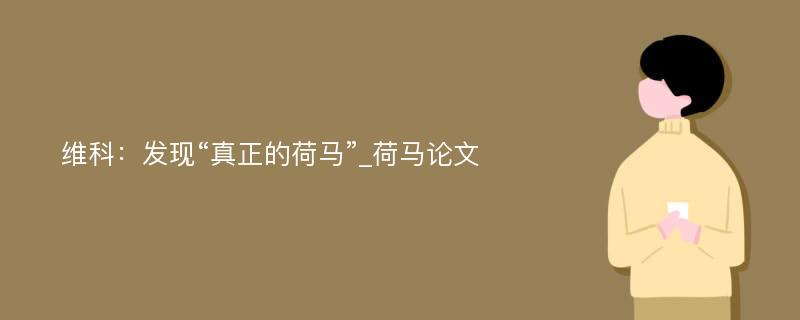
维柯:发现“真正的荷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马论文,发现论文,维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柯的时代盛行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在其影响下,现代思想家们试图把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运用于传统,并以现代理性这块“千锤百炼的真理的试金石”为武器来鞭挞他自己时代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他们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对如何学习和理解传统真正了然于心,因为“哲学家使人类心灵的真正规律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类,他们谙知如何恰切地置身于这个世界最久远的年代”①。他们视诗歌为无理性,将其与哲学相对立,并坚持认为,只有理性本身才指向更崇高、更高贵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张废黜荷马,因为荷马生活在蒙昧无知的年代,而且作为“诗人的君王”,荷马的美德和品质看起来并非完美无缺和永恒不变。在这种背景下维柯寻找“真正的荷马”不仅是他对理性主义思潮作出的深入回应,也是他试图解决诗歌与哲学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密匙”。
一、什么是“真正的荷马”?
克罗齐指出,虽然维柯对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那些习俗的分析不准确之处俯首可拾,而且从总体上看又过分夸张和片面,但这个分析作为一个整体却是巨大的进步并开辟了荷马批评的新方向;而且荷马评论中的这种新转变,不仅给古代文学史,甚至对阐释那些书面档案不可靠的历史时期,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②维柯自己也称,他超拔于前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揭示出“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③的事实,这使得他之前谈过有关“诗之起源”问题的人,例如,哲学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意大利帕特里齐,语文学家和评论家——包括斯卡理格和卡斯特尔维特罗都大谬不然。在他看来,“那些陈旧的、‘被柏拉图抛出、被亚里士多德肯定的’原则都是武断和偏见,他们把具有诗的理性的作家引入歧途。甚至像帕特里齐这样庄重的哲学家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关于歌和诗起源的一些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他‘不好意思提及的’”④。维柯指出,关于诗的新原则不只是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我们的卡斯泰尔韦特罗的不同,而是截然相反,这些新原则是想象的原则,由此人类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语言——诗,在《自传》中,维柯就曾夸耀自己早已发现了那些“希腊人、拉丁人和其他民族关于诗的一直相信的原则之上的神话的原则”⑤。克罗齐称维柯不仅是事实上的革命者,而且作为革命者,他对此有着充分的意识,他知道反对在他之前的所有的诗的理论,并以他自己探索的关于诗的新原则“推翻了首先由柏拉图提出、尔后又由亚里士多德直至我们的帕特里齐、斯卡利里、卡斯泰尔韦特罗提出的所有的诗的起源之说,确定了卓越的诗是由于人类推理的缺乏而产生的说法”⑥。在《新科学》中这种观点变得更为明确,维柯批评说:“他们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原则去推论,好像创造语言的各民族都须先向亚里士多德请教!”⑦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自柏拉图至17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批评家们一直有一个共识,即:他们都认为荷马是拥有深奥的智慧、神圣的道德感以及关于伟大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知识这样一些才能的人。事实上,虽然荷马史诗描绘的都是伟大的君主、优秀的统帅,所有民政、军事和家庭美德的光辉典范这样一些高贵的英雄,但问题是,以阿喀琉斯为代表的这些英雄却被描述为充满激情、暴烈、固执、感情用事,既受慷慨大方的冲动驱使,又受野蛮的义愤驱使,对此,柏拉图以及后来的许多人都感到荷马描绘的其实是一个非道德的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抱怨说,荷马让英雄情感脆弱,遇事恸哭,又不善于自我控制,常“狂笑”,而且还贪财,这些怎么能用于教导青少年?通通应当删去。⑧在维柯看来,如果想要驱散对荷马英雄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除了把这个残忍的阿喀琉斯的形象与希腊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对比之外,别无他法。维柯在《新科学》中开始直接思考荷马问题,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却从中发现了打开人类历史大门的钥匙,事实上,正是由于发现了真正的荷马,才导致维柯发现了《新科学》中所提出的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原则。⑨他说:“凭他构思出的某些神话学原则,他赋予了这些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种不同于迄今所具有的面貌,证明了这位诗人在处理这两种题材时多么明智地把两组希腊故事编织在一起,一组属于渺茫难稽的时代,另一组属于英雄时代。”⑩几年后维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说:“在这部著作里,维柯终于充分认识到他先前著作中提及的那种原则,即他前此还只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原则……[维柯发明的这门新科学是]用一种新的批判方法,从诸民族创始人所创建的一些民间传统故事中,耙梳出该民族创建过程的真相。”(11)在这个意义上,荷马与其说是发现《新科学》的结果,不如说是原因。
即使对文明社会的普通人来说,心灵与感觉也已完全分离,他们的心灵已被书写技艺变得敏锐,已经习惯于自由地运用抽象术语,因而要想领略原始人混沌的幻想非常困难。在维柯看来,原始人的心灵不是抽象的、精确的或精神的,而是沉溺于感觉之中,被激情弄迟钝了,被躯体所掩盖,他们只能凭借想象、幻想和情欲来感知和认识周围事物,荷马史诗就是当时的人们这种思维和认识方式的真实呈现。他说,荷马对英雄性格的贴切表达是后来擅长哲学和诗学的批评家们所无法达到和理解的,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性格不是受过任何一种哲学驯服和教化的心灵的性格,因此荷马所描绘的那些可供老婆婆们哄小孩用的生活和故事使我们很难把玄奥智慧归于荷马。但为何荷马采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希腊方言?为何许多希腊城市都争着宣称荷马是属于他们的公民?维柯说,这是因为“真正的荷马”就是英雄时代整个希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其所知的唯一方式创建了人类早期文明,后来随着哲学的缓慢发展,人们逐渐丢弃早先诗歌的天然幻想,后来的希腊人必定对原初的荷马史诗进行窜改和修正,并采用寓喻解释,以使之更易于被当时的人接受。卡西尔指出:“在希腊文化的历史上,我们发现有一个时期,旧的诸神——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诸神开始消亡。关于这些神的流行概念受到激烈的攻击。一种由个别的人们所形成的新的宗教理想产生了。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思想家们——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创造了各种新的智慧和道德标准。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荷马的诸神就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它们的拟人特征被清楚地识别出来并且受到严厉的批评。”(12)总之,通过荷马史诗这个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最为古老的诗歌作品作为证据,维柯断言,早期人类历史的真实特性是这样:是诗人而非哲人,他们运用想象力而非理性书写了第一部人类历史。因此作为诗人,荷马和他的史诗一起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一个特别显赫的位置。
二、为什么“寻找真正的荷马”?
在维柯看来,“荷马”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人类各种制度的最初起源,如果想找其它更早的起源,那纯属好奇心,这是界定最初原则的特性,而说明事物最初原则产生的方式,也就说明了事物本性。“真正的荷马”就是人类文明的奠基者,他们通过创造神话创建了人类社会,并在神话所提供的幻想形式中逐渐理解了自己的社会需要,并凭借神话所奠定的制度来规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荷马,就可能对自身及其发展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
克罗齐说:“一个民族没有上帝的现象在历史中是找不到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穷乡僻壤流浪之人的闲谈中。”(13)“荷马”的核心是宗教,宗教不仅是早期社会制度的实际需要,也是早期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维柯看来,如果没有以宗教为核心的传统智慧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带领社会穿越历史的不同阶段,哲学本身就会是不可想象的,简言之,哲学的根源就是宗教。但现代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如果世界有了哲学家,就能凭理性而不凭法律过公正的生活,那就不需要有宗教了”(14)。维柯指出,哲学一方面没有能力区分理性的形而上学的结果和数学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区分出城邦赖以统治的或然规则。(15)哲学反思的最大弊病就是要将理性规则应用于不那么理性的人类活动,它总是试图从传统的一切驾驭中解脱出来,并将理性直接应用于政治事务。可以说,当现代人遗忘了自己起源于神话诗人后,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其自然本性;当理性的人们逐渐淡忘了社会共同体的根基时,社会也将无法抵挡道德的腐败和制度的分裂。维柯曾赋予统治罗马早期和晚期社会两种根本对立的原则:前者依靠荷马的凡俗智慧,后者则是通过理性和自由。早期的罗马有着宗教迷信、严格法律以及深层阶级对立,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罗马人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理性的,但其社会却体现着一种活泼强健的文明,但随着罗马习俗缓慢地沿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哲学最终成为文明的最高成就时,罗马却覆灭了。在维柯看来,宗教迷信并没有阻碍罗马早期文明的发展,相反,正是由宗教所导致的罗马人谨守虔敬的德性反而促进了罗马的进步。当罗马人一旦变得理性,他们就开始“言不离体面和正义,正像人天生就是要谈论一些装作是,但却不是的东西,而别无其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他们的宗教(他们自然对此不能否认也不能拒绝)的抵制,所以为了安慰他们迷途的良知,他们就带着不敬的虔诚,用同样的宗教来使他们缺德邪恶的行为神圣化”(16)。维柯称这种现象为“反思的野蛮”,它不同于其之前“感性的野蛮”。在《新科学》中,维柯描述了服从于“反思的野蛮”中的民族所处的状态:
因为这类民族,像那么多的野兽一样堕落到一种习俗里,人人都只想到个人的私方利益,达到极端软弱,或较好一点,达到极端骄横,他们就像一群野兽一样,稍有不快意时就耸起鬃毛,勃然大怒,拳打脚踢起来。这样,不管他们的许多肉体挤来挤去,冲来冲去,他们都像一群野兽一样,在意志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孤寂地生活着,任何两个人都不能达成协议,因为每个人都只服从自己的快感或反复无常的幻想——由于这一切,天意就注定了他们通过固执的派系斗争和拼命内战,把他们的城市变成森林,又把森林变成人的兽穴和兽窝。这样,通过长期的野蛮生活,后来使他们变成野兽的那种邪恶心眼所产生的那些刁钻古怪的想法,几生锈腐烂掉了。原始人是曾被感觉功能的野蛮性作弄成的一些无人道的野兽,而现在这批野蛮人却被反思功能的野蛮性作弄成为一批更无人道的野兽。因为原始人还显出一种宽宏大量的野蛮习性,人们对这种野蛮习性还可以自卫,逃脱或保持警戒,而现在这批野兽却具有一种卑鄙的野蛮习性,在甜言蜜语乃至拥抱的掩护下,图谋侵害朋友乃至至亲骨肉的生命和财产。(17)
文明的雅典和强盛的罗马最终都被这种“反思的野蛮”所摧毁。维柯指出,人类在经历了诸神时代的恐惧和英雄时代的残暴之后,开始变得温柔多情,形成了“对安逸生活的爱好,对婴儿的温情,对妇女的爱情,对生命的愿望(贪生)”(18)等这些在母亲必定痛恨自己子女的粗暴时代所没有的性格,他视这种性情的软化为历史发展的进步,但他同时意识到这种进步所产生的间接的、负面的社会影响,那就是,当维持社会稳定的人类共同意识逐渐变得松弛,进而被人人都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这条原则取而代之时,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摆在了第一位。虽然,维柯把集体的公共公平,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个人主义的私人公平都看作是正义观念的扩展和实行,但他更关注个人主义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它的正义。当看到与私人财产和权力相伴而生的是派系斗争、内战、暴乱以及对贪婪的崇拜时,维柯认为公共精神或社会正义的衰颓更令人不安。
现代思想家们在将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和传统时曾自信:人可以通过理性来控制自己的命运,但事实并非尽如人意。近现代欧洲已日益上升到理性和科学的顶点,但其社会却日益呈现出衰颓的状态,维柯发现,导致这种衰颓的正是“他在罗马共和国中发现的同样的破坏性社会力量”:日益增生的感觉精细、私人化、宗教衰颓、质疑权威、抛弃传统教育,及“渎圣的虔诚”(19)。在这个意义上,维柯寻找“真正的荷马”也是在寻找一种人类形成之初使人之为人的精神意识,即原始人通过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一种英雄性格,这种性格洋溢着关于公共正义实践的人性精神。
三、“荷马”的人文主义内蕴
斯卡里格在他的《诗学》里发现到荷马的全部比喻都是从野兽和野兽事物中取来的,就感到愤怒,但在维柯看来,那些不可思议的神话的属性组合,即那些“想象的类概念”是混合了不相容属性的形象,它们其实是原始人诗性本性——一种把不同的功能和观念结合在一种形象中,例如,既是女人又是大地的西布莉、有羽翼的马、半人半马的怪物、树神等——的自然结果。文明人的心智已不再受各种感官的限制了,使心智脱离感官的就是与我们近代语言中的抽象词语相应的抽象思想,而人类心智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原始活力、直接性和想象力的丧失,如果按照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标准加以判断,荷马的世界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对维柯而言,历史的道路不是用真理而是用确定和秩序铺成的,他说,心灵在认知上经历了从没有注意的感觉,到伴随着被干扰和混淆的理解能力的注意,再到明晰心灵的反思几个阶段。(20)在意志上也经历了从自然状态到实践的“确定性”(21),再到实践真理几个阶段,这些相互联系的现象对应着三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人类从蛮荒过渡到英雄的野蛮状态,再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相应的,历史就有了三种自然本性,三种习俗,三种法律,三种国家,三种语言及书写方式,三种权威、理性和正义。(22)英雄的神话作为原始社会所使用的特殊概念和范畴,它不同于人的时代所形成的概念和范畴,换言之,“荷马”并不是对人的时代更准确地表达的意思的不完美解释,而是真实描述了英雄社会的实际状况。维柯指出,荷马史诗的崇高就源于它真实地反映了英雄时代普遍的人性特征。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荷马”揭示出人类达到《新科学》所创立的理想的永恒历史这种完美状态的等级,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不朽的事物一样,必须依照各个等级在极限范围之内循其道而行,达于终端。
那么,历史中是否存在真正的人性?什么才是人的真正本性?从原始人阴暗的洞穴到荷马英雄神话,然后再到民主制度的过程,这些不断变化的心灵创造形式和人的真正本性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维柯指出,正如在人的心灵之内埋藏着永恒的真理种子,在人类中也埋藏着永恒的正义种子。(23)他说:“英雄智慧的根基就是人类精神不死这个观念,这几乎是人类的一项传统。人们不尊崇肉体,因为肉体他们触摸得到,而对于更高者的意象却不能。这就是诗人们的神学,它把人的精神描述为‘关于更高者的人性意象’。”(24)对维柯而言,人唯一要紧的是灵魂的意向和内在态度,人的真正本性就寓于那些摆脱了一切外部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中。必须承认,在某些明显的方面,一个理性取代了神话、一个存在着人人都公认的正义标准,人们不再实行活人祭的理性时代绝对要优于把天空视为一个用雷鸣电闪来表达愤怒的巨大的生命体,以及阿伽门农让人杀死自己的女儿祭献给女神的时代。克罗齐指出,暴力时期的神话不可能有哲学概念的严格性,因此当维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时,他认为荷马的英雄们从伦理上讲是最好的。原始人拥有极大的体力,理解力却是低下的,第一声雷鸣使敬畏天神的意识在他们心中觉醒,他们认为诸神是比他们更强壮的存在物,因而被迫执行众神的命令,由于想象具有一种强有力的欺诈力,维柯并不怀疑,第一个有序的“人”的社会建立在恐怖的宗教——神的权威之上。维柯设想是天意的智慧命令这些狂暴之人,在没有被理性所驯服时,至少应该对暴力的神圣本质心存恐惧并以此标准衡量理性,而这就是“战争的外在正义”(25)原则的基础。换言之,荷马时代理性规则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强力崇拜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履行相当于理性规则的功能,因此荷马颂扬“用矛尖来表明权利”的阿喀琉斯为希腊英雄,并赋予他“‘无可指责’这一不变的称呼!”在词源上,“最强壮的”和“最好的”也被认为是同义词。人的时代则是依据人的理性本身而不再以力量为标准来评价彼此。如果我们想在荷马的英雄们身上寻找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美德、正义和仁慈,那将纯属徒劳。随着人类心智从野蛮起点缓慢成长,任何有关永恒不变的真理、正义观都是不存在的,相应的,每一个真理都有它实际的一面,都有它的实际后果;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人类的本性和发展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指导实践的路线。在这个意义上,荷马时代的强力法律就可以理解为是以特定的理性原则来实现的某种永恒的公正,因此要想寻找对各种社会形态进行判断时所依据的共同准则和标准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寻找真正的荷马”,维柯将永恒置于人类的历史实践中,给了真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位置。在《新科学初版》第50段中,维柯给出了关于正义如何既是永恒的又是可变的绝佳例子,他写道:
在希腊最古老的时代里,当雅典人把雅典的所有土地都献祭给主神宙斯,并在他的统治下生活时(如同希腊黑暗时代史所叙述的),只有获得宙斯的恩准,他们才可拥有一片农田。在另一个时代里,例如后来古罗马人的时代,因为十二铜表法而需要一种庄严的委托,即所谓“契约”。但是,在又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各民族中间持续至今,只要实际委托农田本身就足够了。获得所有权的这三种方式全都依据这种永恒正义[原理]:如无物主的遗嘱,一个人不能成为属于他人的物品的所有者,而遗嘱必须预先备妥。最后来的是哲学家,他们懂得,所有权本质上绝对取决于遗嘱;有清楚的表示就足够了:所有者决定把他对于某个特定物品的所有权遗赠给另一个人,而不论这种表示是直截了当的语言还是无声的行动。(26)
加林指出,“正是在对待过去的文化,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明确地确定了人文主义的本质。这种态度的特征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赞赏或喜爱,也不在于更多地了解古代文化,而是在于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观。‘野蛮人’并非不了解古典著作,而是不能从当时真实的历史环境出发来理解这些作品。虽然维尔吉利奥或是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已为人熟知,但人文主义才算是真正地发现了古代人,人文主义把维尔吉利奥送回到他的时代,使他置身于他所处的世界中。……因此,在人文主义里不可能,也不应当区分古代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因为他们是合二为一的。发现古代世界就是衡量自己同古代世界之间的距离。”(27)在历史的长河里,哲学家就如同长者,诸民族的奠基者就像小孩,但正是这种特性使荷马在那些早于人类发展的事物,例如,诗歌和想象上更有优势。这种优越性使维柯认识到了一个存在于古人中的原始基点:好的诗歌与演讲不可能同时出现,诗歌属于英雄时代,演讲则属于理性思想更加散文化的时代。具体地说,有别于科学的逻辑思维使用分类和系统化的方法将生命划分为各个独立的领域来说明实在,古人基于生命一体化观念的诗性思维更易于沟通多种多样的个别生命形式,这使得古人对许多未被我们注意的特别方面非常敏锐,在这方面他们比现代人更占优势,因而在散文、演讲盛行的今天,诗歌依然有其巨大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用当代术语来讲,荷马既非古人也非今人,而是一种迥异于我们时代的声音”(28)。对维柯来说,荷马与柏拉图的鸿沟如同诗与哲学的鸿沟一样巨大不可跨越,但维柯始终认可对古代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不仅有益于文学和哲学,也有益于历史本身,而且他相信,只要在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的帮助下,荷马就有可能被正确地理解和复原。黑格尔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圣经’。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29)维柯寻找真正的荷马就是在寻找最初民族得以形成的一种精神意识,这种意识虽然是模糊的,却是至关重要的,让人无法忽视,因为对人而言,如果他对自身本性从何种开端以及如何从这种开端发展而来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么他也永远不会对自身发展有正确地理解。(30)
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人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创造过程,而回顾历史就意味着重新创造和记住传统。对荷马史诗所具有的创造性价值的设想和回顾,不仅是维柯思考传统智慧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实践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试图进一步认识现代理性的结果。虽然维柯认为理性的时代才是真正的人的时代,它是人类发展的顶峰,但从他对“各民族在复兴时所经历的各种人类制度的复归历程”的描述来看,理性时代似乎也暗示着人类文明衰颓的序幕。在这个意义上,维柯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并不是一个进步的东西,在他看来,人对无知和感性的胜利永远也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最多只能说是人对他在堕落中养成的恶习的一种不完全的升华。至此,人们自然会问,历史中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自由?如何才能避免人类社会的衰颓?维柯发现真正的荷马的巨大价值似乎就在这里,它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引起思考。
注释:
①Joseph M.Levine,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2,No.1.(Jan.-Mar.,1991),pp.55-79.
②克罗齐:《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王立志译,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3-131页。
③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
④⑤⑥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1、71、71页。
⑦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明竹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6-391页。
⑨Michael Mooney,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200-201.
⑩(11)Joseph M.Levine,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2,No.1.(Jan.-Mar.,1991),pp.55-79,55-79.
(1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3)克罗齐:《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王立志译,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3-131、165页。
(14)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
(15)《加姆巴蒂斯达·维柯先生的第二答复》,载于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张小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43页。
(16)意大利版《维柯著作集》中《新科学》第1406段,转载于马克·里拉:《维柯:反现代性的创生》,张小勇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263-264页。
(17)(18)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17-572、477页。
(19)[美]马克·里拉:《维柯:反现代性的创生》,张小勇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20)(22)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5、459-493页。
(22)英雄时代的权威和法律不是真理,也不是纯粹的确定性,而是真理与确定的混合物。克罗齐指出,维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确定性”这个词,虽然没有一致性,但“它们的所有含义都在一种与心灵的反思形式相区别的自发的一般观念中联结起来,毋宁说是混合起来。确定性在它的实践意义上意味着一种与意志的‘真理’相对立的其他事物。一言以蔽之,它就是与平等和正义相对立的暴力,与理性相对立的权威,与道德意志相对立的纯粹意志”。但“权威就是确定的形式,正如理性是真理的形式一样;同样,权威是理性的部分,正如确定是真理的部分一样”。——参阅克罗齐:《维柯的哲学》,柯林伍德译,陶秀璈、王立志译,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载于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张小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参阅维柯《论唯一原则》,转引自马克·里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第102-104页。
(23)Vico:The First New Scienc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on Pomp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NS49 50.
(24)维柯:《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维柯论人文教育》,张小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3-214页。
(25)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26)Vico:The First New Scienc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on Pomp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NS49 50.
(27)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28)Joseph M.Levine,Giambattista Vico and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2,No.1.(Jan.-Mar.,1991),pp.55-79.
(29)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8页。
(30)Leon Pompa,Human nature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Hume,Hegel and Vic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