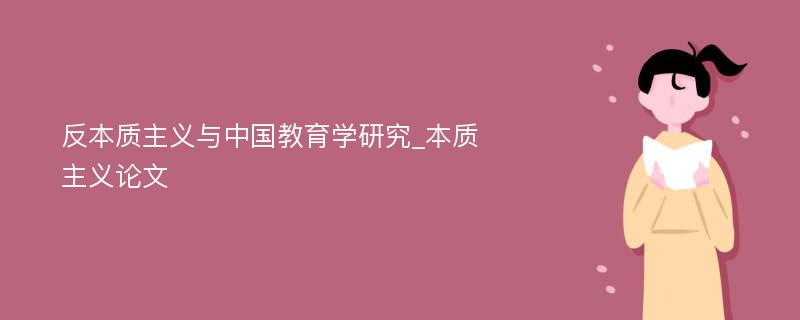
也谈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中国论文,也谈论文,本质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长期以来,“教育学是科学吗”这个让中国教育学者心痛已久的追问,使教育学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总是处于孤独的彷徨之中,既不能消解实践者隐性知识的抵触,也阻滞了后继研究者的热情。中国的教育学在“西西夫斯”的苦役中受尽煎熬。于是有学者要砸碎身上的枷锁,喊出了“教育学消亡”的口号[1];有学者要用“另一种言说方式”来解读鲜活的教育[2];有学者要从对“体系”的解构上建立起教育学的“问题”意识;有学者要从方法论的基石上开辟新的路径;更有学者对教育学的宏大叙事和本体追求进行哲学上的“挥泪斩马谡”。中国的教育学是进入了研究的“丛林”,还是开始了学派的划分?抑或是皈依了“现象”,无“学”存“术”了呢?
学科史让我们知道教育学胎生于哲学,而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就为“实体主义”和“现象主义”所左右,至笛卡尔“主客二分”以后,其两大流派的对峙就愈发尖锐,演绎出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攻击的西洋歌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两大哲学基石上又派生了诸多“主义”,如“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现代主义”、“工具主义”、“形上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价值主义”、“形下主义”等等,让人陶醉于概念的游戏之中,而遗忘了哲学“爱智”的天性。西方的教育学从赫尔巴特后分裂了,但它从西方哲学中汲取了少许的“求真”精神、“求善”品格、“求实”态度、“求美”风范、“求异”方法。两厢比较,中国教育学不但缺少如此科学与人文的辉映,而且是舶来品,是“借腹育子”,不但不是中国哲学的“亲生子”,而且是个多元混血儿。它既无“天人合一”的境遇化追求,也无“唐吉诃德”式的执着,更丢失了“中庸”而道的儒学命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学想回家,但不知道家的方向。
那我们研究教育的就看着教育学的式微而怨天尤人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要审视、要反思、要解构、要重构。但我们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知识论和认识论基础是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对20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影响有一个由大到小、由点到面、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逐渐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3],其结果是“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了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3],焕发教育学的生机活力就要“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本质主义”[3],因为它不但导致了教育学成为政治的下贱的婢女,也导致了教育学研究的“学霸”和“学阀”气焰。
二
我们找到了救命的稻草,那就是反本质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作为一股哲学思潮,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沉思,是对当下世界去魅性的剖解。“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对二元对立模式,在试图消解和弥平本质/现象、中心/边缘、确定/不确定等两极性关系上,尤其在质疑传统理论中的某些偏执与霸权上确有深刻之处。但后现代似乎只是反思了、解构了,它摧毁了一个旧的世界,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后现代主义者不屑也似乎没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因此,在欧美学界专事拆解而无力建树的后现代主义已越来越显出颓势”[4]。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认识上的路标,却无法在这个路标的指引下走上我们心仪的康庄大道。
中国教育学的痼疾是源于知识论和认识论上的先天营养不足吗?多多少少是的,也就是深受“本质主义”定势的左右,让我们在“头脑”的泥沼中挣扎。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教育领域,所谓的教育思想家一般都首先是哲学家,换言之,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纯正’的教育思想家,教育思想家的存在,即是哲学家于教育领域言论的‘影子’,这种‘影子’是教育领域异于其他领域的一种独有现象。是以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有什么样的哲学意识形态(笔者注:不仅是哲学意识形态,更是政治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即成型于这一影子之中。”[5]但波普尔所反对的本质主义似乎与我们的教育哲学家们信奉的不太一样。波普尔反对的是那种以“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或本质”[6]的本质主义。这里的本质主义曾为(也可能还会)人类认识世界提供强大的方法论基础。但我们对“教育本质”的反复拷问不是从教育学和教育现象本身出发的,而是政治意识的派生物,所以在中国教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以“穷理”为指向的本质主义,中国教育学的“‘本质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换言之,它乃是一种伪本质主义,有本质主义之名却无其实”[5]。
既然中国教育学研究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那我们还要反本质主义吗?当然要,因为他们虽是伪本质主义,但却衣钵了本质主义最应抛弃的一面,那就是先验性的预设和逻辑上的自慰。但我们反的不应是本质主义本身,而应是本质主义的方法论。我们可以假设教育没有预设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过程中体验教育、创造教育,但我们的体验和创造总要有个坐标吧,总要有个信念的支持吧。我们可以不去“钻营”教育是什么,但我们总应该“计较”教育为什么吧,否则我们会不会再次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呢?所以在反教育学本质主义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保留一点“对教育”的思考,而不能一味地去“为教育”而教育,我们已经尝够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苦衷,这种非此既彼的二元思维方式是不是过于“革命”了?况且我们还不知道要革谁的命,去救谁的命。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完整地看待事物。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注:关于教育思维中介的问题,毛亚庆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从两极到中介》中曾鲜明的提倡并鼓噪。),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7]“可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样也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但反对的目的在于建构,在于使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为中介”(甚至“亦此亦彼”),而不是一句“本质主义”就宣判了传统理论的死刑。其实这种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4]另外,我们的学者将“本质”“科学”“规律”“真理”作为四个孪生的范畴,又对列宁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的过程”进行了曲解,认为列宁试图找出事物的一级本质、二级本质、三级本质……,是个“剥核桃”的人,而不是一个“剥洋葱”的人。事实上,列宁所谓的“真理”“本质”是一个过程,强调的就是每种学说、理论都是历史的,都处于不断地发展的建构和完善之中,终极真理并不存在。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科学”的真义?是否如同科学之源的西方一样已经进入了“科学主义”的时代,进入了后科学境地?笔者认为未必。我国有教育学者也喟叹“没有科学,何来主义”,也有老先生执耳询问: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8]所以我们可以多点耐心,多点宽容,去让那些伪本质主义向真本质主义学点精髓,让那些反本质主义者也理清一下方向,要为我们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学知识基础。当下的中国教育学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发展的眼光对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极端化理论在内的一切理论进行清理、选择、扬弃、吸纳,以之为思想资源和学理参照,来建构既有对传统经典的继承,又力求解答“阐释”覆盖当下的新的教育理论。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学理论知识(我们说的是中国教育学,而非普通教育意义上的教育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不是太复合化思维了,而是太简单化描述了,不是学派霸权了,而是没有学派、没有争鸣,有的是“自命清高”和“同根相煎”,我们需要百花齐放,我们需要“各美各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9]。
三
如上所述,反本质主义以其强大的意识流在涤彻着陈腐的教育学话语体系,给教育学研究以巨大的认识论指向,我们是应该清理一下我们中国教育学躁动了百年的知识体系了,但清理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建构具有本土化的教育学知识基础。反本质主义仅在认识论上指明道路是不够的,还应在方法论上给出突破重围的出路,教育学是应有其自己的特别是中国化的文化性格,“是应根据一定的文化理想对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批判、辩护和重构”[10],但我们应知道这“一定的价值理想”从何而来。那么我们应用什么样的意识和行动去实践和实现这种价值理性?我们反思、批判不能停留在泛教育的层面上,不能只是口号式的批判,那只会导致我们游离于教育之外,导致一种无根基的“假批判”,这种假批判不仅不能促进本土化教育学知识的更新,反之,由于其虚假的性质往往可能导致人们对教育价值或教育真义的弃用。
笔者不想用“主义”这个抑贬抑褒的词来提升自己的拙见,只想用“意识”来阐明一些观点。教育学研究者应具有三大意识,即教育中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注:此处借鉴了劳凯声教授在北师大教育经济管理博士成立仪式的讲话中提到的三大意识,但内容与其并不一致。)。首先是问题意识,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虚荣且惨淡的教育现实,必须直面泡沫化的教育理论本身。从现实而言,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去看我们身边具体的问题,有发现问题的意识,有研究问题的耐性,有解决问题的欲望。就是说教育学的研究应走向教育政策的研究,教育政策的研究在此进行二维分野,一维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旨归,一维是以关注主体价值为支点,进行教育政策问题分析和教育政策价值分析,关注中国社会中具体的事、具体的人;从理论而言,就是要构建起以本土知识为核心的问题理论、情境理论,不再成为西方教育理论殖民化的产物,不再成为没有国史的教育理论,不再成为哲学的影子,从教育学的“失语”状态中走出来,建立起教育学自身的语用体系。其次是学理意识,我们不能以所谓的本质主义就否定了我们对教育问题逻辑上的拷问,事实上学者们所说的反本质主义,其立论基础仍借用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它和本质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只不过是同根共生的藤,研究教育不可能不关涉教育的价值、教育中生命的指向,不能不做“能做”和“应做”式的形上思考,不能不挑战传统的认识论和知识观,等等。这些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廓清有助于我们更结构化地看待问题(注:事实上,西方在对近代教育理论进行批判和省思时,不仅有后现代主义一个流派,还有结构—功能主义这个强大的科学主义流派的呼应。)。最后是方法意识,教育研究问题化、情境化、科学化和学理化就要求教育研究要以“复调”的方法进行“事理学”、“时代学”、“成人学”的研究(注:叶澜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论坛上的报告,2004年2月26日。)。笔者认为运用叙事研究有助于发现问题,有助于降解浮躁的研究心态,其研究的效度可以停留在一般教育实践者和初步研究者层面,欲穷问题的答案(此处不说问题的实质,以免有本质主义之嫌),教育研究者还应对此问题进行科学和哲学式的实验与思辨,还应把发现的问题继续进行定量的、定性的,特别是思辨(真思辨)式的探求。用这种复合的方法时间上可能是漫长的,精力的消耗是巨大的,所以要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合作共同体式的研究。进行复合方法的探索,不一定验证问题的普适性,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理智品格、学术责任、思想勇气与生存智慧”[3]。
据此,笔者认为中国曾有过所谓的“本质主义”,但那不是教育的自生物,而是政治的派生物,是一种“伪本质主义”,中国后来也出现了“真本质主义”,但不是太多,而是太偏,不是太深,而是太浅,不是太实,而是太浮。中国教育研究的“本质主义”并没有奠定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也没有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视野中。中国当前也需要“反本质主义”,但过犹不及,我们提倡最好以“生成主义”或“去本质主义”来温和地“挽救本质”。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教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教育本质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