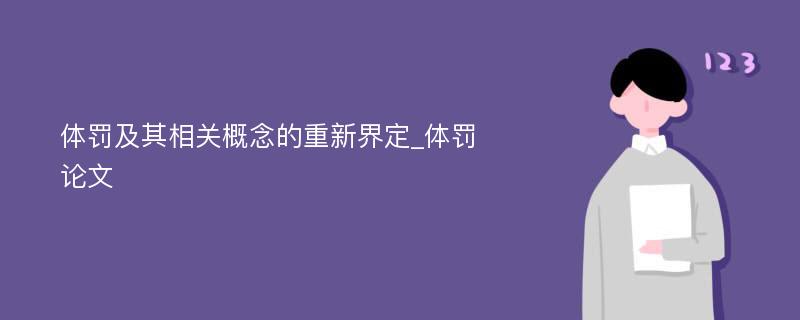
体罚及其相关概念的重新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相关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15)08-0010-04 一、体罚概念的界定 (一)体罚的概念 关于体罚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为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体罚”。这些界定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大体分为两类。之前对体罚的界定比较清晰,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提出,体罚是“用罚站、罚跪、打手心等方式来处罚儿童的错误教育方法”[1]。《辞海》将体罚定义为“成年人对小孩身体使用的惩罚,其严厉性从打手心到打屁股不等”[2]。《教育大辞典》将体罚解释为“以损伤人体为手段的处罚方法”[3]。这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比较权威的界定,都是把体罚界定为对孩子肉体的惩罚。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赋予了体罚新的定义,例如:但汉礼在《关于中小学体罚现象的比较研究》中这样定义体罚:体罚是指以损伤人体、侮辱人格为手段的处罚方法。[4]王洪明在《案例与评析:“校园惩罚”问题》一文中提出,体罚是以伤害学生的身体和心灵为手段的惩罚方法。[5]显然,这些学者把教育者对学生的人格、精神伤害也归入到了体罚的范畴中,原有的体罚概念外延扩大,于是“变相体罚”的概念应运而生。我们认为这样的界定从学理上、管理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它造成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分辨不出一般性的教育惩戒和精神上的惩罚的区别,从而在使用惩戒权时不能把握好惩戒的尺度。 (二)体罚的构成要素 体罚的构成要素是判断教师的行为是否构成体罚的关键因素。体罚的要素主要包括: 1.体罚的行为主体是教师。对未成年人的体罚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家庭内部的体罚;二是教育机构的体罚。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发生在教育机构的体罚,是在学校教育背景下教师对学生身体进行的惩罚。实施体罚的是中小学教师,受罚者是在校的中小学学生,因此,体罚的行为主体是中小学教师,行为客体是中小学学生的物质性人格权和生命健康权。 2.体罚的对象是学生的身体。体罚必须诉诸学生的身体,不论是以直接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在我国,由于对体罚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所以教师在惩戒学生时接触学生身体,比如推、拉学生中使其感到痛楚,都可能被认定为体罚。对于不诉诸身体的惩罚我们不应该认定是体罚,如罚款、语言羞辱、冷暴力等。有些学者把伤害学生的心灵、尊严等处罚方法也归入体罚,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在法学上,身体的伤害和精神的伤害是严格区别的。教师对学生的冷嘲热讽、当众辱骂等侵害学生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是属于我们常说的“心罚”的范畴,与体罚相对,因此,心罚应该从体罚的概念中剥离出来。 以学生身体的“痛楚”或“痛苦”界定体罚是不科学的。体罚肯定会造成学生的身体痛苦,不引起这些痛苦的惩罚则不是体罚,如罚写三遍错字或罚站两分钟等。有些非击打身体等惩戒措施,如罚站、罚写、罚背书等,有时也使学生感觉肉体痛苦或羞耻,但是这些措施被认为是教育的必要措施,因为这些痛苦或羞耻感能够唤醒并警觉学生认识错误,矫正其不良行为。在国外,有些国家是允许体罚的,但是这些国家对体罚中击打学生的身体部位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教师只能击打学生肉比较厚且神经比较多的身体部位,例如手心和屁股,这些部位很容易使学生产生痛感,而把握好度则不伤身体。但这些国家不容许教师击打学生的关键部位,如头、颈、胸、腹部、裆部,这些部位易造成身体伤害;也不允许打学生的面部、嘴,扯学生的头发、耳朵等,对这些部位的打击除了对身体的伤害外,对学生的精神伤害更大。 3.体罚的行为客体是学生的身体健康权。体罚超出了学生身体承受的限度而侵害了学生的生命健康是界定和判断体罚的关键因素。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实质不产生影响而仅仅使学生产生痛苦和羞耻感的惩罚行为不是体罚,我们将其归于一般的教育惩戒范畴,例如学生总写错字,教师为加深其对汉字的印象,罚学生抄写词语三五遍;学生经常迟到,教师为维持班级纪律,罚学生站两三分钟等。即使教师间接惩罚学生的身体,如罚站、罚跑、不让学生上厕所、不让学生回家吃饭等措施如果超出一定限度而危害学生生命健康也属于体罚。一般性的教育惩戒是以大多数学生的身体可接受并且不造成伤害为参考的,如在惩戒时,学生感到极度的疼痛或因疲劳而损害身体健康,或者学生被打部位出现明显的红肿、流血、骨折等状况,这便是超出了学生身体承受的限度,即损害了生命健康,这就属于体罚。 二、体罚或变相体罚与教育惩戒的区别 (一)体罚不同于教育惩戒 体罚不同于教育惩戒,它超越了正常的教育惩戒的范畴。教育惩戒是指具有惩戒权的教育主体对于具有不良品德行为的学生做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教育惩戒权是教育权力的下位权力,是学校与教师惩戒违反校规的学生的权力,是作为教师应有的一项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权力,它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教师通过对学生的身心施加某种影响,使学生感受到荣辱、对错、痛苦等,帮助其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增强为自己过失负责的责任感,从而达到矫正和教育的目的。在我国,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体罚,尤其是对所谓“变相体罚”的“零容忍”,教师的惩戒权在理论研究上被悬置,同时,由于适当的合理的教育惩戒也会被当成是体罚或变相体罚,加上学校和教师担心引起事故纠纷,所以教育惩戒在实践上被看作不合法而被取消。教师因头顶“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利剑威慑而不敢管学生,实际上这是放纵学生,对教育教学和学生的社会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前部分中小学生无法无天,社会上流行的暴力欺凌现象层出不穷,这与教育惩戒的缺失,与体罚、变相体罚的规定不完善密切相关。 体罚与教育惩戒有着本质的区别: 1.方式和手段不同。惩戒的方式主要包括心理惩戒和身体惩戒等。心理惩戒的方式主要有当众批评、心理暗示、与家长沟通等等,心理惩戒只要不造成学生生命健康的损害,我们不认为是体罚;身体惩戒主要有罚站、罚跑、罚学生抄课文等,身体惩戒只要不造成学生生命健康的损害,我们也不认为是体罚;体罚的方式比较单一,我们只认可对学生身体的惩罚才是体罚,它通过直接摧残学生的肉体使学生感到极度痛苦来达到教育效果。 2.程度不同。这是体罚与教育惩戒最根本的区别。二者虽然都是通过实施惩罚使学生感到痛苦来达到教育目的,但痛苦的内涵和程度不同。教育惩戒是通过对学生施以轻微程度的身体惩罚,使学生在惩罚中悔过自新,从而“不愿”再去犯错,并且教育惩戒遵循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体罚则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使学生惧怕皮肉之苦,从而使学生“不敢”犯错。体罚的程度一般都超出了未成年人身体承受的范围。[6] 为了使体罚的概念更为明晰,我们认为还应该采用早期的界定方式,可以将体罚定义为:在学校背景下,教师通过对学生身体实施击打,使学生肉体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的处罚方法。这种界定简洁明了,实践中易于辨析,并且能够跟教育惩戒和所谓“变相体罚”相区别。 (二)变相体罚不同于体罚 “变相体罚”的概念不明晰,不是正规的法学概念,变相体罚常指教师为了维持教学秩序,不直接对学生的身体诉诸拳脚和工具,而是间接地处罚违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使受罚者身心感到痛苦或者屈辱的惩罚方式。体罚伤害的是学生的身体,侵害的是学生的物质性人格权、生命健康权,而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来看,变相体罚侵害的是学生的精神性人格权,主要是隐私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体罚和变相体罚有以下区别: 1.作用的对象与影响不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体罚往往是作用在学生的身体上,通过对学生身体的摧残使学生感到极度疼痛或疲劳,从而来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变相体罚则是不直接伤害学生的身体,以侮辱的语言间接地对学生的身心施加影响,使学生感到屈辱,从而获得一定的教育效果。体罚学生直接摧残的是学生的身体,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发育,严重的会造成学生身体的残疾甚至会威胁到学生的生命;而所谓变相体罚的直接后果则是对学生精神和人格的伤害,常常会引发学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体罚带来的是显性的危害,是短暂的伤害;而变相体罚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是持续性的、影响深远的危害。[7] 2.性质与层次不同。虽然“变相体罚”的危害性不可低估,但是其行为本身大多属于道德范畴,而非法律范畴。面对屡教不改的儿童,家长或其他人员有可能不会拳脚相加,但是对其极端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不可避免,不能认为这种行为犯法。同样,教师对犯错学生的挖苦讽刺等行为虽然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但是还未达到违反法律的程度。尽管教师因其专业教育者的身份比其他非教职人员要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但因学生犯错误而对其进行责骂或采用其他具有不友好的非暴力行为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除非这种行为侵犯了学生的人格权或引起学生重大的伤亡。 将师德问题法治化使教师难以区分体罚、变相体罚和教育惩戒的界限,直接造成了教师不敢对学生使用正常的教育惩戒,也不敢开展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最终受伤害的是我国的教育。因此,应当将“变相体罚”这一概念废止,将部分师生冲突中双方身体接触但没有造成身体健康危害的行为归入教师正常施行的惩戒权;将非暴力但侮辱学生人格的行为列入侵犯学生的精神性人格权专列,并明确学生的精神性人格权的内涵、外延与加害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体罚的范围、程度 我们通过对国内外一些资料的研究、借鉴与参考,重新界定了体罚的范围、类型和程度。 (一)体罚的范围、类型 教师对学生的惩戒必须是轻微的,严重的惩戒则会构成体罚。日本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在必要时,校长及教员有权利对学生和儿童实施惩戒,但不得体罚。日本针对体罚的类型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侵害受罚者身体的惩罚,诸如殴打、踢等,是体罚;对学生的身体给予痛苦的惩罚,如长时间使其保持端坐、直立等姿势,是体罚;不让学生如厕,超过用餐时间后仍留学生在教室等造成学生肉体痛苦的行为,也属于体罚范围。日本还规定:教师不得剥夺迟到的学生进入教室的权力;在罚迟到者或偷懒者打扫卫生时,不得有过度要求;对于有偷窃行为的学生,教师不得强迫其自白或供述。[8] 教师体罚学生的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有时一种体罚方式也有多种罚法,我们将教师体罚学生的类型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直接过度责打学生的身体,如:打耳光、扯头发、揪耳朵、打臀部、让学生自打或互打,甚至在学生脸上刺字等。(2)让学生长时间维持特定的姿势,如:长时间罚站、罚跪、罚晒、罚半蹲等;罚站不仅仅指在教室中罚站,还有在烈日下、在暴雨中罚站,更有甚者,罚站还演变成了“金鸡独立”或“四足顶地”等。(3)让学生长时间从事剧烈运动,如:罚跑步、罚俯卧撑、罚单腿跳等;罚跑又分为穿鞋跑和赤脚长跑等。(4)让学生过度从事特定的工作,如:超负荷地罚写作业、抄写课文,罚过度劳动等。(5)长时间剥夺学生的生理需求,如:长时间不准学生吃饭、上厕所、午休而侵犯了学生的生命健康权。 (二)体罚的程度 教师的惩戒必须是轻微的,不得超出学生年龄段所能承受的范围。韩国颁布的《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认可了教师有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实施一定程度的体罚的权利,并对体罚的程度、方式等做了具体规定:体罚小学生、初中生,要用直径1厘米、长度不超过50厘米的木棍;对高中生,可使用直径1.5厘米,长度不超过60厘米木棍;教师不能用手或脚直接体罚学生;体罚男生,只能打臀部,女生只能打大腿部;在体罚数量上,初高中生不得多于10下,小学生不得多于5下,程度上以不在学生身体上留下伤痕为准。[9]在美国的一些州,体罚造成疼痛或微小的伤痕是合理的,这是教师的特权,但是体罚造成学生身体某部位的脱臼、深度青肿、流血、骨折等,就是过度惩罚且具有民事侵权性质;体罚学生禁止使用诸如刺棒或断木板等器具;体罚某个有潜在健康状况的学生而造成严重伤害时,教师不负有法律责任。[10] 我们认为,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时必须保持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陷入了体罚范畴。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以大多数学生的身体状况为参考,我们对体罚的程度、数量等作了以下界定:对学生体罚会使学生感到明显的疼痛感、疲劳感或不舒适感,甚至会造成学生身体残疾、长时间晕厥等。责打学生身体时,在程度上以留下伤痕为准,发红但不肿不起泡、微小的伤痕不属于体罚,而被打部位出现深度青肿、扭伤或骨折等,则都属于体罚的范畴;在维持特定姿势或罚学生运动方面,如罚站、罚蹲、罚跑步等超过一般性运动限度则属体罚,学生只感到轻度疲劳的属于一般的教育惩戒,而烈日下罚站、暴雨中罚站、“金鸡独立式”站立都是体罚;体罚中的罚抄是指罚学生抄明显超量的作业,比如罚抄词语、诗歌、课文等超过十遍以上等;在剥夺学生生理需要方面,如不准学生吃饭等超过一定时间,比如十分钟可归为体罚。 四、严控体罚,明确教育惩戒程序 教育中对犯错学生的惩罚在不伤害学生身体健康的范围内属于正常的教育惩戒。教育惩戒除了要程度适宜外,还应该坚持程序正当,否则就成了体罚。2002年,韩国的《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对体罚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体罚前教师要向学生讲清体罚原因;体罚前要检查学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必要时允许延期体罚;学生有以校内义务劳动代替体罚的权力;体罚时必须要有校监或生活指导老师的监督;体罚要避开其他学生。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也规定了体罚的程序:学年初,家长要和学校签订一份是否同意体罚学生的声明;当其他教育方法都无效时,教师才能实施体罚;教师不能在其他学生面前实施体罚;教师体罚学生要有证人的监督;与受罚学生有冲突的教师不能实施体罚;体罚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来实施;体罚要打学生身上肉多的部位。[11] 只有严格遵守教育惩戒程序,才能严控体罚。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定惩戒的程序,从而减少对学生的伤害。我们认为,教师在对学生的身体进行惩戒时,应当坚持以下程序: 1.教师惩戒学生前要向学生讲明理由。老师对学生进行惩戒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学生因违反纪律造成对课堂和校园秩序的破坏,学习态度不端正,不听老师的反复教导与训诫等。 2.教师直接责打学生身体必须是在其他方法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惩戒前应该坚持先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先提醒学生,给学生一个改正的机会,只有说服教育不起作用时才可以轻微地责打学生的身体。 3.教育惩戒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身心发展特点等因素来实施。对学生进行处罚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而且应该针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方式,个别学生有必要坚持不公开原则,以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此外,我国还应该考虑建立专门的惩戒学生的机构或部门,例如,美国部分州规定教育惩戒由副校长或教务主任实施,并且在班主任等专人监督下避开其他学生在专门地点进行。标签:体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