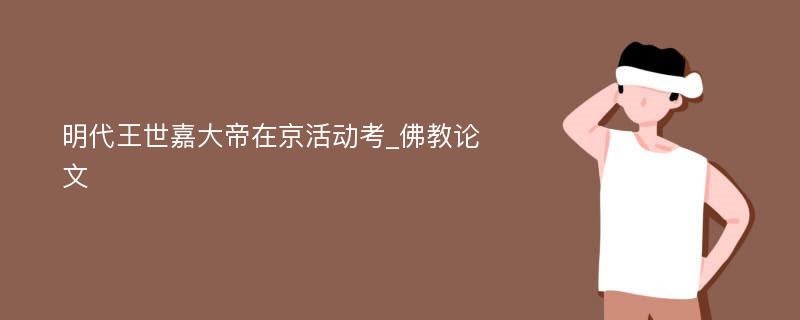
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北京活动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迦论文,法王论文,明代论文,北京论文,大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4)04-0091-07
明代大慈法王(1354—1439年),本名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高足弟子,是元、明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历史上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宗喀巴的近侍弟子,他跟随师尊参与了格鲁派创建前后一系列的宗教与社会活动,而且亲自主持修建了格鲁派第三大寺院色拉寺;作为一个格鲁派僧人,他勤学苦修,不仅精通格鲁派显教经典义理,更是擅长格鲁派的密法仪轨;作为一个应诏入朝的藏传佛教高僧,他谨遵师命,不辱使命,两番入朝,永乐朝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朝晋封“大慈法王”,对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特别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一个最早来内地的格鲁派高僧,他恪尽僧人本分,随处教化,在南京、北京、五台山及青海、甘肃等地区都留下了他弘法传教的印迹,为格鲁派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客观上也是对藏汉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藏汉民族的团结友谊做出贡献。
一、宣宗皇帝遣使致书礼请释迦也失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二次入朝经青海、甘肃抵五台山,在五台山驻锡传教约五年时间,其后应明宣宗皇帝邀请,前来北京,受到朝廷封赏礼遇。《清凉山志》中记载了宣宗皇帝于宣德二年(1427年)夏写给释迦也失的一封信函。内容如下:
“朕惟佛氏,道体冲玄,德用神妙,厥大无外,厥高无等。历代人主,罔不崇信。朕恭应天命,主宰华夷,体祖宗一视同仁之心,隆佛氏慈悲不二之教。追惟皇祖太宗文皇帝,皇考仁亲昭皇帝,鞠育深恩,如天罔极。欲举荐扬之典,一念之诚,夙夜倦切。惟大师功行高洁,定慧圆明,朕切慕之。特遣太监侯显,赍书礼请,冀飞锡前来,敷扬宝范,广阐能仁,以副朕诚。朕不胜瞻望之至。”[1]
从宣德皇帝这封信文,我们似乎又见到了那种御前大臣代笔的诏敕公文的文风,与成祖信函的平易体贴、缱绻情怀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它表达的是另外一种信息,这就是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仍会按照先祖特别是太宗(即成祖)皇帝的既定政策去做,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礼遇藏传佛教高僧,这是维护包括广大藏蒙地区在内的边疆地区安定团结的客观需要,是将先祖皇帝创下的这份“家业”继续维持并发展下去的客观需要。而代表格鲁派的高僧释迦也失不仅与永乐皇帝有多年的亲密联系,而且在五台山及甘青地区有重大影响,宣德朝若继续永乐朝的治藏政策,优礼藏传佛教高僧,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释迦也失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宣德皇帝果断迎请释迦也失来北京。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释迦也失在北京居留期间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及影响等。
二、释迦也失驻锡大慈恩寺
释迦也失应宣宗皇帝邀请前来北京,关于来京的时间,由于找不到明确记载,一般只言宣德九年(1434年)入朝而已。笔者根据汉藏文献零星记载,认为释迦也失来京时间大抵在宣德四年至宣德六年之间。如果说释迦也失圆寂时间是在正统四年(1439年),那么,他在北京驻留大约有八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释迦也失来北京后住在什么地方,一般都认为他驻锡于法渊寺,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日本学者佐藤长先生,见其所著《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根据是桥本所译妙舟《蒙古佛教史》中将藏文“a yan si”对译为“法渊寺”。[2]笔者考证这一对音应为“华严寺”,即五台山“显通寺”,此寺原名“花园寺”,所以认为佐藤长氏的说法有误,仅凭尚搞不清是否准确的对音就认定释迦也失住在北京法渊寺的结论实在缺少依据。但几十年来,人们对此未再深究,每言及大慈法王于宣德九年入朝,就会提到法渊寺,几成定论。
今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北有嵩祝寺街,即为原嵩祝寺遗址。嵩祝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嵩祝寺东面即为法渊寺,西面是智珠寺,以嵩祝寺规模为最大。
清代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对三寺情况有所介绍:“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3]而且,于敏中书中又引朱彝尊《日下旧闻》(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中原文:“……番经厂,念习西方梵呗经。凡有佛事,本厂内官易番僧帽,衣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日或三昼夜。汉经厂念习释家诸品经,僧伽帽,袈裟,缁色衣,与僧人同,惟不剃发耳。佛事毕仍易内臣服色。”
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直至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撰《日下旧闻》时,邻近内府库的番汉经厂依然如故,大约百年之后,于敏中等奉钦命作《日下旧闻考》时才补注,往日的番汉经厂于今已变成了三座寺院。当然,寺院中的僧人也是专职的了,不再是一会儿僧衣一会儿官服的内官了。
不用再著一字,可以断定,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绝不可能驻锡法渊寺,那时还没有法渊寺,他也不可能住在番经厂。
明朝初年,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及大护国保安寺。在这四所寺院中,释迦也失最有可能驻锡的是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位于北京什刹海西北,在明代嘉靖初年毁于火灾。据《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记载,该寺为金、元古寺,寺名多次改易,诸如“庆寿寺”、“双塔寺”等。明初时为“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改名大慈恩寺。[3]
大慈恩寺在毁于火灾之前一直是明代西藏僧人居京修持之重地,号“第一丛林”,皇帝亦曾“临幸”。[4]只可惜一朝毁于火灾,没有留下更重要的文物资料,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找到一些零星的内容。
言及释迦也失与大慈恩寺的关系,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大慈恩寺于宣德四年重建,并敕改寺名。在时间上与宣德初年诏释迦也失入京时间相吻合,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被加封为“大慈法王”,也似与“大慈恩寺”相照应。
2.大慈恩寺在宣德、正统年间位列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之首位,其首位之序应来自其驻锡僧人之地位。释迦也失是京城藏僧中地位最崇者,就是以后也未再出现可以与其相提并论者。
从《明实录》中也可找到一些佐证,如明正统元年朝廷议减在京诸寺番僧时,有记载:“减在京诸寺番僧。先是,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都纲、曰剌麻,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潆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潆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动,其余愿回者听,不愿回者,其酒馔廪饩令光禄寺定数与之。”[5]
从上述材料分析,京城诸番僧共有七个等级,除大慈法王外,其他都是对某一级别的称谓,而列于首位的大慈法王历史上并无第二人,也从不用作某种高级藏僧的泛称,就是释迦也失,大慈恩寺列京城藏庙首位,由此认定释迦也失居于大慈恩寺顺理成章。
3.释迦也失去世之后,其大弟子阿木噶也一直驻锡于大慈恩寺。成化年间大慈恩寺住持札实巴(bkra shis pa)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特殊关系也可提供一些佐证。
札实巴是明宪宗时期最受优礼的藏族僧人。《明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平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诏许之,不为例”。[6]其后不久,又被加封为“崇化大应法王”。[7]大应法王札实巴曾于成化九年呈奏朝廷:“陕西弘化寺乃至善大慈法王塔院,岁久损坏,乞敕镇守等官修筑城堡,如瞿昙寺制。”得到朝廷的批准。
札实巴之所以得知远在青海(明时青海地区属陕西布政司,奏章因言陕西弘化寺)的弘化寺大慈法王塔院损坏,是因此前,大慈恩寺灌顶国师端竹也失去河州办公务时去弘化寺查看过,回来后禀告大应法王。
至成化十年,大应法王札实巴圆寂,皇帝隆旨按大慈法王之例葬之。《明实录》成化十年三月庚子条云:“初,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中官遂请造寺建塔。工部言,‘大慈法王惟建塔未尝造寺,况今岁歉民贫,寺费难给,宜惟建塔’,上是其言,命拨官军四千供役”。[7]
从上述内容可知大慈法王与大慈恩寺是有直接关系的,先有灌顶国师去青海弘化寺查看大慈法王塔院保护情况,再有大应法王札实巴奏请朝廷采取保护措施,而后大应法王去世后又援大慈法王之例安葬,这些应不是偶然巧合。联系前面的二条理由,笔者认为释迦也失在京寓所即是大慈恩寺。
三、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主要的宗教活动
藏传佛教对北京地区的影响由来已久。在元代,由于蒙古王室崇信藏传佛教,不仅任用藏族僧人为帝师及宣政院高级官吏,也同时招徕乌思藏特别是萨迦派僧人长驻京都。据不完全统计,元朝皇室及贵族所建藏传佛教寺院有十余所,其中主要有:大护国仁国寺、大圣万安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永安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源延大寿寺、大永福寺等。从朝廷到民间,经常举办各种藏传佛教法事活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自永乐朝迁都北京后,明朝所实行的“多封众建”政策更使从藏区来京城的喇嘛僧人日益增加。《明实录》记载礼部尚书胡潆奏请朝廷裁减番僧,从宣德十年至正统元年就裁减了一千余人之多,最保守的估计,释迦也失在北京时,京城藏僧数量不减二千人。如此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喇嘛僧人,构成了明代京城文化内容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某些仪轨习俗也逐渐在宫廷内乃至民间流传、渗透。
据明人笔记记载:当时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都供奉藏传佛教佛像。由近侍司掌灯烛香火,万寿圣节及正旦、中元日于番汉经厂内悬幡设帐以“做好事”外,还要在隆德殿内“跳步吒”。[8]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等高级藏僧也会被经常召入宫中,传授皇帝以“密法”,他们口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他们出入寺院坐棕轿,朝廷派锦衣卫队执仪仗前导,达官贵人在街上遇见,莫敢不避路,宦官们见了一律行跪拜之礼。他们不仅能得到朝廷经常性的赏赐,而且每日膳食费用均由光禄寺支付,供养藏僧是朝廷每年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
释迦也失奉旨来京后,他自然成为在京藏僧的领袖人物,除了自身例行的修持外,更多的是要参与主持一些朝廷与各大寺院举办的法事活动。现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是助缘修建北京法海寺,其二是主持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荼毗法会。
明代修建的法海寺坐落在北京西郊石景山翠微山路之玉河,明时这一带又称为磨石口。关于法海寺的创建,现存有立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的两通寺碑详记其事,东碑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为明英宗时礼部尚书胡潆撰;西碑称《法海禅寺记》,为明英宗时礼部尚书王直传。[3]近年有学者在考察研究中发现在《法海禅寺记》寺碑之碑阴还记有藏族助缘僧人题名,其中包括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僧官、开山喇嘛等,兹将其碑记节录于下:
“敕赐法海禅寺助缘法王、尚师、国师、僧官、剌嘛、僧众官员人等。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释迦也失,妙法清修净慈普应辅国阐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哑蒙葛,弘通妙戒普慧善应辅国阐教灌顶净觉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净修弘智灌顶国师锁南释利、弘善妙智国师舍剌巴(下略)”[4]
这段碑记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从碑记中可知当年参与法海寺创建助缘的僧俗官员共计四百余人,而碑记中详记姓名者仅有18人,其中10人为当时在北京的藏族高僧,第一位便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释迦也失的大弟子阿木噶(碑文作“哑蒙葛”)位列其次。第三位是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dpal ldan bkar shis 1377—?),他是来自安多地区的藏族僧人,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就曾奉命赴乌思藏迎请噶玛巴大宝法王,以后又几次出使乌思藏,对朝廷实施“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做出过卓越贡献,景泰三年(1452年)明代宗晋封他为“大智法王”,关于他的事迹,笔者曾著专文,兹从略。[9]另外的几位开山喇嘛领占巴、扎失乳奴、扎失远丹等更是参加了建寺的全过程。
法海寺正式破土动工是在正统四年(1439年),于正统八年告竣。在京城众多的寺院中,法海寺算不上是大寺院,但它却具备三大特点:
其一,该寺是汉藏两族僧俗官员共同集资创建,并留下镌有汉藏助缘人士题名的碑刻作为历史见证,是汉藏合璧之杰作,这在北京寺院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其二,该寺大雄宝殿所绘九幅大型明代壁画,背龛后三幅为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像,正中水月观音像,丈余长线,一气呵成,富有表现力,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后殿门左右为佛教护法神二十天礼佛图,生动传神,个性鲜明。左壁的鬼子母像,酷似人间慈母;右壁帝释天,气宇轩昂;东西山墙描绘五方佛胜境,祥云缭绕,百花盛开,表现手法高超。全部壁画反映了明代早期融合汉藏佛教艺术精华之特色,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极为珍贵的遗产,法海寺因此成为以佛教壁画闻名于世的寺院。
其三,寺内现存有一口铸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的大钟,此钟上半部铸有梵文陀罗尼楞伽佛经、白伞盖咒(注:白伞盖:藏文称“gdugs dkar”,又译“大白伞盖佛母”,是藏传佛教密宗中重要的护法神,佛母尊有大威力,放光明,以大白伞盖为三昧耶形,以示覆盖一切众生之意,故此尊名曰大白伞盖佛母。据藏文经典,其缘起为:六道中之阿修罗所居地——非天与天界相隔处生有一树,天人若有所求,向此树祈愿能如其所望,阿修罗众见天人有此福报,大起瞋恨,聚众攻打天人,天人偶有不敌,帝释往求释迦牟尼佛加持,佛化为白伞盖母,千面千臂巨大伦比,阿修罗众惊避奔逃。本尊形相有一面二臂、三面六臂或千百千臂。手中最主要法器为伞盖,高僧遮阳之物,列为七珍八吉祥之一,表达离邪念,佛之净德覆盖一切。参见《佛教法象真言宝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6页。)藏真颂等二十余种经咒,其经题为汉文,经咒为梵文,乃为研究经咒的珍贵实物。[4]
释迦也失主持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荼毗法会是在宣德十年六月,即释迦也失受封大慈法王一年之后。这位智光和尚也是京城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1402年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派遣僧人智光携带诏书,“晓谕馆觉、灵藏、乌思藏必力工瓦、思达藏、朵思、尼八剌等处,并以白金、彩币颁赐灌顶国师等,凡白银二千二百两,彩币百一十表里”。[10]正是在智光入藏之后,明成祖进一步了解到噶玛巴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在馆觉等地的活动情况,便决定召请年仅二十岁的噶玛巴到京会见,从此使明朝既定的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得以一步步施行。智光和尚也以其不同寻常的贡献而得到三朝皇帝的赏识信重,永乐朝即封为国师,擢升为僧录司善世;仁宗朝又加封为大国师,并命居大能仁寺;宣宗朝再加西天佛子之号。[11]
关于智光和尚居大能仁寺事,《日下旧闻考》中录有胡潆《大能仁寺记略》:“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其殿堂楼阁,高明宏壮,像设庄严,彩绘鲜丽,禅诵有室,钟鼓有楼,庖湢库庾,幡幢法具,靡不完美。”[3]
智光和尚于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示寂,享年八十有八,僧腊七十三。智光临终前日颂偈辞:“空空大觉中,永断去来踪,实体全无相,含虚寂照同。”随即俨然坐化,三日入龛,又三日掩龛,举体柔和,容貌如生。荼毗之日,大慈法王亲自秉持法炬,置于薪龛之顶,“智火迸出,五色光明,化毕,骨皆金色,舍利盈掬”。[3]智光和尚的弟子分其舍利建塔寺多处,其荼毗之所亦建塔寺,名曰西域寺,在北京阜城门外,早已颓圯。
四、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圆寂
关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圆寂的时间和地点,正史缺载,总结汉藏史料的记载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1.宣德十年(1435年,藏历木兔年)寂于返藏途中。
这种说法在各类藏文材料中都可以见到,是在藏地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主要来源于格鲁派教法史籍《大慈法王传》、[12]《噶丹教法史》和《黄琉璃》。后世学者如东噶·洛桑赤列也持此种意见,在新近出版的《东噶大辞典》(藏文)中的大事年表藏历木兔年(公元1435年)条记: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从北京返归西藏的途中,在卓木喀(mdzo mo mkhar)地方示寂,堪布释迦楚臣(shvakya tshul khrims)在其地为大慈法王修建了寺院。[13]
在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也是按这一说法叙述的:
“此后,大慈法王又受到明朝永乐皇帝的邀请,因此他在任命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曲杰达吉桑波担任色拉寺的法台后,于公元1424年即藏历第七饶迥木龙年前往内地。当大慈法王抵达京城皇宫的附近时,永乐皇帝去世了。永乐皇帝的儿子宣德皇帝比其父亲更加礼敬大慈法王。大慈法王又在内地居住12年建立事业后,他安排自己的侍从聂塘巴国师阿木噶和曲杰索南喜饶二人作皇帝的上师,他自己动身返回西藏,在途中走到卓莫喀(意为犏牛城,在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的转导乡)地方圆寂,当时是他82岁的公元1435年即藏历第七饶迥木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大慈法王圆寂后,由许多善知识大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超荐法事。在被称为‘厂房’的地方,由国师贝丹巴为首的许多善知识大德和大臣、官员、军官等,聚集僧俗人众,火化了他的遗体,在当地为他修建了安放遗骨的灵塔,大慈法王的亲传弟子释迦楚臣还在当地兴建了一座寺院(该寺汉文称宏化寺)。[14]
这段文字中将明宣宗皇帝误记为明成祖之子,一些藏文史籍在涉及汉地皇统世系时常有舛误。
关于大慈法王示寂之具体日期,《大慈法王传》中为木兔年的十月二十四日,这一日期在藏文资料中是没有分歧的。上述《藏族通史——松石宝串》中十月二十二日的说法应该是笔误或系翻译印刷时出现的错误。因为直至现在,整个藏族地区,每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大师忌辰(十月二十五日)“五供节”的前一晚上要举行“四供节”的活动,就是纪念这位为藏汉民族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2.宣德十年在北京示寂,灵骨运抵卓莫喀安葬说。
比起前一种说法,关于此种说法的记载少得多,主要见载于《安多政教史》,该书引《黄琉璃论》中所言:“法王赴内地的途中,曾预言若在这里(指卓莫喀——笔者注)修建寺院十分吉祥。当在内地迁转佛土,遗骨运回西藏时,马车在此陷入泥沼之中,无法前行。于是忆起往日的授记,永乐(应为宣宗或英宗——笔者注)皇帝乃在此修建了一座城池,兴建了灵塔等许多依止物。留大弟子森格桑波(sang ge bzang po)在此住持。”[15]
另外,该书又援引一位名叫圣·噶登嘉措的话:“大慈法王享年八十二岁,木兔年(公元1435年,明宣德十年,乙卯)十月二十四日圆寂。遵循皇帝旨意,由曲结索南喜饶(bsod names shes rab)、曲结森格桑波两人将灵骨塔迎至犏牛城,建造了神圣的佛殿供养。接着修建了比丘伽蓝,至今昌盛不衰。”[15]
3.于正统四年寂于北京说。
这种说法更少,连《安多政教史》也都没提到。这种说法详见于《循化厅志》,《河州志》及《厅卷》等方志中亦有相应记载。兹录《循化厅志》中援引《厅卷》相关记载如下:
“雍正四年鸿化显庆二寺世袭国师张洛住坚错呈:明永乐十二年差太监侯显诣乌思藏请大慈法王,路由河州,其从张星吉藏卜跟随入京。正统四年法王圆寂,敕建渗金铜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赐名鸿化,随给附近之高山穷谷永作香火之需,高官僧五十五名。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给国师、禅师之职。”
《循化厅志》对上述记载又做解释,按语言:“正统元年,礼官奏汰番僧,命大慈法王如故,史不言其所终,盖座于京师如《厅卷》所言。”(注:《循化厅志·原循化厅寺院》,转引自谢佐等著《青海的寺院》附录三,青海省文物管理处印,1986年,第151-152页。原文标点错误较多,所引文字系笔者重新标点。)
对于上述几种说法,笔者无法回避,也不应做简单的并存了事。笔者以为《循化厅志》中关于正统四年大慈法王在北京圆寂的说法更为可信。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关于时间问题。笔者曾在上文提到,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朝臣曾议裁减在京番僧事,历数在京藏僧有七等级,其首位便是大慈法王,礼部尚书胡潆奏请再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等寺院藏僧四百五十人,英宗降旨: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师还按原来待遇,其他人去留听便,继续留住者,光禄寺将限量供应他们的膳食费用。如果说大慈法王已于一年前返归乌思藏并已在途中示寂,与《明实录》中这条记载的矛盾无由解释。当然正史记载也有错误不实之处,特别是在记载民族地区或外蕃历史时,这种情况更会多些。但在记载朝中大事时,虽常有因故回避讳饰缺漏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与事实完全相违的重大错误。大慈法王就住于北京,他辞归之事也许会漏记,但不会已经离开了或去世了还完全不知道或假做不知,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上文中提及的大慈法王助缘修建法海寺事,法海寺也是在正统四年动工,助缘事是在正统初年开始运作,《法海寺碑记》助缘名单上明确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列在首位,虽然也可以将此事解释为其大弟子阿木噶代师助缘,但不是更缺乏根据么?
关于地点问题。笔者注意到了藏文材料记载关于释迦也失圆寂地点的分歧,一般说来,西藏地方多持返藏途中寂于卓莫喀,而安多方面则持在京圆寂,奉皇帝旨意在卓莫喀地方建寺安葬。
笔者在《安多政教史》中还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记载,其内容大意是一位出生于清雍正年间名叫强巴格勒坚参(byams pa dge legs rgyal mtshan)的安多高僧,此人曾在拉萨色拉寺求学并考取第一等级拉然巴格西,在其年长后将堪布职位让与弟子,自己以一遁世者身份云游安多各地静修圣迹。当其弟子前来看望他并希望他回原来寺院转世时,他说道,色拉寺的喇嘛死在内地,因没有自由,不再转世;如果有自由,更是不再转世,不会再来到这个动乱的世间。[15]这位高僧所说的“色拉寺喇嘛”就是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从这些记载我们知道,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在什么地方圆寂,还是关乎转世的大事。而在安多地区,大慈法王寂于北京已是不争之事实。
释迦也失的生平事迹牵涉广泛,各种藏汉材料记载既有欠详细,又多有相互矛盾之处。但笔者以为对于各种记载的判断还是有一个大体上的原则,其在西藏本土时的历史大多以格鲁派教法史及大慈法王传为主;其在内地活动及入朝受封入贡等史事应以正史记载为主,辅以藏文史传材料为参考佐证;其在五台山、青海等地情况则应以地方史志记载更可信些。
而《循化厅志》中这样重要的记载,长期以来却几乎完全被置于忽略不计的状态。《厅卷》等方志的成书时间虽与大慈法王时代相隔很远,但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值得注意,那就是释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时,路经河州,从那时起便有一个来自河州的叫张吉星藏卜的随从一直跟随他入京,此人出生于河州藏汉杂居地区,因随汉人习俗,也有汉姓,当然也不排除为藏化汉人的可能。释迦也失在内地,身边需要有一个藏汉兼通的随从。张吉星藏卜之徒裔后人也被封国师、禅师,并且住持鸿化寺及其属寺显庆寺,这是一条重要的没有间断的线索,张吉星藏卜一直跟随释迦也失,又汉藏兼通,对大慈法王的行踪应是最为熟悉之人,来自他的后人的记载应更可信。而且,不论如何,大慈法王最终的归宿是在青海宏化寺,青海地方志就是最直接的参考资料。根据以上这些理由,笔者认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圆寂于北京。
标签:佛教论文; 大慈恩寺论文; 明代皇帝论文; 藏传佛教论文; 安多政教史论文; 明实录论文; 日下旧闻考论文; 格鲁派论文; 智光论文; 法海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