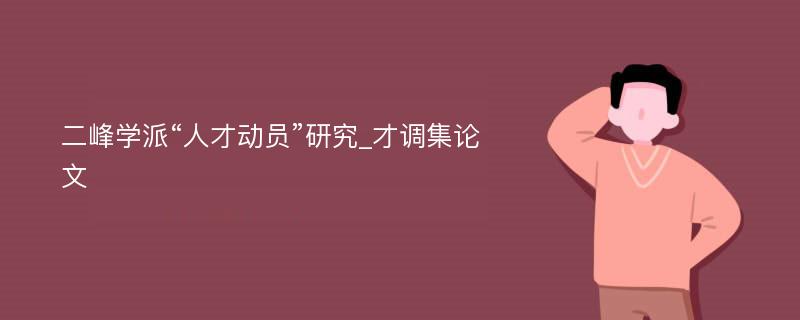
二冯校本《才调集》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才调集》①十卷,蜀韦榖编,“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不论作者世次、声名,兼收初、盛、中、晚唐各家,且每卷收选人数不等。据垂云堂本目录所载,收入有姓名者193人,无名氏2人,共计195人。其中重出者为16人,实际收选179人。在现存唐人选唐诗各本中,数量最多。从《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诸家书目著录情况和诗话中的称引情况来看,《才调集》在宋代就流传很广。南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卷一并卷六至卷十皆补配清抄本),至今犹存,藏于上海图书馆。明清之际,更是掀起一股校勘、评点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且影响最广的当属冯舒、冯班兄弟。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各大图书馆藏目录,与二冯有关的版本主要有四种:
1.明刻递修本,佚名录徐玄佐,清冯班、陆贻典批,辽宁省图书馆藏。
2.明刻本,佚名录明冯舒、清冯班批点,湖北省图书馆藏。
3.明刻本,怀古堂藏板,录有冯舒跋文一则,国家图书馆藏。
4.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垂云堂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各大馆均有藏,并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四本之中,怀古堂藏本仅录冯舒跋语一则,归属存疑;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和湖北省藏本之评点均为过录;垂云堂本经冯舒、冯班从子冯武审阅辑刻,较为可靠,而且此本前录韦毅《才调集》原叙和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集后录徐玄佐、冯舒、冯班、陆贻典、钱龙惿、钱谦益、汪文珍跋语七则,详细说明了《才调集》的刊刻、传阅、抄录、残缺、增补、重录等流传情况,价值最高。故本文主要依据垂云堂本,并参考其它三本,略述怀古堂藏本跋语的归属问题和冯舒评本、冯班校补本的参校本以及垂云堂刻本的底本问题。
一、国家图书馆藏述古堂藏本之跋语的归属问题
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刻,怀古堂藏板《才调集》,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白口,无鱼尾,左右双栏。书名页有跋语一则,云:“《才调集》向少刻本,万历闾邑中沈氏始付之梓,惜为俗子所窜,伪谬实甚。今取沈氏原刻,一仍宋本,并集状元徐玄佐抄本校正,凡汰去讹字二千二百余字,重经新刻者三十二板,此本庶为完书矣,识者拜上。”
书名页后有冯舒跋语一篇,云:
《律髓》之诗,大历以后之法也,大略有是题则有是诗。起伏照应,不差毫发,清紧葱倩,峭而有骨者,大历也。加以骀荡,姿媚于骨,体势微阔者,元和、长庆也。俪事栉句,如锦江濯彩,庆云丽霄者,开成以后也。清惨入骨,哀思动魄,令人不乐者,广明隆基也。代各不同,文章体法则一。大历以前,则如元气之化生,赋物成形而已。今人初不识文章之法,谓诗可作八句读,或一首取一句,或一句取一二字,互相神睈,岂不可哀。曾读《律髓》,以此法读之,今纯以此法读此诗,信笔书此。且诗之为物,无不可解,《关雎》、《鹿鸣》,首尾通畅,只因误解“秦时明月”四字,遂生多少梦寐,学诗者不可不破此关,不可以自落此鬼蜮。丁亥(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廿二日孱守老人(冯舒)识。
此篇跋语垂云堂本署名为“钝吟老人”,垂云堂本底本为冯班校阅本,此本乃为过录本,则垂云堂本更可靠。纪昀《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亦署名为“钝吟老人”,而且与《才调集》冯班的评点更合,所以此段跋语当为冯班所作。
二、马舒校本和冯班校补本的参校本
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三年汪氏垂云堂刻本,卷末冯舒跋语,曰:
万历三十五年(1607)借得研北翁孙氏本,即沈氏所刻之原本也。沈本为俗子所窜,伪处不可胜乙,崇祯壬申(1632)严文靖曾孙翼馆于余家,携宋本至,前五卷为临安陈谢元宗之家刻,后五卷为徐玄佐录本,始为是正,又从钱宗伯假得焦状元本,亦从陈书抚写,与孙本不殊。焦本尽改“娇娆”为“妖娆”,可当一笑,今悉正之。乙亥(明崇祯八年,1635)夏孱守居士记。
冯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借得孙研北抄本,崇祯壬申(1632)借宋本前五卷和徐玄佐本后五卷,并从钱谦益处借得焦竑写本,校正了沈春泽本,时为明崇祯八年乙亥(1635)。也就是说,冯舒校本为以沈本为底本,参校了孙研北抄本、徐玄佐本和焦竑抄本。
冯班跋曰:
崇祯壬申假(1632)别本于宗伯钱公,盖华亭徐氏旧物也,卷末有跋语云“失后五卷,借抄本于钱伏正氏写补之”。戊寅洞庭叶君奕示余抄本,首尾缺损,聊为装之,线缝中有题记云“万历丙戌钱伏正重装”,始知即徐氏所借也,中脱一叶,徐亦仍之。是岁十月得赵清常录本为补完。冯班记。
是岁冬,江右朱文进中尉寓吴,有宋本,介郡人邵生借之不可得,携本就勘,颇草草。朱本亦残缺,却有第九、第十卷,唯第八卷全失,而叶本第六卷独完好,惜第七卷“薛逢”以下不复存,参以抄本始具,命之重写,因记。冯班。
冯班于崇祯壬申(1632)从钱谦益处借得徐玄佐抄本,戊寅(1638)从叶奕处得钱伏正重装残宋抄本,此本中间脱失一页,徐本此页亦脱,遂于十月据赵清常抄本(存后四卷)补录。同年冬冯班又借得朱文进藏宋刻残本,虽缺第八卷,然有第九、第十卷。冯班遂据钱重装本、赵清常抄本、朱藏宋刻残本校补完徐玄佐本,并命人重新书写。
那么二冯参校的这几本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钱龙惿跋,曰:
右沈氏所刻《才调集》,原本不甚伪,为不知书人铲改,殆不可读,今为改定千余字,重梓者廿余叶,皆以临安陈本为正。凡得别本六:徐本得前五卷,叶本得第九卷,朱本得第九、第十卷,焦状元、钱复正、孙研北三抄本皆完具无缺,第八卷未有宋版,取以补之抄本,行墨如一,皆出于临安,又赵清常本仅后四卷,不知所自,亦旧物。
徐文敏本前五卷,朱藏宋刻本第九、十卷,焦竑抄本,钱复正抄本,孙研北抄本以及赵清常本(残存后四卷)皆源自宋临安府书棚本。
再看徐玄佐刻本的底本情况,徐玄佐跋,曰:
先君文敏公素有此书,盖宋刻佳本,惜分授之时,匆忙失简,逸去其半。后逾三十年,幸交符君望云,获闻其亲钱复正氏有抄本家藏,因而假归,特嘱知旧马公佐照其款制,摹以配之,共计一百有六幅,凡二千七十三行,装池甫毕,展卷焕然,顿还旧观矣。
则徐玄佐刻本以朱文敏家藏宋刻本补配钱复正抄本,而钱复正抄本出自宋临安府书棚本。徐本底本搞清楚了,再来看沈春泽刻本的底本,陆贻典跋,曰:
沈刻原本系邑人研北孙翁家藏,沈与善,因假此,并《弘秀集》合梓之。按二书俱本临安刻版。
沈刻本原本即孙研北抄本,而孙抄本直接来源于宋临安府书棚本。
通过钱龙惿、徐玄佐、陆贻典三人的跋语,已经大致理清了《才调集》的版本源流:一,徐文敏本、钱复正抄本、焦竑抄本、孙研北抄本、赵清常抄本、朱藏宋刻残本皆出自宋临安府书棚本,则《才调集》的版本源头为一即宋刻书棚本;二、诸本之中,焦竑抄本、孙研北抄本为完本,其余各本皆残缺不全:钱复正抄本缺一页、徐文敏家藏宋刻本仅存前五卷、朱藏宋刻本残存后两卷、赵清常抄本残存后四;三、明嘉靖中书棚本缺失,仅存前五卷,徐玄佐据钱复正抄本补完后五卷,于万历十二(1584)刊刻,并仍钱本缺失一页;四、沈春泽刻本以孙研北本为底本。
是以冯舒参以校定沈春泽刻本的诸本中,孙研北抄本和焦竑抄本直接来自宋刻书棚本,徐玄佐本前五卷为残宋刻书棚本,后五卷据钱伏正(亦作钱复正)抄本补入。冯班所见诸本中,钱伏正抄本、赵清常抄本、朱文进藏残宋本均源于宋刻书棚本。徐玄佐本前五卷来自书棚本,后五卷来自钱伏正抄本。徐本与钱抄本皆缺一页,钱本并第七卷“薛逢”以下均缺;赵抄本仅存后四卷;朱藏本缺第八卷。于是冯班据赵抄本补入钱抄本和徐玄佐本中间均脱佚的一页,又据朱藏宋刻残本(卷九、卷十)和赵清常抄本补完钱抄本缺失的后四卷(第八卷,朱藏本缺),补完后又命人依据旧式重为书写。
虽然二人校勘之底本和参校本有所不同,但二人尽可能参校所能亲见之本,且诸本皆出自宋刻书棚本,来源为一,所以冯舒校本和冯班校补本在后出诸本之中价值最高。傅增湘先生曾曰:
同时海虞冯巳苍及定远,笃嗜此集,与叶石君(树廉)、陆敕先(贻典)诸人寻求旧本,匡谬正伪,俾臻完善。康熙甲申,新安汪文珍访诸后人,获其遗迹,为之授梓,并刊二冯评点,以示学诗之指的。记其先后访得者,华亭徐文敏家、江右朱文敬中尉家宋刊残本,钱复真(又作伏正、复正)、焦弱侯、赵清常、孙研北四家抄本,改正沈刻至千余字,其所据依,皆出临安陈氏书籍铺本也。②
现冯舒校本和冯班校补本无缘得见,故只能从版本原流之角度,大致窥探二本之善,甚为可惜。
三、垂云堂刻本之底本
所幸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均藏有康熙四十三年新安汪文珍氏垂云堂刻本《才调集》。汪文珍叙述刊刻始末,曰:
近日诸家尚韦榖《才调集》,争购海虞二冯先生阅本,为学者指南车,转相摹写,往往以不得致为憾。甲申春,余获交钝吟次君服之冯丈,始知汲古阁毛氏所藏,钝吟手阅定本,默庵评阅附载其中。丹黄甲乙,各有原委,其从子简缘先生实能道其所以然。因托友人假汲古阁所藏,并影写宋刻,取沈刻暨钱校本,重加校雠,而乞例言于简缘,遂谋登梓。
可知,垂云堂本以汲古阁所藏,附有冯舒评语的钝吟手阅订本为底本,并影写宋刻,参校钱允治校本。
傅璇琮、龚祖培两位先生称垂云堂本以:“有二冯批校语之本(可能就是冯舒校正的沈本)为底本,以影宋本、钱校沈本参校新刻一本,是一个精校本。”③顾玉文云:“在现在常见的几个版本中,垂云堂本广参汲古阁本及二冯手阅定本及其它各本,其文字最优。”④刘浏先生以白居易《代书一百韵寄微之》为例,列表对勘四部丛刊本、垂云堂本、汲古阁本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南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得出结果为:“垂云堂本是在忠实于《才调集》原本的基础上,对文字明显错讹处作了改动;而汲古阁本则依据传世白集对《才调集》原文作了相当多的改动,而类似改动,非止白居易一家,余皆如此,可见汲古阁本已经背离了《才调集》的原貌。因此,垂云堂本在《才调集》历代诸本中当为最接近宋本原貌的本子。”⑤都不同程度的肯定了垂云堂本的文献价值。
然对于垂云堂本的底本,大家却持不同意见:傅璇琮和龚祖培两先生认为,垂云堂之底本即二冯批校之本为冯舒校沈刻本;刘浏先生则认为“垂云堂本是以汲古阁藏影写宋刊本(附二冯评阅)为底本。”⑥试分析两种提法,如下:
首先,前文已经指出冯舒校本是以沈本为底本参校了徐本、孙抄本和焦抄本,如垂云堂本以冯舒校本为底本,冯武就不会有:“沈雨若刻本舛错纰缪,不可穷诘,幸钱求赤多方求购影宋抄本,历三处而得全”⑦之语了。
其次,冯舒校本是校沈刻本;冯班校补本是以钱抄本为底本,参校徐本,又据赵抄本补录钱抄和徐本俱脱之页,并据朱藏宋刻残本(第九卷、第十卷)、赵抄本补完后四卷。即冯舒校本之源为孙抄,冯班校补本之源为钱抄,二者虽都源出宋刻书棚本,但并非一个系统。
再次,汪文珍言垂云堂本底本为“钝吟手阅定本”,则此本当为冯班阅本,冯舒评点只是附载其中。至于默庵之评点是冯舒手书还是别人过录,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垂云堂本依据的汲古阁藏二冯评本为冯舒校沈本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为冯班校补本。
综之,冯舒校本和冯班校补本参校了当时所能见各种源自宋本之抄本,在《才调集》校本中价值最高,惜版本之缺失,我们无法知晓二本之差别,亦无法考证二本如何精善。幸垂云堂刻本吸收了冯班校补本的优秀成果,并参校钱允治校本,在现存刻本之中最接近《才调集》原貌。而且二冯的评点刊刻其中,极好地保存了二冯的评点体例和诗学观点,这为我们研究二冯的文学思想以及二人对《才调集》的传播与接受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①关于《才调集》的版本,傅璇琮、龚祖培,《才调集考》,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61-165。刘浏《〈才调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章《〈才调集〉编者及版本研究》均有详细的论述。对本文的编写启发很大,在此表示感谢。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945-946。
③傅璇琮、龚祖培《才调集考》,《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63。
④顾玉文《韦榖〈才调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
⑤刘浏《〈才调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8年12月,页51。
⑥刘浏《〈才调集〉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8年12月,页48。
⑦冯武《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凡例》,清康熙垂云堂刻本。文中引用之跋语未注明出处者,皆出此本,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