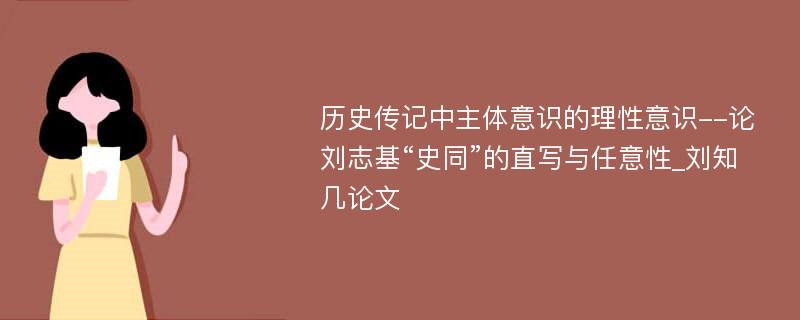
史传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刘知几《史通》中的直笔、独断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笔论文,主体论文,自觉论文,理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71(2002)05-0043-05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 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他在长期修史、精研史学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传 理论专著《史通》。
《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 九篇,外篇十三篇。因内篇三篇亡佚,实存四十九篇。所涉内容,包括史籍源流、体例 、编撰方法、史官建置沿革以及各类史书得失,可谓全面系统,博大精深。宋代黄庭坚 曾把《史通》和《文心雕龙》并称,认为书中“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清 人黄叔琳谓《史通》“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因此,《史通》 可说是我国第一部史评和史传文学的理论著作。
直笔:“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
直笔是中国古代史官自古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直笔就是秉笔直书,书法无隐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史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作为衡量一个优秀的史官必须 具备的条件。《左传》中记载的两件事情足以说明这一点。
其一,《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 。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记载了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等人的事迹,体现了作者对“书法不隐” 的良史的赞颂。后来刘勰称赞说:“辞宗丘明,直归南、董。”[4]北周史家柳虬慨叹 :“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因此直笔的原则,实为古代史家记史的原则,秉笔直书的精神,成为古代史家提倡的一 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成为史传批评的最高标准。
后代被称为“直笔”榜样的是《史记》。扬雄称“太史迁实录”。班彪论司马迁说: “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7]班固则称: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8]这些评论,都肯定了司马迁 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司马迁主要从下面两大方面来体现实录精神的。 第一是“考而后信”,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司马迁用这些史料与古籍 互相参证,弥补了旧史的许多缺漏,纠正了传闻旧说的不少偏颇。这种“考而后信”的 原则增加了《史记》的可靠性。第二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迁不仅对先秦帝王敢 于善善恶恶,毫不隐晦,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揭露汉代统治者的阴暗面。
在唐代,一方面,在强大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史官的记注、撰著皆要适应现实政 治风向。另一方面,由于上古政教合一的史官制度在唐代史馆中的重演,使得刘知几把 史家的理想形象确立为“道”的化身,他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利,并对之进行监督和评判 。《史通》“直笔”论就标志着这种“以道自任”的史家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
刘知几把儒家人伦纲常抽象上升为客观永恒的“道”,它不以现实政治的利害为转移 ,凌驾于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权势之上,乃是常伸于天下万世的公理正义。《史通》之 “直笔论”就是要求史家在史传的修撰中完全排除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以“道”为惟 一的客观标准记述和评判历史,从而写出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千秋金镜”,“直笔 ”的精神实质,不在于力求恢复历史本身全貌的客观科学态度,而是不屈于权势,“直 道而行”的道德勇气:“若南、董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沉魏书,假回邪以窃位; 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未曾喻足高下也。”——“以道自任”成 了赋予史传作家以独立人格的高尚理想,闪烁着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道德 光辉。这都是我国古代史传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传的 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论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家 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直笔而 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到:“南史抗节,表崔杼之 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 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
《史通·载文》篇中说到:“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禧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 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又说:“至如诗有韦孟《讽谏 》,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 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 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刘知几极力赞赏这 些作品,因为它们都言之有物,能够“不虚美、不隐恶”,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发 挥了美刺作用。
刘知几既然提倡直笔书法的求实精神,必然反对那些任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史传 作者。刘知几撰《史通》,有“直笔”、“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 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刘知几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 ”、“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 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 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 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 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 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惑经》篇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多 为贤者讳,有惭良史。”《曲笔》篇又说:“夫以敌国相仇,交并结怨,载诸移檄,则 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也。”《采撰》篇又说:“夫 郡国之记,谱牒书之,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 乎!”这样,便使回护之辞,攻顸之笔,充塞于旧史之中,所以他在《曲笔》篇中痛斥 了那些丑态百出的史学家。他认为:“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其有舞词 弄礼,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裴子野)、休文(沈约),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之同疾也。”而且更甚者,“亦 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之仇。若王沈《 魏录》,滥术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这些都鲜明地表达了 反对“曲笔”和写史应“彰善瘅恶”的主张。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 作史确实投下了严重的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 “曲笔”终究掩盖不了“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 史家直书,不绝若线,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传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 作瓦砾长存”这恰是中国古代史传的魅力所在。
独断:史家研究撰述不受羁绊的主体意识
刘知几在《史通·辨识》篇中提到了“独断”的观点。他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 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 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 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 得失者哉!”
“独”当指史家主体,而“断”则是对史家的史料收集、拣择、分析、研究、评断全 过程的精炼概括。故“独断”可视为史家主体独立地、不受外界约束与羁绊地进行史学 研究和撰述的一种形式,而官修史学是一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较有组织的史学研究和撰 述的形式。刘知几提出“独断”说,是在分析史馆修史的弊病,针对当时史馆有名无实 之情状提出的。刘知几对官修史书情况之指责,主要集中在《史通·忤时》篇。他认为 当时馆修史的弊病实多,于是条分缕析,概括提出五不可理论,第一是当时的史馆,滥 引非材,人浮于事。第二,不可指的是缺乏必要的史料供应。第三,保密问题。当时史 馆保密不严,导致权贵干涉撰述。第四,指归问题。第五,监修铨配不明。
“独断”说即是站在地主阶级的所谓“公正”立场上,不能“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 理”。《史通》认为以前史籍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 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这是不正确的态度,而正确的史学批评是当如“明镜 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 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掇其应也。史官执简宜类于斯。”他认为史官应当仗气直书 ,不避强暴,无所阿容,这样才会被后人称颂。而谄媚以偷荣,曲笔为尊者讳的史家, 则为后人所不齿。一言以蔽之,封建史家所修的史书应当首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标准,即符合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理”与“本”。
刘知几提出“独断”之说,并无否定史馆修史形式之意,况且刘知几于《史通》中还 写了《史官建置》专篇,详细叙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情况,并认为“有国有家者,其可缺 之哉!”他只是针对当时已出现的问题,加以纠弊补偏而已。他认为这些弊病必须纠正 、及早改革,否则只会极大压抑史家个人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史馆修史的优势的发挥 。于是,刘知几以其敏锐的眼光、自觉的意识对当时史传进行深刻反省,痛说病处。
刘氏的“独断”之说是我国传统独断思想的重要一环,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 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独断”思想的萌芽早已有之。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通过记载齐桓、晋文争霸 之事,体现自己的治史观点与目的。司马迁也曾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的远大志向,将史传作为建立个人学说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来说,孔子的“ 窃取”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实际就是一种“独断”,但仅为零星言论。到唐代, 设馆修史诸多弊病逐渐暴露,刘知几遂大倡其“独断”之说,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理论。至清代,章学诚受刘氏启发,故有“独断于一心”的论述。 他认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可见,“独断”思想是在我国古代 史传文学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对我国史传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刘知几的“独断”之说开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探讨之先河,刘知几“独断”之 说首次对史家主体建设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以较为明确的自觉意识进行详尽 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家主体修养理论的坚实基础,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
“独断”不但是一个著史的方法论问题,从创作主题的角度来说,它反映人们对历史 著作创作主体素质的要求,显示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古 代历来重视史家主体素质的强化。上古时期的史官,职位虽然不高但都是学识渊博的知 识分子。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一个好的史官,不但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 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 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在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史传作者的素养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他在回答郑惟 忠所问为何“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指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因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学、识也。夫有学而无才 ,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置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尤 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楠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 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刘知几认为,只有才、学、识三者兼 优的人才可以担任史传创作,而从古以来,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在传记文学理论上, 像刘知几这样明确地提出了对史传作者素养的要求的,还是第一次。到了清代,章学诚 在继承发展刘知几“史家三长”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说”,弥补了刘知几之论 的不足。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德、才、学、识的人,才能称得上良史。
从刘知几与郑惟忠的对话及《史通》全书中,可以发现,刘知几讲的“才”,主要指 对“史体”的精熟理解,全面掌握,敏锐感觉;“学”主要指有关“史实”的丰富知识 ,渊博学问,也包括过硬的文字表现功夫。所以说,有学无才,只有后者,没有前者, 就像愚笨的商人,手里有钱,买不到货物一样。不懂得“史体”特点,不具备这方面的 能力,“史实”掌握再多再熟,文字表现能力再强,也写不出符合“史体”的文章。反 之,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像灵巧的工匠没有木料工具,建不成房屋一样。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史体”再精明熟练了,“史料”不足,表现功夫不够,也是照样作不成史 的。
至于“识”,不仅包含一般所说的才识、学识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指的正直之德, 铨综之识,即“善恶必书”的品德和胆识,以及对于“史实”的分析综合能力,鉴别能 力。这是最重要的。“物有恒准,无鉴无定识”,“识有通塞,神有晦明”历史事实是 客观存在,而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则有毁誉不同,爱憎各异,这主要是“识”的高下决定 的。他例举《春秋》三传中,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但长期以来,竟不列与学官。《史 记》、《汉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然大抵同风,可为连类”,但自张辅劣固优迁 ,班书“巧心”反为“拙目”所嗤,就是受到鉴识不明之人的嗤笑。一些缺少文史有别 的史识,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尺度来衡量史书,致使有些优秀史籍长期淹没。 于是刘知几反复慨叹“识宝者稀,知音盖寡”,“时无识宝,世缺知音”。其中不无身 世之感,从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出“识”的重要。而“善恶必书”的品德胆识,就更不是 任何从事治史工作的人都能做到的了。
刘知几在《核才》篇中还详细分析了文士不宜修史的原因,一是不“达于史体”,二 是“多无铨综之识。”如蔡邕、谢灵运等著名文士,即是这样,作文行,作史则多不合 要求。这并不是说史家高于文士,只是文与史特点不同,对作者所要求具备的特长也不 相同,所以“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各有千秋。当然 ,也不能因此就说任何人都不能兼具文史之才,如班固、沈约就兼长文史,但这种人毕 竟太少了。
一个传记作家,必须具有才学,即广博的知识,但如果“学穷千载”而无识见,不过 是“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因此,“识”应在才学之上。有了“识”,才能“探 赜索隐”,“辨其利害,明其善恶”能在“征求异说,采撰群言”的基础上进行“善择 ”。那些华而不实,乃至互相矛盾之作,就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所致。 批评家也是如此,如无见识,就会“妄生穿凿,轻究本源”,难以对作品进行全面而深 入的理解。
收稿日期:2002-05-20
